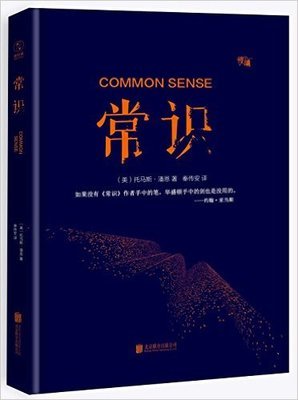
《潘恩选集》是一本由托马斯·潘恩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32图书,本书定价:19.20,页数:51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潘恩选集》精选点评:
●所谓常识、天赋永远是相对的,但却是有效的。只有有限的才能是真的
●“世界形势在不断改变,人们的看法也在改变;政府是在为活人而不是为死人服务的,所以,只有活人才对它有权。在一个时代被认为正当和合宜的,在另一个时代可能被认为不正当和不适宜”,“一切世袭制政府按其本质来说都是暴政”,“要控制大自然对智能的分配是不可能的,大自然随心所欲地赋予人以智能”,上帝(我认为就是我们口中的老天爷)是存在且唯一的,但是《圣经》是伪造的;
●如果国家是属于活在当下的人的,为什么人们要受到“制宪先贤的智慧”约束?保守主义者可以提供诉诸传统以外的合理理由吗?
●大白话。论述独立的费用很独特,北美的柏油、木材、铁、绳索的生产能力,造船和养船的费用,独立后土地的收入,军事人才的剩余。旧世界遍地盛行着压迫,自由到处遭到驱逐。及时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
●潘恩对于法律还算精通,人权与宪政的理论是他的专长,可是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和自然科学以及神学,就是各种肤浅幼稚,居然连语言学也一起连带抨击。争论小册子的局限在于:针对性、时代性、煽动性,不过偶有闪光之处就足以流传千古。
●真叫一个骂死王朗狗血淋头哈哈哈。
●拨开迷雾。
●读《常识》并综述,翻译赞
●我能说这是人类政治史上最激进的一本书嘛。。。
●两个世界的英雄,除了拉法耶特,他潘恩也当得起这个称呼。
《潘恩选集》读后感(一):“常识先生”
潘恩的文笔确实朴实而出彩,文章读起来非常流畅,看他骂人也相当过瘾。《常识》的内容放到现在看也还是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与煽动性,《林中居民》明晰了一些观点性问题同时让我们看到“常识先生”的骂人功底,《理性时代》作为对宗教的反思批判与自然神论的宣张在论证上其实还是缺少证据,对于《圣经》的批判难以称之为全面彻底,但好歹意思传达到了,作为“绝笔之作”也相当富有感情。(《人权论》打算放到读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再品味一下) 从邢程吉的文章里了解到了很多不清楚的潘恩的故事,对潘恩的态度也从刚开始的“革命使者”发展为“英美关系搅屎棍”再到现在认为是“具有悲情色彩的世界主义理想家”。在那个时代有很多潘恩这样的或是出众或是被埋没的理想主义者,也有很多被主流观点所忽视的观点态度(此处应@约翰•迪金森先生)。历史的宏观故事应该被铭记,在这之中细小的声音也不应该被埋没。
《潘恩选集》读后感(二):历史让一个小人物占据了一个显眼的位置
潘恩屡次失业,婚姻不幸,对英国政府不满,在英法及北美三地煽动革命,他的思想主要以启蒙思想反对世袭君主制、反对渐进改革支持革命、反对宗教、反对私有制。(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议会高于王权,潘恩的批判有很多漏洞)。他没有从政经验,读书不多(杰弗逊说他想的比读的多),只是个空想主义者,传播革命的激进分子,他的思想与同时代的人相比并无高明之处。此人善于批判,不善建设,拙于谋身。
他的革命理论在被美国利用后又被抛弃。革命的理论在革命成功后就没有用了。其实潘恩不满的不是君主制或是渐进改革,他不满的是现实中个人的命运。历史让一个小人物占据了一个显眼的位置。
这种危险分子,英国政府应该早一些扼杀于萌芽之中。
此人晚景凄凉,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失去祖国的下场。
《潘恩选集》读后感(三):泛论政权的起源和目的
人们一般认为现今世界上的那一群国王都有光荣的来历:而最可能的实际情况是,如果我们能够扯掉古代隐蔽的掩盖,追溯到他们发迹的根源,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始祖只不过是某一伙不逞之徒中的作恶多端的魁首罢了,他那残忍的行径或出名的阴险手段为他赢得了盗匪头领的称号:由于势力的增加和掠夺范围的扩大,他吓倒了手无寸铁的善良人民,逼得他们时常贡献财物来换取他们的安全。可是那些推选他的人决不会想到要把世袭权给他的后裔,因为他们这样的永远放弃自己的权利,是与他们声言在生活上所要遵循的不受拘束的自由原则相抵触的。因此,君主政体初期的世袭,只能作为临时的或补充的办法,而不能作为理所当然的制度来推行:可是,由于那个时代几乎没有留下或根本没有留下记录,口头相传的历史充满着虚构的故事,因此隔了几代之后,就很容易捏造一套当时可以顺利地散布的、像关于异教始祖的传说般的、迷信的鬼话,三番四复地向民众宣传世袭权的概念。也许,在首领逝世而要推选一个新的首领时,骚乱的局面(因为歹徒中间的选举是不会很有秩序的)使许多人感到惊恐或似乎感到惊恐,诱导他们最初赞成世袭的主张;因此,正如此后所发生的那样,最初认为是一时的变通办法,在以后却硬说是一种权利了。
...........
《潘恩选集》读后感(四):常识与理性
在思想史上归为启蒙思想家的潘恩的《常识》早有耳闻。 9月22日在***主席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出席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的演讲中提到这本书,一下子又使潘恩热了起来。作为两个世界的英雄的潘恩,穿行于作为新世界的美国和作为旧世界的欧洲,他的小册子传播的启蒙思想,深深改变了新旧两个世界。但是潘恩讲了些什么?启蒙思想?社会契约?天赋人权? 《潘恩选集》包括四本小册子:《常识》《林中居民的信札》《人权论》《理性时代》。其中最为广泛流传的是《常识》和《人权论》,成为公民社会理论和国家学说以及人权研究的必读经典。《林中居民的信札 》则是紧接《常识》回复论战的对手“加图”的小册子,”加图“就是伯克的笔名。作为保守主义之父的伯克,他的代表著作 《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 一定要找来对照着对一下。 引起我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言论自由与新闻传播的关系。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以新闻报纸和小册子为载体的各种论战,一方面为革命做了理论宣传,奠定了革命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客观促进了美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殖民地大大小小的通讯社,成为思想和舆论的汇集地。大大小小的报纸和各派别的小册子,硝烟味十足。在有形的战争开始之前,无形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几十年。正如迈克尔·埃默里在《美国新闻史》中所说的“谁能过高估计语言在激发人们斗志方面的巨大力量呢?从古至今,语言使武力倍增,从而使一些本无取胜希望的战争或战役取得了胜利,这样的事迹比比皆是。报纸是靠争论而兴旺发达的。 ”用自由的论战来争取更多的自由,而争取的自由更加保障言论自由,“只要它能够自由参加讨论,哪怕自由程度不大。报业在18世纪上半叶之所以有重大发展,正是由于它战胜了限制那种自由的势力。”可见新闻传播史就是思想自由斗争史。 引起我注意的第二点是北美殖民地的精英们,在踌躇满志地构想他们的共和国时,总以罗马共和国的诸位先驱为榜样。这一点从他们笔名上就可以窥见一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三人为争取美国新宪法草案获得批准而在纽约报刊上撰文的共同笔名“普布利乌斯”就是一位挽救了共和国的高尚优秀的英雄,是共和制的坚定信仰者。l罗马人愉快地服从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治理。人们称呼他为“普布利科拉”,意即“人民敬爱的人“。汉密尔顿等人以此为笔名撰写后来编为《联邦党人文集》的一系列论战文章时,想必是以这位维护共和制的历史人物自居。而潘恩的对手伯克这位以“加图”自居的人,也是希望能够以死捍卫共和。但是历史上“加图”下场并不好。保护共和,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口号。但是什么是共和?须知今天的共和已经不可能是古希腊罗马意义上的共和国了。共和除了不搞君主制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其它内涵。当今世界有众多名为共和国的国家,但是很多是徒有共和之名,而没有共和的精神实质。也有学者主张复兴共和,也有一些对共和的精神的探讨,我认为这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始终要记住,不可能复兴古罗马的共和。在公元前1世纪,从共和制走向帝制是地中海世界的大趋势;而在两百多年以来的东西方,从帝制走向共和则是新的历史大趋势。这个新的共和必然要有新的时代内涵。 《理性时代》是我所认为最差的一本。晚年的潘恩开始批判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在这本书的上下两部分中,他不厌其烦地逐篇批判了《旧约》和《新约》的虚假性。从年代学家的角度对二者的成书年代以及冒名作者还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做了一番审查。可是,我认为潘恩这么做只是在做一件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18世纪末,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经过伊拉斯谟和伏尔泰为代表的反教会神学思想家的口诛笔伐,社会精英分子对于教会的虚假性的有了普遍的认识。另外,潘恩对宗教的本质的认识也并没有超出他的时代,并未如马克思或者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那样深刻。潘恩只是反对教会专制,反对那些贪婪的教士以教会名义敛财、占据高位,反对宗教裁判,反对宗教战争。除此之外,他所谓的“理性时代”,我并未看见有什么可以称之为理性时代的东西。须知,理性时代,必须是唯物主义的世界,必须是“上帝死了”的时代。 当然,这两个册子的不如人意,并未掩盖《常识》和《人权论》的光芒。其中大段大段的精彩论述,尺度之大,即使放在今天的微博上,也是绝对引发疯狂转载的,就思想深度来说,潘恩绝对是当时一流的思想家。语言平白易懂却令人深省,这是当时最好的论战册子的文风,就文笔来说,潘恩是最优秀的争论家之一。深刻的思想和浅显的文字,以及革命的时机,这三者促使了潘恩的小册子的广泛流传。但是,争论小册子的局限在于:针对性、时代性、煽动性。不过,对于各种疲于应付论战,奔波跋涉中的急就章来说,偶有闪光之处就足以流传千古了。宣传常识和理性的小册子,偶尔也有偏离常识和理性的时候。 最后,再说说我对潘恩的几点不满。潘恩对于法律还算精通,人权与宪政的理论是他的专长,可是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和自然科学以及神学,就完全局限在他所处的时代的水平。作为一个思想家,认为古典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是死的语言,“废除死的语言的研究,而象最初一样,致力于科学知识的学习,对于学习是有利的 ”,这点我实在无法理解。这简直就是违背常识和理性的。作为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杰斐逊对古代语言的看法则要客观的多,恰恰是因为杰斐逊是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精通语言学,研究语言学做了大量的笔记,日后成立的弗吉尼亚大学也非常重视对古代语言的研究。语言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恰恰可以从已经死了的语言中挖掘出古代的重要信息来,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阿拉伯的发现和传回意大利,比如国法大全在13世纪的发现和研究。作为重视语言和习俗的典范的历史法学派的奠基人萨维尼,通过对古代罗马法的研究构建了现代民法体系。同样对于宪法和政治语言的研究也是一样的。《尚书》中的表达方式可能还影响着今天的公文书写作和政府思维。也许潘恩的这句话只是反对学死语言耗费了学习新的科学知识的时间。但是,恰当的理性正需要重视历史经验。如果是理性扼杀经验,那和经验扼杀理性一样,都只会制造灾难。
《潘恩选集》读后感(五):一些琐碎
神性的共和
当潘恩决定要对抗英国政权,并坚定北美独立信念的时候,他需要做两件事:一是指出另一条至少是行得通,或甚至能被人相信是更为美好的出路;二是阐明为什么原来的路行不通。毫无疑问,从写作策略层面来看,这两件事他都做了—并且从民众反应来看,文章的效果非常棒。
当他首先提出共和制度的时候,他的论证还是基于一般的人类发展的科学规律:首先说明政府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职能与作用,然后说明共和制能够胜任这样的任务,这一环的论证就基本完成了。
所以他首先从一般的角度推演出了政府应该达成的目标:社会是欲望的产物,政府是控制邪恶的产物。当人们想要普遍地遏制人性中的恶时,政府便应运而生。在他看来,政府的本质是为了控制人们德行中的软弱无力而必须采取的治理世界的方式。所以政府的出现的目的和意图,本质上还是为了社会的自由与安全。
然后他又从社会普遍发展的角度简单论述了共和制的优越之处,最终得到的结论是:「因为这一种不时的互换会同社会的每一部分建立共同的厉害关系,各部分就会自然地互相支援,正是基于这一点,才产生政府的力量和被统治者的幸福」。前面的论证十分粗糙,但是面对这样符合人的价值理性又诱惑力十足的结果,大众的情绪自然高涨。
说实话,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大体上还不能察觉这是一篇「交给 公众」「煽动情绪」的文章。但是当作者开始批判现有制度的时候,我便对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有了深入骨髓的了解…
他批判的基本思路是:因为英国不好,所以与英国相关联的制度和政策就不好,所以和英国和解的策略也不好。所以整个批判的基点建立在「批判英国」这个看似没什么关系的命题上。
从批判的策略层面分析,作者从宗教入手来批判一个政权体制的合理性,从理性角度来看,这样的批判在说理方面缺乏逻辑性;但是从煽动情绪的角度而言,直接从信仰层面否定英国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和英国统治的劣根性绝对是无比高明的方法。
当我看到作者批判世袭制度时,脑子里立马浮现余秋雨先生在解释大禹选择世袭时说道:「高明的大禹必然能够预见,自己必然有昏庸无能的后代给这个国度带来灾难,但是世袭是在那个远古时代,为了避免因权力争夺而引起的无限战争所做出的无奈选择」。我很能够接受「世袭不再符合当下的社会模式」这样简单粗暴的答案,但是作者却非要把它解释成一种「欺骗」…初读只觉得莫名其妙,但结合时代背景和写作目的之后,便茅塞顿开了。
作者最终还是要为共和制加上佐料,辅以腌制,以便于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最大的影响。已经记不住是在哪一个部分了,作者说过这样类似的话,大意是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神,共和是耶和华支持的选择云云。我总以为,一种制度被大众接受只能是因为它本身的高超和科学;而不应该是因为宣传者尽其所能迎合大众的喜好。那是文化上的蔑视和钝化,是一种深层的卑劣行径。但现实和历史却常常告诉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我始终认为我们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生活应该是一种大众可以理解的生活,否则民主、理性等等,都只是假象。虽然我理解作者,但我还是觉得,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为自己的生活或是方向赋予神性;《圣经》和耶和华没有这样的能力。
冲破牢笼
抛开一种审判的视角和前提,我问自己,如果我前文所述的那些所谓的「策略」「写作目的」只是我自己臆想出来的,如果作者真的认为宗教的东西可以为政体赋予正当性,又应当如何看待这篇文章呢?
我突然发现自己每次看书,每次思考,尤其是批判的时候总是开上帝视角……是的,以现在的基本认知来看某些过去的观点和论证确实毫无逻辑可言,但它们也绝对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虽然我不一定能够察觉)。
我忍不住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冲破时代牢笼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是觉得,从结果来看,秉持着真正先进的理念推动时代前进与仅仅凭借对现实的不满莽撞地前进这两者间的区别不大。甚至真正前进之后会有更好的环境和土壤来培养真正先进的理性。很多思想的出现本身就是鲁莽的产物,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从前总是觉得要先有一种超越时代的理性出现,才有打破牢笼的可能。【可能是历史学得不够好的原因???】但或许现实情况下,先不分青红皂白从表层打破僵局,而后发展跨时代的思想理念这样的模式更为常见,可行性也更高。可是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没有一种确切的思想引领,这一种「不分青红皂白」只能是鲁莽的尝试,一旦出错,后果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理论层面的失败,而是真实的人类灾难。试错的成本太高,难以践行。
我还是从这篇文章里得到一些启示:即便它满口的胡话,它还是有天赋人权的影子,有最基本的人性光辉。或许在宏观的角度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理念先行或说是绝对的莽撞先行,所有试图冲破限制的行动都是试探着的,小心翼翼的,既有野蛮的表征但也散发着一些真理的光芒。所以我决定不再那么苛刻,也不再那么自卑。不论是个人,还是人类,都大步向前吧!其他的事情都交给命运吧。所谓「打破了时代的牢笼」云云都是后人的评价了,身处于时代之中,既要有追求理性的信念,也要有及时救场的勇气。
伪装
读完常识全文,我脑子里浮现起前一段时间因为一个官方宣传爆发的公众情绪。
支援疫情的时候,官方媒体刻意把剃了光头的女性医护人员拿出来宣传,在微博上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当看到大众对于这样政治正确但是不太人性化的行为反感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开心的,这意味着民众素质的提升,意味着国家层面没必要靠卖情怀博大众欢心,意味着潘恩这样的写作策略和说理方法在现在的中国或许已经失去效力了。
再结合之前为了维稳的疫情谎报与瞒报,以及阿中哥哥等等一系列的文化符号,我突然发现政府层面一些令人苦笑不得的行为的背后,很可能是对公民素质的怀疑。怀疑公众能否处理直接粗暴的信息,怀疑大家能否再一些关键问题的抉择上及时选择对的方向,然而疫情以来无数对政府不满的情绪已经回答了这一疑问,不要再把公众当傻子了吧。想起徐贲先生在《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里对公众的定义:公众不是简单的个体相加,而是由对特定事件的关注集合到一起的集体不断重叠的结果。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社会有愚昧的人,有封建的力量;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学者、青年和独特的经历与知识。
我觉得是时候让政府在某些层面脱下从前不得已的伪装,与大众坦诚相待了。阿中哥哥、光头医生,这些作为政府伪装的宣传符号或许在几十年前很少会遭到质疑,但是在今天,很多人会反感,会抵触。我其实真的蛮开心这样真实的大众情绪及时的出现,或许真的能给我们的政府在某方面敲响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