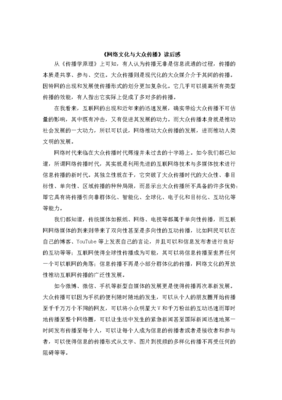
《媒介事件/传播学名著译丛》是一本由丹尼尔.戴扬 / 伊莱休·卡茨著作,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页数:310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媒介事件/传播学名著译丛》精选点评:
●也是新闻传播理论导读的必读书……翻译奇差
●写的还是比较系统的,但是有些地方有点牵强,过于强调仪式和象征。不过用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解释媒介事件,这点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Katz老爷爷又让我膜拜了:绝对是对电视的深描,把能说的特点都说了还特别准确。当然为什么特点如此凌乱没有条理,这就是方法论本身的问题了。
●为了期末......
●很经典~不多说。
●影视社会,学新闻的必看,下学期又上他的课。大爱sl。
●木有读懂。
●翻译实在是...
●阿弥陀佛
●写的太好了,本来想着卡茨作为拉扎斯菲尔德的学生,肯定还是老生常谈的效果论那一套,看完后才发现把说服、批判、满足和技术四种理论全都纳为己用,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去重新审视媒介事件,深描组织者、媒介和观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直线性,而是系统的和循环的。
《媒介事件/传播学名著译丛》读后感(一):零零碎碎,再改
我其实不太懂这本书的精妙之处何在,就是对电视媒介内容的文本分析,就当我没有看懂这本书吧。很可惜这学期没有看到老师对这本书的分析,虽然看了一些针对此书的论文,其中不乏专业大佬,但是终究还是觉得差了点什么,希望之后有机会看到社会学领域的大佬系统的剖析一下这本书吧。
这本书说是从仪式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媒介事件,可是通篇下来,我还是不太懂什么是媒介人类学。作者本身就已经预设了这些事件是仪式,不是新闻,也划分了仪式和新闻之间的区别,仪式事件和新闻的相互作用也在转化型媒介事件的论述中略有涉及。媒介在面对这些事件时多与政府等事件组织者站在同一立场上,其一直标榜的客观在媒介事件中不复存在。这种媒介态度的转变在中国也并没有太多明显,我们平时就没有标榜自己是独立客观的,只不过在媒介事件中,这种态度倾向被放大了而已。
从单纯的事件来看,就像作者开头直面的质疑:没有媒介,这些事件照常会发生。所以媒介在事件的发展中有无作用,若是有,又是什么样的作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或许可以通过比较电视媒介产生之前的重大仪式性事件与电视媒介产生之后的仪式性事件来回答,更加科学的话或许可以比较广播报纸时代的媒介事件与电视媒介事件。但是我在书中似乎没有看到系统的比较,但是在书中零零散散地记录着电视媒介产生之前人类的仪式行为。
看这本书最好还是跳出传播学和媒介的角度来看吧,或许会有新的收获,读完整本书就有种思维局限在本专业的感觉,我还是摆脱不了从媒介的角度看世界,这不好,越学越死了。
《媒介事件/传播学名著译丛》读后感(二):《媒介事件》读后小结
全书以几个典型的媒介事件为例——如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婚礼、肯尼迪的葬礼,阐释了这三类媒介事件在传播学、社会学、符号学、人类文化学等方面的意义,将媒介事件分为三种叙述方式:竞赛、加冕和征服,以及媒介事件得以实现时的组织者、电视台、受众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同时充分说明了媒介事件获得成功的动力和压力,它所产生的多方面的社会效果。
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只是对文中内容进行了总结,上课老师让我们讨论时才意识到,我没有继续思考,如何用这个理论解释中国的媒介事件?这个理论如何在之后的研究中运用?
老师提到《景观社会》和《议程设置》,不同的理论看人文社会会通过不同的视角,用“媒介事件”也好,用“议程设置”也好,只是视角不同而没有对错之分。与《景观社会》相比,媒介事件是一个中立观点的理论,没有涉及阶级层面。
戴扬和卡茨的媒介事件写于20世纪90年代,与现在的媒介事件相比有不同之处,原因在于,卡茨的媒介事件的媒介是电视,电视与网络相比,电视是家庭层面的,网络则是更加私人化,因此电视的加冕效果大于网络的加冕效果。
另外需要区分新闻事件和媒介事件,书里举了一个例子:肯尼迪遇刺是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肯尼迪的葬礼是一个重大仪式事件,崇尚秩序及其恢复,提前策划。
这本书里用到符号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所以读起来有些不好读,但作为一本传播学的经典著作,读完之后有很大的收获。
《媒介事件/传播学名著译丛》读后感(三):何谓“媒介事件”
戴扬在第一章“媒介事件的界说: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对什么是媒介事件做了定义:(1)从最宽泛的定义上说,媒介事件是那些能让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划时代的政治和体育竞赛;表现表现超凡魅力的政治使命;以及大人物们所经历的过度仪式。(2)从媒介事件的性质——即仪式性来说,可以将媒介事件成为“电视仪式”或“节日电视”甚至“文化表演”。这种媒介事件有着浓厚的利益、敬畏的气氛,让观众为了激动,令他们神往。
(3)戴扬将媒介事件视为特殊的电视事件。这主要体现在:1,媒介事件事实上是对惯常的干扰,干扰着正常播出乃至生活的流动,且这种干扰具有垄断性(所有的频道都把平时计划好的节目撤掉,以满足重大事件的播出)2,媒介事件是现场与远地点的结合,在这里电视台只承担中介的角色,将现场发生的事情和离我们很远,我们无法亲身参与、感受的地点连接起来呈现在我们面前。戴扬称之为“技术上和仪式上”的胜利。3,媒介事件都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所以它不认为重大的新闻事件是媒介事件,因为它没有提前策划。
我认为应该适当的更新戴扬对新闻事件与媒介事件异同划分的思路。
戴扬除了认为二者的区别是媒介事件是提前策划外,在第四章“媒介事件的表演”中多次论及二者之间的差异:(1)认为媒介事件具有一种“使徒”的角色特点,其目标就是促成事件的存在,并且在其具有感召力的宣传下,倾向于观众按符合事件发展目标的方向,也就是说媒介事件是推动事情向它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在此,媒介事件是与新闻所强调的客观性、中立性相对的。(2)从文本上说,新闻事件采取一种第三人称的表述行为,对事件采取客观、无意识报道,这种报道讲求描述的条理性,例如新闻联播。所有的几日大使必须在规定的事件、贵点的语速和画面播放完,不可多一字,也不可少一字,换言之,这些事件都被程序式的放入连手续的镜头中,观众被排斥在外,而媒介事件,采用的是一种电影化的叙事,尤其考虑事件与空间的配合、协调,所呈现处的事件也像是电影式的讲故事,它强调播出的条理化秩序,更能将关中带入事件中。
“现场的观众被安排在规定的位置,这一位置能说明导演选择的镜头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注意。所以,现场观众代表事件的主体宣讲人,这样家庭观念就可以像看故事片那样观看大众事件。”(P30)
到此,我认为现在的新闻事件与媒介事件融合已经是大势所趋。
(1)更多的新闻事件不是提前策划的,但却更有媒介事件的特征。
例如,许多突发的事件像汶川地震,显然不可能有什么提前策划,但许多电视台的具体播放、形式、演出却更多的有媒介事件的特点,比如让经历地震现场的人描述当时的场景,将一线官兵救人的场面通过剪辑不断重复播放,对受灾百姓哭泣的特写,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拍摄救灾的各方队伍,对敬礼娃娃的故事讲述等等。
(2)新闻事件能够干扰其他事件,并具有垄断性。
汶川地震的出现,迅速成为各大电视台争相报道的事件,其他计划播出的节目全部停止。
(3)新闻事件也带有某种仪式性。
例如各大网站在地震事件中所使用的黑白标题、主持人播报时的沉重语气。
(4)新闻事件也可以是电影化的叙事。
所以我认为戴扬对两种事件的划分有改进的地方。
《媒介事件/传播学名著译丛》读后感(四):愿你也能在媒介事件中见证自己的历史
1969年全球有近2亿人同时目睹了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的壮举;1981年英国皇室为查尔斯与黛安娜举办的婚礼在79个国家现场直播,观看人数超过5亿;1999年岁末,全球几十家电视台联合现场转播了24个时区中,十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相继跨入千禧之年的盛况,更是吸引了几十亿人的目光。电视媒介,如今看来几乎快要沦为家具装饰品的通信工具,却在20世纪下半叶大放异彩。与印刷媒介不同的是,电视媒介不仅跨越了人们在空间传播的距离,而且缩短了信息传播在时间上的延缓。这些传播潜力尤其在特殊的电视节目——“媒介事件”中得到解放,它进一步区分了直播之于录播的差别,就像假日之于平日一样,媒介事件的直播似乎具有某种魔力可以让人们一起屏息以待,以至于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往结构。
当然,与如今的直播不同,彼时的电视直播的“媒介事件”仅限于关乎全体社会人员的重大事件,它由事件组织者(主演)策划“脚本”和定义,并与电视台(媒介)进一步协商,以提前告知并邀请受众(广发电视观众)参与事件的方式,再进行三方对事件的签署协商。其中,电视安排“媒介事件”的播出是排他性、垄断性的,它可以直接撤换日常的节目播出,并经过事先的精心安排使得事件能够在类似节日或仪式的氛围里完成,以期能够完成组织者原定给事件的定义。当然,观众也并非是完全被动的情况,一方面,他们受邀请参与“媒介事件”中,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受到种种因素而对于事件有不同的解读。在看似如此繁琐的形成机制中,“媒介事件”却愈加顺其自然地为协作各方所接受,使之甚至成为分裂、整合乃至设计社会结构的渠道。
春晚、奥运会、国庆阅兵等,电视直播曾经带给无数观众激动人心的时刻,它使得人们自觉地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它将装有电视的起居室变成了“无拘无束”的大众空间,它还让“不在场”的观众得以获得类似无差别 “在场”的体验,人们史无前例地共同见证了历史。然而,正如戴扬和卡茨在书中所提出的,“媒介事件”的直播重新定义了组织者、中介人、电视台以及观众的相对权力,并且重新定义了大众事件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媒介事件就像是个各方权力的博弈场,各方进入协商过程的法则,都是基于控制事件的定义及其品质,并取得与之协作的最大收益的愿望,最终组织者、电视台和观众,在协议过程中总是有得有失的。
以古鉴今,网络直播的“媒介事件”也在暗涌中,或许与戴扬和卡茨所提出的概念有所不同,但从他们对以电视为载体的“媒介事件”的描述,似乎可以看到以网络为载体的“媒介事件”也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如此举一反三,电视时代的直播节目,似乎就像网络时代的网红热点,它们同样具有汇聚众注意力的潜力,它们同样能让大众共同见证历史,它们还同样可以改变人们的社会结构。不同的是,它们不止有“竞赛”、“征服”和“加冕”的脚本,也不止有组织者、媒介和受众的协议人:各大仪式晚会的直播、各种社会事件的特别报道,甚至是平民百姓的居家小事都可以通过网络的赋权而创造出让全社会共鸣的“媒介事件”;这些“媒介事件”背后还会有更多参与协议的各方,政府的政治权力、企业的经济利益、公民的文化参与,处于各种目的的各方似乎都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赛博空间,邀请他们的观众来积极参与他们的“媒介事件”。也许,这也是“媒介事件”的另一个定义——特别创造出来以供媒介报道的事件——所衍生出来的原因之一。
相比于电视,网络似乎可以天天播出足以让“常规节目”撤掉的“特殊节目”,当假日如平日一样出现,或许人们便不再如往常般期待,又或许人们会乐于沉溺于每日的“狂欢时段”,但此时的“媒介事件”必然不会有以往如此大的号召力,它可能会保留一些助力于统合社会或者改革社会的功能,只是分众化的受众很难因此而刻骨铭心,取而代之的或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又或是西西弗斯式的小抱怨。可以预见的是,汇聚在客厅里的“媒介事件”正在转移到分散在卧室里的“网络热点”,我们依然目睹着新型的“媒介事件”的到来,我们还期望着大家仍然可以共同见证历史,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更加希望能在“媒介事件”中见证自己的历史。
愿你也能在媒介事件中见证自己的历史。 http://t.cn/A6yU6Odc
《媒介事件/传播学名著译丛》读后感(五):《媒介事件》读书报告
《媒介事件》研究的对象是“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并且对中国观众来说异常熟悉,香港回归、国庆阅兵、奥运比赛、神六发射的各种直播……“媒介事件与其他电视播出方式或样式之间的最明显的区别是媒介事件具有非常规性。事实上,它们是对惯常的干扰,干扰着正常播出乃至生活的流动。电视事件向观众提供例外的事情去思考、去见证乃至去完成。”
从观众角度来看,作者说道“观众把它们看作一种邀请,停止日常惯例来参加一项节日体验”。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验,比如全家人聚在一起,一边吃零食一边看直播并谈论。电视给予观众“在场”的感觉,模拟仪式参与。尽管普通人没有能力进入现场,但电视对进入事件的渠道进行平等化。而观众被拖入事件的象征意义,甚至超过现场观众,就像我们平时会说“现场的人还没有我们看得清楚”。“看得清楚”一方面是指电视观众不像现场观众那样受某一固定角度的观看局限,他们能够随着镜头“移步换景”了解事件全貌;另一方面,因为电视突出组织者的定义并增加了解释,观众得以更好地掌握事件的重点和意义。
从整体来看,协商媒介事件生产的三方相互配合,强化了整合、秩序和共同体验。就如作者所分析的——
“典型的事件组织者是媒介与之合作的公共机构,它们是社会核心中的部分,在统治集团中有地位,代表舆论一致的价值,具有博得我们注意的权威。”(组织者)
“电视很少闯入媒介事件本身,它维护组织者对事件的定义,解释事件的象征意义,只有很偶然的分析干预并且基本不带批评色彩。”(媒介)
“这些事件的发生是在崇敬和礼仪的气氛中完成的,主持人也拿出尊敬甚至敬畏的态度。这种播出把我们带到了社会的神圣核心的某个方面。”(媒介)
“仪式的本质属性喻示一种反应的存在,电视突出这种反应,首先突出现场观众的反应,强调体验的大众性,强调观众对事件颂扬的价值和象征性的一致拥护。”(媒介,受众)
“这些仪式使极其庞大的观众群体为之激动,促使观众聚集在电视机前进行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庆典。在庆典过程中,观众常常被赋予一种积极的角色。这些事件以集体的心声凝聚着社会,唤起人们对社会及其合法权威的忠诚。”(受众、效果)
虽然作者也提到如果协商的伙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就会出现媒介事件的病变,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三方能够共同协作生产媒体事件,观众通过参与这一事件产生某种集体意识——所有人都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经历了共同的历史性事件,甚至产生一种超脱于日常生活的集体感、崇高感、神圣感。因而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关于社会整合和共识的模式。
作者对这一整合和共识模式进行了后续的思考,丹尼尔•戴扬此后又提出“表达性事件”,意味着事件的表达过程中不仅有共识也有分化。另外他认为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例如博客、微博,“它们反过来跟主流媒体、有‘中央和边缘’之分的媒体、想象集体的媒体进行对话。博客作者往往打乱中央电视对集体的想象,勇于挑战官方垄断的形象。他们清楚表明大众也可以是表演者,大众也可以是自己形象的创始人。比如撒达姆之死,有官方的处决洁本,同时也有流动电话兼网络的形象幻灭版本。新公共空间的特征便是散布各式各样互相对抗的、不协调的影像。(参考文献:《“媒介事件”概念的演变》,《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