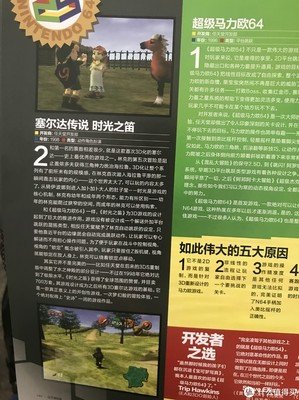
《档案中的虚构》是一本由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Natalie Zemon Davis)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2.00,页数:27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档案中的虚构》精选点评:
●和福柯的无名者对读,很有意思。
●感觉论述过于简单,想兼及历史法律文学,但每一个点都浅尝辄止。然而其视角是很有启发性的,还是很有趣的一本书!
●好琐碎啊……
●不是早有台北麦田版杨逸鸿译本吗?已经翻译得很好了,为何不引进来,还要低质量重复良莠不齐的集体劳动?这也是一种刺激经济增加个人创收的做法吗?
●我要读完戴维斯所有的书!
●戴维斯此书是探讨历史叙事与历史真实方面的经典,也是新文化史的基石类作品。不同的身份(男人、女人、教会、国王等)如何表现一个事件,既是一种社会建构,同时也是不同的语言运用的结果。
●整本書的內容好像沒有一條主線,不厭其煩的列出一個個赦罪故事,然而不知意義何在。總之是不知所云,已弃。
●翻译极烂
●三星的书,加一星给那些原始档案,套路这种事情,真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少给一颗星,翻译这个锅要背,翻译的中文也太差了吧
《档案中的虚构》读后感(一):你我都是一个故事叙述者
简单记录一些零碎的思路,短评太长了找个地方放,并不是什么严谨的书评。只是一些碎片和近况。
1.赦罪书经过多手,究竟在反映谁的心声?
2.要在感情上博取他人的同情与认同,获得赦罪,就必须讲述一个故事,故事的连贯性使它真实,情节又使它动人。
3.突出了男女性社会地位的不同,分享了体液论,男性生来热血暴躁易冲动,女性阴冷黏稠,除了为了保护婴孩和坚守信仰之外的赦罪很少被认可。
4.女性的赦罪书少于男性,她们更少被判刑,还是她们更少拥有被赦罪的机会?
5.女性杀婴被认为有罪,是出于淫荡和羞耻。与近期美国禁止堕胎对比,可以思考社会思潮。
6.女性获得赦罪之后更难回到以前的生活和恢复名誉。7.处在历史中的人们是怎么看待大历史的?有时候历史忽略了她们,有时候她们也忽略了历史。近期华为与美国的事件,读了李晓教授的文章,写得真好,我们也处在一个大历史中,我是怎么看它的呢?它又怎么看我?
8.从故事里可以读出一个社会的底色与人们的想法,但是需要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等学科作为一些基础的支撑,真的很想读人文和社科实验班233
9.今日感觉到了朋友之前说的无趣,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对着一点点的知识,我也终于有了这种感觉。在无趣的历史里局限着不能前行。但是有一些学术专著和深层次的文章让人感到满足,今天模考做到了最近看的一些书的相关史料,感觉对于它们的了解与目光和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样,这是我喜欢的一条道路。也许是胃口悄悄被调高了。
10.最近几次模考已经看得出模拟题和高考题的区别和拟合程度,算是一大进步。也许内在的转变为尽数显化,但是让人欣喜。对了两科答案,考得还可以,感到满意。
11.对于之前中山大学提出的问题:对于历史的看法,以后想要从事的学术方向。如今我深信当时我是无以回答的,就算如今有了一点点感觉,也是朦胧的一片。他为什么会这样问我呢?我,应该知道吗?
12.讲故事的人。人天生会讲故事,是吗。不识字的农民,在长辈给后辈讲述生平的时候,在酒吧茶馆里传说着的街巷传奇......历史与小说有什么明显的界限与区别?你我都可以成为,也都是故事叙述者。
13.今晚被点亮了关于经济学的兴趣。经济法律 社科。历史政治 人文。写自己的故事。
《档案中的虚构》读后感(二):《档案中的虚构》读书笔记
译序
面对历史档案,作者追求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下的真相,而是通过档案写作手法的分析,探究“虚构”背后的故事,并且特意挖掘了不同性别的声音。【作者如何辨别记录是否是虚构?难道不需要与真正的“真相”做比较?】
绪论
作者直言受到海登·怀特、罗兰·巴特等启发,对语言、语序等要素予以特别关注,把历史还原到叙事语境中。探究的问题:“16世纪的人们如何讲故事,他们心目中的好故事是怎样的,他们如何说明动机,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叙述来理解始料未及的事件,并使之与当下的经验相吻合”。【提供了一个看待档案的新角度,也启发人去辨别史料的真实性。】
【关于海登·怀特。“他对语言和修辞的关注,导致他得出结论:在构建解释时,语言和修辞会产生不可避免的选择。他的立场意味着……‘建构某种特定的阐释,并没有客观的外在标准,不比另一种阐释更准确’。而卡洛·金兹堡认为,如此激进的相对主义,不仅不能够区分真理和谬误,而且从根本上和意识上,起源于文化法西斯主义评论。”】
第一章 讲故事的时代
求赦者是第一讲述者,通常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才承担得起请求赦罪的费用,他们能够利用重构时间框架,比如嵌入特殊节日、事件以转移注意力,来激发听者的时代性情感,而一般平民百姓平时在公众场合也有听故事、讲故事的经历,会刻意淡化或突出某些情节以博得同情。法官、律师是第二讲述者,都接受过专门的教育,具备一套关于法律修辞学的知识,可以对故事进行渲染。【本章的举例有些零散,故事没有太引人入胜,分析似乎也不太得力,而且逻辑没有形成体系,无法透过案例看到16世纪的某种特点。或许可以从社会心态的角度切入,分析讲故事的两个主体心态形成的背景。】
第二章 愤怒的男性与自我防卫
【先抛开翻译的问题不谈,作者论证的逻辑本身欠清晰。首先,本章内容并没有紧紧围绕“愤怒”、“男性”、“自我防卫”展开,有所提及,但不成系统;再次,对案例的叙述让人费解,读者无法抓住重点,也难以弄清要论证的问题;最后,个人认为由于作者开头并未明确提出本章要探究的问题,所以造成行文松散,结尾也缺乏结论。】赦罪叙述并非单纯的叙述,而是带有表演性的展示,要创造某种对求赦者有利的情景,使法官认为求赦者发怒是合情合理的【理论观点比较薄弱,“什么样的情景”、“如何创造”等问题上没有深入研究。】。作者提到了一个“事实效应”,以细节积累来体现事情的真实性,这是求赦者增加说服力的手段之一。除了求赦者的官方背景可以提高成功率外,作者还观察到了国王的个人意愿以及凌驾于王权之上的上帝力量,求赦者的虔诚所引发的奇迹有助于得到赦免。16世纪,赦免背后还存在不公正的问题,甚至造就了赦罪书某种固定的习惯和风格【什么习惯、风格?如何造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没有还原到时代背景中。】。另外,作者还谈到赦罪故事作为文学素材时采用的叙述方法【什么方法?个人并没有看到语言学、文学方面的分析,也没有历史、人类学的阐释。】。
第三章 流血事件与女性的声音
这一章关注性别对赦免的影响,相比于男性,在女性求赦者的故事中,性别代替社会地位成为铺设舞台的元素。性荣誉通常是关于女性的流血事件的关键问题。
结论
作者不仅认为文学作品中的真相具有不确定性,还认为文献中的真相也不可避免这一性质。结尾句带有人文关怀的语气,对赦罪书中的历史人物予以宽容:“把恐怖的举动转变成一个故事,乃是使自己疏远这件事的一种方法,往坏处想它是自欺的一种形式,从好处想它是原谅自己的一条途径”。【行文偏通俗风格,最后也没有落到学术意义的结论上。“真相不确定性”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怀特的相对主义影响,个人不敢苟同。】
2019/05/06
《档案中的虚构》读后感(三):【平猫爪记】戴维斯:《档案中的虚构》摘记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饶佳荣、陈瑶译:《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档案中的虚构》,不是直接从档案中探究历史的“真相”。而是探讨其“虚伪”——即叙事层面,探究“虚构”的创作与手法、文学策略与依靠的假设及相关的阶层、性别等社会变量,以及这种文类兴起之政治过程(刘永华语)
戴维斯在皇家赦罪书中发现了这些文献的“文学性质”,或称“虚构性质”,即它们的作者把一个犯罪事件塑造成一则故事的程度。作者希望采取一种不同的策略,把“虚构性质”作为分析的重点。其中所谓“虚构”并非捏造,而是词根,即关注文本中语言的构成、塑造和定型的成分,关注叙述的技巧。在此,虚构的修饰并不必然使叙述变得虚假;它也可以使叙述栩栩如生,或带来道德上的真相。
作者想要探寻的是:16世纪的人们如何讲故事(尽管是在特殊的赦罪故事中),他们心目中的好故事是怎样的,他们如何说明动机,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叙述来理解始料未及的事件,并使之与当下的经验相吻合。他们的故事如何因讲述者和倾听者的不同而变化,以及这些情节规则在司法的暴力和恩典故事中是如何与同时代更广泛的解释、描述和评价惯例相纠结的。
赦罪故事基本上是关于杀人的,杀人者在自我辩护时宣称杀人是未预谋的、非蓄意的,或者根据的法律是正当的、情有可原的,以此来达到赦罪的目的。故事的叙述必须说服国王和法官,并建构一个能击败对立版本的故事,而不是使他们感到困惑。在赦罪书的创作中,至少有两位作者,通常会有更多人牵涉进来。皇家公证人及其秘书与求赦者的代理人共同拟一份草稿,然后把定稿抄录到羊皮纸上。
赦罪书是一种为了免除刑罚的自我辩护,作者想从中知道,赦罪书作者为自己设置了何种时间。为了解释事情的原委,为这种意图辩护,或使行为连贯一致,他们会借助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或超越案犯当下的生活吗?在实际操作中,历史情境没有成为一个核心的组织手段,它们要么被认为与案情无关,要么被作为无须评论的背景编入故事。这与当时用其他方式讲故事的习惯没有太大的区别。私人日记记录趣闻轶事,注明日期,但常常不寻找符合历史解释的框架。相比之下,仪式和节庆时间显得更为重要,故事讲述者利用仪式或节庆框架协助辩解和解释所发生之事。节庆引导行为,并对行为作出评判。行为则暴露出节庆的某些危险和潜在的冲突。此可谓赦罪书形成之背景。
随之,作者讨论了男性和女性在赦罪书中的叙事。赦罪书的世界是个愤怒和出人意料的世界。国王,而不是上帝,掌握着这个世界的赦罪之权。在男性叙事中,为了获得原谅,赦罪叙述一般被迫转为“展示”而不只是“叙述”当事人的喜好和感受。他们最大的天才在于创作“模仿的幻觉”:为他们的读者和听众重新创造一种情境,求赦者突然发怒是合情合理、可以理解的,他们对自身的生命产生了恐惧。
这些愤怒的情节因当事人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男人的故事中,关于行为的某些主题和假设看起来与社会类型密切相关。绅士故事的特征为求赦者是一个维护自身权利的领主,一个维持自身尊严的绅士,而当我们一旦涉及工匠和商人的故事,我们就进入了工作、酬劳、盗窃和债务的世界。因而,赦罪陈述的文献中,某些叙述完全视求赦者所自觉的社会地位而定,为了替自己辩护,人们可以借用对自身固有的社会地位的独特理解。
为了达到求赦的目的,赦罪书对叙事结构做了细致的安排。它们当中某些故事以私人的争吵或宿怨开头。更多的赦罪故事以求赦者平静地处理日常事务或参加节庆开始,以无法避免的悲剧或血腥的结局为高潮。这种处理可以建构出行为主体是无辜的、无恶意的或正当的形象,另一方面通过“细节政治”,提供足够逼真的材料使人信服,以细节来证明事情确实发生过。
赦罪和被赦是一种皇权的表现,赦罪书的运作是一场塑造君主权力的戏剧。到15世纪末,国王基本上建立起他对杀人案或其他任何重大案件独断的赦免权。赦罪故事中的各种分歧有着一种关联,即“逼真的”和“真实的”之间不确定的关系,而国王的各种赦免之间的分歧也有一种关联,即实际的皇家赦免与依照神和人类的法律可赦免的行为之间不确定的关系。虽然国王自称遵守纪律,但君权的强化使国王意志有可能逾越法律的约束。在真实和貌似真实的领域之间,皇家恩典和权力滋长,而求赦者将恢复原有的生活与好名声。
与男性不同,女性缺乏许多男性通用的赦罪理由。女性的愤怒似乎只在少数情况下才切实可用。就等级制度本质而言,妻子得忍耐服从丈夫,丈夫得纠正管教妻子,适度的殴打是允许的。这意味着妻子可能得大力寻找一套使委曲合法化的说辞。由于不愿用简单的、表示愤怒的程式,也不愿利用作为隶属者的妻子的程式,女性在演绎她们的故事时被迫更有创造性,被迫提供更多符合赦罪规约的细节。
在赦罪的可能性上,女性比男性要低许多,女巫和杀婴的质控几乎无法得到赦免。女性的求赦书并不像男性那样常常以职业或社会地位的故事情节为中心。更多的是有夫之妇和寡妇的故事,这些故事中,铺设舞台的是性别而不是社会地位。毋宁说是性别角色建构了女性的故事,她的陈述略过不提工作的事实,却把它安置在以家庭、性名誉、继承权为主题的叙述中。
总的说来,与男性相比,妇女的陈述更少利用礼仪和节庆做背景,更多会声称保护合法的财产索求和遗产继承以赢得理解。此外,对妇女而言,更普遍的问题是保卫她们的家,特别是她们的身体和人格免受非法的性侵犯。这种性别自称上的曲折是因为《圣经》和民间故事传统未能给她们提供在巫术、下毒或秘密行动之外别的叙述模式;这使女性求赦者很难找到一种冒险的或悲剧的方式,使她们可以在自己公开发生肢体冲突的情况下寻求赦免。
以上
平猫
2018年11月25日
《档案中的虚构》读后感(四):于不疑处有疑
从表面上看,本书讨论的是一堆琐屑的小事:16世纪时一些犯下罪过的法国平民,如何在赦罪书里讲述自己犯罪的过程,并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向国王和法官请求宽赦。但和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同,这里的重心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历史上的当事人如何“讲述”这些事件——基于可以理解的缘由,所有这些求赦的故事都隐藏着自我辩护的主观动机,因而总会“宣称杀人是未预谋的、非蓄意的,或者根据法国的法律是正当的、情有可原的”。一份成功的求赦书需要洞察掌握着赦免权的国王和法官的心理:同样一件事,怎样讲述才能取得谅解而被从轻发落?
这乍看起来似乎是常识:一个试图自我辩解的人,多半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文过饰非,因为真相或许对他是不利的,对他所说的话尤其需要小心对待。就像那个著名的笑话所说的,同样一件事,写成“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那给人的印象几乎截然相反。即便是纳粹集中营战犯的供词,按他们自己的陈述来看似乎也都显得仅是无害的“履行公务”而已。历史人物的自传、回忆录、甚至日记,都可能存在同样的倾向,因为他们可能预先就想到了后人会阅读这些材料。从新闻报道到自述,说什么和不说什么、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多说什么和少说什么,都是至关重要的叙述技巧,所呈现的“事实”便大为不同。概言之,“即呈现在作者和读者看来都真实、可信、有意义和可解释的一个陈述,需要对语言、细节和次序进行选择”(本书页4)。
需要澄清的是:这些并不纯然就是“撒谎”、“伪造”或“虚构”,当事人甚至并不一定是有意如此,他们也有可能是记不清、甚至为了不去触碰某些伤痛的记忆而让自己都相信了另一套叙述。只不过那些以审讯口供为基础的史料更容易受到怀疑,正如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中谈及曾静一案时所说的,“所有以审讯口供作为重建生活史或心态史的尝试都是踩在地雷上的危险工作”,因为犯人面对刑讯,总会本能地希望脱罪而扭曲自己的陈述。
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如果我们不回到西方史学发展的学术脉络中去,可能很难理解原著在1987年问世时所引发的那种震动。一言以蔽之,《档案中的虚构》是一本“历史学者写给历史学者看”的书,它牵涉到历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并从根本上质问和动摇了原先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
和其它社会科学不同,历史学不能创造自己的材料(那无异于丑闻),而只能依赖对现有存世材料的解读。19世纪初兴起的兰克史学坚信在行动过程中产生的文献尤其真实,他们真诚地相信,只要通过正确而“科学”的研究方法,就能恢复唯一的历史真相。这种信念极大地推动了档案文献的开放、以及对这些史料细致入微的批判性查验,一代代的历史学家都将档案馆视为天堂,从中能寻获历史事实的圣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学者对待史料的态度,常常像是寻求法定证据的法官,其探求真相的过程也类似于刑侦术。这种研究途径本身或许就与中世纪神判衰落之后纠问式程序的兴起有关:一位积极的纠问式法官或侦探试图通过科学方法来查获真相,区别只是历史学家无法拷打笔下的历史人物来榨取口供。
对于这样一个学术传统来说,《档案中的虚构》无异于一份革命宣言:它不再坚信历史学家能寻获某个单一的“真相”,反而致力于去探讨其“虚构”(fiction)。在此它体现了那种解构主义的基本精神:反对存在一个能把握真理性的主体形象、甚至否定存在终极真相,阅读史料也绝不是为了寻找原初意义,“事实”或许早已湮没在历史中,因为我们所能面对的仅仅只是遗留下来的这些文本而已,借用德里达的那句名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
因此,《档案中的虚构》看似是历史著作,但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它的成功其实是方法论和哲学层次上的胜利。它在很大程度上倒是颇有人类学的意味——借用列维-斯特劳斯著名的比喻,人类学者是“在历史的垃圾堆里捡破烂的人”,从一些史料碎片中确立观点。就像书中所提到的那些求赦书一样,对本书也不能孤立地去理解——它是一个众声喧哗时代的产物,其中隐含着某种时代精神,即真理的一元性已遭到否弃,而“再现”(representation)的客观性也被质疑,并要求从更深入的语境和社会关系中去理解人。
这场反叛并不源于史学界内部。虽然早在1951年,C.C.伯格就已撰文认为,像14世纪的《爪哇史颂》等书由于其显而易见的夸大成分,根本就不能算是历史著作,而只能从产生它们的社会这个框架内去理解;但史学界真正受到震动,还是在1960年代兴起的“语言学转向”,这一思潮认为对意义和思想的理解只能在语言本身之内进行理解。1960年问世的《故事的歌手》已提出:史诗的结构可以解析为若干主题集合,吟游诗人可以借用或重复这些情节;到1973年,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更提出:史学文本也是修辞,从而破除了那种“历史撰写是对真相本源的再现”这一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后出版的《东方学》(1980)、《报道伊斯兰》(1981)、《写文化》(1986)在不同领域都提出了挑战,主客体单向关系的科学定位遭到普遍质疑,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人们越来越怀疑,是否能有一个主体能“客观再现”自己所面对的客体,或者至少,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再现”?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历史学界对于这些思潮的反应是滞后的。黑泽明1950年的著名电影《罗生门》就已生动地体现了这一主题:“个人的主观陈述都不是全部真相”,而“唯一的真相掩埋在层累交错的陈述中”(我们今天称之为“编织”)。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或许正因历史学界对于“档案呈现的便是事实”的信念根深蒂固,人们并未普遍运用这一理念去批判地审视史料,《蒙塔尤》(1975)一书便以教会的审讯记录为准,实际上假定了村民的口供都是真实的。
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学家对“事实”的追寻,不应拘泥于轻信这些档案文献本身,而应转而关注产生这些文本的社会环境。是谁在说?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向谁说?他没有说出的部分是什么?为什么隐瞒或淡化?他是意在对听众产生什么效果?而这些听众也不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在求赦故事中,法国国王有足够的意愿来展现自己的宽宏与仁慈,因而在这一点上它与求赦的那些讲述者形成了共谋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么许多文献和著述所默认的求赦对象便是它的读者。
所有预先就设想好了留给后人看的文献档案都可能存在自我辩护的可能,历史学家理应批判地怀疑这些材料,并根据其隐藏的历史语境来达到更深切的理解。据说蒋介石即便在最忙的时候,每天也总要拨出不少时间来写日记,甚至花费不少力气去润色,毫无疑问,就像早先的李慈铭一样(李氏的《越缦堂日记》甚至在其生前就已被人传抄),他也料想到了自己留下的这笔材料一定会被人细细翻阅,而许多学者也果然信之不疑,完全从他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认为他的处境都是有情可原的。与其说把这看作是“历史真相”,倒不如说这是蒋氏留给后人的一份“求赦书”(这本身或许也是我们理解这个人物的关键点之一)。历史学者的职责并不是历史当事人的辩护律师,甚至也未必是审判他们的法官,但至少应是一位对他们的陈述有着敏锐理解的陪审员。
已刊2015-12-6《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