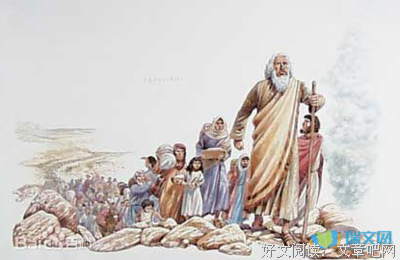
《关于犹太人问题》是一本由马克思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00,页数: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关于犹太人问题》精选点评:
●25岁!!对人权实现和政治国家建立的关系的论述精妙无比,但对犹太人本质的断言过于伪哲学。承认人的自然本质是利己,也没用到类本质的特征,是不是说明马克思已经是个唯物主义者了?
●渠敬东老师说,马克思要把黑格尔调转过来。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要让市民社会跃升为国家。马克思说,市民社会是本质,国家只是幻想。
●这版翻译得好棒~
●3.5 马克思的文风太缠绕了,而且骂人也太狠了,像在摁着对方的头,把一块炭放在他面前不断烧热。第二部分说犹太人的世俗基础(贪钱)被抽离后,他们的宗教意识也会不复存在。伯林说马克思在这里一直抗拒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认同;第一部分有往后学说的种子,不过“市民社会-人的解放”的二分没详细展开,论战价值大于思想深度。
●百读不厌的书。今天找出来又读了读,依然被二十多岁的马克思shock到了
●他人不是我们自由的限制,而是我们自由的完成。再读论犹太人问题,感觉又不一样了。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最后市民社会的人被认为是本来意义上的人。因为他是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马克思试图走出这一二元对立,但今天依然如此。
●重看了一天的课堂笔记后再读真是激动
●就是看看马克思怎么创造一种人的本质与随之而来的自由观。
●燕妮给马克思的信中这样写过:我常常提醒你注意一些其他的事,注意生活和现实,而不要象你所喜欢做的那样整个地沉浸、陶醉在爱的世界里,耗费你的全部精力,忘却其余的一切,只在这方面寻找安慰和幸福。——夫人明察╮(╯▽╰)╭
●只有犹太人和基督教那点说的在理
《关于犹太人问题》读后感(一):上帝都为难的问题
今天的两河流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文明的地区,古老的闪米特人就生活在两河流域地区。依据《圣经·旧约》的记载,诺亚是亚当的后代,他有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闪的后裔就是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犹太人,闪族有一个族长亚伯拉罕被上帝选中,带着族人迁徙到了迦南地,就是今天以色列、西岸和加沙,以及邻近的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临海部分。迦南的本地人称他们为“希伯来”人,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意思。这个时候就有了两个种族的矛盾,这是发生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的事情。
亚伯拉罕的嫡子以撒的儿子雅各是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时代犹太教已经开始形成。雅各的后代迁移到了埃及,后来沦为奴隶,约公元前1290年前后,摩西带着以色列人逃出了埃及,以后有了兴盛的以色列王国,后来以色列被罗马征服,公元70年和公元135年,犹太人发生了两次反抗罗马统治的大起义,在这中间,犹太人被屠杀了150万人以上,他们又继续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公元630年,伊斯兰教登上历史舞台,犹太人被赶逐,到处流散,从北非、西班牙、到欧洲,加洛林王朝接纳了犹太人。所以,在德国境内的犹太人问题就是一个有着复杂历史的问题。西欧主要的信仰是天主教,后来又有新教,犹太人并没有放弃犹太教,所以,这种复杂的矛盾就是民族和宗教的矛盾。
宗教的问题在于,亚伯拉罕的后代,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一神的宗教,你不皈依我,就是反对我,所以宗教冲突总是接连不断。公元700年以后,西班牙首先宣布奴役犹太人,1026年,英国驱赶犹太人出境,1358年,法国开始彻底驱赶犹太人,1492年,西班牙、葡萄牙开始驱赶犹太人。犹太人成了每一个国家都讨厌的对象,只要有国内动乱或经济危机,犹太人都会成为替罪羊。
公元1516年,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将全市犹太人驱入一个造枪炮的工厂内,使之与外界隔绝。欧洲各国仿效推广这一做法,发明了集中营。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的欧洲革命使犹太人的地位获得了一些改善,1848年,德国给犹太人以公民权。
但是,犹太人的苦难问题还是很严重,二战期间,犹太人被杀大约600万,相当于总数的三分之一。一战到二战期间,英国强行在巴勒斯坦划出了一块土地给犹太人,1947年,第二届联合国大会决议巴以分治,巴勒斯坦是逊尼派穆斯林,以色列是犹太教,所以,以色列从建国到如今,战争不断。
《论犹太人问题》发表于1844年,马克思写作此文是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这一个时期,正是欧洲社会激烈动荡的时期,政治民主和民族国家在快速形成,所以犹太人在德国受到了种族歧视。犹太人要求解放,鲍威尔认为犹太人想获得政治解放的话,就要放弃自己的犹太教信仰,用民主国家的政治理性消解宗教矛盾。
马克思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不会放弃自己的宗教偏见,他以北美为例,证明政治解放之后,宗教不仅存在还表现出了生命力和力量,财产、宗教的不平等继续压制着个人,所以,马克思认为,没有得到人类解放便要求政治解放,是不彻底和矛盾的。
在这一基础之上,马克思对启蒙思想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人权是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是脱离了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政治革命瓦解了封建社会,剩下了利己主义的个人,这还不是最后的解放。马克思认为,个人成了类存在物之后,人类解放才能够完成。
在第二篇文章中,马克思继续把这个问题进行引申,马克思指出,宗教的犹太人和世俗的犹太人是不同的,做生意的世俗的犹太人是自私自利的,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有世俗谋利的基础,市民社会是利己主义和自私的,它把人的世界变成了相互隔绝的、个人的世界。
所以犹太人问题的本质不是抽象的宗教的本质,而是世俗的经验的本质,只有消灭了这种经验本质,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消失了,犹太人和社会就都会获得解放。
在我个人看来,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启蒙思想、理性精神、激进主义等等思潮影响下的一篇文章。马克思用深刻的思辨批判了鲍威尔的观点,用更高级的人类解放批判了民族国家和市民社会,文章中显示出的雄辩、自信、激情、深刻是令我非常佩服的地方。民族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建构是启蒙思想和理性主义的产物,马克思在这个地方超越启蒙思想,又显得有一些激进,当然他继承了启蒙思想家的理性精神。
时至今日,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思考马克思,中东地区的犹太人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各个宗教也确实不打算放弃他们的信仰,人类的解放也还没有实现。犹太人的问题估计连上帝都会感觉很为难,我们这些凡人还能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关于犹太人问题》读后感(二):政治解放的限度与人类解放的图景
《论犹太人问题》发表于1844年的《德法年鉴》,是马克思第一部专门探讨犹太人问题的著作,也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政治解放、社会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力作。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而究竟什么是人类解放、马克思研究解放问题的意图、人类解放与犹太人问题的关系、如何达成人类解放等,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个人认为凭该文本的理论地位,应当加入《选集》第一卷,但可惜没有。重读本文后依然叹服于千年思想家的思辨性、深刻性、批判性与创新性。梳理文本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政治解放的限度
什么是政治解放?政治解放与宗教是何关系?是不是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国家就真正获得了国家的本质?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人类解放是何关系?
马克思有强烈的靶向意识,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过程中延续宗教批判,摆正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并阐明政治解放的限度。鲍威尔认为犹太人“必须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别人”,这里的“解放自己”指的是政治解放,也就是国家从宗教中摆脱出来,成为真正的政治国家。具体说来,犹太人放弃犹太教,随后将宗教废除的问题普遍化,即废除所有的宗教,以便实现公民的身份。鲍威尔以为在政治上废除宗教就能实现宗教的完全废除,其实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片面的解放观,也是种颠倒的宗教观。鲍威尔没有弄清楚,宗教的根源不是在于国家和政治,而是在于世俗,也就是市民社会。人自身的异化产生了神灵,神灵和宗教的泯灭必须要解决人的头脑和精神世界的问题,依照历史唯物主义,人的意识和精神的基础是现实实践。所以,真正的宗教的废除需要落实在世俗之中。
在考察“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北美各州的案例中,政治解放的限度更为凸显。在这些未把某种宗教设立为国教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还充满生命力,也即“宗教的定在和国家的完成是不矛盾的”。但是宗教存在本身就是世俗生活有缺陷的表现,国家可以通过政治革命(改革)从形式上摆脱宗教的桎梏,但信奉宗教的国民不可能在实质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人的自由也不是实质自由。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的、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
二、天国的生活VS尘世的生活——政治与世俗的二元对立
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国家,公民的存在方式是怎样的?自由与人权能否完全获得?
在政治国家,人无论在思想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这里就显示出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天国的生活”在这里并不是指神圣宗教,而是政治生活,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人将自己是做“社会存在物”行使公共权力;“尘世的生活”则是市民社会的生活,被奉为圭臬的是市场规律和资本逻辑,人的劳动及其人本身都是谋生的工具。这样一来,宗教从公共领域被驱逐到了私人领域,成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领域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战争”的精神。还需要补充的是,仅凭政治领域的解放,人不可能是现实的“类存在物”,不可能获得人权和自由,因为“在民主制中,却是感性的现实性、现代性、世俗准则”,政治国家何尝不是由世俗精神所主宰的呢?
那民主制之下鼓吹的自由民主人权到底是什么?马克思引述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对自由的界定——“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情的权利”,随后指出,这种自由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的联合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分隔基础上,这种权利就变成了自我和他人界限分明的且局限自身的权利,将他人视作自我的对立面,他人是实现自由的限制而非助力,长此以往就造成社会与人类自身的分裂。这种权利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权,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但是私有财产起源于异化劳动,本身就携带原罪,本身就是不公平不自由的。个人自由和公平的保障不是在市场交换领域,也不仅仅是在政治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具体来说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分配权上。依靠政治解放来获取的所谓自由和民主,与经济领域的丛林法则和马太效应相比,太伪善也太虚弱了。
三、犹太人解放的图景
批判了鲍威尔的犹太观,也彻底剖析了政治解放和市民社会的法则,那么犹太人如何获得真实的解放?
马克思说,寻找犹太人的秘密,“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现实的犹太精神、犹太人的世俗基础就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对多数犹太人来说,宗教成为一种摆设,虔诚也只是一种手段,现实利益才是目的。金钱和私有财产成了新的神,一切世俗生活都浸泡在利己主义的冷水中。因此,犹太人的解放就是从自私自利的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这需要批判私有财产、考察社会关系。
资本主义时代下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有犹太人的影子。犹太人问题完全可以上升为普遍性问题,犹太人的解放就是整个人类的解放。
2019.8.14
《关于犹太人问题》读后感(三):国家和教会: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的成熟,以同青年黑格尔派相分裂为标志。他和布鲁诺.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争论,实际上讨论的是国家和教会的关系问题——国家和教会的关系是宗教批判理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而宗教批判理论,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展示出马克思批判哲学的内在逻辑。
关于国家和教会的关系,早期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同时又与黑格尔的理论具有重大区别。在黑格尔看来,像其他所有的重要概念一样,国家和教会的关系必须放在他的绝对精神发展史中才能被理解,二者都是绝对精神的环节。大体来说,绝对精神的发展,是经过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的阶段而回到自身的历程。宗教已经到达了绝对精神回到自身的层次,但宗教还不是最终的、最纯粹的绝对精神,因为宗教是依靠感性的存在和信仰的情感来把握绝对精神的,它需要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的形象和信徒的非理性的崇拜和自我牺牲的情感。在黑格尔看来,关于绝对精神的绝对知识不是宗教,而是哲学。哲学和宗教作为把握绝对精神的方式,其对象是一致的,都以作为个别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自在自为的绝对精神为对象,但是哲学扬弃了宗教中的感性和情感因素,达到纯粹以理性的、冷静的概念来把握绝对精神的高度。而这正是绝对精神自身的高度。“绝对知识是在精神形态中认识着它自己的精神,换言之,是精神对精神自身的概念式的知识”。 另一方面,国家则是客观精神阶段的最高形式。它是个人和整体、主观自由和客观自由的统一,是至高无上的伦理实体,是“地上的精神”。事实上,世界历史将终止于最高形式的国家,具体说来就是日耳曼国家。而关键的问题是,足以终结历史的日耳曼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
根据黑格尔,既然宗教并非绝对精神的最终环节,那么最高形式的国家就不会是简单的基督教国家,特别不能是教士阶级掌权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在黑格尔看来,教会想要在世俗世界建立起上帝之国,其实质是在世俗世界实现非世俗世界的、超世俗世界的理想。而这种理念本身就表明,在宗教的眼中,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是处于不可调和的分裂中的。只有在这种分裂和对立之中,上帝之国的建立才是有意义的——上帝之国是世俗世界的反对者。宗教看不到这种对立的虚幻——它追求的神圣的上帝之国只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形象化和情感化的表现形式,而被它贬低为世俗的,恰恰是绝对精神将自身异化为客观精神的领域,国家正是这个领域的最高实现形式。因此,宗教眼中的神圣和世俗,只不过是绝对精神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实现形式,它们从根本上讲并不是对立的,它们源始的统一就基于:它们都来自于同一个绝对精神。事实上,世俗国家自身就是“上帝之国的实现”,换句话说,就是绝对精神客体化的最高环节。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教会和国家必须得到调和,而这种调和在宗教这里是不可能的,因为宗教必须以神圣和世俗的对立为前提;这种调和只能在世俗国家中得到实现。能够调和神圣和世俗、教会和国家的世俗国家,就是最高形式的国家,就是能够终结历史的国家。既然哲学或理性是绝对精神的最终阶段,那么最高形式的国家就应该是哲学的国家,或者说理性的国家。在理性的国家中,宗教不再是国家的基础,相反只有在国家之中宗教才有自己的位置;宗教也不再能够干涉政治,相反它被理性的政治整合入统一的国家的结构整体之中。对于黑格尔来说,如此一来,人类就和世界实现了和解,历史终结了,绝对精神在日耳曼国家中实现了自身。
这种解决宗教政治问题的基本思路,成为黑格尔主义的基本思路,被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所继承。马克思曾经也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员,然而,马克思开始形成自己独立思想的过程就是以他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为起点的。马克思早期的两篇著名的文章,“布鲁诺.鲍威尔:《论犹太人问题》”和“布鲁诺.鲍威尔:《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是直接回应和反驳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的,二者各自的观点大致如下:
布鲁诺.鲍威尔认为,犹太人想要得到政治解放,除非放弃自己的犹太教信仰。犹太人的奴役问题是宗教问题,犹太人同基督教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宗教矛盾,因此,除非消除宗教,犹太人将不会得到解放。在一个基督教国家中,犹太人是不可能得到解放的——唯有在民主国家中,犹太人人才可能得到解放。民主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它不以任何宗教为自己的基础,宣布笃信宗教仅仅是公民的个人私事。在这样的国家中,犹太人将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而与周围的基督徒处于政治上的对立(尽管无疑仍会存在宗教上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不具有政治形式,不带有政治后果),从而获得解放。 可见,布鲁诺.鲍威尔基本上是延续黑格尔的思路的,也就是要把宗教消解于民主国家的理性政治的结构之中,用理性政治解决宗教问题。基督徒想要获得自由,就要将自己的宗教解体。犹太人想要获得自由,就要信奉启蒙理性。也就是说,人的解放就是把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而这就等于建立废除了国教的民主国家。
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对犹太人的解放只是“政治解放”,但政治解放是一种有限的解放,它不是人的解放的最终实现形式。首先,民主国家真的将人们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吗?没有。在民主国家中,宗教虽然退为个人私事,但它仍然生气勃勃地存在着,只不过在法律上不具有政治形式而已;在真实生活中,各种宗教对立仍然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民主国家看似要废除宗教,实际上却恰恰最终实现了宗教——也就是说,实现了基督教。因为只在这样一个民主国家中,基督教才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即“彻底的彼岸性”。再也不能干涉政治的基督教,同时也就再也不用干涉政治了,它在严格的意义上建立起政治之外的“上帝之国”。因此,黑格尔的民主国家只是把它自身,亦即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了出来,而没有把这个国家中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宗教不仅仅在民主国家中仍然存在,而且,这时候它存在的基础恰恰就在民主国家之中——民主国家造成了“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之间、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二元性”,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二元性正是现代基督教的新的基础。这样一来,黑格尔的民主国家和理性政治,不仅没有真正把宗教驱逐出政治世界,实现国家对宗教的整合,相反为宗教提供了新的现实基础。
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宗教冲突只是表面现象,在宗教背后的本质层次,也就是宗教赖以存在的现实层次,犹太教和基督教是一个东西的两面。马克思说,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做生意,犹太人世俗的神是金钱。只要市民社会依然存在(也就是说,自私自利的人性、做生意的需要、金钱之神依然存在),那么现实的犹太教就不会灭亡。而民主国家非但没有消除市民社会,反而实现了市民社会的最终形式——因为民主国家虽说废除了国教,但实际上,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它却是基督教的实现。正是“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伦理的、理论的关系变成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从而在基督教的民主国家中,“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从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这样一来,基督教就成全了犹太教,成全了市民社会的“犹太人精神”。人类的真正解放,是从这种市民社会的自私自利、金钱崇拜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
并非犹太人从犹太教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其解放——真正的最终的解放也并不是这种政治解放;实际上,犹太人根本不用放弃犹太教也能实现政治解放,只要他们承认对犹太教的笃信只是纯粹个人私事,并在现实生活中对公共政治事务的要求做出让步。犹太人真正的解放(进而一切人真正的解放)恰恰是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从而也就真正地从宗教中获得解放,因为民主国家正是宗教赖以存在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最终的解放就要求人类彻底推翻民主国家,而推翻民主国家的实质最终是废除作为民主国家之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句话说,就是要废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在国家和教会的问题上,马克思挖掘了黑格尔主义的内在问题,并且揭示了黑格尔的政治理想——民主国家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后来越来越清楚地论证了,这个现实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说,就是“犹太人精神”。从而得出结论:犹太人的解放就是人类从犹太人精神中得到解放。
《关于犹太人问题》读后感(四):The fundamental Jewish spirit--liberalism
A form of religion abstracted from its associational foundation was popular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 and modernism. Religion is best when it leaves state, family, education, politics alone, is best when it is reduced to faith and belief. This Zeitgeist sprang from Protestant reformation, passed down to Marx here. The emphasis on reading of the sacred scripture is essential in this spirit in its religious form, that on theorizing of the politics is essential in its secular form.
The Jewish tradition always questions authority, question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questions the reliance on community and state. In the old covenant, Jewish heroes face to God by conscience directly yet not through the mediatory roles of religious leaders, angels, authorities, or family. The wandering experiences of the Jew further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any associable form of security based on commu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hosts or even among themselves. Financial capital became the best trusted source of security when all other forms of assets are essentially communal, therefore they did not just turn to usury due to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owning land for the Jews(which is not always true at the first hand), they inherited the fervor of investing invisible "capital" from 1) the old covenant's emphasis on the transi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ir society, and the important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God or any ultimate source of security; 2) their wandering experiences that exerted an alienated image of secular condition, which is also the reason why Jews tend to be favorite of liberalism and against the tradition-preserving conservatism.
Understanding this will ease the reading of Karl Marx, an essential Jew, liberal, revolutionary, interested in the invisible capital, who naturally oppose the idea of emancipating Jew by assimilating into Christianity. A real Jew cannot assimilate not because of discrimination or religion, but out of his fundamental distrust of human association in any form. In the book, Karl Marx embrace the idea of a secular civil society which deprives of religion, personal affiliation, family values, etc at public level:"Far from abolishing these real distinctions, the state only exists on the presupposition of their existence; it feels itself to be a political state and asserts its universality only in opposition to these elements of its being."; and reduce the problem of Judaism or Christianity to the problem of the lower infrastructure of the society:"We no longer regard religion as the cause, but only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secular narrowness. Therefore, we explain the religious limitations of the free citizen by their secular limitations." He was also wise asserting that religion only attains its truth when political intervention disappears, and a theocratic state is not really religious:"Indeed, the perfect Christian state is not the so-called Christian state – which acknowledges Christianity as its basis, as the state religion, and, therefore, adopts an exclusive attitude towards other religions..The so-called Christian state is simply nothing more than a non-state, since it is not Christianity as a religion, but only the human background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which can find its expression in actual human creations."
Though, when Karl Marx relegate the position of religion to private matters out of public views, he acknowledged that religion is often a force of conflict and differentiation, rather than unification. E.g.:"Religion is no longer the spirit of the state, in which man behaves – although in a limited way, in a particular form, and in a particular sphere – as a species-being, in community with other men. Religion has become the spirit of civil society, of the sphere of egoism, of 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 It is no longer the essence of community, but the essence of difference. It has become the expression of man’s separation from his community, from himself and from other men – as it was originally. It is only the abstract avowal of specific perversity, private whimsy, and arbitrariness. The endless fragmentation of religion in North America, for example, gives it even externally the form of a purely individual affair."
Here comes the problem, Karl Marx desired a mitigated power of religion in society, reduced to individual faith, contained under a liberating laïcité, yet he observed the obvious phenomenon that religion denomination fragmentized and caused trivial conflicts in his favorite example of secular land-North America (he compared France, Germany, and North America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only the last's constitution was truly free of religion). How could this paradox reconcile: when religion is contained as private property and politics were emancipated from religion narrowness in North America, it simultaneously led to 'bellum omnium contra comnes'? It could be a longer thesis but my point is concise: reducing religion to a private choice, an afterthought, a conscientious decision, a preference or taste, a rational argument, from its original social manner which Marx criticized as a mere human background of religion rather than religion per se, is dangerous. It does not emancipate human from fully living civil life without the disturbance of dogmatism, on the contrary, it causes fragmentized conflict, and makes religion "the essence of difference" than "the essence of community".
ow we are back to our original discussion: the Jewish question. An accurate depiction of Karl Marx' theory is not his criticism on capitalism, on materialism, or his espouse of dialectics. These are all but a manifestation of his alienation theory. Surprising similar is that you will find Jewish intellectuals all are amazed by the same question: not the oneness of God-for Islam is even stricter in this criterion, not Zion or money, but it is the alienation experience that fascinate this group of wandering people. All the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can trace down to this alienation experience, which deprives the Jews of the trust of associations and traditions. No wonder one will find disproportionally more protestant in support of Israel and the Jewish settlement in Palestine than any catholic or orthodox: Protestantism emphasis on sola fide, its bleak depiction of a sinful earthly world, its enthusiastic argument that faith should take root primarily in personal determination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rather than family inheritance or communal diffusion, all reflect a resemblance to the Jewish spirit: the fundamental distrust of associations and the abysmal sense of insecurity.
This book appeared as an argument against Bauer who thought Judaism is an obstacle for the Jew's assimilation. Yet Marx only expounded so fully enough his fundamental liberalism with Jewish characteristics, which spread throughout the book, and peaked finally in saying: "the right of man to liberty is based not on the association of man with man, but on the separation of man from man".
《关于犹太人问题》读后感(五):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读书摘要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读书摘要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写于1843年10月到12月,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同发表于1844年2月的《德法年鉴》。《论犹太人问题》是一篇论战文章,批判对象是马克思的老师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篇文字中所表达的观点。该文在马克思学说史上甚受重视,缘由有三:一是集中展现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体的批判,阐述了“人的解放”设想;二是勾勒出市民社会的异化关系;三是显示了犹太人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历来该文与《导言》都被当作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思想的经典文本,也确实如此。
思路复述:1、马克思概述鲍威尔《犹太人问题》一文的观点,认为鲍威尔一方面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以获得公民权,一方面却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这两个方面是相互矛盾的,暴露了鲍威尔理解犹太人问题的片面性——混淆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界限。批判基督教国家所达成的政治解放并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因为政治解放的限度让人分裂为公民与私人,犹太人问题最终归结成政治国家对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的冲突关系。犹太人在政治国家层面得到了解放,但在市民社会层面却依然受到压迫。犹太人问题的解决需要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解放是一种批判政治国家、超越政治力量的解放类型,弥合了公民与私人的裂隙,使人的世界回归于人自身。
2、马克思认为,鲍威尔是从神学的角度把握犹太人问题,而他则是从世俗的角度阐述犹太人问题。通过分析犹太教的世俗本性、犹太人与金钱的关系、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总之,通过批判犹太精神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要求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
文辞:马克思的文章是强势、畅快的,不过阅读中还是存在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尤其是第二部分充满论断却缺少详细的分析论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一、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
1、复述鲍威尔
马克思概述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的论述思路:鲍威尔从论述犹太人与基督教国家的关系入手,将犹太人问题归结为“宗教对国家的关系问题、宗教束缚和政治解放的矛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23,下同】但马克思认为,“一方面,鲍威尔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求一般人放弃宗教,以便作为公民得到解放。另一方面,鲍威尔坚决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25】这是对犹太人问题的片面理解。在马克思看来,理解犹太人问题,不能仅仅批判基督教国家,还必须批判国家本身,“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25】犹太人问题被提到人的解放的高度。
2、犹太人问题的表述及政治解放的局限
马克思描述了犹太人问题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述,这也是回应鲍威尔矛盾的例子:一是在不存在政治国家的德国,是纯粹神学的问题;二是在立宪国家的法国,是立宪制的问题、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三是在共和制的北美各州,是真正世俗的问题。宗教对国家的关系呈现本来的、纯粹的形式。国家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从第三点来看,宗教和国家的完成是不矛盾的。宗教是有缺陷的特殊,须从世俗局限性、世俗束缚、世俗限制来说明宗教的存在。神学问题要化为世俗问题。“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27】政治国家在宗教上的无能为力是由其世俗结构决定的,即政治国家和它的前提的矛盾所致。
因此,政治解放有限度:“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28】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首先,“人通过国家这个中介得到解放,他在政治上从某种限制中解放出来,就是在与自身的矛盾中超越这种限制,就是以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方式超越这种限制”【28-29】;其次,“人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就是用间接的方法,通过一个中介,尽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而使自己得到解放”【29】;最后,“人即使已经通过国家的中介作用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就是说,他宣布国家是无神论者,这时他还总是受到宗教的束缚,这正是因为他仅仅以间接的方法承认自己,仅仅通过中介承认自己”【29】。总之,“人对宗教的政治超越,具有一般政治超越所具有的一切缺点和优点”【29】。政治超越宣告人民的每一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但“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30】。
3、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
接下来,马克思根据前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特征,指认了人的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人是“社会存在物”、“类存在物”、“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后一种人是“私人”、“尘世存在物”、“一种不真实的现象”【30-31】。前者服从后者的统治。
按照这种区分,人作为特殊的宗教信徒这一身份(差别的本质),隶属于市民社会,与公民身份(共同性的本质)冲突,在国家中的生活只是一种外观。所以“犹太人问题最终归结成的这种世俗冲突,政治国家对自己的前提的关系。”马克思指出,鲍威尔任由这些世俗对立存在。
二元结构表明政治解放仅仅是迄今为止世界制度内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却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提醒说:“但是,我们不要对政治解放的限度产生错觉。人分为公人和私人,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这不是政治解放的一个阶段,这是它的完成;因此,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32】。
然后,马克思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政教分离就是政治解放本身,是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政治方式,由此产生的政治国家会有压制市民社会的时候,于是,马克思再次警告:“当政治生活感到特别自信的时候,它试图压制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要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现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但是,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只有宣布革命是不间断的,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正想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政治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的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33】从这里可以透视出国家专政力度的有限性及其转型的内在动力。
4、基督教国家批判
接下来马克思花了不少的篇幅展开了对基督教国家的批判。这是值得注意的内容,因为批判基督教国家、倡导政教分离自霍布斯以来已成共识,马克思何以再次花费篇幅论述这一问题确实费思量。或许缘于德国旧制度的历史情势,但马克思在《导言》中贬为不值一驳的东西;或许是想说明十七世纪以来政教分离的原则并不足以解决犹太人问题。
“所谓基督教国家只不过是非国家,因为通过现实的人的创作所实现的,并不是作为宗教的基督教,而只是基督教的人的背景。”“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通过基督教来否定国家,而决不是通过国家来实现基督教。”【33】因为基督教国家是以宗教的形式而不是以国家的形式信奉基督教,所以“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不完善的国家,而且基督教对它来说是它的不完善性的补充和神圣化。”【33-34】马克思此处区分了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的国家基础,“完成了的国家由于国家的一般本质所固有的缺陷而把宗教列入自己的前提,未完成的国家则由于自己作为有缺陷的国家的特殊存在所固有的缺陷而声称宗教是自己的基础,二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34】
接下来马克思通过分析鲍威尔的论述指出基督教国家的不可能性——国家世俗目的的卑鄙性与宗教意识的真诚性的冲突,这也是中世纪政治图景的面相。“面对这种主张世俗权力机关是自己的仆从的教会,国家是无能为力的,声称自己是宗教精神的支配者的世俗权力机关也是无能力为的。”【36】只有在民主制国家中,宗教精神才能以世俗形式出现,才能实现世俗化。但民主制的出现与基督教的关系密切,“政治民主制之所以是基督教的,是因为在这里,人,不仅一个人,而且每一个人,是享有主权的,是最高的存在物,但这是具有无教养的非社会表现形式的人,是具有偶然存在形式的人,是本来样子的人,是由于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而堕落了的人、丧失了自身的人、外化了的人,是受非人的关系和自然力控制的人,一句话,人还不是现实的类存在物。基督教的幻象、幻梦和基本要求,即人的主权在民主制中,却是感性的现实性、现代性、世俗准则。”【37】并且,在完成了的民主制中,宗教或神学因其没有政治的、世俗的目的,而是直接关注真正的彼岸的生活,显得更具有宗教意义、神学意义。
马克思归结到:“任何一种特殊宗教的信徒同自己的公民身份的矛盾,只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普遍世俗矛盾的一部分••••••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等于现实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37-38】这是政教分离原则、政治民主制的缺陷。
5、政治国家的批判
犹太人无须放弃犹太教即可获得政治解放,这是政治解放的限度。接下来马克思通过批判鲍威尔的提法阐释政治解放对公民权和人权的区分。
公民权与人权的区分。人权区分为“droits du citoyen”(公民权)和“droits de l’homme”(人权),前者属于政治自由、公民权利的范畴,后者属于市民社会的范畴,是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40】
自由。“自由式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这里所说的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40】
私有财产。“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的、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41】
自由和自由的应用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人不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这是马克思对近代自由观的批判。可联系《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来看。
平等。非政治意义上的平等。平等是自由的平等。
安全。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利己主义的保障。霍布斯的恐惧、黑格尔的“需要与理智的国家”。
马克思对以上人权的总结。人权“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42】市民社会成员的联接依赖自然的必然性、依赖人的需要和私人利益,依赖利己的人身保护。
6、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
马克思提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谜。“公民身份、政治共同体甚至都被那些谋求政治解放的人贬低为维护这些所谓人权的一种手段;因此citoyen[公民]被宣布为利己的homme[人]的奴仆;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被降低为人作为单个存在物所处的领域之下;最后,不是身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为bourgeois[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43】
谜的解答。
政治解放之前。旧社会是封建主义,“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的性质,就是说,市民社会的要素,例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但是,“人民生活的这种组织没有把财产或劳动上升为社会要素,相反,却完成了它们同国家整体的分离,把它们简称为社会中的特殊社会。”结果,个体隶属于特定的市民社会领域,与国家整体分离开来,“使他的特定的市民活动和地位变成他的普遍的活动和地位”,“国家统一体••••••必然表现为一个同人民相脱离的统治者及其仆从的特殊事务。”【44】
政治解放之后。“政治解放同事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政治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是人民同自己的共同体相分离的众多表现。”结果,“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44】政治解放之后的市民社会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个体,一是构成这些个体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旧市民社会中的“特定的生活活动和特定的生活地位降低到只具有个体意义”,由此“公共事务本身反而成了每个个体的普遍事务,政治职能成了他的普遍职能。”【45】
总结。“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甚至是从一种普遍内容的假象中得到解放。”【45】利己的人、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是国家通过人权予以承认的人。
7、近代自然权利论批判
国家的建立。“政治国家的建立和市民社会分解为独立的个体——这些个体的关系通过法制表现出来,正像等级制度中和行帮制度中的人的关系通过特权表现出来——是通过同一种行为实现的。”【45】
市民社会成员。非政治的人、利己的人、自然人,人权表现为自然权利。“利己的人是已经解体的社会的消极的、现成的结果,是有直接确定性的对象,因而也是自然的对象。”【46】
政治革命。“它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做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看做无须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从而看做自己的自然基础。”政治革命分解了市民社会,但却没有变革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
由此,“人,正像他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一样,被认为是本来意义上的人,与citoyen[公民]不同的homme[人],因为他是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以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
接着,马克思引用和肯定了卢梭的一段论述,表明公民权与人权的结合。卢梭在这里的出现值得注意。
最后,马克思提出了人的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中、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46】马克思将政治力量作为一种异化、一种压迫,必须转变这种力量,将其转化为与现实的个人不再对立的社会力量,才是解放的完成。
二、布鲁诺•鲍威尔:《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二十一印张》第56-71页)
1、复述鲍威尔的观点
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批判”的关系。
鲍威尔的问题:犹太人还是基督徒谁更有能力获得解放?或者,什么使人更加自由,是对犹太教的否定还是对基督教的否定?
由于“鲍威尔把犹太人的理想的抽象本质,即他的宗教,看做他的全部本质”【48】,所以犹太人的解放的问题还是神学的提法与神学的解决方案。
2、看待犹太人解放的视角转换
“在我们看来,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问题,变成了必须克服什么样的特殊社会要素才能废除犹太教的问题”。【49】对这一提法的揭示,马克思认为是由犹太教在现代社会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安息日的犹太人——日常的犹太人
犹太人的宗教与秘密——现实的犹太人与宗教的秘密
以上是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视角转换,其实这在第一部分已经表述过。
接下去是马克思对犹太教、犹太人的一系列断言。说它们是断言,因为根本没有分析论证,只是充满尖锐的论断。尤其是这些尖刻论断与马克思的犹太人身份相联系时,更加充满了解读的张力。当然,更多的论者将其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从经商牟利和金钱解放出来——因而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49】
接着提出消灭犹太人的社会组织。呼吁犹太人直接为人的解放工作。
因为犹太教具有现代的反社会的因素,这种因素即将解体,所以“犹太人的解放,就其最终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50】在这里,“反社会的因素”大约是指现代社会中的唯利是图、追逐金钱和“犹太精神”。
3、犹太精神与现代社会(金钱)
在现代市民社会,通过金钱,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犹太精神实际统治了基督教世界。“犹太人的实际政治权力同他的政治权利之间的矛盾,就是政治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51】“犹太人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殊成员,只是市民社会的犹太精神的特殊表现。”【51】
犹太人与金钱。“犹太人的宗教的基础本身是什么呢?实际需要,利己主义。”【52】“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52】“犹太人的想象中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一般地说,是财迷的民族。”【53】
犹太人与法律。狡猾的规避法律。
犹太精神的完成。犹太精神是实际需要的世界观,“实际需要的宗教,按其本质来说不可能在理论上完成,而是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因为实践才是它的真理。”【53】
4、犹太教与基督教
再论市民社会完成与基督教的关系,也可说是对政治民主制的论述。“犹太精神随着市民社会的完成而达成自己的顶点;但是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伦理的、理论的关系变成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54】这段话与第一部分中马克思论政治民主制的那一段话,充分显示了马克思对基督教在资本主义社会兴起中的作用的认识。
接下来是对犹太教与基督教关系的一系列论断。犹太人是唯物论的,基督教是唯灵论的。唯灵论的基督教从理论上使人从自身、从自然界自我异化出去,唯物论的犹太教在此基础上,把外化了的人、自然界变成可让渡的、可出售的、屈从于利己需要的、听任买卖的对象。马克思对犹太教与基督教之关系的论述需要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与把握。
5、犹太人解放的实现
马克思认为,“不仅在摩西五经或塔木德中,而且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都看到现代犹太人的本质不是抽象本质,而是高度的经验本质,塔不仅是犹太人的狭隘性,而且是社会的犹太人狭隘性。”【55】所以,犹太人的解放需要消除这一经验本质——经商牟利及其前提,消除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因此,“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55】犹太人的社会解放是对政治解放限度的超越。社会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