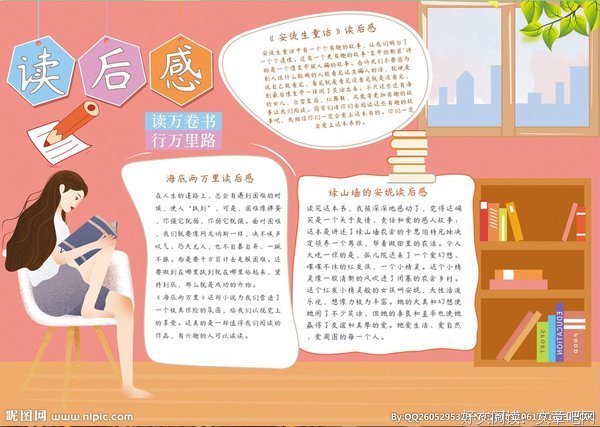
《皇帝和祖宗》是一本由科大卫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46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皇帝和祖宗》精选点评:
●相对来讲广州被王朝所同化的历史较短,才能缩成这样一本书。虽然史料在文中堆积太多,但其中的手法和角度都非常有启发性。总体来讲是非常有意思的地域性断代史研究。
●“社会史研究如果要有说服力,就必须结合地理,去研究人类的活动如何影响区域社会的形成。”学地理的人大概乐于读到作者的这句话。另外,这本书翻译得很活灵活现,虽然人名偶有译错,但是基本没有翻译腔,读起来很流畅。
●推荐,从历史的角度谈宗族的演化
●中国史研习营的时候没有看这本书,现在补上哈哈哈
●“从里甲过度到宗族,是充满着不幸的。”把一个土皇帝的时代变废为宝,改造成自己的时代,这种聪明,今天的文人还有吗?
●没人吐槽一下这书怪怪的翻译么?
●体格大个儿的书。以前只知道“唐宋大转型”,这书谈了个“明清新社会”(16-18世纪),主要线索还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了,官僚制科举取官在地方造成有政治庇护的士绅阶层,士绅和地方社会整合为一体的关键是作为集体组织(corporate)的宗族,宗族在各种控产组织(田产、投资、宗教、民事乃至军事)的背后成为地方秩序内在的一部分。这书的翻译非常尽责!
●这本书是个标题党。但是资料还是很有意思:尤其对现在研究所谓公民社会啊,社会组织和国家互动啊之类的可以看看。最有活力都是财产利益之争,比如古代为了沙田,现在是为了房产;古代以宗族为组织动员的模式,现在以什么业主委员会啊之类的
●华南研究
●看三遍了,每次看到尾声都很膜拜,也很感动,“以这种方法书写中国历史,不知还能维持多久,时间恐怕不多了。明清时期的社会建构的伟大成就,还有些痕迹保留至今,还能让当代历史学家看见。当代历史学家应该感到幸运,把握这个机会,写出明清时期的社会建构的历史,这应该是当代历史学家的责任。”科老师对学术厚重的感情是在里面的。
《皇帝和祖宗》读后感(一):宗族:何來何去
作者基本采取歷時的線索,追溯華南(廣州)地區宗族的發生與消亡。兩個時期是關鍵時期:16世紀的明代,基於儒家禮儀的宗族成為聯系國家與社會的紐帶;19-20世紀,現代民族主義和政治革命成為宗族消亡的力量,法律取代禮儀,形成合股公司。(18)
作者在序言中對宗族進行了界定:總國歷史上的不同時段,區域社會和王朝國家的關系,體現在不同的詞匯、儀式、統治風格、信仰之上。把這些詞匯、儀式、統治風格、信仰一言以蔽之,並以之命名一個制度,就是華南的“宗族”。(8)全書探討了王朝國家和鄉村及市民社會之間的關系,主要觀點是:社會通過禮儀和國家制衡,而禮儀的基礎是宗教之神廟與宗族之祠堂。(17)
“從裡甲到宗族”和“宗族士紳化”這兩大部分是談明代宗族的形成和擴大。作者認為明初的裡甲制度從勞役攤派變成收稅戶口,新的政治意識形態扎根,把禮儀和宗族變成了聯系國家和社會的工具,最終造就明清社會。(128)宗族建立後,其“大姓”通過控制市場、投資沙田等方式擴張發展。到17世紀,宗族與宗族禮儀已經在珠江三角洲扎根,社會所有階層的生活方式都受到文人影響(174),也就是所謂的宗族“士紳化”(gentrfication).
接下來的第三四部分談清代宗族的變遷。明清易代的動亂使得士紳的活動范圍超出了縣份的界限,清代,宗族不斷擴張,小宗族聯合成大宗族。通過節令祭祀等活動,宗族聯盟把宗族結合到地方秩序中(252),進而通過具有政治意義的儀式將社區整合到王朝國家中(256)。同時,宗族作為集體財產的管理者,類似股份制公司(266),因此,文人/商人的二元區分在宗族這裡是行不通的(274)在這部分,作者最後通過出版業探討18世紀珠江地區的日常生活(285):粵語文學的形成,加之文化運動,形成了廣東人的身份認同,出現了廣州的“中產階級”293。
在最後的總結中,作者指出:區域研究的關鍵制度就是宗族(431),社會史研究必須結合地理──不是地形圖,而是人類的活動如何影響區域社會的形成,政權如何擴大到地方。地方神靈與祖先如何被整合到國家中的;2)王朝基層政府如何建立的,這是宗族研究中最大的兩個問題(432)。
本書是作者二十年的研究成果,以華南為例,追溯了宗族發生直至消亡的歷史。在國家/社會的框架中,作者考察了軍事、商業、農業生產、文人文化等諸多因素對宗族的影響。其中涉及中國史研究的方方面面,作者在提到的若干問題中都引述了相關研究的成果。在原始材料方面,作者結合歷史文獻與田野調查材料,對廣州地區的歷史、地理、風俗、傳說都進行了詳細的敘述。
作者所提出的宗族基於商業發展,否定了宗族基於血緣和繼承的觀點,這似乎都我們理解中國傳統是不小的挑戰。秦暉研究漢簡,指出漢代西北某地幾乎無宗族,國家權力深入鄉村;宗族只在上層貴族中存在。不知道我們視之為傳統的宗族是否真是近代商業發展的產物。那麼再古代的中國又如何呢?
本書對文學研究的啟發有二:1) 作者強調中國研究中的區域特征以及人類學田野研究的重要意義,但是在文學研究中人們似乎很少考慮類似因素。文學是否有區域性呢?又如何超越區域限制呢?這可能和語言文字本身的特征有關系。2)文人作為國家和社會中的成員,其文學作品與其社會身份之間的聯系是什麼呢?不同文體與這種社會身份是否又有不同的意義呢?比如詩文集可以列入族譜的記錄總,創作了《金瓶梅》也要寫入嗎?詩文可以作為文人官員間酬唱的方式,小說戲曲是否有這些功能呢?總之,文學作品和作家,以及社會之間的聯系究竟是以何種形態存在的,這將是永恆的話題。
另:朋友介紹今天的中國,特別是南方,國家力量收縮,宗族勢力復興,不知在大歷史背景中這是否落入某種規律。
经过元末动荡,明朝前期的珠三角地区被地方强豪所控制,在这里推行里甲制度,这一本土化的过程本身就代表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与博弈。与以往的历史不同,本书开拓了地理历史的空间维度,围绕珠三角沙田的开发、合法化登记、税赋、防护等问题,描绘了王朝与地方两者以文化为资源和手段展开利益博弈的过程。王朝凭借里甲制度和将神明合法化的方法控制和承认地方的合法性;宗族为保护其本族利益,通过模仿对中央政制和推广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地方社会并以文化资源拒绝或归顺中央。
宗族的产生得益于两种制度:家庙与族谱。前者来源于1521年嘉靖皇帝的“大礼仪”争论。当时皇帝拜祭生父而非前皇帝,当时几位重要的珠三角官员站在皇帝一边,并在他们的家乡修建了表达政治立场的“家庙”。后者源于1581年里甲制度的推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登记户口直接关系到赋税服役,在对外贸易繁盛以及沙田产权纠纷问题突出的珠三角,则逐渐演变为赋役折银,登记人口逐渐演变为丈量土地:这也促进了文书的记录和教育的发展,进而有了追溯家族祖先的族谱。这场16世纪的社会革命促进了家族的产生,也使珠三角本土的理学思想纳入到王朝的意识形态,宗族的合法性开始从追溯祖先转移到科举功名。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为17世纪宗族的乡绅化提供了社会思想基础,也使地方与中央通过科举结合得更加紧密,宗族利益借助理学的包装,在乡镇建设和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此“皇帝的=祖宗的/我们的”这一方程式开始成立。
17世纪中期,明朝覆灭,南明、平南王和靖南王在广州的暴力统治随着康熙平定三藩而结束。清王朝进一步推进明王朝16世纪的变革,如“一条鞭法”和1712年的“摊丁入亩”,但里甲制度逐渐丧失了赋税的功能,成为乡镇组织保卫工作的制度。地方文人以乡饮酒礼表达其对汉族王朝的效忠,皇帝则通过承认广州的神明而表示中央对珠三角的亲善态度。王朝更替并没有带来制度上的深远影响,乡绅化的宗族依然通过皇帝的承认控制地方,比如修建桑园围。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海防压力增大,地方与中央在厘金收取的问题上产生竞争,聚焦在巡抚和总督的矛盾在鸦片战争时期达到顶点。19世纪华南海盗侵袭、英军攻打广州,1853年天地会叛乱、朝廷开始下令各地组建团练,拉开了地方军事化的序幕。这一转变使中央无法照常征收地税,因为地方有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能力和中央就税收问题讨价还价。这一转变迫使中央把税基转移到贸易税上,这也推动了商会、行会组织起来对抗政府的征税行为。
清末民初,“宪政”、“议会”、“共和”等政治新词汇开始广泛传播,通过召开咨议局和国会等方式,地方乡绅化的宗族以联合的方式组织起来继续掌控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甲午战后,中央政府的在政制上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是中央与地方矛盾激化的表现,其实质是:中央对地方的盘剥使掌握财政命脉的地方乡绅要求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主权。在清末到民初的过渡时期,华南的宗族继续以各种新鲜的名号争取自己的利益,这也可以解释革命后参与政权建设的主要群体仍旧为乡绅了。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市场的完善使宗族在城市控制地方成为可能。前者是科大卫教授所没有谈及的,在施坚雅的《农村社会结构》里谈得很清楚。由于编练新军和咨议局的召开,地方政治中心开始从乡村转向城市,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也迫使知识阶层游离出乡村,走向城市,城乡开始拉开一道大大的口子。打掉皇帝的人,很多是这样半新半旧的知识人,他们以行动和思想培养下一代的新式知识分子。皇帝没有了,剩下的祖宗很难从中央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转而组织更强的地方联合,这也是太平天国时期东南互保的遗产:联省自治。宣传地方而中央的合法性,进而维护中国的统一、抵御外国列强的入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思想最初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之前康梁等人“保中国而不保大清”的思想。
地方社会要权利的政治诉求在共和与复辟的折腾中石沉大海,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始终无法在政制层面上解开。文明的革命没有带来幸福,反而带来无尽的战争与贫困。青年知识分子正是在希望与失望中成长起来的。眼见乡绅、知识分子们耍弄着“共和”的旗号,却没有兑现承诺,于是他们恼火了。他们觉悟了,其“最后觉悟”,不是批评“共和”的水土不服,而是把矛头指向半旧半新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在乡村乃至城镇的老底揪出来,搬出更为现代的“科学”与“民主”。任何他们有关的乡约民俗都被打上“封建”的标签,无情摧残,而所谓的“民主”,则龟缩在角落,悄然从大众直选演变为“专政”。
《皇帝和祖宗》读后感(三):《皇帝与祖宗》分享提纲及读书笔记
《皇帝与祖宗》一书分享提纲:
1.广东在宋代以前的边缘化和边疆化
2.两宋时代广东的地域建构与整合——地方士绅阶层的崛起,理学思想的传播与影响,佛教寺院与王朝国家和地方社区的整合
3.明代广东地域建构与整合的新特点——里甲制的强制推行,宗族结构的进一步催生(嘉靖十五年开始允许建立平民祠堂),文人阶层的崛起,宗族与礼仪家训的结合,宗族的士绅化
4.从明到清,广东地域建构与整合的变迁——南明政权在广东的长期存在,迁海令的负面影响,清初对宗族的打压到康熙之后的支持,雍正时期的族长入律,清代的小政府与宗族自治,宗族的枝节化,以庙宇、寺庙为中心的士绅集团的出现,乡村小传统与王朝大传统的整合,宗族成为控制财产的组织
5.19世纪新变局下的广东地域建构与整合——19世纪初粤语文学的出现和文化运动的兴起对广东人身份认同的催生,作为权力中介人的士绅权力的进一步强化,团练组织的出现让宗族集财产权和武装力量于一体,宗族和行会成为税收的重要中介
7.延伸思考——粤语文化的形成与鼎盛,近现代广东在革命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之后广东作为开风气之先和边陲之地的双重身份的重要作用,广东地方语言文化的独特地位
8.延伸阅读书目: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马立博《虎、米、丝、泥》,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许华安《清代宗族组织研究》,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麻国庆《山海之间》
《皇帝与祖宗》一书读书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1宗族概念始创自弗里德曼,P4佛山的乡镇发展史,P7经济发达是促使宗族形成的重要原因,P10明王朝通过法律创造里甲,而宗族通过礼仪继承里甲,P11宗族是地方社会与国家整合的产物,P12祠堂的遍地开花,源于嘉靖皇帝即位后的大礼仪之争。
历史地理:
22广州原住民起源并非汉人,P26岭南作为边陲的光怪陆离形象,让其在人们的想象中进一步边缘化,P29南汉王朝在广东历史上的显著作用,P33—34北宋时期广东文教大兴,带来的乡绅阶层的诞生与崛起。
36从北宋到南宋,广州的地方士绅阶层开始崛起,P38宋代广州外籍人口人数众多,力量强大,P43理学思想在广东发生影响,比全国大部分地区更早。
49广东文人传统在元代发生中断,P50-52我们:地方统治圈,他们:猺、客家等,P62明初开始的我们与他们的合一。
77有宋一代,供奉本地神灵的庙宇没有囤积土地,而佛教寺院却能囤积土地,这是佛教寺院与王朝国家和地方社区整合的证明。
从里甲到宗族:
81元明之际,珠三角由地方武装豪强主宰,他们要求下属只忠于其个人,明王朝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强行推行里甲制的,P84华南移民的珠玑巷传说与华北移民的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的对比,P88里甲制绝不只是统计人口,它涉及到纳粮当差的赋役和政权的人口控制,P91里甲制对宗族结构的催生。
100黄萧养之乱促成的里甲登记的大大系统化,P103登记里甲与控制土地。
116明初乡村的移风易俗,把王朝正统性,建立在里甲制秩序基础上,P118嘉靖朝大礼仪之争,继嗣与继统,P119广东三杰对皇帝的拥护,让地方与中央合流,随之而来的打击淫祠运动,维护儒家正统,P127到15世纪,里甲制不再是劳役摊派制度,而是收税制度,P128新意识形态把礼仪和宗族变成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工具。
129从16世纪到18世纪,文人阶层在广东的崛起,P139宗族作为礼仪家训的载体,P145对百姓的政治庇护,拓展王朝国家的理念。
宗族士绅化:
161拥有共同祖先和士绅传统,成为霍氏宗族的维系特征。
174-176各家大姓的士绅化,到17世纪,宗族个宗族礼仪在珠三角生根,士绅社会开始出现。
从明到清:
180明末清初,珠三角士绅一直效忠明朝,P192地方武装与势力的兴起,P194士绅与暴力的结合。
196广东三忠的抗清运动,P199广州1650年第二次落入清朝手中,大屠杀与剃发易服,P202奴变在明清鼎革时期广东的横行,P208台湾平定后,康熙帝授意的祭南海神之举,标志着清朝不再与明遗民为敌。
218清代宗族的枝节化,P228合族祠在广州的兴盛。
252以庙宇、寺庙为中心的士绅集团的出现,标志着宗族社会的发展再进一步,P253乡村社会内化了王朝国家的礼仪,同时又维护自己的身份认同,P256乡村宗教对王朝制度的模仿,乡村小传统与王朝大传统的重合。
257在祠堂里祭祀祖先,让宗族成为控制财产的组织,P270宗族之间围绕土地和商业资源产生的激烈争夺,P274明清时期的财产权,是以宗族为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士农工商并非截然可分,彼此之间有重合。
286十九世纪初粤语文学的出现,加之诗人发起的文化运动,催生了广东人的身份认同。
十九世纪的转变:
319作为权力中介人的士绅权力,到19世纪中叶被进一步强化。
339从民壮到团练,广东社会自组织在19世纪的兴起。
341朝廷对乡村的依赖,进一步推动了地方防卫联盟及其背后的宗族力量,P348在广东政府高层瘫痪的情况下,广东团练的代行权力,P357广东政府恢复之后,正式政府与团练组织之间的权力冲突。
360作为一个制度的宗族,恰恰是地方社会整合到国家的结果,P380广州许家在近代的人才辈出。
382清末新政质疑宗族对新中国的作用,P391宗族和行会成为税收重要中介,P395清末新政和废除科举,让商人代替士绅成为崛起者,P400两广宣布独立,但与民国政府也相独立,P407宗族的衰落,难以见容于现代中国。
尾声:
411区域史与整体史的关系,P432明朝或许是全球最早的民族国家,田野行走与书斋史料搜集的关系。
(本文是蓑翁为2017年12月20日金陵读书“《皇帝与祖宗》与华南的地域建构”沙龙准备的分享提纲和读书笔记。)
《皇帝和祖宗》读后感(四):性别视角看“华南”——关于“宗族”
“中国其他地方又如何?你能谈一谈吗?”
这问题很可怕。
——科大卫在《皇帝与祖宗》一书的“尾声”中如此说道。“可怕”!这话令我不禁大笑,因为我也在某次研讨会上问过他类似的问题,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请他谈一谈中国其他地方,而只是一个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即“华南学派”(权且以为他们自己也认可了这一称呼)所摸索总结出的一套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模式,是否可以为我们观察其他地方的社会组织模式提供参照?
尽管科大卫十分谦虚地不予回答,但他的同道萧凤霞老师却坦承他们是有这“野心”的:“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人口,朝廷是怎样把他们统一起来的呢?”(大意)这个回答十分真诚,实际上这个问题还隐含着历史学家们出于谦虚谨慎而未说出口的对中国现实的观照。如果说历史可以为今天提供借鉴,那么关于明清时期华南社会历史的研究可以从相反的方向对今天的国家-社会的整合模式提出疑问:原本形态各异的地方社会在今天是否必须被纳入整齐划一的中央-基层政治权力体系当中?这不止是一个关于现代政治制度的有效性的问题,更是对其正义性的质疑。当然,这个质疑是由我私自引申出来的,实际上我的疑问是:假如传统中国地方社会有其完善的自治模式并能良好运转,那么在今天,国家(中央)安插直至村一级的党员“干部”,这一行为是否可以视为对地方的强硬干涉乃至侵犯?
在科大卫等人的研究视野中,宗族可以说是地方社会组织运作的基本和核心要素:通过修族谱、建宗祠(家庙)来追溯祖先,从而确立本宗族在地方社会当中的正统地位,进而在本地资源竞争中谋取一席之地。宗族的壮大继而发展了地方经济和文化,让一个地方社会看起来生机勃勃,颇有韦伯笔下的为基督教所鼓舞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意味。
照此看来,宗族不但合理,不但不该作为“封建糟粕”被革除,反倒还应该大加鼓励,任其自由发展,今日中国称霸世界似也未可知。
在科大卫等人笔下,宗族被视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或许因秉持史家的客观中立态度,他们未对宗族作任何批判。但问题恰在这里。在《皇帝与祖宗》一书中,科大卫多次提到女性,如广州光孝寺在南宋时期曾拥有28位“大施主”,其中男子11人,女子17人,出手最阔绰的是一位女施主,她很豪气地给寺院捐出了“数万亩田地”,而另一女子在出嫁前因丈夫溺亡,遂将夫家聘礼全部捐出(P76)。(这种事例并不罕见,我在田野当中也多见有碑刻记载妇女捐出田地给庙、庵的事例);再如,一些大族在制定族规家训时,“都把妇女局限于‘内’”(P136)。
照科大卫所说,礼仪不但是宗族身份正统化的象征,也是宗族势力与王朝权力得以整合的有力手段,然而他却不愿指出:宗族礼仪化的过程,也恰恰是妇女被排挤、被压迫的过程。
美国人类学家盖尔•鲁宾提出“社会性别制度”这一概念,意在说明,性别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与经济、政治制度相并行又整合为一体的制度。对于用“性别”这一范畴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有效性,学界一直存有争论,即便是女性主义学者内部也没有给出十分自信和肯定的回答。同样这也是长久困扰我自己的一个问题。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否基于对性别的操作?甚至,对性别的规范并使其成为一套制度是否是人类社会基本乃至核心的组织方式?
从人类学诞生之初便把婚姻家庭制度作为一项不可或缺的考察内容这一事实来看,关于性别对于解释人类社会的有效性的疑问,是应该可以给出一个肯定回答的。然而,也许由于性别对于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太过基础,以致于多数人都将一切关于性别的问题视为自然而不屑于探讨。关于性别的议题,“华南学派”中间似乎仅有萧凤霞和刘志伟有所涉及。萧凤霞写过一篇《妇女何在?》,似乎也仅有此一篇,不过我认为这篇文章意义极大。她在这篇文章中谈到广东小榄妇女“不落夫家”的习俗,被当地或本族的士绅文人作为一项符合儒家礼教的行为加以赞扬和支持。而刘志伟的《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大致也延续了萧的看法,提出“对女性形象的重塑,是士大夫在地方社会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既然都已看到关于女性的议题是地方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那么,问题只在于,这些手段对于建构或组织地方社会的意义和作用究竟有多大?是辅助性的手段,还是基础性的手段?
如果我们去翻看一下各地方志的“风俗”篇,多会看到对于有关男女的习俗的论述或批评;事实上,地方新官上任——尤其是在南方被视为“蛮夷”的地方——常常要施放的一把“火”就是对婚姻习俗的变革或根本革除。科大卫在本书中也提到这样一个例子:明时广东巡按御史戴璟曾为正风俗而拟定一系列规章,其中“正婚姻”一条有称:“槟榔乃夷人取新郎之义,以资欢笑也,有何意义而相沿弗改哉!”(P133)连槟榔作为嫁妆这样一个小小细节都会被批评,可见儒家文人官员对于男女婚姻制度在意的程度。
伴随着华南地区宗族的兴起,必然而来便是对性别制度的重构,或者说,正是通过对性别制度的重构,宗族礼仪和规章制度才得以与王朝正统相吻合:对父系血统的重申,对嫡长子继承制的严格限定,以及外婚制(男娶女嫁)正统性地位的确立,无一不是社会性别制度的重要内容,同时这些礼仪和规章制度也无一例外地将女性地位一再贬低。换句话说,如果不是通过对社会性别制度的重构,宗族便无从谈起,因为宗族本身即是社会性别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只不过通过对性别制度的重构,通过创建宗族,华南地区的男人们建立了一种有利于他们的父权制社会性别制度。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西方现代政治制度视为典范的新兴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在推翻帝制、建立现代共和国家的过程中,像过去那些儒家官员一样,他们也敏锐地看到了“性别”议题的重要意义,妇女被作为妨碍现代化进程的“问题”被提出;而更为激进的共产党人则旗帜鲜明地将“神权、族权、父权、夫权”相提并论,视此为束缚妇女的“四大绳索”力图将其消灭。
那么,从这点来说,现代国家的建立以及现代政治制度的推行,将国家权力延伸到地方社会则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似乎唯有国家力量才足以对抗作为父权制核心内容之一的族权,而地方干部则取代族长,成为地方秩序的维护者。
科大卫在“民族国家的矛盾”一章最后写道:
16世纪的礼仪革命,为王朝国家提供了一套理论,使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相结合。这套理论已经谢幕。新的理论教导我们:工人阶级崛兴于城市,而原本作为宗族及乡村成员的人,现在成了“农民”,“农民”据说是封建社会的残余。主导中国新社会的制度,从沿海城市诞生;主宰中国的精英,从现代学校诞生。从此,乡村社会就要靠边站,即使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也不自安,因为据说,必须由上海的尺度来衡量中国,这样才算现代云。(P407)
这段话印证了我最初的猜测,即“华南学派”的历史学家们有着对中国当下现实的观照;同时这一感伤的语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他们亦有着我在本文开头提出的质疑,即关于现代政治制度之正义性的质疑。然而他们似乎没有看到,不止是新社会、新精英借助这一政治制度得以诞生,新女性也由此诞生。当然,仅仅因为新女性的诞生,并不能全面回答关于现代政治制度之正义性的质疑,更何况,这一制度走到今天,资本主义与父权制进一步的融合,已经让我们对“新女性”之“新”产生了怀疑:冲破族权束缚,女性就真的解放了吗?与此同时,伴随着所谓“新农村建设”,我们却看到了族权的死灰复燃:大修族谱、大建宗祠,甚至清明祭祖竟成为国家法定节日——这一切,不由得我们不再次警惕。
《皇帝和祖宗》读后感(五):空泛地写写此书的笔记
本人学的是社会工作,并非人类学专业,对于正规学术上的明清史更是近乎无知,上学期某位老师指定几本历史人类学著作让我们阅读,本人“有幸”抽中《皇帝和祖宗》,对于我这个门外汉来说,异常艰苦,下文如有错漏,望得指正。
一、本书主题
科大卫直接表达理论的篇幅很少,书里头更多的是一大堆繁杂的史料,与其说他在写学术研究,不如说是在用珠三角的地方志、族谱等史料来描绘一幅历史图景,本人按照目录,对书的框架粗略地作出如下概括:
1.序言,介绍本书线索与写作目的;
2.历史地理,描述中原地区对南粤的“他者”印象,以及广府人对猺、疍的“他者”印象,介绍明朝之前的儒家理学及土地情况;
3.从里甲到宗族,讲述明初里甲制度的实际推行情况,宗族制度的历史;
4.宗族士绅化,佛山霍氏的宗族扩展趋势,出现合族宗祠;
5.从明到清,明清更替,宗族之于一个地方的地位——社会组织;
6.十九世纪的转变,宗族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由盛而衰;
7.尾声,珠三角研究的关键制度是宗族,但中国其他地区呢?所以要走出华南。
《皇帝和祖宗》的地方研究则是建立在详尽繁多的历史考证之上,难以将这本书的线索简单地归纳为经济或政治的研究,但还是可以看出学术研究里头常见的一个漏斗式模型:
文化 经济 政治
/
宗族制度
/
沙田 里甲 祭祀 士绅……
《皇帝和祖宗》一书利用地方资料考证,详细描绘了明清时期珠三角地区沙田开发、里甲制度、儒家礼仪的推行、士绅阶层活动等情况,而众多的内容仿佛难以用一条单一的线索将其归纳,但是以上所提及的内容均有一个共同的交汇点——宗族,《皇帝和祖宗》好像在说着以宗族为主题的众多南粤故事,通过描述地方的经济、治安、礼教等活动来表现珠三角宗族制度明清这几百年里的变化,再从宗族理论来回看出地方的文化、经济、政治变迁。
二、宗族的社会意义
(一)对萧公权的乡村控制理论的反叛——中央在古代未必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
萧公权的《中国乡村》大致分为三部分,首先是勾划乡村地区的各种区分,诸如村落、市集、城镇以及保甲与里甲之行政分配。第二部分叙述乡村控制,涉及保甲监控、里甲税收、社仓等灾荒控制以及乡约等意识形态的控制。最后讨论乡村与宗族控制的有效性,以及农民对控制的反应。
萧公权的研究指出,满清政府对乡村的控制相当严密。最直接的还是使乡民相互监视的保甲制度,所有居民都有向甲长打报告的义务,不遵守者与罪犯同罪。还有了帮助税吏征收的里甲制度,以及帮助农民缴税与消灾的社仓。里甲和社仓实可被视为对乡村作经济监控的工具。此外,还有各种意识形态控制,例如以程朱理学所强调的纲常,来普及忠君爱国的想法。
萧公权认为,如此庞大的帝国控制,显然支撑了200余年的满清统治。但自上而下的集权统治实亦松动了帝国的基业。任何集权政体但求安定而忽略了群众生活的改进与参与,以致于变得十分被动,听天由命,似于统治者无害,但当帝国控制最后失控时,被动的乡民不仅没有能力为政府效劳,而且无从抗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欺凌,以致于不信任和恐惧官府,从而发动暴乱。至此帝国控制便有了反弹。都无法消除帝国控制的后遗症。所以萧公权的结论是:传统中国乡村不存在任何性质的自治政府。[1]
但科大卫对萧公权的理论并不认同,在《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中,科大卫得出新界乡村的宗族制度并不是天然的,而是被引入到乡村;同时受到Freedman理论的影响,即对于宗族有了新的看法——宗族的形成与运作主要是通过追溯共同的祖先而不是靠谱牒,宗族更像是“合股公司”之类的社会组织。基于这两点,科大卫想知道新界以外的宗族情况,并且想知道宗族制度在其他地方又有何具体的意义,就选择了珠三角为研究对象。珠三角民众与帝国的关系在500年里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皇帝的严密控制未必如萧公权所想在华南乡村得到彻底执行,皇帝与民众之间,并非是正规的官府来维持稳定,而是带有地方自治色彩的宗族组织。
(二)华南宗族组织的变化
Freedman所提到的类似“合股公司”的宗族组织,也是经过一系列历史过程才发展出来,在《皇帝和祖宗》一书里面,科大卫则为我们描绘出了华南宗族在明朝以后的变化,而在变化的过程中,通过详实细致的考证,展示出了宗族之于社会各阶层的意义。
明朝以前的宗族与清末时有很大的不同。明以前,宗族制度更多是通过血亲关系来控制入住权,而社会上的控产集团更多是庙宇道观,并不是日后的宗族。明初,为了管理人口和分配徭役,王朝推行里甲制度,但民众多会想方设法来逃避徭役,里甲制度并不是完全按照王朝律例而推行。但里甲制度对于民众也有其好处,就是可以通过里甲登记来确认自己的田产,以及在战乱的时候用里甲身份来表明自己是朝廷的合法子民。
由于里甲登记的更新没有跟上人口增长,户口内的实际人口比在册的往往要多,里甲就慢慢地成为管理田产的工具,而由于白银流通增加,通过“一条鞭法”实物税渐渐改为了货币税,里甲制度的运行也失去了原意。而为了更好地用宗族来管理产业,民众去迎合王朝的儒家理学宣传。
明朝嘉靖皇帝的“大礼议”之争,支持嘉靖皇帝的几个广东官员回乡后建立了“家庙式”的祠堂以表支持,本来只能是贵族才可以建立的家庙在民间得到普及,同时,族谱的文字记录也加强了宗族制度。通过兴建“家庙式“宗祠来祭祖、族谱记录表示出对皇帝和儒家礼仪的支持,宗族的”合股公司“成型,衍生了”蒸尝“管理。
明清的朝代更迭,但这种变化并不是瞬间完成,明朝皇室南下反清,利用儒家理学礼仪来发展势力,但随着清朝对明皇室残余势力的打击,渐渐掌控了华南地区。在这更替的过程中,宗族的管理结构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到了清朝,随着贸易增加、经济增长,宗族掌控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沙田开发、行业协会的兴办,也参与了社会大型工程的建设,例如桑园围。宗族组织有自己的武装,并通过筹钱来兴办团练,对抗土匪和暴乱。[2]
科大卫将宗族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培养百姓对国家的忠诚;培养邻居的互信;建立公司架构控制财产进行投资;地方与王朝共谋,宗族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
三、社会学视角的思考
“不论是施坚雅、弗理德曼还是武雅士,都把我们从过去只着重探讨官僚体制如何从上而下地对地方发挥影响的问题困局中释放出来。他们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让我们掌握地方社会的互动。”[3]科大卫不仅仅将华南宗族视为一个祭祀的场所,而是承担了各种社会功能的社会组织,他的研究方式并非把宗族定格在了某一个状态或使其,而是变成了一段动态的历史来研究,有如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科大卫结合了“移情”与“逻辑”, 通过详细的地方志考证,总结当时的制度,将历史上的人视为“活生生的人”而非制度的执行者,站在历史当事人的角度去诠释那个时代,并打破主流观点之于该时代先入为主的印象。
读《皇帝和祖宗》,不禁想起社会学的老问题:社会如何组织?也就是肖凤霞所讲的:不论在帝国时期还是在现代,有那么大的地区文化差异,又经过那么繁复的兴衰周期,它是怎样维系着人民共同的想象的呢?[4]如何做到涂尔干所提出的有机团结呢?
一个社会的联结固然要有制度去作为规范,但在社会中的人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会去懂得轻重利弊,很多民众就逃避了明初的里甲制度,有令不行,社会的统一性何在呢?然而人既不是单纯的制度执行者,也不是完全理性的经纪人,在规条和利益计算之外,还有重要的文化一环。在《皇帝和祖宗》里,地方的宗族乡绅利用儒家礼仪来表示对国家的忠诚,皇朝政府也通过建立礼仪制度来承认地方的民众合法性。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孝悌等价值观成为信仰的基础,纵然未必人人都信奉儒家,但这种礼仪文化成为了民众与皇朝沟通的平台,在礼仪的话语下行事来获得行动的合法性。而宗族组织更是这种文化的载体,日常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例如节日祭祀、兴修水利、商业买卖等活动,常以宗族为单位进行策划组织,而就是在这种互动之中,国家的共同想象就在人们的脑海中渐渐形成,所以,国家的联结更多是建立在文化上而非制度上。
四、当下中国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反思
中华帝国的社会结构是“皇权—士绅—手工业者/农民”[5],变成了目前“民族国家政府—民众”的社会结构。抗衡王权的统治,需要有一个公共空间作为平台与王朝结构沟通,西方后来诞生了代议制以及其他民间团体,而中国则是用宗族来保护民间利益,通过利益这项保护伞,表示出形式上王朝的支持、归顺,而一旦有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冲突或地方想牟利时,则通过礼仪这意识形态话语来缓冲、博弈。“王朝律例外,还有情和理。”
在历次的社会变革运动中,原来作为合法组织的士绅宗族被打散了。在社会转型期间,原有的宗族组织被打散,政府却严格限制民间自发的社会组织,缺乏相应的法律,经济、政治制度的运作逻辑发生重大改变,社会问题亦随之产生。与明清时期相比,目前掌权者受到更少的制约和监督,宗族被打散,儒家礼仪的话语权消失了,而西方那套公民社会尚未建立起来,权力缺乏制衡,可以逾法、破坏体制。在众多社会问题中,尤其是公民人权被侵害的事件,往往是原子化的民众面对强大的利益集团和政府,而知识分子被排挤在权利之外,随着曝光的事件增多,民众只能日渐麻木和无奈。
[1]汪荣祖,《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燕京学报》,1995年新1期,431-53
[2]科大卫 (David Faure),卜永坚 翻译,《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2009 ,江苏人民出版社
[3] [4]肖凤霞,《廿载华南研究之旅》,《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1期,第181-190页
[5]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2004,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