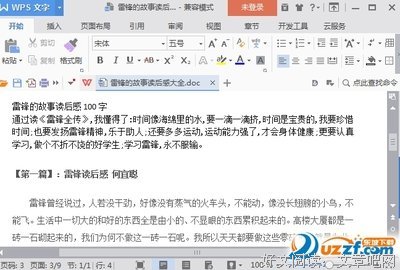
《故事开始了》是一本由[以色列] 阿摩司·奥兹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15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故事开始了》精选点评:
●四星半,里面有一篇惊到我了,所以打五星
●晚上睡不着拿这本书消夜,虽然其中的一些篇章有过度解读的嫌疑,但是奥兹所推崇的对于文学作品的这种小口啜饮的阅读方式还是颇为认同,一切快速阅读的方法都不适用于阅读文学作品。
●为此书而读莫兰黛。译者实属多年来未有的好译者
●2016年第六本书,begin~ "几乎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用这根骨头逗引女人的狗,而那条狗又使你接近那个女人"。// 轻松自在又博学深刻的讲述,小说的各种开头的分析,真是不看都不知道自己这么浅薄。同时很赞赏译者的严谨细致。// 有感于深层次的,与历史无关的,人性本质的恶意。// 分析,引申,解剖固然有益,但是对于阅读,慢慢品味的乐趣才是真正的原动力吧。真是一本好书,值得多读。
●其实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本书,因为我尚未读过那些作品,难以共鸣或者深刻体会,但我相信这也是我的开始,开始看一些文学评论,了解文学的构成发展延伸。
●首先,我觉得这本书太“隔”,所以未必很适合所有读者。就像译者自己说的那样,有的作品就连他自己,别说读过了,听都没听说过。其次,就我个人而言,倒是印证了自己对于雷蒙德·卡佛的阅读印象。第三,书太贵,一百多页字体还那么大,居然敢要22!译林是在抢钱吗?
●作者自己的自说自话,另外其中评论的作品都太生僻,平常人无法见到。
●15年4月20日,好读
●对写作其实没什么用吧 但是读来很有趣
●虽然用来分析的小说都不熟,只读过卡佛那部短篇,但通过作者的概述和细致的分析,还是能够领略这些小说独具一格的开场魅力的。对我有一定启发。特别令我着迷的地方不多。
《故事开始了》读后感(一):故事的开头:用肉骨头来“调情”
摘自《广州日报》 作者:来颖燕
几乎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你用这根骨头逗引女人的狗,而那条狗又使你接近那个女人。
现世往往在故事开始的地方投下了一个巨大的影子,真实与虚幻互相纠结缠绕。在这场纠结缠绕中,作者意欲表达些什么?文辞流转间,这些意图又实现了几何?这看似浅显,实则意味深长。用这本《故事开始了》的作者阿摩司•奥兹的话来说:“开始讲一个故事,就像在餐馆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调情。几乎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你用这根骨头逗引女人的狗,而那条狗又使你接近那个女人。”
奥兹是一个风格独特的文学评论家,因为他的骨子里是一个极具才情的作家。所以这本《故事开始了》,虽然是奥兹以评论家的身份分析小说开头的作用的理论之作,却纵横捭阖,才情洋溢。在他看来,这场骨头与狗,狗与女人的勾连,就像是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展开的一场你猜我度的拉锯战,试探着,迂回着,充满意趣和回味。而这场“调情”的关键,便在于那根“骨头”是否成功地吸引了那条狗。于是,奥兹非常郑重地申明了“骨头”的重要性:“故事的开头是应当细读的,它是作者和读者订立的合同。”
合同,意味着作者对于读者的邀约,通过这契约你能在小说中得到什么,或者,你干脆什么也得不到。而开头和整个文本纠结着,就如同履行合同的过程,迂回而充满不确定性。于是奥兹拿出不少名家作品的开头细加玩味,似在示范如何“履行合同”,他深入肌底又汪洋恣肆的解读,让这“履行”过程本身成了一个故事。
在奥兹的眼中,德国小说家特奥多尔•冯塔纳的小说《艾菲•布里斯特》的开头仿佛是一张游客的图画明信片,树影婆娑,缓慢而宁静,而这宁静之中遍布着一种奇异的紧张,如果错过,整个故事的格调就被打破了。果戈理的《鼻子》的开头却与《艾菲•布里斯特》相反,有着浓重的官僚气,能让人闻到一种“破烂的尊敬”,但是读完全篇,会发现小说开头本身的破绽百出就是作者给读者订立的一份合同通过这个“鼻子”我们出发去探索的那个世界,本身就是破绽百出、令人生疑的谎言……
对于小说形式的研究,历来不乏巨制。单以《小说的艺术》命名的作品,就有亨利•詹姆斯、戴•洛奇和米兰•昆德拉等大家写过。但奥兹仅仅用 “故事开始的地方”,就让我们浸润在了小说奇幻的世界里。奥兹的做法颇有点“釜底抽薪”之感从小说浑然却内里的核心出发,用感觉和恐惧、想象力和激情去把握作者的意图。所以,奥兹的解读还原了那些在只将小说作为修辞的艺术去研究的阅读中被阉割的乐趣,质感而动人心魄。
《故事开始了》读后感(二):作家的视角
通常,作家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看法、观点、角度都和一般的读者不一样。比方说纳博科夫对于《堂吉诃德》的解读以及对于弗洛伊德的一贯嘲讽;三岛由纪夫则非常看轻与他风格非常相似的太宰治;中国博文第一人韩寒对于中国最能赚钱的写手郭敬明更是时常调侃。可以说这本《故事开始了》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全新的阅读视角。
阿莫斯•奥兹,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一。他的作品我虽然没有怎么读过,但是一个当代文坛举足轻重作家的见解还是很值得期待一下的。奥兹确实也在这本介于论文与散文之间的文本中展现出了他对于文学独到的理解,我想这应该是本书能够带给读者的最大价值。
在这本文集中,奥兹筛选了十部小说的对它们的开头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所选择的十部,有我们熟悉的也有我们不熟悉的——熟悉的,就是果戈理、马尔克斯、卡佛、契科夫、卡夫卡这几位大师;不熟悉的大多是希伯来语及其他小语种的作家,当然原因也很简单,奥兹这个文本最早肯定是面向本国读者,选择母语作品是必然的,要是面对中国读者,大概会讲解四大名著的。
读书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阅读的乐趣往往是不能言说的,因此即便再好的作家也很难传达出他对于这种乐趣的感受。因为阅读体验本身是不能替代的,只有自己读了才能有所感悟,才会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击节赞叹。奥兹这本书并不是去教人怎么阅读,或者告诉读者那些地方怎么好,而是纯粹的介绍自己的阅读体验,给读者一种抛砖引玉的效果。
就拿我自己来说,阅读第一章“难以觉察的树荫移动”的时候,了解到的就是一种“势”的概念。这说起来有点像围棋,但其实很多作家看似无异议的景物描写其实就是在“造势”,“势”的基调奠定了,对于小说后面情节的展开有很大的帮助。
再说说第三章“一脸的郑重其事”,果戈理的作品接触到的往往就是被定义为讽刺社会的帽子,但是具体怎么讽刺,我们可能只注意到了类似于《死魂灵》、《钦差大臣》这些的故事情节。但是奥兹在对《鼻子》这篇小说细节部分的分析中又找出了很多例证,比如夸张的手法,比如一些细节的颠倒等等。而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阅读中无法注意到的。
最后说说第九章“把它弄出去,趁我还没吐”。卡佛的作品是书中作者中我最近读到的,卡佛极简主义的风格和那种美式冷硬的腔调现在越发受到欢迎,而卡佛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些开放式的结尾。而奥兹却只是分析作品的开头,通过对开头细节的探索和分析逐渐解析到小说结局的那种必然性,让我突然理解的那些看似无厘头结尾的原因。
总体上来说奥兹通过对于一些小说开头部分的分析介绍了自己的阅读方法,同时也变相的教会读者如何寻找阅读的趣味,可谓是对于自己阅读体验的言传身教。他的很多观点你不一定会赞同,但你不得不佩服他看这些问题的视角以及所看到的细节,而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中经常忽视的地方。
很多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都是很有野心的,可能只有另外一个伟大的作家才会敏感的发现这些精彩的地方。这也就是奥兹是著名作家而大部分读者只能看看小说的原因,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确实如此。有很多作品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深入的分析让它的评价和地位降低,不可能每个作家都得到鲁迅、曹雪芹的待遇。奥兹在这本书中看似是在分析一些小说的开头,其实是在向读者介绍阅读的乐趣和方法,告诉读者读什么,怎么读。
《故事开始了》读后感(三):悠闲的乐趣
文:奥兹
报纸上的广告引诱我们有些人去学习各种各样的快速阅读课程:这些广告承诺,我们只需交纳一笔小小的学费,就能学会如何节省宝贵的时间,学会每分钟看五页书,如何一目十行地浏览,如何略过细节,迅速到达最后一行。本书中所提的建议,对十部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的开篇合同的十次粗览,倒是可以作为慢速阅读教程的入门:阅读的乐趣和其它的乐趣一样,应该是小口啜饮,慢慢品味。
我们上六年级或七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的护士走进我们的教室,英勇无畏地走到三十个男孩子中间,揭示了生命的事实。这个护士的胆略真是惊人;她毫不畏惧地向我们展示了各个系统及其作用,在黑板上画出生殖管道的示意图,描述了所有的器官,讲清楚了所有附属物的作用。她什么都给我们讲了,无一遗漏,卵子和精子,各种膜和运作机制。她接着给我们做了一场真正恐怖的演示,把我们吓得毛骨悚然,她描述了卧在性交大门口的两头恶魔:怀孕和性病。我们都惊呆了,吓坏了,两个小时后,我们离开了教室。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但已经或多或少弄明白了,什么东西应该进到哪里去,什么东西应该接受什么东西,我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样可怕的灾难,然而那时候,我这个孩子还弄不明白,为什么每一个神志健全的人从一开始就心甘情愿被抓进这令人恐怖的笼子里。恰巧,那个精力旺盛的护士虽然毫不犹豫地给我们透露了所有的细节,从荷尔蒙到各种腺体,然而,她却略过了一个微小的细节:她没有告诉我们,甚至连暗示都没有,这个复杂的过程也伴随着,至少偶尔,某些乐趣。或许她觉得,不讲这些,就会使我们天真无邪的生命更加安全吧。或许她也不知道。
这正是文学界的有些人对我们做的:他们什么都分析到了,分析得令人作呕,技巧、主题、逆喻和转喻、寓言和内涵、隐含的犹太典故、潜在的心理基调及社会含义、原型人物和重大的主题,等等等等。他们单单把阅读的乐趣阉割掉了——只是一点点——免得它碍事;以便让我们记住,文学不是玩游戏,而一般来说,生活也不是野餐。
然而,果戈理笔下的鼻子、伊兹哈尔笔下的橘黄色调、阳台上的母牛、雅各布?沙卜泰笔下的叔叔们,甚至卡夫卡笔下那恶魔似的马——所有这一切,除了给我们提供了教育、信息等众所周知的大餐外,还诱导我们进入一个有乐趣、有快乐的游戏的世界。在所有这些小说里的不管哪一篇,我们都能获得一些“圈外人”不允许获得的东西:不仅仅是对我们熟知的世界的反映,也不仅仅是进入未知世界的旅程,而恰恰是触摸那“不可思议的”东西时的那种魅力。然而,一旦到了故事的里面,它就变得真实可信了,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感觉和恐惧,用想象力和激情去把握它。
阅读的游戏要求读者您积极地参与,把您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您自己的纯真感情,还有审慎和狡黠,带入这个领域。作品的开篇合同有时是捉迷藏,有时是“西蒙说” ,有时候则更像是棋类游戏。或者是扑克牌。或是纵横字谜。或者是恶作剧。或是请君入迷宫。邀人共舞。或者是一种嘲弄人的求爱,承诺了却不兑现,或者兑现错了,或者兑现的是从来没有承诺的东西,或者只是兑现一个承诺。
最后,和任何合同一样,您如果不阅读那些小字的附属细则,您就会上当受骗;不过,您有时候上当受骗恰恰是陷入了那些小字的泥潭中不可自拔,从而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我的邮箱里每天都塞满了请我出席各种会议和座谈会的邀请函,请我在会上讲“阿以冲突在文学中的形象”或“民族在小说里的反映”或者“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的镜子”之类的题目。但是,你如果想要的只是照照镜子,那干吗还要读书呢?
很久以前,在一片裸体海滩上,我看到一个男子,赤身坐着,津津有味地沉浸在一期《花花公子》杂志里。
就像那个男子一样,好的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应该进入作品中,而不是停留在作品之外。
《故事开始了》读后感(四):【读品】109辑荐书·文学
没有诘屈聱牙的句子,更没有故作艰涩的表述,阅读《故事开始了》是一场愉快的体验。大约因为本身是个作家的缘故,阿莫斯·奥兹把一本可能该称为理论作品的书写得意趣盎然。通常来说,作家对他们的同行的看法可能会和普通读者不太一样,历来也不乏名作家对小说形式进行研究的著作,譬如纳博科夫一贯性的嘲讽,譬如哈罗德·布鲁姆对经典的解读。光以《小说的艺术》为题的书,就有米兰·昆德拉、亨利·詹姆斯和戴·洛奇写过。而奥兹无疑给读者提供了另外一种解读方式,他试图仅仅通过对“故事开始的地方”缜密的分析,将读者带入故事的核心。
奥兹认为文章的开头及其重要,它是作者和读者之间订立的“合同”,当然,这些合同“各种各样”,有些是可信的,有些则缺乏诚意,有些则刻意布下了谜团。这是作者对读者发出的邀请,而之后的行文则是对这合同的兑现,是作者对其合同履行的过程。这过程曲折迂回,充满悬念和趣味,如同作者与读者之间展开的一场拉锯战,读者通过这些合同能够看出什么,其间充满了智慧。
书中奥兹分析了十篇小说的开头,实际上他通过这些分析介绍了自己的阅读方法,并通过那些幽默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向读者植入了他的阅读乐趣。小说中一些常常被忽视的细节被奥兹重新标注出来,也许只有出于作家特有的敏锐,才能发现他的同行们写作时那些匠心独运的暗笔。相信通过他的分析,很多读者会惊觉以前不曾觉察过的“细枝末节”。
然而这本书的缺点和其优点同样明显。奥兹的分析总在精彩处戛然而止,仅仅停留在对小说开头的文本分析,并没有深入小说的内核,以至于这本书看起来仍是一本略显散漫的随笔,而不能成为真正的理论作品。
那么相对于以上介绍的内容,在奥兹自己这本书的开头,他和读者订立的又是怎样一个开头合同?在引言的一开始,奥兹用妙趣横生的笔触描写了他面对着空空如也的稿纸时的感受,并大段大段地假设了作家针对某事写作的种种可能性:写、划掉、重写、再划掉。这一切都很容易让读者误以为这是一本旨在指导生手们如何写作,如何“无中生有”的书。这样的开头属于奥兹定义的各种开头中的哪一种?它是否可信,是否充满了诚意?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这本谈论开头的书的开头的可疑。(冯早早 推荐)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著:《故事开始了》,杨振同 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22.00元。
本文刊于【读品】109辑
或发邮件至dupinjournal@gmail.com订阅
《故事开始了》读后感(五):边缘困境:当代故事开头的经典模式
故事的高潮历来是文学创作的难点,也是故事内容的精髓。而开头原是故事的导入,只起到铺垫或伏笔的作用。但随着故事的多样化与商业化,故事的开头却成了一个引爆点,其成败直接关系到故事的可读性。在故事喷涌而出的今天,传统的巴尔扎克式开头已令人厌烦,缓慢的景物描写,喋喋不休的述说,另观众过早散场,即使故事有着极其震撼的高潮,那也不得不沦为小众读本。《故事开始了》这本书以散文的形式,向我们介绍了许多作家对故事开头的掌控力。而对于当代故事开头的模式,我也有了一个较为初步的认知。当代故事的开头必须爆炸般打破人物生活的平衡,并使局面达到边缘困境的状态,另人感到惊奇。
一个好的故事在起初便要出现激励事件,或是主人公的精神抉择,或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巧合。对于故事的人物而言,肉体和精神,非得有一个处在折磨之中。比如“卡夫卡式”的开头,便常常能将这折磨提升到新的高度。格力高尔变成甲壳虫既是肉体上的痛苦,又是精神上的冲击。这种开头不仅能激发出观众的好奇心,也能引发人类经验的极限,对后续的高潮形成铺垫。这种开头的创造往往是站在主人公的角度,尽量将世上的所有好事和坏事往身上放,反差越大便越好。比如开头便让主人公站在悬崖上,并有个坏蛋对他举着枪。这无疑打破了主人公的生活平衡,内心自然也激发出生存的欲望,而这样的开头便能理所当然地写下去。因为你要描写的便是主人公由死到生的挣扎。
当代故事开头的节奏往往要非常紧迫。或是如《鼻子》中的叙述——“圣彼得堡发生了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或是如《在她风华正茂时》中的叙述——“我母亲在她风华正茂的年龄就逝世了。”这种开头的主题便是——奇,尽量用说书人的强调,引发读者“欲知后事如何”。所以,我说,当代故事是属于卡夫卡,属于马尔克斯的。如《族长的秋天》的开头——“元月的一个下午,我们看见一头奶牛从总统府的阳台上凝视落日的余晖。”看毕这个开头,读者不免会产生许多遐想,奶牛为什么会在阳台上?为什么它要凝视余晖?这些问题便是作家设置的蜜糖陷阱,邀你入局,进入他的游戏。
本书中介绍的诸多开头,见仁见智,有许多便是我不热衷的类型。如 《米克达莫特》的那种哲理式的开头,故作“神曲”般的隐晦,未出现人物,未发生事件,这种开头像诗歌,而不太像故事。但《傲慢与偏见》的开头却是好的,虽然也是哲理性的语言,但也显得另类别致,另人产生顺从或是反驳的欲望。所以这类哲理性的开头,大概也要表现一种奇的观点,而不是故弄玄虚。还有《历史》那种充满神秘感,充满内涵的开头,大概要为后文埋一些伏笔。但我作为一个读者,看到那么多串记录,早就已失了兴趣。这种情况也出现在《红楼梦》中,很多人总是看不完《红楼梦》,便是因为其前五章埋了太多的伏笔,有了太多的内涵,没有故事情节,甚至没有主人公出场。假若不是因为其后文如此精彩,放置今日,急躁的编辑看完前两页便会讲这本世界名著扔掉。
看毕此书,总结如下,当代故事的写作已经呈现一种现代诗的趋势。激励事件是其主心骨,边缘困境是基本状态,而惊悚奇幻便是要追求的风格。所以,“一个杯子碎了”或许不能成为开头,但“穷人家唯一的杯子碎了”便可以,倘若“杯子碎后,还能化为一滩血水”那便更佳。但作家仍该意识到故事开头只是一个桥梁,一个骗局要用数万个谎言来圆。所以当你用奇崛的开头,讲读者引诱进去,要做的是持续制造高潮,留住他的心,如同恋爱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