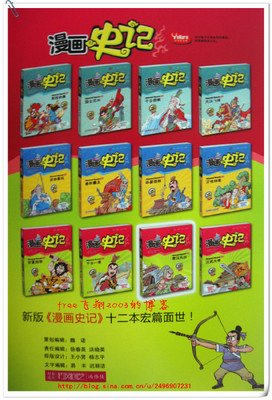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是一本由辛德勇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精选点评:
●今天见到辛神啦,并且他还在书上写了祝我生日快乐o(≧v≦)o辛神的观点呢总有一种真的这么简单嘛,不太敢相信唉!正好今天又学李贽,讲日用讲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辛神也不断强调这个思考角度:从最基本的人情事理出发去还原历史场景。听起来返璞归真,其实需要强大自信。
●新版,老辛一如既往的怨念、吐槽加开黑。本文考证过于繁冗枝蔓且论述的先后顺序似可调整,更重要的是个人感觉其论证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即使加上回应商榷的文章,我依然不赞成他的观点。。。
●在「輪台罪己」問題上對《通鑑》的政治構建問題爬梳得相對合理。但在巫蠱之禍這一問題上對漢武帝和戾太子關係上的分析就顯得心證過度了。諸如在第六章:〈漢武帝謂戾太子不類己故事的原型〉中,對王儉建構漢武帝與戾太子關係所參考的「漢家故事」僅憑心證,在沒有文獻證據的支撐下便推測王儉是通過漢高與漢惠,漢宣與漢元之間的「子不類父」建構出了漢武帝與戾太子的矛盾關係,顯得太過單薄。此外,在附錄:〈漢武帝太子據施行巫蠱事述說〉篇中,對「壺關三老」勸諫的過程亦做了心證十足的分析,從而間接證明太子據在巫蠱事上的「不清白」,亦顯得很奇怪。作為一本志在通過文獻整理梳理《通鑑》對漢武帝「史學建構」的「製造漢武帝」過程的論著,存在這樣的論證薄弱環節,會使得作者本身的論述亦是在「製造」一個作者心目中的「漢武帝」。
●蠢货屎学国永远在讲“这人太耿直”,没人管这事是非曲直。窝看搞个屎学裁判所,把丫儿们当牦牛粪烧了算了
●昨天中午在三联大致翻了翻,挑感兴趣的地方看了,辛老师这股劲儿是学界蛮难得的
●其实我觉得本书写得真心不错,最精彩的莫过于两点:第一是戾太子为何喜欢谷梁学——因为谷梁学最看重嫡长,对于母后可能被废而失位的太子而言,提供的即位理据最足;第二是王俭的《汉武故事》有王俭为自己父亲参与的刘劭身为太子谋反南朝宋文帝的感慨与同情。我觉得遗憾的是,尽管辛德勇在南京工业大学的讲座中反复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但对于什么是科学却了解有限,实际上科学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可参照查尔默斯《科学是什么》一书。辛德勇勤力沟梳文献自然应予肯定,但文献学之外,实有更广大空间。我很欣赏辛德勇正文里提到所有人都只提姓名,不言身份,亦不言身份。这种态度值得肯定,否则就有以身份压人的嫌疑了。历史学本身就存在着如王明珂所说客观的历史和主观的“历史们”,而如何展演也有意思,值得思考,辛德勇和田门弟子皆如此。
●想不到居然这么短。主要(能立得住的)结论是:司马光为了政治需要将汉武帝塑造成“那都是年轻时犯的错啊”,但实际上茂陵刘郎其实是“余之生涯一片无悔”。其他相关的推论就真的很推论了,反正材料不够多随便推。
●和《秦汉史探微》一起服用甚宜。辛德勇先生给我的感觉就是犀利潇洒。去年12月底在南大的讲座如此,前两天在公众号吐槽北大亦如此。本书可见先生的史料学功底之深厚,且敢于挑战田余庆之权威论断的精神。缘起部分一句“信不信由你”让人觉得无愧辛神之誉。所以历史就是遗忘与重构的过程,历史构建的复杂在本书得到体现。历史不容假设,但“山寨”制造就能被容许吗?
●《附录》一篇答疑,一篇补刀。太坏了2333333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一):读《制造汉武帝》司马光制造了汉武帝
支持辛德勇 司马光制造了汉武帝 年代早的史料可信 就像 汉书 虽比史记所引用的史料多 却都是画蛇添足 如对贾谊董仲舒的书写美化成分太多 这种衬托似乎更显现了汉初汉武帝对儒家 儒术的重视 却不知武帝朝的 儒术 仅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史记的作者是 当局者 他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而汉书的作者不过是拾人牙慧帮腔作势的远观者 自以为拆解了当局者迷的藩篱 实则是墙倒众人推把虚伪和聪明砸在了墙角下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二):史料真伪的辩驳,于无声处听惊雷。
《制造汉武帝》辛德勇
阅此书,还要多谢几位同学的推荐,加之今年有《秦汉史》一课,因此不免怀着功利之心。
之前久闻辛德勇教授大名,此书切入点虽小,但范围广博。以轮台之诏切入,史料广泛,指出史学界所公认“刘彻彻底转变其治国方针的纲领性文件”仅仅只是军事上策略的调整,而《汉武故事》中武帝与戾太子的故事系作者王俭自己的政治意向,却又阴差阳错,为司马光用于《资政通鉴》。司马光,王俭为何要重构汉武帝与戾太子的故事,原因各自不同的时代与政治背景。
司马君实先生大作《资治通鉴》,被朱熹评价“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蒙文通评“(司马光)毁斥用兵之类,盖亦以激于熙宁间事”。因此,辛德勇先生指出“王安石兵法所主张之富国强兵政策,与汉武帝之敛财于民、用兵于外,正相类似,而这却是一贯主张“以拊循百姓为先,以征伐四夷为后”的司马光所极力反对的”。
而王俭的背景则更加复杂,在宋文帝刘义隆与太子刘劭的宫廷斗争中,其父母也受牵累,因此“借神仙故事来曲折地表现他对这场宫廷斗争的看法”。
正如封面所言,“本书是一个案式的史学研究,提示研究者和普通读书史料的正确性是历史著作立论的基础。”此书大兴考据之功,简单史料,作者却能准确找到端倪,值得历史研究者前去学习。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三):卫太子施行巫蛊了吗?
按照辛德勇老师的说法,《汉书》从未提到过江充陷害卫太子一事,而石德和太子的惶恐表现也可证明其确实施行了巫蛊,且太子并没有打算亲自面见武帝证明自己的清白,更说明他确实施行了巫蛊,因此心虚。
仔细检视,辛德勇老师的这几个核心看法,都可有不同的解释,足以对其论文的观点产生冲击。
其一,《汉书·戾太子传》明言:“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可知江充与卫太子及其拥蹙早有嫌隙,担心武帝驾崩,卫太子即位后会对其不利,正好赶上武帝穷治巫蛊事,因此江充借这一机会陷害政敌,带有自保的性质,《汉书》字里行间早已将导火索指向江充,如何能说没有证据证明其陷害卫太子呢?江充陷害卫太子的性质,与赵高矫诏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打击某人,未必是因为支持另一人,只是权衡利弊下的选择而已。
其二,辛德勇老师认为石德听说太子宫内挖出巫蛊一事后第一反应不是问太子是否确有其事,而是“惧为师傅并诛”,所以石德可能也知道太子施行巫蛊的事情。辛老师这一说法其实存在很多破绽,在太子宫挖掘出巫蛊道具前,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公主乃至皇后弟弟的儿子卫伉都已经因为巫蛊之事而被诛杀,武帝统治下本就人心惶惶,第一时间众人想到的自然是很可能因为这件事被杀,更何况石德为太子少傅,无论巫蛊之事是否为真,他都有不可推卸的失察之责,是很有可能作为最终担责的替死鬼的,如何能不首先为自己的性命着想?
其三,辛文认为石德对太子说“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邪?无以自明。”是在暗示卫太子将此事指向江充。其实实际情况就是江充在太子宫确实掘出了巫蛊,众目睽睽,太子确实并无绝对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无以自明”一句,如果按照辛文的说法,该是对江充讲才对,这不合史实。
其四,辛老师认为如果卫太子是冤枉的,可以轻易见到汉武帝说明被陷害的实情,而他却直接造反,更说明施行巫蛊确有其事。其实政治上的事情绝对不能这么简单地思考,彼时“上疾,辟暑甘泉宫”,且因为年事已高,久在养病,太子本人很久没有见到武帝了,羽翼也被武帝剪除了不少,可以说是不再受到信任。而武帝晚年尤其宠爱钩弋夫人之子,甚至以“尧母门”暗示偏向,37岁的卫太子怎么不心生畏惧?他一定担心自己的地位,一定担心被取而代之,而且这确实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当他听说在自己的宫里发掘出巫蛊时,不管是否属实,他都会认为这是武帝开始废长立幼行动的开端,再联想到扶苏之事,他自然会觉得造反是最好的选择。
巫蛊案我觉得回归到事件本身,就是汉武帝晚年因为有了更多儿子,在储君问题上他存在一个徘徊不定阶段,晚年又多疑,对巫蛊又敏感,又确实有人干了,他就授意江充去看看太子有没有干,其实是一种政治考察,而江对武帝这个想法有体察,趁机兴风作浪。
至于太子是不是真的施了巫蛊并不重要,这一问题并不能得到实证,即便江充挖到的巫蛊不是卫太子埋下的,也不能证明卫太子没有在其他地方埋。但三个对武帝忠心耿耿的臣子去掘地三尺调查太子,太子必然认为自己有很大被废的可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听从石德建议,先下手为强,终致起兵造反而败亡。
武帝自身身体和精神状态存在不稳定,导致其在储君问题上发生犹豫,赋予了野心家们施行阴谋的空间,这就是巫蛊之事的本质。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四):汉武帝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读《制造汉武帝》
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么?这个“人”就是历史的书写者。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当代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给女明星卸妆。 辛德勇教授的这本书,首先是遵从其师黄永年先生的教导:《资治通鉴》的秦汉及其以前的部分,不能用作一般意义上的史料。因为司马光并没有依据今人不掌握的史料,完全依据《史记》和《汉书》改写。有一手证据不看,却依赖有可能夹带私货的二手材料,不是严谨史家所当为。(第1页) 辛德勇教授发现史学大家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恰恰是依据《通鉴》立论,且这篇文章影响极大。辛德勇教授不得不在黄先生和田先生的治学方法之间作出选择。 辛德勇教授通过研究发现司马光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而按照自己的意愿构建历史。 辛德勇教授此书的精彩之处在于: 首先,司马光使用的史料《汉武故事》是不靠谱的。 其次,司马光明知《汉武故事》不靠谱而用之。他并非“误用”,是故意的。朱熹就已经发现了。“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 再次,司马光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资治”(针对宋朝的政治现实劝诫皇帝),不仅故意用了不靠谱的《汉武故事》,还用了更不靠谱的《赵飞燕外传》和《天宝遗事》(杨贵妃洗儿)。《赵飞燕外传》是我高中时读过的古代情色文学,跟当代网络色情文学相比,那是相当含蓄,同学们就不用读了,除非你读《莺莺传》或《西厢记》也能嗨到飞起。 很多史学大家都知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非历史实录,但并不否定他删改历史的做法,比如钱穆,反而指导学生要体会司马光为何删改,体会其用意。 这就涉及对为何书写历史的认识问题。如实记录历史并不是古人的共识,西方也一样。写历史是为了写下范例为后人提供榜样。现实可能没那么好,没有那么黑白分明,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写得黑白分明,把人写得高大上。这样才能教育下一代。 这一信条至今不绝如缕。 所以司马光并不是异类。 更精彩的是,辛德勇教授考证,司马光选取的《汉武故事》系南朝时王俭所著,而王俭写这个故事构建戾太子形象是为了表达对刘劭反对宋文帝之举的同情。也就是说,王俭不敢公开表达对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同情,就把这个情绪投射到历史上的人物,通过书写历史来表达对当下的看法。 这种借古讽今的思路至今不绝如缕。 读完这本书的感想: 1.司马光不傻,以为司马光傻“考证辨别,皆为不苟”的才傻。 2.能够发现司马光引用的史料不靠谱的人不傻,知道司马光引用的史料不靠谱但并不觉得他傻反而细细体会他删改用意的人有大智慧。 3.黄永年先生的教导无疑是对的,但是田余庆先生真的不知道《资治通鉴》引用的资料不靠谱么? 有两种可能:一是真不知道,那田余庆先生就不配为史学大家。二是田余庆先生跟司马光一样,明知不靠谱却故意引用。 为什么? 因为田先生的论点是想指出汉武帝晚点有个钦定的太子跟他的思路完全不同,结果被小人逼迫兵变失败自杀,证明武帝晚年朝中其实有两条路线之争。 他会不会跟司马光乃至王俭一样,为了资治,为了以古喻今? 戾太子被写成喜欢儒家,“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读历史的乐趣,就在于即使读了原著,也未必有考辩的能力,所以还要看大家的解读,“我C,好NB,我怎么没看出来?”;看了大家的解读,还要看大家的争论。“他们都好有道理的样子,究竟谁更有道理?谁的证据更扎实?谁的逻辑更严谨?” 看他们往复辩难,就学会了独立思考。 学会了读历史,也就学会了读当代史。 今天我们耳闻目睹的一切,皆是历史。 司马光都不能信,罔论媒体。 不论自媒体,还是传统媒体。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当我们接收一条信息,看到一张图片,首先要问题三联: 作者要传达什么?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要卖东西,卖课程,还是要promote ideology? 《制造汉武帝》这样的书,值得指导孩子细读。
《制造汉武帝(增订本)》读后感(五):以历史学之名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无法通过史料学独力解决
仅散记读后所感若干点。
1、行文精彩。本想给五星,但五星(于我而言)意味着对作者方法与结论的全盘接受,故改为四星。我全盘接受辛先生的视角与方法,但少数具体结论略有一些操之过急感。
2、少数立论似乎尚属“必要非充分”,这并非作者文献学考据技术层面的原因(再说我也无力评判),而是史料本身有限,而所提问题本就无法仅依靠文献提取充分的论据。
3、倘若说本书的“唯一目的”是证明司马光《资治通鉴》对西汉一段史料记载之不可信,估计不会招致众多非议。但这样一来,行文或许就不这么引人入胜了。
4、《资治通鉴》言汉武帝晚年之改变政策路线,这一记载是否可信,当然首先是历史问题,但其次也是历史心理学、比较文化学、政治哲学的问题——因为一旦得证其不可信,那么紧接而来的“司马温公为何如此构建?”的问题,就进入了阐释的领域,而如何阐释,对于如何运用证据进行科学论证,是至关重要的。文末的讲座中,辛先生将“科学的”历史研究与“历史研究艺术化”相对立,我当然能get先生的用意。但“科学的”历史研究当然不仅限于某种可“量化”的分析。何况素材的不足,使得更”艺术化“地、但也是科学地运用间接素材,成为一种必然。
5、本书的逻辑,是从最初的大问题入手——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是否真实?(此一形象,始于《资治通鉴》,经由田余庆,成为今天某种官方见解)先以史料学的思路,尽可能地作必要性推论,得出《汉武故事》并非信史之后,再返回来做某种”充分性“的论证。这一往一返的结合处,就在于《汉武故事》究竟有哪些不可信之处。作者实际上提炼了次第渐进的三个疑问:(1)巫蛊之乱是否源自兴利尚功与“守文”的路线之争?(2)戾太子的人格是否“性仁恕温谨”?(3)戾太子是否真的行了巫蛊之事。
6、可见,以上第一个疑问,也对应着司马光为何要构建出“汉武帝晚年改变治国路线”的问题。第二个疑问,对应着王俭为何要构建出戾太子这般形象的问题。这已非纯然考据的问题,而是结构主义式的阐释。我认为,对于第二个疑问的阐释尤其精彩,特别是对这一命题的论证:从戾太子“私问《毂梁》而善之”并不能得出“性仁恕温谨”——涉及《春秋》开篇(隐公与桓公之争)问题的三种说法,这一段绝非冗长无谓。不过,这一阐释,无论如何做不到理工科般的“科学”(也即“充分性”),因此作者仍需一个关键性的反面证据——因此进入第三个疑问,证明戾太子确实犯有巫蛊之罪。
7、戾太子是否真的行了巫蛊犯上之事——本身是单纯的历史问题。但因文献极为有限,探究方法实际上已超越了历史研究的传统方法(文献考对、名词考证),而运用了心理学、文本分析、文化研究乃至人类学的解读。个人而言,觉得壶关三老的上奏文本,作为戾公子巫蛊之罪的实锤,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各个段落,以开导武帝息怒为始;进而引导武帝自责、换位思考;再到怪罪奸人、为太子开罪;再到劝释前嫌、息事宁人。这般套路,的确从侧面坐实戾太子的有罪。——不知辛先生在后语中所言的“幸运”,是否也指能如愿得证这一历史。顺便,这一论题其实非常有分量,不知为何作者在最初没有放在论文原文里面,而是在这一版附录中补充说明。
8、因为只要戾太子确非无辜,那么指其“性仁恕温谨”的说服力就大打折扣。果真,他采取一种合乎儒家理念的守文之道的可能性也就大打折扣。正因戾太子并非如此,才可能反过来寻找一个可能性的阐释,来处理梁齐之朝的王俭为何要为戾太子构建出这般形象的问题。进而,如果王俭之构建《汉武故事》的动机“充分”,那么司马温公之构建《资治通鉴》的动机也就能得到阐释。《资治通鉴》此段史料之不可信性也就能够得证。
10、但可见,以上凡属阐述的部分,其实都是多少具有“艺术性”的——并非史料学考据本身所能完成,而因史料的有限、文本的特点、文化史的规律,永远需要从典籍字面的表相,深入历史的本相。但这种阐述所需的艺术性,并不代表旁人不能判定其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我们永远可以判定一种阐释比另一种阐释“更加合理”(正如一件艺术品比另一件艺术品更“令人感动”)。我认为作者就上述问题所做的阐述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11、至于起初的大问题:汉武帝晚年是否真正“悔过”。我认为仅以本书的论证,是尚难作一锤定音的结论的。《盐铁论》虽是很好的证据,但仍存在“构建”的问题——霍光的构建、班固的构建,等等。毕竟,悔过与否,是以儒家民本伦理为标准的一种评判,而现实的矛盾冲突则有更为具体的机制和缘由。以现代历史科学之名,这些都是不得不深究的问题。
12、同一种构建的表相,对不同人来说可能出于不同的动机,对应不同的本相。于司马温公,可能他一心把汉武帝作为一个反面教材,以其“悔过”警示后世君王——“看,即使贵如汉武帝,也要认罪自责”。历史上其他同类的情境,当然不难想见。也可能将“悔过”作为一种粉饰手段:“……毕竟最终有所醒悟”云云。甚至将“悔过”当做一种最终人格趋于完满的象征。恰似那句:Ecce ho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