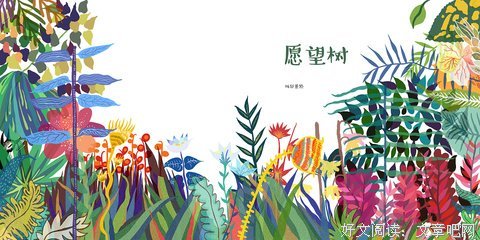
《愿望树》是一部由钦吉兹·阿布拉泽执导,Lika Kavjaradze / Soso Jachvliani / Zaza Kolelishv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愿望树》影评(一):愿望
物都有灵魂,草叶上的露水就是大地的眼泪.大地带着盛开的花儿微笑,天空带着闪亮的星星微笑.哪里有母亲的泪水,哪里就会长出美丽的兰花
世界上有三样永不存在的东西,通向天空的梯子,跨越海洋的大桥,最后就是正义
革命前封闭落后的格鲁吉亚农村,如石榴花般纯洁美丽的少女玛丽塔在贫穷和传统的压迫下慢慢枯萎.....
格鲁吉亚导演(那时还是苏联的一部分)阿布拉泽"往日三部曲"之二,在国际国内都大获好评.节奏缓慢,多处使用远
景和长镜头,在音效上进行了有趣的探索,画面则犹如清淡素雅的水彩画般美丽,不但塑造了老疯女普帕拉,顽固牧师齐齐柯尔,"预言家"约拉姆等
许多个性鲜明的角色,还把角色的性格构造成了一个相互对比影响的体系以帮助主题的发挥.当愚昧的村人准备处死无辜的玛丽塔时,之前被众人
鄙视的懒汉,疯女,叛乱者和荡妇纷纷跳出来欲阻挡队伍的前进却被那沉默的灰色洪流逐一吞没,这一段的镜头运用极为冷静有力.虽然表面是控
诉旧社会制度的套路片,但是导演充满抒情和神秘色彩的手法却将其蒙上了一层诗性的轻纱.一曲旧日时光的挽歌.
女主角玛丽塔的笑容非常纯美,第一个正面特写镜头真是看得我呆了.其实题材和画面与很多国内第五代导演的乡村片都类似,可是在他们的作品
里我永远找不到如本片般哀伤悠远的诗意.
《愿望树》影评(二):观影心水之 2:静心止水
星光飞舞,清辉朗朗,沁人心脾。不知今夕是何年。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就写了很多诗,由昆仑出版社出了一本《总是估算及其它诗篇》,朴素、节简又清澈,一如其人,当年牵着驴子走出白宫的人,就有着这样的诗情。他喜欢英国诗人迪兰·托马斯的诗。
这段时间,把前些年喜欢的电影“再次仰望”:如《蓝》《深秋的春光》《伤口》(前南)《今生相随》(阿根廷)《艾美的世界》(澳大利亚)《黑板》、《小巴舒》(伊朗)《萨拉戈斯手稿》(波兰)《寂寞的死亡之日》(玻利维亚)《哈法欧尼》(突尼斯)《菲茨杰卡德》(又译《陆上行舟》·德国)等。
当然,终于看到了一直想看的格鲁吉亚电影《愿望树》,阿布拉泽“三部曲”中最有名的一部,之前看过另一部《悔悟》。其中的美丽、悲悯与邪恶,混合在真切的现实中,于是那种无边的诗性情怀,通达到你这样一个远离格鲁吉亚的人心中。
姜文写了“念奴娇”,虽然威尼斯未能如愿,相信《太阳照常升起》。
只是,我们需要仰望,需要谦逊,需要广度与深度,需要如水的星光,洗去我们内心过多的尘埃,直至静心止水。
2007、9、11
《愿望树》影评(三):导演说
《愿望树》是苏联著名导演坚吉兹·阿布拉泽三部曲的第二部(另外两部是《祈求》和《悔悟》)。影片据格鲁吉亚人民诗人列昂尼泽的同名散文诗集改编。在诗集中,列昂尼泽怀着深深的感激和眷恋记录了他童年的感受。这里有诗人对故乡的回忆、童年生活的印象,还有少年时代丰富美丽的遐想。诗集由21个独立成篇的小故事组成。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鲜明的抒情形象。在诗人的特殊的抒情世界里,故事情节是不连贯的。因此,在改编中,导演阿布拉泽首先面临的是,把原作中“平行地存在的”主人公们导入同一个故事,纳入同一条轨道,从而创造出一个电影化的完整可信的世界,同时又保持一个成年诗人回忆中的童年诗人的精神世界。在《愿望树》中,导演阿布拉泽和剧作家伊纳尼什维里一起,以20世纪格鲁吉亚农村生活为背景,以美丽少女玛丽塔的不幸爱情为叙事主线,成功地把一系列具有鲜明色彩的抒情形象再现在银幕上,使影片的整个形象结构,它的风格和主题都渗透到诗人的文学世界里去。
影片《愿望树》全然不是材料选编式的银幕改编,而是一部具有完整严谨的剧作结构的影片。阿布拉泽在一个个抒情形象中,开掘每一位演员的新的、甚至连他自己都尚未发现的潜质,从而突现出形象的精神美。在《愿望树》中,有许多幻想家。埃利奥斯孜孜不倦地寻找魔石、金鱼,他期待着有朝一日那些具有魔力的东西能给他的可怜的女儿们带来好日子;弗法拉幻想着爱情,虽然这爱情她从未经历,但对于她,那幻想的爱情永不会死去。在《愿望树》中,阿布拉泽最大限度地运用了演员的潜质,表现出那些善良人们的美好愿望最终都未能实现的悲剧美。
玛丽塔的形象是由当时还是业余演员的丽卡·卡弗扎拉泽创造的。在对这一形象的造型处理中,阿布拉泽突现了少女玛丽塔的超人世的美,而卡弗扎拉泽的纯情表演,则最大限度地加强了整部影片的悲剧气氛。
弗法拉一角,使她的扮演者著名演员索菲柯·齐阿乌列里获得极大成功。透过那层白色的愚蠢的面罩,齐阿乌列里在观众面前展现了弗法拉那彷徨无着又无助的内心痛苦与渴望。她衣衫褴褛,却还要涂脂抹粉,她走村串户地讲述自己臆造的爱情故事,其实是一种自嘲自怜的手段。因为那幻想的幸福爱情就是她的生活意义,那么,她的生活也就成了这个非现实的“表演”体现。契阿乌列里恰到好处地再现了弗法拉的“表演”过程——每到一个村子时就紧张不安,就像演员即将上台一样。震惊于玛丽塔的惨死,弗法拉纵情地在自己幻想的废墟上为自己的命运哭泣。齐阿乌列里以令人惊叹的可信性把面对残酷的现实的弗法拉在虚幻的想象中寻找生活支持的无奈与徒劳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阿布拉泽挑选演员的外部条件很讲究。他善于在演员的脸上、在他们的造型中突现真正的美,并用电影手段记录下来。在《愿望树》中,奶奶玛拉基阿一角几乎没有台词。她总共在银幕上出现了五次:玛丽塔回到村里,在小河旁,奶奶坐在岸边,迎着太阳眯起双眼,欣赏着孙女的美丽。随后是她和儿子被齐齐柯尔说服的那场戏。在玛丽塔的婚礼上,当玛拉基阿听到“出卖了!出卖了!把美丽的塔玛尔出卖了!”的喊叫声后,她慢慢地转过头去,默默在注视着喊叫声远去的方向……她似乎已经看到她轻易应允的这门婚事将酿成孙女的悲剧,她感到自己铸成了不可原谅的大错,那种无尽的痛苦,被女演员塔凯什维里以震颤心灵的真实的面部表情体现出来。还有当她看见孙女尸体时那段迟缓的、无声的内心独白,使观众也仿佛与她一起再一次听见了那“出卖了!出卖了!”的喊叫声。在玛拉基阿这一形象中,导演通过演员饱满深刻的表演处理,揭示出玛丽塔悲剧的实质。
《愿望树》充满了美和生活的真实,呼唤着欢乐、怜悯和深深的同情。影片阐述的不是某一个主人公的感受,而是在生活的全部复杂性中阐明某种客观的真实。因此,《愿望树》在观众面前展现的世界是非中心的。在格鲁吉亚那个农村的小世界中,故事情节随着主人公中心地位的转换而展开。影片中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作“次要角色”的人物。这里所有的人物都是主要的,而同时又都是次要的,无论是那个带着傻儿子在村里徘徊的老太婆,还是美丽的玛丽塔。影片中的一个场面:齐齐柯尔站在乡亲们中间。乡亲们按照他的指示把不宜放牧的地方圈出来。在这几个镜头里,他明显地处于主要人物的地位。然而,当约拉姆喊叫着跑来把乡亲们打好的木桩都拔掉时,中心人物便成了约拉姆。接着便出现了打着小伞、满脸涂白的弗法拉,她不由自主地又取代了约拉姆的中心地位。这种非中心的主人公处理,体现出《愿望树》的艺术构思的客体化特点。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体现了人的价值。“世界是一个剧场,而世上的人们则是演员”,《愿望树》证实了这句话。同时,可以说,《愿望树》是愿望、幻想的集体形象,而不是这些愿望和幻想的实现。
阿布拉泽在影片的造型处理上非常严谨。从《愿望树》的最初几个镜头所渲染的情绪氛围,到影片结束前玛丽塔惨死的悲凉情景,都完满地体现了导演所刻意追求的外景美,造型优雅、镜头内线条的清晰和镜头结构的严谨。阿布拉泽的影片不仅是艺术作品,而且始终是民族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在《愿望树》的导演处理中,阿布拉泽不仅吸取了格鲁吉亚绘画、音乐、文学的各流派的特点,而且还吸取了建筑学的各流派的特点,开掘出为格鲁吉亚文学艺术各领域的某些流派特点继续发展的一块新天地。影片《愿望树》超越了一般的改编界限,它是一部完整独立的作品,是用当代电影意识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精神作出深刻理解的一次成功的创造。
《愿望树》影评(四):电影《愿望树》的诗化表现
世界上有三样永不存在的东西:通向天空的梯子,跨越海洋的大桥,最后就是正义。——“学者”勃布拉
格鲁吉亚导演阿布拉泽以他的作品《祈祷》、《愿望树》奠定自己诗电影导演大师的地位。《愿望树》改编自格鲁吉亚诗人列昂尼泽散文诗集,是阿布拉泽电影三部曲第二部。故事讲述了20世纪格鲁吉亚农村少女玛丽塔的爱情悲剧,里面零碎对呈现了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理想矛盾。
1.色彩
导演在电影中的色彩的诗意化运用,极富张力。电影开始,深蓝的天空下一只孤雁飞翔,鲜红的绿地上一匹白马静躺,穿白色布衣的男孩站在血红的花丛中,马挣扎跳起来挣扎,白色在血红中闪动,白布飞奔在血色的花中,朝葛迪雅(马的主人)飞去,告诉他的马将死,镜头摇到葛迪雅镰刀下,枯黄的草中零星点缀紫白色的碎花,他回头,镜头上移,传一身深红的布衣。镜头特写白马的眼睛,黑色的眼睛里留下几滴泪水,奇奇科尔叔叔赶来,传统的黑色,用短刀结束了马的生命,镜头被血红色慢慢充满,深蓝的天空下大雁再次飞去。
在影片的77’29处,镜头仰拍已光秃秃又分叉不断的树,有寻找魔法树的艾利奥兹,白色的天空被灰色的分叉划切,随后镜头从艾利奥兹的视角俯拍,地上一片枯黄的落叶,镜头再次正对艾利奥兹,深蓝袖子伸出的左手遮住左眼,右手用树叉叉住淡黄色的玻璃瓶,眼睛注视前方。在84’30处,全境,远处白茫茫的雪中三棵布满雪花的树。
2.声音
在影片的15’21女主角玛丽塔从雾中走来,马上的铃铛声清脆悦耳,伴随马滴答滴答的声音从远处走向镜头。水声,古老的乡村取水要到泉水口,水哗啦流向水罐中。笛声,悠扬的笛声从傻子的口中滑出。老疯女普帕拉反讽地讲述她的逝去的爱情,钢琴响起,一丝淡淡的忧伤。“没有你,我无法生活,你让我着迷,在炎热的仲夏,我也会冷的打颤,没有你,我无法取暖”。村边的妇女取笑的声音。“你为谁在荒废你的青春”。疯狂的“预言者”伊尔莫将耳朵贴在地上,轻声的耳语响起“来了,我们的幸福…….空气中充满火药味,来了,来了,这个旧大陆即将彻底垮台,飓风来了,暴风雨即将来临,啦…啦…啦…….”。46’15,伊尔莫带着一群孩子模仿火车前进的样子,火车的声音响起“巧克,巧克,巧克,巧克…….”,随后真的火车声音响起,而又被牛声盖住。暴雨中,伊尔莫嚎叫“咆哮、雷鸣、闪电劈开天空,塌下来!擦去所有的污垢,净化泥土与空气”。61’40,女主角玛丽塔在溪边踩洗毯子,清水在她的脚下激起一阵阵泡沫,声音如她一样清澈。玛丽塔和心爱的人葛迪雅偷偷相聚时,一种虚幻的声音响起,玛丽塔恍如梦境。“什么也听不到,既没有鸟叫声,也没有树叶的沙沙声”。结尾玛丽塔被处死的钟声,继而转向N年后某人的独白“去年春天,我去看过玛丽塔以前住的地方,一切都已枯萎、一片寂静。房子所在之处已是废墟一片,没留下一棵树。只有在以前壁炉坐在的地方,长着一颗石榴树,盛开着火焰般的花朵,在我面前容光焕发,好像在笑,就像玛丽塔的脸,一朵重开的石榴红,我看着那鲜红的花朵,无法相信,玛丽塔已经不在存在。难以置信,这棵耀眼的树,竟然在那片废墟里茁壮成长。美从何而来?又去往哪里?或许也许只是暂时的躲避吗?”
3.人物
4.尾声
最后,让我们把镜头转向男女主角在山地上的约会,他让她闭上眼睛,拿出一对送给玛丽塔的平底皮鞋,他说以前经常带他心爱的马来这里。玛丽塔说:“万物都有灵魂,草叶上的露水就是大地的眼泪。大地戴着盛开的花儿微笑,天空戴着闪亮的星星微笑。哪里有母亲的泪水,哪里就会长出美丽的紫罗兰。”玛丽塔抛起鞋,镜头仰拍天空,那只鞋化成一只飞翔的鸟。
电影资料:
愿望树Древо желания(1976)
导演: 钦吉兹•阿布拉泽(Tengiz Abuladze)
编剧: Georgi Leonidze / 钦吉兹•阿布拉泽 / Revaz Inanishvili
主演: Lika Kavjaradze / Soso Jachvliani / Zaza Kolelishvili / Kote Daushvili / Sofiko Chiaureli / Kakhi Kavsadze / Erosi Mandjgaladze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格鲁吉亚 / 苏联
语言: 格鲁吉亚语
上映日期: 1978-08-11
片长: 107 分钟
又名: 欲望之树 / 欲望树 / Natvris khe / The Wishing Tree
¬
《愿望树》影评(五):这个世界上,只有三样东西不存在
从杜甫仁科开始的苏联诗电影,总显得不那么讨喜。无论是塔科夫斯基还是卡拉托佐夫,他们的电影都诗意浪漫却无法令人沉醉,悲戚落寞而不道尽哀伤,精雕细琢中透着现实的冰冷,让观者很难单纯从情感上得到愉悦,阿布拉泽也不例外。尽管「愿望树」远离了战场与战争,那种艳丽的、压抑的、原始的情感,依然静待喷薄。
人类岁月长河,战争的急促掠夺与时间的悠长蹉跎,有时真说不准哪个更残忍。一对恋人,一个轻而易举地死在了战场上,一个空耗了一生的忠贞,守着记忆凄凄苦活。同样的爱国,要么付出生命断腕,要么付出人生苟活,哪个,更沉重?阿布拉泽对这些问题并不纠结痛心,他表现得甚至像个旁观格鲁吉亚的史学家,熟知但用情不深,灵动却无法热烈,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他只是更懂得这个民族骨血下镌刻的“韧”,顽强,也更为顽固,当他们被放之裂变前夕,情感沉积到爆发,这群人比谁都勇敢。只是那之前,漫长的拆筋剥骨之痛,如何承受?
暗流触礁,无处可见却避无可避
影片色彩饱满,风景秀丽,但与之相对的却是画面的粗糙,这与同时代许多苏联导演追求光影与线条精致的做法不同,并直接导致了影片呈现的画面感是艳俗与别扭的,如同普帕拉的脸,明明生活困窘到鞋跟断了,阳伞遍是漏洞,却偏偏要将脸抹得雪白,以摆出自己贵族的姿态。阿布拉泽没有给她柔腻的光线和高雅的音乐,而是任由她在简陋的小路上,踢踏着烂泥,挎着全部家当,自己哼着小曲儿走来,镜头只在观者的位置,沉默地注视。这就是1917年前的格鲁吉亚乡村——闭塞、贫穷,封建制度的余毒在这里尤为深重。
1917年的十月革命对于格鲁吉亚,是国家历史上的新的篇章,从1801年东格纳入俄罗斯帝国开始,整整一个世纪,这个国家都在与四围伊斯兰民族的战火中纠缠,在沙俄的同化政策中挣扎,数以万计的格国青年无辜充当了硝烟中的炮灰,所以十月革命之后,格国尽管只维持了片刻的独立,就又卷入一轮来自苏联的信仰清洗,但至少对当时的格国人民来说,是困兽到新生的蜕变。于是「愿望树」的背景设定,暗示了大革命前的压抑与躁动,这个国家像一叶无法自控的扁舟飘荡在时代洪流之中,当涌动的暗流触最边缘封闭的地带,战争必将来袭。
格·列昂尼泽说,电影里的故事来自他童年的记忆,那么他极可能就是村子里嬉戏的孩童之一,感受沙皇统治下的贫困,封建制度下生存规则的苛刻,以及信仰外化为宗教形式所带来的思想禁锢。当然电影远不止如此,任何坏时代,都拥有细枝末节的温柔,在「愿望树」中,这种闪光点是村落封闭性带来的亲切感与人情味。所以多数时间,你不会感受到阿布拉泽的批判和愤怒,即使电影开篇,白马就因为愚昧惨死,或者普帕拉因为未婚被嘲弄,乃至恋人被生生拆散,都不会让人有太多触动,毕竟愚昧、偏见以及专制,自始至终贯穿整个人类的历史,她变换着脸谱,升级了姿态,依然无法超越当代的眼界,所以尽管内容残忍,却不能上升到邪恶的层面。只有夺走一个人的一切,他才会站起来,阿布拉泽做的,就是展示这个过程,所以他批判,却不控诉。当仅存的侥幸心“或许……”被撕开——或许玛尔塔走进无爱的婚姻会幸福,或许普帕拉空首一段美好记忆就能感到满足,或许,埃利奥兹找到魔法树就会圆满……当代表美与纯洁的玛尔塔被无辜控罪,凄惨死去,一切变的无处遁形。所有目击者心中粉饰的太平与侥幸,都在个人意志轻而易举凌驾人命之上时,被粉碎一空。
草长鹰飞,腐朽的土地生生不息
电影开篇一个天空的空镜,蓝色阴郁,一只雄鹰在其中飞翔,发出如哨声一般的鸣叫,预示着革命信息正在传来。乍看之下,青天黑鸟,但细下探追,才发现这并非是个晴天的蓝色,灰白的云层不安分地笼罩,孤鹰切切哀嚎。苍云之下,漫山遍野的石榴花随风摆动,娇艳无比,这片土地从未改变自己的美丽,可居住其上的人却如苍鹰一般,正经历着以喙琢岩,自拔羽毛的痛苦,等待漫长地蜕变。阿布拉泽的细致在于,既能将民俗野趣展示得活泼,也能让严厉控诉如风暴般猛烈。
作为阿布拉泽格鲁吉亚“往事三部曲” 的第二部,电影贯穿着“无辜的被告”的设定,除此之外,三部影片在主题与风格上都是不同的。「愿望树」既没有「祈祷」(1968)那般充满诗意的哲思,也不如「忏悔」(1984)那般浓烈的政治批判,但就导演风格而言,「愿望树」比另两部走得都更远。无论是纯真与野趣的跳跃饱满,还是浓雾狂风下的暴烈批判,乃至人物群像地塑造,阿布拉泽都能运用朴素但严谨的镜头展示。难得的是,他能将反差如此之大的画面融合地恰到好处,当玛尔塔身着素黑,坐在马匹上穿过深灰浓雾而来,马蹄踢踏,银铃轻响,让人想到的不是同时代的任何一位苏联导演,而是在安哲罗普洛斯「哭泣的草原」(2004)中,踏着水波而来希腊人,沉寂、肃穆,虽然一无所有,但仍然让人觉得神圣,所以现实,并不总是功利。
影片基本以固定镜头和摇镜头为主,冷静地展示当时的乡村全貌,但因为节奏轻快,人物动作活泼,所以与塔科夫斯基抒情诗般的诗电影相去甚远。与塔氏质感细腻的形式美,擅长场面调度,善用特殊镜头以及神圣、优雅、静谧的气氛不同,「愿望树」多采用自然光,阿布拉泽并不着迷于通过光影打磨细腻的画面感,他既不经心雕刻线条与构图,也几乎不使用特殊角度的镜头,只通过多场景的内容展示,带领观者看遍这一片乡村,既是平行地观览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能通过智者的口了解过去,伊尔莫的话守望未来。当阅尽这土地上的人,你就很难对谁只抱有极端地态度——二元的批判或者赞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星星之火,终将燎原”,所以压抑、愤怒,但不绝望。电影采用时间叙事,依靠的是多人物场景的诗意拼接,将所有激烈的情感压缩在生活细节之中,直至最后的喷发。此外,他也采用了卡拉托佐夫在「雁南飞」(1957)中做到极致的黑阴影面积变化,来表达女主人公薇罗尼卡心境与现状变化的手法,虽然阿布拉泽做得并不明显。
尽管不算十分注重场面调度,阿布拉泽还是沿袭了苏联电影的严谨传统,即不执拗于细节,但却非常注重画面的表现力。他利用色彩划分人群:玛尔塔身穿白色长裙,她是圣洁的化身;奇奇柯尔、智者、神父身穿黑色,他们是权力与保守派的代表;整日醉酒的懒汉和智商低下的傻青年身穿明亮的黄色,他们虽然愚蠢,却是快乐的;葛迪雅、普帕拉、娜琪扎身戴红色,他们是充满朝气与活力的一群人,穿着灰色的伊尔莫看似癫狂,却是最为冷静的,身着蓝色的埃利奥兹代表了神圣与浪漫。因为影片的色彩十分艳丽,明亮的黄、艳丽的红、蓬勃的绿,阿布拉泽并不吝啬以多种跳跃的颜色来打造民俗风情,但随着玛尔塔被迫出嫁,埃利奥兹在枯黄的树林中迎来暴雪,室外,再无春色。所有的生机,被浓雾掩去,只有一片灰黑。
此外,本片几乎可以成为研究苏联诗电影隐喻与象征的范本,大量的象征——鹰、白马、石榴花、蒲公英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答案。在所有看似啰嗦的对话中,几乎没有一句台词是废话,除了玛尔塔和普帕拉两个主要女性角色之外,所有的台词都趋向叙事意义,而非抒情,这使得影片聚合了大量信息,或是直抒胸臆地直指大变革的来袭,或隐喻地表达格鲁吉亚的信仰与爱,涵盖了一个国家的历史、现在乃至未来。
美、信仰与羸弱的假道学
片中,玛尔塔与葛迪雅的爱情悲剧是主线,阿布拉泽通过两人的命运,交代了当时格鲁吉亚的问题——民族单一(荒谬的血统纯正性)、封建(阶级制度)、专制(家长制)、迷信(自我意识的捆绑,毫无由来的惶恐),也展示了在这样的社会,美的不堪一击。玛尔塔是美与圣洁的化身,她的出现或许可以在片刻感化人的心灵,却不可能通过对美的向往,引导人类做出非利己性的选择。片中除了一段普帕拉如同偶剧般逗趣的钢琴曲,其他五次无源音乐全部围绕着玛尔塔,曲调空灵神秘,仿佛只有她是超越现实的,是值得歌颂与不容侵犯的,可是美本身从来都是脆弱而没有话语权的。
在电影中有一个智者,出场时就如传教般殷切激昂地向少年感概国家的没落,他切切地指出国家的危机,铿锵有力地讲述历史的重要,呼吁孩子们尊重自己的文化,他张口所说全部都是智言,比如“忘记过去,是国家衰败的第一个征兆”,“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件东西不存在:通往天上的梯子,横跨海洋的大桥,还有正义”,然而面对不公正,他却心安理得的袖手旁光,甚至关上了己家的大门。这个智者的懦弱,是知识分子的悲哀,阿布拉泽展示了个人选择的冷漠,却也借他的口强调了一个正在被忽视的事实:我从过去知道我是谁,如果格鲁吉亚的历史被遗忘,那么我们都是谁?不过放之影片之中,在历史转折面前,说什么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从来是做什么,当所谓善恶关乎历史洪潮转折时,一瞬间的选择就是生或死的极端。
此外,还有不顾家庭的贫瘠,一心带着6个女儿寻找能带来幸福的超自然物质寄托(刚开始是魔法石,后来是魔法树)的埃利奥兹。他的坚持让人不无感动,当没有人理解的时候,他依然固执、虔诚地相信并寻找不知在哪里的“终极天堂”,直至被大雪冻死在一棵“与众不同的”树下,也毫不知悔地沉醉于那株可爱的树。埃利奥兹寻找魔法树前,家人为他穿衣批巾,最后的耶稣造型,预示了他殉道者的命运,一场必定死的旅程,他的死表明了在这个时代,单纯依靠信仰的无能为力。但阿布拉泽对信仰(而非以神父为头的宗教)绝非否定,相反他相信信仰的力量,于是影片结尾处,埃利奥兹的女儿给树枝系上丝带,继承了父亲虔诚的衣钵,继续寻找能让他们幸福的魔法树。
浓墨重彩之下,尽是冷静
在片中数度响起教堂的钟声,肃穆、庄严,似警醒,但更似哀悼。虽然本片的故事背景是1917年前夕,但实际拍摄时间是1977年,从格鲁吉亚的历史来看,他们与俄罗斯民族事实捆绑已经近两个世纪,因此不排除阿布拉泽对民族信仰陷落的哀悯之情。历史上的格鲁吉亚,几乎不是普希金笔下“我忧郁而快乐,我的哀愁是明亮的”那般浪漫,他存在于高加索地区四围的穆斯林民族包围,在对俄罗斯地依赖和摆脱中苦苦摇摆,但这个顽强的国家却在如此之长久的同化政策中,从未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们依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国家认同感,直至1991年独立。格鲁吉亚信奉东正教,这种信仰根植于民族传承的方方面面,关乎着历史、文化、思想、习俗,但在苏联期间,格鲁吉亚民族的信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迫害,信仰的断代和破坏,给格国造成的伤害是永远无法复原的,阿布拉泽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经因为「愿望树」在苏联受到了高度地认可和肯定,但也一转身因为「忏悔」触碰历史的敏感,几经周折。尽管比起「忏悔」中影射斯大林政治暴力的情节,「愿望树」的时代显得更为飘渺,但就导演风格而言,「愿望树」呈现了更为独立和饱满的美感。
除了「愿望树」,与阿布拉泽同样被提及的作品,诸如奥塔·伊奥谢利阿尼的「落叶」(1966)、尤里·伊利延科「带黑色标记的白鸟」(1972)都不约而同地以更为奔放却压抑地姿态,展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诗意现实。但相较两者,阿布拉泽对影片整体的把握,对自然民俗地展示更为自然流畅。他既没有个人碰撞时代的尴尬,也无神秘诡异的仪式感,一切顺畅地犹如乡间溪水的平实与坠打瀑布般的激荡。他镜头下的干净与冷静,超过一个人对故土认知与感情的眼界狭隘,当然这种激烈包裹下的冷静也让观者更加难以忍受,因为他的电影中有太多的人,他既不脸谱化他们,也不细致地雕琢他们,而是把太多关于人物的人生细节留白,也许不交代,也许一笔带过,还不如「忏悔」中愤怒、偏执、思辨来得淋漓尽致,不过或许,阿布拉泽想要的就是一幅关于那个年代格国乡村地景图貌,有陈腐、有挣扎,也有属于当时的人土风情。所以不必画蛇添足去痛诉时代,因为时代原本就是那个样子。
原文首发于《看电影》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