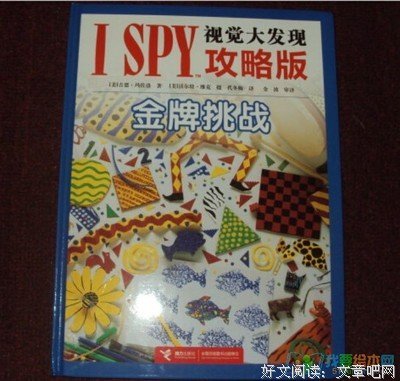《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是一本由[英]柯律格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读后感(一):第五章备忘。
虽然柯氏在文中说“丹青”是绘画最早的艺术最早的名称之一,却并不出示任何文献来帮助读者理解,我认为这是十分不妥当的做法。
“一群画论家所持对颜色的偏见,在当代艺术家中依然清晰可见。”
究竟是哪一群画论家?我不明白,是张彦远吗?还是宋徽宗吗?或者是董其昌吗?请原谅我的无知,如果不说清楚,我也不知道究竟哪一群画论家,究竟是怎样的偏见。
又柯氏的研究对象是明代的图像,并非唐代的绘画,所以我认为柯氏应该将明代画论中如何界定绘画,如何界定颜色,如何描述实际绘画的运用相关的文献列举出来,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另外五章第一页中柯氏引用了,晚唐张氏的《历代名画记》卷二 “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原文之前还有一段”夫阴阳陶蒸,万象错布,玄化亡言,神工独运。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彩。”
柯氏认为运墨五色的五色是五颜六色,但实际上这之前的描述才应该是五颜六色。而运墨五色,我理解成,墨分五色,焦、浓、重、淡、清。也就是墨只需要调制成各种程度的浓淡,就可以代替五颜六色。
柯氏又说五方,五行与宇宙学的观念,这我还是一头雾水,宇宙学究竟是哪一种宇宙学?天圆地方?
噢我太无知了,明代利玛窦已经引进的新式的宇宙学。但恕我无知,至今仍无法理解此宇宙学,是如何与老子,张彦远等一群画论家的五色观联系在一起的。
(待续未完)
《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读后感(二):明朝那些看得见的事儿
谈起明朝历史,总能引起后人的满腹狐疑。张岱在《石匮书序》里如是讽刺明史——“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个诬妄世界。”既然正史不可靠,于是,研究者自然就要另辟蹊径,纷纷跑去《金瓶梅》和“三言二拍”里挖掘明代的饮食、服饰等文化史。文化研究学者在文学文本里找到突破口,弥补了历史文献的疏漏。面对着大量艺术品存世的明代,艺术史家自然也可以如法炮制。正所谓“眼见为实”,从艺术品实物的图像意义而非考古学价值出发研究历史,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
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图像证史》一书就旨在论述关于如何将图像(images)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彼得•伯克的方法论受惠于图想学。图像学源自19世纪在欧洲美术史研究领域里发展起来的图像志研究,它所关心的是艺术品的主题内容以及题材背后延伸的深层内涵。简言之,如果说艺术史关心的是“怎么画”,那么,图像学更关心“画什么”。
柯律格(Craig Clunas)的《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和《图像证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作者从印刷术与商业的双重繁荣出发,强调了图像在明代日趋充盈的理由——印刷术赋予图像以可复制性,商业促使图像成为可流通的商品。这二者在图像制作(picture-making)层面上提供了保障,而图像从制作到流通的过程使得明代社会迅速形成“视觉经济”。在另一个维度上,柯律格也考察了明代的图像观赏(picture-viewing)。当然,这种观赏并非出自艺术的审美需求,而是文化中的心理认同机制。
譬如,张路《东坡玉堂宴归图卷》中一路贬谪的苏轼荣归翰林院,这无疑满足了怀才不遇的士大夫将仕途与抱负寄托于明君的美好愿望。又譬如,明代社交生活中礼物的赠送量急剧增多,礼物的炫示性意义波及到了盛放礼物的盒子,由此形成了漆器上的精美图案与纹饰。再如,逐渐增多的肖像画,它的形成也有诸多潜在原因。儒家文化里男尊女卑,男性处于祭祀礼仪的中心地位,祖宗肖像的出现受到朱熹《家礼》的理论支援。与之相对的是,《金瓶梅》中西门庆雇人为李瓶儿画遗像的例子暗示着,女性肖像(俗称“美人图”)充满了色情意味,成为男性注视下的欲望傀儡。此外,另一个在明代迅猛发展的图像类型就是“春宫图”。遗憾的是,对此,柯律格的描述只停留在现象层面,并未触及本质。依旧没有超越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在《秘戏图考》与《中国古代房内考》中的见解。
然而,瑕不掩瑜。无论如何,在浩繁的艺术史研究著作中,《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以图像学的研究路数令人眼前一亮。毕竟,在一个诬妄的历史话语中打捞起艺术碎片,并由此重组成为一个“看得见”的艺术世界,这不仅需要艺术史的视野,更在于作者如何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施展一套华丽的拳脚。
《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读后感(三):作为早期现代主义的明代和作为视觉文化的艺术史
Craig《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预设的读者并非我们这样的中国人,而是那些在70-80年代对于中国艺术并不了解或者西方中心主义的艺术史家。我并不清楚类似的偏见有多大,但是当时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重镇因为Cahill而在美国,并不在英国。所以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也就能容忍本书的第四章“视觉实践”,也能容忍本书的片段化写作方式。有论者说此书是若干文章的合集,倒也不假,其第七章结论部分也显得过于仓促。但是仍然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视觉文化研究。对我个人而言,其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历来我们都直到70年代以来,艺术史研究逐渐转化为视觉文化研究。但是看到的实例比较少。而结合这本书,倒是看到作者从工艺品,版画入手对照商业画和文人画构建出来17世纪晚期的视觉文化氛围。特别实在第三章穿插了章回小说,第七章穿插教会资料作为旁证。看起来非常过瘾。
其次,Craig和Jonathan一样把17世纪下半期作为一个现代主义文化的发源期来研究。这一断定有若干依据值得我们思考。人口增加与科举名额变之间的矛盾导致很多非功名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新的城市精英。而这也是文人画作为象征资本的原因。此时盛行旅游和旅游相关的出版物(《湖山圣览》),盛行对奢侈品的研究(《长物志》)也盛行对其他知识的了解作为社交圈的敲门砖(《顾氏画谱》)。游荡的城市精英、闲暇生活、炫耀式消费、文化商品都是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化的要素。
第三,Craig借用图像回路的方式非常具有启发性。图像环路(Iconic Circuits)指的是图像的循环。一种环路是由精英私人创作仅限于内部圈子。另一种环路则是由商人,匠人参与的图像公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印刷术而出现变化。在1400到1700间,中国出现了这两种环路。一个是指示性的图像,另一个是自我指示性的图像(文人画)。后来自我指示性的图像取得精英阶层的统治地位而使得两个环路越来越分离,直到最后前者被压制,而叙事性图像的叙事性几乎无法辨认。图像环路的理论来自Carlo Ginzberg。而正是这一理论架构了文人画与消费图像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视觉文化具有可能。(我当年也看见过TJ 克拉克试图比较早安库尔贝先生和18世纪版画之间的关系)而这对当代艺术的领域也会有意思。
第四,Craig对于中国图像呈现的场合比如在文人画,漆盒、屏风、瓷器之间的转换有了详细的了解和清醒,同时对图像的场合,观看的方式进行的界定(观、赏、读),并匹配英文的词汇。看似琐碎,但其实即使对于国人来说未尝也不是一个理性梳理。当把场合、礼仪混合起来的,很多图像的含义就变了。比如男女混居的场合是否意味着性诱惑,《闺中规》的版画是否满足读者的窥探癖等。一旦将“场合”作为一个变量引入图像的制造过程中,很多普通的行为就变得富有意味。比如顾氏画谱中因为印刷要求裁剪文人画面也渗透着谋着文化商品或速成文化的集体无意识。
第五,Craig 谈到色情文学导致的文人对图像的恐惧,也谈到了传教士导致的文人对西方绘画的矛盾态度。而这个态度和传教士教会描述的部一样。比如吴历皈依了天主教,但从来没有用透视和名暗画法作画,可也用这个写了不少的诗歌。由此,在结论已经开始涉及到中国人的图像观,艺术观以及诗书画关系的老问题了。这个倒是可以和维辛的《拉奥孔》做对应研究。
虽然是若干文章的集合,但是这本书确实让我们激动的看到了视觉文化在艺术史研究中的可能。而且埋下了很多点。当然问题还是有的。虽然作者提出无法用西方视觉文化基本概念对应中国,但是用下方那个现代主义的标准来套明代的现实还是让人有些不安,它势必导致是否还有“另一种现代性”存在的可能这一类的讨论。同样对于苏轼回朝这个题材的研究,作为中国人直观的说在不同图像之的穿插尚有商榷之处。但是这些仍然属于瑕不掩瑜。总的说来本书非常有启发性。
此书难以翻译,目前水平基本可以。但是责任编辑的水品就不敢说了。该书的论坛里已经列出了数处错误。我想抱怨的还有作为一个视觉文化研究的读本,为了节约成本,图文关系一塌糊涂,图片顺序及其混乱。
《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读后感(四):身份决定“物”的“品”!
——(法)布迪厄
本来买读此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物质文明所承载的美学意韵,想要的美学意韵没有找到,却意外发现了元朝解除的政治家与文人画大师赵孟頫也是“春宫画”巨匠,可以说中国的情色文字与图画消费在明朝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即是唐朝的性学专门家白行简之流的倘若穿越至晚明,那也将自愧弗如的。
关于明朝有太多的矛盾之处,没出现一个中兴之治,更别说盛世了,又以苏州为中心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市井文化与商业生产和消费极为发达。明朝初期,朱元璋为恢复秩序,限制经济要流动,目的是为了增加农业生产量,他的措施获得了成功,生产量的提高造就了进入贸易流通领域的剩余农产品,剩余农产品的经常性流通促成了从剩余生产向商品生产的过度,这就迫使朝廷慢慢的放宽对社会流动的政策限制,带来的副产品就是人口的增长。明后期欧洲,美洲,东南亚随贸易白银大量流入,朝廷又允许劳役折算为实银随税一起征收,出钱雇人服役成为普遍情况,至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成为官方正式政策,税收方式的改变有力促进了市井文化的发达和城市的发展。
最重要是在明朝科举这个学而优则仕的制度才形成完整制度,文人阶层得到进一步壮大,地方士绅阶层的形成,这些有文化的人,思想被禁锢在八股文的形式上,东厂,锦衣卫机构的进一步加大了专制制度。社会的精英只好把闲暇时间放在享乐上,商业的发达,使得这些人难以抗拒纵乐,骄奢和游惰,在字画,器物的消费上,日益开始追求时尚,许多文人一面为官宦,一面则成为某一器物的收藏者,鉴赏家等,有的具有士绅身份的人,也兼有商人身份。
许多文人也有剩余金钱和闲暇去与青楼女子嬉戏,这成为了身份,面子和地位的表现。高级艺妓此时大量出现,这为男人们提供了一个帮助女子挣脱特定的文化束缚的机会,高级艺妓具有文化修养,书法,绘画,诗歌等方面能满足男人的文化享乐。这些艺妓同时也带动了奢侈品的消费,成为了时兴服饰的最先体验者。将妓女的纯粹性关系重新塑造成一种文化关系,甚至是志同道合的金兰之交,这种重塑来自男人无力改变现实中的包办婚姻或者金钱婚姻后,在婚姻和妻妾制度之外追求浪漫的才子佳人式爱情故事中的红粉知己,因此才子佳人故事也极多。
明朝印刷业极为发达,这些不仅表现在中国古典小说与戏剧进入了巅峰期,各种刻板图画也非常发达,这是因为在晚明城市的书肆上完完全全是作为市民的文化消费品而地下的或公开的印刷出版。好书与坏书,在书商的眼中,犹如今天的光盘碟商一样,有没有利润才是衡量的唯一标准。
本书揭示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文人阶层,为了体现与社会其他阶层农、工、商区别,在物质的消费与鉴赏上,形成了能体现自己阶层独特品味的审美情趣,却又滑向一个以戏剧,园林,古玩,书画,器具为中心,只知纵情享乐,自私又堕落的景象,儒家道德体系日倾在解体。商品社会的混乱纵乐,财富的诱惑与伦理的丧落,都是通过漆器,古玩,书画,甚至春宫画等的奢侈消费品来控诉体现的。
《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读后感(五):Pictures and Visuality
《早期现代中国的图像与视觉性》(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下文简称《视觉性》)一书虽早自1997年便问世,不过新近中文译本之出版却丝毫无减其引领中国近世视觉文化研究的先锋理念。于柯律格(Craig Clunas)而言,这本章节内容看似纷杂、内里却一脉相承的著作是他多年对明代艺术关注的一次提纲挈领式总结。早期于1991年撰成的《长物志: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中,他便尝试从文震亨《长物志》为首的士人闲赏文本中对器物的鉴赏、分类语汇出发,来考察以晚明江南文士为与大众文化相区隔所建构的文化话语。另外,他在《雅债》(Elegant Debt)中同样显示出其运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来处理文徵明为中心的吴地文士社交网络。虽然在早期写作中,柯律格便致力于将文字中趋于理想化的晚明士人形象还原到当时更为宏大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但是《视觉性》标志着他以此为分水岭,从文氏家族、李日华等士人的书写文本,开始投向在明代社会流通更为广泛的流行文化。在2007年出版另一部讲座论文集《大明帝国》(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即是在此基础上的一次深化与案例分析。
柯律格在第一章导言指出:“所有的物质文化都包含视觉成分,而任何一种的视觉文化都依赖物质性的存在。我认为物质与视觉文化是无法分离的。”柯律格将中国器物所蕴含的物质与视觉文化的兴趣与其长期浸淫于博物馆的工作经验不无关联。目前方兴未艾的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研究把一切与“看”的行为有关的物品(object)都作为研究对象(subject),既包括被看之物,也包括观看主体以及与视觉相关的话语权(discourse)。柯律格认为艺术史家所处理的主题不应“自说自话”,应具与历史对话的延展空间。艺术史之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或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都源自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降对二战之前德奥传统的“内向化”艺术图像之风格与形式分析所形塑的相对自给自足的空间的一种反省。在“新艺术史”与文化史碰撞之下,社会艺术史(亦被称为“左派思潮”一支)与视觉文化研究自此应运而生。这两种新的处理艺术/视觉物品的视觉都摒弃以往艺术史闭门造车的尴尬局面,结合跨学科研究成果与理论之余,对艺术对象的处理同样不拘泥于形式分析(线条、色彩、构图等),关注这些“文本”(text)所呈现的单方面或多方社会力量操作的特殊观点,如何建构出为社会所普遍接受或相应改造的事实,这种话语权背后折射的意识形态塑造、人心同化的作用。正是在此要旨之上,英国率先掀起了视觉文化的研究浪潮。柯律格在开首针锋相对的布列逊(Norman Bryson)即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然而,在提及此书与“视觉文化”的关联之时,柯氏却陷入一种悖论矛盾中:一方面他在导言中澄清此书并非旨在明代视觉文化,但话机一转又承认自己受到相关范式的影响,所处理的议题涉及其中一部份。他以检验“明代视觉性文化”(Ming culture of visuality)这一含糊的词来代替“视觉文化”简易标签,以避免将原有产生自西方母体内赋予的学术定式移植到中国研究后产生一定预设观念。
通常而言,艺术史作为广义上历史研究,其思潮同样有“上下”之别——“精英的”与“民间的”、有“左右”之隔——“激进的”与“保守的”、 有“远近”之论——“宏观的”与“微观”的、有“虚实”之异——“思想的”与“物质”的、有“内外”之分——“内容的”和“形式的”。作者试图在本书中打破上述二元观念的界线,在本书中“处理了明代规模庞大的图像制作以及图像观赏活动中的某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向来不为正统的中国艺术评价体系所重视的“工艺美 术品”和“具象艺术”。如果说以文人画为代表的纸上“绘画”(painting)是传统上研究明清艺术史的核心,明代世界中充满的“图画”(pictures) ——墙上的、纸上的、书本中的、过年时门上贴的、信笺和契约文书上的、瓷碗上的、屏风上的、漆器上的、衣物上的——则长期处于主流之外,而柯律格“要关注的正是此类数量更大的‘物品上的图画’。”从中西比较角度切入来探讨明代的图像问题,这涉及到内核的“现代性”(modernity)议题,然而分析材料与作品材质的转换也会为行文叙事带来相当程度的跳跃性。因此,诚如作者所言,“与其说是一部专著,不如说是一组互相关联的文章。”
开篇中,柯律格便引用了英国新艺术史作家布列逊关于中西方“展演性”(extensive)和“泯除性”(erasive)比较性笔法的理论。后者的观点承接的是西方一直以来对于中国绘画中具象艺术的再现(representation)特质的缺席。从社会史入手,柯律格指出了在17-18世纪时中西在艺术市场上的表现及其语境的相似性,如明代的南京和同时期的荷兰阿姆斯特丹、意大利等巴洛克绘画市场都是同样的活跃。另一方面,他进一步指出这一种关于中国艺术笔触“毫无生气”的论断之所以延续至今,也和早期的西方艺术史学者(包括喜龙仁、索伯等)以文人画研究为中心,受到明清传统文人追求写意“墨戏”的书写话语影响。为重蹈前人研究中的“陷阱”,柯律格尝试在书中将明代文人所试图掩盖或故意避免的大众图像呈现出来。
在第二章,柯律格以唐宋公共寺观壁画在明代的衰微以及同一时期印刷文本图像的勃兴及对前者的取代来说明图像展示所呈现的公共与私密空间。有明一代,大型壁画作为精英群体与公共性质的图绘走向式微,而印刷出版物的大规模兴起带动了新型的视觉趋向,这一特征在作者眼中显示出明代突显出中古社会少见的平等性和私密性。书籍的插图满足了下里巴人、粗通文墨者的视觉享受以及观看欲望,经济和贸易的发达也使图像成为主要的奢侈消费品,虽然如文震亨之流的精英群体对此种具象艺术甚是不屑一顾。对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颇为熟稔的柯律格在此借用了一组概念。首先是来自沙蒂耶(Roger Chartier)的“挪用”观点,即精英的绘画惯例可以被更加广泛的读者群所挪用,这个概念拒绝以所有者、制作者或消费者的社会地位为依据来限定个体物品及其具象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用以调和“精英”“大众民间”二元对立。第二个概念是“图像环路”(Iconic circuits),意指一套具象艺术的体系,其中某类特定图像在涉及图绘的不同媒介之间流通,这个概念为图像的交换、移动以及传播过程提供了一种隐喻。柯律格独到地提出,在1400-1700年间明代视觉性文化通行着两种在不同材质、媒介间流通的“图像环路”(iconic circuits),其一为指示性图像(referential picture),偏向于公共空间;另一为自我指示性图像(self-referential picture)——主要体现为文人画形式——由文人为首的上层精英文化所垄断。诸如“苏东坡荣归翰林院”一类的“指示性图像”,在当时通过印刷、拓片、粉本、谱子、口诀等方式得以流通;《西厢记》那样的通俗故事图绘,更是通行于多数的图像介质之中。柯氏还提醒读者关注物品与场合使用的关系,他借用了人类学的“礼物”概念,指出婚嫁、寿诞、生子这类的过渡仪式事件,皆有适用于这些场合的物品,物品上有表现相应图像学主题的视觉形式。在中国的艺术评价体系中,出于画匠之手的“园景画”和“祖宗画像”是上不了台面的,而柯律格将明代的这类图像信手拈来,分析其社会功能和欣赏习惯:“园景画”有可能是为了满足旅游市场的需求,“祖宗画像”是礼仪所需,还有一些“名人肖像”,是为了满足大众对于名人的“窥视癖”。至于春宫画,上层和精英试图对其加以防范和控制,可是它在民间各阶层的流传却如火如荼。这种大众与精英图像之间的框架对于笔者建构关于晚明文士对雕漆的“雅俗之辨”有较大的启发。
通过两条图像环路的阐释,既反驳了西方早期对于中国绘画“了无生气”、毫无叙事性可言的看法,也让我们看到图像在不同材质间的流通以及在明代社会发达的技术生产背景下的图像文化。在第三章中,柯律格以《三才图会》作为一个案例来分析流行图像回路的散播。《三才图会》又名《三才图说》,它是由万历致仕陕西给事中的王圻及其儿子王思远合力编撰的一部百科全书式日用类书,成书于明万历年间。从这本充斥流行通俗观念的图像中涵盖代表“天”(heaven)的星象图、描绘地理状貌(earth)的地理图、景观图到关于“人之知识”(humanity)的肖像图的分类,柯律格转而延伸到对于这一类“图像”的语汇分类和“考古学”,来勾勒出明代中后期所特有的一种延展至多个社会阶层的知识观念体系是如何通过图像来呈现并实现自我强化的。
“画”(paintings)、“图”(pictures)、“像”(portraits)等词语的分类在有明一代人士眼中,除了先天的“临摹具象”“非具象”的对应关系外,还有代表后天的“雅俗”“私密-公开性”间的区分。从“看”(see)、“观”(contemplate)、“读”(read)等观看图像的语汇分析中,柯氏进而提出了一个关于观看艺术的主体性问题:即中国人是否是以自身观画者的基于主体性认识论基础上的一套思维方式。对于这个问题,他通过明代木刻画谱《顾氏画谱》及其制作者的历史考察,指出顾柄对于自己所认可的大师的摹本,把绘画作品的知识和如何作画的知识分离开来,对知识体系进行重组。在作者论述之中,与本雅明(Benjamin)的马克思技术决定观点不同的是,顾柄的“机械复制”具有主体性再创造的痕迹,并无历史证据的“灵晕”。
在尾章部份,柯律格的图像环路主线与中西比较这条暗流合二为一。对于利玛窦等传教士引入的西式绘画,有明一代各阶层各有不同看法:从文中分析材料中,可以得知在朝廷与文人士大夫等“上流精英”心目中,这种栩栩如生的具象艺术有悖礼仪,被视为奇技淫巧;大众对这种“栩栩如生”啧啧称奇,商人也将其挪用以牟利,但是透视技法始终为社会的主流趣味所拒斥,这对“西方主义”亦是一个挑战。从而引起“图”(公开性)、“画”(私密性)之争。在柯律格看来,“‘画’在明清中国首先是一个关于图像生产活动的话语对象,并非是一个有固定界限的范畴。它的构建是一场持续竞争之所在,重新肯定与否定,一整套命题皆意在强调其与‘图’之间的差异,而‘画’时常面临与‘图’相似的危险。”
与以往偏向于从晚明士人为首的精英文化(雅士品味)视角出发有所不同,《图像与视觉性》对中对明代视觉性研究更加着眼于流行文化(通俗图像)一端,柯律格对于社会史中“高”与“低”的取舍无疑是对近世中国现代性所体现的大众文化之崛起埋下一个很好的脚注,其立意令人钦赞。但鉴于篇幅、材料的庞杂与中西在“早期现代性”对比上的复杂性,作者显然无法在文中完全解决所有问题。另外,过于强调“图”“画”的对立似乎难以呼应其立意核心——中国人创作绘画是基于自身主体性,鉴赏图像也是从观者本身出发的。作为一位“他者”,对中国观看文化上引入一系列的西方学术概念,来试图证明研究对象的“主体性”,除易于落入先入为主之嫌,还很可能产生一种先天悖论。
《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读后感(六):史家的艺术之眼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中国展厅,挤满了黄皮肤的小学生。女老师的汉语很标准,飘到耳中一句,却是《论语》里的“父母在,不远游”。我仰头一望,是了,这里有两轴硕大的祖先画像,一男一女,面容端肃,正襟危坐,袍服鲜明。本该是祠堂里的物事,具有仪式化的功能,如今被从语境中抽离出来,悬在这局促而黯淡的空间里,简单图解着什么是“孝道”。
这祖先画像,在《红楼梦》里是被称为“遗真影像”的。第53回贾府祭祖,先写腊月开始布置祠堂,“开了宗祠,着人打扫,收拾供器,请神主,又打扫上房,以备悬供遗真影像”。这里的“神主”是木制的祖先牌位,是要供于祠堂里的;而“影像”是纸质的祖先肖像,是要挂在正堂上的。除夕傍晚一切布置妥当,祠堂“里边灯烛辉煌,锦幛绣幕,虽列着些神主,却看不真。”正堂上“影前锦帐高挂,彩屏张护,香烛辉煌;上面正居中,悬着荣宁二祖遗像,皆是披蟒腰玉;两边还有几轴列祖遗像。”祭祖仪式又分两个部分,先是祠堂里祭祀神主,由贾敬主祭;随后是正堂上拜影像,由贾母主持。最后,到正月十七,再次行礼,掩了祠门,收了影像,才算祭祖仪式结束。
英国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 1954- )的《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1997)在2007年出美国版时,封面用了一张男女并列的祖先画像。这次中译本出版,内页有布拉格国家美术馆收藏的类似的一幅。虽然前者是官服、后者是常服,但画面居中都有一个小几,上有神主、花瓶香炉等等,使画像具有了“仪式套着仪式”的特点:他们生前也曾供奉祖先,如今子孙供着他们的影像,显示的是“孝”的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颇为有趣的是,“在明代的祖宗之礼中,这类画像的正统地位不甚稳固,但还算受人尊敬;它们绝非必要,但为多数论者所容忍。”保守的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家礼》中认为,男子有画像,用之无所谓,而女子在画工面前抛头露面,“殊为非礼。”一般论者不似朱熹这么关注“男女大防”,因此对这类画像颇为宽容。至于民间,则有五花八门的态度。例如《金瓶梅》第63回,李瓶儿死后,西门庆叫来一位韩画师,“我心里疼她,少不得留个影像儿,早晚看看,题念她题念儿。”一轴大影、一轴半身,西门庆付给画师一匹缎子、十两银子。为了追求“逼真”,韩画师“非礼”地看了李瓶儿的遗容,画出的影像比活人“只少口气儿。”又如《醒世姻缘传》第18回,浪荡子晁源为去世的父亲安排画像一事,许给画师二十五两白银,要求画三幅,一幅朝服、一幅寻常冠带、一幅公服,晁源对画师说“你不必管像与不像,你只画一个白白胖胖、齐齐整整,扭黑的三花长须便是,我们只图好看,哪要他像!”最后,画师按照文昌帝君的样貌画了出来,皆大欢喜。这两个不同的文本里,西门庆是为了“题念”爱妾,为此追求画像效果的逼真性,李瓶儿的身份并非正妻,即便画了像也入不得祠堂,所以最后只称为“美人图”。晁源与西门庆不同,他是为了礼仪需要而请人绘制父亲遗像,死者的“社会性躯体”比“个人性躯体”远为重要,所以象征着社会地位的衣饰细节比容貌的逼真性更能引起他的重视。柯律格敏锐地指出:“我们所面对的肖像画,对其最重要的是观者如何接受这些画像,上述段落展现了肖像画的另一个领域,在此画像并非作为礼仪中产生效用的一部分,而是作为被展示的视觉文化的一部分。”
20世纪至今的西方艺术史研究可谓山门林立、流派纷呈。芝加哥大学美术史论系教授詹姆斯•艾尔金斯(James Elkins)将1970年以来的西方艺术理论划分成8个运动17种派别。我国学者曹意强则言简意赅地指出,无论艺术史家在观念上的差异多么重大,大略而言,他们的侧重点只是在构成艺术史的两个要素之间移动:“艺术”和“历史”,有的向“艺术”倾斜,有的向“历史”靠拢。1999 年,一次著名的国际会议干脆命名为“两种艺术史:博物馆与大学”,以博物馆为基地的“专家”关注的是“艺术”,包括作品鉴定、归属、分类、修复、整理相关文献的问题;而以大学为基地的“史家”更注重“历史”,侧重于对形式、内容、历史情境的解释与说明。这两类研究者之间时常发生冲突,甚至相互轻视。如果将柯律格教授放入这个框架中加以考察,当会看出他由“博物馆”走向“大学”、由“专家”而“史家”的研究路径与特色。
柯律格教授是苏格兰人,先后在剑桥大学东方研究院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学士(1977)和博士学位(1983),他主修汉语与汉学,曾于1974年来北京语言大学进修中文。从1979年开始,他在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中国部当了十五年馆员和策展人。该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的中国工艺美术作品,柯律格浸淫于此,磨炼眼力,对木器、漆器、玉器、瓷器均有心得,陆续出版了有关中国园林、外销画和家具的书籍。在一次访谈中,他坦陈,由于整个大学期间都在与语言搏斗,对理论无暇顾及,直到在博物馆工作时接触到布尔迪厄等理论家的学说,始有豁然开朗之感。从此后,柯律格注重运用文史互证的方式,并从人类学和社会学中汲取营养,依照社会脉络与历史情境来进行研究。1991年出版的《长物志: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是他第一部成熟的作品。该书出版后,高居翰写信祝贺,说一位博物馆策展人能够写出这样的一本书令他十分惊喜。1993年,柯律格到芝加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并在该校出版的《艺术史的批评词类》中负责“艺术社会史”一章的撰述,想来对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深有会心。1994年他任教于苏塞克斯大学艺术系,三年后晋升为艺术史教授。2003年,他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聘为中国与东亚艺术教授。2006年荣膺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称号。2007年起任教于牛津大学艺术史系,并成为该系首位以亚洲艺术史为专长的系主任。
从艺术史的学理上看,柯律格的研究可归于“艺术社会史”之列,也就是强调艺术作品影响社会环境同时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关注艺术、社会与政治之间丰富的交互作用。如果说,通常的艺术史与整个史学大潮一致,有“上下”之别——“精英的”与“民间的”、有“左右”之隔——“激进的”与“保守的”、有“远近”之论——“宏观的”与“微观”的、有“虚实”之异——“思想的”与“物质”的、有“内外”之分——“内容的”和“形式的”,那么“艺术社会史”则试图打破上下、左右、远近、虚实、内外的重重隔阂。不仅如此,柯律格的“艺术社会史”同时也是“物质文化史”和“视觉文化史”。“物质文化”是美国人类学界开始的研究方法,与“日常生活”高调唱和,又与“视觉文化”暗通款曲,柯律格指出:“所有的物质文化都包含视觉成分,而任何一种的视觉文化都依赖物质性的存在。我认为物质与视觉文化是无法分离的。”目前红极一时的“视觉文化研究”是把一切与“看”的行为有关的东西都作为研究对象,包括观看的对象,也包括观看的人,还包括运行在观看行为背后的制度环境与社会力量。在给中国读者的《前言》中,柯律格指出:在写作《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之际,“英语国家的艺术史学界正热衷于‘视觉文化’的讨论。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围绕以下问题,即有哪些物品或是哪一类图像,此前不被重视,而今却应纳入新近得到扩展的艺术史研究中去。因此,本书以‘图绘’(pictures)这一范畴来连接绘画作品和印刷作品以及诸如陶瓷或漆器这类物品上的图像(images),这可视为是对那场论争的一个贡献。”
柯律格在本书中“处理了明代规模庞大的图像制作以及图像观赏活动中的某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向来不为正统的中国艺术评价体系所重视的“工艺美术品”和“具象艺术”。如果说以文人画为代表的纸上“绘画”(painting)是传统明代美术史的中心,明代世界中充满的“图画”(pictures)——墙上的、纸上的、书本中的、过年时门上贴的、信笺和契约文书上的、瓷碗上的、屏风上的、漆器上的、衣物上的——则长期处在冷宫之中,而柯律格“要关注的正是此类数量更大的‘物品上的图画’。”
有明一代,大型壁画作为精英群体与公共性质的图绘走向式微,而印刷出版物的大规模兴起带动了新型的视觉文化,这一文化突出了平等性和私人性。书籍的插图满足了粗通文墨者的视觉享受以及观看欲望,经济和贸易的发达也使图像成为主要的奢侈消费品,虽然文震亨之流的精英群体对此种具象艺术甚是不屑一顾。对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颇为熟稔的柯律格借用了一组概念,首先是“挪用”,精英的绘画惯例可以被更加广泛的读者群所挪用,这个概念拒绝以所有者、制作者或消费者的社会地位为依据来限定个体物品及其具象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第二个概念是“图像环路”,意指一套具象艺术的体系,其中某类特定图像在涉及图绘的不同媒介之间流通,这个概念为图像的交换、移动以及传播过程提供了一种隐喻。柯律格指出,在1400-1700年间中国出现了两种环路,一个是指示性图像,一个是自我指示性图像,由于后者——即今日所说的“文人画”——在上层文化中取得了霸权地位,致使前者被历史所遗忘。诸如“苏东坡荣归翰林院”一类的“指示性图像”,在当时通过印刷、拓片、粉本、谱子、口诀等方式得以流通;《西厢记》那样的通俗故事图绘,更是出现于几乎所有的介质之上。柯律格还提醒读者关注物品与场合的关系,他借用了人类学中的“礼物”概念,指出婚嫁、寿诞、生子这类的日常生活事件,皆有适用于这些场合的物品,物品上有表现相应图像学主题的视觉形式。在中国的艺术评价体系中,出于画匠之手的“园景画”和“祖宗画像”是上不了台面的,而柯律格将明代的这类图像单拈出来,分析其社会功能和欣赏习惯,“园景画”有可能是为了满足旅游市场的需求,“祖宗画像”是礼仪所需,还有一些“名人肖像”,是为了满足大众对于名人的“窥视癖”。至于春宫画,上层和精英试图对其加以防范和控制,可是它在各阶层的流传却如火如荼。
作为一个西方学者,柯律格能娴熟地“挪用”西方理论概念,但可贵的是,他始终有一种自觉,也就是时时关注不能被简单套入西方模式的中国实际。比如,在一个印刷术主导的“机械复制的时代”,明代出现了《顾氏画谱》这样的出版物,它是“想象的摹本”,是对图绘的重组,它的存在可以对本雅明的理论提出质疑。又比如,利玛窦等传播的西式绘画在中国的遭遇十分复杂,大众对这种“栩栩如生”啧啧称奇,商人也将其挪用以牟利,但是透视技法始终为社会的主流趣味所拒斥,这对“西方主义”亦是一个挑战。总体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文人画家在作品中远离了一切有叙述意味的题材,假如“视觉的去叙事化”被福柯等人视作“现代”的特征,那明代画家岂不是早已进入了“现代”?
自然,本书并不是完美之作。首先在结构上,全书由七章组成,“与其说是一部专题论著,不如说是一组互相关联的文章。” 其次是篇幅上,以不到20万字解决如此一个宏大的主题,显得论证不够充分。最后是一些概念难以厘清,第四章虽然试图解释“图画”(pictures)、“绘画”(painting)、“图像”(images),以及“观”(viewing)、“看”(looking)和“欣赏”(appreciating)之间的关联与差异,特别是中英文对译,可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致柯律格本人也在前言中承认过于强调“图”和“画”的区别了。基于此,柯律格的雄心之一——证明中国的认识论是以认识者为中心的、中国的视觉文化是以观者为中心的观看——也就显得功亏一篑。不过,正如柯律格的其他著作,本书那些“纷然而独具的细节”、以及那些信手拈来的框架与概念,总会令人激赏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