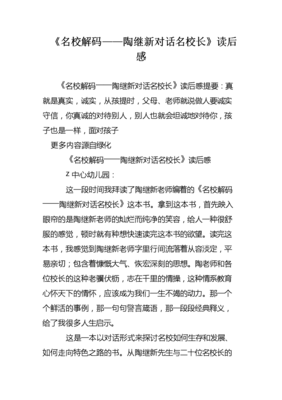《最后的对话 Ⅰ》是一本由[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 [阿根廷] 奥斯瓦尔多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4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后的对话 Ⅰ》读后感(一):读了,感觉到了,也就懂得了
《最后的对话》文/文小妖
“我既不为少数人写作也不为多数人写作,而是每当我感到有些东西需要表达出来时,我便提笔写作。”关于写作,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曾如此说道。这位阿根廷最杰出的诗人、小说家兼翻译家如同一位神秘而又极具魅力的思想巨人,洞悉着世间一切,他的作品曾经影响了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的先锋派作家。同时,这位极具非凡影响力的作家也令中国的许多作家为之着迷,比如余华、格非、苏童和马原等国内知名作家。纵然如此,未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博尔赫斯是心中的一道隐痛,为此,他一生都耿耿于怀。
最近,阅读新经典新出版的博尔赫斯和阿根廷作家奥斯瓦尔多·费拉里的经典对话集《最后的对话》,对这位被誉为作家中的考古学家的作家又多了几分了解。
对话集中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了方方面面的内容,关于政治、宗教、哲思和阅读等方面。每一个话题中,都融合了博尔赫斯的精准解读和思想的凝结,他毫无保留地与奥斯瓦尔多·费拉里进行深度探讨,幽默中透着睿智,见解中透着广博,让读者感受到其魅力的同时,也能从这些谈话中找寻到一种思考的导向。
较之博尔赫斯很磨人耐性的小说而言,《最后的对话》显然读起来相对要轻松很多。博尔赫斯的思想如同行云流水一般,每一朵泛起的思想浪花里都带着哲思和智慧之光。他谈及家乡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自己的身份,把历史、现实、文学和哲学融为其中;他谈及地理与内心的南方时,却能明澈的倾吐出自己的写作方向:试图忘掉过去,将自己投射到未来而活。从写作方向上升华到一种睿智的生活态度;他谈及爱,深刻而深情,从肉体到灵魂,再上升到一种广博的洞见,源于他对这世间的一切报以极大的热忱和爱……他关心人类的状况,更关心人的灵魂与思想,他与奥斯瓦尔多·费拉里的每一次的谈话,总能让人心里激荡起各种大大小小的涟漪,产生一连串有趣的连锁反应。我想,这大概就是博尔赫斯的魅力吧!
很多人都觉得博尔赫斯的作品并不好读,线头多而纷繁,对词汇的运用极度苛刻,尽可能的精确到位。读他的作品容不得一目十行,只能老老实实的一字一句进行解读,当然,如果读完了,读通了,整个思想境界又会上了一个新的层次。记得苏童在谈及年轻时读博尔赫斯时曾写到,“坦率地说,我不能理解博尔赫斯,但我感觉到了博尔赫斯。”我想说的是,读了博尔赫斯的这本《最后的对话》,除了能感觉到博尔赫斯,至少或多或少也能理解博尔赫斯!
《最后的对话》《最后的对话 Ⅰ》读后感(二):《最后的对话》译后记 陈东飚
博尔赫斯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我的第一本译作(尽管不 是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是《博尔赫斯1923-1967年诗选》,那本书 是以博尔赫斯一生中最初写下的篇章开始的;而我迄今为止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此时此刻在为博尔赫斯最后的对话集(我们已经看到博尔赫斯也将其视为一种写作)写译后记。翻译博尔赫斯的时间也就是我的整个翻译生涯的时间,连我都为这种作者-译者的对应而略感吃惊。
不过我马上意识到了我的错误,事实上这种对应并不存在。真正与作者对应的不是译者而是读者,译者仅仅是读者之中无关紧要,或毫无意义的部分。尽管我也曾经是其他一些作家的译者,但我无法自称为他们的读者。我相信人人都会同意,花几天时间读完了一本书并不足以让一个人成为这本书的读者,而译者仅仅是把这几天拉长到几个月或几年而已。读者的时间不是这样计算的,他的时间是心理时间,是他真正打开一本书的时间。作为一个阅读量很少的人,我发现我仅有不多几本真正打开的书,而其中若干本在一二十年前就已经被我合上了,因此读者这个词通常来说离我很远。只有在说到博尔赫斯的时候,我才有胆量说我是博尔赫斯的读者,甚至我的一个网名也是由此而来(可见博尔赫斯的读者是我为自己设定的身份之一),我是译者这件事则纯属偶然了。
因此在博尔赫斯与我之间真正有意义的是作者-读者的对应:作者的写作与读者的阅读之间的某种重合(如同我在本书第一卷的译后记中所提到的“共时”)。这种对应存在于所有的作家与他们的读者之间,不同的是博尔赫斯始终将自己视为一个读者:一个接近于原型的读者,仿佛阅读了一切的读者;而上述的对应让我在阅读博尔赫斯的时候也变成了这样一个原型的读者。换句话说,这是一 种双重的对应,博尔赫斯的读者与博尔赫斯这个作者/读者的重合。 这或许解释了博尔赫斯对于我的特殊意义:阅读博尔赫斯仿佛就是在阅读博尔赫斯读过的书籍,阅读所有的书籍,并通过这一接近原型的阅读行为来创造一个世界,成为作者(顺便说一句,“作者” 或许是博尔赫斯的El Hacedor最贴切的翻译,而不是“创造者”)。
我不知道别的博尔赫斯读者是否也有同样感觉,我不知道别的作家是否也能提供这种感觉,总之我的阅读世界是贫乏的,但我有博尔赫斯这个“阿莱夫”。像故事的主人公一样,我着迷于这无限的一点—阅读博尔赫斯—时间与空间汇聚于这一点,并由这一点铺开,成为博尔赫斯的每一首诗,每一个故事,这本书里的每一段对话。
以上对博尔赫斯故事的套用或许过于夸张,但我只是描述我的感觉,那种近乎原型的纯粹愉悦:无限的事物才可以如此单纯,即使重复也丝毫不减其效力。我发现这本对话集里谈论的主题都是博尔赫斯在他的所有著作里早已谈论过的,而博尔赫斯也从不讳言它们的来源。博尔赫斯关心的事物,在耄耋之年依然与青年时期一样,也是人类最初的思想者关心的事物:时间,星辰,梦,生命,勇气,怀疑,智慧与不可知,等等,其中也不乏我们孩提时曾经想过的东西,对于博尔赫斯来说这些是真正有意义的事物,无限向他呈现的东西。我相信博尔赫斯之所以打动我们,也正是因为他呈现的是这些原初的事物而不是别的更新奇或深奥的东西。它们汇聚在博尔赫斯这里,不存在空间与时间的距离,“史诗的味道”就像口中的水果一样真实而令人感动,斯威登堡也像楼上的邻居一样近在咫尺。
对话让博尔赫斯的对话者领略到了这一切;继而通过阅读,即前面所说作者-读者的对应,这种原初而无限的感觉也为我们所有。我们置身于博尔赫斯所在的时空之中,像博尔赫斯一样对遇到的一切熟悉而又惊叹—阅读本书的意义和乐趣大概就在这里吧。
在本书第一卷的一段对话中,博尔赫斯主张卡夫卡已经是人类记忆的一部分,“一场可怕的诉讼,不断延长,直至无限”,必将成为不断再现的主题;那么,在博尔赫斯之后,人类的记忆是否更丰 富了一点呢?化身为作者/ 读者,将无限时空中的人与物汇聚于一 点(一个幻象,一座迷宫,一个梦中之梦,一局棋,一本书),加以观照并与之对话—我相信这就是今天人们共同拥有的,名叫博尔赫斯的记忆。
陈东飚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最后的对话 Ⅰ》读后感(三):不可盲目崇拜,但可以盲目崇拜博尔赫斯
一
经过了数十年的文化饥渴,八十年代终于迎来了知识热,无数的海外作品被译介,进入中国文化圈。回想起来,当年的书首印几十万册,只是一个常规印量。中国读者开始疯狂的阅读、研究、学习。
这其中,有两位拉丁美洲作家赢得了崇高声誉,写作圈几乎人手一本,一位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其《百年孤独》的盗版神话终于在千禧年后被新经典收复;另一位是来自阿根廷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为什么要说是“写作圈几乎人手一本”?因为博尔赫斯是作家中的作家。
二
作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作家,一种是作家中的作家。前者是被广泛接受、认可、阅读,甚至赢得了上百年的经典地位。但另一种作家,他开辟新的写作理念和实践,他启发更多的作家如何去写作,他传递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惊讶:“原来还可以这么写!”
而对于更多的读者来说,博尔赫斯作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代表人物,所带来的还有更加广泛的意义。20世纪上半叶,文学的中心在欧洲,有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稍晚一点是萨特和加缪,等到了20世纪中后半叶,文学的中心已经到了拉丁美洲,是博尔赫斯、聂鲁达、马尔克斯、略萨、科塔萨尔,晚一点,还有波拉尼奥。
三
“这个人,这个作家,这文学的精灵,那些只知道他作品的人,现在可以认识这个作家,认识博尔赫斯这个人、他创造的事物下的理念……”读过了太多博尔赫斯的小说、寓言、诗歌,现在,终于有机会领略他的长篇访谈《最后的对话》了。
本书来自于奥斯瓦尔多·费拉里与博尔赫斯在一九八四年做的一档电台对话节目,费拉里是阿根廷作家的后起之秀,博尔赫斯已是八十五岁高龄。按照不同的谈话主题,本书涉及到了博尔赫斯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博尔赫斯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本书便是关于百科全书的全面注释。
四
一个原因大概是失明吧,即使看不见也要感受那些国家。再者,假如我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呃,我的生活是……很糟糕的,我必须不断地想故事……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读者来说,当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首先会想到博尔赫斯那本著名的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如诗中所传递的饱满情绪,我们一遍遍地想象诗人的状态……多少年过去了,当博尔赫斯垂垂老矣,虽然仍对世界抱以好奇,四处旅行,坚持写作,但他坦诚地说出了“呃,我的生活是……很糟糕的。”
重点是这个省略号,难以想象博尔赫斯到底省略了什么,关于他的生活的苦楚,我们所知甚少。从这本书的开头,博尔赫斯的令一面慢慢显露出来。
他谈到了自己的衰老:
一个人活到了八十四岁时,他就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是往生之人了,能够被人爱戴而且没有很大的风险,不是吗?没有太多的不适,这或许正是衰老的形式之一。所以,当被问及博尔赫斯的“篇幅”,往往是一页多一点,极度凝练,他坦诚又不失幽默地表示:
实际情况是我很懒,写不了更多,大概是吧?我很快就会疲倦,于是这就被称作简介了(两人都笑了)。但我真的耗尽了自己。这可能是关于博尔赫斯语言风格的最有趣的回答。笑过以后,“我真的耗尽了自己”,又让人感到了深刻和痛苦的一面,那是写作一生,获得世界性声誉之后,年迈作家的真心吐露。
还有一点可爱之处。博尔赫斯聊到“一个作家几乎预知了——他将会在自己国家的文学史册中占据的位置。”话音刚落,费拉里马上调皮地咬住问,“您又会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这个时候了,哪怕是前面所言,八十四岁可以没有风险地被人爱戴了,但他还是避而不答,丝毫不敢美誉自己,转而开始谈历史。
更多的,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仍能够感觉到博尔赫斯作为诗人的特质,他谈论了很多词,每次都会分析词源,谈论了很多句子的修辞,以及完美的节奏。本书同样也是一部大作家的文学史课,汪洋驳杂,观点犀利。
最后引用一句书中出现的句子:
“要不是有人告诉我这是爱,我会以为这是一把赤裸的剑。”博尔赫斯说道,这是一个完美的句子,超越了比较,超越了将爱的概念与剑的概念相混淆的隐喻。这是对于爱情之痛的完美表达。
《最后的对话 Ⅰ》读后感(四):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20世纪的西班牙文学里,大概无人能与博尔赫斯比肩,20世纪的世界文坛里,博尔赫斯亦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而我们谈论博尔赫斯时,绕不过他新颖奇特的创作风格。在一个起点到一个终点的直线叙事的文学时代,他创作的表达方式跳出了写实叙事的传统窠臼,成为“叙事形式的反叛者”。他开创性的叙事架构着实启发了世界上太多的文学作家,包括苏童、余华、格非等中国先锋小说作家,让他们意识到原来文学可以一环套一环,可以把现实与虚幻、真实与虚构、叙述与评论融为一体。
博尔赫斯文字饱含思辨性和哲理性,复杂又纠结如坠迷宫,所以他的作品,对一拨人是毒药,令人深深迷恋不可自拔,对另一拨人,则会被作品的烧脑不适敬而远之。其实,当我们谈起他独特的写作形式时,他为他人撰写的序言也容易成为谈论主题。他把对文学的热爱和对作家的热爱更多地表现在序言里,为青年作家或尚未知名的作家康概作序。尽管依然是维持着“烧脑”的高水准,像之前整理出版的《序言集》因极其庞大的信息量就被读者评论看不懂。能稍微轻松阅读的似乎只有他的对话集了,平实、清晰、明确,却丝毫不会遮掩他渊博的学识。而众多对话集中,《最后的对话》更为珍贵。这本可以当成是博尔赫斯向世界发出的最后的声音,算是遗作。
这本对话集的起源,是阿根廷国立电台为博尔赫斯策划的一档对话节目,与之对话者是深受博氏影响的拉美文坛后起之秀——奥斯瓦尔多·费拉里,节目长达三年,1984-1986,正是博尔赫斯生命最后的三年,直到他肝癌逝世终止。博尔赫斯家族有遗传性眼疾,父亲在他中学时完全失明,对话中的他也早已失明。于是我们能想象,一位被荣誉环绕的著名作家,一个失明的八十多的老人,在这次与生命并肩行走的对谈中,流淌出太多智慧,碰撞出太多强烈的思想火花。
如果说“他的散文读起来像小说,他的小说是诗,而他的诗歌又往往让人觉得像散文,沟通三者的桥梁是他的思想。”那么像这样对话集就是他思想的直接输送。文学、诗歌、宗教、绘画、哲学、写作等等各个领域的话题纷至沓来。他谈失落的阿根廷文化或东方哲学,谈伏尔泰身上某种蛇性的东西和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细数爱尔兰文学里的伟大作家们,忆起童年遇到的诗。完全不同于故事里那些复杂的隐喻,对话随心而动,随意而说,还时而跑题。前一秒才聊起克维多写作的品质,后一秒就开聊到印度转世的观念,跑题情况发生后往往是由费拉里拉回主题。记得当谈起自己新诗集时,博尔赫斯扯开对话内容,面对费拉里执着地重拾主题,只能笑道:“其实我寻找题外话就是为了不谈论我的书。”这出现在书中特别愉快的一幕,让我觉得这位作家在创作这“难懂”的作品的时候,还是保持着一个老人可爱和简单的天性。
当然,博尔赫斯的眼睛是难以避免的话点。他曾追寻过天堂,他说“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看不见后,他被重新任命为国家图书馆馆长,被九百万本书所环绕,却一本也无法阅读,只能嘲讽“上帝以如此绝妙的讽刺,同时给了我书籍和失明。”但八十多岁的老人不再有年轻时的心态,不再写“世界很不幸,是真实的;我很不幸,是博尔赫斯”此种悲怆的诗,他说:“一个年轻人,或许对生活有太多期望,他关注的主要是幻灭之处,在他心里首先是失望。反之,如果是一个老人,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感激。尤其是我,因为超越了失明这个身体的意外,是人们对我的热情接纳。”他对所有人的支持和包容都充满感激。
这位老人还坦言:“我以前经常写东西攻击别人,现在不这样了;我很久没写过一行对抗性的,或是稍微有敌意的文字。我相信那毫无用处。”可能岁月改变了他,爱与幸福的感受抵挡了他一生的跌宕,然后他全新的感受投射进对谈中,使得深邃的哲理,过人的才智流露之间,更加温和亲切。
实际上博尔赫斯抛开失明,也并没有一个美好的人生。《最后的对话》中他讲家庭只提及了父亲母亲在文学上是如何帮助他,没有讲家庭给他带去的压力和抑郁,他无法完成父母对他的期待,多年背负内疚,而爱情婚姻更是搅碎他的心。值得一提的,他晚年终于找到了灵魂伴侣玛丽亚·小玉在博尔赫斯的母亲去世后,成为了博尔赫斯的秘书,从此不离其左右。在查出癌症后逝世前的两个月,他们毅然结为夫妇,不知这是否是完满的一生,但总归是博尔赫斯走完的一生。
也许时间可以让博尔赫斯感受世界的方式有所变化,然而他的内心准则无畏时间清洗,他对写作的思考与态度,强势生长,永不妥协。他倾付才华创造文学,从写作最初到生命最后,都依然坚定:“我不为任何人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感到了一种这样做的内在需要。”他也依然认为:“也许我相信自己是在写一首新诗,其实我写的是我往日写作的一个回声,一次差劲的抄袭。”他一生的轨迹,是因为阅读所以写作,去完成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是尝试某些谦逊之极的变体,讲述同样的故事,去完成一种文学的命运;他是完成了博尔赫斯的命运,成就我们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伟大作家。
《最后的对话 Ⅰ》读后感(五):成为N个博尔赫斯的N种方式
在收录于《虚构集》的小说《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里,博尔赫斯让虚构的作家梅纳尔受诺瓦利斯一段语言学论述的影响,决定和塞万提斯“完全自居等同”,重写《堂·吉诃德》,摒除三百年来各种外来的影响和歪曲,在这本“小说的小说”的某些方面与那位十六世纪西班牙作家的真正意图不谋而合,而在某些方面则大相径庭。有两种道路可以通向新的“吉诃德”:一是通过某种方式(阅读、模仿、考察、调查、还原、刻意遗忘等等)成为塞万提斯;另一种则是借由自身的点滴体会而在写作中逐步接近吉诃德。
梅纳尔放弃了他认为较为容易的前者而选择了后者,其成果就是如同特洛伊遗址般重重修改的手稿(事实上从未有人见到)。最重要的细节是梅纳尔在他的《吉诃德》里写下了一段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九章中逐字逐句完全一样的话:“历史所孕育的真理是时间的对手,事件的储存,过去的见证,现在的榜样和儆戒,未来的教训”,但意思完全相反——完全相反,完全相反。
笛卡儿的怀疑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以及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驱动了小说《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也驱动着一代代走火入魔者透过现有文本去追索所谓的本原。这几乎是种一般现象:如同上帝无法直接控制自己的造物,所有作者在自己的某个创作完成后,就失去了对文本的控制——他的初始意图也许实现了,但也许只是众多效果中的一种;每个读者在阅读莎士比亚时就成为了莎士比亚——然而是他以为、或者成为的那个莎士比亚。文艺本身的复杂性、过多的批评诠释、个人自以为是的解读(“一千个哈姆雷特”)和人文意识形态的流变都可能影响甚至扭曲一部文艺作品本来的面目。
在《最后的对话》(En Diálogo)中,博尔赫斯不止一次提到:有人当面问他是否见过阿莱夫,或者有没有《特隆,奥克巴尔,奥比斯·忒提乌斯》百科全书的第七卷;在得到否定回答后,提问者都将写出给他们如此深刻印象小说的作家当成了大骗子。“骗子博尔赫斯”,无论千百万其他读者是否赞同,这也是一种博尔赫斯的形象。《伊利亚特》折射的荷马和《永生》反射的荷马都是同一个荷马,《麦克白》或《亨利四世》背后的莎士比亚与《什么都是和什么都不是》里约伯式的莎士比亚都是同一个莎士比亚。在纯粹文学和心理学的意义上,梅纳尔是伟大的先行者;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N种自己的方式接近、或成为N个博尔赫斯。
普遍经验告诉我们,当思维以言说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其完整性已经被削弱了一部分;而以文字创作的形式(不管是何种体裁)表达时,尽管那时可能会有种种更复杂的形式、更迷人的修辞、更激荡人心的力量,这种完整性更会被进一步阉割。众所周知,人类并不具备三体人思维透明的生理特质, 那么面对面的对话天生自带朴素、直白属性,无疑是交流的最直接和最有效方式。相关的对话记录则是后人了解前人的最直接和最有效途径。的确,《柏拉图对话录》、最早的佛经、《论语》都是对话录或准对话录。可以说,某几种哲学、宗教和学派的建立都是从这些对话录中演绎发展而来。
“在基督教时代之前大约五百年,大希腊发生了世界历史中有记载的最好一件事:对话的发现。”博尔赫斯在《最后的对话》序言中直截了当地使用了这种略有溢美之词。
最后的对话。我理解中文译本为何在书名中加上原文所没有的“最后”二字。博尔赫斯在给这本对话录写出序言后的八个月零两天就永远离去,事实上这的确是“最后的”一系列对话,并且由于“最后”一词带有更多的戏剧性而更引人关注。
但这真的是最后的对话吗?我认为并不是。在“秩序与时间”这一节,博尔赫斯说道:“我试图让我的写作不那么随意,就是说,我试图呈现宇宙的某种物质,哪怕它在根本上就是混乱。”与他对话的奥斯瓦尔多·费拉里在序言中承接了这个说法:“在八十四岁的年纪,博尔赫斯将他的宇宙传递给了我们。这些对话是从每一个主题出发来记录这宇宙的……”
这是个没有人格化上帝的宇宙;神秘主义、不可知论、唯心主义是它的根本运行规律和逻辑;欧洲大陆的,以及略次之的阿根廷或西语南美的历史、宗教、文学传统,构成了这宇宙中基本的星系、星云和暗物质;来自泛东方文化的类星体会时时发出耀眼的超强辐射;梦、镜子、面具和书的主题是让任何路过的光线都发生弯曲的强大黑洞;不需仔细观察,最容易分辨的星座是一千零一夜、神曲、堂吉诃德、马丁菲耶罗等等。
只要有一个人试图进入这个宇宙,对话就还在继续。差别在于是停留在宇宙的边缘还是抵达它的腹地。即使只是无心一瞥,也能窥见一两颗坠入大气层流星:我们都以为博尔赫斯最喜欢的诗人非但丁莫属,但在这个对话录里,他亲口说自己在维吉尔和魏尔仑中间会选择魏尔仑;音乐方面,在勃拉姆斯和德彪西两个人中,博尔赫斯会倾向哪一个?我是完全猜错了。
他的原话是:“我对勃拉姆斯有感觉,而对德彪西毫无感觉。”为了平衡,他又补充了一句:“无疑这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