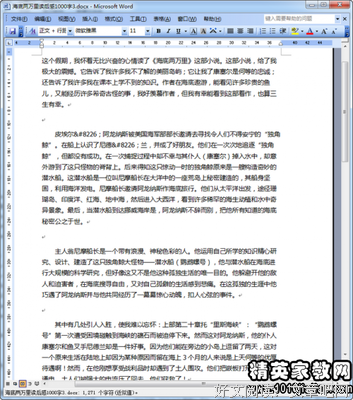《横渡大西洋》是一本由(波兰)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看来,我可以不必再担心愤怒的咆哮了——《横渡大西洋》和读者的冲突发生在几年前,在波兰侨民界,现在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到了防止其他不安全状况出现的时候,亦即,要让对这部作品的阅读不至于太狭隘和肤浅。
今天,在这部作品波兰国内版出版的前夕,我必须要求实现对于本文更深刻和更全面的解读。我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民族,而我们的心态,无论是在海外侨民当中,还是在国内,在这一点上,都还不是充分地自由的,还依然是扭曲的,甚至是受到操纵的……简直可以说,我们还不善于阅读关于这一论题的著作。一直到今天,我们的这种波兰情结还是太强烈,我们依然受到传统的拖累。有些人(我就在其中)几乎惧怕“祖国”这个词语,似乎这个词语让他们的发展延误了三十年。这个词语把另外一些人立即送上了我们文学中给人布置任务的刻板模式的道路。我这样说是否有夸张之嫌呢?但是,邮局不断给我送来国内关于《横渡大西洋》的各种话语报导,并且作证说,这是“沙文主义辞令的杂文”,或者还是“对战前波兰的讽喻”……甚至有人把他看成是关于萨纳齐(皮乌苏茨基1928年以后的继承者们——译按)的杂文。 在这里,我也许能够享有的最高的评价是把这一作品视为“民族对良知的清算”以及“对于我们民族缺点的评判”。
但是,既然我还有其他的和更具普遍意义的关注,为什么我还要和已经死亡的、战前的波兰或者和以往风格张扬的爱国主义搏斗呢?我是不是在那些已经过时的琐碎小事上浪费了时间呢?我属于那种如果放枪、也只对着粗大动物瞄准的、有抱负的猎人。
我不否认:《横渡大西洋》是一部讽刺作品。而且,甚至也是十足的清算……显然,不是清算某一个特别的波兰,而是清算波兰历史的存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条件造成的波兰(亦即羸弱的波兰)。我同意,这是一艘私掠船,走私很多炸药,准备炸毁我们迄今的民族情感。而且,在其内部,甚至隐藏了针对这一情感的明确准则:战胜波兰民族性。要松动我们对波兰的忠诚态度!即使摆脱一点也是好的!从下跪的姿态站立起来!展现这第二种情感脉络,令其合法化,这一个脉络令个人面对民族而自卫,正如面对每一种集体强力而自卫一样。最重要的是,要获得自由,脱离波兰常规,而且,身为波兰人是成为比波兰人身份具有更深广、更高一级意义的人!这就是《横渡大西洋》在思想方面的私货。进一步说,这里涉及的还有被推动得更远的,是对于我们与民族的关系之重审——这是彻底的重审,这样的重审也许能够完全改变我们的自我感觉和释放出来最终能够服务于我们民族的力量。请注意,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审,这是我愿意向其他民族的人们提出的重审,因为问题涉及的不是波兰人与波兰的关系,而是个人对民族的关系。最后,这还是和全部现代问题最紧密地联系起来的重审,因为我注视着(我一向就在注视)个人生活的加强和丰富,要使得个人的生活对于压抑成性的大众势力具有更大的抵御力量。《横渡大西洋》就是以这样的思想色调写作的。
我在《日记》中数次论述过这些思想;《日记》是在巴黎《文化》杂志上发表的。现在,《日记》已经在巴黎成书出版。1957年3月号《文化》刊印的日记片段没有收入这一卷《日记》,这一片段也构成了对于我异端邪说的注释。
然而,上述的思想就是这部作品的主题吗?在总体上,艺术就是对于主题的解说吗?这些问题大概是适时的,因为我担心,国内的批评界还没有完全摆脱社会主义对于“主题艺术”要求的狂热。没有,除了所叙述的故事,《横渡大西洋》没有什么主题。这只是一部小说,只是某一个得到述说的小世界——这个小世界也许值得注意,因为它显得滑稽、色彩斑驳,有揭示性质,有启发性——这是某种有光泽的、闪亮的、不断变化的世界,有多重的意义。《横渡大西洋》都有一点你们所看到的内容:讽刺、批评、论说、娱乐、荒诞、戏剧——但是又不单是其中之一,因为它不仅仅是我、我的“震荡”、我的宣泄、我的生存。
这是不是关于波兰的呢?但是,我只写我自己,从来就没有写过关于其他事物的一个字——我觉得自己没有被授权去写波兰。1939年,我定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远离波兰,脱离了我以往的生活,处于非常困苦的境地。过去被完全摧毁。当时的现实有如黑夜。未来还不能看清。什么也不能倚凭。在普遍的变迁打击之下,形式正在破裂、崩溃……过去的一切都只是软弱无能,正在到来的、新的一切,都是暴力。在无政府主义造成的无路可走的局面下,在被赶下神坛的众神当中,我只能依靠自己。你们希望我在这样的时刻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消除对未来的期望吗?……投身于未来吗?……是的……但是,我已经不想以自己的本质来投身于任何事物,任何即将来临的形式——我想要比形式和格式更高级、更丰富。《横渡大西洋》里的嬉笑正是来源于此。我的这一遭遇多少也是这样的,从这一遭遇中产生了这一怪异的、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揪扯的作品。
为了周到一些,还要补充一点,虽然这样的补充可能是多余的:《横渡大西洋》是幻想的故事。一切都是设想出来的,和真的阿根廷、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真实的波兰侨民界只有十分松散的联系。我的“逃兵行为”在实际中体现得也很不一样(我让查验官去看我的日记)。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一九五七年
《横渡大西洋》读后感(二):【文学评论】《贡布罗维奇反抗贡布罗维奇——解读贡布罗维奇及其小说创作》
一 、 我第一次看贡布罗维奇的小说便被《费尔迪杜凯》一书所吸引。“费尔迪杜凯”是作家生造出的一个虚构之词,它像飞溅的唾沫一样,被以一种嘲讽戏谑的方式吐向了文学史的重要领地,和它的创造者——这位“被流亡的”波兰先锋作家一起,构成了一股矛盾的反抗之力:它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是作家自己创造的新词,但它作为书名又确实存在了;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波兰语里没有明确的含义,但作家后来写信表示“这个词是反传统、反媚俗的象征”,于是它便又有了意义。这个虚构之词和矛盾之力皆是有意为之,我们甚至可以听到类似“呸呸”的声音,以示作家和他的作品是多么奋力地反抗这个已然存在富于“形式”的世界。这本小说不同凡响之处比比皆是,仅仅强调虚构之词的书名未免显得哗众取宠。透过小说内容,我们可以臆见这位作家耐人寻味的文学形象:一个破坏游戏的孩子,表面满不在乎,其实什么都在乎,即使乱了脚步犯了错误,也会给自己欢呼。正如法国评论家巴塔耶在《文学与恶》一书中写到:人不同于兽,在于他们遵守禁忌,但禁忌是模糊的。他们遵守禁忌,但也需要违反。……违抗所必需的勇气是人的成就,尤其是文学的成就。文学的优先行动是一种挑衅。真正的文学是富于反抗精神的。真正的作家敢于违抗当时社会的基本法规。文学怀疑规律和谨言慎行的原则。而贡布罗维奇深谙其中道理,从著书立说起,便皆以“形式的反抗者”、“反传统主义者”、“反崇拜圣像者”的形象示人。他在《费尔迪杜凯》里所发出的长篇议论,富于智慧和狡黠,通过标新立异作为冒险精神的显现,用发人深省的哲思嘲弄经典与正统等一切具有形式感的事物,以故弄弦虚、滑稽逗笑的语调模仿一派天真的顽童之举。他刻意把故事置放于荒谬变形的处境,人物和情节共同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学细节,就如卡夫卡《变形记》里人变成甲虫一样,他的“青年作家尤瑟夫”也被人为地从心理上逆生为“少年尤齐奥”,这一切的写作皆是天马行空、打破常规的。甚至他在写“孩子气十足的菲利贝尔特前言”这一章节时,通篇居然都是在讨论“前言的功用”,并以作者的口吻身处其间大发感慨,完全给人以作者在作品内部如上帝之影般现身的惊愕感。 《费尔迪杜凯》让我想到国产动画片《没头脑与不高兴》。“没头脑”指向学校和老师愚弄学生,对其进行蒙昧教育,夺其心性,损其智力,使得他们永远处于无知和不成熟的状态;而学生对前者的抵制与反抗之举也属“没头脑”行为,以无知抵制被无知化,以不成熟对抗被不成熟化,这种荒诞的极致和绝妙在于为了提出疑问:何种情况下塑造出的人是毫无生趣却滑稽可笑的。作者白描出丑角群像,有以令人憎恶的伪善表情示人的庄园主人们、甘受奴役的无知仆人们以及空心情人佐霞等,都是令人“不高兴”的角色。作家在小说里利用主角的便利,操起一口戏谑嘲讽的腔调,模仿起气急败坏的吵吵嚷嚷的孩子的口吻,大叫、高喊,有声发布着对这个世界和某种人性的不满,他无非想表达人永远无法自由的绝望:人从来无法为自己成为自己,永远都将是为了别人而成为自己,永远为了适应别人对自己的期待而塑造自己,因为人永远依附于人。这样就永远不会有独立的人格,永远将是一副扭曲的装腔作势的“不高兴”面具示人。作家的写作肆意而漫不经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的写作植根于生活”,尽管作品充斥戏剧性场景。他也许更愿意说自己更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思的现实主义和果戈理的幽默讽刺,而对立于博尔赫斯的“想象的智识”。但实际上,他的想象也颖异灵动,丝毫不逊色于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当然,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作者在语言的运用上可谓个性十足,风格显著:俗话俚语、双关多义、谐音反话,遣词造句肆意拈来,制造或混乱或空洞或晦涩的语言,从而织就了变态丑恶的世界和人性虚空的图景。而贡布罗维奇本身也生性内向、容易情绪起伏神经紧张,其作品自始至终反对传统和形式化,并带有强烈的离经叛道色彩,文字夸张、扭曲、怪诞,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或丑态百出,或乖张古怪,内心充满了被外界侵扰和威胁后的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 他的小说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解构了波兰小说传统写法,也的确像破坏游戏的孩子玩弄的把戏。 二 、 1939年八月初的某天,贡布罗维奇踏上游轮开始横渡大西洋的游历,抵达阿根廷后不久因二战爆发,德国侵占波兰导致滞留他乡,顷刻间,荣耀与财富化为乌有,失去一切,祖国、家庭、财富、头衔乃至语言,由此被迫成为“流亡”作家。《横渡大西洋》不久便由此而来,作为一部半自传体小说,甚至可以打上“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这样的标签。它短小精悍但风格有趣、语言生动,与《费尔迪杜凯》这部长篇小说一样,依然运用荒诞的手法,尽辛辣讽刺之能事,通篇以阐述作家自身对于文学、哲学、心理学和社会现状的认识和想法为内容基调。作家自己毫不否认火药味十足的讽刺指向自己的祖国——波兰,这个作家从35岁离开后再也没有真正返回过,却依然被书写被议论被嘲笑被批评的国度,它饱经历史沧桑,经由恶邻欺侮,战争蹂躏,屡败屡战致其羸弱,而曾为历史上的欧洲大国,又使其淬炼出了伟大的民族集体心理,民族的共同信仰和坚固不动摇的民族性。从贡布罗维奇看来,正是他的波兰同胞们那种毫无原则的、疯狂的爱国表现,民族自豪感与民族信仰:将个体让位于集体,个人利益让位于集体利益,以个体的跪姿取代了人格的独立,才造成波兰人内心存在着自我矮化和个体面目不清的严重自卑心理的糟糕局面。作家明确表示,小说并非为探讨波兰人与波兰的关系,而是个人与民族的关系。确实,后者的视角选得更为宏大,并具有形而上的现实意义。从某种事实角度上来说,贡布罗维奇恰恰与米兰昆德拉相反,之于各自流亡于祖国之外在别处生活,前者是实际意义上的返乡者,并且同样作为爱国者而存在,尽管他的嘲弄、讽刺地行文貌似表现出他对祖国厌恶得要死的神情和腔调。他的“爱国心”完全可用“爱之深,恨之切”来表达,而往内里深究,他似乎还带有某种暗自庆幸,这是 “自我留存”后的得意之情。他远离他的国,才有能力以明晰的力和傲然的勇气去书写一切,就此,他曾这样感慨:我感谢万能的上帝让我远离波兰,就在我的文学境遇刚有起色的时候,将我抛向南美大地,丢进陌生的语言,让我陷入隔绝的孤零、无名之辈的新鲜感以及一个艺术还不及母牛丰盛的国度。漠然如冰封,恰好保存了傲骨。此时的他颇像西西弗,不是那个永推巨石的抵抗虚无的荒谬英雄,而是那个从地狱里逃逸而出的,重新领略人间美好的欢乐英雄西西弗。 一切都不妨碍贡布罗维奇对波兰的“爱与恨”表现的浓烈并驱,“爱”体现在他脱离不了“波兰”的一切:始终用波兰文写作,他写信及交流的对象多数是波兰友人,长篇小说的背景也以围绕波兰人与事为主。我愿意夸张地断言,他对波兰的依恋是孩童恋乳式的。而他的“恨”表现为“怒其不争”,才有了他极力表现各种不合时宜的不满行为:讽刺、批判、重审乃至清算。贡布罗维奇的爱恨与傲慢之姿,还体现在他将《横渡大西洋》认定是一艘载满火药的私掠船,而把自己认定为是一个“只对着庞大动物瞄准的有抱负的猎人”。这种傲慢源于他抽离了事件中心而“被流亡”的状态所致。他在《杂文集》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自己的“流亡观”: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名副其实的是流亡者。这种对流亡的认识或者说属性认定是区别于大多数的流亡作家的,比如茨威格、纳博科夫或者昆德拉。米兰.昆德拉在一次访谈中明确了贡布罗维奇的流亡属性,并深刻地理解了他:他(贡布罗维奇)也许是想说他那种特别强烈的个人主义不可避免地会使得自己成为一个隐喻意义上的流亡者,作家的本性使得他永远不会成为任何类型的集体代言人。他(贡)认为作家的本性是反集体的。而传统的波兰人则一向是把文学当作是必须为民族服务的事情,这也是波兰作家的伟大传统,比如密茨凯维奇这位伟大的波兰诗人就是民族代言人。而贡布罗维奇是贡布罗维奇,作为享誉欧美文坛的现代派作家,以小说、戏剧和散文见称。这位自诩比“博尔赫斯好太多了,并站在他对立面”的,如一个“葬礼上的狂笑人”,不合时宜地说话行事,以某种惊世骇俗的言论和语调,将文学的反抗精神形而上又形而下地贯彻始终。他的奇谈绝非自夸所得,昆德拉就赞誉他为二十世纪最伟大小说家之一,位列“中欧四杰”。20世纪荒诞派文学也有他的重要一席,是波兰荒诞派文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亦正如他自己日记里所说的那样,他才是他笔下的所有主人公里,唯一被赋予了重要性的人物。 三、 贡布罗维奇在离开波兰前便以嘴利著称,常被波兰文化圈拉黑了事。他的“恶言恶状”真正“蜚声”国际文坛,大概是从《横渡大西洋》一书发表伊始。究其原因,大概是他在祖国遭逢悲惨历史时刻之时,却迅速以轻快自由的笔调经由主角的口吻对其足够陈旧腐朽观念进行毫无忏悔的无情揭露:他展示波兰文化反同性恋的狂热,表现类似殉教主义的民族性的可怕,讥讽以密茨凯维奇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与爱国主义,在这一底蕴中,“他发现了反自然的、和反肉体的顽疾”,像屏障也像牢笼抵抗也桎梏了个体的自我与天性。而他对抗这样的桎梏首先就是用语言的大音量地进行击毁,砰砰砰、啪啪啪、哈哈哈,那种斩钉截铁式的、高声呐喊式的,呼叫着对话或内心独白,营造出一种阴阳怪气的语调氛围,恰如贡布罗维奇示意要鞭挞的那部分固步自封的以民族原则和爱国精神为主体的文化怪圈所散发出的糜烂怪异的气息。他把密茨凯维奇赞颂的英雄主义和枪骑兵精神拉下了马,按照贡布罗维奇所理解的,恰恰是波兰枪骑兵类似一种种马神话迷惑或者说欺骗了那些青春少年,而两者正是对立面的存在。而类似的对立面无处不在:“爱国主义的田园与鬼蜮、父国与儿国、善心少校与放荡子、公使与会计、规范与偏离、杀父与杀子……”。作为一位以“反传统主义”的反抗者而著称的作家,贡布罗维奇与著有《反抗者》一书的加缪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紧紧相贴又面向不同。他们同时代,前者比后者出生得略早过世得略晚,一个书写荒诞不经的现实世界,一个强调从精神上反抗不可避免的荒诞。两个人都认可“苦难”的必要性,无论是从自我的经验上看,还是他者的经验。贡布罗维奇的小说创作是经由哲学的思辨性书写故事而非叙述性,乃至他的小说作品也大多呈现松散的诗体和散文化特征。实际上,他对散文题材更为擅长,这样他的狂放之言、奇思怪想方可信手拈来随手图就。贡布洛维奇的小说不仅具有思辨性,哲思隐逸于夸张大声的对白或独白中,而且,他大段的抒情式议论及言语(而非抒情本身)也构成了诗的语言特性,还带有明显的戏剧剧本的倾向。虽然也许他不愿意明确承认,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态度有某种骨血上的相似,但从作品的角色与文字间隙中可以瞥见一二,他们的作品本身散发着“现代人的气质,不惧怕世俗的讥讽”,并同样充满了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当然,两人对于荒诞本身的处理及其所涉及的提问与回答,区别了两者的相异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存在小说家”,而贡布罗维奇是手持“荒诞之矛”的荒诞小说家。如果说贡布罗维奇并非传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骨血,那是否具有一丁点的相似呢,这我们也无法确定。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尼采,翻开贡布罗维奇的小说《色》可以窥见端倪。 1960年,旅居阿根廷的贡布罗维奇出版了其创作后期的重要长篇小说《色》。该小说的时空背景依然设定在二战时期的波兰。这本小说通过书名撩拨着读者的兴奋神经。但实际上,这并非真正通常意义上的色情小说,没有直白的肉欲性爱描写,而是指向书中人物对待青春与肉欲、新与美的臆想与意淫。这里面的“新”与“美”并不是通常概念里的“真”与“善”,而与“假”与“丑”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宗教的探讨,最终走向真正的死亡。贡布洛维奇类似畸零的审美主义曾于一时使他受到西方文化批评界的一致抨击。但正如这本小说的主角“弗雷德里克”与尼采同名,贡布洛维奇也因而增添了几分尼采主义的色调。而尼采在《偶像的黄昏》里早就把美丑看开了:没有什么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在这一简单的真理上建立了全部美学,它是美学的第一真理。我们立刻补上美学的第二真理:没有什么比衰退的人更丑了,——审美判断的领域就此被限定了。从生理学上看,一切的丑都使人衰弱悲苦。它使人想起颓败、危险和软弱无能;在它旁边,人确实丧失了力量。……只要人在何处受到压抑,他就可估出某种“丑”的东西近在身旁。他的强力感,他的求强力的意志,他的勇气,他的骄傲——这些都随着丑的东西跌落,随美的东西高扬……在这两种场合,我们得出同一个结论:美和丑的前提极其丰富地积聚在本能之中。在这里,一种憎恶之情油然而生:人憎恶什么呢?毫无疑问,憎恶他的类型的衰落。他出于至深的族类本能而憎恶;在这憎恶中有惊恐,审慎,深刻,远见,——这是世上最深刻的憎恶。因为这,艺术是深刻的。尼采谈论到的“憎恶感”,是多么的像贡布罗维奇对于僵化导致的衰败产生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恶感呢。1963年,当贡布罗维奇离开阿根廷及那个“以博尔赫斯为首的文化圈”时一定满怀“愤意”,那种因被放逐或自我放逐而离去时的自我嘲讽,以及背对文学阵营的恶感情绪,在他的小说里也通过主人公之一费雷德里克与阿梅利亚夫人关于风景与木桶的对话体现了出来,后者对待前者的态度“小心翼翼”,前者则报以“随随便便”的姿态以示回应。《色》这部小说已经从《横渡大西洋》这本同样以波兰为背景的内容里走远了。但它虽无关国家革命与民族信仰、斗争与牺牲,甚至在小说后面以这些无关物作为给小说主题的献祭,却依然书写着贡布罗维奇式的母题:反抗与荒诞。 四、 贡布罗维奇通过语言的“多义性”指代了现实生活中多重意义的境况与景象。书中主人公“我”——维托尔德,作为叙述者与另一个主人公弗雷德里克均认定自己要以一种怀疑主义的眼光来审视生活,以期从中发掘出生活中的新意。而无论这种新意本身的善恶美丑,都将是打破生活僵化与形式的武器。两位主人公像一对躲在教堂地窖里淬炼第一支香水的杀人犯,进行着一个“邪恶的计划”,反复淬炼他们猎取到的少年男女这一对象透出的青春之美。年长者因得少年心气和精气而重新焕发青春。这种描写何其美又何其糜烂,恰恰充溢出小说书名的感觉:色,多么的情色!与作者同名的主人公“我”则不吝向读者道出他的同性情结,仿佛就是作家自己的独白。而他最热情洋溢的笔墨不是献给如花的少女,正是泼洒于健美青春的少男身上。贡布罗维奇的文学之笔描写的隐逸的色欲,既浸染于肉体间隙,更加填充起精神内核。小说结尾,弗雷德里克手持利刃,刀上沾满鲜血,涂写了被囚的金发男孩的命运。最终,青春之死才是最有破坏的色欲。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到文学评论家米哈乌.格沃文斯基如此评价《色》:它,“不仅是一部哲学小说,而且——无论如何也可以认为——它是一部情色小说”。也许正是因为它是贡布罗维奇的哲学小说,所以,它才更加反情节化。就像《色》这本小说里的人物既有非全知叙事者的“我”,也有更具有故事发展掌控能力的“弗雷德里克”,他们像一体的两人,进行思想上的共谋与对话,从而使得小说产生了丰富的可解读性和多义的指向。实际上,要充分准确地谈论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的创作,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也是作者自己的策略,他一定在想“我无法被形式固定”。所以,作者既是自己的评论者、阐释者、精神分析者,又是文学作品的主角和叙事人,多元化的身份和功能让他从反抗之反抗中脱离出来。贡布罗维奇无疑是优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许按照脾性,他甚至会不屑于这个“之一”的说法。但这种不置可否的傲慢之姿也颇为符合他毕生精力所行之事,根据他创立的怪异逻辑,为了反抗而反抗,反抗传统和秩序,反抗原则及标准,反抗世俗与现实。他甚至反抗文学本身,站在了文学性的对立面,并声称自己植根于“生活”。为了反抗固有状态,他模凌两可地承认自己的同性情结:他,“既是也不是同性恋”。而为此给出的原因则是:因为一个人在某个生命阶段或环境里是同性恋;——而且没有人能够发誓自己从未经历过这种诱惑。在这个问题上,要一个人做出一刀切式的供认实在太难了。是的,任何做一刀切的论断都实属不易。正如他去世前所写道的自我追问般的话语:“我对形式的攻击带给了我什么?还是形式。……结果却让我变成了一个以形式为主题的作家。”他说,“我简直有愧于自己。”写到此处,我不禁想起香港Beyond乐队的那首老歌,“破坏游戏的孩子”,就像是写给我心中所想的贡布洛维奇在文学史中的形象,一个顽皮又聪明地孩童。我想,他毕生所做的最终意义就是为了,贡布罗维奇反抗贡布罗维奇吧。 【已发表于 《书城》2013年11月号】
《横渡大西洋》读后感(三):不到位的感受《横渡大西洋》
这两周在思修课上看的书[捂脸] 《横渡大西洋》写法怪异荒诞夸张,里面的矛盾,纠结,让我一度怀疑这作者是有强迫症。表示还不太习惯这种激烈的情感表达。但是贡布罗维奇敢于站出来批评自己的民族劣根性(波兰)无所畏惧的这种精神,真的是很佩服。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同性恋这个隐晦话题的描写了,在那时,应该20世纪30年代,同性恋是新兴词汇,不被社会认可,是失范的。贡萨洛使尽力气对另一个小伙子的热烈追求,作为波兰作家的“我”当时的矛盾从最开始的排斥到认可,这也写出这个社会对同性恋的认可趋势。 再补充这大胆的封面,黄色的屁股带上一顶帽子,老实说,现在都没看懂。出现屁股,大概是因为小说中以狗屁和狗喻人,狗是那些上层人物,狗屁就是那些上层人物的走狗。。至于为什么是黄色。。。。。。大概屁是黄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