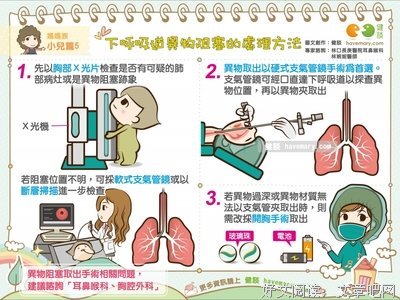《胎心、异物及其他》是一本由阿丁著作,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双封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25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胎心、异物及其他》读后感(一):《胎心、异物及其他》:平凡世界的光怪陆离
城市的夜并不寂静的。倘若你有心,推开窗子总能看到夜幕下的点点灯光。在每一扇或明亮或黑暗的窗子背后,都正在或曾经发生着故事。这个世界或许平凡,但每个故事,总独一无二。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如果刚好,你是个喜欢听故事的人——再来个会说故事的家伙,你便会拥有一个完美的“故事之夜”。
很巧,阿丁先生也许正是你希望遇到的那个人。《胎心、异物及其他》中的每个故事,都令人印象深刻。
阿丁先生身上有两个很鲜明的标签,一是“七零后”,一是“前麻醉师”。我印象里的“七零后”,大多很会讲故事。或许是不太热衷社交媒体和热衷于社交的缘故,他们可以收集到很多故事,且不会太忙,以至于连踏实地完成一个故事的时间都没有。至于“麻醉师”,则是一个有些有趣的职业了——至少听起来,他们是在人类的清醒与迷醉之间游走。
如果故事说得好,也会有如此的效用吧。
《胎心、异物及其他》中共计十二篇故事,“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蹩脚的魔术师会把自己的乏善可陈归结为生不逢时,然而太阳之下“本无新鲜事”,厨师的高明与否,也取决于对已有味道的驾驭。这点颇雷同于小说的创作之道了,人人都可如李长吉“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然“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却举世无双。
由此,阿丁的创作特色说来简单。素材总能“道听途说”,随手拾得,但经由他的“加工重组”,一个个令人欲罢不能的精巧故事,便跃然纸上了。
小说集的首篇作品《美颅》便是如此。故事“始于师兄们讲给我的真事”——其实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仅仅是一个场景:“有位师姐在一个阳光炽烈的午后纵身跃下,师兄说有人曾亲眼看到死者在五分钟前刚刚晾晒了衣服。下楼探看,衣物静静滴水,散发着洗衣粉的香气,不远处,香魂却已渺渺。”没有人知道从起点最终会走向怎样的终局,但找到起点,并且走下去——人生如此,小说之道,也无出其右吧。抵达人生终点的方式也许很多,但小说家最好的路径,显然只是想象——缪斯眷顾,有想象,一切才那么有趣。
“一部好作品也总是争议之作”。阿丁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他对于素材的处理应用在短篇小说的体例中也恰到好处。然而故事中弥漫的“光怪陆离”却常被认成“负能量”。国人热衷“大团圆”绝非一日之事,如木心所言,“看戏,一家子嘻嘻哈哈,最后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大家仍嘻嘻哈哈,吃夜宵去了。”如此说来,阿丁的故事,也真的有“不识趣”的味道了。一个故事,又何必当真?
只是平凡与平庸,绝非同义。
阿丁做过麻醉师,所以他的小说中涉及医护知识的不少,甚至在《鱼以及饵》中设计了一个“蓝翔卫校”的故事发生地,很是有意思。同时,他的小说中还有着一股浓重的福尔马林味,飘扬在每个角色的身上,即使是《魂斗罗》中的孩子们,无一幸免。那是种什么味道呢?就是把抽干了情绪的真实。
阿丁曾在《无尾狗》的采访时说,他书中的内容只有三成不到的真实,剩下的都是虚构,但虚构未必就是不真实。这《胎心》这本书中,阿丁延续了这种“虚构”,书里的很多故事甚至能在现实中找到相对应的新闻素材,譬如《死党》中那个城管与小贩的纠葛,那个叫强强的爱画画的孩子,指向是多么的明显……只是变成了小说,变成虚构的人和事,却仿佛更多了层真实。这种真实就是阿丁的矛,是他在无论长篇或是短篇的创作中都极力保留的东西。
他的矛总是不遗余力的刺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也许真实的疼痛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获得。阿丁做医师时,用药物麻痹人们的疼痛,改行做作家后,倒是更加卖力的撩拨人们疼痛的神经元。他选择的角度既有少年人纯纯的爱慕(《美颅》),也有少年学校的旧时记忆(《魂斗罗》),甚至巨细靡遗的描绘了一个老人对孙子深邃的爱,却又在故事结束之前,给了他一把仇恨的刀……这为小说造成了一种很古怪的真实感,让人痛,却又摸不清伤处,就这么直愣愣的感受着,说是情怀也行,当个故事随意看看,也行。
坦白说,《胎心、异物及其他》这个名字实在有些随意,仅仅感觉像是为了说明是小说集而随意捉取的。而里面的故事也和这名字一样,选择的都是世俗生活的普通人。他们以普通融入这些故事背后,看似荒诞,却又好像有迹可循。像是于丽娜,那个在《我不喜欢开玩笑》中因为玩笑而摧毁一个男人的女人,这个故事有多么的荒诞,但一切又发生的顺理成章,像是故事的结尾那样——“这世上还真他妈发生过这种事”。而为了从所有的虚构中脱离开来,阿丁还将好友孙一圣也引入其中,他赋予了孙一圣清秀、干净的形象,使他成为了两位宿命截然不同的女老师联系的线索,和读者对照二人的镜子。这种方式,在阿丁的《寻欢者不知所终》里就有所涉及,读者通过这些虚拟又真实的人物,将书中的故事也虚虚实实的读下去。
黑塞曾有首诗,诉说着春天的生命力,“活下去,生长吧,开花吧,爱吧。高兴点,抽出新的嫩芽。”阿丁却反其道而行,在所有负能量似的故事背后,用真实,抽出了生活全新的嫩芽。阿丁在《锁》中通过主人公告诉读者,这个世界由千千万的孤独构成,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每扇门的背后拥有着怎样的人生。但只要有故事我们却总能知道一些。阿丁的故事以灰暗的方式让我们面对真实,生命脆弱的真实、生活残酷的真实,以及荒谬中总有新芽的那种真实。
《胎心、异物及其他》读后感(三):最光怪陆离的是人心
粗算有三年多,成天跟文字较真,起先是学习,之后是工作,作为结果,不知是幸或不幸,而今既患上了随时抓虫的强迫症,也生出了被某友等同于钻牛角尖的中文过敏。自身文字水平没几斤几两,却一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模样对他人挑三拣四——如此无可救药的我,遇到阿丁这本短篇集,不得不说——如获大赦。
文字——手术式的精准与客观。没有废言,字字到位。这是种很难传达的质感,也因人而异。我只能表述我个人所感,设想如下画面,内容————在不停跳心脏的情况下实施二尖瓣膜修复手术[二尖瓣膜是左心房(上)左心室(下)之间一个可开闭的膜状结构,起到单向阀门的作用,保证血液在心脏收缩时从心房到心室单向流动,如果受损便需要修复];视野——胸壁切口,四方形,正中,搏动的心脏,砰砰、砰砰,一次性医用乳胶白色手套包裹的一双手,握银色手术工具,在其上切开小口,探入,捕捉开闭中、开口面积不超过六厘米平方、厚度以毫米计的二尖瓣膜,迅捷、稳当、毫不犹豫地穿针引线,修复,完毕。
摘封底文字共赏:
我的名字后面,平生第一次挂上了“开锁技师”的头衔。这活儿和我以前的勾当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都需要打开陌生人的门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多锁上几岛就安全了,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即使有一千个锁点,锁芯也只有一个,突破一点,所有的锁点都会乖乖弹开,步调一致得如同团体操表演者。我昔日的伙伴们为自己筑造了无数条心理防线,可是在老警察眼中,根本就毫无用处,他们会迅速并精准地找到你的“锁芯”。那一刻的感觉就像一根针刺入心脏,每一根肋骨都形同虚设。春天来了,枯枝开始饱满,嫩芽如粉刺一样钻出,我再也压不住它……不以为然的读者,可以试着改变或删减其中任一字词。这是用来检验任何一部作品文字能力的最好方式。
文字如此,故事如何?
这是令我大为惊异之处——相对于文字的清晰利落甚至可谓冰冷刚硬,故事却是模糊不定且有一种血性的炽热。在豆瓣留下短评的书友,对此分歧很大。一方觉得用力过大,写得浅薄了些,一方表示喜欢诡异的脑洞。我是后者,又不是后者。
在此书中收录的十二篇短故事里,死亡/暴力或/和分离是如影随形的存在,这一过程发生之猝然,对于习惯只在新闻和推送中看到有头有尾的恶性场面的人,未尝不似在哪个关键配置上不小心出了错的平行世界。有妻有儿家缠万贯的成功人士离家出走,变成把狗当作灵魂伴侣对话的臭流浪汉(《异物》)。因一句和前夫所言丝毫不差的玩笑话,苦心布局以自杀的方式陷害多年未见也未曾有过同学以上关系的玩笑者(《我不喜欢开玩笑》)……确实是常人所无法理解,却也并非真的非现实,指不定真的在哪里发生过。
不认同?
好,请麻烦设想一位矮个的黄种男子,趴在一具白人女性的尸体上,尸体呈俯卧姿势。男子趴在尸体臀部位置,试图啃咬,未果,用刀具切割,黄色的脂肪粒在盘中看似玉米,但肉尝起来却是生鱼片的味道。很美味。饱腹之后,他开心地和尸体合了照,这还不够,这可是他深爱的女子,于是,性交。案发,判刑,入精神病院,四五年后,回国,病愈,自由身,出书,不止一本,改编漫画,粉丝众多。本人细细回忆起来,小学一年级看到同班一位同学的大腿,就想着“很好吃的样子呢~”
这个故事如何?
难以想象。
真的,男人叫佐川一政,在世。
能理解?
恐怕只有跟他一样的人。
疯子,不错。然,再怎么骂其禽兽,科学地讲,他终归还是一个人,胸腔里的还是一颗人心。
阿丁的故事是脑洞,有猎奇元素,但赞同与否、是喜是厌,描绘的到底是活生生的人心。
人心是什么?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就曾对意识和疯狂进行过阐述,也一度流行如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这等任性的心理学说。那时,心理学更像是信仰,结论依靠辩论、逻辑、权威。如今,心理学已成为一门跨多种学科的科学,但仍然无人能为我们不足3斤的大脑的思维活动给出一个牛顿力学定律一般的公式。
你在想什么?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潜意识局限)?你能够表述出你所想的所有吗(语言局限)?你真的能够传达给对方你的所想吗(认知局限)?——你真的知道自己是谁,而身边最亲近的那个他又是谁吗?
——每个人,也许都活在一个名为理所当然的玻璃球中。它并非坚不可摧。
阿丁的文之所以让人会感到荒唐,正是因为跳脱了这种常态,试图窥探光怪陆离的人心。在这本短篇的最后,收录了两篇非虚构。在个人看来,阿丁最想说的话,就藏在了这两篇里。一个是对门曾经出手相助过的邻人大哥哥,一个是曾经一同饮过酒行过乐的半个朋友,两个人都犯下了看似无端残忍的命案,就这么仿佛未曾存在过一样蓦然消失了。
“你不会哪天就突然消失了吧,跟安得林一样。”“怎么可能。”我说,“只有死才能把我跟你分开。”“呸呸呸,不许说那个字。”她把我的脑袋轻轻推开说,“他说他要写作,世界上还真有人为了什么写作,冷血地撇下老婆孩子和……一个温暖的家?想不通想不通,只有疯子才会干出这种事。”“嗯,八成是疯了。”我附和道。可我那时想到的是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那个叫斯克里特兰德的人。我没跟他说,世上是有这样的人的。对这种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会作出相同的判断:此人抛弃妻子,冷血无情,是不折不扣的人渣。只有极少数的人,蔡慧祥书中的那个塔希提女人,持与世俗的目光相反的态度。“以后咱别提那个人了,”我摩挲着妻子水肿的脚脖子,“就当他死了吧。”《胎心、异物及其他》读后感(四):阿丁,硬顶上!
想不到阿丁今年如此高产,3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先后出了一本长篇《我要在你的坟前跳舞唱歌》和一本短篇《胎心、异物及其他》,当听到其短篇出版的消息以及第二天就从当当上收到实体书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会如此神速。(相比我喜欢的另一位作家阿乙,咳咳……)
不看目录,你会觉得书名和封面很诡异,乍一看还以为是胎教书,其实就是几个短篇的篇名罢了,不过封面图是什么意思一直不明白,手语吗?(懂了,上下其手。)
翻开目录,有几篇就非常眼熟了,《我不喜欢开玩笑》来自早夭的坚果小说;《海鳗与石斑鱼》来自第二胎果仁小说(其中还收录了阿丁的另外一篇短篇《天注定》),而其他的几个短篇几乎全部都在他微信订阅号里出现过片段或整文,想想还是挺良心的,至少让我感觉到他写作绝不只是为了钱。
近来闲时较少,断断续续才读完。简单地说一下感受。
《锁》是印象比较深刻的,边缘人的刻画以及那种被遗忘的恐惧深入人心,对于某些情节的留白也恰到好处,最后的“三百字。”看着还是挺绝望的。
《胎心》是以一个很独特的视角——子宫中的胎儿来阐述的,这也是我的阅读范围内第一次见,让我想到了电影《蝴蝶效应》的结局镜头。
《异物》、《硬顶上》都是交叉叙述的手法,而且《异物》的结合处很有意思,当然,阿丁自己也说了,让人想到了海明威和安德森。一篇讲究叙述技巧的,中国精简版《月亮与六便士》。
《魂斗罗》是看得比较过瘾的一篇,有点满足了自己儿时的幻想。少年侠客,荡气回肠。
《海鳗与石斑鱼》的翻译体味好浓,不过也挺对这篇题材胃口的,阿丁说是通过卓别林的传记有感而发,姑且当一篇历史悬疑小说看吧。
《口吃的人》看完后还特地上网查了查,确有此事,感觉小说中的情节突然如幽灵般附在了现实身上,背脊一阵发凉,不知阿丁得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这样。
其他几篇短篇题材就大同小异了,这些内容也许在以前的长篇中能更加体现出来。
最近阿丁的微信挺爱自嘲的,感觉自己的作品是“被低估之杰作”,不过还打趣说挺以为豪的。嗯,给中国一点时间,给读者一点时间,我相信时间能证明一切。
最后,阿丁,加油,在写作这条路上,硬顶上!
《胎心、异物及其他》读后感(五):《锁》读后
我找不到那条新闻了,说的是北京一女子和她的两个孩子死在出租屋内,被发现是一个多月之后。搞不清怎么死的,饿死还是病死。总之一个家庭凭空消失于世上,如果不是恶臭飘出,竟无人发现。人和人真的成孤岛了么,就没一人发现异常?就没一个密友,没一个亲人,这不是独身女子,这可是拖家带口的三个人。
看到这条新闻时,我怔了很久。我想我和阿丁,为同一件事触动过。可其实我想说的不是这条新闻,是另一条。“中学教师送医后被扔进垃圾堆,之前车祸受伤昏迷辣椒地里三天”,时隔两年我仍能凭内容找到这条新闻,可见当时它对我的触动,地址在这:
http://news.sina.com.cn/o/2012-04-12/015324256977.shtml
被发现了又怎么样呢,你以为除了那极个别你的亲人,你的死活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没有联系方式、身份信息,再如果没有反抗之力,神志不清,说不定就被丢在某处的垃圾桶里,像一株濒死却未死的植物那样,等待着苍蝇虫蚁蚕食掉自己最后的生命迹象。
从看到这条新闻开始,我时时带着手机,并保持手机24小时不关机了。他说,媳妇,以后我每天给你至少打个电话,不管怎样你一定得接,即使接不到,过后一定得回。你要是不回,我就报失踪了。我怕你被丢进垃圾桶。这大概是我听过的,他对我讲的,最动人的情话了。即使凄凉。我们在这个城市里相依为命。我是他在这个陌生城市里,唯一的亲人。
对于孤独终老的最大害怕之处,就是自己死了都没人知道吧。这条最凄惨了,打败了所有其他条。于是拼命的社交,建立亲密关系,就怕自己凭空消失了,会没人发现、没人惦记。谁都想在世界上留下点什么,划出点痕迹,以示自己来过。
可有没有想过一点,与你相依为命的那个人,如果想害你,或者对你置之不理,你就真像一根风筝失去了线,彻底的与地面失联了。就像《锁》里那个老板的情妇。他大概是她在这个城市,唯一的依靠了吧。一个单身女子,只身来到大城市闯荡,找到一个自以为的靠山,猝死(谁知道是不是呢?)在了他家,为了避嫌,他设了个局,让她“死”在了自己租住的房间里。一个月后,恶臭飘出,被发现,新闻版面的角落里300字交代了她的一生。她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像一张废纸被写过然后揉碎再扔进垃圾桶。
我再猜想下开头那条新闻,单身母亲身患重病无处医治,死在了出租房内(或者做了个甜美的梦随即猝死),总之死掉了。两个孩子却是活着的。因为太小,房门反锁,无处呼救,在自己死去的母亲身旁兄妹两无助的哭泣,多日后双双被活活饿死。
人如蝼蚁,人如蜉蝣。我是一直相信的,所以才弱小又艰难的爬行。想要创造一些抓点,才不至于无声的滑落。
阿丁这篇小说,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很棒。立意到成文,都棒极了。我出门之前读了一遍,回来又读了一遍。我喜欢他的第一人称,第一人称说出的事情,都是鲜活的。我被深深触动了,再次觉得他是这世上仅存的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了。能写的出这样的小说,就说明他是最优的,他有这个能力。
锁这篇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信息量很大,几乎每句话,都在透露一些心事,我看完很是感动,不仅仅因为故事。
《胎心、异物及其他》读后感(六):透过故事看故事
《胎心、异物及其他》
——阿丁
老实讲,我完全不认识阿丁是谁。看到这本书的很多书评里都写的跟阿丁很熟悉的样子,我实在是不认识他。我所要坚持写这一片书评的理由之一是他的文笔和文采,经此而已。当准备下笔的时候又发现那种优美的文笔,我也确实写不出来;就好比你欣赏过一朵花的美之后,你被吸引的同时是无论如何都不忍采摘的感触一样。
还记得很早很早的时候,看过陈丹青采访韩寒的一个视频。在这个视频里面,陈丹青作为一个60后的卓有才识的人,提出了很多有趣、有智慧也有针对性的问题,简短的问了几个大家都想问韩寒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1、你为什么不读书了。2、你为什么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上。3、什么是促进你写作的最大原因?韩寒的回答大体是这样的:“我不是不读书,我是不读他们要求我读的那些书,或者说我读过之后发现我不喜欢读他们规定的那些书(笑);走上写作道路是偶然,我虽然考试不好成绩不好,但我喜欢读书,喜欢读我自己喜欢的那一类书。我读书看重两样东西,一个是文字优美、文笔好,再一个是文风好。”说到这里的时候,陈丹青做了一个很惊讶的表情,然后深有同感的表示这个观点很独特。他们同时讨论到余华的《活着》,作为陈丹青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作者,而作为韩寒是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作者,但对余华这个作家他们得出来的结论,《活着》故事性好,但文笔并不好,文学性也并不十分好。这个视频最近又找来看了一遍,顺便把《活着》再看一遍,也貌似懂了一丁点韩寒和陈丹青对话的意义,文学不仅仅是文笔、文学性不是仅仅故事性。
就这个意义上来讲,阿丁的这本《胎心、异物及其他》里的小故事,符合陈丹青和韩寒说的那种标准,即文笔优美、小品文的文学性凸显的非常好。我不是一个文科生,完全不懂为什么要把众多的作家按照各种各样的标准分成不同的流派,但这样的分派只能让一个初识文字的人感觉起来很confuse。在《胎心、异物及其他》中前面两篇短文很吸引人,一个胖子的爱情故事时下颇为流行,但结局和故事的穿透力却又具有十分强的穿透性,透过故事让人思考。
对于这样文笔较为优美,故事较为流畅的故事,我到是没有太多想说的话。你拿到书,读一读故事,看几篇文章,那种才情是能感受的到的。
读完真本书,也似乎不太明白书本标题的用意。取奇用极的做法,还是特别的强调这两篇文章的突出点呢?在阿丁的这本书里,故事都有很多笑点,但转折后遇到的痛点、泪点让人有种七上八下的感觉。读着轻松愉悦的文字,突然进入一种内心稍暗淡情绪,颇有座过山车的感觉。这是一种写作能力的锻炼,也是一种表现手法吧,我想。
《胎心、异物及其他》读后感(七):《胎心》读后
刚拿到这本书,第一篇就读了胎心这篇。大概是因为此刻我的肚子里也孕育着一颗小小的、还不到一个月的小生命。我想知道,将来这个小东西,会怎样看待有关于我的一切。
最早读到这篇是在阿丁的公共微信账号,是那个母亲进电梯并偷情的片段。单从这个片段是无法揣测这篇小说的全貌的,通过一个小小胎儿的视角,究竟能看到什么。
显然这又是一起新闻事件的重述。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这种角度呈现。阿丁说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荒唐透顶的新闻事件,小说创造重来不缺乏素材。看完《锁》与这篇,我基本是相信了。这本小说集,如果放在多年前,你可能会觉得故事太过奇特,纯属虚构,难以置信。可是经过这么些年,只要你稍加留意,就能在每一篇里找到故事的原型。人间惨剧时有发生,再多写十本也写不尽。
再回到这篇,没读到后半段,我的好奇心还停留在这小东西会想些什么、感受到什么上。不得不说阿丁的想像力是超乎寻常的,胎儿有思维么?乘坐电梯是否真的会不适并晕厥,对于周围的气味是否真能感知,抚摸会让它舒服。对于做母亲我还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我第一次听说胎脂、胎便,我甚至完全相信了阿丁对胎儿思维的解读。结局当然是有点玄乎,但纯粹如胎儿也感到了生而为人的耻辱,不愿与世人为伍,那么那些活着的、穿着衣服伪装成人形的残暴动物们,真的有资格称为人类么?
之前看过一个韩国恐怖片,让我相信胎儿是有感知能力的。说不清道不明,但那个时期它所经历的一切,可能更深的影响到他一生。就像人们所说的童年阴影、童年创伤。那个电影的男主角是一个残暴毫无人性的杀人狂,一手铸造了多起杀人事件。可看到结尾却觉得他非常可怜。他是为数不多人流手术失败而产下的胎儿。大概是在一名小小的胎儿时期便感受到了来自人类深深的恶意,尤其是来自于自己的父亲母亲,这种被遗弃被戕害的感觉比生下来丢进孤儿院,更加冷峻无情吧,它们滋生怨念与恨意,并深深的根植于一个胎儿最初的大脑记忆深处,伴随他罪恶与复仇的一生。
很庆幸阿丁这篇里的胎儿不需要经历这些了。虽然真实的事件里,与其相悖。为那个背负着耻辱的小东西祈祷吧,希望他不必背负他爹娘带给他的耻辱,健康的生活。
《胎心、异物及其他》读后感(八):喜剧演员的悲伤
我第一次读阿丁的书是那本《寻欢者不知所踪》,看第一篇就知道是我的菜,可是他的文字我一直不知道用什么合适的词眼来描述。《美颅》也是,一开头就被吸引——“初恋是神圣的”,这是关于一个死胖子的初恋,因为不被理解,这神圣的初恋,也只能被把玩与嘲笑。初读的时候,觉得煞是欢喜,但是很快,悲伤的意味来了。到死胖子摩挲着昔日爱人的颅骨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个悲剧故事了。
或许,我想到了比较贴切合适形容他的文字的语句了,那就像是,喜剧演员的悲伤。在看台下,我们跟着喜剧演员的一颦一笑陆离搞怪而哈哈大笑,谁知道欢乐背后的眼泪?或者更贴切的说,是那带给你欢乐的欢乐的悲伤,你是否了解?他的文字畅快、够辣,但是往往,笑着笑着,有人就这样笑下去了,有的人却笑出了眼泪。
很奇怪医生这个行当,为何转行了做起文字工作者,都要比别的职业转行过来的辛辣、一阵见血,而且还时常用表面的怪诞戏谑来掩饰骨子里深刻的悲伤。麻醉师,也算医生的分支吧。阿丁的文字中写关于医学的,那是顺手拈来,比如《美颅》比如《胎心》。《胎心》我初读的时候有点看不懂,但是我觉得看完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实都能看出来,这个故事是影射的哪个新闻故事。小说没有评判是非,只是单纯的用一颗初初来到世界上的稚嫩的心脏在感受一切。我想,这是一颗敏感的心脏,而作者也有一颗敏感的心脏。在那颗稚嫩的尚不知善恶的心脏的世界观里,他们——他们又是谁呢?他们能够告诉他这个世界的原罪和不公平是为什么吗?一切都是无解的,这已经注定是被遗弃的一颗敏感心脏,于是他将自己弄成了难产的姿势,他在懵懂未知时已经知晓了愤怒的滋味。《异物》写了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我实际上没有看的太懂,模模糊糊,感受到阿丁在接触那些边缘、追求自我的人的世界的时候的困惑。看的比较难过的故事是《顶硬上》,每一次看袁崇焕的故事,心里就充满了悲怆,更是为佘义士的17代守诺而感动。
《我不喜欢开玩笑》更像是个玩笑,《高考》和《死党》结局吊诡。我相信很多人都能从那其中读到新闻事件的影子,可是,真实的生活不就像个玩笑,有时候结局出人意料吗?
阿丁是个写故事的高手,同时,他也蛮高产,我喜欢看他的故事。更喜欢那笑看冰冷现实的一点点冷酷,嗯,就像个医生一样。
《胎心、异物及其他》读后感(九):这世界的夜晚 ——《胎心、异物及其他》,暗黑的镜像
这世界的夜晚
——《胎心、异物及其他》,暗黑的镜像
还记得《无尾狗》中那个长长的白色巨塔中的暗影的读者,大抵是不会忘记阿丁的风格的,这个前麻醉师总是带着一种口罩罩住的模糊不清的面孔,却眼神犀利而让人震动的感觉。幻象、吸引力,甚至是说明不了的那种被麻醉后的欣快感,以及阅读完成之后的被现实世界激动的冷痛,吸附在他的作品上,让读者总是欲罢不能。
《胎心、异物及其他》作为一本短篇小说集,充分的展示了社会的多样性的一面——当然,主要是这城市略带疯狂和迷离的夜晚。人们会为这夜晚的五光十色和灯火辉煌而沉醉,也会在这夜晚阴暗和湿冷的夜晚中体会城市的丑陋的面貌。
阿丁的故事们总是光怪陆离的。在父母肚子中的胎儿会有思想么?真的有小偷能够秒开大门终成一代名技师么?有八旬老翁会被七旬的老汉刺杀么?有有钱的董事长会邮件通知离家出走么?这些故事看上去都那么其特而不真实。而这些不真实的设定,可悲地让我们觉得太过贴近生活。
是的,我们似乎是见过《胎心》这个故事的。在社会新闻的版面上,曾经有过一个护理学院女生被孕妇诱杀的新闻。我们也曾听说6070年代曾经发生过的惨剧。城市中人们死在隔壁被发现的小报版面上的都市传说一样的新闻也屡见不鲜。被构陷的入狱、城市中本地人对外地人的“蝗虫”评价……目录里面,一个个列举的故事似乎就不再是故事,而是某年度这城市当中不可思议但是确实发生的新闻的某种集锦了。
这是夸张,我想要这样否认。但是当我们从网页弹出的新闻里、从手机客户端看到的头条里、从报纸的社会版面里,都找不到否认的理由。甚至,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疯狂。
山东招远的麦当劳的血案,杭州、烟台等地的公交车案件,女大学生搭错车遇害案,地沟油、过期肉——媒体人永远也不乏吸引眼球的血肉爆点。而我们也因为这些,在一次次冷酷的事件当中变的冷漠和自我,也在一次次欺骗和被欺骗当中塑造刀枪不入的精神壁垒,无奈而又凄凉。
人人都有病。精神世界的痛苦似乎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阿丁的故事里面,有《美颅》这样虽然诡异却可爱的爱情,也有《异物》这样找不到自我的自我价值的丢失。这个夏天,连一贯标榜传统唯美的韩剧都来了一发《没关系,是爱情啊》游走在多重人格的边缘。我们在找什么呢?我们在找自己的过程当中已经丢失了那个单纯的自我,而没有丢失掉的那一部分,也被沉浸到欲望当中了。
这是这个世界的夜晚,是《罪恶之城》式的,也是阿丁自己的风格的。它说着最残忍却也最明白不过的事实,它是现在,但希望不是将来。
y 林怿
2014-08-22 14:55
写于5号6楼
《胎心、异物及其他》读后感(十):真实点,抽出新的嫩芽
阿丁做过麻醉师,所以他的小说中涉及医护知识的不少,甚至在《鱼以及饵》中设计了一个“蓝翔卫校”的故事发生地,很是有意思。同时,他的小说中还有着一股浓重的福尔马林味,飘扬在每个角色的身上,即使是《魂斗罗》中的孩子们,无一幸免。那是种什么味道呢?就是把抽干了情绪的真实。
阿丁曾在《无尾狗》的采访时说,他书中的内容只有三成不到的真实,剩下的都是虚构,但虚构未必就是不真实。这《胎心》这本书中,阿丁延续了这种“虚构”,书里的很多故事甚至能在现实中找到相对应的新闻素材,譬如《死党》中那个城管与小贩的纠葛,那个叫强强的爱画画的孩子,指向是多么的明显……只是变成了小说,变成虚构的人和事,却仿佛更多了层真实。这种真实就是阿丁的矛,是他在无论长篇或是短篇的创作中都极力保留的东西。
他的矛总是不遗余力的刺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也许真实的疼痛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获得。阿丁做医师时,用药物麻痹人们的疼痛,改行做作家后,倒是更加卖力的撩拨人们疼痛的神经元。他选择的角度既有少年人纯纯的爱慕(《美颅》),也有少年学校的旧时记忆(《魂斗罗》),甚至巨细靡遗的描绘了一个老人对孙子深邃的爱,却又在故事结束之前,给了他一把仇恨的刀……这为小说造成了一种很古怪的真实感,让人痛,却又摸不清伤处,就这么直愣愣的感受着,说是情怀也行,当个故事随意看看,也行。
坦白说,《胎心、异物及其他》这个名字实在有些随意,仅仅感觉像是为了说明是小说集而随意捉取的。而里面的故事也和这名字一样,选择的都是世俗生活的普通人。他们以普通融入这些故事背后,看似荒诞,却又好像有迹可循。像是于丽娜,那个在《我不喜欢开玩笑》中因为玩笑而摧毁一个男人的女人,这个故事有多么的荒诞,但一切又发生的顺理成章,像是故事的结尾那样——“这世上还真他妈发生过这种事”。而为了从所有的虚构中脱离开来,阿丁还将好友孙一圣也引入其中,他赋予了孙一圣清秀、干净的形象,使他成为了两位宿命截然不同的女老师联系的线索,和读者对照二人的镜子。这种方式,在阿丁的《寻欢者不知所终》里就有所涉及,读者通过这些虚拟又真实的人物,将书中的故事也虚虚实实的读下去。
黑塞曾有首诗,诉说着春天的生命力,“活下去,生长吧,开花吧,爱吧。高兴点,抽出新的嫩芽。”阿丁却反其道而行,在所有负能量似的故事背后,用真实,抽出了生活全新的嫩芽。阿丁在《锁》中通过主人公告诉读者,这个世界由千千万的孤独构成,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每扇门的背后拥有着怎样的人生。但只要有故事我们却总能知道一些。阿丁的故事以灰暗的方式让我们面对真实,生命脆弱的真实、生活残酷的真实,以及荒谬中总有新芽的那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