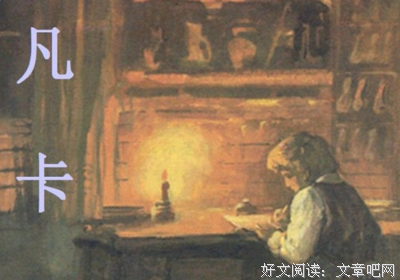《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是一本由唐诺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51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读后感(一):漫长的相逢
用了两个月终于看完,之所以耗用这么长时间,一来篇幅确是不短,509页,44万字;二来每个句子也很长,总是有两个以上的副词并排开去,读一句话都会让人上气不接下气;三来作者的思维太天马行空了些,很多时候会让我追不上。 但收获还是很大的,主要是信息量很大,从中让我认识了约瑟芬-铁伊、雷蒙德-钱德勒,作者多次援引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文字也让我坚定了去看这两位文学大家原著的信念。 就把它当做很多很多书的压缩版吧,读完了这一本不太好读的书,权当快速地看了很多很多的书。这样一来,这书不是太长了,反而是太短了。 因此,通篇看完,方才提到的缺点也变成了优点:篇幅和句子的绵长算是对我即将要看的俄国超长篇的锻炼,思维的天马行空也应该对我即将要追的意识流巨著不无裨益。 最后再吐槽两点,这也是我没给它打五星的原因:一、书的装帧很差,才看了一天书皮就开胶了,真的很恼人;二、作者似乎是个星座狗,如果没记错,书中用星座来分析人物的地方接近十次,每次看到我都会用笔在上面不留情面地画个大大的叉。
《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读后感(二):常常沒有辦法得到的一種優待
我會推薦唐諾這兩本書,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唐諾作為一個作者,他能夠用我們很少看到的有趣活潑的或者帶一點辛辣諷刺的輕蔑態度,來解釋一些在台灣常常被忽略的一些概念,這些都是在一些高傲的知識份子寫書的時候,常常沒有辦法得到的一種優待。我覺得在看唐諾寫推理小說的時候,能夠因此吸收到非常多...老實說跟推理未必那麼有關的想法,一些歷史上的演化過程當中所產生出來的支線的知識,這些都是閱讀的樂趣。如果你是希望很有效率地吸收推理小說的簡介,我覺得唐諾的書未必是首選,可是如果你要讀一本有趣,然後可以遍及地去培養出非常精確而且標準比較高的對文學的鑑賞能力,我覺得唐諾做了一次非常好的示範。
《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读后感(三):如何不剧透地推荐一本推理小说
早几年时间,大家似乎对“剧透”这件事还没那么敏感。好的小说、好的电影,看过的人从头到尾细细讲来,讲得好了,眉飞色舞,点评加注,听的人如临其境,仿佛自己也完完整整看过一遍。过后也一定记得,如有机会,自己也要找来看一看。至今还记得初中时同学讲给我听《燕尾蝶》和《梦旅人》,带着阴冷残酷的色调。多年以后自己真的找来这两部片子看时,观感却并不尽相同,语音的记忆和眼前的画面相映成趣。
通过转述来推荐一部作品,费劲唇舌地想用自己的语言传达出它的好和自己的喜爱,而不惮于“剧透”的条件或许都建立在那四个字上:“如有机会”。在看电影还要去录像厅、租碟乃至只能看“内参”,小说还要借助图书馆或是手抄的时期,这个自己真的看到“机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来。所以“剧透”并不可怕,信息占有的不平等普遍存在,而且是被默认的。人们甚至有点希望“被剧透”,那样自己也就可以占有这些信息,转头去对他人“言传身教”,抢夺信息的制高点。但现在不同了,每个人都被海量的信息环抱,接触的机会似乎都是均等的。只需要你告诉我一个名字,一个评分,或者仅仅是“好看”两个字,就可以自己去看,并不需要你告诉我后面展开如何。
只是偶尔被问及“好看在哪”,难免束手束脚,一时语塞,生怕不小心“剧透”。这种情况在推荐推理小说上,尤其困难。推理小说的华彩往往就在谜题解开的那一刻,想要不带一点剧情地推荐一部推理小说,似乎也是“mission impossible”了。所以唐诺上一部推理导读集《八百万零一种死法》放了很久并没敢翻开,总想着先要达成看完全部马修•斯卡德系列的“雄图霸业”。误打误撞,反而先看了这本《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因为翻翻里面的作品,似乎没有打算看或是感兴趣的,不怕“剧透”。
但唐诺不愧是唐诺,达成了这个“impossible mission”。身处这个巨大的文字迷城里,很多时候都让你忘了这是在看一本推理小说导读。
不谈剧情,他都谈了些啥?
唐诺写自己打谱逾十年,近半数时间摆的是吴清源的实战谱,在其他的文章中也常常会提及吴清源的棋与人,可以看出其中偏爱。但吴清源能和推理小说有什么隐秘的联系?书中提到的这篇,是汉密特《玻璃钥匙》的导读。落笔先写吴先生当年“十局大赛”的光辉战绩,再写吴先生棋“快”:思考落子的速度往往只对手一半或三分之一,从布局到缠斗脚步轻快,一骑绝尘。竟为的是引出《玻璃钥匙》开篇的“快”和对小说节奏快慢的讨论。在抽象地谈论节奏,进入听上去让人昏昏欲睡的“文论”之前,黑白子相互追赶的紧张形势和吴清源落子生风的身姿已先行进入了脑海。《玻璃钥匙》讲了什么只字未提,留着我们自己去感受汉密特的“快”脚步。
东尼•席勒曼的推理小说深深扎根于纳瓦霍族印第安人的文化,主要侦探角色也是纳瓦霍人,并不是古典推理那种移地观光式的写法。于是导读中唐诺用十来篇文章来向读者讲述了纳瓦霍的创始神话、生死观、性别观、对恶的定义等等。即便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这个民族,读过之后,你也会深深记得他们的诞生之地是四面圣山环绕的“四角之地”;现在是第五世界,由自地底第四世界而来的人们建成;他们异常忌讳死亡和与死亡相关之物,没有轮回转世的生死观,却又对衰老者的逝去显出异常的豁达;凯欧狼是恶的化身,同时也颇具智慧、给人以启发;纳瓦霍语作为没有文字的语言,是二战中盟军使用唯一没被破译的密码……另一方面,原生文化面对强势文化介入如何自处也是他不会放过的好论题。
数数古典推理的大限
这是书中为数不多让人感到确实在读推理导读的段落。倒也不太费心解释,默认面对着一群对“古典推理”“冷硬派”“本格”“社会派”等切口已熟稔的推理迷们。唐诺多次谈到古典推理诡计的困境,因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因为纯粹理性难题的解答需要历经几代人的努力。其中多少有自己身为书写者的思考,所以他最津津乐道的是那些在各类型、派系成规中寻找突破的尝试。比如阿婆借由马普尔小姐在一派英式贵族风气的古典推理中打开了一片下层平民的视角,到更新近的被唐诺赞为“新的推理女王”的米涅•渥特丝,这下层的视角中又添一分“左”的激进色彩。面对古典推理“不谈恋爱”的明文规定,他认为多萝西•赛耶斯颇具争议的《俗丽之夜》坐实了作者与自己笔下侦探温西爵爷的恋爱,加入了罗曼史反而为赛耶斯的写作冲出一方天地,在卷轶浩繁古典推理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特殊性和新的可能。又或者如丹尼斯•勒翰,学习好莱坞,打通各类型的界限,迎头把握住潮流的所在,又不忘在作品中加入点自己所坚持的元素。
他所着墨最多的也是那些不那么为人熟知的作者,比如米涅•渥特丝、比如写纳瓦霍探案故事的东尼•席勒曼、比如法医出身的派翠西亚•康薇尔,几乎是连篇累牍。而那些鼎鼎大名的,就一笔带过,比如埃勒里•奎因,短短一篇,甚至让人觉得有些敷衍的味道。
博尔赫斯与本雅明常在嘴边
这两位的话常常冷不丁出现在文中,此外不止一次被点名的还有卡尔维诺、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格雷厄姆•格林,以及朱天心。但这些“引经据典”的段落往往并不突兀,有时还能让人会心一笑,他们的出现更多像一种信号:现在我们要谈点严肃的话题了。
一处引用博尔赫斯评《神曲》的《贝雅特丽齐最后的微笑》,构成了那篇导读标题“只为着偷偷塞进去一些东西”。原以为只是个讨论作者“夹私货”的篇目,其实源自博尔赫斯对《神曲》的一个美丽猜测:也许但丁写下这不朽的诗篇,“只是为了插进一些他同无法挽回的贝雅特丽齐重逢的场面”,如同他提到六十个女人的名字,只为了偷偷塞进贝雅特丽齐的名字。唐诺借它来比康薇尔类型小说写作中“志业”的追求和虚假故事中的真实,延展到现实人生中人们的职业、志业之辩并非不可调和,我们仍可以“在六十个乏味的工作中偷偷塞进去一个名字”。他自己说这种比法有些“糟蹋好东西”,但却令读者难忘。
不忘现实世界的当下与未来
导读中常浮现台湾社会的影子,其时岛上走红的电视明星、正在发生的选举事件与响亮的政治口号,原住民的生存抗争……与所推荐的小说篇目论题打通,笔锋就会触及。在末尾乔瑟夫•芬德《偏执狂》的导读中,更联系到国家企业化的进程与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忧心的未来。如此读来,一个个推理小说就不只是存在于纸上只供消遣娱乐的探案故事,它与严肃文学血脉相系,更与现实息息相关。
在“最后致意”中唐诺提到推理小说是特殊的,少有如此讲求知识、讲求理性的小说创作,并且为了保持活力、设计出新的诡计,作者们还会不遗余力吸纳各种知识,把推理小说建构成一个“各种知识碎片组成的世界”,天文地理无所不包。这些碎片的储备指不定什么时候能为读者开启一片崭新的世界。
好的导读和推介似乎也是如此,也许深度与广度达不到,但脱离开它所要推荐的文本依然有其可读性与生命力的,充满宝贵的知识与思考的碎片。“剧透”,在这里也就不是个问题了。就像唐诺的这些导读,仿佛一座文字迷宫,角落中藏着小小的宝箱,等你一路发现。但并不会迷失其中,忘了出发点,铁伊的《时间的女儿》、渥特丝的《冰屋》、席勒曼的《亡者的歌舞之殿》……一系列推理小说一定已经悄悄列入了你的计划书单。
《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读后感(四):将类型小说读出纯文学的哲理
唐诺的《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和《八百万零一种死法》一样,是他为推理小说写的导读。导读推理小说当然不能剧透,于是唐诺跳出罪案本身,从推理小说中提取最不推理的内容,去研究小说家们的技巧。比如约瑟芬·铁伊善写细节塑造圆形人物,而不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模式化人物,即使她们的小说都很好看。唐诺从推理之外看推理,将它们延伸到更纯粹的文学层面,思考小说家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呈现出最极端人性之恶的小说世界。
推理小说导读和唐诺之后探讨纯文学(乃至文学观念)的长篇宏文不同,这些借题发挥的小文章是亲近的小品,在不长的篇幅内介绍各位作家的风格,又不失唐诺善分析的特色,所以读起来比较可口。就像喝汽水而不是喝酒,感到冲击喉咙的爽快又不会宿醉而头晕。
“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源自《圣经·士师记》,恰切概括了推理小说笔下罪案横行的混乱模样,直到最后“王”出面将这一切荡涤干净——是澄澈清明,仿若大雨过后的蓝天;还是阴沉压抑,发现豪雨过后只会倍加闷热——这就是英式古典推理与美国冷硬派推理的区别了。
这就是本书聚焦的两个方面。从个人兴趣看,他更偏爱后者,因为前者即使再精巧,也不太好解释:死亡这么严重的事情,难道仅仅为了显出侦探的智慧就该让它发生?相比之下,美国冷硬派(hard-boiled)小说将侦探卷入严酷的现实,让他们身不由己,看到自己并非拥有万花筒般的技巧可以辗转腾挪,轻松干净地站在局外解谜,占据智商和道德的双重特权,他们必须硬碰硬地直面这个不宽容的世界和深达内心的黑暗肮脏,与罪案搏斗也是与内心的魔鬼角力。这样的小说,或许与真相贴得更近。
推理小说中的罪案是为了逼出人性的恶之极限,从而发现一些人性中的问题和可能。罪案的背后窥见的是人心,但人心的错综矛盾并不必然以罪案来呈现。因此唐诺越分析推理小说,就越会觉得它们处在“未完成”的状态。有些东西纯文学已经走得更远,而推理小说因为题材的牵涉,必然要牺牲一点深刻,去满足读者追求刺激和速度的欲望。但不可否认,推理小说具有的智力和专业性(将每个领域都用科学化的视角精细解剖),一定是读起来永远不会过时的好东西。
《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读后感(五):少作
唐诺说过,45岁之前的作品,他都没有留底,他认为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是《文字的故事》。这部《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是他的少作,写于他45岁之前。
再之前,则是《遍地神迹》,一部NBA篮球评论集。这三部作品风格差别明显,很能够代表他三个不同时期,由青涩渐渐变得成熟,用他的好友张瑞芬的说法是“九0年代中后期以降,结合社会观察与博览群书的‘杂家’、‘博议’书写风格就确立了,只是近年纯度愈炼愈精而已。”
毫无疑问,本书的精纯度还不够,没有《文字的故事》以后诸书的穿透力。这样子说好了,看完这部书后,如果哪一天我想找点侦探小说看,我会重新翻开它,依着唐诺的指引,逐一找来读。否则,它就可以束之高阁了。然而,《尽头》不是这样子,《世间的名字》不是,《眼前》也不是,它们是我会时常重新翻开来读,不一定会从头读到尾,尤其《尽头》这种大块头,我会挑某些篇章来读,再一次顺着唐诺的思绪,叩击某些问题的大门,又或者再一次聆听唐诺始终坚守着的某些价值信念。
在我身处的这片大地上,唐诺的读者不多,但也有一些。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他的书后,会对他时常讲的这些价值信念在意,有多少人会愿意将它接过来。在《文字的故事》后的系列书写中,唐诺经常会引用到日本的一种称谓,即“一代目二代目三代目。”我们这一代应该有很多人对这几个名词不陌生,只要你看过知名的日本动漫剧《火影忍者》。唐诺的昔日挚友骆以军也很喜欢它,并写过一部以剧中角色命名的书叫《我爱罗》。我觉得唐诺没有看过这部剧,他是从日本的文化中借用过来的。“一代目二代目三代目”这种称谓,这种文化本就深深植根于日本,他们有很多专门的技艺,很多百年的老店,都是这样子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的。正如唐诺多次强调自己的书写是希望诱拐更多的读者去读更优质的文学,我相信他在这些书写活动中,一再伸张他坚守的价值信念,也是希望有人听到,有人接纳,有人继续“一代目二代目三代目”地传递下去。
这些价值信念为何?太多了,其实即便在他的少作如这部推理小说导读文集中,也早见端倪。“勇敢不同于血气,它通常不来自鲁莽挡不住的性格使然,而是对某个信念或某件自觉有价值事物的坚持,因此甘冒其他不韪的意志和决心。”“一个以写作为职志的人,如果不信任生命本身莫名的驱动力,还能信任什么呢?我总想像真正的创作者像某种蔓藤类植物,它外表纤弱,但本能地缘墙缘树而上,有多高爬多高,在力尽之处仍奋力将触须深入空中,迎风试探。”
可以了,抄再多也无益,重要的是去读他的书。对于这部书,如果你想看点侦探小说,又或者本就喜欢看侦探小说,我很推荐你买来读读,不然还是从《文字的故事》开始看吧,这是他的第一部书。
《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读后感(六):《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满嘴扯闲篇的类型小说推广?
今年我下定决心要好好看两本大部头的书,这本相当于至少两本标准侦探小说的推理小说科普集子就此进入了我的视野。本来是想要看看一个推理小说爱好者,本着推广类型小说以及顶着作家的头衔会给出什么诚意之作的,只是没想到看了一本长篇大论满嘴跑火车的长书。还我时间来!
开个玩笑,这本书虽然不禁让我满意,但大致上来说还是有些收获。作为推理小说、悬疑小说和剧情片的爱好者,不理清楚这种类型文化的历史是不行的。在跟朋友装逼的时候,不知道几个小众的不错的作家似乎也说不过去。本着这样的目的,这本书的水准还算叫人满意。即使之前对英美推理小说再不懂,看完这本书也至少知道了所谓的古典推理小说两次黄金期和推理小说在新大陆的冷硬派变体。然而这点了解似乎并不能让一个求知欲更旺盛的人感到满意。据我所知,欧洲大陆上还有很多知名的推理悬疑小说家这本书完全没有涉及,至于近邻日本独特而适合中国人口味的侦探小说更是只有宫部美雪和横山秀夫这两位入镜。当然,这本来就是一本导读的集子,在不知道会集结成书的情况下,编排不周也是常有的事情。只是真的作为书拿出来卖了,注重全面还是必须的、至少的诚意。
说完了对内容编排的不满,然后就要说到作者的思想性和文笔了。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我深知在引用名言表现自己思想性时的一大窘境:有些名言和例子如影随形,每次写文章都忍不住想要引用。但是只要用上个两三次,读者都背得出这段话了,这种引用就会被读者认为是无能的表现。有时候,甚至同一个名人出现的次数多了都会引起别人的反感。唐诺似乎就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引用喜欢看推理小说的博尔赫斯的话没有问题,把马尔克斯的段落拿出来作比较也可以,把文学理论家本雅明作为引用对象也很高,但也不用通篇都是这几位吧?我想作者不至于阅读范围这么受限制,以至于只能引用这老几位的评述。一个作者就是要站在读者前面,大声高呼门里边的世界有多么精彩。如果叫读者都看透了他们会使用什么梗,就显得弱小了,很难服众的。如果把引用的逼格放在一边,这本书的思想性倒是还有一定得水平。但是毕竟这不是思想史著作,读者翻开来也不只是为了听作者扯闲篇的。很多观点都并不新鲜,至少我翻开来的时候没有太多惊喜可言。不知道这和这本书毕竟是十年前的作品有没有什么关系。看到要让枪手打死蔡英文的那一段我倒是笑了。
作为一个挺宽容的读者,我很少给四星以下的评价。这本书本不该获三星殊荣,只是因为它太长了令我生厌,在感性上又给扣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