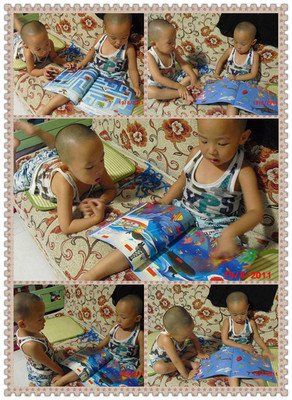《书蠹牛津消夏记》是一本由王强著作,海豚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48.00元,页数:27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书蠹牛津消夏记》读后感(一):装帧精美的书
买藏书大家出的书,有时会惊艳。比如韦力的几种:《得书记》、《失书记》、《古书之爱》,以及现在价格炒上去几倍的《芷兰斋书跋》初集,都称得上秀雅精致,内容充实。我想,原因是好的藏书家对书特别讲究,自然不愿自己的书出得不像样子。 可惜韦力收藏中国古籍,他写的书却不能雕版印刷、线装装订,如他钟情的宋元善本一般。在这方面,收藏西方书籍的王强就幸运得多:他能把自己的书做成心仪的理想模样。比如我手上这册《书蠹牛津销夏记》,就能让读书人如登徒子见了梦露一般,神不守舍、目不转睛。
此书16开本、圆脊,书口刷金,这就比较特别了,因为中文书刷金很少见。硬纸板精装;封面用特别定制的朱砂般的正红色PU,纹理细腻、手感柔和;书名题签与封面双栏都烫金压印,触摸上去有明显凹凸感;这都让人欢喜。最特别的是在封面下部,以浮雕工艺呈现了英国名画家透纳画的牛津高街,效果惊人。这书做得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觉得:富丽堂皇!
打开书,环衬的图案与色彩很特别。我查了一下出版社微博,原来环衬特意使用了来自奥斯曼土耳其特有的 “湿拓法”工艺。微博上这样介绍“湿拓法”:“轻轻滴落在水间的颜料渐渐随水波晕开,等到水上图画完成后,再将白纸盖在其上吸取颜料,然后将纸慢慢抽离水面,继而神奇的、不可复制的“水中画”便由此诞生。”这环衬和封面一样,本身就是高级的工艺品。
书除了前后序跋,主体分为四部分。每部分之前有半页极薄带暗花的透明扉页,用绿豆为原料的描图纸制成,每页扉页暗花都不重样。内页的纸张厚度、白度恰好,不透字,十分挺括,翻起来很有感觉。版式上段落、字体、行间距、天头地脚的安排均美观悦目。每章题目上又印有别致的题花,每章题花也都不同。相关几百种书影的彩印插图亦极清晰,位置安排基本能紧密联系文字段落,却不会过于影响阅读。页码数目字用了特别的暗红色花体。可以说,这册书各处都能看出设计者、制作者的巧思与技术来。
连封底也有惊喜。正中金色双圈中印了一位秃顶修士骑马的图案,图案源于英国乔叟的名著《坎伯雷故事集》。图案摸上去是凸起的,原来用了热转印工艺。朋友看了说,此书英伦风很浓。诚哉此言。
这本写西方书籍装帧、版本与藏书故事的书,在书的各部分用上相应各种西方现代书籍装帧工艺,内页各处也特意运用题花、花体阿拉伯字母等等西方古籍的若干元素,加上里面又有几百种珍贵英文书籍的漂亮的彩色书影,因此有内容与形式之间互相呼应、相得益彰之妙。我翻阅起来真觉得琳琅满目,爱不释手。
这本让人赞叹的书当然也不是没一点毛病。比如封面书名题签写的是:书蠹牛津销夏记,这是对的。扉页上书名却是“书蠹牛津消夏记”,而书的序言中也用这个书名。书名用“消”字肯定错了。唐代白居易《销夏》诗:“何以销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唐陆龟蒙 《奉和袭美<太湖诗·销夏湾>》诗:“遗名复避世,销夏还销忧”。都可以证明应该是“销夏”而非“消夏”。
第二是环衬黏贴太紧,让书不能轻松打开,也不能摊平。半圆书脊不能摊平,不算合格。虽然些许白璧微瑕,但从装帧整体来说,《书蠹牛津销夏记》的确是集合了不少西方装帧工艺,让人开眼界、长见识。
海豚出版社出版。海豚的主事者俞晓群是一位很有追求的出版家。他在辽宁教育出过轻巧、朴实、合用的新《万有文库》。到了海豚后他特别重视西方装帧工艺技术,出过著名的维德《鲁拜集》。他做的董桥小开本很漂亮,陆续在出的“海豚文存”系列也有特色。负责此书印刷的是北京雅昌艺术印刷公司,这是中国最好的印刷公司,特别在画册印刷上。2008奥运会中国的申请报告就是雅昌印制的,嘉德的拍卖图录也是由雅昌负责。作者自己是行家里手,出版与印刷都是好手,这才能合作做成这么漂亮的一本书。
随便说说书的作者李强。新东方的三位创始人之一,现在做天使投资人。他最大的爱好是藏书、读书,重点在西方近代文史的珍贵版本。他在这方面的收藏数量质量在国内是第一流的。他说的这句话:说到藏书,总有人问,你要挣多少钱才买书?这太外行话。当你有钱才想到买书的时候,已经离书很远了。我觉得,对于真正爱书的人,永远不要问他两个问题:这书你花了多少钱?你买的都读过了吗?我很有同感。
他买书藏书并不是在发家之后。他在初到美国第一个圣诞节,夫妻两人账户上仅有29美元,他也去买了一册《鲁拜集》。看书和谈恋爱一样,爱了就不管不顾了,如果要万事俱备才去看书去恋爱,那能叫爱吗?当然,这不是叫人不切实际,而是说人要真喜欢一样东西,就会克服困难想尽办法去争取。于是我买了《书蠹牛津销夏记》,而且从书里还找到了买书的充分理由。
《书蠹牛津消夏记》读后感(二):王强的读书乐:“像唐老鸭在成堆的美元里泡澡”
对于藏书者的读书之乐,没有比意大利作家艾柯描绘得更好的了,他大胡子嘴上叼着雪茄,不无惬意地说:“必须一个人在晚上翻阅它,就像唐老鸭在它成堆的美元里泡澡一样。”(《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
我自己藏书最高时也近万册,对艾柯的比喻自然心有戚戚焉。可近日读到王强的《书蠹牛津消夏记》一书,我却有点自惭形秽了,因为我的藏书多是国内出版的“大路货”,他收藏的则是外国名著原版,有的还是初版。两相比照,王强才是艾柯所说“像唐老鸭在它成堆的美元里泡澡”的人,而我充其量只是“在人民币里泡澡。”
中国内地出版的书,装帧普遍比国外和港台的差,但2011年故宫出版社的《陶庵梦忆》,选取《十竹斋笺谱》作插图,加上栾保群先生的注解,让人惊艳。海豚出版社这次为了做好王强的书,特意派人去欧洲学习装帧技术,除了牛皮精装外,封面油画还用了烫金工艺,摸上去有凹凸感,让书的触觉更舒服了。
王强让我妒忌,不只是因为这家伙收藏了20个版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囊括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这两百年间有代表性的作品,他买书的故事也很有趣。
伦敦书店有套王强心仪的《兰姆著作集》,可惜被“雅贼”顺走一册。老板愿意半价卖给王强,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没买,“我把这套书抱回家,直到生命的终点,一定会天天记挂这消失的一卷兰姆,这会让我失去阅读其他所有书的兴趣。我会天天琢磨它,寝食难安。除非我亲眼再见到它,亲手抚摸过它,知道它经历了哪些故事最终又回到我手里得成全璧,心灵才获得彻底解脱。为了不让自己深陷执着沉迷的无望,我必须割爱。”这种对藏书的爱,他还用了维吉尔的诗句来形容“犹如母熊舔仔,慢慢舔出宝宝的模样。”(杨周翰译)
逛欧美的书店多了,王强也晓得了不少门道。比如,架上那些珍本书,怎么取下来,怎么用手翻,怎么将其归架,都是大有讲究的。“稍不留意,就会把书弄坏。店主心疼他的宝贝,眼睛会像探照灯一样,紧紧盯着你,烧得你畏手畏脚。你必须让他产生信任,接下来的时光才会属于你。”所以,在书店逛的时候,为了早早获得信任,王强常常故意走到书商眼前,取下一本比较贵重的书,“露一手”给老板看。场面之微妙、刺激,还真有点像《林海雪原》里土匪接头,主人说“天王盖地虎?”来客必须对“宝塔镇河妖!”之后才算是自家兄弟,喝酒吃肉,其乐融融。
从“书话”写作看,王强的文字不算出色,他没有黄裳的清峻、孙犁的隽永、董桥的精致,更不要说周作人那“佛骨舍利一样的内蕴”了。但他见多识广,思维活跃,比起一般的读书人,更有“生”气。
王强收藏了不少《爱丽丝漫游奇遇记》的英文版,这貌似只是一本儿童文学书,为什么却引起书友前仆后继的集藏?他先是想到了贝克夫人《阅读的首次历险》里的评论: “英格兰的空气中存在某种东西——或许是北部湾流气候令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雾气濛濛,晦明晦暗——这使得英国人形成结论或诉诸行动时,更多的是靠触觉而不是视觉,着意避开拉丁逻辑所固有的尖锐清晰的轮廓。……从事物的本质方面说,这恰恰是儿童与他们生活的世界互动的方式,只要大人们允许他们不必长大。”这段话从地理学、哲学、民族心理学角度解释了一个民族对某部文学作品的热爱,未必可信,但绝对可爱。
可《爱丽丝漫游奇遇记》的粉丝不只是英国人,又怎么解释呢?还是要回到文学本身,王强提出了“没有意思的意味。”二十世纪初,两位中国文人已经敏感注意到了《爱丽丝》中“没有意思的意味”对人的精神成长的必要性和重大价值:一位是赵元任,“没有意思,即不通、不成事体,要看不通派的笑话也是要自己先有了不通的态度,才能尝到那不通的笑味。”另一位是周作人,“人间所具有的智与情应该平均发达才是,否则便是精神畸形……对于精神的中毒,空想——体会与同情之母——的文学正是一服对症的解药。”
接下来,王强还节录了一篇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论文。虽然引文不完整,大意却可以猜出: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很多哲学困扰是误用语言造成的,“词语的组合若不可能准确被理解,就是无意义”,应该“赶尽杀绝”;后来维特根斯坦慢慢认识到,语言的意义在运用中,“无意义的语言”也有意义。他还引了文学评论《无意义的诸意义》里的话,“他们(乔伊斯等现代派作家)的实验性写作,蔑视语言的意义制造功能。他们是在人们通常理解的意义边缘甚至之外写作的。”
这“没有意思的意味”,其实还可以从很多角度补充阐释。有学者就认为,当代作家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味道。汪曾祺自己解释说:“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联系的。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
这么说吧,语言的无意义、句子的稀松平常、人生的空虚发呆,就像是围棋的“气”、藕媒的“眼”、国画的“留白”,正因为它们没有被“意义”填满,才有了全局的“生”气。这大概也是王强要花大精力读“无用之书”的原因吧。
三,翻译与文本细读
王强自承,藏书读书受钱钟书、周作人影响。但他英文明显比中文好,看起来受钱钟书影响更大些。他以前写过一篇《关于索引》,先是追朔了“索引”的英文原义,然后提到约翰逊博士《英语辞典》index释义之三“书之内容表”下,征引了莎士比亚悲剧《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中的一段话“And in such indexes,although small pricks to their subsequent volumes,there is seen the baby figure of the giant mass of things to come at large”朱生豪先生据以意译为:“但一隅可窥全局,未来的重大演变,未始不可从此举的结果观察出来。”等于就把具体的比喻漏译了,王强直译出来是:“就这些个索引,虽说对于其后的书卷不过是区区的小刺/撮要(此词这里双关转义),却也从中可见未来全局巨人之躯那孩子般的身影。”这就更有利于读者把握原意,体验莎翁“语言多喻”的美感。
这次,王强又说买了高罗佩“狄公案系列”的英文原版和法文版,将之与中国内地风行的海南出版社2014年版8卷本《大唐狄公案》对照,着实出了一身冷汗,原来中译本窜改和肢解原著比比皆是。比如,高罗佩写林中警觉的狄公:“His hand moved to the hoit of the sword hanging on his back ,”王强译为:“他的手探向背在肩后的宝剑剑柄,”南海出版社版则译为:“狄公不由紧握住腰下佩着的雨龙宝剑的剑柄。”将宝剑从“背后”移之“腰下”就是窜改,更让人气愤地是,“将那只手‘尚未触及’的动感的悬念,定格为‘已然紧紧握住’的静态结局。”高罗佩原本是想刻写狄公的“警觉”,南海版这样一译,不就成了“害怕”吗,狄公威武何在?
但揪错并刻薄别的译者不是王强的本意,他的关怀在于,“高罗佩的‘狄公奇案系列’用的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材料(取自唐宋明清),做出来的却是色香味俱全的西方大餐。也就是说,它们叙事是古代中国的,呈现方式却是西化的、现代的。”所谓“西化”,就是“聚焦在人物细节的描写,而非大而全的全景描写;写实质,而不是描外表”;所谓“现代”,就是“选取的巧妙情节是依照英国推理派的路数再造的,环环相扣,步步逼近。”正因为涉及对文本的准确理解,王强才对翻译错误耿耿于怀。
翻译与文本细读密切相关,要翻译好必须有文本细读的功夫,反过来说,认真翻译对提升一个人文本细读的功夫也是大大有利的。汉学大家杨联陞先生曾指出韦尔伯《前汉奴隶制度》里的一些翻译错误,却申明“并无不敬之意”,反倒主张:“我以为读古书要有翻译的精神,一字不可放过,方才能细,在大学史学课程中,遇有重要的而难懂的史料,教授应当在课堂中与学生共同讲读,不可强不知以为知,囫囵混过。中国人写论文引用中国书向来不翻译,实在作者懂不懂所引的书,有时候真成问题,西洋人引中国书必须翻译,所以他们的学者读书,有时候很细,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汉学书评》)当下搞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以余英时及其门人(王汎森、罗志田等)最盛,盖因他们的文本细读功夫很强,创见也就多。而余英时当年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正是杨联陞,这一学术史线索值得重视。
我自己虽然读不了英文原版,却喜欢找不同的中译本来比照读,《蒙田随笔集》我就收齐了所有的中译本。还有就是找林语堂、许渊冲、杨宪益等名家的中诗英译来读,也可加深对古诗文的理解,比如李清照的《声声慢》里那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杨宪益夫妇译为“Seeking, seeking, Chilly and quiet, Desolate, painful and miserable.”许渊冲译为,“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都不如林语堂译得神,“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不但压韵,连音节也与原词完全一致,前面用六个形容词描绘周围环境,而以“dead”一词收住,情境交融,层次递进,将李清照“淡不得、浓不得”“轻不得、重不得”“说不得,捂不得”的凄苦无靠完美地体现了出来。
余话
自从罗永浩从“新东方”英语学校出道成为网红后,我一度以为所有从“新东方”出来的人都会“说相声”。王强是“新东方”英语学校的联合创始人,口才也优秀,为什么却没给我“业余相声演员”的印象?很简单,不管身份如何变化,王强始终以“书蠹”自命。
为什么要读经典?王强打了个比喻:“当你踏在高速列车上,速度可以越来越快,但是它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玻璃窗必须有减速的视觉效果,人才能够适应,否则你就晕了,甚至崩溃了。读经典,有一种减速作用,让我不晕眩,让我的心更加‘定’。这是看清现实、深入思考的一个基础,也是收藏、阅读抗衡时间飞逝的关键。”正是阅读带给王强安宁和笃定,也就中和了他的“相声腔”(自恋,能吹善侃,表演性人格)。
但王强也不保守。一般的书话作者多少带着点“纸书遗民”气,像鲁迅说的“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王强却带着从新东方英语学校出来的朝气,“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所以,他不但拥抱互联网超链接带来的“实时、深度的阅读革命”、“相对主义的知识观”、“以速度、兴趣、个性化为基本特色的数字化阅读。” 而且投资VR 产业,并断言VR时代就是“我们人类最后一个器官的一个解放过程。”
这真是一只能在书页上翻跟斗、秀“一字马”和“鲤鱼打挺”的书蠹。
原文刊发于《南都阅读周刊》
《书蠹牛津消夏记》读后感(三):#彤阅读#2017之16《书蠹牛津销夏记》
这本书20万字,装帧非常精美,内页图片很有可看性,也是我购买新版书最贵的单本,定价人民币148元。
王强,大家非常熟悉,是新东方联合创始人,也是真格基金合伙人。 虽然他没有《中国合伙人》邓超的帅气,但一说话却能吸引人入胜,这就是内才。 这本书,作者将自己在全世界找书、读书、购书的经验,集于一册,他全部收藏的是英文经典版本书籍,真是让我佩服且羡慕。 人和人差距,不是想拉近就拉近的。如我,爱看书,但因为基础知识构建的水平差劲,只能阅读中文书籍,所以,面对英文经典译本,真是可遇不可求,就比如《尤利西斯》,我就买了三个不同译本比阅读,这就是知识基础弱的无奈之举。 走到中年,更懂得阅读也是一种选择,一定要尽量的阅读经典,对于书,买回来为的是吸取书中精华,为的是阅读,而不是为了摆放家中。 凡物而善用之, 则贵比黄金。 不善用之, 玉亦劣于瓦砾。 从小喜欢看书,绝对不喜欢看教科书
《书蠹牛津消夏记》读后感(四):出版美学的产物
周五下班回家,途经方所,看到晚上有场新书宣传讲座,主讲人名叫王强,书名为《书蠹牛津消夏记》。人名普普通通,未有耳闻,书名倒是奇怪得紧。仔细一看,原来大有来头,这个王强简介是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也就是和俞敏洪,徐小平并称的新东方三驾马车中的“佟大为”。成功人士出书不稀奇,不过书名显得这么书生气的就少见了。加之看到是毛尖作的序时,我决定去讲座看看。
“王强自称书蠹,倒是童叟无欺,光是文章标题,就篇篇涉书。不过书海悠游,我们只看得到小丽或者玛丽,王强却能直接敲开爱丽丝或者血腥玛丽的门,甚至,把她们带回家,如此,看王强的文章,时不时给我一种从来没真正看过书摸过书的感受。” 毛尖如此写道。
于是乎我发现了王强的另一个身份——藏书家。西方语系出身的王强酷爱西方文学,从二十个版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到四百余本《现代文库》,从伍尔夫的小说散文集到亨利·詹姆斯的书信集,讲座上王强讲起自己收藏的珍本善本,神采奕奕,沉浸其中。王强还特别迷恋作者签名,从马克吐温到狄更斯,从哈代到劳伦斯。单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来讲,既有达利插图签名版,亦有草间弥生配图版,而上面签有“小爱丽丝”名字的那本更是可以媲美牛津博物馆的收藏。讲座听完,我突然想起那句张岱的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然而我是对藏书这种雅好没兴趣的,一来没钱,二来缺乏知识分子气息。动手翻了翻样书,坦率来说,文字不错,但远没到一流书话的地步。不过看一看一个真性情的人去淘书的见闻,尤其很多都是自己不会接触的外文初版,也算有趣。但真正吸引我最后促使我掏腰包的,是该书的精美文艺的装帧和独居匠心的设计。
枣红色的真皮封面上,书名“书蠹牛津销夏记”几个字采用小楷字体,烫金设计,一红一黄,加上背景纹路,一种西方传统装帧的艺术气息就跃然眼前;书皮下方是牛津高街的浮雕,背面选取了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小马图”。打开环衬页,却又是土耳其的湿拓画设计,画风似又流动,似又庄重。扉页的描图纸薄如蝉翼,色彩雅素,既不影响文字阅读,定睛一看,又是一番纹理图案。书的纸张厚实,触感上佳,页面版式清爽,有关藏书的照片更是清晰精美,与文字相得益彰。乃至于最后我已经不把它作为一本书话来看,而是当成一件工艺设计的样本,出版美学的产物。
虽然此举颇有些买椟还珠的意味,不过倒让我想起了有关电影的定义。电影算是剧本内容,叙事结构,镜头语言,表演情绪一系列的综合载体,一部优秀的电影不会在任意一方面粗制滥造,形式往往和内容并重。那么一本实体书同样也是文字内容和装帧设计的结合,文学和美学。在生存环境大不如前的出版行业,能产生如此完美严苛要求的作品,作者和出版商想来均是极爱书之人。
所以在最后签售时,我没有请求王强老师写什么特定寄语,而是希望签上一句他对书籍的看法。王强略一思索,落笔四字——“书是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