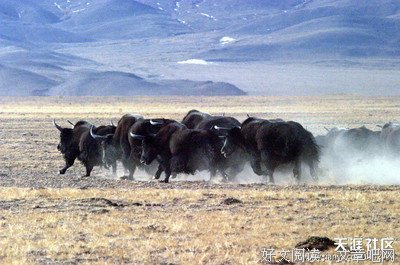《西域生死书》是一本由瓦尔著作,武汉出版社出版的323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011-1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域生死书》读后感(一):悬疑史诗
看完《西域生死书》,我最喜欢其中这一段描写,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人性,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这个世界的今天:
“伊利亚斯和重甲骑兵冲在最前面,他的呼吸瞬间凝滞,叶尔兰的意识也跟着进入一种虚空,他想象出每一次被马蹄挖掘出的泥土开花怒放;听得见自己每一次粗重呼吸,一如回荡在峡谷的烈风;伊利亚斯将宽刃长刀拖曳在身侧、堪堪触摸到深长的牧草——那刀身光洁得如同镜子,上面映照着纯蓝色天空和久远故乡的白云,阳光水一样在刺眼的锋刃上流淌;刀口迎面劈斩着草杆,发出恓恓惶惶的吟唱咏叹,生命结束得异常脆裂,还未及开花就堕入尘土。敌阵近了,王子刀身一转,映照出身后无数亦人亦兽的扭曲面孔——千万齐奔的马蹄从侧面看像是海浪围墙轰然怒卷,时间和灵魂被迫加速冲刺——伊利亚斯湛蓝的双眼开始溢满泪水,并非出于恐惧,而是对绝美生命的悲叹……”
个人感觉,“史诗”一词是不能滥用的,不仅要有是一样的灵动和韵味,更要有深入历史事件的深厚理解。还要有对今天社会的现实借鉴意义,着诸多优点,《西域生死书》无疑都做到了,更难得的是,这还是一本充满商业元素的悬疑小说,除了文学性强,我还很欣赏这本书写作时,运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
比如这本书第二十六章节 黑海往事 中的段落:
“托米莉亚遥望远方冬麦一样起起落落的原野,兴致高昂仰天高唱:
我看不见黑海退役的木帆船
和她身上青色水锈
从桅杆框架望上去
只是天空苍白
大雁一季而归
我看不见高加索的残雪
和它地下黑土悠然
裸麦从农妇手中下坠
和为争夺它而生的仇恨……
她嗓音清越高亢,尾声伴着沙粒,古老的曲调深沉忧郁,宛如一柱狼烟升至高空,最后袅袅抖散。
伊利亚斯听着眯眼朝向太阳,他惊觉自己20余年青春蹉跎虚度,刀光血影随父征伐总未及回头,此刻蓦然回首,人间——不过是张洗去了血污的脸。不知和平是否永远像地平线远端,看得见却走不到……”
西域,直到今天真的太平了么?人们有幸福感么?如果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本书能给我们答案。
《西域生死书》读后感(二):远古的虫洞——推荐《西域生死书》的七条理由
1、创意点绝妙:奥运赛场一支忽然偏转的箭,一桩离奇命案,引发一连串时空连锁反应,从北京到西域、从当今到远古,纵贯欧亚大陆的千万年历史,如同神箭射出了一个故事虫洞,凿出一条奇幻深邃的人类历史秘道。
2、复合性写作:考古学实证、人类学勾联、西域文化探源、奇幻故事虚构、悬疑探险揭秘,像夜光杯里,调配出一杯古今变幻、东西叠汇的葡萄美酒,朵颐!
3、元素混搭效应:中华武术、萨满巫术、西域探险、神秘遗址、上古传说、离奇谜案、诡异现象、人种变异……古老、时尚、本土、异域,种种元素,在故事虫洞里,混搭拼贴,又天然和谐,美妙的阅读化学反应。
4、人类史视野:国人往往局限于两种视野——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现代的西方中心主义,链接欧亚两大文化板块的西域,则长期被忽视淡忘。目力所及,《西域生死书》几乎是第一部摆脱两个中心立场的汉语小说,立足西域,在上古欧亚交流史的文化考古中,打破了区域、国别、民族的文化屏障,让视野得以拓展和开放。
5、立体综合素养:作者瓦尔身为哈萨克族,天然禀有一种浪漫纯粹的独特性情;多年深研考古,对西域文化拥有深切、扎实而又开放的体认;专修英语专业,又具备了西方、现代的视野;从事影视艺术职业,对美与时尚,触觉敏锐;长期坚持汉语写作,文笔精确优美……跨越东西、兼具古今,融合民族与国际,作为写作人,素养得天独厚。
6、双重写作路线:中国畅销小说的写作有两条大道,一是复古化,二是国际化。《西域生死书》的题材同时天然具备两大特征——小说中人物,有中华武术世家、北京国际刑警、蒙古国际侦探、法国考古学家、萨满巫师……组成国际化人物团队;同时,穿越时光虫洞,又将视线引至上古西域的神秘历史,在悠久古老之中,又敞开一个上古的“国际化”大背景。
7、耐心纯净的书写:文如其人并非总是有效,但《西域生死书》是个明证。字里行间,能清晰感受到作者的写作心境,是把这部小说当作精美工艺品细细打磨,词句优美、结构精妙、情节流畅。尤其是文中时时流露出的情感,真诚、柔软、善良,不论对男女情感、自然景物,还是人类的命运,都饱含深情,令人感动。
《西域生死书》读后感(三):狡猾的圣徒——评新锐小说《西域生死书》
在如今纷纷扰扰的各类通俗畅销文学作品中,悬疑探险小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成了市场的宠儿。于是,中华大地上四处散步着扛着洛阳铲到处打洞的“摸金校尉”和设备精良,兵强马壮,随时准备为考古事业献身的科考队员们。而且我还发觉一个规律,这些人的目标大都指向了中国的西部。似乎那里耸立着的,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就是一切神秘事件的发源地。当然,在攀登雪山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忘记另外一个地方——那赤地千里,浩瀚壮阔的新疆戈壁滩。
但这样的题材并不好写,在一般人的眼中,对于西部那边沙漠的了解,仅仅停留在那吐鲁番的葡萄、清甜的哈密瓜和来自大板城的漂亮姑娘上。稍微再有些涉猎的朋友,会知道那里不光出产好吃的水果,还有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古丝绸之路、精绝古国及如今在互联网上成为敏感词的某些字眼等等。虽然说,靠着这些八卦,编排一本似是而非的所谓“边疆探险小说”已经足够,也很容易吸引住众多读者的眼球,但如果说那就是真正的新疆,未免有贻笑大方之嫌。
所以,在拿到瓦尔的《西域生死书》,在翻开小说那古朴而又不失现代流畅感的封面前,我对这本书其实不太期待,对于那句封面语——此书之前,无人读懂新疆,也只是付之一笑。直到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酣畅淋漓地读完了这本小说,我才真正意识到,《西域生死书》构建的是怎样的一个新疆。也才认识到,原来关于新疆的故事还可以这样写,原来那片表面看起来无比荒凉的戈壁滩背后,能够挖掘不仅仅是石油和国家精英们在那里种下的一朵朵蘑菇。我更是第一次知道,曾经在那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过的民族竟然达到47个之多。在那里飘扬过的,有关信仰的旗帜,也不止是今天的新月旗,而是有7大圣徒,前仆后继地在那里留下了他们对世界和生命的探索。
这就是我佩服瓦尔的第一点,透过他那犀利的文字,我能感觉到他对于《西域生死书》虔诚,这种精神不输于任何一个具有无上信仰的圣徒。我无法想象,在一个个寂静夜晚,他是怎样怀着一股殉道的热情,翻阅着那些尘封已久的资料,或是在互联网上查询一条条目录和文献,为一个小小的注解纠结万分,为一个小小的细节绞尽脑汁,从而写出这些关于新疆的文字。诚如前我所说,他其实没有必要那么严谨和苛刻。但若是他真如其他“小报”写手一样去创作,又如何能对得起那些千百年前,在戈壁滩上迁徙跋涉的人们。这一点,瓦尔很清楚,因为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上,他自己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圣徒。
不过,对于瓦尔这个圣徒,我认为他多少有点狡猾。新疆盆地2200年的历史,47个民族的兴亡,7大宗教的更替,想要说清楚,谈何容易。更要命的是,在这些陈年往事中,“雷区”和“禁地”比比皆是,稍有闪失,就真有可能让这部作品成为殉葬品。于是,瓦尔在这里和我们玩了一个花招,他借助了一个让我啼笑皆非的手段。
我相信,但凡有些通俗小说经验的读者对于“穿越”这个词一定是心领神会。在《西域生死书》中,瓦尔设计了一场精妙绝伦的“穿越”。我们姑且不论他的用意是不是在避雷,只看他让主角叶尔兰、康妮和他们的伙伴们籍由追寻一场诡异的凶杀案,成功地跨越千年时光,就足以震撼我们的心灵,因为那也是一场虔诚的,寻求真相的涅槃之旅。瓦尔在小说里成功地驾驭了两条泾渭分明而又互相纠缠的线索,追寻小组在现代探查的是凶杀案,而叶尔兰借助神秘力量回到千年前的新疆各部族中,探寻的却是这边土地本来的面目。在这两个世界的来回旅行中,现代科技与远古巫术的完美融合,光明与黑暗的终极对决,生与死的考验,爱人的缠绵与诀别一一上演。而借助这些,新疆这片土地的面纱才真正被一点点撕开,展现出一个完全和流行于市场上的八卦小说赫然不同的世界,向世人奉上一段原汁原味的,没有经过任何篡改的新疆编年史。
我相信,瓦尔玩的这个游戏一定达到了他的目的,至少对于我来说,当合上这本书的时候,我信手拈起一枚来自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时,竟然在那甘美清甜的味道之下,品尝到一丝淡谈的沧桑。
《西域生死书》读后感(四):灵魂的重量
新疆古称西域,世界上三大游牧民族都在这里谱写过波澜壮阔的英雄主义史诗。《西域生死书》写的便是他们的故事,关乎历史、种族、信仰和爱,关乎前世今生。
故事的主线是,哈萨克神箭手叶尔兰在奥运赛场上失手伤人,凶器竟是来自2600年前的外域青铜箭,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一切很可能由意念遥控而生,行凶者是一位身处远古的萨满(巫师)。叶尔兰在现代图瓦人萨满的帮助下重归历史深处,附着在青铜箭的主人——古代鬼方“独目人”部落王子伊利亚斯身上,他正率领部众抵御强邻“格里芬人”发动的侵略战争。“独目人” 与一山之隔的“格里芬人”本是血脉同胞,但由于外敌征服,沦为附属,伊利亚斯深爱的女首领托米莉亚不幸成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伊利亚斯和托米莉亚密谋出逃,却遭到敌对部落强大萨满神巫的追杀。逃亡和复仇的路上,伊利亚斯一步步接近真相,借用伊利亚斯躯体的叶尔兰也一步一步走向原初……小说采用充满张力的延迟式结构,以人物往生之死生、今世之生死,双线并进交织,令本来就具足紧张感的故事情节悬念迭出、高潮迭起,读之不免慨叹称绝。不同于其他悬疑抑或是魔幻小说的是,《西域生死书》并不耽于仅仅以其曲折、离奇的故事性及独特的技巧立足。它也绝非一般的区域性历史人文探秘小说,绘制自然风貌,讲些流传已久的传说。它所展现的对古老游牧民族的活性精神的颂扬、对在全宇宙空间视角下的生与死之命题的探讨、对镜面人性的挖掘、对种族的止息与延续的思索、对大中华概念的理解才是本书拥有非一般气场的原因所在。
一、活性精神世界
《西域生死书》开篇即提到奥运会,有些读者大概会以为这不过是情节需要,一个离奇的案件借世界范围内关注的体育赛事加强轰动性而已。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造物主生之于人便赋于其繁衍的本能,由此延伸出竞争的本能,即斗争的本能,表现在生物特性上便是活性精神元素生而有之。因此,人是最怕耽于安乐的,丧失了竞争力,个体及其依托的种族便会停止繁衍。游牧民族的竞争意识更为突出,因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本来就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游牧民族的身体里拥有更多的活性精神物质,这一点可以解释他们乐于挥戈征战,铁骑绕龙城的历史行为。但活性精神元素并非存在即活跃,它们会被人的另一些特性泯灭——惰性与安享。
为了保证人们在和平时期不至消沉腐败下去,使活性精神元素始终处于亢奋状态,体育便诞生了,它成为人类活性元素的练兵场。奥林匹克精神本质上就是对活性元素的激发,促使人类保有长备不怠、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精力。我听见过不少人置疑一些体育赛事,其实都是对这种精神的不理解。小范围的比赛体现的是个体、小群体的精神面貌,大范围的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赛事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外展示精气神、宣告不容侵犯的政治手段。《西域生死书》以奥运赛事开篇,恰好为接下来将视线拉到广袤的西域提供了精神上的对接。因为古老的游牧民族正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源发者和秉持者。直到今天中国新疆的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还保留着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比如哈萨克族的姑娘追和叼羊、锡伯族的箭术比赛、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的马术比赛等。
活性精神元素由此成为贯穿《西域生死书》的精神内核,无论是伊利亚斯王子率领部众抵御格里芬人的侵略战争还是后来参加规范更大的欧亚战争,抑或只是在对抗邪恶的萨满巫师的争斗中,作者很好地把握了游牧民族体内的活性精神物质,使全书的西域特性张扬而持久,无时不令人血脉贲张。
二、生死与人性
优秀的小说多是形象大于思想的,依靠形象来揭示蕴含其中的深刻思想。《西域生死书》便是这样一部思想建之于形象的优秀小说。个人认为它的形象不在故事本身,也并不附着于结构,而是隐藏在生死穿越背后的穿越方式。
我曾经在一本超个人心理学著作中读到过这样的理论:人类如果在物质—心智—灵魂—灵性的进级中失败,就会自下退回,直至回复到物质层面,肉体生成,轮回产生。反之进级成功,则会找到自性,结束被迫轮回的遁环。读了《西域生死书》后,我感觉作者也是接触过这种理论的,并且吸收了它的精髓。这使这部书的起承转接,尤其是人物的往生今世的对话含有了一定的哲学色彩。
“黑萨满能运用法力控制他人灵魂,对付他的唯一办法是将灵魂隐蔽起来,可一旦真情流露,魂魄就会显现。”
“我们一直活在天国边缘,只是我们找不到进去的门,因为那扇门关闭在自己心里……”
类似的充满灵性的句子在书中比比皆是,无不含摄着对生死轮回,对灵魂去向的叩问。
“每个人的灵魂都一样重,这只能由腾格里来称量。你杀的每一个人,并不能让你得到更多,相反会让你失去所有!你没有亲人、没人同情,注定会被千古万人唾弃和咒骂,你会永远是个游荡的恶鬼亡魂!”托米丽斯女王说。她是叶尔兰意识附着的古王子的爱人,与其现世的爱人康妮一起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形象。他们四个人是正义的象征,一起维护着灵魂的中性意义。灵魂有上行的动力,也有向下的自然力;它可以逾越生死,也可以在轮回间散尽气息。正因为如此,人性才具有无限多的棱面,它就像一面镜子,不以你的形象而选择是否显现,它是绝对忠实的看客。递进而上,它不选择,所以意识才可能胡作非为,才会出现正面和负面此消彼涨的交织性发展。小说以对伊利亚斯为代表的正面力量同黑萨满所代表的黑暗势力的较量为镜,让人性在特定的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充分显像。这其中意识既是穿行于时空和操控凶行的工具,亦是揭开谜底的本然。这是一个有趣的角度,含摄了人性的意识在书中浓墨重彩,这一点超越了地域之神秘、事件之神秘、工具之神秘,使本书通体闪现出灵性的光芒。
三、种族的止息与延续
国内目前关于新疆的学术研究水平还较低,很多方面都是发现在国内研究在国外。这并非因为国人不聪明,不好钻研,而是因为西域的很多考古发现与西亚和欧洲有关联,国人很少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期间就有一个文化障碍的问题。《西域生死书》的作者是一位出生于新疆的少数民族,在深刻浸染了本民族的文化基础上学习了汉语,大学时又主修了英语,这使他可以非常便利地在各个文化频道上进行切换。为了写这部书,他钻研了整整四年西域人种学,对第聂伯-顿涅茨文化(Dnieper Donets Culture)的历史分支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大胆推测。例如:
“这群人是最早的草原骑手,生性残暴勇武好战,他们一直向东接连征服并同化了众多不同民族,约4500年前到达西伯利亚,融合原始阿尔泰土著之后,先后演变为阿凡那谢沃、安德罗诺沃、卡拉苏克以及塔加尔文化族群,是今天部分中亚都兰语族的共同祖先。这也证实:奥古兹人并非中国新疆的土著民族,他们古代一直居住在西伯利亚和外蒙古高原,直到南北朝时期才进入新疆。”
除此之外,对于种族消亡,作者也通过书中人物之口道出了活性元素极端膨胀的负面作用:“托米丽斯望着东方发白的毒日头,刺眼的面具下双眸亮得像两汪湖水,她想了好一会才缓缓说:“从我记事起,所有草原人只知爱护自家的帐篷、牛羊和族人。我们看得见天有多宽、地有多阔,却永远迈不出这个狭小的圈子——我们的心只对腾格里敞开,却从不对我们身边的异族邻居敞开,甚至有人容不下自己的血缘兄弟!”
就这样,随着小说中案情的发展,种系间交错繁杂的结构和生死进程被勾画了出来,他们有交融也有争斗,有发展更有自我毁灭,不断推衍着进化着。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为小说带来了很强的学术气氛,令情节发展变得如史料般真实可辨。
因而我说,本书封面文案上的“一部可供考古学家借鉴的……”之提法绝非沽名钓誉。
四、大中华情结
种族的链条从远古走到今天,混血是难免的。当前中华大地上的民族之分其实只是原初血统含量的多少决定的,并无彻底的分界。高建群在《游牧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演讲中曾有这样的论述:“瞻望来路时,不管愿意不愿意,你只有承认,是农耕文明和游放文明双重力量,支撑起了中华文明的大厦。”千百年来,这两种力量的区别逐渐只在生存方式上得到呈现,至于人种上则慢慢交融演变。当然每个民族仍有着其特殊的符号,比如王蒙在《我的塞外16年》中这样描述独具特色的维吾尔族的语言:“无穷的词汇、小舌音、卷舌音和气声音,这都是汉语里所没有的,它们和所有的能歌善舞的维吾尔人联结在一起。它们和吐鲁番的挂和葡萄、伊犁和焉耆的骏马、英吉沙的腰刀,喀什的大清真寺和香妃墓、和田的玉石与地毯连接在一起……”这样的区别在大中华的概念中成为一统之下色彩纷呈的最好表现。概况来说就是:“区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吸纳、渗透、融合、发展,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而伟大的民族精神也在不同的区域文化中得到具体体现。”(罗豪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这样开阔的民族观在《西域生死书》中也有体现,最直接的便是书中的男女主人公一个是哈萨克人一个是汉人,他们有着相同的身份,即中华同胞,他们无条件地合作,也因日渐了解而相爱。通过他们,作者表达了血统无贵贱,信仰可沟通,而爱则是合作和发展的根本的观点,这正是大中华精神的实体意义。
在新疆,诗人比作家更古老也更有一种神圣的意义。这一点可以从当地人独具意象的语言特色上反映出来。我本人曾在新疆生活了十八年,因而对这个地方诗一样的古老谚语很熟悉也很迷醉。《西域生死书》的文字便有如此特色:
“生命不过是洒落风中的洁白羽毛,有太多偶然和无奈。不可知的未来一如变幻莫测的险峻山路,将所有苦难埋伏在人类前方,每个人真能找到灵魂的救赎吗?”
“忽听这魔鬼说:‘狗没用了就该杀掉!你们既然自己送上门来,我就不再需要这蠢货做诱饵。为了保守我的秘密,门外所有士兵都已被我送入昏睡!’”
……
也许有人会认为既然是写西域的,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事实是,纵观国内各种区域小说,大多只是说的是那个地方的事,用的却是作者自己的语言。即使作者本人生在故事发生地,但如果缺少对当地历史的深刻理解,便很难如实表现原汁原味的区域特色。《西域生死书》就不存这个问题,小说中的语句读来优美拂人,节奏感强烈,字里行间不但流动着诗一样的、寓言般气息,还充斥着游牧民族的血性,美哉壮哉。
至于小说对新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神秘的人文风情的描摹我就不再累述了,我以为这是西域小说最基本的要素,做到了可称之为西域小说,但若要精彩,还得靠上述各点加码。《西域生死书》无疑是获得了各种加码的精彩之作。
最后借一个问题引出我的推荐:灵魂真的存在吗?《西域生死书》说存在。不仅如此灵魂还有统一的重量。你认为呢?
二0一一年十一月于武汉
《西域生死书》读后感(五):一部高雅与通俗完美结合的非凡小说
一部高雅与通俗完美结合的非凡小说
------评瓦尔的《西域生死书》
亲爱的读者,我向你们推荐青年作家瓦尔的长篇小说《西域生死书》。我相信你们读完了不会骂我,不会后悔浪费了时间,我有这个底气。
当今世下,读书之人越来越少,究之不外乎人心浮躁、诱惑太多,而能够打动人心,引人入胜、融知识与趣味一炉且又格调高雅的好书实在难得一见,也是原因之一。
六七年前,一部《鬼吹灯》曾火极一时,国内出版界与读书网站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兴奋点与利润增长点,以盗墓探险灵异恐怖为主要看点、缺少思想与情感内核的各类粗制滥造的商业小说于是大行其道、铺天盖地而来。可惜好景不长,这样的快餐吃多了,实在会令人反胃。
西域,泛指东起新疆,西至地中海东岸,南起喜马拉雅北麓,北到乌拉尔南缘的广大地域。由于其间横亘着数个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无垠沙漠与戈壁,这片地区的奇特的地形地貌,漫长的历史文化与复杂的民族状况,汉民族历来知之甚少、最为陌生。即便是在被称为“地球村”的当今时代,对于这样一个广袤而遥远的地方,这样一个令人神往而又心存畏惧的地方,这里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国家与民族,这里曾经发生过多少不为人知的或雄奇、或凄惨、或美丽、或奇异的故事?
一部最新的小说《西域生死书》,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西域生死书》虽然也以灵异、巫术、武侠、恐怖为吸引读者的手段,但是对于内地绝大多数对西域知之甚少的读者而言,仅就书中包含的极其准确、极为丰富的西域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息,该书的知识性与可读性已经很能够吸引人了。
《西域生死书》描写了当代与古代两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其间有着令人唏嘘感叹的情感的波澜,读来令人为之动容。两个爱情结局不同,却都能够使人感受到爱情必须生死相依的人生真谛。这对于视爱情为游戏的不少当今世人,必是一番心灵的洗涤。
《西域生死书》虽看似商业小说,却有着很多这类小说所没有的思想内核。它通过惊心动魄的故事描述,个性鲜明的人物演绎,逐步带领读者走到了这样一个思想境地: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说着各种语言、信着各种宗教、有着各种风俗文化的民族之间,“复仇”二字应该抛弃,而真诚沟通、相互融合、和谐相处、共同进步,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真理。
《西域生死书》使用着美丽、准确而新颖的语言,各种新颖的表达常常出人意料而又产生出神入化的效果。这样绮丽而有着浓艳西域色彩的文字,也是小说具有强烈吸引力的重要因素。读者在阅读之中,不断会因为语言而产生出高雅清新语境的审美体验,往往会惊叹于年轻作者横溢才华,从而更加认同这部非凡的小说。
《西域生死书》跨界于商业小说与严肃文学之间,它不仅能够吸引喜欢武侠探险灵异的读者群,也能够吸引要求阅读思想情感丰富的作品,有着很高审美情趣的读者群,体现了雅与俗的完美结合。
《西域生死书》------一部非凡的小说,相信你读后一定会赞叹不已。
本文作者:常 江
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
贵州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
教授
《西域生死书》读后感(六):史学中的文学精品
作为一名大学历史教师,长期以来的困惑是教材过于枯燥乏味,通常引不起学生浓烈的兴趣,每当遇到死记硬背的细节,台下昏昏然欲睡者甚众。
读《西域生死书》对我而言实乃偶然,是我的一位专修西域史的学生几次三番向我力荐,因而忍不住拿过来一阅。刚开始以为就是一般的悬疑小说,无非胡编一些惊险刺激的情节,不过觉得故事编的尚有可圈可点之处,也被激发起一些好奇心。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此书作者必定在新疆远古考古、人类学研究领域有相当深厚的造诣,不仅故事涉及到的考古材料都有据可查,还很详细给出来中外文献的作者和出处,引用的国外文献资料有的甚至出自蜚声世界的学术泰斗之手,不仅开拓了我的个人眼界,也对我国的西域历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探讨思路,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
最后想说说故事浸透出的人文情怀,作者一直着力强调作为“人”这种高级生物必须保有两种基本品质,那就是爱与慈悲。这是很开放的胸怀和灵性体认,无疑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作者在书中对于人类文明演进的思考,对于人类族群和睦团结的心理基础都做了精到的评述。
总而言之,对喜爱历史的人来说,是一部很好看的经典教材,对普通读书消遣者来说,也是一本精彩的悬疑小说,读之幸甚。
《西域生死书》读后感(七):草原民族的前世与今生
关于新疆的草原游牧民族,一直以来在我大脑中始终有挥之不去的疑团。有太多悬而未决的稳态,太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
为何会如此呢?因为我国的汉语历史资料,历来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记述比较混乱,可能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史料中的名称都大不相同。比如说“蒙古”,这个概念其实很玩的时候才出现,但是古代跟它有关的族群,可能就包括东胡、鲜卑、契丹、柔然……等等,只不过时间地点不同罢了。
另外,过去我一直认为丝绸之路是西汉时期张骞“凿空”之后才出现的,其实不是。早在公元前2000年,北方的欧亚草原地带就出现了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青铜之路”,而且其物质文化水平还非常的灿烂,这些都是从我看完这本《西域生死书》之后,才真正了解到的。
个人谈谈看完这本书以后的最大感受吧:
首先它是小说体,故事不仅跌宕起伏,还有很深的悬念感,读起来欲罢不能的体验,非常过瘾。
其次,是这本书的文笔非常有特点,比通俗文学更有文化底蕴,有文字的美感,读起来也是一种享受。
第三,是这本书最闪光的地方,就是基本完全脱离了我们过去所知道的,我国古代非常有限的历史记载,大量引用了近30年以来国际上关于新疆的最新考古学、人类学专业文献,其中也有许多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提出惊人的结论。读完这本书,我对人类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史,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历史,有了脱胎换骨的颠覆性认识。
第四,对人性深层次的触动,这本书是具有灵性的。一般来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描写的不应该是仅仅限于某一个群落,或者一部分人,一个民族的人的事情,优秀的作品描写的,应该是整个人类的集体无意识。这个观点也是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提出的,《西域生死书》对于反思人类的生存方式,生存态度,以及对掠夺、征服、以及人类和平与爱这些观念的理解,都达到了其他同类作品没有的新高度。
最后,我想总结的是,这本书还是非常适合真正想要了解新疆历史前世今生的人阅读,非常物超所值。
《西域生死书》读后感(八):灵魂的重量
——评瓦尔长篇小说《西域生死书》
文/谢络绎(新锐作家,代表作《外省女子》)
新疆古称西域,世界上三大游牧民族都在这里谱写过波澜壮阔的英雄主义史诗。《西域生死书》写的便是他们的故事,关乎历史、种族、信仰和爱,关乎前世今生。
故事的主线是,哈萨克神箭手叶尔兰在奥运赛场上失手伤人,凶器竟是来自2600年前的外域青铜箭,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一切很可能由意念遥控而生,行凶者是一位身处远古的萨满(巫师)。叶尔兰在现代图瓦人萨满的帮助下重归历史深处,附着在青铜箭的主人——古代鬼方“独目人”部落王子伊利亚斯身上,他正率领部众抵御强邻“格里芬人”发动的侵略战争。“独目人” 与一山之隔的“格里芬人”本是血脉同胞,但由于外敌征服,沦为附属,伊利亚斯深爱的女首领托米莉亚不幸成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伊利亚斯和托米莉亚密谋出逃,却遭到敌对部落强大萨满神巫的追杀。逃亡和复仇的路上,伊利亚斯一步步接近真相,借用伊利亚斯躯体的叶尔兰也一步一步走向原初……小说采用充满张力的延迟式结构,以人物往生之死生、今世之生死,双线并进交织,令本来就具足紧张感的故事情节悬念迭出、高潮迭起,读之不免慨叹称绝。不同于其他悬疑抑或是魔幻小说的是,《西域生死书》并不耽于仅仅以其曲折、离奇的故事性及独特的技巧立足。它也绝非一般的区域性历史人文探秘小说,绘制自然风貌,讲些流传已久的传说。它所展现的对古老游牧民族的活性精神的颂扬、对在全宇宙空间视角下的生与死之命题的探讨、对镜面人性的挖掘、对种族的止息与延续的思索、对大中华概念的理解才是本书拥有非一般气场的原因所在。
一、活性精神世界
《西域生死书》开篇即提到奥运会,有些读者大概会以为这不过是情节需要,一个离奇的案件借世界范围内关注的体育赛事加强轰动性而已。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造物主生之于人便赋于其繁衍的本能,由此延伸出竞争的本能,即斗争的本能,表现在生物特性上便是活性精神元素生而有之。因此,人是最怕耽于安乐的,丧失了竞争力,个体及其依托的种族便会停止繁衍。游牧民族的竞争意识更为突出,因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本来就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游牧民族的身体里拥有更多的活性精神物质,这一点可以解释他们乐于挥戈征战,铁骑绕龙城的历史行为。但活性精神元素并非存在即活跃,它们会被人的另一些特性泯灭——惰性与安享。
为了保证人们在和平时期不至消沉腐败下去,使活性精神元素始终处于亢奋状态,体育便诞生了,它成为人类活性元素的练兵场。奥林匹克精神本质上就是对活性元素的激发,促使人类保有长备不怠、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精力。我听见过不少人置疑一些体育赛事,其实都是对这种精神的不理解。小范围的比赛体现的是个体、小群体的精神面貌,大范围的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赛事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外展示精气神、宣告不容侵犯的政治手段。《西域生死书》以奥运赛事开篇,恰好为接下来将视线拉到广袤的西域提供了精神上的对接。因为古老的游牧民族正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源发者和秉持者。直到今天中国新疆的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还保留着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比如哈萨克族的姑娘追和叼羊、锡伯族的箭术比赛、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的马术比赛等。
活性精神元素由此成为贯穿《西域生死书》的精神内核,无论是伊利亚斯王子率领部众抵御格里芬人的侵略战争还是后来参加规范更大的欧亚战争,抑或只是在对抗邪恶的萨满巫师的争斗中,作者很好地把握了游牧民族体内的活性精神物质,使全书的西域特性张扬而持久,无时不令人血脉贲张。
二、生死与人性
优秀的小说多是形象大于思想的,依靠形象来揭示蕴含其中的深刻思想。《西域生死书》便是这样一部思想建之于形象的优秀小说。个人认为它的形象不在故事本身,也并不附着于结构,而是隐藏在生死穿越背后的穿越方式。
我曾经在一本超个人心理学著作中读到过这样的理论:人类如果在物质—心智—灵魂—灵性的进级中失败,就会自下退回,直至回复到物质层面,肉体生成,轮回产生。反之进级成功,则会找到自性,结束被迫轮回的遁环。读了《西域生死书》后,我感觉作者也是接触过这种理论的,并且吸收了它的精髓。这使这部书的起承转接,尤其是人物的往生今世的对话含有了一定的哲学色彩。
“黑萨满能运用法力控制他人灵魂,对付他的唯一办法是将灵魂隐蔽起来,可一旦真情流露,魂魄就会显现。”
“我们一直活在天国边缘,只是我们找不到进去的门,因为那扇门关闭在自己心里……”
类似的充满灵性的句子在书中比比皆是,无不含摄着对生死轮回,对灵魂去向的叩问。
“每个人的灵魂都一样重,这只能由腾格里来称量。你杀的每一个人,并不能让你得到更多,相反会让你失去所有!你没有亲人、没人同情,注定会被千古万人唾弃和咒骂,你会永远是个游荡的恶鬼亡魂!”托米丽斯女王说。她是叶尔兰意识附着的古王子的爱人,与其现世的爱人康妮一起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形象。他们四个人是正义的象征,一起维护着灵魂的中性意义。灵魂有上行的动力,也有向下的自然力;它可以逾越生死,也可以在轮回间散尽气息。正因为如此,人性才具有无限多的棱面,它就像一面镜子,不以你的形象而选择是否显现,它是绝对忠实的看客。递进而上,它不选择,所以意识才可能胡作非为,才会出现正面和负面此消彼涨的交织性发展。小说以对伊利亚斯为代表的正面力量同黑萨满所代表的黑暗势力的较量为镜,让人性在特定的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充分显像。这其中意识既是穿行于时空和操控凶行的工具,亦是揭开谜底的本然。这是一个有趣的角度,含摄了人性的意识在书中浓墨重彩,这一点超越了地域之神秘、事件之神秘、工具之神秘,使本书通体闪现出灵性的光芒。
三、种族的止息与延续
国内目前关于新疆的学术研究水平还较低,很多方面都是发现在国内研究在国外。这并非因为国人不聪明,不好钻研,而是因为西域的很多考古发现与西亚和欧洲有关联,国人很少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期间就有一个文化障碍的问题。《西域生死书》的作者是一位出生于新疆的少数民族,在深刻浸染了本民族的文化基础上学习了汉语,大学时又主修了英语,这使他可以非常便利地在各个文化频道上进行切换。为了写这部书,他钻研了整整四年西域人种学,对第聂伯-顿涅茨文化(Dnieper Donets Culture)的历史分支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大胆推测。例如:
“这群人是最早的草原骑手,生性残暴勇武好战,他们一直向东接连征服并同化了众多不同民族,约4500年前到达西伯利亚,融合原始阿尔泰土著之后,先后演变为阿凡那谢沃、安德罗诺沃、卡拉苏克以及塔加尔文化族群,是今天部分中亚都兰语族的共同祖先。这也证实:奥古兹人并非中国新疆的土著民族,他们古代一直居住在西伯利亚和外蒙古高原,直到南北朝时期才进入新疆。”
除此之外,对于种族消亡,作者也通过书中人物之口道出了活性元素极端膨胀的负面作用:“托米丽斯望着东方发白的毒日头,刺眼的面具下双眸亮得像两汪湖水,她想了好一会才缓缓说:“从我记事起,所有草原人只知爱护自家的帐篷、牛羊和族人。我们看得见天有多宽、地有多阔,却永远迈不出这个狭小的圈子——我们的心只对腾格里敞开,却从不对我们身边的异族邻居敞开,甚至有人容不下自己的血缘兄弟!”
就这样,随着小说中案情的发展,种系间交错繁杂的结构和生死进程被勾画了出来,他们有交融也有争斗,有发展更有自我毁灭,不断推衍着进化着。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为小说带来了很强的学术气氛,令情节发展变得如史料般真实可辨。
因而我说,本书封面文案上的“一部可供考古学家借鉴的……”之提法绝非沽名钓誉。
四、大中华情结
种族的链条从远古走到今天,混血是难免的。当前中华大地上的民族之分其实只是原初血统含量的多少决定的,并无彻底的分界。高建群在《游牧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演讲中曾有这样的论述:“瞻望来路时,不管愿意不愿意,你只有承认,是农耕文明和游放文明双重力量,支撑起了中华文明的大厦。”千百年来,这两种力量的区别逐渐只在生存方式上得到呈现,至于人种上则慢慢交融演变。当然每个民族仍有着其特殊的符号,比如王蒙在《我的塞外16年》中这样描述独具特色的维吾尔族的语言:“无穷的词汇、小舌音、卷舌音和气声音,这都是汉语里所没有的,它们和所有的能歌善舞的维吾尔人联结在一起。它们和吐鲁番的挂和葡萄、伊犁和焉耆的骏马、英吉沙的腰刀,喀什的大清真寺和香妃墓、和田的玉石与地毯连接在一起……”这样的区别在大中华的概念中成为一统之下色彩纷呈的最好表现。概况来说就是:“区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吸纳、渗透、融合、发展,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而伟大的民族精神也在不同的区域文化中得到具体体现。”(罗豪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这样开阔的民族观在《西域生死书》中也有体现,最直接的便是书中的男女主人公一个是哈萨克人一个是汉人,他们有着相同的身份,即中华同胞,他们无条件地合作,也因日渐了解而相爱。通过他们,作者表达了血统无贵贱,信仰可沟通,而爱则是合作和发展的根本的观点,这正是大中华精神的实体意义。
在新疆,诗人比作家更古老也更有一种神圣的意义。这一点可以从当地人独具意象的语言特色上反映出来。我本人曾在新疆生活了十八年,因而对这个地方诗一样的古老谚语很熟悉也很迷醉。《西域生死书》的文字便有如此特色:
“生命不过是洒落风中的洁白羽毛,有太多偶然和无奈。不可知的未来一如变幻莫测的险峻山路,将所有苦难埋伏在人类前方,每个人真能找到灵魂的救赎吗?”
“忽听这魔鬼说:‘狗没用了就该杀掉!你们既然自己送上门来,我就不再需要这蠢货做诱饵。为了保守我的秘密,门外所有士兵都已被我送入昏睡!’”
……
也许有人会认为既然是写西域的,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事实是,纵观国内各种区域小说,大多只是说的是那个地方的事,用的却是作者自己的语言。即使作者本人生在故事发生地,但如果缺少对当地历史的深刻理解,便很难如实表现原汁原味的区域特色。《西域生死书》就不存这个问题,小说中的语句读来优美拂人,节奏感强烈,字里行间不但流动着诗一样的、寓言般气息,还充斥着游牧民族的血性,美哉壮哉。
至于小说对新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神秘的人文风情的描摹我就不再累述了,我以为这是西域小说最基本的要素,做到了可称之为西域小说,但若要精彩,还得靠上述各点加码。《西域生死书》无疑是获得了各种加码的精彩之作。
最后借一个问题引出我的推荐:灵魂真的存在吗?《西域生死书》说存在。不仅如此灵魂还有统一的重量。你认为呢?
二0一一年十一月于武汉
《西域生死书》读后感(九):重新认识新疆
说实话,以前多次在书店看到这本书,但是因为封面比较平淡所以一直没有注意到它,一直到我的同学向我郑重推荐。
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也是新疆的原住民。由于民族血统的原因,我从小一直非常关注新疆的民族演变历史。但是说实话,从课本以及电视里面能够得到的信息都非常有限,一涉及到远古时期就说不清楚,或者说写的不明不白让人看了也看不太懂。
这本小说最了不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讲清楚了新疆的远古历史,从地名、人名的考证,从考古文物的比较方面,都让我大大开阔了眼界,也对自己民族的起源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里要非常感谢小说的作者瓦尔,是一个知识非常渊博的学者。
另外让我思考的就是,我们游牧文化的兴衰变迁,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得到的还有逝去的,我们的荣光和鲜血流淌在一起,真理和自由才是唯一的归宿。
学习,值得每一个游牧民族的子孙们学习!
《西域生死书》读后感(十):新疆人自己的精神家园
新疆人自己的精神家园
——评瓦尔长篇小说《西域生死书》
文/沙荣-沙金玉 (哈萨克教师)
关于这本书,我起初只是因为它是描写新疆的故事才看的,结果往下看,又看见了阿勒泰,又看见了布尔津,这里是我的家乡,我生我长的家乡。我曾经在繁华的都市待过七八年,可是每每魂牵梦萦的就是家乡的山,水,树。没有来过新疆的人,以为新疆是落后的,人们都是骑马的,没有高楼,住在帐篷里......等等等等。
我岂止是爱我的家乡啊,我爱新疆,爱的很心疼。所以几乎每个从新疆出来的作家我都相当的支持。
我是一个少数民族,父亲为了让我体验生活,要我住在舅舅家:骑马,牧牛放羊。做这些是我小时候的最爱,因为可以去远处的树林,可以流连在额尔齐斯河畔。也可以驰骋在荒蛮的戈壁上。躺在河边,你可以欣赏蓝的清澈的天,白的暖暖的云;夜晚,你可以看见一条宽宽的银河,无数盏的星星... ...依傍着额尔齐斯河长大的人们是勇敢的,善良的,可爱的,一如瓦尔书里的主角叶尔兰。
从小听着家里人关于河里的“阿克多斯”老太太的故事长大,不让夜里去河边,因为会被诱惑着掉入河中... ...
河边总会有个女人穿着白衣,把头放在自己的腿上,不停的梳着,而放在膝盖上的头在吟唱着... ...
静静流淌的额尔齐斯、如画般的喀纳斯、神奇的的禾木、童话般的布尔津、美丽的阿勒泰、神秘的新疆。所有这一切如画卷一般,慢慢的展现在这故事里。神秘,美丽,让我如饮甘露。
接下去我深深被这本书的故事所吸引,通过叶尔兰、伊利亚斯王子的传奇故事,我看到了草原民族内心最痛苦的挣扎和最纯洁的梦想。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个苦寒之地,人们为了生存不断与大自然斗争,与自己内心斗争,演绎出一段段悲欢离合、惊心动魄的故事。《西域生死书》很好地把握了新疆草原民族的精神内核,完全将听众置身于故事发生的第一现场,让人真正走进新疆原住民的内心世界,完全融入新疆的土著文化,细细品味它的壮美和悲凉……
我想,世界虽大,每个民族的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但唯有一样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人类的天性,对善恶的取舍,爱与恨、生与死的永恒对立命题。小说的作者之所以能逾越文化障碍,让所有观众感动,是因为《西域生死书》的文字激发出每一个人的内心共鸣,至性至情、至真至纯的文字,分享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生命体验,从这个角度说,这本书堪称新疆原住民千年不变的精神家园!
你真的确定你了解新疆吗?
如果还不够,我真心推荐你阅读《西域生死书》倾听来自新疆原住民内心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