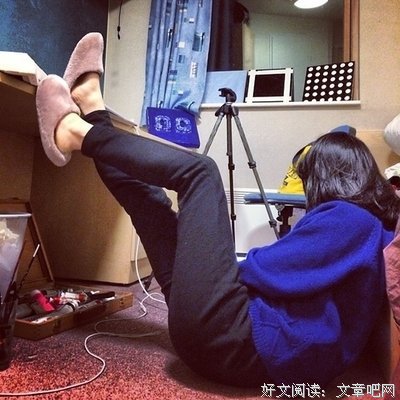▼
听她的声音| 会上瘾
安妮喜欢过的那个男生发了一条朋友圈说: " 最后一天了,打个卡,再见。 " 配图是一组他和自己女友去青海旅行的照片。
去青海,曾是安妮20岁那年最想做的事。
那时她穿着松垮垮的T恤和牛仔,指着精品店里茶卡盐湖的明信片,晃着那时总和自己形影不离的男生的胳膊,说: " 这也太美了,以后赚了钱,咱俩一块去吧。 "
大学毕业时,男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储蓄卡,说: " 不到八千,咱俩凑凑,穷游的话应该差不多了。 "
安妮只好告诉他,自己打算离开家乡去上海试试,口袋里的钱得用来维持生活。
那时候她还不叫安妮,她只有一个很普通的中文名字。在她走进静安区的高级写字楼里之前,她都没觉得那个名字有什么不好。
直到同事端着冒热气的咖啡问她: " 你英文名字是什么?大家在公司都叫英文名的。 "
那是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与这个城市的格格不入,她只能红着脸胡乱编一个英文名字,好让自己看上去更像这楼里的大多数人。
从此,她变成了公司里永远在做图的设计师助理安妮,也变成了上海拥挤人潮中无人问津的甲乙丙丁。
在不知道熬了多少次夜以后,安妮终于从设计师助理变成了能独立承担项目的高级设计师。
涨工资的那个月,她毫不犹豫地从郊区十几平米的合租房搬到了公司附近,虽然那间房子每个月都要花掉她半个月的工资。
她终于不必担心新买的裙子会在地铁里被挤皱,也终于可以每天早上给自己画个从容的妆,遮掉因熬夜加班而生的痘痘和黑眼圈。
也是在那天晚上,她久违地给男生打了个电话,叽叽喳喳地向他描述自己新房子的样子。
等她说完,男生在电话那头问她: " 家里安排我去相亲了,你呢,要一直留在上海吗? "
安妮愣了一下,才发现原来他们早就长大到不能把暧昧假装是爱的年纪了,她知道她该给对方一个答案,但她还有很多想在这个城市完成的事没做。
于是只好让男生来做选择,男生用很慢的语气对她说: " 那么,要照顾好自己啊。 "
然后,就像约定好了一样,他们没有屏蔽彼此,但谁也没有再联系过对方。
去年国庆有个很要好的朋友打算多请几天假去一趟西藏,问她要不要一起。
她想去,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拒绝了。
因为在28岁的这一年,她突然发现一起长大的那些人里,只剩下她一个人还没车没房没对象。
她第一次感觉到来自年龄的恐慌,她想攒钱,想给自己在这城市里安个家,于是连一日三餐都不放过的开始节省。
而关于20岁那年明信片上的那个地方,只能再次被新出现的愿望顶替掉。
她的生活里好像总是有数不清的事情,让她一次又一次放弃原本想要做的事,她一直以为自己只是被生活推着走,以为自己并没有做选择的权利。
但这一刻,她看着男生发在朋友圈里的那句 " 再见 " 和照片,才终于明白:
如果毕业那年,没想那么多选择去穷游,自己的青春里是不是就多了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如果同事问自己英文名字时,大胆坚持用自己的名字,那些被署着安妮的作品会不会看上去更像自己的?
如果在他离开前,勇敢说出那句喜欢,今天出现在他朋友圈里的人会换成我吗?
她常常劝自己,风景总在那里,早一点晚一点都无所谓。
但,风景不会动,人却是会走丢的。
她想起《请回答1988》里那句经典的台词:搞怪的不是红绿灯,不是时机,而是我数不清的犹豫。
一句突如其来的告白,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次不计后果的反抗,我们年轻的时候把这些叫做勇气,长大以后却把它叫做冲动。
那个你喜欢的人,一定要在最喜欢的时候紧紧抓住,那个你想去的地方,一定要在最想去的时候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