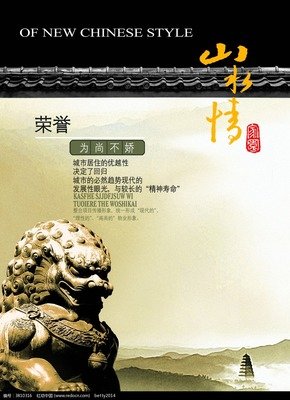●假如肥胖真的是由卡路里摄入平衡与否所决定的,那么这背后的逻辑暗示着,你每天仅需多吃几口苹果,20年后你就会多长出20千克的肥肉。反之,你需要每天控制自己少吃一口汉堡,就肯定能解决肥胖问题。这显然是个站不住脚的假说,而它背后依靠的逻辑,也正是站不住脚的“热量平衡”理论。
许多人几十年来一直保持清瘦,也有许多肥胖的人一直保持很胖,这些事实不都正好说明,在控制体重方面,一定存在比单纯的卡路里平衡理论更确凿的证据吗?
接下来,将证明,所谓热量摄入平衡与减肥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多么的荒谬。我们既不会由于多吃少动而发胖,有意识地少吃多动也不能解决问题或预防发胖。 ----盖里·陶比斯《我们为什么会发胖?》
●因此,显而易凡的是,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而是让人去信仰的。只有对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们才会有百分之百的信仰。" 一种能理解的教义会缺少力量。-旦我们理解一样东西,它就会像是发源于我们自身。显然,那些被要求抛弃自我的人不会从发源于自我的东西上看到永恒确定性。凡是他们能完全理解的东西,其有效性与确定性在他们眼中都会失色。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
●有成功意识的心灵会迅速发挥作用
在我跟数百位成功致富人士的访谈中,我注意到他们的内心对成功有多么地全神贯注。其中有些人的学历很高,有的人显然对所谓的“学校教育”毫无涉猎,比如亨利?福特。这些人之所以有力量把自己的心灵运用得这么有活力、有效果,从来就不是因为有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不是靠过人的智慧。那么是什么激励了他们的内心去认定伟大的目标,然后筛选所有的人生处境,并善用能帮助自己施展抱负、达成梦想的条件?那就是成功意识。 ----拿破仑·希尔《心静的力量》
●显然,有心给你添堵的人不会自责只会怪你太矫情。
●时间发出“突、突、突、突”的声音,沉重地向前拖行着,好像我再不做些什么它就要累垮了似的。但显然,它比我想象的要更坚强些。我依然生活得安然无恙却又行将就木。 ----《在月亮上写信的人》
●我打开车门一面叫一面向他跑去,但是荷西已经踏进这片大泥沼里去了,湿泥一下没到他的膝盖,他显然吃了一惊,回过头去看,又踉跄的跌了几步,泥很快的没到了他大腿,他挣扎了几步,好似要倒下去的样子,不知怎的,越挣扎越远了,我们之间有了很大一段距离。 ----三毛《撒哈拉的故事》
●很显然,在记者们面前,他放过了她,不代表在这些人面前,他还要放过她!她已经是名符其实的凌太太了,他的女人,他就要让那些觊觎她的男人看见,也让那些觊觎他的女人看见。 跟他抢女人,他们,迟了! 跟她抢男人,她们,也配?
●世界是现实的,社会也是现实的,所谓现实,就是人们喜欢跟随自己的感官视觉走,跟着物质走。跟着能解决或满足到自己的需求的欲望走。现实的最明显特质就是:“重比较,重利益,重物质,重舒适,重欲速,重窍门,重心机,重轻易…。”当然重现实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倘若当所有人都走如此路线,这显然容易导致塞车,容易导致社会一片狼藉,周围一片乌烟瘴气,到处一片哀声叹气,着实令人摇头叹息。 ----叔叔的书《财疏学浅》
●过去这些年,我一直在各地旅行,观诸世间大地山河,心怀敬畏之情。从少年到中年,推开了世界的门,又走入了生活的迷宫,翻越了自己心中的一座座山峰,游走于自由与世俗的边界。
太多人问我旅行的意义,我其实比任何人都想知道它究竟改变了我什么。可很多时候,它并没有带来什么。无用,一次次地,是我对于旅行最诚恳的评价。
很多次旅行回来,我也以为我会到此为止。人生有很多正经事可以做,旅行显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什么正经事,他们一直希望我买房结婚,好像这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一样。而我也只能冷眼远望他们的人生,觉得他们活得既安稳又成功。
但是我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属于哪里,即使去了那么多地方之后。 ----李沐泽《你是浪子,别泊岸》
●把地球压缩成葡萄一样大小,但是质量不变,而且还会越来越大;那么地球就是一个黑洞。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啊
●人类移居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差不多到大跃进的时候才实现。随后接着发生的人类活动范围的又一次扩张,是进入欧亚大陆的最寒冷地区。虽然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冰川时代,对寒冷的气候已经适应,但他们再没有向北进一步深入,只到德意志北部和基辅为止。这并不奇怪,因为尼安德特人显然没有针,没有缝制的衣服、温暖的住房以及其他为在最寒冷气候中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技术。从解剖学看,确实掌握了这种技术的现代民族,在大约2万年前进入西伯利亚(对此通常都有一些认为时间还要早得多的说法)。这一扩张可能就是欧亚大陆长毛象和长毛犀绝种的原因。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原来有些东西是学习、模仿,尝试不来的,比如感情,比如爱。而对于这一点显然我没意识到。对这陌生的世界充满恐惧和距离感,与周围的一切显得那般冷硬生刻。我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又在彷徨什么,只是觉得隐约在自己生命里曾失去过什么?可为什么想不起来?我还在路上走着,我还在去尝试、去模仿、去学会。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有什么意义,但我只觉我该去、会去、愿去。
●慈心的所缘境:“愿等同虚空的一切老母有情具足安乐及安乐因”,这显然是以不具安乐的有情作为所缘对境,希望他们具足乐因及乐果即是行相。 ----益西降措仁波切《益西降措仁波切官方微博》
●人为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这一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迷,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困扰着所有的哲人。人的斯芬克斯之迷,实际上也就是人的本质的理性和非理性之迷。
显然,理性并非就是人性、人的本质的代名词。当然,我也不同意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把非理性作为人性、人的本质的代名词。认为:
“生命的本质便是那不能遏止的盲目冲动。”
“人的全部本质就是意志。是一个饥饿的意志。人世的追逐、焦虑和苦难都是由它而来的。意志是人生苦难的泉源。”
人是“贪欲之我”。欲求是无休无止的。满足是短暂的,缺乏却是经常的。
“欲求与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 ----青泽
●“亲爱的,不要走。”她说,听见自己的声带不由自主发出呜咽声。
“我非走不可。”他语气平淡,显然这句话很久以前就说得腻了,但他的双手依然熟悉地在她身上游走,并不觉得厌腻。
“不对,你不是非走不可,”她在他耳畔低声说,“你只是想离开,你不敢再继续下去。”
“我走不走跟我们的事没关系。”
她听见他的口气中透出些微怒意,同时感觉到他强壮温柔的手滑下她的脊椎,伸进裙子腰带,来到大腿上。他们就像一对配合娴熟的舞者,熟知对方的每个动作、脚步、呼吸、节奏。首先他们会做爱;他们的性爱是纯白色的,而这是美好的部分。做完爱之后,他们就得迎接黑暗的部分,也就是痛苦。 ----尤·奈斯博《雪人》
●美国之后,将不再有帝国;也意味着,权力的转移,也不再只是大国间的游戏。权利分享,会成为世界格局重塑的主题。
显然,美国做为当今世界的老大,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甚至根本就没打算有这种准备。这一点,从美国的一些顶级智囊为什么反复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话题,即可窥出美国人当下的心态。很遗憾,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刻舟求剑”:以为只要打压住挑战者,就可以保住帝国江山永不易帜。
但,任何人,任何力量,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与趋势对抗,特别是当趋势已经如此明显之际。美国不可以,中国也不可以。 ----乔良《帝国之弧》
●人不在多,而在精。
擎社上下一心,而日韩商会那方虽说海纳百川,但很显然,川流汇聚的太多了,也容易让大海出现杂质。 ----吃草的老羊《重生校园之商女》
●丑男人露出疑惑的表情,说:“那你如何发现的我?”
楚钰秧大言不惭的说:“因为我是一个机警的人。”
丑男人笑了一声,显然其中讥讽的意味比较多。
丑男人又问:“你怎么知道我戴了面具?”
楚钰秧笑着说:“因为你丑的很有个性。”
丑男人:“……” ----长生千叶《仵作先生》
●为什么一个与此迥异的旧体系会奔溃,我们就必须探索的更加远一点。假如16.17世纪的英格兰不存在可辨识的农民阶层,那么它是在先前的什么时候消失的呢?近期有一种意见是:虽然如罗德尼·希尔顿所言,14世纪末显然存在一种“农民”的社会结构,但是最近发现的证据表明,这种社会结构在15世纪中叶之前已然崩溃。 ----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和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比,手刃仇人时的快意显然更具有吸引力。复仇之火已经燃起,唯有鲜血的浇灌再能让其熄灭。 ----三天两觉《贩罪》
●人都是要死的,我们也许总是在担心这个时刻的到来,但很显然,没几个人会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葬礼。 ----蓝涂《我的葬礼》
●熟悉《圣经》的读者应该能够猜得到,叙事者没有说出口的经文,显然便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那句“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又或者是《约翰福音》里的“不要将表象作为判断的根据”。《圣经》反复告诫凡人不能彼此论断是有道理的,因为人和人的相互了解往往肤浅、局限而片面,能够做出公正的评判只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假如这样的上帝果真存在的话。 ----李继宏
●佟悠,死不算什么,跳下去不过也就几秒钟的事情。可是比起死,活着显然更难过更痛苦。你要是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他,那你不如活着,好好折磨你自己 ----满城疯语《如今温光如故》
●高瞻远瞩的第一个技巧就是思考未来,你会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技巧,但是高级管理人员显然很少思考未来。相反,我们总是疲于奔命地应付眼前的事务,深陷于当前琐事的泥沼,很多时候还不能自拔,并乐此不疲。 ----默多克
●“这世上的事呢……只要有女人掺和进来就很容易坏事……”猫爷一脸慵懒地吐出一个烟圈。
“你说什么呢!你妈不是女人吗?”显然水映遥对他这套歪理非常不满。
王诩却点头道:“不,他说得有道理,他的出生就证明了,他妈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三天两觉《鬼喊抓鬼》
●许多历史学家把思想和现实加以比较, 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1789 年以前的法国贵族对自己的看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例如, 他们自认为是公元5 世纪法兰克人的后裔。但是, 很显然, 这种自我认识规定了他们的认同, 强化了他们的高傲意识,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行动方式。因此“, 思想”可能成为历史的决定因素。约翰·洛克是对18 世纪启蒙运动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他早就指出“: 实际上,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或意象是看不见的力量, 时时支配着人们。”叔本华也说:“ 观念主宰世界。”人们在采取行动时可能完全超越了对直接的外部刺激做出最简单的反应, 而是根据自己头脑中的某种概念或思想。因此, 历史最好被理解为思想的集合。 ----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
●正是因为你凡事苛求完美,所以常常难以避免缺憾。精益求精固然好,但事事想要百分百,显然会让自己陷入条条框框而后艰难的行走。这个世界本就不存在什么完美,若有,那也是以完美的心态去迎接或许并不完美的明天!
●我自己多少有些知识成就感,在个狭小的圈子里,我还是小有名气并受人尊敬。经济上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不需要去上班就有一份不错的收入,相当于全国年平均收入的两倍,可以一直拿到我去世。但是我明白我已走到了自杀的边缘,这并非是出于绝望还是什么特别的伤感,而是由于比沙所说的‘抗拒死亡那套功能’ 的失灵。纯粹要活下去的愿望显然与一个普通的西方人必须去承受的痛苦和人生折磨无法对应。我已无法为自己活, 难道我还能为其他的人活?人无法让我感兴趣,事实上,人让我感到恶心。我认为人不是我的兄弟,尤其是他们中的某部分人,比如法国人和我以前的同事。然而,很不幸的是我发现人很像我自己,正是这种相似让我回避人。 ----米歇尔·韦勒贝克《Submission》
●一个人这样凶狠将自己损坏,心中不会对别人有半点慈爱。
说什么你对任何人怀有爱意,你对你自己如此的漠不关心!
你要承认,是有很多人爱你。
很显然的,你并不爱任何人。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一个民族有几个哲学家没有什么稀奇,但一个民族能以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那就真是非常的事了。无论如何,中国这个民族显然是比较有哲理眼光,而比较没有效率的,如果不是这样,没有一个民族能经过四千年有效率的生活的高血压而继续生存的。四千年有效率的生活是会毁灭任何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在西方,狂人太多了,只好把他们关在疯人院里,而在中国,狂人太稀罕了,所以我们崇拜他们;每一个具有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的人,都会证实这句话。我所要说明的便是这一点。是的,中国人有一种轻逸的,一种几乎是愉快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气质的最好证据,是可以在这种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里找到的。 ----梁实秋《人生不过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