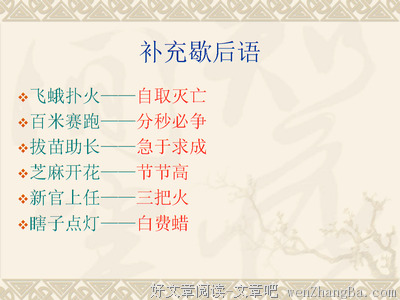●我从未离开,只是活到了过去,或是说从过去走了出去。过去正是现在,不仅是以短促的瞬间回忆形式出现。与“感受”的永恒当下相比,成千上万个推移时间流逝的变化,如梦般短暂虚无,也如梦般缥缈不实。那些变化蒙骗我,让我这个病人们待着痛苦和担忧前来就诊的医生,自以为拥有不可思议的强大自信和无畏。 ----帕斯卡·梅西耶《里斯本夜车》
●我们为什么会为无法出门旅行的人难过?因为他们无法跨足外在世界,内在不能随之延展,无法丰富自我,因此被剥夺深入自己内在的可能性,没有机会发现自己还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变成什么模样 ----帕斯卡·梅西耶《里斯本夜车》
●谁要是相信,彻底改变惯常生活的关键时刻必定惊天动地、内心情绪强烈激荡,便是大错特错。……事实上,真正牵动人心的生命经历往往平静得不可思议,既非轰然作响、火花四溅,更非火山爆发,经验发生的片刻往往不引人注目。 ----帕斯卡·梅西耶《里斯本夜车》
●奥斯陆,这个在初雪中带着韵脚的美丽音节,终于成为伯格赋予其情人和欲望的名字。但是我们能够确信这个名字是诞生于当初肌体交缠的真实之境么?抑或是通过事后多年的追忆和虚构对当年的完成?在这个曾燃起他无名欲望的女人死去多年之后?我们不得而知。
许多东西我们不得而知。伯格迷失在记忆中,而我们作为读者,迷失在对伯格的阅读中。
原本分离的那些,却丝丝缕缕嵌在了生命里。记忆似乎随着时间不可避免地萎缩,但是萎缩之后又重新伸长。空间呢,从未去过里斯本的母亲与伯格重遇于里斯本,空间也获得如云朵在天般的驰骋。于是,这终于导致了记忆和真实并无边界。在场与不在场并无边界。远方与此时并无边界。死亡和生并无疆界。 ----击节《豆瓣》
●我们不只在时间上延伸,空间上亦然,远远超过可见的空间。我们离开某处,总会留下一些东西;人虽已离去,心却依旧留在哪里。有些事,只有回到原地,才能再度寻得。当单调的车轮声再者我们通向过去的一段生活,不论过去距今多么短暂,都让我们驶向自我,回到自己的世界。我们不只是到达了远方某处,同时也抵达内心遥远的地方,一处或许非常偏僻的角落,我们身在异地时,这角落便深深隐身于黑暗之中。 ----帕斯卡·梅西耶《里斯本夜车》
●玩把至俗的!哈哈……
尸位素餐不羡仙,
御用腹气充榴莲。
无奈终将新鲜至,
释回本真归自然!——屎
溯及源头乃大善,
千回百转旮角钻。
参与循环走一走,
不觉变味熏臭天!——尿
斯本世间蕴真气,
杂粮五谷致其迷。
勿论震音与焉响,
实无一物终是虚!——屁
●我们总是无法看清自己的生活,看不清前方,又不了解过去,日子过得好,全凭侥幸。 ----帕斯卡·梅西耶《里斯本夜车》
●我们只关注此地此刻,相信因此理解了生命本质,那可大错特错了,是荒唐愚蠢的暴力行为。重要的是,我们应怀抱适度的幽默和忧郁,冷静自信地来往于时空上皆扩展开来的内在风景,那风景代表了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会为无法出门旅行的人难过?因为他们无法跨足外在世界,内在不能随之延展,无法丰富自我,因此被剥夺深入自己内在的可能性,没有机会发现自己还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变成什么模样。 ----帕斯卡·梅西耶《里斯本夜车》
●诗人贾梅士(即卡蒙斯)着迷于疯狂的爱和天赐的狂热,有一次,他曾写道,里斯本是“……所有城市当中的公主”。我们会原谅他的浮夸。只需给里斯本她本来的样貌,富有文化气息、现代、整洁而有条理,并且没有丧失任何其内在的精神,这样就够了。 ----若泽·萨拉马戈《谎言的年代》
●我可以跟你说件事吗?我想你之前注意过圣胡斯塔高塔吧?就是下面那个,它归里斯本电车公司所有。塔里面有座升降梯,但那座升降梯真正说来哪儿也不到。它把人载上去,让他们在平台上瞭望四周,然后再把他们载下来。那是电车公司的。现在啊,约翰,电影也可以做同样的事。电影也可以把你带上去,然后再带回原来的地方。这就是人们在电影院里哭泣的原因之一。 ----约翰·伯格《我们在此相遇》
●主教气冲冲地继续说, “在西班牙语里,你甚至找不到吉诃德这个姓氏的出处。连塞万提斯本人都在书中说,姓氏有可能是吉哈达,盖萨达,甚至是盖哈纳,堂吉诃德临死时又称呼自己为吉哈诺。” ----格雷厄姆·格林《吉诃德大神父》
●尽管他回答问题时避重就轻,传递出的信息也不多,但是乔布斯本人非常有气场。他流露出的强烈自信让我不得不认真倾听他说的每一个字。他回答问题时字斟句酌,即使是回答意料之外的问题也是如此。25年后,在他的追悼会上,乔布斯的妻子劳伦证实了他从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拥有“成熟的审美品位”。从他的回答里,能听出他对于自我判断和品位的自信,而且在整个访谈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他始终在试探我是否能够心领神会,是否能够理解他以前所做的事和将要在NeXT做的事有什么特别之处。后来我意识到,乔布斯之所以不停地试探,是因为他要确保每一篇关于他和他公司的文章都能够达到他心目中的质量标准。 ----《成为乔布斯》
●你很难概括说里斯本是什么,你只能说它不是什么,它不只是一座山城,不只是一座海城,不只是个首都,它有些地方明亮到令人眩目,有些地方见不到太阳,在晴天,街道像斑马一样,你随时在一片片明暗里行走。你到处可以听见大航海时代的典故传说,但那属于之前的里斯本——那个1755年就被地震毁掉的里斯本。 ----桃花大人《任务之异国选夫》
●每当我阅读报纸、听收音机,或坐在咖啡座留意人们的谈话时,心中常涌起厌恶感——为那些一再重复说出、写出的言词,一再重复使用的措辞,空洞的言词或譬喻感到厌烦。最糟的是,当我听到自己的言谈后却不得不承认,自己也一直重复使用同样的言词。这些言词已被彻底使用和毁坏,因使用了百万次而破损。破损的言词还具有意义吗?当然,语言交换依然有其作用,人们因此而行动,让人微笑和哭泣、向左走或向右走,让侍者端来茶或咖啡。然而,这并不是我想要问的。我想的问题是:这些言语还能表达个人思想吗?或只是效果强大的声音结构驱使人做出种种行为,只因为闲话铭刻在心的痕迹不断地散发光芒? ----帕斯卡·梅西耶《里斯本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