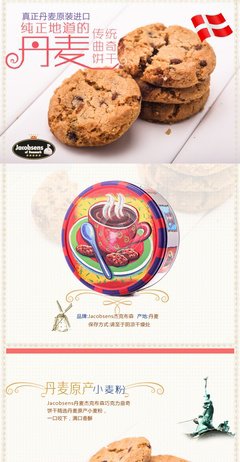●千叶城真的很像香港旺角 ----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
●在我身后的那座不夜城里,探照灯扫射天空只为了取乐。我想像他们聚集在大理石铺地的广场上,井然有序,机智敏捷。我看到他们明亮的双眼中饱含热爱,他们热爱灯火通明的街道,热爱银光闪闪的车辆。 ----威廉·吉布森《全息玫瑰碎片》
●他们越来越富有,也越来越自我,他们在迷光里修建的是自我躯体的延伸。我们将自己锁在自己的财富后面,内向生长,制造出一个毫无缺口的个人宇宙。 ----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
●他想象一辈子都替一家大公司打工的生活。公司宿舍,公司赞美诗,公司葬礼。 我知道全世界为什么那么多人热爱这本书了,这好像一个科幻版的搏击俱乐部,只不过更迷幻,更摇滚,而且是在一个又熟悉又陌生的异世界发生的版本。 ----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
●十一分钟后 ,杜鲁门总统宣布事实上承认以色列 。受埃迪 ·雅各布森的鼓励 ,杜鲁门秘密向魏茨曼保证 ,他支持分治 。但是当美国驻联合国外交人员试图搁置分治方案时 ,他几乎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 。他的国务卿乔治 ·马歇尔 、战时总参谋长和美国公共服务界的老前辈 ,坦率地反对承认以色列 。可是杜鲁门仍选择支持这个新国家 。不过第一个官方承认以色列的却是斯大林 。 ----西蒙·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
●“请把它当作一个架空的、或然的美国:八十年代从未到来,这些建筑是由破碎的梦想构筑而成的。” ----威廉·吉布森《全息玫瑰碎片》
●将人的意识复制进硬盘中。如果在脑死亡之前复制出,那么其人即使肉体死亡意识也不会消失。凯斯的师父泡利的意识即在思想盒之中。 ----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
●我雇了一个意大利导演,为了生计,他接一些在暗室里洗照片、在泳池旁安装露台的活儿。他把我为唐尼斯拍摄的所有照片底片都冲洗了出来。我自己压根儿不想看那些东西,不过,它们似乎对这位李奥纳多老兄没有什么影响。他取出照片后,我像洗牌似的快速浏览了一遍,检查无误后就把它们封好,走航空邮件寄望伦敦。接着,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去了一家正在放映《纳粹性爱汽车旅馆》的电影院,可从头到尾我都闭着眼。 ----威廉·吉布森《全息玫瑰碎片》
●药力消退下去,曾经打磨光亮的骨架一点点被侵蚀,血肉开始僵硬,整个躯体再次变回自己的肉身。他无力思考。他异常欣慰于这种状态:充满感知,无力思考。他似乎能融入眼前的每一样东西:公园里的长椅,古老街灯旁的白色飞蛾群,黑黄相间的机器园丁。 ----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
●你看,这些设计师都是民粹派:公众想要什么,他们就设计什么,而公众想要的当然就是未来。 ----威廉·吉布森《全息玫瑰碎片》
●他想起她肌肤的味道,想起港口边那黑暗酷热的房间里,她的手指是如何扣住他的后腰。 都是肉体,他想,都是肉欲。 ----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
●想想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其他人生活的碎片。难道不是这样吗?欧洲旅行的几个瞬间被遗弃在空白磁带的灰色海洋里。他终于也去过那里了,可是她因此变得更真实了吗?他们之间因此变得更亲密了吗? ----威廉·吉布森《全息玫瑰碎片》
●如果你想听更高级的解释,我会告诉你,你遇见了一个符号幽灵。举个例子吧,所有这些被接触者的故事都基于一种渗透我们文化的科幻意象。我愿意承认外星人的存在,但我绝不相信他们长得像五十年代连环画里画的那样。他们是符号幽灵,是从深层文化意象中剥离出的碎片,它们有自己的生命。比如那些堪萨斯的老农夫,他们总说自己看到了儒勒·凡尔纳笔下的飞船。而你看到的是另一种幽灵,仅此而已。那架飞机不过是集体无意识的一次体现而已。 ----威廉·吉布森《全息玫瑰碎片》
●三十小时的幻觉,这是如何的感觉 ----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
●她像是打算横穿街道,就在她走下路牙的那一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的发色居然变了。起初,他以为那是灯光照射的效果,可这条路上并没有能发出彩色光斑的霓虹灯啊!她的发色不断变幻,像水面上漂浮的油膜般扭曲融合。接着,这些色彩晕开了,三秒钟后,她换上了金发白肤。一开始他坚信那只是灯光的作用,可随后她身上的衣裙也像压缩塑胶袋一样扭曲起来,一些卷曲的衣物碎片掉落下来,散布在人行道上,仿佛传说中神奇生物身上脱落的鳞片。科雷蒂走近时,地上的碎片已经化为绿色的泡沫,嘶嘶作响,缓缓溶解,最终消失不见。他再次抬头看她,她已经换上了一身绿色的绸缎衣裙,缎面在路灯下光华流转。她脚上的鞋也变了,瘦小的肩膀裸露着,上面仅有两条细细的肩带,柔美的长发变成了一头针芒似的短发。 ----威廉·吉布森《全息玫瑰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