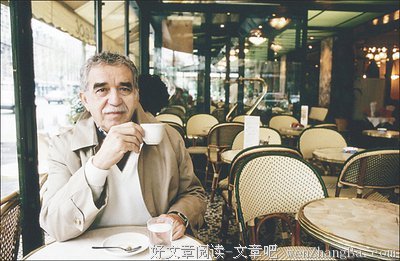1、和沈从文一样,废名的思想与创作带有强烈的民本倾向和“反智”特征,所不同的是,沈从文偏于理性,而废名则更具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 ----《博尔赫斯的面孔》
2、福楼拜将自己从叙事中隐藏起来,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显露”;对叙事视角进行限制,其目的正是为了让叙事获取更大的自由。 ----《博尔赫斯的面孔》
3、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里都想过别人的日子,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根本悖谬所在
4、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被封闭在一个黑暗的匣子里,而普济的天空就是这样一个匣子,无边无际。他所看到的就是一些很小的局部,幽暗不明。他没法知道一件一件的事是如何发生的,这些事情是经过什么样的丝线缝合在一起,织成怎样一个奥秘。而现在,他自己就是奥秘的一部分。 ----《人面桃花》
5、你纯真的眼 倒映着我的脸
祈祷时间能 停留 这一刻
曾经 年轻时 无忧无虑
透明的快乐
像风一样 散了
一句话 一个吻 别的都不管
两个人 两颗心 就是全世界
不在乎 是否已 想得很清楚
直到 我们都迷路
你纯真的眼 倒映着我的脸
祈祷时间能 停留 这一刻
曾经 年轻时 无忧无虑
透明的快乐
像 风一样 散了
在多雨季节里 我总是 想起你
后悔着当初 沉默地 离去
紧紧握住的 那指缝中的
一点和一滴
终于还是 流尽
一句话 一个吻 别的都不管
两个人 两颗心 就是 全世界
不曾想 有一天 我也会 唱着
这首怀念你的歌 ----《忆中人》
6、忏悔本来即是一个理想的"矛盾结构"一一忓悔是对道德的维护(一种隐藏得很深的自我保护),而忏悔的内容,往往才是作者真正的意图所在. ----《伦理学的暗夜》
7、在《审判》与《美国》中,主人公K和卡尔视觉上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是叙事上的视角限制,也不是人为的修辞学和方法论,而是一种被决定的命运逻辑,也就是说,无论是K,还是卡尔,他们所看到的只能是局部,局部的局部,……《城堡》中所蕴含的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并不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抵消,而是它的提纯物。这种不确定性以K内心的迷惘感以及在完成某种使命时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障碍为前提,同时又构成了超越这种障碍的全部基础。这种自相矛盾的排斥性力量形成了卡夫卡喜剧的中心情节。 ----《博尔赫斯的面孔》
8、痛苦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清除的,只能用一个新的来盖住那个旧的。 ----《春尽江南》
9、由于卡夫卡小说的强烈的荒诞色彩,他的写作不仅仅是对现实和历史一般文化状况的总结,它开向未来,是对一个远为深刻、复杂、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的直觉性寓言。这个世界,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我们一时还难以看到它的边际。 ----《博尔赫斯的面孔》
10、文学写作的基本目的,是运用语言去阐述个人与他所面对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文学创作的基本材料往往来自于个人经验和记忆。个人经验对于写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作家仅仅拥有经验和记忆是远远不够的。一般来说,个人经验永远是封闭的,琐碎的,习以为常的,有时甚至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文学所要发现的意义,犹如宝藏一样,沉睡在经验和记忆之中。如果没有梦的指引,没有新的经验和事物的介入,经验和记忆本身也许根本不会向我们显示它的意义。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文学写作的意义,实际上并不存在于单纯的经验之中,而是存在于不同经验之间的关系之中。同样的道理,真相并不单纯的存在于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之中。 ----《博尔赫斯的面孔》
11、所有这些往事,秀米以为不曾经历,亦从未记起。现在却一一植入他的脑中。原来,这些最平常的琐事在记忆中竟然那样亲切可感,不容辩驳。一件事会牵出另一件事,无穷无尽,深不可测。而且,她并不知道,哪一个细小的片刻会触动她的心房,让她脸红气喘,泪水涟涟。就像冬天的炉膛边正在冷却的木炭,你不知道捡哪一块会烫手。 ----《人面桃花》
12、在这里,写作的意义被卡夫卡严格地限定在了记录的范围之内:用一只手挡住耀眼的光线,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说,检测黑暗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意味着检测光明和欢乐短缺到了什么程度,在普遍异化了的现实境况之中,个人只有通过充满警觉的洞察,复活心中被遮蔽的人的理想,获救才会成为可能。 ----《博尔赫斯的面孔》
13、我以为中国小说叙事除了史传与笔记小说的传统之外,还有一个诗性的传统。这个传统在中国的小说史上若隐若现,至《红楼梦》终成蔚为大观,五四以后,又得以延续、演变和进一步地发展。 ----《博尔赫斯的面孔》
14、人心像一座孤岛 ----《人面桃花》
15、不惜一切手段达到没有可能实现的目标,这就是卡夫卡为他的喜剧所设置的前所未有的形式维度。 ----《博尔赫斯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