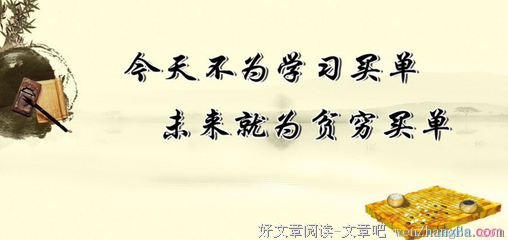●回溯往事,在那种放大中还有一种深层的共鸣——仿佛癌症已经击中了民众灵魂中震颤的焦虑。一种疾病如此强力地潜入一个时代的想象力,往往是因为它触动了那种想象力中潜在的焦虑。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ADIS)如此大规模地出现,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是一个被性和自由困扰的时代;在西方社会原本就为全球主义和社会接触传染忧心忡忡之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一时间又掀起了对于全球扩散传播的恐慌。每一个时代都将疾病投射在自己的想象中。社会就像身心枯竭的危重病人一样,把医学的苦难匹配给心里的危机;当一种疾病碰到这样一个内部和弦时,往往是因为这种共鸣早就在震颤了。 ----悉达多·穆克吉《众病之王》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属于自己的秘密,莫卡也有一个,他竟然做了那种彩色的梦,梦里的自己很模糊,带着情欲的脸忽暗忽明,而对方的脸却很清晰,那张脸莫卡到死都不会忘记,那张脸的主人叫辰格。梦里面,他忘记了自己是个男人,对方也是个男人,只有粗重的喘息,和辰格若有似无的触摸,那带着火一样的指尖,把莫卡燃烧的很彻底。莫卡扭动的身体一遍又一遍的叫着辰格的名字,以获得欢愉。
莫卡不是被这个梦给吓醒的,是在解脱完以后慢慢苏醒的,他抓起被子往下身看了一眼,然后捂住头,双腿在被里乱蹬,发出懊恼的声音。有些梦明明醒了就会忘记,可有些梦却一直徘徊在脑海里。莫卡为自己这个梦在床上恐慌了足足两个小时,才决定起床,他最最在意的是自己在梦里竟然是被捅的那一个。幸好今天是星 ----angelina《世界有点甜》
●即使遇见了很多困难与挫折,但生命中依然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值得去珍惜,就像漆黑夜空中闪亮的星辰,虽然微末的无法照亮整个天幕,却因为它们的点缀而使得夜空褪去了令人恐慌的黑暗,变得比白昼更加璀璨。
●我忽然觉得恐慌,那些你拖拖拉拉的念想,好像随时都会成为绝望。
●我们的战争充其量不过是内心之战,我们最大的恐慌就是自己的生活。 ----《搏击俱乐部》
●实际上,只要你不被自己的贪嗔痴疑慢所左右,根本也不存在卖错的问题,很多人,在连日顶分型的雏形都没有的情况下就卖,为什么?不过是贪嗔痴疑慢,觉得高了、觉得恐慌了,觉得惊吓了。而到真正的顶分型出来了,反而要假设这顶分型是假的,调整一下就可以突破的,就不觉得高了,不觉得恐慌了,不觉得惊吓了,人的颠倒,往往如此。 ----缠中说禅
●不必恐慌,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都会走。
●湖面,清风吹拂,涟漪悄悄荡开,莫名的思绪就在这万千的世界随波而来。我想不明白,即使夜以继日的思考,也不能透彻的明白。也许这是发自本身的,令人恐慌同时又另人沉迷,我喜欢着这样感觉的同时又在憎恨,寒意,在冰封自我的同时又在冰封世界,我敞开了笑却又痛哭着。
●每月更换牙刷的我,用塑料杯收藏旧牙刷,它们的握柄都还鲜艳,软毛却已变硬变乱,我生活得小心翼翼,去除对消耗品的消耗,还有回应礼节的彬彬有礼,极简是我能接受的极限,不喜欢留下痕迹,却更恐慌于流水汩汩,刷牙时不能望进镜面,据说虚实之间任何距离都会翻倍,这是否意味着,我总也追赶不上我的衰老。 ----倪湛舸
●睁开眼睛,我仍然只能站在这里,站在原地,而你依然遥不可及。从你所说的那些点滴,心里莫名的有些恐慌,我知道自己已经越来越怕失去。这是条看不清未来的路,迷雾重重,无论向哪走,都是你的影子,我从来就没给自己留过退路。要么爱,要么不爱,还能退到哪去呢。也安慰自己,其实我们也没什么,可心里投入了多少是无法伪装的。也想象过自己的结局,在某个无法忘记的季节,流一次泪,发不出一点声音,然后躲在某一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地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让我永远放不下的人。
●我会踏过很多山川河流,我会见证很多崛起和荒废,在那些我曾跌倒和流血的地方,我会建立起一个游乐场。有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巧克力贩卖店、有亮晶晶的摩天轮,有永远哼着歌的旋转木马。
那是年少时代我错过的游乐园。是我没有体会过的轻盈和快意。
虽然它迟了些,但它是你的。你可以抛开那些恐慌和警惕、焦虑和不安了。你可以光着脚在泥地里奔跑,像踩在云朵上那样。
或许这才是大多数人的成长故事。我希望有天在院线上看到的,不是打胎打架式的胡作非为,不是青春期狗血遍地,成年后蝇营狗苟的剧情,而是主人公努力补齐缺憾、跟往事和解,最终成长为一个勇敢又柔软的大人
青春期会过去,但我还是我。
●再被嘲笑的日子里恐慌,谁又知日后的成长,岁月雕琢人的模样?
●因为知道自己的生活是如此不堪,所以才强装欢笑,所以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