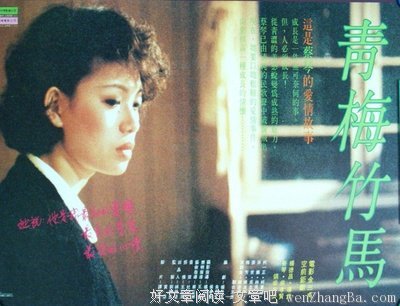开学季,《每日人物》杂志采访了叶蓓,唱着“白衣飘飘的年代”的她是曾经校园民谣的代表。那个年代的“矮大紧”老师长相清瘦、尖下巴,长发披肩,穿格子衬衫皮夹克大军靴。
那个年代的他们聚在一起录《青春无悔》,谈理想聊人生,即使知道时光一去不复回,依然义无反顾地唱着:都说是青春无悔包括所有的爱恋,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
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年轻。就如同我们信奉杰克凯鲁亚克那一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坚信着理想万岁,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不免俗地变成了曾经非常不屑的“不露声色的大人”。
“我们奔跑着又跌倒
只为挣脱生活的牢”
——莫染《给英格兰友人》
校园里,曾经深夜畅饮着笑谈人生的朋友们,终于还是会在面临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道一声再见。囿于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尖锐的棱角终究会被一点点磨平。
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尽管很多人告别过后就此相忘于江湖,但不管过多久,出现在彼此的记忆里的,还会是青葱岁月里最意气的模样。
“什么时候再回到春熙路去看一看成都的雨”,成都的雨一季一季下得依旧,看雨的人都再不是此间的少年。告别是漫长的,成长却是一瞬间。
一如北岛的那句诗: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你像我见过的那个少年
背着青春走在九月的街头”
——李志《九月》
王小波有一段著名的话:“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不知道生活这个“缓慢受锤的过程”对每个人的感知而言是否一样,有时候,一种日子单调乏味我却无力改变的丧气充斥身心,内心曾经的期许和坚持愈发在生活的试炼下显得渺小而可笑;可是有时候,却依然觉得自己能够一直生猛下去,尽管已经过了二十一岁生日,尽管亦不知这样的想法能持续多久,但是总归觉得,就算日子艰苦,还是该有些盼头的。
《奇葩说》辩手姜思达在微博上聊过类似的话题,他说:“对我来说丧并非常态,快乐也不是,时间拉长我的情绪跟快要断气的脉搏一样变成不痛不痒的直线。我常常把自己拉到旁边看自己,说,你看,你这里挺好的,那里也挺好的,确认一切正常之后开始刷微博看网页订外卖等着晚上到点洗澡睡觉。”
如此这般波澜不惊,如此这般不痛不痒。微博上转发的全是关于养生和“老年式”作息的话题,再也没有那些喝醉酒大哭大笑、肆无忌惮挥霍青春的日子。
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
——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说到对内心理想的坚持和基于现实生活的妥协,可能有的人并不会有太多的感触。在他们看来,“成为不露声色的大人”不过是个按部就班的事。
小时候,人人都说“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我要考北大清华”,最终真的达成这两个flag的人却少之又少。考上一所排名尚可的大学,毕业后有了份或稳定或收入不错的工作,人生无限重复的模式就此展开,谈恋爱,结婚,生娃,娃信誓旦旦地说“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要考北大清华”。
可是做过了色彩最绚丽的梦,你让他醒来回到按部就班的现实中,怎能甘愿。能把理想主义坚持到底的总是极少数幸运的人。
《血色浪漫》里的钟跃民可以说是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人设,重义轻利的他追求变化与新奇,讨厌被束缚,及时行乐,生活和爱情于他而言是个不断探索和感悟的过程。
那群出生在文革年代的年轻人,完美地把“鲜血”和“浪漫”二词诠释在一起,从兵荒马乱的青春中长大,却在时代洪流中不断被命运捉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会同样出现在当下,但他们经历过的热血和青春却依旧能够被共情。
没有理想的人真的不会伤心吗?
“理想永远都年轻
你让我倔强地反抗着命运
你让我变得苍白
——赵雷《理想》
你有过一个人在陌生城市无家可归的经历,你四处碰壁却也从不认命;你在写字楼高层里加完班已是东方既白,在靠着咖啡续命的日子里熬到了发年终奖的那天。
生存和生活面前,理想到底是一个精神安慰般的存在,还是心中真正向往的伊甸园和理想国?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会一样。不管长大之后的我们对理想的定义有何改变,那句“理想今年你几岁”却是唱给所有人,它让人踌躇又充满斗志,它让人茫然却勇往直前。
不管你一直坚信着、曾经相信过,哪怕是现在认为暴富最重要、理想它丫的算老几。理想万岁,青春无悔。
文丨Verity
图片来自网络
未经允许 禁止转载
《文周》开放征稿-回复“2”了解详情-
点击文章标题看“八月”文章精华“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在“好死”与“赖活”之间,我宁愿选择好死把你的影子腌起来,老的时候下酒“仇恨是让人活下去的好东西”
一份死亡功课我这条命是字幕组给的!你或许正被人24小时偷窥着春天分手,秋天会心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