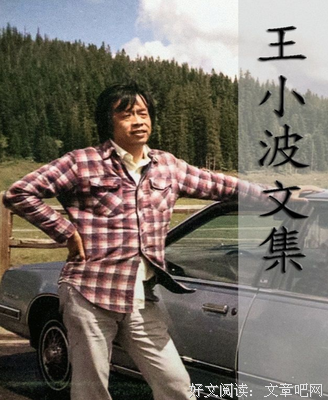初次接触王小波还是90年代上美术中专的时候。买的他的第一本书叫做《沉默的大多数》。翻开目录,有一篇叫《奸近杀》,那时候年轻气盛,正是荷尔蒙分泌最旺的时候,看到这种字眼,就激动万分直奔那一页。
“奸近杀”这个词来自于《阅微草堂笔记》就是作者看见两个蚂蚱交配,正看的起劲儿,突然旁边跳出来一个大蛤蟆,一口把两个蚂蚱都吃了。作者感叹,发生男女关系真的很危险啊!
这让我记住一段话:男欢女爱,人之大欲,绝然无伤,但一不可过,二不可乱,过则为淫,乱则成奸。淫近败,奸近杀,此乃千古不易之理。
《奸近杀》的文章有这么一段,说他的邻居家有个傻子,智商低到吃屎的程度,但对通奸之类故事迹象却大有兴趣——看见公鸡踩蛋也要上去轰开,并且嘴里喊:流氓!
王小波写道,红色年代的小伙伴,看到男女接吻就要扔石头,他把石头往银幕上扔,人家知道他有这毛病,就不让他进,但石头还是会从墙外飞来。你抓住他,他就一阵傻笑。 不知为什么,傻人道德上的敏感度总是很高。
这段文字越想越好笑,好在傻人的道德观实施起来害处有限,顶多是冲银幕或自家屏幕上扔扔石头,害处大的是那些不傻的,这种人很知道和权力一起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多么风光、安全,并好处连连……在附逆这件事上,哪个时代都有不肯缺席的文人。唉!
读王小波的文字,他身上有一种孩子气,就像《皇帝的新衣》里勇敢说出真相的小孩,你看他的杂文,鞭辟入里,既享受思维的乐趣,拥抱理性与常识,也跟随灵魂的舞蹈,在凡俗生活之外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我的精神家园》有一篇“伟大一族”的文章,里面王小波提到鲁迅杂文里有这样一个人:他梦想的最高境界是在雪地里干呕一口血,由丫鬟扶着,懒懒地去院子里看梅花……
王小波说看后很生气,我却突然被奇异的击中。一个病秧子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安然欢惬,这样死在雪地里怕也是极美得了。
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总是胸怀天下,怀揣梦想。理想,远方,与诗与酒:渴望建功立业。 这样的人有个好处,就是不太流于俗套,缺点是梦想无着的时候总会隐隐作痛,即使不怨天尤人,也会暗地里抱怨怀才不遇。 流光暗换,韶华逝矣。梦也会有散场的时候。
《我的精神家园》是我1998年买的,书皮都掉了,现在还在床头没事翻翻,常常会有一个想法:如果王小波在世,他对现在发生的事会怎么写? 如果鲁迅还在世,他对现在发生的事会怎么写?然后就一阵阵的失落和遗憾,就像我喜欢看某人写的公众号文章,读着读着此人却停更了或者已被销号了。
不是就在公众号里写点文字嘛,怎么说死就死了呢?有个故事说,一只老虎和一只猪在一个山洞里,一夜之后老虎死了,那么老虎怎么死的?
猪说,这是一桩无头悬案。
这个故事很像王小波写的一篇题目叫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家伙,他笔下的那头猪后来也逃了出去,成为了一只自由自在的野猪。
活在老虎洞里的猪都不甘心,但真正愿意冲破这个老虎洞和这个世界勇敢说不的猪又太少。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的原话: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如此无视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猪和老虎在山洞里,猪又逃不出去,然后老虎又抓了只猪进去和前面的猪交配。猪又生猪崽又生崽。而老虎杀了又吃,吃了又杀。经过N代以后,猪认为老虎吃自己的孩子成了天经地义。用王小波的话说,“每个人的贱都是天生的,永远不可改变。你越想掩饰自己的贱,就会更贱。唯一的逃脱方法就是承认自己贱,并且设法喜欢上这一点。”真是深刻而又无限悲观的人性洞察!
不过,真正天生的贱是你永远无法意识到的,因此才永远不可改变,岂能承认而喜欢上呢?正如鲁迅说的(大致):“做猪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猪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猪了。”所以,改变的出路是让直觉与概念分离,这是个逻辑问题。但是,我仿佛听到老虎哈哈大笑,猪们只是吃,谁还在乎逻辑?
是啊,在猪眼里逻辑值几毛钱一斤?总感觉这只老虎在嘲笑我自己。最早看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时候,曾经心里暗暗告诉自己要做只特立独行的猪,但是这几年下来,特立独行没做到,猪做得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