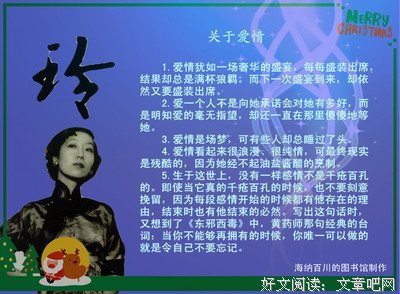这是一个有趣有味儿的公号,很多读者都置顶了(点上边蓝字关注)
文 | 丁小村
一
我今天丢了一本书:我从来不觉得丢书是个不快的事儿,但今天例外——因为丢的是张爱玲的《赤地之恋》。
为什么我觉得丢书不坏事儿?一般来说,书被人拣去,那就等于替作家传递了一回——让张爱玲重新活一次。当然,也有比较小的可能性:这本书被人拿去当做废纸卖了。
我跟张爱玲的这点缘分,是因为《赤地之恋》。大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满世界的张爱玲热中,望着架子上的一堆张爱玲,连多看一眼都没有。
我这个人有点儿倔头倔脑,觉得流行什么,我偏偏不赶这个热闹——后来甚至连《十八春》都被改编成了电视剧,《色戒》被改编成了电影,我才开始看张爱玲。在此之前,我随便看了几篇她的文字,比如《谈女人》之类,觉得她十分机智,这种聪慧可能非一般女子所能比,但她也会栽在胡兰成这样的男人手上——是人都有软肋,张爱玲的软肋就在于她是一个正常女子,渴望获得正常的感情,愿意付出正常的情感。
二
1995年秋天,一位朋友告诉我,张爱玲去世了。我看了看新闻,才知道张爱玲在美国的寓所里离世,被发现时已经是一周以后了,她孤单地蜷缩在地板上一张灰蓝色的毯子里:朋友们依照她的遗言,把她的骨灰撒进了大海。
尘归尘,土归土,生死不过是人间常态,一个作家肉身逝去,所有爱恨情仇也烟消云散,唯一可以继续的是她的那些传世之作。
这时候我才下意识地看看我的书架,上边一排张爱玲的作品,我几年来都没翻过一次,蒙满了灰尘。我随手拿起一本,随手翻开,我忘记了张爱玲的模样,记忆中我是看过她的照片的——我在灯下,开始阅读张爱玲,猛然间,世界不复存在,只有一片斑驳的月光、几声走调的琴声……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张爱玲《金锁记》)
安安静静读张爱玲,才能读出几分文字的韵致、气氛的清淡、时光的舒缓,还有那一点点慵懒。
在我们提倡了几十年的革命文学的背景下,这样的文字与世道多么相违、何等地不搭调。大概是在1995年的某个冬夜,我第一次感受到张爱玲的这点清凉,夜凉如水啊。
三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胡琴上的故事是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搬演的,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鼻,唱了、笑了,袖子挡住了嘴……然而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张爱玲《倾城之恋》)
这把胡琴就这样扎在了我的阅读记忆里。此后每次翻开张爱玲,我心中都会默念着这些句子。我对于那些时尚话题、赶热闹读书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读到的,就是属于我的张爱玲。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林黛玉。没错,这话看起来简单,其实是对作家最高的褒扬:哈姆雷特和林黛玉能活多少个世纪,作家就能活多少个世纪——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啊,这才是作家的功业。
帝王的功业是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碑上、写在史书中;富豪的功业,是把自己的钱拿来修永不崩坏的墓,把自己的牌位放在家祠中;那些伟大的智者和圣者,把自己的精神写在世人的心中……唯有作家的功业,就是让自己的文字像音乐般穿过时光,回旋在每一个后世读者头脑中。
我在这个冰冷的秋夜,一盏孤灯下,打开了张爱玲的书,拂去灰尘,让那些文字活过来:这时候张爱玲已经飘散在某个大海的水波里,她的光芒,却照耀着一个远隔万里的读者。
四
下班时,我把张爱玲的《赤地之恋》夹在电瓶车的后座上,准备带回家阅读。我得经过一条小巷,小巷里有一个幼儿园,放学时挤满了接孩子的家长,他们的小车、电瓶车、自行车,挤满了小巷……这时候一个清洁工推着垃圾车,闯进车流中,她和她的车把小巷的车流彻底堵住了。我只好掉头绕道回去,绕过这条小巷,我飞奔回家,在楼下停下电瓶车,突然发现,我把《赤地之恋》丢了。
我心有不甘,甚至回头按照原路重新走了一次,当然,不出意料,我没找到书。我在心中祈祷,希望这本书被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捡到——那将是张爱玲的另一次重生。
我舍不得,觉得遗憾,是因为这本书是我特意让我的一位学生从台湾带回来的,皇冠出版社出版。丢了这本书,我一时半会儿再也找不到了。
《赤地之恋》我当然读过很多次,我和张爱玲的一点缘分,就属于这本书。
五
1996年左右,我几乎读了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当然只限于中国大陆出版的。我没有台湾香港的朋友,当然也看不到港版台版的张爱玲。我知道,有两部书,在大陆是所谓的“禁书”——是不是明文规定的禁书我不知道,但大陆没有出版过,这是事实。
这两本书是《赤地之恋》和《秧歌》。
我的一位好友给我复印了一本台湾版的《赤地之恋》——这本书当然来之不易,朋友对我说,为给你复印这书,差点儿烧坏了一台复印机。
于是我在厚厚的一本复印纸上,阅读《赤地之恋》。大概也是在一个清凉的秋夜,我读出了张爱玲的热情、悲凉和孤单。
《赤地之恋》开头写的就是一对年轻人参加土改运动,在满世界的革命歌谣中,在群众运动的如火如荼中,他们感受到的是一份孤单,需要相互拥抱——但他们不能拥抱,甚至不能牵手,以慰藉对方同样的孤单和惶恐。
这和我在1996年左右的心境很相似——我还没结婚,算是个年轻人,对于大时代感觉十分惶惑,对于当下的生活无从把握,别人在这儿那儿创业,在南方北方发财,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条沙滩上的鱼,不知道天地有多宽阔,只觉得孤单无助。
这是我从《赤地之恋》里读到的某种孤单:在某个大时代里,个人的命运就如同风雨中的小舟,既孤单又无力,既迷茫又惶恐。
我十分喜爱张爱玲在《赤地之恋》中描写的这种心境。过了好些年,我明白了,这不是一个年轻人的孤单,而是一个人在世的孤单——你只能以你自己的方式活在人间,也许你可以牵着一只手,偎着某个怀抱,来相互温暖,相互慰藉,但那也需要缘分。
六
我后来又在网络上找到了《赤地之恋》的电子版,收藏下来,偶尔还传给想看的朋友看看,我有时候会在电脑上翻一翻。
那本复印版的《赤地之恋》,我一直放在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像是一个纪念品,又像是一个活着的张爱玲,我时常可以和她交谈、与她对视。
前几年,我的一位学生常去台湾,我特别叮嘱他一定给我带一本《赤地之恋》回来,终于,他没有失信,给我带回了这本书,摸着走了几千里路的纸张,我特别开心。
我经常翻翻这本书,有时候带到办公室去翻翻。在我的书房与办公室之间,它行走了无数次了。
我觉得,让张爱玲活着,是我一个后辈作家应该做的事儿。
但是很遗憾,今天,我又把这本书丢了。所以我特别希望,捡到这本书的人,是一个特别爱书,能读张爱玲的人——
—The End—
(阅后请点赞!最好的支持就是将我的文章分享给其他朋友,谢谢!)
点下边的题目链接,阅读公号最新热文:◆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我读《红楼梦》:听一曲中国女性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