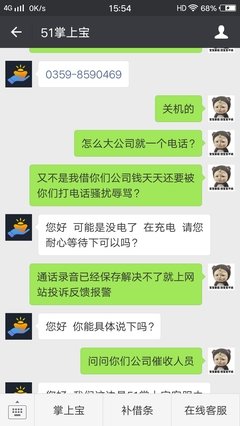别让我一个人。
文 / 刘白
因为每个星期妈妈都会打电话给我,然后把那段时间的所有八卦说给我听,大到我的二表哥做爸爸了,小到家里换了个新冰箱。
这个清明节,妈妈照样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聊到邻居家的小孩时,她有点怜悯:“龙仔的父母,清明都没空回来。”
妈妈开玩笑地说:“你也没回来啊,那我们也是留守父母了?”
一。
我承认,我被“留守父母”这四个字击中了。
电话挂断后,房间归于安静,我才忽然发现,原来妈妈语气中的怜悯,不是因为邻居家的小孩,而是因为她自己。
我算了算,自己也有小半年没回家了。
可能小时候被寄养过的小孩,长大后都不会太恋家。因为已经尝试过父母不在身边的滋味,就会觉得,原来离开他们我也可以生活下去。
于是初中开始寄宿,舍友想家想到躲进被子里哭的时候,我在无动于衷地看书。
高三那年我很拼,一个学期只回了三四次家,而且只是匆匆吃个晚饭,就拎着妈妈为我准备的一大袋核桃,赶回学校晚修。
好像就是那个时候,妈妈的口头禅变成了:“别急,慢慢吃。”
二。
打完那通电话,我洗了把脸,准备睡了。
枕头下的手机震动起来,是妈妈发来的信息:“听说江北那里建了个新的小学,准备招老师,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但我睡不着,因为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直到现在,妈妈还是那么固执地想我回家工作。
而且我已经向他们证明了,自己在广州也可以过得不错,但他们就是不肯支持我。
虽然我也不那么需要他们的认同,但对于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少了来自家人的理解,始终会觉得缺了点什么。
我却不肯罢休:“对他们来说,把我留在身边这件事,有那么重要吗?”
作为旁观者的男朋友,看东西似乎比我清楚得多,他反问:“其实,你平时也很少给父母打电话吧,节假日也很少回家吧?”
一阵心虚让我转了个身。
见我许久没说话,男朋友伸手把灯关了,眼前所有的东西都被黑暗隐去,耳边只剩下他睡前说的那段话:
“他们也不是一定要你留在身边,只是你的不在乎,让他们害怕自己会在哪一天,被你忘了。
你要知道,即使是父母,也是需要安全感的。”
三。
但我难过,不仅是因为自己没有给到家人足够的安全感,还因为我发现,他们总能把自己的脆弱隐藏得很好。
他们家小房间很黑,在那个米色黄花的枕头上,我流过很多眼泪,都和缺失的陪伴有关。
每个周五,我都不会穿我认为最好看的那套衣服,因为要留到周末去见爸妈时才穿。
有时候太想爸妈了,会吵着给家里打电话,明明按号码前,已经想好了要说什么,但一听见妈妈“喂”的声音,就什么都记不起来,只会哭。
那段时间,我会不停地怪他们:“为什么不来接我?为什么不来见我?”
没想到十几年之后,我和他们的身份,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互换。这段关系的主动权,也渐渐转移到了我的手上。
而我也越来越少回家见他们了。
只是我不陪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像当初我怪他们一样怪我。
因为只有小孩才可以肆无忌惮地怨恨父母不回家,父母却不能自私地苛求小孩,放下工作和自己的生活来陪自己。
挺不公平的。
不然,我很久没回家的时候,妈妈也不会什么都不说,只是在电话里暗示一句:
可迟钝的我,每次只听见了“荔枝”,却没听见那些可能存在,却被他们藏得很好的想念。
最后。
我本来以为,“留守父母”这四个字,不过是妈妈的一个玩笑。
直到我在搜索栏中,敲下这四个字,才发现这已经成了当下社会的特有现象。
汽车站里有多少拉着行李箱的大学生,北上广的地铁里挤着多少要上班的年轻人,几百公里外的二三线城市中,就可能有多少对被留守在家的父母。
还记得我开头写的那句话吗?“每个星期妈妈都会打电话给我。”
我想,这个星期,该换我们打这个电话了。
作者/ 刘白
如果你愿意,听听我不说话
歌曲/ cry for the moon
插图/ 一一
问两个问题:
点好看了吗?
星标我们了吗?
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