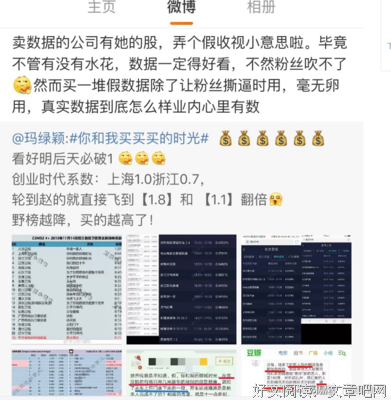新片《地久天长》,三个小时,跨度三十年,讲述了两个家庭跌宕起伏、悲喜交加的人生故事。
导演王小帅,用他一如既往白描式的叙事手法,在宏大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中,勾勒出小人物清晰细腻的生活画卷。没有喧宾夺主的夸大和浓墨重彩,平实、节制地娓娓道来,大片的留白,让观众可以在其中自由填充和释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
不同的人,看同一部精品电影,站在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内在经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心灵碰触、共鸣和领悟。
从心理学角度看,《地久天长》之所以优秀,原因之一就是,人物和情节发展的心理逻辑是存在和自洽的。接下来,我会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尝试梳理出一条与系统、创伤以及自愈相关的理解脉络。
1系统创伤推动下的个人不幸心理学的系统理论认为,如果把社会视作一个大的动力系统,那么,家庭就是这个系统的基本单位——子系统,而在家庭这个子系统中,每个成员是基本构成单位——个体。
当主系统发生巨大变革和动荡时,必然产生一系列创伤性体验,而承接这些后果的,就是子系统。简单地说就是,社会不稳定,家庭受害;家庭不稳定,成员受害。类似于蝴蝶效应,这是一个动力性传递过程,不是断裂的,而是环环相扣。
带着系统观,再来看电影《地久天长》中两个家庭之间发生的故事,就会清晰许多。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和转型的时期,十年动乱刚结束,严打、计划生育、改革开放和打破铁饭碗又陆续开始。变革接二连三,旧的平衡不断被打破,新的平衡还没建立起来,让人来不及去适应也很难驾驭。每个家庭和每个人都在动荡、不安和迷茫中努力维持着自己岌岌可危的稳定和平衡。
剧烈变革的获益指向未来,而伤害留在当刻。如果时代的创伤必然要落在某一部分家庭和个人身上,哪些人最容易成为牺牲品和受害者呢?心理学告诉我们,系统中自我分化程度最低,主体性最差,依赖性最强的那一部分家庭和个人。
电影主人公耀军、丽云夫妇与英明、海燕夫妇,同为知青好友,同在工厂上班,同样育有一子,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两家岁月静好,当变革来临时,两个家庭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命运走向。
英明和海燕一家在大变革中生存和适应下来,在社会规则层面越走越远、越站越稳。而耀军和丽云在接二连三的社会冲击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跌落,最不幸的,还在意外中痛失独子。
弗洛依德说,这个世界没有偶然,所有的偶然背后都隐藏着必然。
在大变革中,能较少遭受系统冲击和伤害的人,不是因为他们运气好,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更高自我分化水平和更强的主体性,简言之,就是有主体性的人,更清楚自己要什么,更善用资源,并愿意为之努力。
外显在性格和行为层面,英明和海燕夫妇会更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变革和适应变革。计生政策出现时,海燕选择成为规则的参与和执行者;改革开放之初,英明主动下海经商,选择成为新规则的制定和使用者;他们的独子浩浩,从小就表现出积极果敢、爱冒险和喜欢挑战,这些人格特质的具身,是家庭系统无意识动力传承和推动的结果,而在这些所有表象背后,彰显出的是成为强者的必备品质——主体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而耀军和丽云夫妇呢?他们的隐忍和善良毋庸置疑,可他们的处处依赖、处处服从和处处被动,不也是自我分化不足、缺乏主体性的主要表征吗?丽云无意中对自己老公的一句评价,也印证了这一点:“耀军不是老实,他就是傻”。
迷迷糊糊地怀了二胎,浑浑噩噩地被拉去人流,莫名其妙地丧失生育能力,毫无准备地被下岗。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也未曾往哪个方向努力过。渴望安稳的背后,是缺乏主体感的迷茫、消极和被动依赖,这使得他们一家向着牺牲品的位置不断滑落。
主体性的缺失传承到下一代,在他们的独子刘星身上,就更加突出。在刘星意外死亡前,有好几处情节和镜头显现出了这个乖孩子的真实状态,胆小、懦弱、纠结、被动。
电影中有一个长镜头我印象特别深刻,刘星坐在岸边,看着别的小朋友在水边嬉戏打闹,即不敢参与又不敢离开,好像被牢固定在一个地方动弹不得,眼神迷茫而空洞。这一刻,他的状态不正是他父母状态地继承和再现吗?
从心理学意义上说,刘星的死亡,不仅仅是一个打闹导致的溺水意外,而是家庭创伤的延续。同时,他的死亡也是一个隐喻:所有迷茫、消极和被动的个体,丧失主体性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自我保存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在激烈的变革和动荡的竞争中,注定要受害和消亡。
写到这儿,我是有一些担心,我的文字也许会引起一些读者的心理不适,因为大家惯常同情弱者,有些人可能会骂我冷血,说我缺少对受害者的基本同情。
同情并不能使弱者走出受害者的位置,只会把他们固定得更牢。我更希望通过促使人们开始去思考自己的位置,开始对自我负责,为避免下一个悲剧和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付出积极主动的努力。
2接二连三的重大丧失和对好友一家的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耀军和丽云一时无法承受和面对,他们选择了回避。于是,在一个晨曦微露的早晨,匆匆地不辞而别,逃离了这个会勾起自己痛苦回忆的城市。
逃掉了身,逃不掉心。回避的态度,是一种对已发生事实的否认和拒绝;逃离的方式,并不能给创伤者带来新的生活,只会令他们永远活在过去。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时间里,即使无数次搬家,即使到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耀军和丽云始终无法放下过去,无法开始新生活。用心理学来解读这些现象,由于对丧失拒绝接受,导致哀悼无法完成,他们开始陷入一种深重和漫长的抑郁状态。用耀军自己的话说:从儿子死去的那一天起,生命已经停止,有的只是时间的流逝。
他们尝试收养了一个男孩儿,可并没有把这个孩子当成一个全新的对象去爱,而是当成了死去儿子的替身。没有一个人甘愿丢掉真正的自己,成为亡灵替身。这种畸形的养育方式,必然会激发起另一个生命的强烈抗议。
意识或无意识中,养子用各种各样叛逆的方式,彰显自己不是刘星的事实,并试图唤醒和逼迫养父母接受刘星已经死去的事实。包括他偷窃同学物品的行为,也不过是在向所有人呐喊和求助:我的人生被偷走了,你们看到了吗?
在一次最激烈的冲突之中养子出走,一场大雨之后,家被淹了,各种物品杂乱的漂浮在水面上,现在的全家福和过去的全家福同时出现在耀军和丽云面前。真实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并打破幻想,他们开始不得不面对和接受丧失,二人失声痛哭。这次痛哭有心理学上的疗愈和发展意义:他们进入了从抑郁向哀伤转化和修通的过程。
把写有养子真名的身份证交给养子,当养子向他们磕头拜别的那一刻,父母和孩子都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分离和确认:一、养子找回了自己身份,成为了他自己;二、耀军夫妇终于接受了所爱客体的丧失,可以试着把养子当成一个全新的客体去爱。
3为了忘却的纪念电影中,命运紧密相连的两家人,承接了时代赋予他们的创伤,在无意识地推动下,借由一个孩子的死亡,分别对号入座,成为现实中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如果说,耀军和丽云背负着受害者的悲伤感和愤怒感,那么,英明和海燕一家,则背负者加害者的罪恶感和内疚感。
对创伤的回避和逃离,直接导致了两家人长达二十年地断裂,他们各自背负着创伤的一部分碎片艰难前行,始终没有得到机会整合和疗愈。
悲剧的亲历者浩浩,一边目睹着好朋友在自己眼前死去,一边背负着过失杀人的罪疚感,这是一次严重的急性应激创伤。这次经历带给他的罪疚感与母亲无心之失却导致好友绝后产生的罪疚感如出一辙,并且有着系统的延续性。
那个年代没有心理治疗,双方父母只是本着对孩子最朴素的爱和保护的愿望,用回避的方式把这件事掩盖了起来。可掩盖和压抑的结果是什么呢?
“你以为绝口不提便会忘记,但从那一天起,我的身体里面就像长了一棵树,直到现在快要把我身体撑破了”
浩浩的母亲海燕患上严重脑部肿瘤。这是一个象征,当创伤带来的各种感受不能被适当言说,就会被固定在身体里的某个地方,拼命向外冲,形成各种各样的症状和躯体疾病。
二十年后,浩浩成为了一名医生,在母亲死亡和自己儿子即将诞生的这个生死节点,内心的巨大张力和整合疗愈的愿望,促成了两家人的会面。当浩浩鼓起勇气,面对星星父母,一字一顿地讲出了当年星星死亡的全部真相。耀军和丽云流泪了,耀军说:孩子,说出来就好了。这句话不止说给浩浩,也说给他们自己。当创伤可以被面对,两部分碎片就会相遇和整合起来,不再传递,疗愈也随之发生。
影片的最后,耀军和丽云来到星星的坟前祭奠。老两口坐在儿子的坟墓两边,看着远方的风景,一个喝水,一个喝酒。没有悲痛欲绝的沉重感,只有一股淡淡的哀伤,这不像是一次哀悼和告别,而更像是一次纪念。
何为纪念?就是我们已经告别和走出了过去,并且接受回不去了。
两家人,用了二十年时间,从丧失、抑郁到哀伤,再到纪念,完成了时代和个体创伤的自愈历程。
小人物的命运,在大时代的洪流裹挟下,虽然显得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些在最低谷、最黑暗之处生长出来的顽强生命力,才最踏实、真实和带给人希望。
最后,我想借用豆瓣的一句影评收尾:岁月流逝,生命滚滚向前。
推 荐 阅 读
猛 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