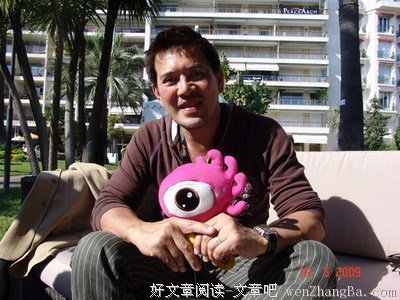《基纳瑞》是一部由布里兰特·曼多萨执导,梅赛德丝·卡布莱 / Julio Diaz / Jhong Hilario主演的一部犯罪 / 惊悚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基纳瑞》观后感(一):“当代电影”与布里兰特·曼多萨
为了区别于现代电影,我们提出了“电影当代性”的问题,并将阿巴斯与侯孝贤作为衡量当代电影的两个标杆。如果说阿巴斯对“道路-寻找”主题、汽车-空间与虚实影像的创造为当代电影提供了母题、表现形式和艺术创新,那么侯孝贤在创造过饱和影像(《海上花》)与松弛影像(《咖啡时光》)上则有独到的过人之处。影像的真实性在侯孝贤的手上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命题,没有哪位导演像侯孝贤那般执着于通过“还原”的方式来再现现实生活的真实,这种“还原”的技能如此彻底,以至于给人一种“笨拙”的感觉。对此进行弥补的是通过不断丰富影像中呈现的信息,从而在过饱和的状态下让观众忘记固定摄影机所处的尴尬状态。
正是在与侯孝贤的比对中,我们发现了布里兰特·曼多萨电影的独特之处。侯孝贤通过固定镜头(中期)或左右摇移的镜头(后期)调制现实的方式与曼多萨用手持镜头快速纪录下现实的方式相当殊异。侯孝贤式“还原”的秘诀在于丰富出现在镜头前的物像,《海上花》开头的那个长镜头全然是设计的结果,观众的注意力简直不知道要看向何处,不再能像惯常情形那般集中于某个人物的面部或动作,因为每个演员都展示着自己的姿态、声音与神情,这种丰富性对摄影机镜头造成了冲击。曼多萨可谓以另外一种极端的方式创造出相似的效果,轻便的手持摄影机如同一阵旋风卷进了马尼拉的底层社会,呈现出小偷、妓女、车夫、警察……共在的如同地狱一般的世界(《丫丫叉叉 》)。因为影像密度的极大化,真实已经不再像新现实主义那样是被捕捉到的,而是自动地暴露于影像中。
除非马尼拉天然地适合于影像,菲律宾人民天生是演员,不然如何解释曼多萨电影中的奇观?那种难以置信的丰富性和真实感。解释也许在于曼多萨掌控与调度现场的超一流能力,摄影机镜头只要一扫过某个人物,这个人物就能够真实地呈现于观众面前(听着像是费里尼的魔法):人物在空间中的走动不断影响着影像世界的生成,同时影像世界的生成也在帮助完善人物。这就是一个自得的世界,一旦给予了足够充足的养分,便可自行发展。在曼多萨的电影中,在叙事线上延展出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发展出一个自己的世界并附加到影像自身的复调体系中。如同曼多萨自己所言,这是“现实最真实的倒影”。
附:电影的当代性:阿巴斯与侯孝贤
《基纳瑞》观后感(二):一场无呐喊的殇痛
一部电影让人读懂菲律宾。
《Kinatay》(基纳瑞),2009年角逐戛纳金棕榈的菲律宾电影,最终在一片争议中斩获最佳导演奖。
试着在GOOGLE用英文搜索,该片词条结果竟然仅为17条,一个叫寒风四起、冷门飕飕啊~~中文词条出乎预料的超过十万(搜索结果可能将不相关词条一并记录,此处忽略),让人感觉还是中国人多、聪明、有追求的。
故事的核心记录着一群警察的黑白身份,一个妓女被凌辱和残忍肢解,一个青年参与其中的内心挣扎。
一个颇有姿色的妓女,因为没有交足保护费,被毫无悬念的殴打、凌辱、杀害、肢解、抛尸,而操作者是一帮当地的警察,其中还有长官。那个白天刚刚办完婚事、一心想要挣钱养老婆和孩子的青年,晚上被警察同事带出来挣外块,遇到了他这场人生中的“第一次”。他震惊、惊恐、害怕,也曾想要报警、出手救人,可最终都无疾而终。
最后,天亮起来,这帮刚刚还凶神恶煞的警察们来到一家早餐当,吃起了汤面,恢复平常人的面貌。一场无呐喊的殇痛就此结束。
而作为引申的片头、片尾却竟然是唯一的两个伤痕冲抵区域:片头,是市井贫困的马尼拉贫民窟生活景象,片尾,是青年的妻子抱着7个月大的孩子一边炒饭。平静、平凡、贫穷,没有挣扎、质疑、纠结,只有服从、认命和无可奈何。
电影都有能量守恒。许多电影非常残忍、黑暗,但导演终究会在某个地方给予希望的光芒,哪怕是一瞬间,也会产生极大的效应来冲抵之前的负面情绪。如,和这部题材有一点点类似的意大利电影《不可撤销》,最终以莫妮卡的丈夫成功殴打暴力者和莫妮卡迎来新生宝宝而给人光明。当然,有小众导演是不愿意处理得这样看似完美的。《Kinatay》就是这样一部电影。那悲伤的、痛苦的负面在这部片子之后可以用什么东西来冲抵呢?或为观者自身正义、向上、慈悲的人心吧。
两匹马的电影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7289287,欢迎来踩~
《基纳瑞》观后感(三):基纳瑞 Kinatay
有人说这是部口味比较重的电影,但事实上在虐杀程度上和韩国日本电影无法相比;个人感觉出彩的是电影开篇全家携子结婚的欢乐场面对于下面情节中隐含的潜秩序下小人物的无奈和可悲,家庭的欢乐从某种意义上预示了后来主人公左右为难却最终选择同流合污的境况;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驱车前往犯案过程中的那几十分钟,观众席上已经有人忍不住离席而去,而我也有点昏昏欲睡,或许是昨夜没有睡好的缘故。对这种摇晃厉害六神无主式的镜头丹麦人已经被道格码兄弟蒙混了,所以不想再多看。观片后和几个丹麦朋友的讨论,大家都认为确实是个好故事,但是完全可以拍得更好;几乎所有人对导演Brillante Mendoza凭借此片赢得去年戛纳的最佳导演奖感到不可理喻。记得有个评委事后对媒体说就他个人而言,他再也不想看这部电影,可见那时在这个奖项问题上评委间争论也是非常激烈。
《基纳瑞》观后感(四):曼多萨的声画与现实国度
曼多萨直接用“虐杀”(Kinatay,2009)来命名这部影片,并不是一个偶然,这位菲律宾导演从第一部作品《情欲按摩院》开始就喜欢用单个单词来作为片名,这也意味着一种明确的定义立即在电影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一个中心的、政治的位置。2009年曼多萨一下推出了两部作品,一部是《基纳瑞》(Kinatay),一部是《祖母》(Lola),分别去了当年戛纳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这两部作品单从片名上就能看出黑暗与光明的对比,但这两部电影的主题都是关于生活的分裂、衔接、排斥和融合,如同一组社会调查,导演在对马尼拉底下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的政治生活所造成的不同表现方式中获得了创作的动力。这种对立不仅仅来源于善良与罪恶、残暴与良知这些二元性质,也来至于无力的抗争、绝望的情感、迷惑的现实等多重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叙事层面。
两部的影片的开场镜头都带我们来到马尼拉热闹的市区,下层菲律宾人的聚集地,他们多是从郊区农村来到这里,企图在大城市中寻找更好的生活。《祖母》中,祖母回到老家借钱企图与抢劫杀人的受害者达成和解,挽救自己的孙子。火车连接了繁华的城市和宁静的乡村,但沿途却是触目惊心的贫穷,走向城市的道路并不是想象的那般美好。《基纳瑞》里城市生活与郊区别墅里的轮奸杀人分尸的对比就更像是一种寓言了,来自城市的这辆面包车如同一个黑暗的魔鬼吞噬着原始的纯真。曼多萨来自菲律宾一个偏僻小城,马尼拉的霓虹灯同样也映照过他的迷茫与孤独。
曼多萨并不满足像前几部作品一样,在封闭的环境中(按摩院、电影院)探索现代化的人性之殇,在这里他还试图创造独特的现实图景,摄影机走向街道,拥挤的人群,车流如织的市集,教堂和银行,警察局与法院,取景框的位置、摄影机的移动、镜头长度、图像切换与每个人的行为方式让潮湿混乱的菲律宾社会变得立体和真实。电影被叙述而不是电影叙述,这些丰富的细节串联起人物与环境的更加深刻的互动。在《祖母》开篇的点蜡烛的那场戏中,第一个镜头买蜡烛的特写开始,观众就跟随摄影机走入到一个慢慢变得残酷的生存图景里,教堂、公车、小偷到祖母大风中艰难地点燃蜡烛,这与人们通常听说的语言词汇来引导图像的方式刚好相反,此刻的观众完全不知道这些情节背后隐藏着的故事,但他们体会到了此刻的忧伤,长镜头,摄影机在狂风中摇摆或固定不动,观众感同身受,我们仿佛和电影中的人物共同生活、一起存在。
在新当选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看来,犯罪是这个国家的罪恶之源,打击犯罪是当务之急,他也因此赢得了大量底层选票的支持,从而成功当选。曼多萨对菲律宾警察系统的腐败深恶痛绝,他在2009年的这两部电影中都将警察司法系统的腐败作为了抨击对象,这个主题也延续到了2016年的新片《罗莎妈妈》中。《祖母》中的两位祖母让我们想起了《一千零一夜》中那个战胜权利和宿命的女主角桑鲁卓,她们能做的就是用自己衰老的身体来对抗宿命般的折磨。《基纳瑞》里,年轻的警校学生在新婚之日被卷入一场地狱般的惨剧中,他多次想要逃离而不得,结尾“慢慢就习惯”伴随着金钱的诱惑也直击腐败罪恶的社会现实。最后一场戏里,主人公坐出租车回家没想到车轮爆胎了,他在司机换车轮的时间里多次想要拦其他出租车,但没有一辆车为他停下来,最后他不得不又坐进了原来那辆车。这是无法逃离的宿命,没有人来解救他,他只能无助地面对罪恶。《祖母》里棺材店中那场戏,祖母找乱跑的孙子,她走入那深暗狭窄的巷子,此时的画面就像是一口巨大的棺材,在巷子的尽头她看到了死去孙子的尸体。这同样也是无法逃离的宿命,人们必须面对生命尽头的死亡。年轻学生的脸和祖母布满沟壑的脸映照出同样的一种情绪,他们本可拥有触手可及的幸福,却被命运无情地抛弃在了玻璃墙的另一边。
警车的警报声和台风来袭的雨声风声贯穿了这两部电影。警校学生用良知进行了一场无用的战斗,祖母的英勇却更像是对这个不公平社会的妥协。要想生存就要退让。我们不会把他们仅仅看作是底层郊区的菲律宾人,把这个故事看作是描述贫穷生活的电影,这更像是反映了菲律宾社会的真实现状,影片真正震撼人心的是它所表现出的社会分化和穷人边缘化的问题,不公平的政治时刻在入侵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基纳瑞》中,小混混向摊贩收取保护费,然后转交给警校学生,学生再将钱转给黑警察的走狗,这就像是一条完整的食物链,弱肉强食,此时的主人公身处其中却浑然不觉,在经历了恐怖一晚之后,他也发现,自己在食物链上的角色是如此可悲,想要挣脱,却早已被栓死。《祖母》中女性中心化的主题同样有趣,两个家庭中一个家庭父亲缺失,一个家庭父亲瘫痪在床,男人被曼多萨边缘化,无疑批判了菲律宾社会男权当道的现实。《基纳瑞》开篇的婴儿主题,再到被杀女人的母亲身份被反复提及,“生与死”的社会现实也被揭露出来,这之间联系居然如此紧密,并且相隔并不遥远。如果说《基纳瑞》里通过图像与声音构建出了一个狂欢般的地狱图景是如此令人绝望的话,那么《祖母》里下层苦难与快乐(捕鱼、邻里相助)的交织就更显希望的可贵,我们能看到贫穷之人摆脱贫困的梦想和为这个乌托邦所付出的努力,曼多萨通过对这片土地真实的记叙,通过图像和声音,成功创作了当今真正打上菲律宾标签的电影,这些元素通常只属于边缘社会,只有用敏锐的洞察和强烈的责任感才能记录下来,电影被叙述,这声音来自内心深处,它被大多数人所忽视,缺少政治影响力,但它代表了最伟大的电影传统,从德西卡、罗西里尼到布罗卡、拉夫·达兹,曼多萨让它在今天延续。
《基纳瑞》观后感(五):恶魔的养成
车上有七个人。司机,老大,第一干将,第二干将,小弟,小小弟还有即将被虐杀的女人。
女人被虐杀,小小弟很惶恐。老大表示非常的理解,老大的最后一句台词就是:你慢慢就会适应的。说明老大以前可能也当过小小弟,或者他的干将们也都是从小小弟那样来的。
这说明两个很恐怖的事实,第一个很抽象,就是说其实恶和你的本质无关,不是你说不当恶人就不当恶人的,前面又长又温馨的铺垫就是告诉我们男主角就是个大好人,20岁就肯担负责任组织成一个家庭,还倍爱老婆和他儿子。第二个比较直观,就是说菲律宾的人民们比较倒霉,他们的警察不可能有他妈好人,都是他妈的类似于蓝翔技校培训班的,强奸,杀人,分尸,弃尸包教包会一条龙服务,还提供N多次的实习机会。长此以往,小小弟慢慢变成能把强奸当成AV来欣赏的小弟,小弟逐渐成为强奸杀人分尸三手抓三手都要硬的干将,当然最后也会成为那个看着分崩离析的尸体说上两句笑话“她的身体都皱巴巴的了。”的老大。这是大环境所致的,恶性循环,没好。
其实这片子的暴力镜头不多,跟老美那种一到暴力血腥镜头时就感觉导演贱兮兮的站你耳儿边说着“爽不爽啊哥们,爽不爽啊,哥们?”的那种片子没法比。但曼多萨就能把你拍的坐立难安如坠地狱,这就是大师。
怎么菲律宾出了这么一帮子人,没有人解释,只有片子里的老大扔出了这么一个原因:工资太低。帮菲律宾的警察叔叔们讨薪,应该不是曼多萨的初衷吧。。。。。。。
《基纳瑞》观后感(六):2009年戛纳最佳导演奖
那一年的获奖作品大部分都偏向重口味,评审团主席是我最尊崇的女演员Isabelle Huppert。我敢说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戛纳获奖影片中最黑暗最恐怖的一部作品。然而当时还未公布获奖名单前,影评人给予的分数却排在最末尾。那究竟这位菲律宾导演是凭什么打动评审团成员的呢?
颁奖后,评审团成员发表评语。关于最佳导演的归属,韩国导演李沧东和土耳其导演锡兰(这位也曾获得过最佳导演和评审团大奖)力挺,他(们)说从来没看过这种题材的影片云云。在我看来,这部片很像上世纪80-90年代香港那种“奇闻轶事”类三级片,什么人肉叉烧包、雨夜屠夫、连环色魔……这种玩意早已不新鲜。但这种题材却从来没有人会这样拍。我想这才是曼多萨最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尤其是坐车的那一段,冗长到令人崩溃,却教人心理极度恐惧,而且是不断升级的恐怖。因为还没抵达屠宰场前,观众跟“纯真”的男主角一样,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坐车这一段,电影里的虚构时间变得近乎于现实时间。令观众有一种亲历其境的心惊胆颤。这一长段再加上后来出来买鸭蛋的那场都让我几乎撑不下去,反而是屠杀的那场我上可以接受。
影片倒数第二场,男主角乘出租车中途爆胎下车等待的那段,简直是神来一笔,主题在不经意间加以深化。电影最后一幕,妻子在抱小孩做早饭然后戛然而止。我认为这才是让人觉得最恐怖最胆寒的场景。有谁会想到自己最亲密的爱人晚上做过些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呢?
这是一部讲述人性的电影,当然也在讲述人性的堕落。我想这也许是获得戛纳青睐的最重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