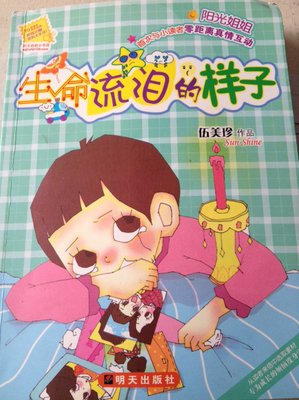《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是一本由[奥]让·埃默里著作,三辉图书/鹭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201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读后感(一):自死的宿命
本书作者让·埃默里在年轻时被送到纳粹集中营,在那里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战争结束被释放后,他以写作为生,1978年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书也是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本书是以一个自杀者的角度,用哲学的方法探讨自杀者逐步走向死亡的过程,其中共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简单来说共情是观察他人的情感时产生的类似的感受,作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一个纳粹集中营的士兵不是因为无法产生共情,而是因为善于想象别人的感受才想出各种折磨人的手段。在痛苦面前,任何语言表达都有局限性,从生理角度来考虑,同样的痛苦由于个人生理结构或是体质不同,产生的痛苦也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说,宁死不屈和屈打成招的人承受的痛苦不一定是相同的,屈打成招的人也不一定是耻辱的。但是否存在于超越与我们生理基础之上的道德意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毕竟没有人能十分确定肉体能承受的极限,也没有人确定最高的道德。 作者提到自杀不同于一般的意外死亡,一个人因为喜爱的歌星去世而自杀,一个人因为忍受不了病魔的侵蚀而自杀,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罔顾这些人自杀背后的心理动机及精神上的因果关系,便不能很好地研究自杀这件事。同时当自杀越被当作一件客观事实来观察,观察者就距离他越远;收集到越多的数据资料与事实真相,观察者距离自死也越遥远。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观点我个人不是十分赞同,例如他说经历治疗之后的这些人不再是他们自己,而变成了其他人。我认为无论何时何地你永远是你自己,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如果每个人都没有权利去更改自己曾经的决定(能改变的前提下),那么这样一成不变,不可改变的人生又有何意义呢? 对于自杀者的所作所为,其实只有那些曾经进入过这种晦暗的人才有资格谈论,而在外面被足够光亮照耀着的人能感受到几分呢?我们应当尊重他的所做所为,不应当否定他们对于生命的参与,特别是不要在他们面前为我们自己描绘一个光辉的形象。让自己彻头彻尾地暴露在别人面前,是件很可悲的事情。所以我们应当放轻姿态,以自由无拘、平静、平常的方式讨论他们。
《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读后感(二):读《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有感
这本书带给我一种黑暗,阴霾,残酷的感觉,当提到战争,人们下意识想到的就是死亡,战乱,流离失所,而集中营一词更是令人不寒而栗,二战中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这些二战中设立的集中营残害了无数的无辜,深恶痛绝,本文的作者让·埃默里便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生于奥斯维辛的他,因发表反对纳粹的言论而被抓至奥斯维辛,地狱般的经历,作者于1978自杀身亡,此书也是作者最后一部作品,书中内容令人感慨万千,更令我们灵魂得以震撼。
不论是美好还是遗憾,这些时至今日我们都难以忘记的瞬间,在后来日益壮大的孤独中被不断打磨淘洗。后来欢乐的记忆更欢乐了,遗憾的事情更遗憾了。记忆变成了我们曾经的成长轨迹,伴随着时光的老去,也为我们编织出需狠狠背负的行囊。 读《直到孤独尽头》让我常有一种浅浅的温暖与淡淡的忧伤交织之感。这里没有什么惊人离奇的故事,也没有什么华丽炫酷的辞藻,有的只是一个小男孩普通平凡中又带着满是孤独感的回忆。那些嵌在记忆中忽然离世的父母、日渐疏远的姐弟、朦胧自负的爱情,让后来的他更加想要努力抓住生活中难能可贵的爱与情。因为变故而陷入回忆,因为回忆不停幻想,因为幻想重回到制造回忆的第一线。这或许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 越是简单的语言和叙事,越是需要真情实感去丰盈,越是需要大巧若拙的掌控力给故事一个好节奏。三十出头的韦尔斯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在记忆中不断长大的男孩,从蜷缩在幻想的龟壳中,到懂得美好记忆要靠自己制造。 书中有很多的遗憾和不完满,可这样的状态就像是照映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真实中混杂着残酷,又充满了希冀和渴望。我们不断与自己争斗,也不停同自己和解,我们不断反抗世界,也不停向世界妥协,我们不断去爱身边的人,也在爱中伤害着他们,我们不断向回忆索取,也不停给予回忆力量。 生活,是一件多么矛盾纠结的事,可生活的动人之处,让我们身陷维谷也在所不惜。纵使生活多么的不易,但我们始终相信生活她是美好的,这份美好是任凭什么时代,什么事都抹杀不去的,也是最真实的,孤独的尽头依然是孤独,但此孤独已非彼孤独,由内而生,向外而长,我们从孤独中学会孤独。
《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读后感(三):译后记
译后记
首先,我要感谢上海三辉图书的编辑给我这次翻译的机会以及对译文的润色,还要感谢我的朋友Sébastien不厌其烦地为我解释作者在文中引用的法语词句。没有你们,我无法顺利地完成本书的翻译。最初会接下这本书,完全是被它的题目“Diskur über Freitod”所吸引。埃默里在此没有使用在德语中常用的“Selbstmord”, 也没有使用英语“Suicide” 同样来自拉丁语词源的“Suizid”,而是选用了“Freitod”一词,它引申自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中“自由之死”(Vom freien Tod)这一章(一译“自愿的死”)。我将这个词译作“自死”,一是作为“自由之死”的缩略写法,同“自杀”、“自戕”这些充满“杀死自己”之罪愆感的词语相对立 ;二是想将把这种行为去污名化,这同样也是作者极力想做的事:自死,是人 类的特权。这“死”也只是千万种“死”中的一种,无异于其他死亡形式,任何想为它贴上“反自然”、“反人性”标签的行为都是不合理的,也是不人道的。
当然,对我来说,翻译埃默里并不是件轻松的事 : 他的文风沉郁迂回,繁冗复杂,尤其是在我看来颇不自然、自问自答式的过渡方式,为他的文字笼上了一层淡淡的“孤独者自白”的光晕。因而我在翻译中尽量采取直译,希望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在写作时内心的激烈交锋与冲突。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我再熟悉不过的自死者重逢:唱尽晨歌却无力渡冬的普拉斯,“ 原谅了每一个人,也请所有人原谅我”的帕维泽,早已将肉身沉于集中营里的策兰,“世上人间厌凋零,晚风催花率先落”,以武士之姿谏世的三岛由纪夫,堕于哈伦湖的沉默者宋迪,又或是查特顿、克莱斯特、魏宁格, 最后,还有在旅馆中服下安眠药溺于永眠之海的埃默里本人。这些选择了把他们“至高空幻的货物”付之丙丁的自死者,以其最终的虚无否定了存在的行为,是否才是他们(曾)存在的“至高空幻”呢?诚如作者所说, 虚无的原理远比希望的原理更加有力。
行过死荫的幽谷,穿过亡者安息之地,遥远溪谷发出声响,星辰寥落,月蓝凉而冷寂。想及苦恼众生,拔苦与乐,奋不顾身。我虽爱极逝亡之温柔,但愿寂灭之外, 我们能拥有更多。
2016 年 4 月 6 日 于布伦瑞克
《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读后感(四):日暮时燃烧咆哮
我在,死亡就不在,死亡在,我就不在,'我’ 不可能做‘死亡’的主语...书中提到一些关于虚无的描述都很有意思,一些存在确实是很难以用逻辑语言来表达。
这本书探讨了关于Sui caedere,杀死自己,译者翻译是'自死' ,(我个人比较喜欢'自放' 可惜。)自知自愿的自杀。这种行为又分成两类:有计划的,周详的死亡,或者一时兴起(一时兴起尝试死亡,真是奇怪)。
自杀的念头,作为该行为的伊始,只是在精神上代表了自杀行为,在研究自杀行为的时候,理论上应将其排除在外。但若认定该念头与行为无关,却又能够从中不经意地探查到出于本能效应的冲动——一种带来死亡的意愿,这却又和真正实施自杀时如出一辙。如果在建造自己的宫殿时经常碰壁,伤痕累累,但工程还在继续,那其间每一个挫折时刻都是在为了跃出做准备,直至最后的'一根稻草' 终于开启了跃出,这是理智型自杀;在突如其来的外界压力下,产生的跃出行为是冲动型自杀。
埃默里似乎是反驳了一些自杀学出版物的理论,我想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毕竟有些领域是需要进入经历才能谈论的。语言本就不能完全客观描述主观感受,何况又隔了一层。
对于提到的女仆、帕韦泽、策兰在被救回后,接受了成功的治疗之后,成为了别的人,这个我想是相对于曾经那个拥有自死想法的'自己' ,那个时候的他们定然不是站在'人最终还是要活着的'这边的。
在关于理智型自杀描述中,作者描述平和表象漏掉的应该有内心描述吧,但因为没有尝试过,(尝试过的人也不可能再次描述出来),或许真的在寻求一派祥和,因为一切都已经接近尘埃落定?;又或许是进行了一番斗争的,可惜内心的存在超脱语言范围。
第二部分提到的'死亡和其自然',关于自然的描述很有意思,或许更接近于一种量化来的习以为常 ?
对于这个通过日常语言来向我们传达意义的世界来说,在最初的震惊渐渐褪却之后,经过长时间沉默的疗伤与适应,所有的死亡最终都是'正常'与‘自然'的。一件事情,第一次闯入大众的眼中,会因为新鲜度保持话题,但重复出现的次数多了,渐渐的也就不足为奇,想起了很久之前看到的关于年轻人猝死新闻,当时看到很震撼,如今再看,竟然有了一种过度劳累猝死也是正常的想法。所有的这些不自然,在经历了开始的感叹或者抵制之后,都会变成'正常'。活到百岁,日暮迟迟中老去是死亡;刚刚呼吸到第一口氧气就终止,是死亡;正是绽放时却永远保持这个姿态,是死亡。
一定意义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纯粹的属于自己了,既然结局都一样,正式自死这种少数人的选择有何不可。
(很可惜没能在刚看这本书时就记录下来一些想法,现在记录总觉得错过了好多,逻辑也并没有很清楚。)
《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读后感(五):理解是为了尊重
(《退稿信》(美—安德烈·伯纳德)一书中提到一位作家:
“美国小说家约翰·图尔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图尔以获得普利策奖的关于新奥尔良生活的滑稽小说《笨蛋的联盟》闻名,但他生前并没有看到自己的这部作品出版。事实上,在《笨蛋的联盟》残酷地遭到各出版社退稿之后,图尔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他的母亲仍然不愿意放弃,于是她又把稿子寄出去,结果又被退回来——退稿事件就这样一再上演。最后,作家沃克珀西( Walker Rercy)出面赞助她,这本小说才得以出版。”这一篇的题目就是《因退稿而自杀的小说家》。
如果用埃默里在《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中提到的观点来分析,约翰·图尔的自杀就可能是“冲动型自杀”。也就是“想要在突如其来的外界压力下,把自己驱逐出这个不堪忍受的外部世界”。退稿是诱因,也是“突如其来的外界压力”,就象下图一样。(图片来源见图上标注)
可这种猜想是对的吗?其实这种猜想就象埃默里说的“他们懂些什么?能从外部世界观察到的都不值一提”。
“那个谷物商自杀了?简直不可理喻!他本可以在吃完官司坐完牢之后,再于能委以重任的专业人士处尽可能地接受咨询,并以一个普通职员的身份继续活下去,他甚至可能东山再起。在任何情况下,他这种不理智的行为都本该受到监控,就因为他是且我们都是一名有用的社会成员。与此相反,主体却坚持维护他的权利。他根本不愿意把自己置入失败的生活中。它向社会,也同样常常向那些把他的自死说得很不堪的亲属(说什么人又不是为了死而活着的云云)发出嘘声。死亡最后一次肯定了他的尊严一而随后洪暴来临。”(埃默里在此处是引用让·巴什勒尔的著作《自杀》,埃默里称此书“也为我提供了完全崭新而客观的学术视角”)
谈约翰·图尔的事并不是消遣谈资,而是试图去理解埃默里在本书中的思想。其实埃默里在书中想表达的很简单,“怀自杀意愿者的处境很糟,而自杀者的处境则更为恶劣。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应当否定他们对于生命的参与,特别是不要在他们面前为我们自己描画一个光辉的形象。让自己彻头彻尾的暴露在别人面前,是件很可悲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应放松姿态,以自由、无拘、平静、平常的方式谈论他们。”
那么,就试着做到理解吧,就象杨小刚在代序中提出的“理解是为了尊重,即便总是存在理解的不可能,但做出理解的尝试已是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