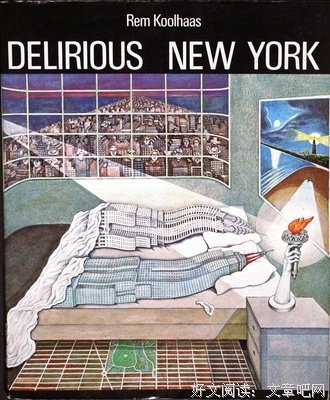《伫立在疯狂里》是一本由帕特里克·勒穆瓦纳著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3.00元,页数:14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伫立在疯狂里》读后感(一):一份手记,一部史——从《伫立在疯狂里》看病患处遇的变迁和精神病学史
正如本书作者所言,他“对世上所有的事几乎都公开发表过看法,谈过厌食模特、顽固性失眠、安慰剂,谈过烦恼、诱惑、滥用药物、夫妻口角是如何产生的,还谈过笑和眼泪,”在法国里昂卢米埃尔诊所(Clinique Lyon-Lumière)工作的帕特里克•勒穆瓦纳(Patrick Lemoine)是位知名的精神科医师,以他的学识和经历,谈论上述议题自然是信手拈来。不过,这本书和他过去的出版品,包括已在大陆出版的《爱如何降临》和《眼泪的性别》等专题书籍相较而言,视野更广,表面上本书是对其从医生涯中所遇种种的回顾和反思,但读完全书,其中的一条暗线——一部病患处遇变迁和精神病学史——也就彰明了。其实,关于这条暗线,他在书中早有交代,“我觉得精神科医生的作用是,让人们不要忘记西方曾经是怎么治疗精神病的”。
精神疾病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一样长。自古以来,能够留下的关于精神病患的记载,几乎全部由非精神病患完成,他们是旁观者,而作为被观照对象的一小撮精神病患则被视为邪魔附体、神譴天罚的结果。而朴素的古医学则秉持了自然主义视角看待精神病患,如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失衡致疯学说,但这些想法在中世纪宗教神权思想控制下逐渐式微,精神病患的命运依旧命途多舛,污名化现象更甚。
17世纪,受笛卡尔身心二元论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渐抛弃恶魔致疯的观点,而将疯狂归因于躯体或大脑问题;随后,英国人洛克将“妄想”视为错误教育所致的意念错误联接之结果,此观点隐含着“疯人也能通过再训练重获正确思考的能力“的思想。
这些思潮一直持续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医生飞利浦•皮内(Philippe Pinel)在其所辖医院推行”道德疗法“,并将精神病人从镣铐中解放出来,这是精神病患在法国首次沐浴到人道主义之光。在某种意义上,自法国诞生的”道德疗法“也可视作日后以巴甫洛夫和斯金纳等人为代表的行为学派之最早源流。
19世纪后,精神医学努力使自身成为一门科学,精神医学重镇也从英、法逐渐转向德、美。在德国,精神疾病起源于神经与脑部异常的观点盛行,威廉•葛利辛格(Wilhelm Griesinger)医师更是主张将精神科和神经科结合成为神经精神科,此举对后世影响极深。这也是为何作者在书中提及1968 年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正式分家时使用“阵痛”一词的原因,此后神经科医生司职硬件(神经)修理,而精神科医师专事软件(精神)改写。
进入20世纪,精神分析、行为治疗、认知治疗等心理疗法的风头盖过精神医学,而精神病学自身也因受到二战纳粹利用精神科医师迫犹太害精神病患,以及战后媒体对精神病院种种丑闻的曝光,使公众有了精神科依旧停留在黑暗时代的负面印象。其实,50年代对精神病学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氯丙嗪、异丙异烟肼和锂盐等一大批具有抗精神病作用的物质戏剧性得被发现。只不过,也正是由于精神医学的重大突破,而使精神病患而再次落入被处置对象的非人道境地。与1960, 70年代西方反权威的氛围契合的是,精神病学领域兴起了“反精神医学“和“去机构化”运动,前者认为精神病根本不存在,它不过是社会构建的产物,后者则倡导改革对待精神病患的方式,即把拘禁患者变为小区照料加门诊治疗。来自哪个时代的问题,“精神医学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保卫生命还是社会控制?是治疗还是惩罚?”在今天的很多地方依然是问题,比如作者所在的法国。
在法国,精神科医师拥有决断病患自由的权力,传统上精神病患又被公众被视为社会秩序的游离或破坏分子。所以,精神科医师很容易无意间就充当了建制的“协警”,虽然其他医学学科中也存在医患权力失衡问题,但因精神病患身份更“卑微”,其中的医患权力落差也显得更突出。作为一名接受过5月风暴洗礼的男人,一位秉承老师教导的“精神科医生必须是个刺儿头,敢于特立独行“的医师,勒穆瓦纳在书中对法国医疗制度多有抨击,而对精神病患所遭受的种种则抱有深厚同情,“我认为,精神科医生应当让民众和相关负责人看到精神病人所遭受的不公。所以,我觉得精神科医生有时候也要充当一下工会领袖。”
勒穆瓦纳首先是个医者,他在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之中更偏向生物取向并不奇怪,毕竟他一入行就经历了抗精神病药物大发现,也见证了近年来脑科学的快速发展。不过,突破对于某行业的从业者而言并非总是好事,一如作者幽默的说,“如果有天发现了抗精神病疫苗或药物,那么全世界的精神病院都只能关门大吉,成千上万的精神病院员工只好下岗。这就像是发现了抗结核病链霉素以后的肺结核医生和肺结核疗养院一样。精神病和精神病治疗者一起出局!”
在勒穆瓦纳看来,”每个人身上都藏着疯狂的种子,而每个疯子身上都有一部分理智。“他们”跟我们之间存在着通道和桥梁。我们对这些生病的同类,最缺乏的就是尊重和同情。“不论,作为读者的你是否赞同其观点,都必须面对现实境遇是,当前的精神病学有把”每一件事情都精神医学化“的倾向:20世纪中叶,西方世界的各种精神病,无论种类或发生率都成长速度惊人;例如,第1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约100页,第2版为134页,第3版近500页,第4版则暴增至934页,2013年第5版将会公布……精神疾病种类越来越多,势必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患上精神疾病……。所以,近10年来,乃至未来,你会有精神疾病正向你款款走来的感觉。
既然绕不过现实,也逃不出历史惯性,倒不如索性豁达起来,从这本书走进去,你会发现这个你原来从不会进入的处所,一如其他你没去过的地方一样,精神病患、精神疾患甚至精神病院也是具体的、有重量的、有故事的、有情感的,有人味儿的。
这,便是了解精神疾病和病患的第一步。
书里写,精神病医生,是医治所有痛苦的心灵。
那个因为一缸金鱼而种下精神病医生念头的小人儿,长大了就变成傲娇卖萌的作者,生动也有趣。
”当精神科医生,就得学会做西西弗斯,把石头推到山顶,明知道还会滚下山去,也要一次又一次往上推,推到哪一天呢?没人知道。“P60
”雇员被迫适应企业,而不是企业适应雇员。很少有企业会在雇人的时候,就确定未来员工的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需求,让员工可以根据喜好、自选工作时段、开放式或封闭式办公室。 掌握工作环境的感觉才让员工更舒服。“P69
”精神病人就是单纯运用一种防御机制的人,而正常人则适时运用各种防御机制。“P140
《伫立在疯狂里》读后感(三):谁更疯狂
第一次深刻感受到精神病人这个群体是在几年之前的《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被书中描绘的精神病人的瑰丽的精神世界所吸引,进而对这个群体开始慢慢关注。
说句大实话,人们在物质生活里对精神病患的感情很复杂。冷漠、遗弃、厌恶、同情、害怕,甚至恐惧,因为有些病患可能存在暴力倾向。即使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往往因为这个病理特征的复杂性而感情疏远。的确,人们在面对未知的事物时,往往竖起全身的刺,进入备战状态,自保是最直接的反应。不少新闻爆料的情况都是:丈夫或妻子被另一方送进精神病院。开始总觉得此类事实过于冷酷,疯狂的人不知是哪个,后来开始思索:精神疾病的源头到底是什么?医师是如何排查精神病患的?又以怎样的标准来证明患者已经痊愈可以回归人群?
《Fingersmith》里纯真善良的苏因绅士和莫德的诡计迫害而进了疯人院,此时,谁疯谁不疯已分不清楚。财富的诱惑和人性的善恶交织在一起,谁疯了呢?或者说,谁更疯狂呢?
《伫立在疯狂里》真实展现了精神病患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生活状态,作者以仁爱慈悲,从人道主义出发,关注精神病患的人权,致力于提高精神病患的生活水平和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治疗的认识。病例小故事广泛反映了精神疾病的状态,译文流畅生动,颇具幽默,值得一读!
《伫立在疯狂里》读后感(四):疯狂的轻盈
据说,人类已经进入了科学昌明的理性王国。欧洲中世纪里焚烧巫婆的火刑架和囚禁疯子的坚固堡垒,如今都成为历史书上精美的插图;中国历史上,从汉武帝的戾太子到康熙帝的废太子,历朝宫廷中屡见不鲜的“厌胜”“魇镇”之术,如今也只是小说中的一段惊险情节。这些曾在东西方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疯狂”事件,在现代人看来可谓“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了。但是,现代人是用何种方式来认知和理解疯子及其疯狂的行为呢?读完法国久负盛名的精神科医生帕特里克•勒穆瓦纳所写的《伫立在疯狂里——一个精神科医生的手记》这本书后,我发现正如人们通常会片面的使用“精神分裂症”来指代所有的精神病类型(精神分裂只是精神病之一种),公共领域对精神病学的看法也存在着巨大而深刻的分裂。
这种分裂正是当代人对精神病学认知的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在大众传播语境下人们对精神病人、疯子的好奇与围观。这一猎奇心态在中国当代尤为突出,书籍、报刊、电视以及网站时常会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来讲述一个疯子的故事。他们有的被家人用铁链锁起来,像狗一样吃食;有的冲上街头做出诸如裸奔、穿奇装异服等离奇的行为;有些女性精神病人甚至还会遭遇性侵犯。大众在围观疯子的时候,固然也不无同情,但也仅仅止于同情而已,几乎不会去想方设法救助他们,更不会检讨自己这种猎奇的心态是否恰当。是的,精神病人的确是人类社群生活中的异类,于是他们的“怪异”行为自然而然成为普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果说这一种倾向更多的存在于普罗大众之中,那么,对一些所谓的智识阶层而言则存在着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极端倾向。我们不妨从法国的福柯说起。福柯写于1960年的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疯狂史》追溯了欧洲历史上疯子及其历史的递变。福柯说:“中世纪期间,疯狂被定位为一种恶德。”疯狂的力量已不局限于宗教,而是一种普遍的坏的德行。因此,欧洲的教权与王权则通过“规诫与惩罚”来限制疯子的行为,特别是通过关禁闭、建造疯人院的方式来将疯子与其他人隔离。在福柯看来,疯人破坏了人的群体性。一个普通的人类群体,不论是家庭还是工作单位,都具有相对一致的行为特征和稳定的规范,而疯子以其自身的行为破坏了群体的稳定性,会破坏其他人对集体的归属感。因此,人类会利用群体的权力将疯子监禁隔离,从而维护自身群体的稳定性。福柯认为,这是一种超出疾病与治疗之外的权力话语,用权力给一些“另类”的人打上“疯子”“精神病”的烙印,从而维系一个群体的平庸及其正常运转。因此,在福柯看来,这一权力话语是非人道的。
在福柯及其理论的影响下,很多欧美的知识界和文艺界人士用自己的方式重述了福柯的理论。譬如由尼克尔森主演的电影《飞越疯人院》就是一例,片中的精神病院不是医院而是监狱,医生也不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而是手握权力的统治者。疯子们则被刻画为并没有疯癫而只是“不合群”的异类。这样,原本是基于“生病——治疗”的行为被人文学者的阐释成了“反抗——镇压”的政治话语。在《手记》一书中,帕特里克也描述了这一思潮对医学界的冲击,那就是伴随着法国“五月革命”兴起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帕特里克概括了这一运动的观点:“他们认为精神病学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医学的一个分支,精神病治疗是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专制工具。”(p65)这种观点对近几十年来的医学、心理学以及人文学科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正面来看,精神病医学中的“权力理论”对疯人院中的权力结构进行了批判,对医生不尊重病人的行为进行了反拨,从而对给予精神病人以人格尊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负面意义在于,这一运动将精神病学看做是维护统治的政治工具,已经剧烈的侵犯了医学的边界,对医治病人也起到了反作用。有些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罹患精神病的患者不仅不是病人,而是罕见的具有异秉的哲学家、艺术家,他们举出一长串疯子光辉的名字:诗人荷尔德林、哲人尼采、诗人顾城等。美国著名的精神病院麦克连疗养院因为收纳了一群哈佛毕业生,而拥有一个“哈佛俱乐部”,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纳什、普利策奖获得者罗伯特•洛威尔都住在里面。于是,有些人甚至鼓励他们的疯癫,却丝毫不考虑病人及其家人的痛苦。这就在争取精神病人的权利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呈现出另一种倾向了。
显然,历史上这两种倾向都有一定的偏颇。帕特里克在《手记》中的所写所感,正是对这两种倾向的“祛魅”。《手记》是一本典型的专业人士写的通俗读物,它不是福柯所著《古典时代疯狂史》这类文化与哲学的精深阐释,也不是大众传媒对精神病人各种行为的窥视猎奇,亦非摄影机镜头里对“天才疯子”的浪漫主义想象,当然更不是枯燥的医学和心理学教条。《手记》里,帕特里克医生用严肃而不失幽默的笔触和大量引人入胜的故事,为精神病学祛除了各种误解与想象,还原了这一医学学科的理性本质。帕特里克指出,“灵魂可以从身体里剥离出来,是一种器官,也会生病,需要治疗,所以需要持证的专业人员。”(p1)“精神病人就是单纯运用一种防御机制的人,而正常人则适时运用各种防御机制。”(p140)换言之,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遭遇到问题,但精神病人不能采取多种方式对其进行有效排解,除此之外,他们与我们没有区别。而这种功能的丧失,也完全可以通过现代医学来诊疗、抑制,甚至治愈。精神病学再特殊,也是医学之一种,也是和感冒发烧、器官病变一样的病症而已。不论是医生还是大众,既不应该把精神病人看做是特殊的奇怪的异类,也不必将他们看做受压迫的高智商人士。
《手记》里,既有作者没能治愈病人的遗憾,也有他锲而不舍救治病人的喜悦。读者仍然可以带着猎奇的目光去阅读,但一定会被他那种温情和关怀深深打动。而这些,才是我们每个人最应该珍视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