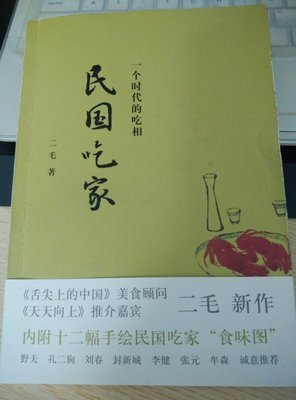《1933,聆听民国》是一本由林语堂 / 梁漱溟 / 胡适 / 柳亚子 / 徐悲鸿 / 郑振铎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为一个85后,一直以来民国在我的心中是一个盛产“大师”的时代,那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时文人才子辈出,那时中西方文化剧烈碰撞和融合,于是有了“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有了国学功底深厚、才气磅礴、议论恢弘的钱穆先生,有了学博中西的“清末怪杰”辜鸿铭,有了捍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有了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沈从文……身处功利浮躁的当下社会,看到那些“房奴”“车奴”“移民族”“富二代”“学术造假者”,很多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总是不断地陷入悲观和失望。可是,我竟然忽略了民国也是一个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战火纷飞、食不果腹的时代,那些大师是产生于文化碰撞和政治动荡的夹缝中的,那时候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是处于富足幸福生活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1932年,中国东三省沦陷,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第四次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利益”……国人陷入激愤悲观之中。上海《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次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向全国各界人士发出征稿函约400份。最终140余位国人发表了244个“梦想”,其中包括林语堂、胡适、柳亚子、徐悲鸿、巴金、顾颉刚、夏丏尊等大批名流。时隔八十年,《1933,聆听民国》这本书帮助我重现了彼时的社会环境和跨越时代的“中国梦”。
林语堂说:我不做梦,希望国中有数座百万基金堪称学府的大学,我只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自办的成样的大学,子弟不进洋鬼学校而又地方念书。我不做梦,希望建设全国道路,只希望我能做帆船回去我十八年不曾回去的家乡。
叶圣陶说: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描写起来只须简单的几条线条,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岂止是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不应该这样吗?中国地方什么时候会涌现这一幅图画呢?恐怕很遥远吧,遥远到不能“梦想”吧。
巴金说:我个人的生活里不敢有什么梦想,黑暗的现实把握的梦景全都摧毁了。在这一片血泪的海上,我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建造我理想中的美丽天堂。在这时候我只能够有一点小小的希望,这希望也许就是不能实现的梦想吧。我的希望是什么?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
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民国的先辈将他们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梦想中的个人生活陈述给我们,读着读着我不禁潸然泪下,民国的大师们是孕育于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当中,乃至于梦到百姓衣食无忧都是一种奢侈。然而八十年多年后的今天,无数仁人志士和勤勉奋进的先辈们居然就这样将独立富强的中国、百姓衣食无忧的中国由梦想变为了现实。这样沧海桑田的巨变都发生了,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当一个无力者和悲观者呢?
《1933,聆听民国》里的场景其实只是这个巨变里的冰山一角,我们的先辈们筚路蓝缕,皓首穷经,于是,薪火得以相传。八十年前的梦想如今看来似乎就和我们能够呼吸到空气一样自然,但是八十年前却几乎没有人敢断定这个梦想能够实现。今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大胆地做梦呢?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践行呢?
“中国梦、我的梦”是一个能带给人太多期望和力量的话题,梦想是我们对生活的憧憬,梦想是我们对应然之事的认同和许诺,梦想是我们对社会的期待。所以我期待我们的学校能够培养更多的独具灵魂和人格的大师,而不是生产流水线的产品;我期待我们的政府可以更好地调控房地产市场,而不是催生更多的“房奴”“蚁族”;我期待我们的医院能够更好的为贫困人群服务,而不是冷漠的“先交钱后手术”;我期待我们可以见到更多的蓝天碧水,而不是生活在雾霾笼罩的城市;我期待我们的孩子可以喝上放心的奶粉、吃上放心的食物、喝上放心的水,而不用担心食品安全;我期待我们的城市规划可以更加合理,内涝、堵车、景区拥堵可以不再出现;我期待我们有更多的中型城市出现,年轻人不必纠结于“逃离家乡还是逃离北上广”;我期待更多的人去关注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我期待……
这注定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与我拥有一样期待的我们依旧任重道远。所以我们不能止步于抱怨,我们理应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梦想让我们一起前行,就像一束光簇拥着另一束光,点亮自己,然后照亮别人。我们去探索,去关注,去呼吁,去参与,终有一天,我们的这些期待和梦想也会如空气那样自如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二):梦醒何时?
在“中国梦”这个词一再被提及的当下,回望1933年的梦想专题,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932年年底,上海《东方杂志》征集“新年的梦想”,“梦”的主题包括两方面: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的?个人生活中的梦想?此次征“梦”活动最终收到140多位国人发表的244个梦想,《1933,聆听民国》正是此次征文活动的合集。
244个“梦”,回复者中有官员、编辑、教师、作家、实业家、学生等等,可以说代表着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想。反观当时的社会现实,物质匮乏,国人大多挨饿受冻,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大部分人的梦想是解除物质痛苦。另一个方面,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梦想着有一个理想的世界,有一个新中国。个人生活梦想则不尽相同,但大家普遍希望生活安定,而这确实要建立在强大的国家基础之上的。
如果现在有本杂志征集同样一则过于“梦想”的文章,分类取样地征集,最后做定量分析,再与1933年的梦想作比较,想来会有很多有趣的发现。
既然还没有杂志做这件事情,在此不妨让我们先大胆假设一番。首先收到的回复一定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随着教育的普及,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也有夙愿畅谈自己的梦想,对公共领域的建设也更有发表意见的诉求。随着物质层面的极大丰富,对国家的梦想一定不在局限于物质条件的改善,在精神层面的梦想会展现地更多。而个人生活梦想方面,差异化多样化的梦想一定层出不穷。
与1933年比较,参与度的提高、对国家梦想的转变以及个人梦想的参差不齐,是当下这个时代的特色。与《1933,聆听民国》中知识分子的梦想对照,无疑具有很大的区别。从这个层面上讲,《1933,聆听民国》是一个时代的标签。
在举国畅谈“中国梦,我的梦”的当下,读《1933,聆听民国》仍然能让今日之我们热血沸腾。随意翻开,看林语堂的国家之梦——“我不做梦,希望民治能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迹。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对照当下,有些梦已成为现实,有些梦仍旧是梦,不知道,这该是我们这代人的幸或不幸呢?
“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读毕《1933,聆听民国》,笔者也有一个梦,希望书中所陈之梦早日一一实现。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三):文不成章,仅能感悟一些情怀了。
收编这样一本书无疑是用心良苦的。民国以及梦想中的国家和生活都是文学中长久不衰的话题。开篇林语堂洋洋洒洒地是十多句“我不做梦”就看得人沉闷起来。字字句句都是如此卑微简单的“只希望”。马上即刻把人带到了那个1933的民族外忧内患地环境中。
再往下翻,会发现每个人的梦想平凡如斯。
叶圣陶: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
洪业:全国的人,都有饭可食,有衣可穿,有屋可住,有人可爱。
朱自清:像一个早晨,大家浴在新的太阳里。新生活一点一滴从一手一足里造出来,谁都有份儿。
这样的梦称之为梦,不禁让生活在新世纪的人仍然心有戚戚。然而再细想,这样平凡的梦如今真的都实现了吗?看看那些《变形记》里的那些孩子,你会发现,世界大同,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大概永远都是个梦吧。
然而我特别赞同的几段话:
一是郑振铎说的:我并没有什么梦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做“梦想”的。人类的生活是沿了必然的定律走去的。因了我们的努力,我们将会把若干年帝国主义者们所给予我们的创痕与血迹,洗涤得干干净净。……这并不是梦想,我们努力,便没有什么不会实现的。
二是刘英士所说:未来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的梦想,而决定于我们的行为。
我们确实通过我们的努力,一步一步更接近我们的梦想了不是吗?好像是给几十年之后的自己写信一般,看到梦想其实还是实现了大半的安慰。国家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已经让教育普及,而不是被少数人独占,我们也成为了霸权主义国家也忌惮三分的大国不是吗。
虽然知道编辑这样一本书非常不易,能够一口气看到很多名家的文章也是难得,但是这本书的硬伤是每个节选都没头没尾,很难让人系统地阅读出什么,文章是碎的,所读感悟自然也难以成气候。这样的编排还是很有问题。或许当时可以做时事新闻来读,而今已经缺乏了背景以及那种心情。
脱离国家的梦想,说个人生活的梦想后半部分,还是比较有共鸣的。哪一个都可以都拿来直接充作自己的梦想。
巴金说希望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该做的事。
这个真的是很难呢。尤其是像我这种公务员……我就不提我在单位写的文章我自己都不想多看了。
冰心说我每天工作,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里,我努力研究我的文学教育。
还有非常有趣的胡适说希望有个理想的牢狱,不许见客,只有周日可会见家属,但是可以读书,可以有纸墨笔砚,每天可以做八小时的读书著述工作,每天还有人监督他做一点钟的体操。他说这样可以把他能做的工作全部做完,岂不快哉。
这个梦想真的很推荐拖延症患者尝试呢。我们或许可以建造这样一个牢狱呢。
哈,还有个打酱油的说,我……梦想卖东西的不讨虚价。哈哈哈哈。一看是个艺术学院的教授,无怪乎提出这么“苛刻”又可爱的要求了。
而且有好几个人都实实在在地说了,我没有梦想。竟然也都收录其中。感觉……这些文人实在是可爱执拗得很。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四):你幸福吗
读了一阵有些疑惑:印如此一本书,难道就是为了沾沾时下极热的“中国梦”话题的光?
全书内容出自1932年《东方杂志》设计的一场问答活动,问题有两个: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80年后罗列一份过时文献有何意义?
然而顺着读下来,看到用来做噱头的许多熟悉名字,许多截然不同却兴致勃勃的答复,感觉有了些兴趣——要知道那是个国土沦陷前程未卜的特殊时期,居然有这么多人认真“说梦”,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今日,虽天下昌平,但精神和信仰层面的全局性缴械已经难以忽视,于是“梦”的主题又被抛出,似非偶然。
组织者在《记者的读后感》一文中对书中几百条说梦的小文作了详细的分类统计,又顺着“有些评论家”的路子把它们分成“载道”和“言志”两类,却似乎并未达到预设的目的,说不出振聋发聩的道理来。
事实上从说梦的内容看来,难以生发出规律性,政府高官和文人教授不一定振振有辞,大头百姓不一定朴素苟且,“梦”这个主题的多义性决定了阐发结果的无序性——最可笑的有不少直接大骂此主题“危险”的,组织者大度保留后表示不接受,估计被改掉或弃掉的骂题文应该更多。当然这组织者毕竟只是民间杂志,若这梦为官方所征,想必这些话一句也留不得。
一是“预言型”如朱自清:“一面想写些诗文给中学生看看。将来也许陪人掉在火里。”一语成谶。
二是“清醒型”如名不见经传的海关职员慕洁,直接希望中国的一切税收机关都交给外国专家,由此财政收益可增加二十倍,而有了钱便有了权和统领军阀的希望,到时拿回税收机关的行令权可谓易如反掌。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想起旧海关在屈辱的被侵略史上扮演的角色,也不得不感叹财政积弊之深居然可从根子上摧毁帝国基业。而此君的个人之梦中说到公务人员只有升级一个梦可做,且妻不云乎:“放掉这件工作,哪里就有几百元一月的工作等着你?”想起前日单位同事毅然辞职下海,众人羡慕嫉妒之余却个个带着幸灾乐祸欲观后效的神色,惊觉职业之梦积怨之深重。
三是“实际型”如顾颉刚,只希望能安定研究,远离纠缠,不生大病,解决自己研究中的问题。这才是最安全也最实际的梦。然而这还算是梦吗?
全书最有趣之处当属后附的《听说梦》一文,早就在鲁迅全集中的《南腔北调集》中见过,却未有如此特别的感受。此文因提到了梦“无阶级社会”者、梦“大同世界”者而被讨论甚多。在读罢作为此文缘起的征文们后再看,不禁发噱,原来这完全是篇目的明确的吐槽文:先是对说梦一事直接讥讽,再爆料许多稿子已经被篡改至面目全非,然后对前面提到的组织者“言志”“载道”之说大加鞭挞,并且直指最该一说的弗洛伊德,力度远非记者可比。
究其根由,恐怕是因为提出“载道”“言志”这一文学分类法并被此次活动的组织者津津乐道的“有些评论家”原来是反目已久的苦雨斋主吧。
然而书中周作人只是引了自己作品中的一段:“信仰与梦,恋爱与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能够相信宗教或主义,能够做梦乃是不可多得的幸福的性质,不是人人所能获得。”
若是脱离字面意思想来,这倒是“主义”与“做梦”拼命要扯上关系的靠谱解析之一,它们都想让人脱离了独立思想,转而重视“你幸福吗”的伪命题。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五):梦想还未实现,我辈仍需努力
《1933年,聆听民国》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
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觉得编辑的思路很独特。在“中国梦”的呼声越来越高的当下,每个人的思维都有了无限扩展的可能。这个时候出一本80多年前的140多个人的关于国家和个人梦想的书,真是既应景又有意义的一件事。
其次,我觉得看80多年前的人,尤其是那些不知道在脑海中想过多少次的人的梦想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有些人在我们心目中原本是很高大上的,可是,现在看看他们那些单纯美好的梦想,竟然是那么接地气,有些竟然有着顽皮的负气。比如,我看著名喜剧家洪深的梦想是:“年龄又增了一岁,在这一年找那个,那些妨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人,当然也得老一岁,或者会多死去几个。这真所谓是“梦想”了”。有些则是很有玩味的,如国立艺术学院教授孙福熙的梦想竟然是:“我……我梦想卖东西的不讨虚价”。这真真是可爱至极的教授的想法。但即使这个很简单的想法,到现在竟然也没能实现。真真是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惭愧至极。
1933年正是国弱民穷的时候,用烂俗的一句话说: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时候《东方杂志》来征集人们的梦想,实在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不仅征集梦想需要勇气,写梦想的人也需要勇气。现在政府虽然提倡“中国梦,我的梦”,可是,有多少梦能变成现实呢?
那些梦虽然多姿多彩,但其实总结下来不论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无非就是国家富裕,人民幸福,“一切的一切都是光明的”。像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的“最好扶桑三国能为中国之一联邦或一联省,以永久消灭东亚祸乱之根”,的梦想就看得让人暗爽;外交部长罗文干的“能戒酒,能涵养,无疾病,勿懒惰,一直到死的一天,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倒是家国的梦想都有了。
这些梦想里,有些已经实现了,比如一个叫竹友的读者五个梦想中,有一个造几间暖室,可以一年到头吃到西瓜、葡萄,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出书啥的也不是问题了,现在甚至有点矫枉过正,任何人只要出钱,出版社就敢出书。“固定职业,固定住所,固定收入”有一部分人也已经实现了。
但貌似,有些梦想永远都实现不了,比如贪官污吏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的问题,比如中国教育的问题,比如……,这样一对比,天哪,原来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实现的空间啊!
忽然想起春晚上黄渤唱的那首《我的要求不算高》:80平米的小窝,还有个温柔的好老婆,孩子能顺利上大学,毕业就有好工作,每日上下班很畅通,没有早晚交通高峰,日日去户外做运动,看蔚蓝的日空,我能挣钱, 我还有时间,去巴黎、纽约 、阿尔卑斯山,我逛商场, 我滑雪山,这样的日子好悠闲,人们的关系很友善,陌生人点头全是笑脸,养老生病不差钱,有政府来买单。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它很小也很普通,我不求变成龙和风,我只想活在幸福中——
这样看来,80年前的梦和现在的梦也没啥区别。
前人的梦想还未完全实现,我辈仍需努力!为了梦想,我们一起做个勤劳的小蜜蜂吧!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六):织梦者 ——《1933,聆听民国》,TA们曾有梦
织梦者
——《1933,聆听民国》,TA们曾有梦
对于每一个学生仔来说,“中国梦”这个词语已经变成了一个头痛而又泛滥的名词。文科生尤甚:政治用上了,思想品德上也在讨论,语文作文更加不用说,材料换了千百遍,题目核心永不变……承认“中国梦”对于一个正在陷入迷茫的社会来说的警醒作用是一回事,而天天反复repeat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1933年的文化界,只属于知识分子而并非普通百姓的底盘,“中国梦”是一个崭新而极为迫切的概念。140多个文化人的244个“梦”,是那个处于存亡时刻的黎明前黑暗中的寻路的梦想。
他们是织梦者,在编织一个属于国家的未来。
关于这个国家的制度、这个国家的教育、这个国家的运行方式、这个国家所缺乏的正义、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忧患——他们活在那个“当下”,又将这个“当下”反映到他们的“梦想”中去。他们中的一些人做的梦正在实现,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本身也成为了一个传奇:林语堂、叶圣陶、俞平伯、郁达夫……这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与他们的梦想一起书写在中国历史的纸页上。
然而纵观本书,存亡时刻的中国文人们,关心的是如何用民主、文化、教育在保卫这个国家,他们埋头苦干,在个人梦想中,也不惮于抨击这黑暗的社会。然而我们却没见到这样的梦想:梦想着改变世界,梦想着改变人们的生活,甚至没有见到努力研究让粮食产量更高以避免贸易顺差的影响、或者制作强大的武器让海军力量更强保卫国土,也没有见到一个类似《海底两万里》一样关于科学、关于人类的未来、关于我们未知的世界的设想……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中国,人们讨论的是拿来的文化、拿来的技术,他们在讨论一个大的未来,却没有见到一个大学生、一个实在的职员,一个正在工作的教育者,自己正在研究新的科技、学术来改变世界;也许这就是不可不说的遗憾。
“未来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的‘梦想’,而决定于我们的行为。”编译馆的刘英士这样说。
“每一个人做他能够做的工作,每一个人享他应该享的幸福。”《大晚报》的记者邵冢寒这样说。
在本书记载的梦想中,也有这样颇具实践意义的话。面对今天,我们不用再纠结在“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问题,但我们会遇到关于未来的麻烦,我们今后的世界的模样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能否让世界变得更加紧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即便不能成为乔布斯那样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人,也至少应该在推动这个世界的更加便利、更加紧密、更加和谐上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看到过去的人的梦想,也是为我们找到自己的梦想,提供了一个最为美好的参照;重要的也许不是梦想本身,而是“我曾有梦”织梦者的能量。
y 林怿
2014年4月6日9:40:08
写于御庭园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七):中國夢,民國夢?
y 亂
對於人民共和國來說,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國號,已經在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城樓上的那句“站起來”之後,成為了歷史辭彙。是的,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了。民國的首都南京,現在只是江蘇省的省會。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被五星紅旗取代,文縐縐的“三民主義、吾党所宗”,被彌漫著火藥味的“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打敗。民國的國家元首叫“總統”,共和國的元首稱“主席”。民國通行的規範漢字正體字,現在更多情況下只被當作藝術字體。
可是,人們又難以否認,“民國”真的是無處不在。它出現在歷史課本裏,活躍在影視作品中,堂而皇之地出現在赴台觀光遊客的手機、相機裏。在與共和國同步的時空中,在僅有3萬6千平方公里的海島上,正有2300萬人演繹著另一種風味的“民國情調”。有人還會說,今天的人們離“民國”太近了,隨便在人民廣場上找一位跳舞健身的爺爺奶奶,一問,幾乎都是“民國”生人。
更重要的是,對於當下的中國社會,民國其實已經成為了一面鏡子。當某地政府的辦公大樓富麗堂皇,而小學校舍卻破爛不堪時,人們就會引用當年四川軍閥劉文輝的語錄:“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當錢學森問出“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時,沒有幾個人不會聯想到,現在我們還能叫得出的“大師”、諾獎的華人獲得者,都是在民國接受的教育,或者在民國就已經揚名立萬。
即便是新一屆領導人提出的“中國夢”,也並非是新鮮事物。早在82年前的1932年,民國廿一年,上海《東方雜誌》就策劃了一次徵求“中國夢”的活動。徵求的問題有兩個,“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夢想”。結果,包括林語堂、胡適、周作人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和各階層民眾共140多人,說出了自己的“中國夢、我的夢”。這140多人的“中國夢、我的夢”的重新結集,便成了《1933,聆聽民國》一書。
正如此項活動的記者吳景崧在“讀後感”中說,“應徵者以中等階級的自由職業者為多,約占了全數的90%。自由職業者中間尤以大學教授、編輯員、著作家及新聞記者、教育家為最多”“占中國人口90%以上的農民、工人及商店職員……現實對他們的壓迫太大了,整天的體力的疲勞,使他們只能有夢魘,而不能有夢想”。現在官方鼓噪的“中國夢”何嘗不是此等情況?
即便是許多“富於憧憬與幻想”的知識份子,似乎也對“做夢”沒有好感。林語堂說:“人越老,夢越少。人生總是由理想主義走上寫實主義之路……記得《笨拙》說過,不滿二十之青年而不是社會主義者,都是低能,年滿二十歲而仍是社會主義者,便是白癡。所以我現在夢越做越少而越短了。這是我做夢的經過。”
“文抄公”周作人則對“做夢”展露了譏諷的功力,他引用自己在《看雲集》裏的話:“信仰與夢,戀愛與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能夠相信宗教或主義,能夠做夢乃是不可多得的幸福的性質,不是人人所能獲得”。時任清華大學教授的俞平伯,則直截了當地說:“對不起,‘和夢也新來不做’。假如定要做的,恐怕也是妖夢吧”。
一些知識份子,則直接將自己的信仰、對現實的不滿,融入了“中國夢”中。上海法學院教授朱隱青的“中國夢”是“無階段專政的共產社會”。山東正誼中學教員徐伯璞在1932年就意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便是中國翻身自強之時……以三民主義為原則的大同世界,便在不久的將來出現了”。作家傅東華則“夢見”侵佔東三省的日本,“發生大地震……一會兒就要整個沉下去了”。時年94歲的教育家馬相伯,則像為未來中國立憲一樣,稱“未來的中國,既非蘇俄式的一黨專政,亦非美國式的兩黨更替,乃民治的國家,法治的國家”,“不但本部,世人周知;即高麗、臺灣、安南、緬甸,暨四境舊屬各地,皆可加入州聯,組織一大中國”。
《1933,聆聽民國》裏的“中國夢”,更像是一個個青春段子,是當時人們對時局、對未來、對國家暢想,不管是灰心冷意還是充滿希望,皆是真情實意。左中右不同的立場和意見,都能在同一個平臺上公開發表,供世人討論、檢驗。魯迅看到《東方雜誌》“中國夢”的徵集後,在《聽說夢》一文裏意有所指:“做夢,是自由的,說夢,就不自由。做夢,是做真夢,說夢,就難免說謊”。民國的魯迅可以大大方方地“意有所指”,現在的我們卻只能大大方方地引用他的話。
【此文已於2014年4月23日在《包頭日報》文化版發表】http://www.baotounews.com.cn/epaper/btrb/html/2014-04/23/content_293073.htm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八):关乎民族民生,不乏意淫吐槽
花了一天半的功夫读完了《1933,聆听民国》这本书,这是著名的《东方杂志》在1932年岁末策划的“新年的梦想”活动。虽然宣称应征梦想的为140余位文化精英,但实际上并非都是所谓“精英人物”,也有不少普通人。至于所言及的梦想,一方面体现了仁人志士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和民生问题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也可见愤青式的意淫和微博体吐槽。某种意义上,今日网络上所见的言论,实际上早已有之,只不过是换了载体罢了。
1933年瞻望中国的未来,是令人辛酸的,此时的中国,外族入侵,内部混乱,经济凋敝,文教落后,究竟叫人如何来谈自己的梦想呢?
《论语》杂志主编林语堂早年和鲁迅过从甚密,后来分道扬鞭,从林氏谈梦想的言辞里,不难看出他的批判色彩,其言论之犀利和迅翁倒有一拼。从他所谈的梦想里随手抽两条,看今日实现否?
我不做梦,希望民治能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
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
与之相应的,孙伏园,茅盾的梦都充满批判主义色彩。
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刘英士先生似乎不是谈梦想,而是预言,他说的话可谓金石之声:人民与国家是拆不开的;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国家不衰弱者……未来中国的国家身份,仍旧是和它的构成分子的知识,能力和道德相称。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知识,能力,对秩序与规则(法律)的坚守,与这个国家的实力是一致的。
中央大学研究生汪漫铎说,未来之中国,每人做他愿做的工作,每人享他应得的物质享受,每个人得他愿得到的知识。每个人爱他愿爱的人。工作,物质,情感,皆可以取决于个人所愿,这其实是对一个成熟的,自由的社会的渴望。虽然说的很细微,其实是一个大问题。
作家韦息予说,生在现今的中国,最使人感觉痛苦的莫若要吃饭,要说话,要行动,都受到不法势力的妨害和钳制……这话熟悉吗?
出版人,作家章衣萍显然是一个悲观的人,他说,这个中国是太老,太旧,太腐败了。中国恐怕还该有长期的混乱。大概,章先生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然而他的悲观并非没有理由。三三年之后又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中国人才算是喘了一口气,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浙江大学教授微知认为,未来要有一个美好中国,要扫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老大帝国的顽疾。贫穷,疾病涉及基本的民生,不解决贫穷和疾病,就没有身体健全的国民,不解决愚昧问题,就没有精神健全的国民,而解决掉贪污,才会有政治清明可言,只有人民有监督直拳,才能根绝贪污,也才能实现政治清明。而扰乱,则出现在中国两千年历史的没一个节点上,乱世军阀混战,不但有坐拥数省的大军阀,还有一县一乡的小军阀,皆是王霸思想的忠实信徒,这批人信奉的只有一条——暴力。因此,这些人存在一日则混乱一日不能休。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既是科学和民主普及的时代,也是暴力受到最大限制的时代。
梁漱溟先生的话总结起来只有一句,在我胸中只是充满了希望和兴趣。从先生后来的行迹来看,不得不佩服的说一句,先生只有一个强悍的人生。
巴金说,我只感到冷,觉得饿,我只听见许多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使我做噩梦。现今有人一提及左翼文学,边说艺术性差,只有口号和宣传。这倒不假,然而在一个连饭也吃不饱的人,他只有呐喊和血泪,那里有兴趣琢磨精致、婉约、小情趣、小趣味这一套。与张爱玲,苏青等人的作品相比,左翼作家的作品今日在读者中确实缺乏吸引力,然而并不必去否定他们。巴金所说的,并非但指他所处的时代,而是任何时代都有这样的人,他们是需要整个社会来关怀的。
上海银行的职员张水淇梦想的未来中国,男女的离合各随其自由意志,政治设施决于国民的公意,公意一决,个人不拿阴谋诡计来破坏。人人以忠诚相处,没有说真方买假药,假情假意妓女式的人。前面几句都说的好,男女离合当凭个人意志,旧式囿于传统思维或经济利益,多少女子被囚禁在婚姻里一辈子不得幸福,毁了一生。可以说,婚姻关乎人的基本幸福,非各随其自由意志不可,然而今日的人们真的实现各随其自由意志了吗,也未见的。至于民主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说。最后一句说没有假情假意妓女式的人物,这一句我十分反感,因为这根本就是侮辱了妓女,就卖假药,贩卖劣质食物,做官贪污,当城管而殴打老百姓之流者而言,他们那里比得上妓女。妓女出卖的不过是肉体,而这类人则侵害民众之安全与利益。
浙江大学教授郑晓沧提出了提高国民素质在于教育,其中有一条颇有意思,就是节育,而且提到了方法的“精密”和使用的普遍。
燕京大学教授滕白也则提出,人人合法持枪……
翻译家查士元说,未来的中国人应该有信仰(宗教心),没有信仰的个人,其努力不待说是放纵的,害社会的,伤国家的。这一句话颇耐人寻味,某种意义上,信仰意味着底线,一个没有底线的人,其越成功,危害便越大。今日流行的各种励志书,成功学书籍,大肆宣传手段和方法,无非是谋略和权术罢了,与查先生的话一比对,直令人寒栗。
陶孟和说,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这句话也颇耐人寻味,陶是社会学家,其言论略有几分反乌托邦的味道。
周作人的话同样耐人寻味,有哲理色彩。他说,信仰与梦,恋爱与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
在诸多思想中,既有民族主义,也不乏世界主义,如柳亚子就提出未来世界史无国界的,是世界联邦,没有监狱,没有金钱,也没有铁血(战争),甚至没有家庭。反家庭这一条,令人不能不联想到马老头和恩老头的思想……章克标也持有类似思想,认为未来之中国,既没有外国,也没有中国,也是世界主义者。马相伯是中华主义者,认为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诸国直接加入中国为好。
总结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想,无非是驱除外辱,有繁荣的经济,政治清明,老百姓过有尊严的生活。而另外一部分人的梦想则令人大大不快,而有些则简直令人发笑。如浙江大学教授俞子夷就提出,每个人成年后要先服兵役,再付工役,只有专门性的生产性的技术学校,学校里没有研究学问的闲人,人人都从事生产劳动。表面上看,这样人人都在劳动,且平等,但实际上把社会变成了一个纯粹生产型社会,无非是一个大工场罢了,充其量只是社会发展的极低级的阶段。以劳动的名义,剥夺了人们思考,从事艺术以及其他人文活动的权利。
赵何如,李权时则怕是两眼一抹黑,不看现实,还沉浸在“老大帝国”的梦里,赵梦想将来朝鲜半岛要“郡县之”(均改为中国的郡县),世界各国也要以中国为中心,李梦想日本成为中国一省。而孙伯鲁,复旦大学教授袁道丰之流则认为中国只有出现独裁者式的人物才能改变中国。
浙江教育厅第三科科长张任天则要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认为天下人皆无知识,皆可教之。就像把全国变成一个大监狱一样,企图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同样可耻。以教之名,消灭人的天然权利,仍然不乏独裁者倾向。
暨南大学教授张相时大概是搞水利的,想把全国的大江大河,水渠小溪从源头开始,两岸与河堤都砌成青石的,不知这种塑料审美观和开挖大运河式的工程出于何种思想,且不考虑经济收益和劳民问题,恐怕与水利专业也不相符吧,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一个叫杨一南的大概也谈了一套政治理念罢,多没记住,其中有一条是“婚姻自由,孀妇有再嫁义务,无偶者可向地方政府申请匹配……”不只是逻辑没学好,还是说了后句忘了前句。后面两句话直接推翻了“婚姻自由”四字,况人不是猪,如何由他人指令匹配之?
女作家谢冰莹大概喜欢团体生活,认为人们应该过着愉快的,有纪律的团体生活。我对团体生活是反感的,何况还有纪律。团体生活只该是社会的一个层面,比如军队,学校,监狱之类,全社会都如此,只怕不大好。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个体主义者,这一点我是大大不愉快的。
持志大学学生娄立斋的梦想是有一个我所想爱的女子,复旦大学教授袁道丰梦想我有一个良女伴,这和今日微博上“我的梦想是找个女朋友”的想法类似,一笑而无可厚非。还有一些,则是文人的吐槽,因无甚趣味,不予一一旁证。
还有些人的文字犀利,映照现实,只可寻味,不可言之,写多了,或写的太白,唯恐豆娘删文,就此打住。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自十八大***总书记把走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思想,中国大地上就掀起了关于中国梦的讨论热潮。
古往今来,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梦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梦想。那些梦想虽不尽相同,但是从国家民主富强,百姓安居乐业方等大方面看是基本相同的。
许多时候,梦想可以帮助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与颓唐之后重新起航,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茫茫暗夜洞见曙光,我们无法看见以及描绘出它真实存在的样态,却不能不相信它所带给我们切肤的感召以及影响……这也是之所以中国梦被几代人传承的主要原因。
《1933,聆听中国》是写在八十年前的中国梦,书中收录了1933年《东方杂志》关于“中国梦、我的梦”的征文作品,全书分为“梦想中的中国”和“梦想中的个人生活”等上下两篇,其实不论是梦想中的中国还是梦想中的个人生活,都饱含了彼时还生活在昏黑年代之中的人们对于中国未来对于中国人的未来的无限期颐,可以说,它轻易披露了八十年前人们现实生活的无限困窘,不过也彰显了如此困窘的现实之中精神世界里那弥足珍贵的富有。
那些梦想中,有“人类无怨,以跻大同;不立语言,以喻大道”之国家民族大梦想,也有“痨虫可以杀尽,老鼠可供驱使,蚊虫有益卫生,遗矢永无臭气;卖东西的不讲虚价”等有趣个人小主张,还有文人墨客“过目可以不忘”,“人人对于国家所当负的义务,所当享的权利一律平等”的思考,和普通百姓们“个人生活从此无忧无虑,欢欣鼓舞”的期望……《1933,聆听民国》让我看到了八十年前人们对于梦想的理解和诠释,虽然他们中的许多梦想带有了鲜明的时代色彩,虽然有些梦想还因过于弘大而略显假空大了,虽然有些梦想甚似空想,不过一路读来,八十年前的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未来新世界的憧憬还是深深地感动了我。
时至今日,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中国人民共同努力下,八十年前绝大多数梦想似乎都已经实现了,但是新形势下还有关于国家民族、自然人文和个人教育、机遇、发展等各种梦想等待着我辈的不断努力和实现,我相信“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我也期颐着任何梦想都不是空想。
《1933,聆听民国》读后感(十):听说有“梦”
1933年11朋1日,著名的上海《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次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征“梦”活动反响热烈,最终142位国人发表了244个“梦想”,包括一大批社会名流。本书《1933》收录了80年前,这百位文化精英构筑的中国梦想。也让如今的我们要以一睹“在那个昏黑年代“,中国文化社会精英们放在角色和架子,畅谈的中国和个人的梦想。
整个阅读轻松愉快,甚至对这些不加修饰的“真挚直言”心生许多奇妙的“猎奇”感,若许在许多正宗文字里读过许多的正腔圆润的主流声音,于是看这些“梦”,多少有些不可思议。比如,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胡适并没有做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之梦,而是坦荡地说,“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胡适在学术上并不是特别的出类拔萃,然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极强,交友应酬甚多,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也只是为了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想来很快意了,胡适一重最看重的《中国哲学史》可惜只编了半部,是一大憾。
人说,1933是墨索里尼、希特勒独裁主义方兴未艾之时,胡适的“梦”,也只是调侃,在他的带动下,旧梦纷呈,全无高大上、英雄主义、民主主义的套话官话,有的只是平凡人的一点念想。彭芳草说,“饿不死,卖得出书稿,买得起必要的书籍,并且有时间看,如是而已。”周谷城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条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翻译家查士元希望,“我不属于任何国籍。”老舍希望,“家中的小白女猫生两三个小小白猫。”
大约是“痴人说梦”的节奏,但有些依稀看出一些时政上的文人思维。比如,李宗武说得铿锵,“我希望我们能杀尽一切贪官污吏。”梁园东“梦想一个政府,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巴金则对民族报以失望,“我们中国民族恐怕没有希望了,他已经是太衰老了。”等等。
80年后读这些梦,有些怪异,却又让人佩服编者的用心,那些光辉灿烂的民国大师民国前辈们终于也走下了圣坛,留些人生琐碎或者消极落魄的模样。然而,读这些前人梦,又是有意义的,一来真实,言论自由;二来见证了当年那时主流思潮下各种“小九九”。这些梦,或者是理想的萌芽,或者是失望的堤案,虽说是梦,其实梦里仍暗暗潜藏着希望、热忱和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