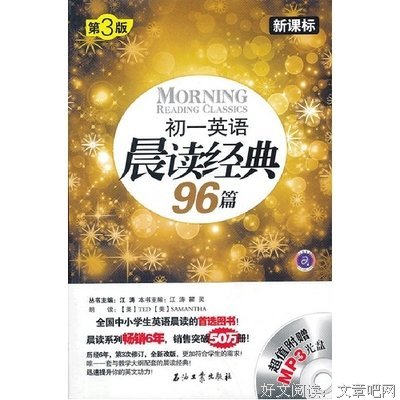《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是一本由Siddhartha Mukherjee著作,Scribner出版的Hardcover图书,本书定价:USD 30.00,页数:59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读后感(一):疾病之王
在疾病里面,癌症是个脾气古怪、难以捉摸的敌手。它冷酷无情,全球每年有800万人死于癌症;它类型众多,人体大部分组织器官都有发生癌症的可能。因此,想为治疗难度极高、疾病机理复杂、研究数量最多的癌症,写一本传记,是个有点“狂妄”的想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癌症医生和研究者悉达多•穆吉克(Siddhartha Mukherjee)做到了,他既梳理了古埃及以降的癌症历史,又重点描述上世纪中期以来的肿瘤三大治疗手段(放疗、化疗、手术)。该书甫一出版,便被评为2010《纽约时报》年度十大书籍之一。
书的封面印有一只螃蟹。原来,Cancer本意是指螃蟹,螃蟹的张爪舞钳,极富侵略进攻的样子,与癌症的特性极为契合,故cancer又指癌症。攻克癌症之路漫漫,但仍要抱以乐观态度和信心。作者认为,量变引起质量,人们在癌症研究上取得的丁点进步,只要循序累积,终将“摧毁”癌症。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读后感(二):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出纪录片了
一共三集六小时。PBS电视台3月30号起东部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1点连播三天。今晚看了第一集,蛮好看的。没想到书里写的很多人现在都还活着,还能在纪录片里讲他们的故事。人类对抗癌症的努力居然在一个人一生的光阴中间获得了这么大的进展。真是让人感动!
电影官网:http://cancerfilms.org
亲测可看的电影链接-第一集:http://video.tpt.org/video/2365450686/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读后感(三):比读专业书有意思的多了
最近在看原著,这是第4本,也是看的最爽的一本。
..............................................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读后感(四):一个物种的战争
这是我迄今为止读过最好的科普书。
毫 无疑问,这是一本工程浩大的经典,一本详实严谨的科学著作,同时,它也是一本史诗般的传记。如果说写作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写作的结果,那这本书的主题 ——被作者称为万疾之王的癌症,在我看来,应该是长长的人类疾病名单中(其实不止人类),为数不多的、当得起如此礼遇的一名。
癌症这种极 其复杂的疾病,在科学史上占有无法低估的地位。尤其在近几十年来,有关它的科学研究层出不穷,说是浩如烟海也不过分。要在不到五百页中,将深奥繁难的科学 道理深入浅出地讲给普通读者听,如果作者自身不具备相当的科学与写作功力,这一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而在这一点上,本书作者Siddhartha Mukherjee得天独厚——他任教于哥伦比亚医学院,拥有自己的基础科学实验室,并屡屡在顶级杂志上发表论文,对于这个领域的科研脉搏有着精准的把 握。他同时是一名癌症专科医生,与许多病人有着直接的交流,这使得他能在残忍的疾病与冰冷的学术知识之外,为书中引入鲜活、充满感情的个人故事。此外,他 还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大概足以证明他的兴趣、爱好与眼界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与行医治病。事实上,在书中他旁征博引,行文结构严密而流畅,语言优雅大气、 充满跌宕起伏的节奏,绝不输于许多文学著作。
要给一种疾病写传记,逃不开的两个核心问题无非是“这是一种什么疾病”以及“我们怎么治疗 它” 。这本书先将重心放在治疗上,只是在点评各种医疗方法、介绍它们之间演变的渊源时逐渐引入一些关于癌症的基本生物学知识。而随着医学史脱开早期匪夷所思与 惊心动魄的蒙昧,随着医生与研究者们渐渐做出峰回路转、让人叫绝的成果,作者也进一步引入更多、更深刻的关于癌症本质的讨论,写作的重心开始偏向于基础科 学对癌症的认识。这样的布局与脉络,在我看来绝非偶然为之,而是作者精心安排的结果,也许正是为了刻意映照科学史的发展—— 在人类对癌症的战斗与发展史上,治疗与认识这两条线索就不断纠缠交错,相辅相成。早期那些现在看来未免荒谬得令人战栗的治疗方法,也代表了先民对了解这个 世界勇敢而茫然的尝试,而正是在漫长而黑暗的摸索中,人类积攒着关于自然和自己的知识,最终将历史的车轮带入了现代科学的晨光之中。从此不但创造出更合符 病理、更对症、更有效的癌症治疗方法,也极大地繁荣了基础科学的研究,进一步在广度与深度上扩展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体会到作者行文的苦心,对理清自己对癌 症研究史的认识与理解,实在是不无裨益。
阅读这本书时一个另一个体会是自己对医学的感觉一直被左右撕扯,很难定位,一时觉得对癌症的认识 与治疗在短短几十年前还古老荒诞得令人难以接受,而另一时又感叹原来许多现在用来应对癌症的常规方法远在百年前就已经成为医界常态。事实上,由于人类寿命 的增长、检测手段的进步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三者的作用大小依次递减——癌症这种原本罕见的疾病,确实在近百年来才变得更加普遍,再加上社会对癌症研究 与日俱增的投入,癌症似乎成了现代社会的标志,高悬在科研的前沿,有时候让人忘记它实际上是多么古老的一种疾病。而另一方面,由于癌症确实贯穿了整个人类 史,见证了我们这个物种的起源、演化与发展,我却又常常忘记人类对它的真正了解与有力挑战,不过是漫长岁月里最近一两世纪的事情。这种古老与现代的对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映的也正是癌症这种疾病本身错综复杂、扎根于生物最基本最深层的核心的本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人类对它的漫长征途。
这本脉络分明的书不断地提醒我去理解各种矛盾而统一的事实,修正我脑中的错觉,以至于在看完之后,我再试图回顾人类与癌症的战斗史,竟然有了前所未有的清晰线索,真是令人欣喜。
癌 症,从本质上来说,是生命体的一部分的生长失去控制的恶性疾病。明确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类史上最早出现的癌症治疗是手术切除这种直观、简单、符 合逻辑的应对方案——两千五百年前的波斯女王Atossa身患乳腺癌之后,就让贴身奴隶替她削下乳房。而麻醉术与抗生素出现以后,复杂的外科手术不再是 医学的禁区,极端的切除手术更成为医学界的主流。然而,癌症不是六指畸形,恶性肿瘤与良性肿瘤之间有着巨大的生物学区别,所以,不管施行切除的外科医生在 技术细节上如何精益求精,由于这种方法并未触及更深层的癌症本质,对于许多、尤其已经发展到晚期的癌症病人来说,并不能起到治愈的效果。
当 人们对生物体的认识深入到细胞的层面,就开始意识到癌症生长来自于细胞的恶性分裂、和繁殖(而不只是一团组织莫名其妙地长大溃烂),这时候,才出现了“杀 死癌细胞”的概念。主流的两种疗法——化疗的放疗——无一不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化疗所使用的药物,以及放疗所使用的放射线,本身就是对任何细胞都毒性或破 坏性极强的物质。只不过它们往往对分裂繁殖中的细胞效果更为明显,而癌细胞比其他正常细胞分裂更快,所以受到的损伤更大。这时的疗法,对癌细胞的针对性、 特异性,实际上并不高。更令医生与病人们感到无比沮丧失望的是,大多数对癌症有效的单种药物,固然能在短时间内起到显著的疗效,却无法阻挡癌症卷土重来的 脚步。
然而,正是在这个阶段,现代医学与药学对癌症治疗做出了最重要最具有突破意义的那些发现,也是在这个阶段,医学开始让人看到了治愈 癌症的可能。实际上,针对癌症卷土重来而做出的那些努力,也帮助人类理解癌症发生发展的根本的特征。在这个阶段,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华裔科学家李敏求。因 为这个故事让我感受颇深,所以决定在此多花一些笔墨重述这段历史。
五十年代,在美国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NCI)工作的李接手治疗几位患有子宫膜绒毛癌的病人。子宫膜绒毛癌是一种罕见而恶性的癌症,按当时化疗流程治疗以后,很多病人都会 在短期痊愈后又经历复发。不过,这种可怕的癌症并非来去无痕,它会导致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在尿液中升高,这也成为检验这种癌症的一个标准。李敏求 注意到,哪怕经过化疗,癌症组织缩小甚至消失之后,在病人尿液中,hCG依然可以检测得到。在书中,李被描写成一个有些木讷、偏执到几近古怪的人,他认定 尿液中的hCG,意味着病人体内还有少量癌细胞的存在。于是他坚持不懈地继续对这些病人用药,直到他们尿液中的hCG完全消失为止。NCI对李的做法异常 愤怒,指责他进行“人体实验”,很快将他开除。可是,经过时间推移,人们发现,经过李治疗的病人,几乎无一人复发。直到今天,李的方法还常规地用在这种癌 症的治疗中,而这种曾经无比致命的可怕疾病,现在享有几乎百分之百的治愈率。
治愈任何癌症,都让人欢欣鼓舞,但实际上,这项发现的意义超 出了具体癌症的本身:李的固执,使得他做出了癌症治疗史上一项重大的发现——“癌症治疗必须是系统的、长期的,哪怕病人体内已经看不到任何癌症存在的痕 迹。”这个结论,初看来似乎毫不出色,甚至让人觉得平淡得不值一提,但我不得不脸红地承认,看到这句话时,我觉鼻子像被人一拳打中,不由自主地酸了一酸。 也许是因为李的固执让人感动,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掂量这个发现背后深广的意义时,足以让我感到心跳加速。
其实,癌症治疗,与使用抗 生素治疗细菌感染,不无相似之处。急切繁殖求生的癌症,正如急切繁殖求生的病原体,它们使尽浑身解数,在自然选择的战斗中孜孜求胜。而它们的法宝也颇有雷 同:通过修改基因,激发那些在正常生理条件下负责生长存活的机制,抑制那些促进细胞有序淘汰死亡的程序,使得自己获得选择的优势。而正所谓宜将剩勇追穷 寇,对于病人来说,生机就存在于“斩草除根”之上,正如医生坚持抗生素的使用必须完成整个疗程,癌症治疗也必须打长期艰苦的战争。事实上,数年后,李敏求 另一项研究成果——使用多种化疗药物治疗睾丸癌——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种系统根除战的必要性。而在具体疗法之外,意识到癌细胞与其他病原体、或其他生物 体之间的相似性,更具有极其深刻的科学意义。读完这本书后,我去网上搜索李的生平,才知道他一生做出许多重要发现,曾是大名鼎鼎的Albert Lasker奖获得者。我松了一口气——那个因为正确判断而被错误解雇的年轻人,终于证明了他当年的发现,并非幸运的偶然。
但是,不管是 传统的放疗还是化疗,都并非仅仅针对癌症的特效药。它们是十足十的破坏者,副作用也异常巨大。经过放疗化疗的癌症病人,无不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九死一 生地留在人间——还往往要在未来面临癌症复发的噩耗。所以,医学界一直在寻找更为特异的癌症疗法。在早期,医学与药学界的发现大多基于盲目的试错与筛查各 种化学物质,而过去数十年来基础科学的发展,则终于为人类提供了基础研究指导药物开发的可能。书中提到的her2阳性乳腺癌的特效药Herceptin, 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在这个部分,作者在描述了一例乳腺癌病人Barbara Bradfield令人欢欣鼓舞的旅程之后,谨慎地展现出对靶向药物前景的乐观。但我想,他作为一个科研者,应该很清楚基础研究领域汗牛充栋的发现中,只 有极少数具有临床意义,而这极少数之中,只有更少的一部分,能够真正地被开发、进入临床医学。实际上在作者详细叙述Herceptin的发现过程中,读者 就不难看到基础研究者(哪怕是科研界大拿、顶级科学家)往往忽略了自己发现的临床意义,科研与开发之间,至今隔着宽阔的鸿沟,令人深深叹息。
在 治疗癌症之外,作者花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来介绍癌症的预防,作为一个拿着cancer prevention fellowship的流行病学研究者,我对这个方向的历史与科研动态更为亲切熟悉。这部分从数百年前清扫烟囱的欧洲男孩的阴囊癌开始讲起,最终将重点放 在烟草与癌症筛查上。这毫不奇怪,烟草与癌症的关系几乎是整个人类流行病学史上最显著、最一致、也对公共健康影响最为深远的发现之一,而哪些癌症筛查、或 如何进行癌症筛查能有效降低死亡率则是近年来科研界内外争论不休的重要主题。而我进一步猜测,作者选择它们,而非其他流行病题材,也许不仅仅是为了展现预 防的意义,或者强调流行病作为一个学科对癌症科学所做的贡献,更关键的缘故,则是因为这两者反映了科学与社会、经济、政治、伦理,医学科研与其他各行各界 之间意味深长的拮抗与互动。
事实上,作者在本书第一章选取Sidney Farber,而非其他医生或科学家来开始本书,大约也正是因为Sidney不但是一个在科研与医学方面做出重要发现的先行者,更重要的是,他后来成为一 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以宽阔的眼界与惊人的热情投入宣传癌症的活动中去,在这方面做出了完全可以匹敌、甚至超出他的科学发现的重要贡献。整本书中,社会的 进程与关键的历史事件不断与医学科研的轨迹相交,影响着每一个医生、科研者、病人、以及癌症史本身的命运。而作者以宏观的视野、深入的分析、独到的结论以 及史诗般的语言,将癌症有机地编织到人类社会之中,这,在我看来,正是本书优于许多其他科普读物的重要原因。
而在所有科研、医学、社会、 历史的大词之外,作者对个人的关注,为这本书添上了格外动人的色彩。在所有个人之中,他对病人细致而克制的刻画,尤其令人动容。实际上,这本书以病人始, 以病人终,似乎自始至终,作者都在提醒读者,在癌症的背后,是一个个与我们血肉相连、气息相通的个体。而某一刻我想,这些个体与癌症的故事,当汇集在一起 时,似乎也具有了超出个体的象征性的意义——那,是一个物种不依不饶的、与一种致命的古老疾病的恒久战争。
在 书中无数个病人的故事里,Germaine的故事,既不是最悲惨的,也不是最幸运的,既不是最鼓舞人心的,也不是最令人沮丧的——也许这是他选择她的原 因?作为一种罕见的消化道癌症患者,Germaine在六年前已经濒临死亡,她想方设法加入了一种靶向新药的临床试验,疗效良好。但癌症终于在09年复 发,并终于夺去了她的生命。在与癌症旷日持久的战斗中,她生活中的一切都围绕着癌症展开,带上癌症的烙印,她一面适应癌症,一面挑战癌症,她曾经取得胜 利,却又最终落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只能“拿出全部的力量与尊严,转动轮椅前去洗手间,似乎她已将这长达四千年的战争浓缩于此”(全书最后一句话)。
刚 看到这句时,我简直不能相信Mukherjee会用如此近乎绝望的一幕来结束这本书——我一直在等待一句激动人心的、具有转折性的警句,一句煽动性的、充 满信心的口号,让这本书,成为一篇面对癌症时人类写下的永不认输的战斗檄文。然而反复品味之后,我却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医生、研究者、癌症专家以他全 部的学识、逻辑、经历所能提供给读者的最大安慰。而作为一个癌症研究者,我自己又怎能不明白这里面的道理?
在这场古老的战争里,当生命体 的局部与整体从唇齿相依发展到敌死我活的冲突、我们作为那个不幸的整体,所面临的敌人是千万年物竞天择中演化出来的精妙而复杂的机制。在复杂得令人眼花缭 乱的致癌因素之下,癌症所体现的是这个自然界最核心、最原始、最顽强的生存需要与能力。每一个癌细胞,都是一个扭曲的、发展的、比我们本人更强大的、适应 能力更高的,我们自己的终极版本。正因为如此,真正战胜所有癌症的时刻,也许永远不会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之中。而充满讽刺——或具有哲学意味的,我们面对癌 症时的挫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体现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在自然选择中的胜利。
但是,哪怕我们不能像消灭天花那样消灭癌症,在与它斗争 的漫长历史里,一代代科学家、医生、病人、社会活动家依然联手探索新领域、做出新发现、进行新创造,打开新天地,不断推进我们认知的前线。说到底,个体的 生命总有尽头,而这些超越生存本能的,专属于人类的智慧与情感,恐怕才是我们能向自然规律这个强大敌人炫耀的唯一东西吧?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读后感(五):癌症似乎是上帝在创造人类时设下的一个基因武器,一旦触发,就是一场人体自身的生死对决
四周的时间终于读完了真本书。还是要感谢周末大块儿的时间,平时上班的晚上真的读不了几页。再加上这本书比较专业,不像一般小说一样读来那么轻松,大块儿的时间让思维也能保持连贯。
这是我今年读的第二本印度裔医生的书,不由得又要感叹印度裔医生在文字方面真的有很深的造诣。这是一本癌症传记,作者追溯历史上所有关于癌症的记载,引经据典,一个个历史故事如数家珍,这背后是得有多大的功夫啊。同时,作者也大量地引用了文学经典中的故事,并解释了很多医学术语的希腊或拉丁语来源,包括书封面的“螃蟹”和“癌症”的关系,可见作者的文学素养。
这本书获了2010年非虚构类的普利策奖,这就是对畅销书最大的肯定,毫无疑问的这本书是一本高质量的科普读物。我第一次了解了几千年来人类为了治疗战胜癌症所做的努力。作者介绍了手术,放疗和化疗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包括各种疗法如何一步步走向极端。切了瘤子还不算,要把能切的都切了。一剂化疗药品不行,要两剂,四剂,甚至更多。这也无不显示出那时以至现在人类挑战癌症的胆量,从中也有一些不耐烦。多少年来医学界都是在try and error,都是在试验,这个不行,试那个,一个不行,再加一个。在没有认识癌症的根源的基础上的一切努力都有些盲目。之所以对这本书感兴趣,就是想了解癌症到底是怎么来的,现有的治疗方法到底有多大效果,未来的出路在哪里。站在现代医学可以解释的最高水平上,作者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对癌症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尤其是从病理上,从药理上,从预防上,从分子基因的层次上。
读这本书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人体和宇宙一样,对于人类就是一个谜,一个黑盒子。一个是微观,一个是宏观,都不是肉眼凡胎能够参透的。就拿人体来说,有了解剖,我们知道了不同的内脏器官,有了显微镜,我们看到了细胞,有了基因图谱,我们似乎已经破解了生命的密码,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基因会这么起作用,为什么基因就会变异,这其中是一个什么力量?就像是自然界中的物质一样,为什么又的能相互反应,有的不会相互反应?为什么有的有生命,有的没有生命,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其中的奥秘深不可测,至少现在人类还没有认识到,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都是逆向解释的。从根源上,我们还没有答案。这就是生命的奥秘,这就是宇宙的奥秘。
这本书读来比较专业,但作者在讲述过程中让读者认识到对癌症的研究绝不只是科学家的事情,这绝不只是一个科研难题,这里涉及到了系统化的临床试验,产业化的药物开发,还有政治游说,广告宣传,说到底癌症研究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里有对理想的追求,也有对利益的争夺和保护,展示了活脱脱的人性。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翻译成中文,或是原版引进,成为国内医学学生的课外必读书目。我们从中学到的不仅是关于癌症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部医学简史。而对于国内的医学尤其是癌症工作者,不仅能学习各种治疗和预防的理念,还有就是其中的医患关系处理,还有系统的工作方法。真的读完这本书,我都想读医学院了。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读后感(六):An immortal battle with an enemy within
(文中的Ella竟然在goodreads留言了,說她已經六十多歲,依然健康,科技真好,互聯網和醫學都好神奇啊^_^)
It is a story of the biggest irony of the human race: after generations of human chasing the pipe dream of living forever, we finally realized it was when one of the very building block of the human bodies, our cells, reached its immorality, we met our own demise. Life gets to live when cell dies; life comes to end when cell won’t die - “ nature satanic humor”.
This is a biography of a disease that at least is 4000 years old: the first medical description of cancer was written in 2500 BC, since then many theori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explain this disease and even more method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trying to cure it, methods of which always resulted with disappointments.
efore 1900, the only resolve to cancer was surgery, which culminated in 1890s when William Stewart Halsted devised the radical mastectomy; however, radical as it was, it extirpated patient’s breast entirely but not patient’s cancer entirely - mastectomy turned out to be futile for already metastasized cancer, many women died with despair hearts and disfigured bodies.
Hope descended but soon aroused with the discovery of radium, high doses of which could killed tumors even the metastasized one; but radiation was soon found out to be carcinogenic itself, and its discoverers- Marie and Pierre Curie - over exposing themselves to X-ray, died from leukemia.
The next treatment of cancer is hardly less intrusive than its predecessors: chemotherapy - the most widely used cancer treatment nowadays - didn’t come into existence until World War II. Sidney Farber, the pioneer of chemotherapy, was the most mentioned medical hero in this book. He specialized in leukemia from which he discovered a folic acid analog that killed rapidly dividing cells in the bone marrow. This folic acid could help patients obtain remissions for a brief period. The concept of remission changed the doctor’s perception of cancer treatment; after all if we couldn’t cure cancer entirely maybe we could make cancer be living with at peace. However chemotherapy is anything but peaceful, the chemical that kills cancer cells also kills normal cells, making patients vomit, loose hairs and enervate.
Cancer treatments were that intrusive and painful, and patients needed to solider up for the procedures, those who couldn’t started to turn to palliative care. Being considered as the antimatter of cancer therapy, the popularity of palliative care seemed to symbolize an admission of failure to the battle against cancer. The world was longing for a less intrusive treatment with high efficacy and it was about to appear, but before that happens, something has to be changed.
Cancer had been a mystical disease that kept defying all the logic. Scientists and clinicians needed to know the cause of a disease before they can seek the cure, but for cancer, the cause and cure, for a long time, “ having feasted and been feted together, separate taxis off into the night.” The cause and cure of cancer finally came into confluence at the age of genetics. With the help of knowledge of genes, cancer was decoded to be a genetic defection which was caused by an activated proto-oncogene and a dis-activated anti-oncogene. Different cancers have different corresponding proto-oncogenes and anti-oncogenes, a discovery that crashed the generations’ dream of “a universal cure” for cancer, but born the new hope of oncogene-targeted drug - the latest weaponry against cancers. Again, being highly effective, this targeted drug is hardly an elixir of cancer. Cancer with an indefatigable power keeps evolving and developing to resist the drug and scientists need to develop new drugs to subside the new version of cancer - a battle between cancer and the ingenuity of human being.
The ingenuity of human being wasn’t only displayed in the medical field. As a disease that kills millions people per year, cancer is also a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 in 1970, a full-page advertisement "Mr. Nixon: You can cure cancer"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showing the zeal of the public to defeat cancer. The campaign of “ War on Cancer” championed by Farber and Lasker (a legendary entrepreneur, socialite and the fairy godmother of cancer research), had been going on for decades. But a political cure didn’t lead to a medical cure; scientific discoveries were too serendipitous to follow a blue print. The only consolation was, although the gigantic campaign didn’t produce an end to cancer, it produced many clinics and organizations both of which became the foundations of latter cancer researches, also the campaign produced a new way of combating public issue that inspired generations of advocates. Action does not always bring success, yet it often brings progress.
Dr.Siddhartha Mukherjee, a cancer physician and researcher, wrote his debut book when he was doing his residency in an oncology department of a general hospital. He said cancer is caused by uncontrolled growth of a single cell, hence it is a distorted version of our self. Cancer indeed is so much like a human being: it too exploits the genetic instability to evolve itself, and the human species as well as cancer ironically are the ultimate products of Darwinian selection. I believe this similarity between cancer and human was the reason Dr.Mukherjee called this book a biography rather than a history. And I also believe it was the plenty personal touches in this book made this book more of a biography than history.
The stories in this book captured patients’ overwhelming despair, pain and confusion. One story articulated the last emotion: Dr.Mukherjee paid a visit to a patient, Ella, who was the only survivor of a trial treatment for childhood leukemia back in the 50s. All of children she knew during the trial succumbed to the disease, only she survives, standing and smiling, at the age of fifty-six. “ I don’t know why I deserved the illness in the first place, but then I don’t know why I deserved to be cured,” Ella said, looking at the album of the days during the medical trial. Once again cancer showed us how it defy our logic, being alive become the the underved. This kind of psychological suffering wasn’t only reserved to patients; it also haunted family, friends, nurse and doctors.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book, Dr. Mukherjee talked about his glumness when he was driving to work, concerning whether his patient, with whom he talked 3 hours yesterday would develop a fatal complicat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book, he talked about when he was finishing his residency he and his colleagues had to decide to work at laboratory or at the clinic, they had this impromptu memorial service at which they read a list of the names of their passed away patients followed short eulogies respectively; latter he talked about the dreadfulness he felt when he saw a pile of death certificates waiting for his signature sitting on his desk… The battle against cancer is a battle fought by patients, patients ‘love ones and professionals that surrounding the patients, all of who are soldier in tears facing this immortal enemy.
The book ended with the story of Germaine, one of the patients of Dr.Mukherjee. She was diagnosed with a rare kind of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and when she was diagnosed her cancer already metastasized with no chemotherapy could help. When her hope was drained, a miracle happened, an oncogene-targeted drug specific target her cancer was developed. The new drug saved her life when she was about to be defeated. Unfortunately after four years of subsidence, her cancer developed a resistance to the drug, reappeared with a mass metastasis. Couldn’t wait for another miracle, she died to the death she had expected five years ago.
It is hard to tell whether it was a happy ending: Germaine did live five more years and the longevity as well as the survival rate of cancer is extended across the board; yet these cold statics can’t give us any comfort. We’re still dread at the image of death, and seeing this battle with so many fatalities, how can anyone have any comfort?
We hoped, disappointed, thrilled, and despaired and then hope again,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most consistent feeling is sadness, sadness for the transience and vulnerability of life itself.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读后感(七):《癌症传记,万病之王》读书笔记
前言
本书是以作者在医院做fellowship第十个月遇到的一个病例所展开,病人是一位三十岁的幼儿园女教师,名叫Carla,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患病之前身体一直很健康,突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作者联想到十个月来遇到的种种癌症病例,不禁感叹无数经过了多年教育的医生在与癌症的不停战斗中都一一败下阵来,一股失败的宿命感挥之不去。
癌症,起源于身体基因突变,导致一部分细胞不受控制肆意分裂、增长,从而吞噬生命。横亘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是如何阻止基因突变,如何在不伤害正常细胞的条件下消灭恶变细胞,以及如何在基因层面区分正常的细胞增长与突变细胞增长?
结束了两年的fellowship,作者渐渐摆脱了那种宿命感,在不停的天人交战中,又有一些问题浮出水面:我们与癌症的斗争是从何开始?我们都做了什么?这场斗争是否已经结束?我们能否赢得这场斗争?这本书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在前言的最后没有提及Carla的结局,只是告诉她,这病在经过一年的化疗后,治愈率大概是30%。
第一部分 Of blacke cholor, with boyling
脓血病
1947年12月的一个早上,一位叫Sidney Farber的儿童病理学家正在波士顿一所医院的化验室中焦急的等待来自纽约的包裹。 Farber已经在显微镜下工作了20年,每天与尸体或组织切片打交道,而他则越来越想面对活生生的病人。长期的病理学工作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知识,他等待的包裹里装是他认为可以抑制白血病的氨喋呤。
白血病被发现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它进行了种种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仅局限于描述白血病本身,对它的治疗方法,毫无头绪。当时的医学杂志这样描述医生对白血病患者的治疗:"确诊,输血,送回家等死。"
1845年,人类第一次发现白血病,就是从困惑与绝望开始的。那一年苏格兰的外科医生John Bennett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病人。这是一个二十八岁的蓝领工人,最初是脾脏肿大,伴有高烧,然后是左侧腹部的肿瘤,持续增长了4个月;接着几个星期,各种症状接踵而至,发热、血疹、腹部阵痛,最后在腋窝、腹股沟、脖子处又发现了其他肿瘤,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他最后无可避免的死去。Bennett对他进行了解剖,在病人的血液当中发现了大量的白细胞,而白细胞增多在当时的医学认知下是感染的重要标志(也是脓的主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这可能是病人一系列症状的病因,但最后他并没有找到可以引起感染的伤口。最后他总结道:"血液自己就变成了脓液。"于是他叫这种病为脓血病(Suppuration of Blood)。
四个月后,一位德国研究者Rudolf Virchow独立发表了一个极其类似的病例,也是脾脏肿大,在做尸体解剖时,同样在血液中发现了大量白细胞,牛奶状地稠密液体漂浮在红色之上。
当在他知道了Bennett结论后,并不认同。他不认为血液会无来由的变成脓液。但是还是有问题困扰这他:为什么脾脏会肿大?为什么找不到任何伤口?他开始怀疑是血液本身的问题,最终他没有找到答案。不过他给这种病起了一个名字,weisses Blut,字面就是白血意思,1847年改称了一个学术化的名字Leukemia,来源于希腊语的白Leukos。
从“脓血病”到“白血病”这种名称上的转换,为了人们理解白血病起到很深刻的影响。与Bennett一样,Virchow也没有搞懂白血病,但是不同的是,他没有去误读这种病症,后来Virchow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白血病,而是在病理学上致力于从细胞层面描述疾病。
他与两位同事共同建立了细胞学,这个学说基于两条基本原则:一,身体是由细胞构成;二,细胞只会产生于其他细胞。如果基于这个假设,那么人类的生长只能有两个情况,一是细胞的变多,二是细胞的变大。Virchow把这两种方式定义为增生(Hyperplasia)与肥大(Hypertrophy)。这种定义把人类对生长的认识提高到了细胞层面。不过他很快就对癌症,这种增生产生的疾病产生了困惑,癌细胞像脱缰野马般不停的增多,好像自己有生命一般,最后Vrichow把这种增生的极端形式定义为癌形成(Neoplasia)。
在1902年Virchow死时,一个癌症的新理论正逐渐形成:癌细胞自发的分裂,这种分裂产生了大量的组织,侵占了正常的器官与组织。基于这些理论,病理学家在19世纪80年代,沿着Virchow的路继续研究白血病,把它当做白细胞的癌形成,而不是脓血病 。
经过了大量的观察,明确了白血病的研究方向。在20世纪早期,病理学家把白血病分类:一种是慢性,缓慢的影响骨髓与脾脏,就像Virchow的那个病例;另外一种是急性,病症因人而异,不过常常伴有发热、出血、晕厥等症状。
急性白血病按照不同细胞的癌变还分成两种,一种是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另外一种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与淋巴癌不同的是,后一种癌变的都是未成熟的淋巴细胞。儿童白血病,几乎都是ALL。
idney Farber生于1903年纽约的水牛城,他父亲是波兰移民的犹太人,对Farber的要求很高,而Farber也不负众望,在水牛城修完生物学与哲学学位后,而后又在德国与美国进修医学。20年代末期,Farber在波士顿儿童医院,成为一名病理学家。他在儿童肿瘤分类上的研究,得到的广泛的认可。但他并不甘于做一名“死人的医生”,而是想真正的治愈病人。在1947年的夏天,他决定在所有癌症中选择最与众不同,也是被人们认为最无治愈可能的儿童白血病作为主攻方向。
这并不是Farber的头脑发热。科学基于精确的测量,要想理解一个现象,必须要能够客观的描述它,而要描述它必须要对其能够进行测量。判断癌症药物是否有效,必须要能够严格有效的测量癌细胞数量。
在CT与MRI的时代前,所有肿瘤的观察,必须借助于外科手术,而唯一例外的则是白血病,它的癌细胞流淌在血液当中,简单的抽血就可以确定癌细胞的数量。如果可以确定数量,那么一种药物是否有效就可以非常容易的观察到。抓住复杂现象的本质进行研究,然后再反向还原,这是科学上颠扑不破的道理。
当同年12月他打开那个从纽约寄来的包裹时,他没有意识到一条思考癌症的新思路,就这样被他发现。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读后感(八):Nature sometimes seems possessed of a sardonic humor
I wasn't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as it has always seemed over-conservative to me. But after cancer stroke my family several times, I begin to feel the deep respect for life behind the conservativeness. Reading this book enhances this feeling within me.
The fight between cancer and human beings is a long history. But only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modern medicine does human beings really tap in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ancer systematically. Early treatment of cancer was mainly operation, cutting out the bad parts. It evolves naturally to new methods of cutting, radiotherapy. Inspired from modern medicine, chemotherapy has been studied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t is only after failure to treat cancer after decades' optimism that scientists begin to systematically question and study the cause of cancer, thus coming the gene therapy.
Coincide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reatment is the growth of pessimism towards cancer. The finding that cancer is innate in the life. Put it another way, where there is life, there is cancer. The new normalcy is the deadly cancer won't disappear as smallpox. Siddhartha reflects such conflicting feelings vividly through patients' personal accounts. The excitement of treatment is always accompanied by the despair of relapse.
The words summarizing my feeling towards cancer after reading this book, quote from the author, "Nature sometimes seems possessed of a sardonic humor".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读后感(九):我目前读到的最好的科普书
最近时间相对充裕,补书一本:众病之王。
这可能是我读过的最沉重的一本传记。它篇幅不短,而矫情的我又历来无法忍受翻译腔要看原版,造成此书断断续续拖了大半年才读完。有的时候能拿出整个下午或者晚上来细读,有的时候仅仅是在漫漫通勤路上努力看上几段,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翻开此书,那种打发时间的轻松都会在短短几行之后迅速消失,整个神经绷紧到一种沉浸、严肃、甚至有点敬畏的状态。有的时候那种字里行间的肃杀感会让你忘了窗外8月的热浪,或者——如果你碰巧喜欢站在地铁车尾——它会配合着空调出风口那道最强劲的冷气直透脊背,让人头皮发麻。
因为这是一本癌症的传记。
这可能是所有人都感到毛骨悚然、同时希望敬而远之的一个名词,甚至连提起这两个字都是忌讳。大半年前我偶然在Kindle上看到这本书的推荐,它拿到了当年了普利策奖,推荐语大概配了这么一句话:“了解当代人类社会最大的敌人。”我心想我上班也上得差不多该健脑了,于是就果断吃下了这颗安利,于是也看到了目前看过的最好的一本科普书。
我明白我永远也不希望碰上这个敌人,但是我必须正视它的存在,而正视它的最好方式就是去了解它。
了解敌人
传记是一个故事,故事都需要一个起源,而这里的起源也是一个悲伤的“恒久远、永流传”的套路。虽然在我们有限的认知里,癌症似乎都是一种现代病,但如果把它视作投射在人类健康之上的一道阴影的话,这道阴影其实和我们的历史、乃至我们的认知一样悠长和久远。早在公元前2500年的古埃及文手稿中,当时的名医印和阗就记录了这样一个病例:“乳房上鼓起的肿块,又硬又凉,且密实如河曼果,潜伏在皮肤下蔓延”(本书的作者称之为可能是对乳腺癌最早也最生动的描述)。印和阗对记录的其它病例都给出了简介的治疗建议,唯独在这一栏下只写了短短一句:没有治疗方法。两千年之后,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在史作中记载了波斯皇后阿托莎在乳房上发现疑似肿块、最终由自己的希腊奴隶帮助切除的故事。当然,这些是有传奇性质的记载,科学的起源考究需要的是通过特殊历史条件保存下来、能够分析检测的肿瘤组织。这些千年的恶性肿瘤还真在南美洲古老的科里巴亚文化遗址处找到了,而且它们和那些传说里记载的古老病例读起来一样吓人:“(古病理学家)在一具35岁的女性木乃伊左上臂上摸到了一个“球状肿块”,保存完整,里面充满了骨针。这是保持在木乃伊体内千年之久的癌症。即使是很小的骨肉瘤,也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痛苦,这个女人所承受的病痛,一定是万蚁噬心的。”
当然,如果只是列举从古至今的癌症病史的话,这本书会成为一本读起来非常惊悚的杀人案集锦,只不过凶手是源自人类自身的一种穷凶极恶的疾病。但一本好的科普书的价值就在,它会按照自然的时间顺序,带着读者一起去了解这种可怕疾病的进化,同时了解人类对它的认知的发展。与此同时,它没有预设任何背景科学知识,我们就和埃及人或者古希腊人一样,从一片空白的状态开始认识这样一种疾病。
假设我们现在就是古希腊人,知道有这样一种病。但我们没有显微镜,看不到细胞,就自己诌出一套体液的解释:癌症是黑胆汁淤积滞涨所致,因为这种粘稠的体液无从宣泄,所以凝结成纠结的肿块。由于当时没有麻醉药和抗生素,手术并不被推荐,医生就尝试用各种千奇百怪的药物来治疗:铅制剂、野猪齿、螃蟹糊等等。
后来到了18世纪,随着解剖学的发展,医生开始在肿瘤里找啊找,就是找不到所谓的黑胆汁,于是人类终于相信体液这种解释是走不通的。而随着消毒和麻醉两项技术的突破,手术从中世纪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开始成为治疗肿瘤的主要方法。但有些时候一次手术并不能解决问题,有的时候手术完了病症还要复发,医生就开始思考了,这是为什么呢?于是19世纪一个叫霍尔斯特德的外科医生横空出世,开始引领更为激进的手术方式,比如在乳腺癌手术中不仅要切除乳房,连锁骨的腺体、腋窝下的淋巴结乃至胸腔里的其它组织也一并切除,目的是用激进的方式把癌细胞清楚干净,从而彻底“根治”癌症。然而付出巨大代价接受这种根治手术的女性,有些最终仍然会癌症复发并且死亡。并且随着统计手段的发展,数据也显示这种根治手术并没有显著提高治愈率。于是,在试错与代价中,人类终于发现,癌症是可以转移的,而手术只对局部癌症有较好效果,而对于那些已经转移的癌症则无法阻止癌细胞的卷土重来。
人类需要其他治疗方法。19世纪末,伦琴发现了通过射线可以看到人体的内部构造,他把这种无法命名的能量叫做X光,在此基础上科学家又探索出X射线能具有选择性杀灭快速分裂细胞的能力,于是用于治疗癌症。但是这种放疗对已转移的肿瘤效果也有限,同时辐射还有可能造成新的癌变。研究者于是又转向其它一些途径,比如他们发现一些化学品可以抑制细胞分裂,有些可以杀死骨髓中快速增殖的细胞,医生于是用这些以毒攻毒的办法去试图消灭癌细胞,取得了部分成效,但终究无法阻止后者卷土重来。
在沮丧和挫败中,科学家们开始追本溯源,决定回到问题的原点,先了解癌症形成的病理成因。虽然癌症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一种族类的疾病,但它们都表现出细胞不受控制异常分裂的现象,而攻克它的前提就在于从根本上了解这种病理性增值的原因。研究者先尝试确定致癌物,又努力探索了病毒诱发癌症的可能性,希望搭建起足够严密的因果联系。最终人类得出了一个确定的答案:癌症不是由外源性病毒引起的,而是通过激活内源性的(致癌)基因而引起的。而治疗的方式,也从而从试图消灭癌细胞,到控制那些促成细胞病态疯狂分裂的基因,也就是所谓的靶向治疗。
然而了解了癌症的基因致病原理也无法让人松一口气,即便是面对靶向治疗,癌细胞仍然可以产生新的突变,不断演化,改变致病基因和通道,让原先的靶向失去靶心。而靶向治疗也因此需要不断开发出第二代、第三代药物来应对这种无法预料的突变。癌症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扭曲的版本,但它更强大、适应能力更强,更像自然选择里的终极胜者。人类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红皇后一样,需要不断地奔跑,才能停留在能与癌细胞相对抗衡的空间里。
好的科普书究竟好在哪里
以上只是一个纯文科生非常笨拙而业余的概述,但是,也只有足够强大的书才能让一个文科小妹坚持看完,并且理出相对清晰的思路。
好的科普书首先表现为对一个普通人认知规律的尊重:所有人在学习之初都是一张白纸,而知识的普及也要从一张白纸开始,添砖加瓦,抽丝剥茧,循序渐进,深入浅出。比如古希腊人以为癌症是胆汁淤积,19世纪的英国医生以为白血病是血液化脓,这些都是在没有解剖学和细胞学基础上的一些猜测。而我们作为非专业的读者,对细胞的概念可能一知半解,也有可能一派茫然,这让我们和中世纪的医生没有太大区别。但也正是因为知识体系中没有预设,我们在读到那些困扰着先人的问题时,才能产生同样的“无知者”的兴趣——看着解剖学的先驱如何绞尽脑汁在人体内寻找胆汁而无果,细胞学的大师如何通过不懈的观察发现显微镜下那些疯狂分裂的变态细胞才是罪魁祸首。染色体、基因、逆转录、激酶,这些概念曾经在生物教材上一闪而过,看了又忘,就像一个你拼命想要记住可是下一次见了还是会脸盲的人。但在这本书里,它们都是在需要解释癌症诱因的问题时才引入的,癌细胞的前世今生和它们的结构、功能都息息相关,环环相扣。这些高冷的词汇,在通过这本书认识之后,你对它们可能依然不会了如指掌,但至少不会再心中茫然。
其次,好的科普书能够避开晦涩的概念把道理讲懂。就拿细胞“信号通路”来讲,度娘上的解释是:“信号通路是指能将细胞外的分子信号经细胞膜传入细胞内发挥效应的一系列酶促反应通路。各个信号通路中上游蛋白对下游蛋白活性的调节(包括激活或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添加或去除磷酸基团,从而改变下游蛋白的立体构象完成的。”这个解释我现在能大概看懂,但如果一本书都是这样写,我肯定坚持不了三页(英文估计两页)。而《众病之王》里是这样描述的:“基因能够编码蛋白,而蛋白通常起着迷你分子开关的作用,激活或者灭活其它的蛋白,就像打开或者关闭细胞内的分子开关一样。蛋白A打开了蛋白B的开关,后者又打开蛋白C的开关,同时关闭蛋白D的开关,而D又打开了E的开关……这种细胞里的连锁反应就叫做信号通路。”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这种区别,但是我真心希望我当年接触的第一本生物书是第二种写法。我始终认为如果要确立对一门学问的兴趣,不能一开始就用过多的术语把它同通俗的道理区分开来。相反,能够联想、推演、迁移的逻辑才能在学术的条条框框中留下进步的空间。当然啦,作为一个文科生,我的想法不一定对。
再者,好的科普书所普及的不仅是科学的概念,还有科学思考一个问题的方法。即便是这样一本针对普通大众的著作,在评价结果或量化进展时也遵循了严谨的论证规则。比如作者建议,在研究和比较群体的癌症治疗效果时,应该使用“年龄校正(age-adjusted)”之后的死亡率来代替存活率;又比如在论证吸烟致癌时,作者并没有简单列举吸烟人群与肺癌人群之间看似明显的相关性,而是详述了英国在医疗卫生国有化中对6万名注册医生吸烟行为和肺癌死亡人数的统计分析,原因就是因为后者完全符合病例对照和随机分配的原则,而正是因为对这些统计原则的坚持,又让他对20世纪后半段兴起的几轮大规模乳房X射线筛检的防治癌症作用,得出了相对保留的意见。
介绍这些实验和统计原则耗费的篇幅不短,但这些并不是一个学究的话痨,相反,这些思考和评测的方法甚至比科学原理更为重要,因为它们能从根本上引导大众去自己解答一些和癌症相关的普遍问题:“我这个年龄的癌症发病率有多高?”、“我是该戒烟还是抽得尽兴、活得潇洒?”、“我到底需不需要去做宫颈涂片检查或者乳房筛检?”。这些问题,科学家和医生有的时候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有的时候简单的答案也并不能让人安心。因此让更多的人了解得出这些问题答案的方法,让更多的人学会从确实的数据中提取出科学的结论,才能平息民粹思维的不安和躁动。苏珊·桑坦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曾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安抚想象力,而不是激发它。”当面对大家都担心的问题时,科学的思考方法可能最适合平息那种恐惧激发的想象。
科普和人文
这是一本癌症的传记,然而因为癌症发于人,它必然不能作为一个客观的物质独立于人的作用而存在。这一点,书中并没有忽视。
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就是记录了癌症作为一种公共议题在社会运动中的变迁。癌症本质上是一个医学问题,但它又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既然癌症危害到公众健康,那它就必然要被攻克,攻克它也必然需要调用公共资源。而如何攻克、如何定义形式、如何分配资源,则是多方角力,暗流涌动。一旦被推到大众视野,癌症就不再是科学上非黑即白的问题了。
书里记录的两次“运动”具有极佳的代表性。一次是由社会活动家玛丽·拉斯克策划的“对癌症宣战”,把攻克癌症提升为一场政治运动:有偶像、吉祥物、形象和口号,也有广告策略和宣传方法。这场运动中,白血病小患者被包装成能唤起举国同情的“海报”人物,同时还设计了极具煽动力的口号:“打赢抗癌战争!”。尽管这样的口号并不一定让科学家称心如意——他们指出战争式的口号带有极强的功利性指向,并不利于癌症的基础研究。但无论如何,癌症都不可避免地从科学研究的地下室转移到了公众的聚光灯下,并彻底改变了发展的轨迹:攻克癌症需要持续的关注、需要争取政府的拨款——它需要成为一个政治议题。书里这样评价道:任何疾病,想要提升到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就得进行推销,正像政治运动需要推销一样。一种疾病,要想实现在科学层面的转变,首先需要政治层面的转变。
第二次运动是由癌症患者发起的一次名为“行动起来(ACT UP)”的运动(艾滋病患者也发起过)。这是因为医药公司在取得研发突破后,通常需要较长的临床试验,药物才能获批并投入市场。然而生命垂危的癌症患者并没有资本等待,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根可能的救命稻草,迫切要求尝试这些在试验人群中已证实有效的药物。这是一种求生本能和研发规则间的尖锐冲突,激动的患者曾经结队游行到开发出赫赛汀的基因泰克公司之内,要求将救命药品开放使用。和他们对峙的不仅有制药商,还有坚持必须完成对照试验的科学研究者。最后双发的利益代表达成了一定妥协,制药公司扩大试验范围,病人则通过随机抽取参与试验。
这些运动是很难去做道德判断的,有些故事读来甚至让人唏嘘。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癌症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而它牵连出来的社会问题也同样不简单。
以史诗的名义
一本普利策获奖著作是需要一些额外魅力的。《众病之王》的这种魅力就在于,它在用严肃的事实冲击人心之外,还同样用温情的语言来抚慰人心。
翻一翻这本书就明白了,每一小节的开篇都摘录了一段或是几段引言,它们有的是诗作,有的是语录,时而沉重,时而讽刺,偶尔幽默,但都能一把抓住章节的要旨。它们可以来自英国诗人威廉·布雷克,来自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甚至还来自伍迪艾伦。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些章前摘录的话,它仿佛是在告诉我们,虽然疾病是冰冷的、不容置喙的事实,但人类的情感却是具象的、有温度的另一种现实。
这种用情同样见诸于作者的笔端。在翻开书之前,我很难想象一个肿瘤学家能有如此丰富的词汇和丰沛的情感。他在开篇就表示,他希望把癌症这个传记主角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对象,而他也做到了。他可以像编一本年鉴一样只记录没有瑕疵也没有起伏的事实,但他没有——他要带我们去领略历史的惊涛骇浪。
他对病人的描写也是极其用心的,既有不输给文学巨匠的细腻笔触,又带着科学研究者的克制与冷静。他在书中写道:“我们就像河里的石头一样,与癌症的遭遇冲去了我们的棱角,把我们磨光,磨亮。”可是即便这样,他对病人的刻画依然让人动容,字里行间依然溢满了本能的悲悯。他这种大气而温婉的行文似乎在提醒我们,每种癌症背后都是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每张面孔背后都代表着与这种千年恶疾不屈不挠抗争的物种。
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认为科学家是不苟言笑的,心里除了实验和数据什么也装不下,顶多装个谢耳朵。但是本书的作者Siddhartha Mukherjee显然向我们证明,除了描绘病理那一丝不苟的构造之外,科学家也同样可以描绘在和“众病之王”抗争的过程中,内心那翻江倒海、百感交集的风景。更有甚者,发现逆转录病毒癌基因细胞的诺贝尔得主Harold Varmus在学医之前,本身就是主修中世纪文学的。他在领取诺贝尔奖的感言中还改述了古诗《BEOWULF》中的诗句(是的,同志们,就是咱们英美文学教材第一页那首):
We have not slain our enemy
Or figuratively torn the limbs from his body
In our adventures
We have only seen our monsters more clearly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这种略带悲壮的意志可能贯穿着他们的日常,贯穿着所有的单调与重复,贯穿着所有的绝谷和希望。
以沉重开篇,以沉重收尾,有的时候都不想翻开,但它却又那么引人入胜。
它可能是最好的科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