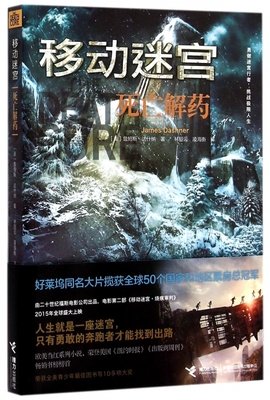《罗斯哈尔德》是一本由[德] 赫尔曼·黑塞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21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罗斯哈尔德》读后感(一):ROSHALDE
《罗斯哈尔德》发表于1914年,这个时候黑塞的儿子得了精神病,因而小说中的维古拉特所遭遇的困境,或许也是黑塞自己的写照,虽然儿子的病情不如比埃尔如此严重,但对于疾病的恐慌是一样的。
也正因为这样,使得小说带有很强的自传性质,虽然无法猜测这个时期黑塞与自己妻子的感情如何,但维古拉特和阿黛乐的婚姻危机,以及之后不久黑塞与自己妻子的离婚,期间的联系始终带有必然性。所以此时黑塞很苦闷,战争、国家、疾病和家庭,所有的困境都集中到了自己的身上,并且外人又无从分担,于是大概只能借助写作抒发忧闷吧。
《罗斯哈尔德》在另一方面也宣示了黑塞自己的某种心情,他希望自己能在生与死之间交汇的那个永恒的瞬间,找到一种归属感和爱,因为那就是生命最强大的力量。维古拉特在比埃尔死时有这样的感悟:这一刻他才能真正拥有自己千辛万苦所争取的东西,而在比埃尔死后为他画的肖像也说明了宗教会衰亡,生命会衰亡,但是只有艺术不会,绘画、音乐、文学,从《盖特路德》到《罗斯哈尔德》,HESSE一直宣告的也就是这一主题。最后,维古拉特带着自己简单的绘画工具和那幅肖像只身前往印度,并如同卸下了所有的负担,真正体会到青春之后的成熟,也可以说是HESSE的心声:他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一生,最后的归属即艺术。
《罗斯哈尔德》读后感(二):简简单单也很美
这本《罗斯哈尔德》是我看的黑塞的第六本书了。故事一点也不复杂,人物也不多,依然是黑塞那种优美的风格。虽然主人公的家庭生活是寂寞的,与妻子的关系是冷淡的,可是想想那个如世外桃源一般的庄园,生活也应该是很美好的。也许对主人公来说,有些矛盾毕竟是很难避免和消除的,这也是主人公为何一直处于压抑与痛苦之中的原因吧。
从黑塞的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对音乐、绘画、宗教等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了解,知识相当渊博。只是在这本书里,小儿子死于脑膜炎觉得有些疑问。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抗生素更没有疫苗,所以造成了死亡的悲剧。
另外,这本书的简介和正文中主人公的名字竟然不一致,不知道算不算错误。
看书的时候,我猜测是否作者的真实生活就是这样——长期和妻子处于心灵远离的状态,孩子是他俗世生活唯一的寄托,唯一的羁绊?
果然如此,本书210页的附录写着:“1914年,小说《罗斯哈尔德》由菲舍尔出版社出版,儿子马丁患精神方面的疾病”。1919年,家庭破碎,在与精神病院的妻子分居,孩子托友人和亲戚照顾。1927年,黑塞50岁生日,与露特·温格离婚。
看来,作者对这一切是早有预感的。作为两人之间唯一纽带的孩子,必将失去他的吸引力,导致婚姻的分崩离析。
黑塞本人大概也如维拉古特一般,除了追求艺术已经心无旁骛。生活如行尸走肉。对待妻子和破碎的婚姻既有内疚又无力。
《罗斯哈尔德》读后感(四):走过生命的缤纷之园
查阅了一下读书笔记,整好是三年前的今天(20100802)我第一次阅读到赫尔曼·黑塞的著作——《悉达多》(我要向您推荐这本书,如果你也在为你的灵魂寻找出路的话)。由此,感受和倾听到作家心中那条“生命之河”汩汩流淌的声响。
在阅读过程中,时不时会遇到一些能与我们的心灵产生共鸣的作家,他们知道那些你似乎已经知道了的道理,他们说出那些你心中有、口中无的话来,按照木心先生说法就是你们彼此有“精神血统”,是“艺术亲人”。(《文学回忆录》003)
黑塞先生就是我“艺术亲人”,毛姆也是。
而这一次,是我和我久别的亲人的第二次相逢。
罗斯哈尔德是一座庄园的名字,住着约翰·维拉古特一家四口和他们的仆人,八英亩(约合3.2万平米,1英亩=6.07亩=4046.86平方米)的土地上除了主楼,还有草坪、马厩、菩提树园和栗子园。更令人羡慕的是,庄园里还有一处林中小湖。
男主人维拉古特是个画家,他很有名气,可他并不在意他的名气;也很有钱,他也并不关心他的钱。 这样的人似乎永远都是他人羡慕甚至敬仰的对象,可惜的是,他的婚姻生活濒临死亡,和大儿子的关系也形同陌路,“几年来”一直过着“废墟般的生活”。(12)
如果从总体上来考量的话,没有谁的人生真正值得我们去羡慕。
与其说画家在艺术上是成功的,而在生活上是失败的;不如说是他因为生活上的失败,促成或者造就了艺术上的成功。
是“生活的凄凉和心灵自我折磨的深渊”让这个男人有了“难以抑制的创作渴望,每时每刻他都在感知中重新捕捉,征服这个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些缘故,“伟大的艺术作品常在安静的观看者心中激起一股奇妙的忧伤。”(72)
依我看,我们对自己的伴侣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太少推己及人的交流,这是婚姻关系中,矛盾的不断产生和无法顺利得到解决的原因所在。
亦舒说的,人们日常所犯最大的错误,是对陌生人太客气,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
其实婚姻最坚韧的纽带,真的就像杨澜说的那样——尽管我非常不喜欢她这个人,但这句话确实是听她说的:“婚姻最坚韧的纽带,不是孩子,不是金钱,而是精神上的共同成长。”
关于婚姻,于丹老师说的更为全面、具体,她说:谈到婚嫁,请一定对对方做好3个方面的评价:
1,你们精神生活上真的有默契吗?在价值观上有认同吗?他的气场是否罩得住你,让你有一种精神上深刻的依恋?爱情这东西不能替代一切,因为你们要过一辈子。一个特别爱钱和一个不太爱钱的人在一起,两个人会互相冲突;一个特别喜欢朋友和一个特别讨厌社交的人也没法协调。这些电光石火的契合非常重要。
2,你们的社会生活能否够融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但婚姻是两个社会群体的事。最好的婚姻就是融合,认同彼此的圈子,爱彼此的亲人,接纳彼此的朋友,因为有彼此,你们更爱这世界的一切,你们比以前更知道父母养育之恩的厚重,更知道要经营自己的朋友圈子,更知道得去世界上去做很多精彩的事。这种接纳,会让你感觉更有根,除了爱情还有恩情。
3,你们的性关系和谐吗?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男女之间的激情,取决于身体之间的融合程度。如果说你们的身体不默契,那你们可能不会直接把这件事说出来,但有点小事就会爆发战争。这也是婚姻的“七年之痒”甚至“三年之痒”的根由。
虽然我同样也不怎么喜欢这个女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她说的对极了。
这本书的封面侧页写到:“在家庭关系中,隔阂与恨意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很多情况下,在婚姻关系中掌握主导权的往往是女人,而男人在一阵短暂的狂暴之后总是不得不选择退缩,将恨意零存,在不久的将来被逼无奈地整取出来。就像作者在书中写的那样:“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力,她占了上风。当时我真恨她,这种恨意到现在还没完全消失。”(67)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说法: “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和50次掐死对方的想法。”
我想表达的是,在婚姻关系中,男人做出了牺牲,婚姻保护了女人的权利,限制了男人的自由。想当年,原始社会的时候,我们男人光着屁股满世界乱跑,该是何等的逍遥、快活、性福、自在呀!
这样美好的时光,估计也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再现,前者我们没赶上,后者我们赶不上,——悲剧啊!
虽然维拉古特先生“努力过,虽然他从未完全断绝渴望,但他依旧错过了生命的缤纷之园。”(204)
随着七岁幼子皮埃尔的病逝,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末路,“清醒的孤寂,冷静的表达趣味,不离不弃地追随那颗星辰——这便是他今后的命运。”(205)
或许,只有事业和友谊,才是我们男人真正的归属和幸福的源泉吧。
翻开阅读记录,惊讶地发现自己给黑塞的每本书都打上了五星,而且每次都是在深夜读完,比如失眠的昨夜,越是夜深浓时,越是无限投入其文字,夜色的罅隙在文字的闭合中越来越幽深,直至浑然忘我,在这个寒冷的冬夜,我再次和这个孤高清峻的灵魂对话,引导我思绪飞升,众多细微的感触如鲠在喉。
视线扫到第一页就被吸引,“园中只有年久失修的花园小径、遍布青苔的长椅、破旧不堪的台阶和荒草丛生的园子”这么一幅凄清冷落颓败的画面全景后,主人公的家世、职业立刻呈现眼前,读者很快沉浸到故事中。一个关系剑拔弩张的四口之家,彼此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维持着家庭最后的尊严和体面。盛名在外的画家父亲成日沉湎工作、忽视妻儿,母亲隐忍耐心、克己奉献,酷肖母亲、性格急躁、与父亲不和的长子,天真烂漫的次子是家庭唯一纽带,因为这个如花朵般娇嫩稚气的孩子,罗斯哈尔德作为他们的栖身之地能静静开放一隅,亦成为全家静心养息的精神避难所。
与暗流奔涌、岌岌可危的家庭关系相比,罗斯哈尔德如此静谧美丽!我热爱黑塞笔下细腻天然、淳朴灵动的景物描写,如果撇去情节,将这些曼妙句子拎出来,那也是本多么清新自然的散文集啊,就如他另一本《园圃之乐》那样,充满田园风味,饱满莹润的文字,仿佛能嗅到阳光明媚芬芳、黄昏明亮的重量、夏日鲜活的光线,他描写温暖多云的夜晚:“他一边品味着略微紧张、湿润而温热的深夜空气,一边小心翼翼地穿行在已长得根深叶茂的黑黝黝的麦田间,淡苍苍的夜幕中,庄园的树梢森然入眼,寂静无声。”他描写阳光下的花园:“这些声音和蜜蜂的翁明、鸟儿的啼鸣、丁香丛和豆花的绵绵不绝的厚重香气交织在一起…..听着随风飘来的孩子的轻柔声音,某一刻,他倏然觉得这一切来自他遥远的童年花园。”不得不说,要翻译黑塞,译者的中文功力要求非同一般,我看过的几本,文字拿捏都叫人满意。
这些诗意的描摹、对人性的洞察幽微、对爱情和理想的追求及幻灭,我曾在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高尔斯华绥《苹果树》、施笃姆《茵梦湖》还有蒲宁《故园》中,都能找到呼应和回声,而黑塞同样出色的心理场景也同样让我击节赞叹!幼子在被大人冷落后的孤寂:“一阵强烈的嫉妒和反感涌上了他的胸口,他顿时热泪盈眶…..他只想尝尽这些孤单和忧伤,真切感受痛楚的滋味。”一个和哥哥为争母爱的孩子背影恍然间拉长,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这种煎熬出来的文字,读来仿佛有小虫在吞噬五脏六腑,温柔地腐蚀着我,漫漫地湮没我,仿佛能听到锉刀在骨头上摩擦的声响,苦味浸到最后竟也能释然,这种体验,只有在读茨威格时才感受过,我如饮鸩止渴般完全沉没;而孩子不知道,每天相敬如宾的父母在各自天地里,承受着千疮百孔的婚姻,“肩负着如此阴暗的负担,忍受着漫长的痛苦岁月、失败的爱情和生活”他们在各自的痛苦里汲取着继续生存的养分和扭曲动力,只为了夺取一个纯洁灵魂的最后归属,当这个薄弱的纽带夭折,分崩离析的结局其实早已注定。
而结局是很有意思的,其实最终悲剧之前,主人公已经决定要和好友东游印度,以求精神解脱,最初的犹疑在长子回家后得到完全消除,他感到“一种深彻的活力贯穿了他的全身,仿佛少年时代的回归,在一种解脱的感恩情绪中,他又想起了远方的朋友……一种欲欲待发的行动意识和自我克制的力量流遍了全身。”第一有意思的是,很多西方文学中,精神上的苦闷和人性超脱,有靠苦行修身,有靠东历神游,在东方禅学佛性中领悟生命真谛、求得圆融共通,比如奈保尔、福斯特或毛姆的作品都有体现,当然黑塞他自己的《悉达多》也是这个主题;第二有意思的是,黑塞有严重的“同志”情结,他在相当多的作品里,都表达出对同性好友精神上的依赖和引领作用,如《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德米安》、《盖特露德》,主人公都有一个知识渊博、精神高洁、不懈追求的男性,在探索理想过程中扮演先知和永恒“女神”的角色,终于引领主人公渡过重重难关、达到理想的彼岸,把握到生命的命脉,真正超脱和解救。
所以,在漫长冬日选择黑塞温暖心灵或洗涤尘埃,会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那么,如果在冬夜,我也愿作一个旅人。
《罗斯哈尔德》读后感(六):你本该摇尾巴的
看「哀痛日记」的时候有种挥之不去的滑稽与荒谬——Roland Barthes 在直面“哀痛”这种人生最饱满、最丰盈的情绪时,竟然词穷至此?语言之贫乏、之单调、之沉闷,想象力之缺失、意志力之颓靡,真真切切只让我想起 Romain Gary 在「童年的许诺」一书中写的那样,像一只狗,爬到母亲的坟墓前哀嚎。
看完「罗斯哈尔德」,不耐烦地打了三星,它在黑塞所有让我敬仰的作品中格格不入——它在象征上如此薄弱,而在对现实的描述上却有如此苍白单调。尔后才发现,竟是黑塞一本自传性的小说——他患有精神病的儿子,还有他当时的痛苦。
于是一切都明白了。
这本书的失败不是黑塞的失败,而是人性与天性的悖论:情绪渴望被言说,当做直接经验被传授;然而情绪却如死神,如黑洞,不可直面,不可描述,只能像猫狗摇晃一条尾巴,被间接传递。至少用一根尾巴,还能玩出一些花样来,而若直直瞪入痛苦与绝望并企图张口描述,那么目瞪口呆只能看起来像个傻子。
因此,用象征手法表现痛苦上,黑塞彻彻底底失败了。他没有拦住自己渴望说话的情绪,他本该摇尾巴的。
《罗斯哈尔德》读后感(七):中年危机
罗斯哈尔德,究竟是主人公的住宅呢?还是一种精神状态。 个人认为是后一种,是一种“中年危机”的生活精神状态。主人公是一位画家,事业上也算一帆风顺,可是夫妻生活上已名存实亡。只是因为小儿子的存在勉强维持着。夫妻两个在暗地里争夺小儿子,丈夫虽然知道小儿子终会象大儿子一样被母亲“夺去”。可是依旧不放弃,想着多陪着几年。 一个远方来的好友惊醒了他,让他认识到世界还有别的,劝他一起去亚洲,一起去体验新世界。主人公心动了,这时小儿子生病并最终死亡了。在这期间夫妻的关系似乎恢复了(在大儿子过去也有过),这让主人公彻底解决了。他永远的离开了。 主人公是一个中年艺术家,这与黑塞的经历极为相似。如何应对中年危机,是为了孩子家庭责任等勉强维系,还是勇敢地选择离开。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容易决定的。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更难,因为他除了是一个人之外,还有着无法抑制的艺术激情。难道艺术家基本上不是好家庭成员(毕沙罗等少数除外)。黑塞的决定是不是主人公的决定。或者相反,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