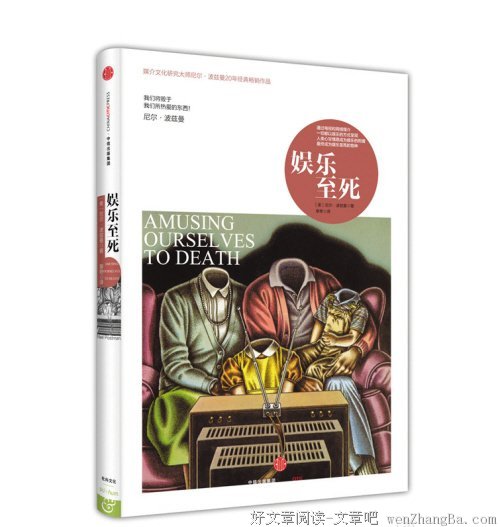《娱乐至死》是一本由[美]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2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娱乐至死》读后感(一):该警惕的不是娱乐,而是不得不娱乐
不久前,新华社官方微信推送了一条“9字简讯”——“刚刚,沙特王储被废了”。其正文也只有一句话:“沙特国王萨勒曼21日宣布,废除王储穆罕默德·本·纳伊夫,另立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新任王储”。这句话动用了3个编辑,还出了1个错别字。这则新闻在几分钟内阅读量就突破10万。其实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不是新闻本身,而是新华社纡尊降贵地与网民在评论区卖萌耍宝。
这不是电视节目,但照样娱乐至死。
如果沙特的国家通讯社仅仅以几十个字报道我国的天灾人祸,评论里都是一水地说编辑机智漂亮,不知道国人会作何感想。
早在1951年,麦克卢汉就预言了媒介发展将会使地球成为一个“村子”,地球上一切事情是在受众面前“同时”发生的,地球人就像过去的传统社会一样变成了近邻。
不幸的是,我们还远未做好当一个地球村村民的准备。每个个人的认知和行动资源远远没有增长到可以参与地球村的活动。事实上,我们可能连自己身边的事情都管不好,哪有精力去管在遥远的沙特王储被废黜了,在我们见都没见过某地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灾难?媒介使我们知道了事情的发生,但我们仍然没有精力去理解,也没有机制去行动。这是波茨曼所说的“行动与信息比降低”的根本原因——不是分子缩小了,是分母扩大了。
同理,波茨曼在书中第二部分列举的电视媒介对于商业、宗教、政治、教育的影响也是因为个人没有那么多认知资源去应付爆炸性增长的信息,故只能抓取那些一目了然,最好还能带点幽默的信息——既然我们无法行动、无法给事情带来什么变化,为什么不干脆只是图个乐呢,至少我们笑了啊。
纵观人类的媒介发展史,技术进步主要有两种趋势,一是传播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二是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前者令信息的来源广泛增加;后者则照顾了受众的每种感官。但这两种趋势充其量是“娱乐至死”的条件,而不是动机,真正的动机是大众媒体的商业机制。
大众媒体的目的是让你知道哪个政客更优秀,哪种产品更好用吗?不,大众媒体的产品仅仅是受众的注意力,在获得受众的注意力以后,将其按照性别、财富、爱好等等条件打包出售给企业和政党。大众传媒们在众多的消息中遴选最能吸引受众关注的事情,关于明星、可爱的动物之类的娱乐消息当然是最好不过。连印刷媒介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都会告诉你:你的新闻故事里最好能包含一只狗。一只被遗弃的小奶狗也许能比路边的冻饿之人更引起关注。
这种商业机制最可怕的是,不论是受众还是内容生产者都无法逃离其中。你知道作为一个新媒体从业者,要让读者千千万万免费的讯息中点开并且读完你的讯息有多难吗?用语要通俗、段落不能太长、人物最好是本来就很具有争议性的,但是你的观点又不能超出读者的接受范围。咪蒙倒是能写《阮籍诗歌与玄学本体论》,你我能看么?
这种商业机制最最可怕的,不仅是受众和生产者无法逃离,而是最后大家都忘了要逃离,反而认为娱乐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这年头,国家主席没有个漫画形象;教书匠不会两个段子;作者不会哗众取宠,你都不好意思出来让别人听你的观点。所以说娱乐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得不娱乐。
如果说除了波茨曼最后提及的学校教育以外,人们还有什么摆脱这种困局的希望——我想会是内容付费。
波茨曼所褒扬的印刷媒介之所以严肃,并非因为它是印刷的,读起来需要专注和理解而变得严肃。而是因为你本身就是出于获得知识的目的去购买它,其作者也是为了以令你有所收获的目的去写的。
获得知识是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的,如果能让人们的钱包也有此觉悟,想必效果会更加显著。
《娱乐至死》读后感(二):科技在进步,人类在退化。
以自由标榜的美国都有人关心:“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沃尔特·李普曼于1920)[1]”所以,我们所以为的可能真的仅仅是我们所以为的。之前试过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觉得很无聊没看下去。而《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一同出现在了《娱乐至死》中。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预言,一边是认为可能会有“老大哥”式的政府,另一边则是认为可能人类会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控制。在这本书之前,我以为注意力不集中,缺乏耐心是人性的一部分,在这本书之后,我觉得现代人的很多特点都要归因于不断迭代的科技。当然,正如波兹曼所反复强调的:技术本身没有错,但是这些技术给人类文化所带来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1]。
“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1]”我们可以从印刷机向电视的转变思考手机对我们文化的影响,但是新的科技总有一天会替代手机,我们的文化也会不断地改变。“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1]”也许这样的变更会越来越快,那么,我们应该何去何从?
1.媒介对文化的影响
“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1]”不仅仅是语言,也不仅仅是文化,人类用自己的方式在诠释和理解这个世界,大自然的规律没有理由被划分为物理、化学和生物,大自然的时间不一定非要被切割成秒和小时。自从学科被分割了之后,人类变得更加专研,同时也更加狭隘;自从时间被分割后,人类变再也感受不到永恒,从此被手表所奴役。
父权是私有制的衍生物,就好像散文是印刷机的衍生物一样。同样的,母系社会是因为最开始女性采摘果实的性价比高于男性狩猎的性价比。但是,随着捕猎手段的进步,慢慢地男性可以圈养一些动物。那么,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猎物应该是自己的,同样的道理,自己的孩子应该也是自己的。于是就与当时的权威抗争,将家长的权利夺取了过来。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1]”。“12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1]”
1.1.纯粹的口语时代
“在一个纯粹口语的社会里,人们非常看重记忆力,由于没有书面文字,人的大脑就必须发挥流动图书馆的作用。[1]”这个时代是人们为句子绞尽脑汁的时候。
1.2.“阐释年代”-印刷机的时代
“达到平衡之后的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1]”
文字是最能够表现思维和逻辑的一种方式,在印刷机的时代,话语更加清晰易懂,严肃而理性。而在电视的时代,语言开始变得荒唐;在手机的时代,语言开始变得不负责任。不是说铅字会就此没落,它会随着屏幕一起衍生下去,只是它所存在的意义跟印刷机的时代不再一样了。因为更加廉价,印刷术在某种程度上削减了阶级的差异,但也就是应为更加廉价,它让文字也变得廉价。自从印刷术的出现,诗歌便成为古人奇特的文化;那么,按照这个趋势,手机朋友圈里面的廉价软文,是不是会让文字进一步贬值?
“除了作为意义的载体,文字没有太多的好处。只不过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沃尔特·翁所说的“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1]”
1.3.“娱乐业时代”-电视时代
直到19世纪40年代,信息的传播还是无法超过信息传播者行进的速度,也就是火车的速度(35英里每小时),当时中国在打第一次战争,美国的各部分是一盘散沙[1]。后来塞缪尔•芬利•布尔斯•莫尔斯的电报消除了洲际界线,将统一美国话语变为可能,中国则步入了硝烟四起的近代时期。但是,电报的出现摧毁了信息原有的定义,导致大量无用信息的出现,让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花边新闻上。不仅如此,遭到电报攻击之后的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1]。信息的作用似乎不再是帮助人们做出决策,而是是否新奇有趣。甚至出现了很多时称“具有人情味的新闻”,只不过是加入了大量的性和犯罪的内容[1]。这样的内容甚至不要求实效性[1]。
在这个失去了语境,无法判断自相矛盾的世界里,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说明了信息多而无关,对人类决策没有任何帮助,大大减小了“信息—行动比”[1]。大多数新闻仅仅是成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1]。
1.4.躲躲猫的世界
公众人物不再关心自己可以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只关心自己可以给公众留下印象[1],甚至这样的印象如何都不重要。专业人士开始不关心如何担当起自己的职责,转而关心如何变得上镜[1]。于是,公众开始失去判断力,仅仅通过外貌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可信[1],通过新闻演播员的表情来判断新闻的严重程度,通过网友的言辞是否足够激烈来判断事情的严重性。
2.无孔不入的广告
在报纸出现之前,广告的影响力并没有这么大。即使是在报纸主导的印刷机时代,广告也仅仅是以精简的语言蜷缩在报纸的某一个角落[1]。“直到里维尔广告(也就是精简的广告)100年之后,广告商们才开始试图改变出版商要求的线形排版。直到19世纪末,广告才真正采用了现代的话语模式。即使在1890年,广告里仍然除了文字别无他物,广告被看作一项严肃而理性的事业,其目的是用文字形式传播信息、发表主张。[1]”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被亚当·斯密倍加赞扬的资本主义,也是被卡尔·马克思倍加职责的资本主义也在发展。慢慢地,到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的时候,人们意识到,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广告完全可以改变消费者的行为。“广告成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理性思维只好移师其他领域了。[1]”
“大多数广告都运用了“伪寓言”的文学形式来传递信息,同时也有广告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心理学原理: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快速解决的,它们的快速解决要借助工艺、技巧和化学。电视广告的主题是教我们应该怎样生活。[1]”
3.新时代的人格魅力
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够像几十年以前站在广场上听总统候选人长达六个小时的长篇大论。即使是政客也兼具了娱乐大众的功能,当代社会更加偏袒那些能够娱乐他人的人。
4.破碎的注意力
从电报的出现,人类第一次开始面对信息过剩问题,同时也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甚至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支离破碎的注意力问题。人们开始习惯快速地转变注意力,习惯无关的信息,于是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将世界拆碎的新闻人有时候试着将世界拼回去,但是讽刺的是,大众并不喜欢完整的世界。
“书籍就是收集、细察和组织分析信息观点的绝好容器。而电报只适合于传播容易被忘记的转瞬即逝的信息。”而看图片相对于看文字而言,甚至不需要理解。因为“照片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物体,而语言则把世界表现为一个概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事物不断进入我们的视野,不断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是的我们的世界变得没有连续性也没有意义,不要求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好像获取了很多信息,但是我们依然闭塞。社交网络使得这一问题更加恶化,因为在网络中,断交太容易了,我们慢慢地只跟自己喜欢的人交流,于是就更加闭塞。
而这一切的不连贯性在电视和手机中显得那么自然。
“我必须指出,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对于那些认为我在这里夸大其词的人,我可以引用罗伯特·麦克尼尔对电视新闻的描述来证明我的观点,他是《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的执行编辑兼联合主持人。他说,好的电视新闻要“一切以简短为宜,不要让观众有精神紧张之感,反之,要以富于变化和新奇的动作不断刺激观众的感官。你不必注意概念和角色,不要在同一个问题上多停留几秒”。[2]他还说,制作新闻节目的奥义是:“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须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准确的文字已经过时落伍。””
5.新时代的教育
有人试图用电视来教育大众,结果仅仅是娱乐大众。教育究竟能不能和娱乐联系到一起呢?手段会将一种东西转变为另一种东西,所以现在的知乎live、在线课程所达到的目的真的和预期的一样吗?
关心受众想要什么的越来越多,思考受众需要什么的却越来越少。“不论是释迦牟尼、摩西、耶稣还是穆罕默德、路德,从来没有哪个伟大的宗教领袖会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给的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东西。”
约翰•杜威曾经说过,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他在《经验与教育》中写道:“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
“美国可以被当作西方教育第三次危机中的一个典型例子。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那时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变更,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应该读一读柏拉图。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6世纪,印刷机的出现使欧洲发生了巨变,要了解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读一读约翰·洛克[3]。第三个阶段正发生在美国,这是电子革命,特别是电视机发明后产生的后果,要想了解其中的奥妙,我们应该读一读马歇尔·麦克卢汉。电视对教育哲学的主要贡献是它提出了教学和娱乐不可分的理念。”
“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参考文献
[1]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中信出版社, 2015.
《娱乐至死》读后感(三):娱乐是必须的,但不代表一切都可以被娱乐
1985年电视机已经成为美国家庭娱乐的主要项目,各式节目24小时不间断播出,波兹曼认为“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三十年后的中国情况类似。自从电视台商业化以来,为了能在收视率竞争中脱颖而出,节目娱乐化的倾向愈发强烈,尤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国内自产的娱乐节目多如牛毛,例如早期的答题比赛和综艺秀和近期的真人秀。但可以看或者说好看的节目却并不多,是我们的口味越来越刁钻,还是我们娱乐的兴趣下降?
“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原因在于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脱离。电视节目愈发的娱乐化形式,带动了其他领域话语形式的娱乐化,甚至“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了娱乐的包装”,最终内容被消解。娱乐之后再无可供回味的内容。
没有形式的内容太过干涩苦味,侃侃而谈的大道理没人愿意听;没有内容的形式太过空虚无聊,哈哈一笑之后还是寂寞孤独。好看的节目或者电影必须融合形式和内容,例如《黑客帝国》中创新的“子弹时间”镜头形式与计算机统治世界的思想内核,《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3D唯美的画面与在残酷现实和童话故事之间选择的思考。
波兹曼并不反对电视节目,毕竟它最大的好处在于“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只不过不应该将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形式扩展至其他各种领域,严肃的内容被挤压乃至被掩盖。因此,“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怎样看电视的方法”。
《娱乐至死》读后感(四):摘
20170820第一遍读完 萧伯纳:理智的人适应环境,而世上所有的进步都仰赖不理智的人。 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做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通过这种强大的暗示力,我们脑中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要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个事物:光是波,语言是一棵树,上帝是一个明智而可敬的人,大脑是被知识照亮的黑暗洞穴。
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内容。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赫胥黎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娱乐至死》读后感(五):《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第一章:媒介即隐喻。信息的载体(媒介)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息的内容,影响了信息的传播。媒介在改变着文化。媒介本身也是一种信息。例如人类从口头交流到书写,从广播到电视。
任何稍微了解人类交流历史的人都知道,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的诞生都会达到某种平衡,有得必有失,虽然这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有时是得大于失,有时是失大于得。我们在或毁或誉时要十分小心,因为未来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印刷术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刷术建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精英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情感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第二章:媒介即认识论。媒介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真理)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最后人们对于知识的理解。作者对于媒介的态度相当公正、开放,这一点很棒! 第三章: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印刷术如何影响了美国,从阅读到文化普及。铅字在人们心中的具有很高的地位,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为什么印刷机能如此广泛地影响美国社会,作者认为原因可能有:美国的新教传统、美国是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印刷品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 第四章: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人们用白纸黑字来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销售商品、创造文学和宣扬宗教。这种书面表达的特点是: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
第五章:躲猫猫的世界。电报如何改变了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
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受众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到处都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使得人们在信息的海洋里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电报可能已经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但这个社区却是奇怪的,因为这里住着一群彼此之间除了了解一些最表面的情况之外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电报生产了大量无关的信息,完全改变了“信息——行动比”。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听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在电报时代之前,信息——行动比基本是平衡的,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能够控制他们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感觉。人们了解的信息具有影响行动的价值。但在电报创造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有的一切都事关每个人。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我们可以说,电报对公众话语的贡献就是使它变得无聊而且无能。还不止这些,电报还使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用路易斯·芒福德的话来说就是,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在这方面,电报和印刷术截然相反。例如,书籍就是收集、细查和组织分析信息的绝好容器。写书、读书、讨论书的内容、判断书的价值,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文明人都会视焚书为反文化的罪恶行为。但是电报却要求我们烧毁它。如果用永恒、持续或连贯来衡量,电报就失去其价值。电报只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因为会有更多更新的信息很快取代它们。这些信息后浪推前浪地进出于人们的意识,不需要也不容许你稍加思索。第六章:娱乐业时代。电视带来的娱乐业时代。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例如,在电视辩论中,人们不再关心辩论者的观点,而是印象。
第七章:“好……现在”。电视本身决定了它的信息展示的形式,展示的方式又影响了其信息(一是娱乐化,一切都是表演,二是信息脱离了语境)。
每个人对于某个事件确实都有一些看法,但这些看法和 18 或 19 世纪的看法完全不同,也许称它们为“情绪”可能更合适些,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星期甚至每天这些看法都会改变的缘故。电视创造了一种“假信息”,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并不是电视在故意蒙蔽,而是信息包装成这种娱乐化形式时,它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是知识,我们该如何做呢?第八章:走向伯利恒。用宗教成为电视节目的例子(非常好的例子)说明了电视的这种形式是如何改变了传教士想要宣扬的内容: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为什么电视节目使得真正的宗教体验无法实现(为什么宗教仪式是重要的)?
……首先,我们无法神化电视节目播出的空间。任何传统的宗教仪式都要求,举行仪式的地方要具有某种程度的神圣性。教堂被设计成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所以几乎所有出现在那里的东西都具有宗教的氛围。但是宗教仪式并不一定都要在教堂里举行,只要事先进行一番净化,几乎任何地方都能胜任。所谓“净化”,就是说要除去它一切世俗的用途。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只要在墙上放一个十字架,火灾桌子上放一些蜡烛,或在醒目的地方放上一本《圣经》……但是,为了实现这个转换,一些行为规范是必须遵守的。例如,在这些地方不能吃东西或闲聊,必须戴上无檐便帽或在适当的时候跪下,按要求无声地静默。我们的行为要符合非世俗世界的规则。但在看电视宗教节目时,我们通常不会遵守这些规范。不论电视上是在播宗教节目还是在播电视剧《达拉斯》,我们都不会改变在自己的客厅、卧室或厨房里进行的活动。我们吃东西、聊天、上厕所、做俯卧撑或做看动画片时习惯做的任何事情。如果观众不能沉浸在非世俗世界的神秘氛围中,那他也就不可能获得一种超凡脱俗的宗教体验……电视屏幕本身也有着很明显的现世主义倾向。屏幕上充满了世俗的记忆,电视广告和娱乐节目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要想把它改造成一个神圣的地方显然是很困难的。而且,观众随时都会意识到,只要轻轻按一下遥控器,宗教节目就会马上变成完全不同的世俗节目……不管是历史还是电视的现实情况,都证明反省或精神超脱是不适合电视屏幕的。电视屏幕希望你记住的是,它的图像是你娱乐的源泉。下面这段话就更加明了了:
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教士,如果能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能够从一种媒介转化成另一种媒介的。如果你以为用某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东西可以毫不损害意义地用另一种形式表达出来,那你就过于天真了。很多散文可以成功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我们知道诗歌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许能够大致了解一首译诗,但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已经丧失了,特别是赋予诗歌美感的那种东西。通过翻译,它已经成为另一首诗歌。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也许发现送一张安慰卡给失去亲人的朋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认为卡片能够表达我们当面哽咽着说出的话的相同意思,那就自欺欺人了。卡片不仅改变了我们要说的话,而且还改变了赋予这些话意义的语境。同样,如果我们相信老师传授的知识可以用微型计算机更有效地复制出来,那么我们也是在欺骗自己。也许有的东西是可以复制的,但我们始终要问一个问题:复制过程中会丢失什么?答案可能是:一切赋予教育重要性的东西。第九章: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用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娱乐化的例子说明了赫胥黎语言的正确。美国宪法起草者担心的是可能存在的政府专制,《权利法案》规定政府不得限制信息和民众意见的流动。我们担心的是电视信息的过剩,而不是政府的限制;在公司国家(corrorate state)美国广播的信息面前,我们根本无力保护自己。作者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但并没有做太多悲观的推断;作者对政府“控制”电视进而“控制”言论的讨论不多,隐约模糊;由于国内的环境,我对本章内容感受不是很深切,毕竟我们还存在严格的审查制度。
第十章: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这一章讨论了我最关心的问题:当人们试图通过电视节目来做教学时,对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电视是如何定义了“什么是知识”,“怎样获取知识”?
对教育的一点浅见:哎,教育实在是一个太大、太重的问题。如何去教育小孩,教育自己?我会试图总结自己童年或过去的一些经历对于现在的影响,或许可以从中发现某些东西,这也是我极力劝母亲写下自己记忆的重要原因。教育是研究知识的传播的,小到从老师到学生,大到社会风气的形成。教育学是一种方法,教育应该是建立在认知规律上的,所以教育学的基础应该是脑科学、心理学、认知论以及社会学。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告。总结式讨论了为什么赫胥黎而非奥威尔的预言更会成为现实。将媒介扩大到了技术:没有技术是中性的,技术并非始终是文化的朋友。作者也提出一个“希望渺茫”的解决方式:学校。帮助年轻人解读文化中的象征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学生应该学会怎样疏远某些信息形式。我们希望学校应该把这样的任务纳入课程之中,甚至成为教育的中心。
问题不在于我们看什么电视,问题在于我们在看电视。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怎样看电视的方法。我相信我们有理由说,我们对于什么是电视还不甚了解,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是信息”和“信息怎样影响文化”这两个问题还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更不要说达成共识了……我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信息的形式、容量、速度和背景发生的变化意味着某种东西,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想得更多。什么是信息?它有那些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形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的知识、智慧和学习方法?每一种形式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作用?信息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有利于思维?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信息过剩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存在信息过剩?崭新的信息来源、传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样重新定义重要的文化意义?例如,电视会不会赋予“虔诚”、“爱国主义”和“隐私”一个新的意义?报纸所指的“大众”和电视所指的“大众”有什么区别?不同的信息形式如何决定它要表达的内容?通过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类似问题,美国人才可能和他们的电视机进行对话。……我这里的建议的解决方法也正是赫胥黎提出的。我无法超越他的智慧。他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样相信,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他不懈地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匆匆看完这本书,有下面几个感觉:一,如果把书中的电报、电视替换成微博、微信结论仍然成立,几十年过去了,信息越来越零散和过剩,碎片化的信息打断了人们的注意力,也造成许多的误解。二,本书让我认识到技术的变革会对社会和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讨论技术的变革对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自己太幼稚,确实读书太少)。三,本书让我害怕困惑但也更加想去了解。对电视、电影产生了恐惧……想去多读一些书籍,去了解教育、了解技术、了解宗教……
《娱乐至死》读后感(六):电视不一定是单刃剑
感觉中信这版中间有些地方翻译的不是很顺,没看原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但总有些地方感觉表达的不到位。作为90后,完全是娱乐的一代,不可否认的是电视的出现确实改变了我们对于信息接受的方式采纳,比如在看这本书时,我就曾不止一次的走神去玩手机,但若说这种方式一定是坏的吗,我觉得未必。从个体而言,电视的出现确实对于思想深度的挖掘弊大于利,很多仅以电视网络作为信息来源的人,其自身的素质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但从整体来看,电视无疑降低了民众接受基础教育的门槛,能最大程度的提高全民素质,这为个体之后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书中提到,教育应该是让人学会脱离现实,而现在的教育则让人学会适应现实。这个观点我之前倒没有考虑过,看到的时候觉得挺震惊的,在我记忆中,教育似乎一直在告诉我们如何生存,现在看来确实有几分实用主义的味道。不过若是一味的脱离现实显然也是不妥的,我觉得先适应现实,后改变现实,这样的曲线上升才比较符合教育的做法,即让以生存为目的的人学会如何适应现实,让以创造为目的人学会如何改变现实,这样的世界各司其职。
《娱乐至死》读后感(七):《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美]尼尔·波兹曼 著
章艳 译
中信出版社
2015年5月第1版
第一部分
第一章:媒介即隐喻
P5
1.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
2.在美国,最让人乏味的是那些专业的演员。
P6
3.我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P10
4.芒福德总结说:“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P13
5.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P17
第二章:媒介即认识论
1.书面文字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是客观世界,而不是某个个体。书面文字可以长久存在,而口头语言即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书面文字比口头语言更接近真理。
P24
2.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P28
3.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
P30
4.印刷术梳理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
P33
第三章: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1.也许我们可以说,美洲文学的滞后不是因为人们的惰性或英国文学的广发流行,而是因为缺少优质的纸张。
P42
第四章: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1.如果要传达意义,内容自然就要严肃。
P61
2.阅读从本质上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P62
3.哈佛大学是为了给基督教公理会培养教士而于1636年创立的。65年后,但公理会内部为教义争论不休时,耶鲁大学成立了,目的是为了纠正哈佛大学的松散风气。
P67
4.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
P78
第五章:躲猫猫的世界
1.电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
P81
2.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整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P84
3.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当然,这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
P94
第二部分
第六章:娱乐业时代
1.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可以换种说法: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
P106
2.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
P110
第七章:“好······现在”
1.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P125—126
2.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还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做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P128
第八章:走向伯利恒
1.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P149
第九章: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1.电视广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自《资本论》发表以来最猛烈的攻击。
P152
第十章: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1.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那时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变更,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应该读一读柏拉图。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6世纪,印刷机的出现使欧洲发生了巨变,要了解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读一读约翰·洛克。第三个阶段正发生在美国,这是电子革命,特别是电视机发明后产生的后果,要想了解其中的奥妙,我们应该读一读马歇尔·麦克卢汉。
P173
2.像字母和印刷机一样,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力。
P174
3.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P175
第十一章:赫胥黎的警告
1.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P185
2.他(赫胥黎)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P194
《娱乐至死》读后感(八):一本极为偏激的书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我一直认为香港警匪片=香港电影,这也是我喜欢港片的原因,从《无间道》至今,我几乎把所有的港片都看过了,如果看的细心的影迷朋友一定会发现《警察故事2013》跟《警察故事》《新警察故事》中的成龙并不是同一个成龙。故事是这样的,《警察故事2013》中的警察角色是大陆的警察角色,在剧本备案后才可开拍,审查中,因大陆对出版物的审核格外严格,其中一条是“警察”形象必须与真实警察保持一致性,不然片子会在审核环节被卡,所以剧组就被审查组派来的警察做了一对一的模仿,大陆警察有规定,必须不能留头发,所以,我们习惯duangduangduang的成龙的长发第一次被中国大陆警察剪成了板寸。
作者波兹曼比谁都了解,电视的出现和普及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文化结构的本质,每个时代的媒介都是在当下时代里的一种颠覆,这无疑成为了统治者最有利的政治手段,文字的出现让秦始皇有了“焚书坑儒”罗马有了《爱的艺术》,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有许多的古希腊书籍遭禁的例子。后来有了报纸,资讯第一次被打开,人们的需求的获捕讯息的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再到后来有了电报,电报让文字实现了即时性,除了即时之外,电报很快被取代了。如今电视把“文字+电报+图片”搬到人们的眼前,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这也是电视所擅长的,所以电视想尽办法以一种观众所喜爱的方式展现内容,电视所传导的正式“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甚至就连美国总统竞选的电视演讲也是如此,他们看中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非证明自己有多么牛的执政观点。
波兹曼也阐述了电视对教育的冲击,当我们理所应当的认为电视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时,往往会忽略电视带给我们的意义,像字母和印刷机一样,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利。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电视成了这个时代唯一的学前教育和启蒙,而这,是带有丰富的娱乐性的。
以上,是这本《娱乐至死》的作者波兹曼的及其有力的批判主义文字,可我并不是完全的服气,虽说这本书得到了不少名人和机构的肯定和赞扬。
我觉得多数地方太片面,偏激,这或许是作者批判主义的文字风格,也可能翻译有点傻逼,总之,作者给我的感受是一个被越来越快迭代的世界遗弃的传统主义理论家,我们常常在追寻新事物的同时思考当下、历史和未来,作者也像民初不肯剪辫子的遗老,怀念除了读书大众没得选的年代,选择多了就变成了世风日下。出生在只有印刷术时代的人,与出生在多媒体时代的人的思维方式一定不是因为媒体传播的介质而导致思想的鸿沟,这最多只是造成鸿沟的可能之一,而这种带来隔代思维鸿沟的有着上千上万种可能,另外,印刷术真的死了么?电视在如今互联网屏读的时代还能存活几年?十年前,我们所有的资讯都是编辑给我们的,而现在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知乎,微博,微信订阅号等种种的资讯早已经把编辑淘汰了,生成这些资讯的正式众包下的普通群众,我们每个人都生产微博,当然也都受益于微博,第一个播报某地发生地震的资讯不再是新闻联播,而是某某人的微博,而这个资讯的生成和传播跟编辑,审查,媒介,平台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小,我们思考当下的媒介给我们带来什么的同时,媒介本身就已经变化了。
《娱乐至死》读后感(九):你为什么不能放下
我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可是这并不能阻止人类吸烟的步伐;我们也都知道,沉溺于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之中,就像吸食鸦片一样,让人无法自拔、痛不欲生。可是,我们仍旧不能放下。
很多人甚至不愿意醒来。他们沉浸于信息时代带来的快感之中,怡然自得。对于他们来说,那是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思考和精神生活。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无疑是我本年度以来看过的最精彩的书,也解释了我心中积淀已久的困惑。
书内只是研究了以电视为主的媒体对人类的影响,证实了赫胥黎的“科技会让人毁灭”预言,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生存的现状有过之无不及。
学术人才的减少,虚拟产业的膨胀,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越来越多,值得抓住的友情、亲情、爱情越来越少……
文字成为我们拿来炫耀以及窥探的工具。朋友圈的生存现状基本上是:90%在晒,5%吐槽,还有5%的友情转发。
人类正手拉手,走向不自知的毁灭。
对于传媒业,尤其是新媒体,我产生了巨大的失望和担忧。这确乎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信息—行动比严重失衡的时代。只是我,突然不想再制造更多的信息垃圾了。
如果你只有半杯水,还不够自己止渴,怎么能够恩泽他人?跟不停地制造笑点比起来,这辈子,我只做好一件事,一件能引起人们的思考的事,就够了。
或许,你真的放不下9.9元的电影票、半价吃大餐、各式各样的一元游。
那么,就拼命地赚钱,狠狠地赚,直到你的物质基础强大到可以摆脱金钱上的束缚。
或许,你放不下的还有那虚弱的存在感、敏感的神经。但是,如果书籍和经历不能给你以存在感,那么手机更加不能。
用大把的时间,去爱、去思考、去在阳光下奔跑和跳跃。
《娱乐至死》读后感(十):一部信息匹配的經濟史
自古以來,人類一直在同一個天然的障礙抗爭:思想被禁錮在一個個軀殼之內。這就意味著,人類的交流只能藉助聲音、文字、圖像、軀體、材質等外在的東西。這就是媒介。
從對話到印刷品,到電報,到電視,到互聯網,人類一直在尋找更快、更便捷、更便宜的媒介。這是人類的剛需,也是媒介的使命。
相比口口相傳,印刷品突破了時間的限制。而後,電報的出現,第一次突破了地域(空間)的限制(在此之前,由於印刷成本的限制,那些所謂的「無用信息」出不了信息源那片地域)。再後,電視打破了以往靜態交互的方式。而互聯網不過是技術的演進,並沒有帶來什麼突破,它的建樹在於以近乎為零的成本,讓傳播信息這件事空前便捷,從而徹底佔據了人類的交互習慣。
然而,這場變革尚未完結,人類心心相通的願景還未見曙光。即使在那之後,人類也還得解決需求的高效匹配問題。早到小報上的廣告,再到當下人們視若自然的搜索引擎,直至時下火熱的共享經濟,人類追逐信息高效匹配的努力從未停止。
電視的出現,被作者視為一個拐點。在此之前,傳遞信息的媒介就像一張濾網,過濾掉噪音、八卦和無序。成本的制約把它們限制在一個個孤島之上,讓其慢慢消亡。在這這後,「無用信息」得到空前放大。與此同時,人類接受信息的速度第一次超過了處理信息的速度。
其實,並不是嚴肅信息被壓制,只是娛樂信息因為成本因素得不到聲張。正如作者所言,印刷品時代與電視時代的根本區別在於:前者因基於抽象符號而嚴肅、理性,而後者因依賴具象圖像而娛樂且感性。以文字為中心的文化依賴推理去認識世界,而以圖像為中心的文化倚重感受。
是的,普通人系統思考的能力受到了損害,思維變得一地雞毛,甚至「我們正逐漸失去對什麼是信息的能力」(作者語,p128)。
但,我並不像作者那樣悲觀。誠然,碎片化對於一個穩固結構的系統意味著崩塌,但對於一個能將碎片隨時隨地重組的動態系統而言,也許意味著交流、重構的成本得到巨幅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