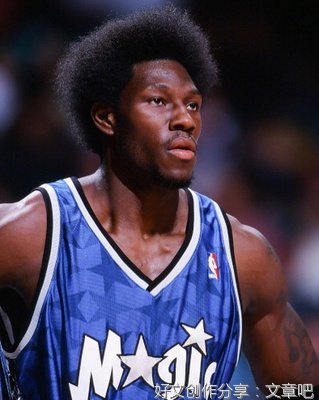
《大自然的收集者》是一本由[英] 彼得·雷比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5.00,页数:36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自然的收集者》读后感(一):...there is no more admirable character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Sir David Attenborough
反正这个号似乎是被系统当做是水军了,所以这篇书评应该也没人会看到吧,那我就随便写了。
作者把华莱士的一生如流水账一般地记录了下来:看完感觉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大事件,也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说的谈资。华莱士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平平淡淡,简简单单。
哪怕是他跟达尔文同时期发现了自然选择的定律,哪怕是他发现了马来群岛之间隐形的动物地理分界线,哪怕是他一生中收集了十余万件的动植物标本,哪怕是他接连荣获了 “达尔文奖章”“林奈金质奖章”“科普利奖章”“英国功绩勋章”和“皇家奖章” ,哪怕是他最后获得了探险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生物学家、科学哲学家、作家、社会活动家等一系列的头衔……但这些仿佛都只是别人故事中的一部分,是其他人传记中的一条脚注。
华莱士的本质,仅仅是那个钟情于“”一个完美的小生物“的野外博物学家。
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靠着跟哥哥一起学测绘的扎实技术,以及踏实好学的积极心态,脚踏实地地走上了博物收集的道路,并最终收获了一大批前沿科研圈的朋友。
他不擅长与人争辩,但但看到他对待自己的研究时异常固执地坚持己见时,显得十分可爱。而看到他对于惟灵论的沉迷,就仿佛看到了深陷传销骗局的邻居大爷一样,让人头疼又无奈。看到他写信给自己的女儿抱怨接连获奖后不想出席颁奖典礼的焦虑,而她的女儿写信给他吐槽他做事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拖延症太严重,真的是让人感觉好气又好笑。
他就是这样一个十分接地气的博物学家,一个走在我们前面的学者,一个在丛林中不断挥舞着捕虫网追逐蝴蝶的收集者。
但他又真的是一个十分伟大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一个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人。
...there is no more admirable character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ir David Attenborough
《大自然的收集者》读后感(二):读人物传记,图的是什么?
(这是一篇掏心掏肺的读后感)
我们小时候都被逼着读过伟人的故事,因为逼我们读的人希望我们也能成为伟人。但伟人很少,平凡人很多,我们就又被逼着做一些可能能把我们塑造成伟人的事情。
可是伟人是什么?为什么要成为伟人?成年了的你,心目中的伟人都有谁?你真正期待的自己,是被附上“伟人”标签的人吗?
至少我不是。生活压力重重,金钱、工作、爱情、亲情、友情上的得失似乎永远在怒号的波涛中沉浮,同时自己的世界又在不停翻新,新知识新技能新想法层出不穷。于是我期望的自己是一个既有能力(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甚至能帮到别人)、又有趣味(为了让自己过好,热爱现实世界)的人。做一个……有意思的人。这太难了。
华莱士可能是个伟人,但我想窥探他的一生是因为他是个有意思的人。作者从一堆上上世纪的书信记录里造出了一个华莱士投影,然后从出生到死亡播放了一遍,仅此而已,甚至不想强调他的伟大之处。没有小说的跌宕起伏,又比现实多了那么一点离奇。他的喜悦与苦恼都只是被平淡地描述了出来,读者却能在很多时候感到共鸣,正是因为他没有伟人光环,没有人粉饰过他的一生。一部关于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传记。
他善良又实诚,羞怯又执着。他大胆地把兴趣当成了职业并坚持了一生。他为自己的每一个小发现而惊喜,并毫无顾忌地将自己颠覆性的想法告之于众;他不考虑自己在学术圈的发展,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理论。作为后人的我一点儿都不在意他是否支持唯灵论,甚至因为这样的信仰给他带来了慰藉而感到欣慰。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和生存需求都不一样,谁也不能否定别人诚恳的信仰。这连犯错都算不上。一个人心中一旦建成了不可摇撼的根基那便不容生生摧毁。社会原本就是多样的,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包容和自己的让步。大概作者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只限于忠实的记录,不敢妄加任何评论。
华莱士的性格和为人,是我的一个不敢付诸实践的理想。我已经在变得愈发油滑,愈发为保全自己的发展而寻求折衷路线。
以前我还会为进化论全然归功于达尔文而替华莱士感到愤愤不平,现在想想……本人都没那么在意,我们有什么可斗争的?大概对他来说,理论发展比歌功颂德要重要上千百倍。
把他当伟人介绍给现在的孩子,我们大概会被孩子反问:“他辛苦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路险象环生,却既没换来荣华富贵,也没换来声名显赫,我们要跟他学什么?”哎,多有道理的质问!这颤颤巍巍的人生好在哪儿!
大概好在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身后名是别人的事情,与他无关。华莱士不是那种会被人捧上神坛的人,但若能在现世认识他,我一定会想跟他一起喝喝茶聊聊天,感受他那温柔的执着涓涓地流进心里。我要也能一直是我自己就好了。
所以读这样的人物传记,图的应该是能认识一个转瞬即逝,却又一直能在心底闪烁微光的朋友吧。
《大自然的收集者》读后感(三):华莱士和他的诸神时代
19世纪,似乎是一个“诸神时代”。
“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德意志,马克思开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远在美洲的林肯成为美国的第16任总统,废除了黑奴制;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改进点灯、发明留声机,贝尔发明了电话,莱特兄弟则让飞机飞上了天空;绘画艺术迎来印象主义,马奈、莫奈、塞尚的大名如雷贯耳;雨果、狄更斯、尼采、丁尼生、马克·吐温等一众作家,留下了彪炳千古的大作。
自然科学领域,也处于空前的爆炸式发展期。“交流电之父”迈克尔·法拉第首次提出电磁感应学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提出细胞学说,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出版于1859年的著作《物种起源》至今热度不减,160多年来不断刊行。我们看到“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字眼时,想到的也一定是达尔文。
但如果将时间回溯到1858年,也就是《物种起源》出版的前一年,我们会发现,“进化论”的署名者有两个,另外一个,正是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华莱士。他不仅是“进化论”的另一位“父亲”,达尔文能在一年后顺利写完并出版《物种起源》,也得益于华莱士在学术上的协助和精神上的激励。
阿尔弗雷德·华莱士,绝对称得上“诸神时代”的一位巨匠。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沦为进化论史上的一个注脚。传记《大自然的收集者》是对华莱士的追忆和一次公正客观的平反,呈现了这位博物学家波澜壮阔的一生。
从“收集者”说起
19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的余波未散,许多收藏家、自然学家、贵族热衷于海外动植物的收集,因利益驱动,也因为对世界的好奇心、对动植物学探索的狂热,许多职业“收集者”纷纷前往海外探险,当收集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通过海运方式送回欧洲,再由专门的经纪人进行推广和售卖。而且,在当时,许多新物种都会以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能够以这种方式流芳百世,即便是一只小小的甲虫,诱惑也令人难以抵挡。这些收集者的足迹遍布非洲、亚洲、南美洲、大洋洲,他们在旅行中展开研究,做出详尽的记录,将大量标本甚至活体动物运回欧洲,促成了博物学的空前繁荣。阿尔弗雷德·华莱士正是其中的一员。
1823年,华莱士出生于威尔士蒙茅斯郡的乡间。他的童年属于大自然,流连于溪边、田野、森林;他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野外进行测量和测绘,一边工作,一边研究和收集昆虫;他热爱阅读,擅长写作;他信仰公平正义,不仅热爱动植物,对“人”也十分感兴趣。这一切,都与探索海外动植物的潮流不谋而合。华莱士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个探险家。
终于,在1848年,25岁的华莱士正式成为职业的海外“收集者”,开始了为期4年的亚马孙河流域漫游,他捕猎、研究、记录、写作、制作标本,抵御猛兽和传染病的袭击,终于从“学徒”进阶成“博物学家”;1854年,华莱士已经小有名气,他又一次前往东南亚,航行14000多英里,展开了马来群岛的8年探险,最终带回120000余件标本。他的标本走进伦敦自然博物馆、剑桥自然博物馆等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他著作等身,你能在《亚马孙河与内格罗河游记》和《马来群岛自然科学考察记》里见证他探索的生动性和准确性;他独立提出了自然选择理论,与达尔文齐名,还创议了知名的“华莱士线”。他在险象环生的热带丛林里,证明了自己对自然科学的身体力行。
以华莱士名字命名的:幡羽极乐鸟(Semioptera wallacii)
以华莱士名字命名的:红鸟翼凤蝶(Ornithoptera croesus wallacei)
从“博物学家”说开去
英国博物学家杰拉德·德雷尔以《希腊三部曲》闻名,高分英剧《德雷尔一家》即由此改编。在英格兰,小杰拉德是成绩差、举止“不妥”的那类孩子。而到了希腊科孚岛之后,那里充满生命力的阳光和动植物打开了一扇另类的大门,培育了他对生命的好奇心与热情。
大自然永远都是最好的老师。她慷慨之至,给人以美景和生趣,也给人似乎永远都用不完的能量,让人探索成瘾,放眼大千世界,也反躬自省。
华莱士一生都在博“物”。他从大自然中获取知识、财富,习得一身本领,也将自己的探索欲延伸到了其他领域以及人类社会本身,这让他在“博物学家”之外,又获得了各式头衔:探险家、作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在野外收集工作的过程中,他画得一手漂亮的素描,也是登山、打猎的好手;他记录了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方言、印尼阿鲁岛人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表达过对婆罗洲迪雅克人道德品质的钦佩之情,考察了海外的殖民体系和政治制度,还在进行博物学研究和收集的同时,开展了大量的地理调查和测量工作,由此发现了亚洲与大洋洲的生物区分界线,奠定了生物地理学的根基,提出了著名的“华莱士线”——这条隐形的界限将两边的生物(不仅仅是动植物,还有人种)分开,界线以西接近东南亚的生物相,界线以东则接近新几内亚的生物相。
华莱士还是一个合格的旅行家,能通过他人的目光来看自己,无论他们是南美洲的印第安人,还是印尼阿鲁岛上的土著。他着迷于当地人的衣着、舞蹈和生活方式,也能立刻认识到,在异域,他自己才是异类,是被观赏的对象这种平等的、不居高临下的心态,或许是他能迅速融入陌生环境、顺利开展收集和研究工作的原因。
博物学是一门人人都可以接触和实践的学科,但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博物学家,除了善于观察,还需要情感的渗透,要与自然建立对话。几十年间,华莱士深入热带丛林,但他从不把自己视作主宰,也从不清高地旁观,相比自然选择等理论带来的荣耀,他更享受自然界及其美丽生物带来的愉悦。从某种程度上说,浓厚的兴趣,或许也是一种天赋吧。
华莱士手绘的隆头翼甲鲶(Ancistrus gibbiceps)
华莱士手绘的飞蛙(Rhacophorus nigropalmatus)
孜孜不倦的“多面体”
1862年,39岁的华莱士结束海外的收集和研究工作,荣归故里。读到这里,传记篇幅将将过半。与前半生作为海外“收集者”的峥嵘岁月相比,回到英国的华莱士仍然孜孜不倦。
华莱士将关注点从动植物更多地转向了“人”。他提出,物种和变种定律不仅适用于动物界,也适用于人类,并发表了两篇影响深远的论文《马来群岛上的人的变种》、《从自然选择理论看人种的起源》。由此,华莱士的理论开始与达尔文产生分歧——他进一步认为,自然选择在人身上产生的作用不同于动物。人类的精神、智慧和道德,是这个世界上的独特现象,无法由任何演化定律而产生,它们源自“一个未知的原因”。出于个人激进的科学信仰和痛失爱子的原因,华莱士开始参加降神会,成为唯灵论的代表人物,在基督派保守阵营和进化论派之间两头不讨好。这破坏了他早先取得的声望,最终成为进化论发展史上的一个注脚,显得无足轻重。
即便如此,华莱士的后半生仍然功绩卓著,精彩异常。他整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并为其做注释——大约有3000多张鸟皮、20000只甲虫和7000种蝴蝶;他为动物学会和林奈学会撰写了不少论文,出版了自己的两部大部头作品——《动物的地理分布》和《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他受邀四处讲座,足迹远至美国,他见识了美国的权力压倒正义和美元霸权,开始反思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成为社会主义家、人道主义者,开始关注土地改革和环境保护议题,关注妇女的生存困境和女性权利,支持个人选举权,提倡土地国有化,提倡机会均等,提倡教育的普及,反对军国主义和死刑制度;他甚至是一个激进的疫苗接种反对者,谴责强制接种,认为这侵犯了人类的自由和健康,还会让国家和富裕阶层忽视疾病的社会根源,即贫穷、拥挤和不卫生的条件。他总是在思考“未来”。
华莱士还是一个“造房子”狂魔。回到英国后,他搬了许多次家,每到一处,都会对建筑进行重新设计和改建,种满奇花异草。一旦庄园四周的自然环境无法满足他的动植物学或地质学研究需要,或是多了新建筑、遮挡了阳光和风景,他就会远远躲开,寻觅一处新的世外桃源,将花草移植到新家,展开新的探索。
华莱士一家最后一次搬家,是在他80岁大寿之前的1902年。那是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多塞特郡的一座庄园,里面遍布着苹果树、梨树、栗子树、橡树,还有一棵古老而优美的冷杉。
华莱士最后的“世外桃源”——老果园庄园
至此,19世纪的“诸神时代”告一段落。
华莱士游历海外时的愿望终于实现——建一栋房子,打造一座花园,安顿下来,好好欣赏他收集的标本。
一个寻常,又多么难得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