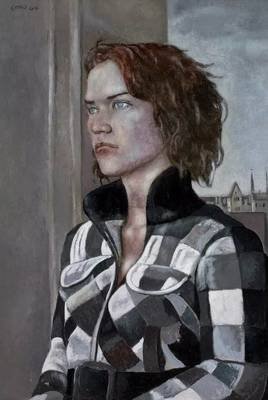
《美国女孩》是一部由阮凤仪执导,林嘉欣 / 庄凯勋 / 方郁婷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美国女孩》观后感(一):美国女孩
2003年,移民美国五年的莉莉因罹患乳癌,抱病带著两个女儿芳仪、芳安从洛杉矶回到新店,与疏离多年的丈夫宗辉团聚。芳仪因为中文障碍在班上成绩严重落后,被同学戏称为“美国女孩”。横衝直撞的她面对母亲生病深感无力,最渴望的就是回到美国。随时担心癌症恶化的莉莉不能谅解芳仪的各种叛逆行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张关係一触即发。在文化衝突、经济、疾病等压力之下,莉莉与芳仪的衝突节节升高,并在小女儿芳安于SARS期间被医院隔离时达到高峰。莉莉原本即将分崩离析的家庭,因一场意外的疫情被迫面对彼此的心结,进而获得重新开始的契机。
《美国女孩》观后感(二):是不是很多電影導演的第一部片都是在處理自己的家庭或成長?
當初來不及消化的感受、忽略的情緒,都透過創作來化解。
電影「美國女孩」中母女之間互動相處、對話衝突,我相信除了導演之外,也是很多母女生活的投射,非常真實自然。
飾演大女兒的15歲新人方郁婷指日可待,的確如文案寫的怪物級新人,演技精湛!本宮認為她未來會是影后不違和。驚鴻一瞥的張詩盈飾演的家長也很深刻,幾分鐘的對戲哪裡是配角的氣場!
無論年紀有多大,對母親自以為的了解,也可能會誤解,本宮當過女孩卻不曾為人母,看戲看電影,就是生活中最好的啟發。
《美国女孩》观后感(三):困境
《美国女孩》:8分
和《小伟》相比,同是处女作,将癌症给家庭的影响,这部《美国女孩》的难度更大,因为它也涉及了“海归”。可贵的是完成度也很高。大部分偏戏剧化的打光直到最后才有一些自然光,注重冷暖反差以烘托人的内心的情绪。
封闭镜头,固定镜头居多,表达人物的困境。而小伟用手持长镜头来传递焦虑感。
剧作:大女儿叛逆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很难适应台湾(用课堂的戏来体现),第二是责怪母亲当年不该不确定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美国(母亲和大姊说的自己当年也不确定,父亲说谁还没个America dream,母女吵架时大女儿说You always have a choice还有better is different),第三是恐惧自己将来会变成跟母亲一样的人,(包括演讲稿上Her fear will become my fear. Her weakness will become my weakness;父亲看见演讲稿,说“你真想去美国,我会送,但如果想逃避。。。”)还有就是一些细节,比如说美国的朋友Jessica,还有美国有马台湾没有马,台湾的网速不好之类的。这些细节都贯穿全片,有前后的铺垫。
父亲就是不相信母亲会死,想要给孩子最好的条件,并且过好当下每一天。
而母亲是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想到未来没有自己,孩子们会怎么跟父亲相处比较焦虑?所以他们几个老吵架。
相比之下,妹妹就是一个比较工具人的角色,起到解释的作用,比如说告诉姐姐,你只是想让你父母离婚,然后就回美国。得肺炎,再此计划一下矛盾。还有台湾学校里大女儿的好朋友和她聊天,大女儿交代出来的,也比较巧妙。
这些都是交替在一起,而且围绕着这个家庭讲,围绕着大女儿讲,时不时镜头到父母,但情绪是连贯的(焦虑、不确定),所以不会有错乱感。
p.s. 所以大姊是谁的姐姐?
《美国女孩》观后感(四):Different is better?
让我们来抓住主线:这是一个“美国”女孩回到台湾后,重新接纳父母和生活的故事。虽然如此,我却对两个孩子的成长没有太大感触,相对的,我更加心疼两个大人,尤其是爸爸。
自私、自大,我想用这些品格来概括我们的主人公(姐姐)应该没有问题。即使是身处叛逆期的年纪,她的所作所为在我看来也有些过了。自私,一心想要回美国,从来没有考虑过家里的经济情况和妈妈的身体。自大,刚回到台湾的时候,经常性地讲英文,在和同学老师相处时总是保持着高人一等的态度,这部分导致了她被排挤。身处这个年纪的小孩子,自我意识是非常强的,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地接纳他人的存在,这我是能部分理解的。但姐姐的行为,不可谓不幼稚,而妈妈在全职照顾她们两个期间,究竟有对孩子认知和性格培养上心了多少呢,我不敢太过高估。
妈妈,拥有大多数我们对孩子的爱,这种爱希望孩子们好,即使她们不一定认可。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爸爸带姐姐去买家具的时候,姐姐就反问了爸爸送她们去美国有考虑过她们的感受吗。妈妈的文化素养想必是不低的,但在育人上,虽然我也没有经验,但仍然不敢苟同。这种对孩子极端的爱,不仅束缚住了自身,同样也强加在了爸爸身上,再加上性子急躁,更加难免和姐姐发生冲突。
爸爸,一个对妈妈很爱,也爱孩子的男人。妈妈流露软弱的次数有点多,最明显的是妹妹被入院隔离,姐姐又吵架离家出走回来后,心忧仍一个人在医院的妹妹,在阳台上收着床单就抱着痛哭起来。爸爸作为家里的主心骨,流露压力的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抽烟来刻画的,唯一的一次,是坐在楼梯上沉默。其实电影里我最心疼爸爸,妈妈生病害怕自己不在了孩子怎么办,他必须强烈驳斥这种言论,只因整个家里所有人都可以彷徨,只有他不可以。妈妈一方面希望他帮家里换房子,但又不让他去深圳出差,这我是有点啼笑皆非的。爸爸最大的缺点在于对于身边的人不够体贴温柔,但很多时候很难强求一个人能够具备两种有些相反的优秀品格,我们都只是普通人啊。
妹妹,嗯,大部分时候充当一个工具人的角色,用来帮助场景起承转合。
除却核心的四个人物之外,在配角之中我最欣赏班主任。在我的朋友中,是有不少从事教师职业的人,从他们的生活中,我能够体会到教学事务带给他们的压力。在面对家长和学校的压力下,他们的本职工作只是完成教学任务,并不是每一个老师都会用心去关心学生。当然,我希望这种好老师,我希望这种需要不是总是被需要,因为很大程度上,是家长自己育人的任务没有完成,转移到了老师身上。我希望我们的家长们,对于自己的孩子,都能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因为我们的老师,也是普通人,也有自己的伴侣,也有自己的孩子。
《美国女孩》观后感(五):情绪勒索对这个家造成的伤害,比莉莉身上的癌细胞还来的凶猛。
已经在聊著元宇宙的我们,仍上演著和《美国女孩》那个年代一样的情节:因为病毒大家戴著口罩、无法自由的教育体制,还有在华人家庭中,无时无刻在上演的情绪勒索。
电影中的时代或许不是每个人都有共感,但电影中各种情绪勒索的手段,多少是大家生活中的一部分。在华人文化中,“顺从”是让社会体制运作的基本要素,而在社会体制中的最小单位“家庭”,“孝顺”更是让父母可以无限上纲、对子女进行情绪勒索的准则。
“那你当初干嘛带我们去美国?”
要你为他们的“用心”背负责任,是情绪勒索者最基本的开价。芳仪回到台湾后,去美国这件事反而成了原罪,她为了这个大人口中的“奖赏”,就必须当一个各方面都要表现优异的女儿。她不知道为什麽这样做就是为她好,为什麽她要为了这个没开口索求的事情负责,反倒是不懂她真正想要的脚踏车,妈妈为何不愿意买给她。
“你一个人生病,搞得好像全家都生病。”
放大自己的需求,并将压力和焦虑转移到别人身上,是情绪勒索者常见的行为。莉莉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生命威胁,还有化疗必经的痛苦,生心理的压力藉由情绪勒索转移到全家人身上。时不时的提到死亡,让爸爸宗辉无法逃避可能来临的天人永隔,还有照顾女儿的重担;想要让芳仪快点成长,这样她才可以放心离去,却让芳仪提早面对不在人生节拍上的变化;而家裡吵吵闹闹,让妹妹芳安意识到父母是不是即将离异。情绪勒索对这个家造成的伤害,比莉莉身上的癌细胞还来的凶猛。
“妈妈很爱你,你知道吗?”
情绪勒索者只在意自己想要得到的,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被亏欠,所以抱著受害者心态来回应这个世界。因为突如其来的重症,莉莉不得不放弃她的美国梦,回到台湾又要处理女儿在文化上的水土不服,重回老公身边让她得再重新适应生活,不知道怎麽处理压力的她,开始无法正确的表达爱。到头来她也被自己的情绪反勒索,觉得被命运亏待的她想著:“那最亲近的家人总该对我好一点吧?”,所以她将她的爱转化成一套标准强加在别人身上,只是勒索不成,反而得到家人的反抗。
“52分在美国是及格的吗?”
受美国教育的芳仪其实是情绪勒索的绝缘体,在叛逆期的她懂得反抗,并没有让莉莉的情绪勒索得逞,但两边的关係却因此更加紧绷。而且不只家庭,芳仪在学校的处境也有严重的文化衝突,学校有酸葡萄心理的同学、有害怕外来文化的家长、有不择手段追求成绩表现的老师(但夏于乔是一道光!),在学校遭到异样眼光看待,回家又要被妈妈勒索,此时的她无法回到美国,受伤的她只好隻身来到遥远的马场,去找她最喜欢的动物。
马象徵著自由不羁,也象徵芳仪在美国培养出来的性格。芳仪好不容易见到马,以为马会回应她的需求,结果却被抗拒,她没想到最喜欢的事物也已经不是她想像的样子了。连被老师和爸爸打的时候都没有屈服的她,却对马说了“I need you!”,是芳仪在电影中第一次请求别人,内心的脆弱在此时表露无遗。这场戏也是一个角色位置的互换,平常莉莉对待芳仪的方式,就像这边芳仪对马一样,都将自己的需求强加到别人身上,而同样的,都得不到对方的“顺从”。
莉莉和芳仪两位失落的美国女孩,最后收起彼此的锋芒依偎在一起,因为爱而展现的恶行,最后也只能用爱来弥补,家人不就是如此吗?那篇导演刻意留白的演讲稿,芳仪到底想跟莉莉说些什麽,好像也不是那麽重要了,因为它只是芳仪的一个手段,希望让妈妈可以好好的听她说话。在电影最后芳仪享受著我们儿时最喜欢的掏耳朵时光,就和妈妈来到它的演讲比赛听她说话一样,爱著彼此的心意用不同的形式(可能是更好的形式),相互交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