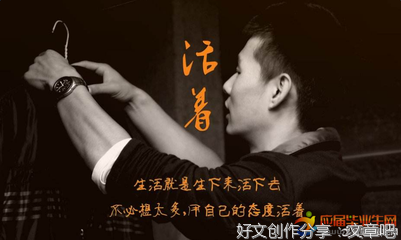
《休战》是一本由[乌拉圭] 马里奥·贝内德蒂著作,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页数:20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休战》读后感(一):欢迎举报
机翻痕迹严重,糟蹋了Benedett的作品。还是老话,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希望出版社至少找西语科班出身的译者翻译这些名家
一本叫《休战》的书,引起了战争;
一份由鲁迅创立的期刊,成了弄权的武器;
一群所谓的学者,高级知识分子,行径却似小人;
一封举报信,一封道歉信。
一滩臭水,一片寒心。
《休战》读后感(二):聊聊翻译问题
翻到书本第三页,2月15日星期五这篇日记的倒数第二段的第一个长句。
原文:En mi trabajo, lo insoportable no es la rutina; es el problema nuevo, el pedido sorpresivo de ese Directorio fantasmal que se esconde detrás de actas, disposiciones y aguinaldos, la urgencia con que se reclama un informe o un estado analítico o una previsión de recursos.
译文:在我的工作中,难以忍受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新的问题:有人出其不意地要求看那份藏在档案、条文和劳务酬金后面的幽灵般的通讯目录,一个急需一份报告或财务分析或资源预估的紧急情况。
这个Directorio,译者很想当然的把它翻译成了“通讯目录”,然而注意一下这个词首字母是大写的,再想想这个词的其他意思,也就是说有可能指的是某个具体的“领导机构”,再结合上下文了解“我”的在办公室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很容易明白这个Directorio是公司的领导机构,理事会一类的。所以根本没有人想看什么通讯目录,只是躲在那啥啥文书后面的公司理事会时不时来找“我”要这要那的。
这后半句更加离谱,明显就是译者完全理解不了这句话了干脆直接放弃治疗,你这句话跟你翻译的前半句有一丝一毫的关联吗?这一段真把我看麻了。
有时间再聊聊别的翻译问题。
————————————
本来想着今晚边看边把读不顺畅的地方划出来等看完后对照下原文,然而实在是太难读了许多地方我读个五六遍才能搞懂这个句子结构......因为这个译者处理长句的方法就是简单粗暴的直译,一些在西语里正常的结构完美复刻成中文后就会造成中文读者的阅读障碍,比如这句:
原文:Porque he aprendido que mis estados de preestallido no siempre conducen al estallido. A veces terminan en una lúcida humillación, en una aceptación irremediable de las circunstancias y sus diversas y agraviantes presiones.
译文:因为我已经明白,我的“前爆发”状态并非总是通往爆发。有时它会以一种清醒的耻辱感、一次对当下情况及其多样而恼人的压力别无他法的接受而宣告结束。
这句翻译放在专八那确实不太会扣分,但总感觉读着别扭。原因很简单,在西语原文中动词“结束terminan en”是放在句首的,因此西语阅读时句子结构就很清晰,即我的“前爆发”状态是结束于......,但翻译成中文就要思考了,你若是翻译成以....结束,那必然将会面临一长串定语造成的整个句子的割裂感,更何况你的翻译习惯特别喜欢用量词,这个“一次....的接受”又把我看麻了。
因为西语很忌讳重复,所以原文就用了“A veces terminan en...,en....”完整的应该是“A veces terminan en...,a veces terminan en....”但中文不一样,大大方方重复就完事了,“有时以...结束,有时以...结束”再润色润色就成了。甚至可以把名词“接受aceptación”改成动词来用,“有时它终于一种清醒的耻辱感,又或是在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状及......后宣告结束。”反正不管怎样把那个量词“一次”给我去喽。
书里类似的对长句的处理比比皆是,读着是真的吃力...
《休战》读后感(三):译后记
对马里奥·贝内德蒂来说,《休战》引起的反响颇为神秘。自1960年出版以来,这部日记体小说再版逾一百五十次,被译成近二十种语言,陆续被改编成广播剧、话剧、电视剧和电影,其中由阿根廷导演塞尔吉奥·雷南执导的同名电影曾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而在贝内德蒂最初的设想中,《休战》与他之前的作品一样,面向的是乌拉圭本国的读者,更确切地说,是蒙得维的亚本城的读者。
“乌拉圭是世界上唯一达到了共和国级别的办公室。”在与《休战》同年出版的杂文集《麦草尾巴的国家》中,贝内德蒂曾这样写道。看似戏言,实则是他亲身经历过的真实。在广阔的拉丁美洲,乌拉圭并不是显山露水的国家,但在上世纪初,这个弹丸小国却有“美洲的瑞士”之称,社会发展程度可与欧洲比肩。“二战”结束后,原本倚赖农牧产品出口的乌拉圭经济开始转型,国家层面上的工业化为民众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在一个无数人尚于动荡中求生存的年代,这样的生活,于外人看来是安稳的。
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还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公务员之城”。《休战》成书的年代,城中公务员的数量比伦敦足足多出三倍。不少职员会比上班时间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只为在当天的工作中抢到一把椅子,因为雇员的数量比椅子多得多。
寻求官僚主义的庇护,过稳定的生活,在当时的蒙得维的亚近乎宗教。即便自幼以写作为志业,在这座城市长大的贝内德蒂也未能偏离这条既定的轨道。他十四岁开始打零工,十六岁为糊口中断了学业,前半生从事过的工作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清单:在汽车零配件公司从学徒一路做到部门主管,曾任国家统计局的公务员,既当过出纳、速记员、房产中介会计,也是英语和德语翻译、记者、杂志主编。
例行公事保障了生活,却无法带来平静。看着身边一个个聪慧、敏感的人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逐渐黯淡,贝内德蒂感到持续的不安。安稳自然不是幸福的同义词,在波澜不惊的表象之下,人的内心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西西弗的神话》中“略带惊奇的厌倦”,也是《休战》的底色。年近半百的公司职员马丁·桑多梅打开了一个日记本,在临近退休的一年里记下生活中不足为外人道的瞬间。办公室生活的庸常与残酷,妻子去世后感情生活的长久空白,杂糅着爱意、隔阂与误解的亲子关系,与同事、友人日常交流中隐藏的暗涌……林林总总,拼贴起荒诞世界中孤独个人的情绪体验。
平凡却不平庸,又因为不平庸而无法平静。桑多梅被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消磨,却仍然珍视自己的感受力和精神世界;不善于表达情感,习惯了以面具示人,但始终相信真诚的价值;逃不出时代的局限,无法摒弃主流社会的偏见,同时又有独特的看世界的方式、过人的洞察力和反思精神。对一个足够敏感、又有能力拆解敏感的人而言,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面前履行职责、守住底限、保全真诚,不啻于一场苦战。
除了对存在意义的追问,《休战》的动人之处还在于对爱情的呈现。阿贝雅内达的出现,使桑多梅发现原来自己在情感上并未干涸。两个拥有清晰自我意识的人,思想碰撞时获得的满足,灵与肉相遇时发出的叹息,逐渐跨越年龄的鸿沟,改变对感情的不愿定义,克服旁人的偏见,甚至缓解了在世界面前的孤独感。而这份爱情也伴随着不安和犹疑,令人陷入更深的无助,几乎无可避免地带来失去——不是一个角色失去另一个角色,而是一个人失去另一个人。
在青年贝内德蒂笔下,日常生活是与虚无对抗的漫长战事,而爱情与爱情带来的真正的沟通,是生命中能够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休战带来的平静转瞬即逝,余下的是不知如何是好,是更深的疏离。这种疏离感无所谓克服,只能描述,只能追问。或许,这描述,这追问,是唯一可抚慰这孤独的。又或许,我们与世界最真实的关系,正倒映在这些四顾茫然的时刻和心生恐惧的瞬间,如同贝内德蒂多年后在诗中写的:
第一次读到《休战》是2012年的冬天,从书架上偶然抽出这本书时,并未想过它会带来如此强烈的情感体验。这不是之前熟悉的拉丁美洲文学,不痴迷于精巧的结构和繁复的文本游戏,没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遣词造句,但贝内德蒂平实准确的文字,犀利的笔触,以及字里行间对具体的人深挚的关心与理解,使我萌发了翻译这本书的愿望。感谢小艾,感谢作家出版社和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赵超老师,让《休战》的出版成为可能。也谢谢多年的邻居和好友Isabel,还有因疫情原因尚未谋面的两位乌拉圭朋友Celiar和Leopoldo,在我们居住的城市最惶然的日子里,仍然热情地为我答疑解惑。虽然桑多梅深信“每个人都只是地球上一个地方的人”,作为贝内德蒂的读者,始终期待他笔下的蒙得维的亚人走到我熟悉的人们身边。译文不足之处,还望读者诸君指正。
韩烨
2020年6月16日
于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