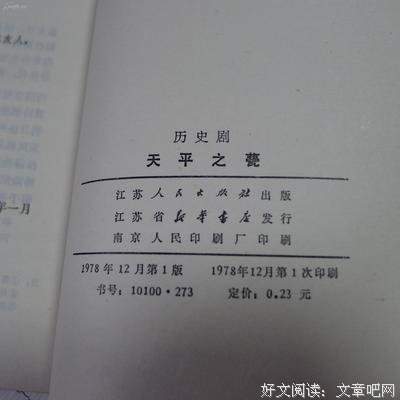
《天平之甍》是一本由[日] 井上靖著作,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1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天平之甍》读后感(一):有人看到盛唐,我却看到了人
读井上靖的书时会有一种感动,可能很多人感受到了盛唐的气质,我看到的却是人。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我们有多少虔诚信徒穿越大漠流沙,九死一生前往西域求取真经。从法显到玄奘,再到东渡扶桑传法的鉴真,他们都是一个个值得尊重的活生生的个体。从魏晋南北朝的乱世走向繁华大唐,他们拥有的自我信念,似乎与时代家国并不相干。也许,今天的我们应该更多地去追寻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将个体淹没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甚至漠视个体本身的价值。
《天平之甍》读后感(二):大世界中的小人物
书中的人物个性鲜明饱满。
介融:一直以来对在禅房书斋中读书表示怀疑,认为人世间的道理在世间,需要用双足丈量,他成为一名行脚僧,体味世间百态,不愿意再回日本。
荣睿:有强烈的使命感,为此消耗了生命。
普照:有使命感,性格上没有介融与荣睿那样刚烈,两人互相看不顺眼,但与普照都可以聊的来。
玄朗:同船四人中最年轻,性格上偏软弱。在唐娶妻生子,最后希望带妻儿返回故土,但因学无所成心中有愧,没有回日本。
业行:一个悲剧人物,花费数十载的时光抄写经书,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最终登上遣唐船踏上归国路,不幸与他抄写的经书葬身海底。
《天平之甍》读后感(三):翻译一般
原著五星,该译本四星。
第一章有几处翻译可再推敲,后渐入佳境。
第四页:“……玉生、铸生、细工生……”
“细工”应该即为日语『細工』,其实就是手工艺人,翻译照搬日语的汉字,不作注释,实在难以理解,难称良译。
另举几例。
第九页:“芦苇间点缀着无数的水路标,有几个上面栖有小鸟,其颜色之白令即将远处的异域的人印象至深。”
第十四页:“把船从山搬下谷,从谷搬上山。”
这几句译文,明显受到日语的语序和措辞的影响,(如读“其颜色之白令即将远处的异域的人印象至深”,立即联想到『その白さが〜させた』,典型的日式表达。)私以为作为中文不够“地道”,欢迎讨论。
《天平之甍》读后感(四):《天平之薨》
井上靖的著作,这是一本由史书而来的文学作品,是井上靖的好友给他的意见,于是这本书就应运而生了。天平是日本的国号,对应于中国就是唐朝玄宗时期,说的是日本遣唐使来中国求法,鉴真东渡的故事。文中的普照和尚为了请高僧去日本弘法,在唐土耗尽了半生。业行和尚日夜埋首典籍,为了抄录经文客居大唐五十年。而最后和鉴真、普照最后一次东渡的时候,所抄录的经文全部丧生大海,真是让人痛心,五十年心血付之东流。业行的恒心让人敬佩,文正公一生讲求一个“恒”,在业行上面正是这样的代表。鉴真大和尚不顾失明之苦,六次东渡,历经艰辛,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这是为了佛法,纵然大海茫茫,又何必吝惜性命。大家既然不去,那么我就去。”应了那句“山川异异域,风月通天。”井上靖的文风真的在高潮处突然停止,其余部分平淡如水,真是让人感觉心中很舒服。
《天平之甍》读后感(五):旷世逆旅的秉笔人
井上靖笔下的世界总是天残地缺,由世事与际遇的各种不如意,衬托着漂泊者的韧性与执念。若依我个人之见信口说来,内里是一个岛国作者,因置身于华夏版图上的广阔天地,而感到的空旷与疏离。
记得十几岁时就读过他的《杨贵妃》,题材是至为热闹的,但笔下总是疏离的态度,始终笼着一团郁郁的雾气。直至死亡,似乎得了解脱。
后来又读《敦煌》,开篇就是主角赵行德错过科试,漂泊西域,结识了爱人,却转而成为军阀的妾侍,继而坠崖自尽,到此差点就读不下去了。然而命运流转不可测度,手录经卷,终于在浩瀚的藏经洞中求得慰藉,求得一个并非也俗意义上的完满。
这本《天平之甍》,曾读过娄适夷先生的老版译本,是民国下来的老一派文风,恰当而圆通。但正因为圆通,似乎缺了几分苍凉悲切的气氛。但愿本版能超迈娄译,求得荒凉天地间的灵魂之完满。
《天平之甍》读后感(六):映照出一人、一国的孤独背影
本书对于日本留学僧的渡海之难,有着平实而动人的描写,仿佛眼前就看到了仰卧在船上的一干人等,寂寞的对谈几句又陷入寂静的场景。
普照入唐,并非一开始就坚定决心非要请到律师赴扶桑而去。而是通过他在唐的见闻,与日本留学僧们的交流和所见所感,各个人等的不同人生抉择,从而磨砺出了坚强的内心和坚定的信念。
对于鉴真大师的描写不多,但是勾勒出了坚毅勇敢、沉静智慧的肖像,如同剪影般留在了历史岁月中,令人难忘。
不过,对于鉴真大师、普照、业行等人的性格描写,可能是限于篇幅和史料,缺少一些更加鲜活的细节,对于他们的思想轨迹,并未细致地捕捉。与井上靖先生的《孔子》相比,缺少了一点点细腻。
延续了井上靖先生的一贯风格,有一些关于自然景色的描写,仿若出现在眼前,很有带入感。
如果是想了解鉴真大师的生平,恐怕会失望。但如果希望理解远隔茫茫大海的日本和日本人的所思所感,可以一读。
《天平之甍》读后感(七):《天平之甍》,文化的足音!
第二次从西安旅游归来,意外地在和一位日本学生交流中“认识”了井上靖,也由之而“遇见”了《天平之甍》。因此,无意中,也找到了了解中日历史的一个突破口――原来日本的奈良时代,正值中国的隋唐时代。对于两国共有的历史知识,我想也可以从这里开始深入了解。 “梦,又回长安”。想起两次的西安之旅,两次在华清池处叹历史悠悠、情愁凄凄。而看《天平之甍》时,又不自觉地再一次重新筑造了脑海里的长安城的样子。这一次的长安城,它有了中日僧侣的影子,佛学鼎盛的魅力! 书里面讲的是日本僧侣来中国留学,学习佛学知识,为的是把佛教引入日本,治理国家。所以书里出现了很多佛教典籍名字和专用术语,对于这一些,我知之甚少,也兴趣不浓。反而,在书中感受到的更多是中国和日本在这一段时期的民间交往关系的友好与密切;钦佩两国的先辈们,是他们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付出了毕生精力甚至自己的生命。 是啊!“一辈子只做好一件事”,不是心里的口号,而是灵魂深处的一份觉知。唤醒了这一份觉知,若在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粗浅的回答便是:用一辈子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且有意义的事!
《天平之甍》读后感(八):发愿与执行的众生
《天平之甍》读完第二遍,发愿与执行这个过程,在不同的人身上因为性格、价值观、际遇等的不同,所展示出来的不同轨迹让人慨叹,这是以人的一生为时间跨度的“传记性”小说能给人带来的独有观感,读“那不勒斯四部曲”是这样,这一本同样如此。
究竟怎样的人能走到最初发愿的终点?从来谨慎、似乎不曾铿锵昂扬过的普照反而成了最终完成志愿的人,戒融像一个左派愤青,走了“到群众中去”的“实践”之道,意志薄弱的玄朗恐怕是一生都为悔恨所缠绕,荣睿倒是与戒融性格很像,都是坚定于各自的志向之人,只是选择的道路不同,而最为人叹息的抄经者业行最终与献身一生的经卷同没于大海,他的一生如何评价?让人想起徒劳的西西弗斯。
而普照与荣睿二人的区别在于,荣睿很早便放弃了自己精进的努力,集中精力延请高僧,普照一边请师,一边仍然苦学,甚至也插手了业行的抄经工作,多线程任务最终都有所成绩,从结果看自然值得钦佩,只是这二十年的唐土生活中他必定也是伴着无数对自己的怀疑,一边前行的吧。
这一次没有读楼适夷版本时那么“享受”,感觉到文字的美感了。
《天平之甍》读后感(九):关于信念
也是一部中断后又捡起的小说,讲的是鉴真东渡的事情。
中断是因为,这本书着实难读。起先我觉得是翻译的问题,因为读井上靖的其他书都很平白,没有文绉绉的辞藻。读到后面渐渐意识到,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是专有的名词、事物实在也是很多,作者译者皆以史实叙述,一定程度上变得难读。而且作者所谓的小说化,其实更多的还是在记录,文学色彩一般,生动有趣不够。
但鉴真东渡事件本身就足以让人沉迷。书中未对鉴真进行大幅描写,更多的是在叙述中描写了众多留学僧、唐僧。每个人身上的故事都值得让人感慨。因为前面读的磕磕巴巴,印象不太深了,后面印象最深的就是业行和普照。普照终其一生终于得偿所愿,业行却身与经均葬于大海。也许是一辈子的执念吧,过于执着非要换船,最后一辈子的心血都毁于一旦。人要像普照那样坚持,形势不好时勇于蛰伏,不能如业行那般,执念会变成绝望。
鉴真大和尚的坚定让所有人都没想到,而弟子的追随也让人感动,众多磨难阻碍,自然的阻碍,人为的阻挠,最终还是要偷偷渡海,因缘巧合没有上第一艘船,福祸相倚最终抵达,还有持不同人生观的僧人们最终不同的结局,就真的让人感慨变化无常。
《天平之甍》读后感(十):传法者群像
日本历史小说家里,井上靖绝对是异类。《天平之甍》全书无一字废话,区区九万言,把奈良时代日本文化最突出的事件——鉴真东渡传法——前后几十年的渊源写完,对比司马辽太郎、山庄冈八动辄数十万言,乃至上百万言的写法,实在是古风犹存。 笔墨篇幅虽然都极简练,但普照、戒融、业行、玄朗、荣睿等遣唐学习僧的风貌、事迹、心境、追求,一一都在眼前了。 戒融是入世求法、行遍世间的行者,代表佛学中的实践精神和怀疑论者;荣睿为请律师东渡传法,矢志不渝,最终客死异乡,未见鉴真成行,代表佛学中精进勇猛的积极一面和求不得的无常;业行清楚的认识到自己力有不逮,无法通过学习将先进文明带回故土,于是穷极一生,抄写经卷,虽然外貌上只是一个矮小枯瘦的老僧,但在佛学上却象征着有十龙十象伟力的驮经力士;玄朗入唐之前充满对大唐的向往,希望日后学成回国,但经过多年艰苦枯燥的唐土生活,最终放弃了留学僧身份,娶妻生子,永别故国,是软弱又充满欲望和烦恼凡人形象;至于普照,在小说中是记录者,是旁观者,同是又是另一个业行、另一个玄朗、另一个戒融,另一个荣睿,是人性与佛性的矛盾综合体。他最终回到故国,完成引进先进文明的使命,成为鉴真在日本弘扬律法的重要推介者,则象征着连接佛陀与众生的阿罗汉。 所谓甍,即是古建筑两端的鸱尾。大唐的鸱尾经渤海国辗转来到奈良唐招提寺,加于大殿之上。从此凡入唐招提寺求律学者,无不顶礼瞻仰。而此时,大唐已从开篇的开元盛世来到天宝大乱。 2020年3月14日晨读讫,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