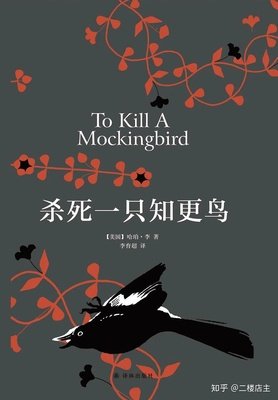
《大法官与总统的对决》是一本由[美]克利夫·斯隆 / 戴维·麦基恩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015-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法官与总统的对决》精选点评:
●有些人之所以伟大,在于能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通过自身的智慧和坚韧,开创历史。这本书是我读过的关于Marbury vs. Madison 这个著名案例的材料里最为细节详实和讲述透彻的一本。
●伟大的判决得益于行政权力的谦抑。
●为专业系列
●1
●案件的意义远超案件本身,此案是美国宪政制度的基石之一,使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并驾齐驱,最终形成三套马车共同促使美利坚合众国前进和发展~始终不能理解既然午夜法官的委任状已经制作好,为什么还有一部分没有发出去~
●因为《傲骨贤妻》与《尽头》,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尽管如此,仍然读得十分费劲,若不是拜前后延误了8小时的航班所赐,估计直到今天还没有读完,我已经变成一个成天看手机的人了%>_<%。很有趣的一本书,也不难读。真没想到美国初建国时也有过这么一段,也是一点点争来的啊。
●写的不错,能让一个对美国历史与观念没有太多了解的人看得懂,这便是深入浅出。且作者必然对于美国历史、政治、文化等等都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如此才能在适合的地方插入其他知识,而这些知识又是读者想要理解的必然辅助物。赞一个
●非常非常好看,翻译得也好,最后是激动兴奋得含泪读完判词。
●这一著名判例的原被告双方从未对判决留下任何评论,最为突出的是做出判决的马歇尔大法官,和判决本身的意义,运用了如此的智慧,在万难的政治纷争中突出重围,有理有力。当然了,判决本身近万字,挺磨叽的,还有,你会因此讨厌杰斐逊。
●案件审理流程先解决管辖权,此案奇葩在于其在最后,前两问证明总统违法马伯里有权获救济;最后一问将此抹干。最高法介入政争恶心共和党,加持联邦党,虚晃一枪。不过,其不光彩却带来司法上最华彩创举,这在《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描述的好:制度初创者不一定具有“神圣的光环”。
《大法官与总统的对决》读后感(一):Everything is earned, not given
人都有局限性,有些来源于人性,有些来自于时代。美国国父们纵然伟大,也会有 partisan,也会在那个时代认为人有阶级而非绝对平等。
但有远见的人,有包容的人,总能超脱于所处的时代,在决策是时候把私利放在一边,做出伟大之举。
而这个过程,不是静待,而是斗争和争取。
这是文明的胜利,和人的光辉。
《大法官与总统的对决》读后感(二):奋进的灾难
读书日记No.4《大法官与总统的对决:马伯里诉国务卿麦迪逊案》:这本书个人觉得有四大看点 其一,美国历史上首次民主选举产生国家总统的“灾难进程”,代表联邦党人利益的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与代表共和党人利益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的党争明争暗斗,危机四伏差点撕裂年轻的美国,酿成“二次革命”。 其二,一个牵扯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 剑指第三任总统杰斐逊 起诉国务卿麦迪逊(后第四任总统)的司法案件,过程此起彼伏,悬念不断,引人入胜。 其三,大法官马歇尔对马伯里诉国务卿麦迪逊案判决的神来之笔,即判定了麦迪逊和杰斐逊的行为违宪保障了司法的绝对权威,又避免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单从结果来看似起诉失败,但其实是美国司法权威的一次华丽转变。 其四,书中有许多亚当斯 杰斐逊 汉密尔顿等开国元勋的往来书信引用,算是小八卦,再厉害的人物,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大法官与总统的对决》读后感(三):很不错的案情历史介绍
本书主要是历史背景介绍,并不深究本案复杂的法理推证,法理推证和司法审查以及最高法是否独享最终宪法解释权这些,就得看其他大咖的书和论文,比如爱德华·考文。
美国司法第一案Marbury vs Madison 最全方位的纵深性历史呈现,以第一政党体系下的政党斗争为线索背景呈现案件,非常详细的来龙去脉,包括涉案人物、委托律师、起诉理由证据与庭审过程的呈现。
普通教科书只会提及本案马歇尔的三层分析,交代与违宪审查相关,较少给出更具体相关法案和政党斗争的沿革,尤其也缺少马歇尔判词中较大篇幅涉及行政法意义上的论述,这些论述交代了马歇尔力图回避当时反对者和舆论大加挞伐的司法权干预行政问题。
马歇尔不断重复最高法并非干政,也无意干政,但最高法必须保障公民既有的权利,总统一旦签发委任状,行政任命即完成,国务卿必须遵循法律送达委任状(不可无故扣留)。
本书更细节呈现出马歇尔庭审此案的各方面行动和遭遇困难,也展现了他的成长过程,也具体描述他受约翰亚当斯委任为大法官的故事。
马歇尔的成长过程真的很吸引人,他其实本也是有私心者,本无意担任公职。美国几个开国元勋,像华盛顿、亚当斯和麦迪逊都对他有栽培和提点,而马歇尔一辈子最厌恶杰斐逊。
让司法权站立起来,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或政治英雄塑造的偶然事件,无论汉密尔顿还是马歇尔,麦迪逊还是帕特里克·亨利,那一代人都有这样的理想,但是马歇尔身体力行将其落地生根。
伟大的思想者播种,杰出的政治家和法律人耕耘。共和国最伟大的财富莫过于梦想家和实干者的同时在场,一代人激励一代人,一个梦想唤醒更多的梦想。
《大法官与总统的对决》读后感(四):19年读书计划之九之《大法官与总统的对决:马伯里诉国务卿麦迪逊案》
《大法官与总统的对决》读后感(五):从马伯里案到布朗案——再看美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保守派的精彩论点
一年前的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以 5:4 的票数支持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主张,该判例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同时,这个以一票之差微弱优势艰难通过的案件也反映出美国精英阶层乃至民间对于何为「平等」;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州权与联邦权的冲突认识始终存在分歧。
如果回顾从美国的司法史,就会发现这样的冲突早在建国伊始就已埋下。早在建国之初,联邦党和共和党对于合众国的政体意见不同:联邦党主张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共和党主张邦联制,即将国家权力更多地放在各个州,以期更为直接的人民民主。最后联邦制获得胜利,而且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联邦政府代表的国家权力逐渐扩大。
这样的结果未尝不是件好事。早在两百年前,联邦党人在《联邦党人文集(联邦论)》中就详述了强大中央政府的必要。很难想象,如果现在的美国是一个如当年共和党期望的那样,没有常备军队,50个州之间相当独立的邦联制国家,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另一方面,在共和党所代表的保守主义者的努力下,联邦权力的扩张始终被遏制。他们坚信权力过于集中的中央政府会滋生腐败和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权利。
两种政治主张分庭抗礼两百余年至今,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上,也是争议的焦点之一。少数派法官反击的有力论点就是州权和联邦权的分界:他们相信,同性恋婚姻是否合法应该归各个州根据当地情况由人民通过代议制立法自行判定,联邦最高法院无权插手。
少数派法官们另一个非常精彩的论点是,他们称婚姻的定义,这样神圣的责任,应该通过民主程序的方式予以确认或修改,而不能由九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学精英自作主张地诠释。这一论点背后其实是司法(解释)权与立法权的冲突。
立法权在民主政体下地位最为崇高,因为它是民意表达的直接方式。相比之下,司法权,尤其在美国联邦法官终身制制度下,这一权力简直就是反民主的「腐朽形态」。因此,哪怕联邦大法官人品高尚,学识精湛,行使司法权时也必须极为克制,以免侵犯立法权。这也是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派法官主张的「司法审慎(克制)主义」,甚至更极端的「原教旨主义」。
保守派法官的意见虽然精彩,可我个人却逐渐倾向于认同自由派的意见,尤其是读了 Cliff Sloan & David McKean 的著作《大法官与总统的对决:马伯里诉国务卿麦迪逊案》后。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发生在1803年经典判例的前因后果,很多细节让我对美国司法权的发展史有了新的认识。
孱弱联邦最高法院
在十九世纪初以前,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中,司法权是最弱的。即便非常担心民粹暴政的立宪者们已经意识到建立一个有足够权威的司法作为守卫法治的最后一道屏障,而决定赋予联邦法官终身制后,司法权仍然羸弱不堪:联邦大法官每年需要在各州翻山越岭地下乡断案,回到首都(那时华盛顿首都尚未建成)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办公场地,更别提如今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看到的那幢恢弘的最高法院了。即便首都建立,地面也坑坑洼洼,总统府还都没修建好,压根没人会想到最高法院的办公地,随便找个楼里匀几个办公室给他们了事。
如此简陋的条件使得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当联邦大法官这个薪水微薄的苦差事,这和如今一个法律人视能被提名联邦大法官为终身无上荣誉形成鲜明反差。
穷苦的工作尚不算什么,最可怜的是司法权被严重轻视:当时社会根本没有联邦最高法院拥有违宪审查权的概念,而这个认识在如今民主国家早已是常识。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政客们看来,最高法院没有权力说某部法律违宪。实际上,换个角度看,他们这么想也不是没有道理:既然从议员到总统,大家都是按着圣经对宪法宣誓效忠的,凭什么联邦大法官就高人一等自称是宪法的解释者呢?
约翰·马歇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担任了联邦首席大法官的。这个在立法行政两个权力机构都曾任职的法律人,决心以一己之力将司法权提升到能与另两个权力分庭抗礼的地位。
神来之笔
1800年,两位开国元勋联邦党人,时任总统的亚当斯与共和党人杰斐逊为下一任总统激烈竞争,最后杰斐逊大获全胜,不仅收获总统宝座,还控制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亚当斯总统在任期间最后时刻孤注一掷,昼夜不停地委任了一大批联邦法官,史称「午夜法官」。不料由于疏忽,一批签署盖章完毕的委任状没能寄发出去,直到杰斐逊上台后才发现。手握立法行政两权的杰斐逊总统对亚当斯把司法权作为联邦党人最后的政治堡垒的做法非常愤怒,命令时任国务卿的麦迪逊扣留委任状,并称该委任状未发出即为无效。马伯里等得到任命却无法获得委任状的太平绅士们一纸诉状告到联邦最高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强制麦迪逊发出委任状。
这个案件表面上是要求获得任命,实际上是两党争斗的产物,也是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对抗。法律理应是公正不涉足政治斗争的,但法官们有着自己的政治倾向,何况这一届联邦高院是联邦党人的最后堡垒,两股力量的角力在马伯里案一触即发。
尽管当时尚未有联邦最高法院对抗联邦政府的先例,违宪判例只在州法院出现过,但杰斐逊总统未敢掉以轻心。他通过国会立法,削减了联邦法官的规模,给了司法机构一个下马威。由此,司法权和立法权也交上了劲。
黑云压城的宪政危机如何应对?马歇尔大法官的应对之道的精彩程度胜过任何一部律政剧。
47岁,刚担任首席大法官的马歇尔以亲切温和的口吻开始宣读判决。在座的来宾将会听到最高法院并不漫长的历史中最为冗长的一份判决书,将近9400字篇幅。马歇尔首席大法官清晰地把整个案件分成三个子问题:
申请人是否有权获得他所主张的委任状?
如果他有权获得委任状,并且这一权利遭到侵犯,我国法律是否为他提供了救济途径?
如果这种救济途径确实存在,是否就是由本院下达职务执行令?
所有人都明白,如果这三个问题答案都为「是」,那这就是历史上首次最高法院与总统的对决。
接着,马歇尔大法官手术刀般地一个个剖析问题。他先对整套官员任命流程的每个节点进行法理分析,认定了不同时间节点的法律意义,并「反复考量种种可能的反对理由」,最终在第一个问题上完全站在马伯里一边。随后,他把第二个问题从「公民自由」角度切入,将问题转变为一个公民的个体权利遭到侵犯时,一个法治合众国政府是否应该提供救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首席大法官通过宪法分析,将总统自由裁量权的政治权利和委任状递送给获任者的义务进行区分,掷地有声地断定「其因为获得任命而取得的诸种权利也就获得了法律保护,不再受总统干预。行政机关无法剥夺上述权利……马伯里应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
到了最关键的最后一个问题。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把第三个问题分成两个子问题:
当事人请求法院下达的令状是何种性质?
本院是否有权下达这一令状?
在回答第一个小问题时,马歇尔抓住机会驳斥了对最高法院僭越行政权的批评,并强调本案并非政治性问题。对首席大法官而言,本案并不复杂,马伯里享有上任就职的法定权利,他有权获得救济,而由法院下达职务执行令则是恰当的救济途径。走到这一步,就差最后一句话了:「本院可以下达职务执行令,要求杰斐逊政府执行法定义务。」
所有人都很清楚,一旦说了这句话,马上会引发一起国家危机。但马歇尔找到了一个两全之策,不仅避免国家两大权力分支陷入灾难性的对抗,又可以建立一个长期适用的重要原则。
这一神来之笔却来自于先拿自己开刀!马歇尔法院得出的结论是: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案,恰恰是因为改法违宪地授权最高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审理申请职务执行令案。
马歇尔根据对合众国宪法的文本解读,提出最高法院是一个上诉法院,只有在明确规定的极少数例外情况下,才能充当初审法院。而本案中,国会在本案之前明确授权了最高法院拥有该案的初审权,同时也享有上诉审管辖权(因为这是一起针对行政机关行为的上诉案件)。两党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首席大法官在整个判词读到最让人血脉喷张的时候突然给所有人浇了一盆冷水。他强调国会违宪地授予了自己不该拥有的权力,而宪法作为立国之本,决不能因为立法机关通过一个普通法案就被修改。于是,壮士断腕后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提出两个重要论断:
在成文宪法的缔造者眼中,宪法显然是本国至高无上的根本大法。因此,宪政政府的核心理念必然是:抵触宪法的立法法案当然无效。这一理念是这部成文宪法的必然产物,因此也是本院视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根本准则。
解决宪法与法律之间的冲突的最终裁决者是司法机关。
这一伟大的判决无论从法理推理还是政治平衡能力都达到了完美的高峰。另一重要启示是:联邦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权要独立于党派利益之外。
作为推动社会的最高法院
美国内战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对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解读一直停留在极为狭隘的角度上,也为「隔离而平等」的种族隔离政策铺平道路。
第一款 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
第二款 众议员名额,应按各州人口比例进行分配,此人口数包括一州的全部人口数,但不包括未被征税的印第安人。但在选举合众国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人、国会众议员、州行政和司法官员或州议会议员的任何选举中,一州的年满21岁并且是合众国公民的任何男性居民,除因参加叛乱或其他犯罪外,如其选举权遭到拒绝或受到任何方式的限制,则该州代表权的基础,应按以上男性公民的人数同该州年满21岁男性公民总人数的比例予以削减。
第三款 无论何人,凡先前曾以国会议员、或合众国官员、或任何州议会议员、或任何州行政或司法官员的身份宣誓维护合众国宪法,以后又对合众国作乱或反叛,或给予合众国敌人帮助或鼓励,都不得担任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或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人,或担任合众国或任何州属下的任何文职或军职官员。但国会得以两院各三分之二的票数取消此种限制。
第四款 对于法律批准的合众国公共债务,包括因支付平定作乱或反叛有功人员的年金而产生的债务,其效力不得有所怀疑。但无论合众国或任何一州,都不得承担或偿付因援助对合众国的作乱或反叛而产生的任何债务或义务,或因丧失或解放任何奴隶而提出的任何赔偿要求;所有这类债务、义务和要求,都应被认为是非法和无效的。
第五款 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规定。
1950年代,堪萨斯州的女孩琳达·布朗申请入学于离家更近的白人公立小学而被拒绝,引发了著名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
该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由首席大法官沃伦领导的法院受理。该案件争论焦点即对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解读。在被告看来,保持种族隔离但形式平等的做法符合十四修正案的精神,也继承了过往最高法院对此修正案的解读先例,联邦政府无权干预本州。
但是,沃伦法院作出了一致判决,采取了更宽泛的方式解读第十四修正案,支持了布朗的上诉,彻底摧毁了美国种族隔离政策。这篇历史性的判词篇幅不长,在逻辑美感上不如马伯里案,但其意义非凡。
首先,沃伦法院的判决推翻了之前最高法院的历史判决,是一个自我纠错的结果,这在一向尊重传统判例的英美普通法系中是不得了的大事。其次,在最后投票前,有三位保守派法官持完全反对的意见,虽然不影响最后的结果,但沃伦大法官更希望的是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以全体一致的方式为判决增加力度。他将法律道德化,认为布朗案所涉及问题在于,美国面临着道德挑战,即美国如何践行国家对黑人公民未尽的承诺。他在演讲中回顾美国在二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迁入集中营的历史,时任加州司法部长的他对此做法坚决支持,如今却非常后悔。作为首席大法官,既为过去的行为道歉,更希望他的同事们能够在终止种族隔离方面有所隔离。
这一判决成为了「司法能动主义」的典范。司法能动主义认为法官应该审判案件而不是回避案件,并且要广泛的运用他们的权力,尤其是通过扩大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去促进公平——即保护人的尊严。
回顾马伯里案和布朗案后,我更加倾向认同司法能动主义的主张。如果没有马伯里案中马歇尔大法官的精妙释法,确立了最高法院拥有违宪审查权,就不存在之后两百年后诸多最高法院影响历史的经典判决。如果没有沃伦大法官历史性的判决,黑人平权运动的成功不知要延后多少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公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让种族平等理念先于社会普遍共识而植入公众意识中。虽然这一做法引发了当年南方诸州的强力反弹,但这也体现了司法作为抵抗暴民政治的最后一道屏障的作用,这恰恰体现了开国先贤们设立最高法院的初衷。其中以阿肯色州小石城事件最为激烈——种族隔离者对联邦最高法院的挑衅,最终使得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联邦军队入驻小石城,贯彻执行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经过六十余年,种族平等的观念在美国已经深入人心到「政治正确」的地步,以至于引起了对「逆向歧视」的担忧甚至反感。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说明种族平等的基本观念已经无可辩驳,所有的社会讨论皆在其边际程度上而已。
回到去年的同性恋合法化问题。尽管最后结果让我高兴,可比较之前两个判例后会发现,如此政治正确,判决后整个社会完全没有引起如六十年前半个国家暴动情况的议题,却反而仅仅以一票的微弱优势通过,这足以让人唏嘘:如今美国社会的分裂是从精英到民众全阶层的。九位法官中八位的投票结果恰如其政治立场,在判词中既看不到212年前马歇尔大法官精妙的法理分析,也没有沃伦大法官携手九人共同创造历史,指引全国人民走向更好社会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