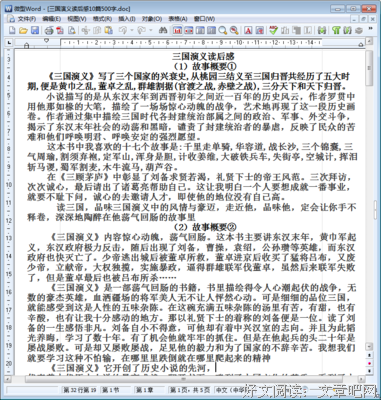
《WKW》是一本由Wong Kar Wai / John Powers著作,Rizzoli出版的Hardcover图书,本书定价:USD 65.00,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WKW》精选点评:
●He knows that true cool isn't an attitude or a style, much less a lifestyle. It lies in trusting in your own sensibility.
●229
●惊世旷世之作也许需要遭逢大难,历尽苦海波澜,食尽人间苦味,在绝望中回首绝望,可健康幸福美满的人生与创造一流的艺术品并不必然违逆。用并没有熟练到可以如杨德昌一般用来思维的英语接受采访也算是典型的墨镜风格,朦胧模糊的语言类似于他酷爱的停格加印技巧。从访谈录的层面评估,只读这一本,足够。
●花样年华算是为我打开电影大门的第一部电影
●值得买一本
●说句实在话,如果纸张能更好一些,质感会更好,现在的纸好像就是铜版纸吧
●説來説去WKW的魅力在哪裏,風格化的影像、迂迴巧妙的音樂、響當當的演員陣營、臭味相投的老拍檔等等固然,但最最迷惑人(擾人)的,還是他戲裏呈現的無法跨越的一道道鴻溝,期望與落空,現實與想像,傲氣與恐懼,記著與忘卻,壓抑與釋放、面對與逃避。人與人,也是人與自己。「我以爲我們不會像他們那樣」、「我一直以爲我是贏的那個」,就算再看一百一千遍,我們仍會這麽以爲,以爲自己比較高尚、比較堅定、比較不屑一顧。其實你越以爲自己和別人不同,就越與人都一樣,那句"I want to be different, just like everybody"不衹是調侃。
●拖最久的一本书,因为实在太沉了。。终于看完了,墨镜真是可爱的小天才。
●他的用功程度比孝賢還要誇張。現場不需要劇本也是他的用功方法之一。相當可怕的創作方式,等同於先榨乾自己,再榨乾劇組,最後再榨乾一次自己
●勉强谷歌翻译看了几段加上看过不少采访大致了解他的观念了。他想要的是人物的行为动作,因为姿态是一个人不能预测的魅力所在。随着看完他所呈现的画面后把能共鸣的还有深层再体会的联系到一起。而成为现在的他和经历环境观念自身经验的东西缺一不可真是分人呐
《WKW》读后感(一):摄影机的角度
在对话五里终于谈到摄像头的角度。他说,“我不喜欢像杨德昌拍摄时从上往下的那种俯视的角度,也不喜欢在拍摄时仰视他们,像小津那样。我喜欢在看电影时,人们与演员们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彼此处在平等的位置,能够与他们共情。”
谈到为何不拍摄家庭时,他说,“我对大家庭或一堆人聚在一起完全没有概念,那是小津或侯孝贤的菜。在《悲情城市》里,你真的能感受到他们每个人都发自内心理解对方,知道他们的过去跟故事。这些我做不到。此外,即使万不得已非要拍家庭的场景,我也不愿意拍孩子。因为我们的拍摄大部分都是夜里进行,孩子没办法参与;另外孩子注意力最多只能保持一小时,这就意味着一大群人要一直等着孩子休息,也不是我能接受的。
《WKW》读后感(二):浪漫艺术电影爱好者可以看看
王家卫,著名电影导演,擅长浪漫艺术电影,曾夺得7次香港电影金像奖和3次欧洲电影奖。
王家卫的这一本书,用250多张照片和电影剧照,带你一同回味他的经典电影。
书中收录鲍尔斯和王家卫展开的六次对话,探讨电影、时间、怀旧和美感等主题。每一次都在不同的地点,包括他拍摄《花样年华》的餐厅和他拍摄《重庆森林》的小吃店。
《WKW》读后感(三):短评
书很有质感(i.e., 重!特别重!),其实文字不是很多,断断续续看完,加起来花的时间估计不多。这在电影类书籍里算良心的,没有煽情性的戏剧人生描写,是根据时间顺序一部部跟墨镜聊他的电影,怎么来的灵感,怎么发展,啼笑皆非的过程,对演员的诚实评价等等,值得拥有。
我对墨镜的熟悉度远不如安叔和杨德昌,跟3H差不多把,认真看过一部代表作和最新的作品,所以看完猎奇感为主,当时记得还有各种感受,跟基友打趣不少。如今过了快一年多,忘记了大多数,就清楚地记得墨镜毫不忌讳地说觉得Maggie不是真心热爱演戏。哈哈,现在回头看Maggie的事业历程,虽然的确是,但是墨镜也忒直接了。
当时看完有冲动按照时间顺序再看遍墨迹的电影,一直没时间没心情。这几天读Kundera的The curtain,突然意识到无论是潜意识还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习惯,按照时间顺序去探索艺术家/艺术流派/学科发展,相较于其他顺序,能得到更多创作者思路的启发。其次,Kundera对于value of art的定义让我对影史地位又有了新的认识。跟基友曾经得出过结论,安叔 墨镜就电影、导演来说,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安叔会在影史上吃亏,因为相对于作者型电影,安叔目前在电影艺术形式上还没有过显耀的突破。所以,虽然我们都在吐嘈沉迷技术安格李,换个角度,安叔又何尝不是在试图突破电影的艺术形式呢!希望Gemini man保本的基础上能冲个票房,让安叔能够继续拍拳击,让我们能够看到安叔在电影史上的突破。
《WKW》读后感(四):记一点感兴趣的八卦
1. 谭家明《最后胜利》某种意义上是《旺角卡门》的续集。两部电影都来自于王家卫和谭家明构思的一套黑帮三部曲,第一部讲两个男主角的童年故事,第二部是青年,第三部是中年。结果先拍了第三部。等到王家卫独立做导演的时候,选择了第二部的故事拍了《旺角卡门》。
2. 传说中的《阿飞正传》第二部:一个1966年香港动乱后的故事。《阿飞正传》本来是想拍1966年香港动乱,但在写故事的时候,王家卫对直接讲述动乱失去了兴趣,于是发展成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1960年代的香港,第二个故事是66年动乱发生之后。
3. 梅艳芳给《阿飞正传》唱主题曲,首映结束后对王家卫说:“我的歌出来的太晚了。”
4. 王家卫和王菲认识于《重庆森林》之前。王菲曾为《阿飞正传》第二部试过镜,角色是张曼玉的妹妹(也可能是姐姐,原文是sister),令王家卫印象深刻的是,当年还叫王靖雯的她,试镜用的是王菲的名字。
5. 宋慧乔不是第一个被王家卫收去护照的人。在《重庆森林》里,绕在林青霞身边的印度人们也被王家卫收了护照。他们是一群来香港的背包客。
6. 和这群印度临时演员演戏,林青霞负责训练他们的演技,效果非常好。
7. 《堕落天使》里,饰演金城武父亲的演员,是重庆大厦里一家旅馆的主人。
8.为了和妮可·基德曼拍《来自上海的女人》,王家卫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在纽约图书馆、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方做了很多研究。然而因为没有等到妮可·基德曼,项目停摆。
9. 《蓝莓之夜》改编自《花样年华》的原始版本——三个关于吃的故事。王家卫拍好了第一个,第二个便是《花样年华》,但越拍越长,最后放弃了第一部分,独立成片。这个短片以《花样年华2001》为题在2001年戛纳电影节大师班上做过放映。
10. 《爱神之手》拍了72个小时。拍摄完全是顺序,巩俐和张震越拍越累,情绪也越来越对。王家卫和巩俐的合作很愉快,便邀请她加盟《2046》,角色戴手套也是因为《爱神之手》的原因。
11. 王家卫很喜欢田纳西·威廉姆斯。曾经想翻拍《欲望号街车》。请巩俐和姜文来演。
12. 章子怡在《一代宗师》剧组里唯一一次崩溃,是自己的嘴突然肿了。
想起来这么多,其他的等以后再翻的时候再补吧。
写完之后又想起来两段:
1. 拍《春光乍泄》片头的那场床戏,给梁朝伟做示范的是张叔平和张国荣。
2. 拍这场床戏,梁朝伟脱到只剩一条内裤,王家卫让他再脱的时候,梁朝伟说这是自己的底线了。等到张国荣离世之后,梁朝伟说,自己有些后悔当初没有脱掉那条内裤。王家卫觉得梁朝伟接《色,戒》有一部分这个原因。
《WKW》读后感(五):春光印畫
那時眼睛還很好,不需要墨鏡王家衛,一九五八年出生在上海。他的父親是船員,十二歲就出來當學徒;母親算得上是大家閨秀,對跳舞與戲院很感興趣。據王家衛回憶,他對電影的啟蒙就來自於母親天天帶他上戲院。除了家衛外,王氏夫妻還有一兒一女。一九五八年時,王氏決定搬遷至香港發展。當時因政策原因,一家只能帶走一個孩子。再三考慮後,王氏因家衛年幼還需照顧,所以忍痛放棄長子長女。爾後上山下鄉發布,也是只能留一個的政策,王大哥代替王大姐去邊疆守了十幾年,最後無妻無子。而王大姐則是在上海成家立業。等王大哥從邊地回來後,王大姐照顧了他的晚年,並於2015年的一個暑期病逝上海。
王家衛的童年是在香港的上海社區過的。當時很多上海人流轉至香港(這就是《2046》的背景),他父親因為當海員,常常不在家。而他母親則因麻將技術高明,曾靠麻將維持過一段生計。在墨鏡還沒開始戴墨鏡時,他因身處在上海社區裡,所以再多種語言下成長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他的電影裡,一個講廣東話的人可以毫無障礙的與說中文的聊天。另外他也強調傳統文學的重要性,說他小時候最喜歡讀《三國演義》,而且讀得很熟(沒想到吧)。當他剛開始在香港無線電視台工作時,邂垢了他後來的妻子:著名的陳以靳。據墨鏡的說法,當他剛發表作品的時候,陳會帶著一家老小跑去電影院看;看到後面,就開始一個人跑到戲院去看了。因為她發現,不管墨鏡拍了多少部電影,裡面有多少個女主角,她都能在這些角色裡發現自己的影子。
每個導演,都會有他自己的創作模式。而這些模式,往往造就了人們所謂的“風格”。比如當昆丁塔倫提諾想拍部片子時,他會跑到唱片架上,先選好音樂,然後根據音樂的風格來奠定電影的基調。墨鏡王有點類似。他首先是有個想法,然後去找相對應的演員。等演員選定後,他會為這個演員量身定制他的故事。(這就是為什麼《手》這部影片會有這麼高的評價。另外墨鏡回憶說在他的長輩都是去量身定制衣服,所以好的裁縫會對客戶的身材瞭如指掌)當然,一旦角色立得起來後,王就會開始去尋找相對應音樂(雖然他找的音樂都是那種悶騷型的)。
出場可能連三分鐘都沒有吧...既然有了角色,那就要開始架構角色。在《阿飛正傳》的最後一幕,墨鏡出人意料的讓他永遠的男一號—梁朝偉入鏡。他既沒解釋這個角色的意義,也沒給這個角色什麼戲份。(我還記得我在電影院看重映版時,觀眾看到這裡時驚呼聲)但即便是這麼匆匆一撇的角色,王家衛也給他定性了:一個賭徒,準備出門。所以他口袋裡有樸克牌,並準備去別人婚禮上揩揩油。等到了《花樣年華》時,墨鏡就對梁朝偉說:你是個靠寫小說維生的文人,所以你身邊要帶把帕克筆,因為如果他沒錢,他可以先拿帕克筆在餐廳典當一頓餐……就是因為這些細節,讓同一批演員卻能給予觀眾不同的感受。就像做旗袍一樣,一種帶有強烈的個人風格,但又帶有量身定做之感的角色的電影,孕育而生。
到底內褲要不要脫給墨鏡拍呢?就以我個人最喜歡墨鏡王作品《春光乍洩》來說,裡面有我鍾愛的皮耶左拉,以及那飽和度飽滿到溢出的濾鏡。此片的英文名子叫《Happy Together》,其實墨鏡原本的想法是用《Heartbreak Tango》作為標題,因為在他讀完阿根廷小說家Manuel Puig的同名作品後,深獲啟發,於是決定以阿根廷為拍攝背景,講述一對男同志遠離香港,結伴出遊的故事。當時剛好是九七香港回歸之時,很多港人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選擇出走,墨鏡決定用他的方式來講述這段故事。他之所以選擇阿根廷,是因為從整個地球上看,南美洲剛好是處在香港的另一端(所以他才會補拍一段上下顛倒的對比片段)。
在出發之前,墨鏡只有一個很潦草的概念,他先選定了張國榮與梁朝偉,然後跟張國榮提起這個計畫,張國榮欣然同意,然後王在找上梁朝偉。在大概講素他要的感覺後,一幫人殺到阿根廷去。當王到阿根廷後,發現因為有個美國劇組在這裡取景,所以器材根場地都被佔用了。但他無所謂,讓當地導遊帶著他閒逛(他稱之為“探索城市”),最後選定一個碼頭時,當地導遊都很驚訝(不過當片子出來後,人家還是認為王把他們的街道拍得很美)。頭三個月因其低廉的物價(紅酒與牛排),每個人都很高興;但久了之後,大家都在等墨鏡的劇本出來。
想當年他剛出道時向觀眾扔帽子,觀眾還把帽子扔回來可墨鏡卻天天窩在咖啡廳想啊想啊,想到連張國榮都等不了,跑來跟墨鏡說他有世界巡迴,沒法耗下去了。於是墨鏡發揮他超常的即興功能,先把張的部分拍完,然後編後面的故事。墨鏡先是找了關淑怡來演幫忙,後來覺得這樣會影響影片的基調(因為他講的是同性的故事),於是又找了當時十七歲的張震出演。在找張震之前,很多人懷疑他的決定,因為他們認為張震很木訥,演技似乎不太行;不過王說了,他要有這張臉才能有後續的故事。然後張震來阿根廷解圍,並把最後的部分拍完。墨鏡在接受才訪時,還語重心長的說:黎耀輝最後還是沒回香港。
在完成這部電影後,墨鏡本來想邀約Nicole Kidman合作,拍一部名叫《來自上海的女人》的電影,後來因為檔期問題錯失交臂,墨鏡甚至都放棄了已經寫好的劇本。於此同時,他應緣際會認識了當時剛紅起來的爵士女歌手Norah Jones。他們倆聊了一會,覺得很投緣,於是想一起合作出一部片子。墨鏡再找到美國的投資方,並找回了創作《花樣年華》時期還沒完成的改念:一部關於吃的電影,並找上Jude Law 合作。這部片子的評價普遍低迷,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觀眾沒法接受,這麼一個標榜高格調的墨鏡,怎麼可以跟俗氣的美國片商合作呢?不過出人意外的是,《我的藍莓夜》在俄國很受歡迎,甚至可視為是他在俄國的代表作。至於為什麼選“藍莓”當標題呢,因為墨鏡讓Norah Jones選她最討厭的派時,她選擇了藍莓派,看到沒,就是這麼隨性。
除了隨性外,墨鏡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敢為人先的精神。早在《重慶森林》出現前,他就決定去拍個武俠片,剛好《重慶森林》給了他一個募集資金的機會,讓他帶著大批頭牌,跑去當時還很落後的戈壁一代拍片。他先是飛到西安,隔天再從西安飛到戈壁。交通不便就算了,那裡的條件非常不便,連個餐廳都沒有。後來有一個當地的醫生(還是博士?我看英文上寫的是Doctor)看到這麼多人過來,直接把飯堂改成餐廳,並且說等他們走完就收了這餐廳,讓墨鏡驚嘆內地人民的效率與智慧。
這可是杜可風用命換回來的畫面另外還有段有趣的插曲,可能是當地的白酒過於猛烈,在他們拍最後一場戲:歐陽鋒燒了自己的房子,準備遠走他鄉時,墨鏡要求這邊得有個鏡頭的。杜可風前天喝得爛醉如泥,卻在不省人事前滿口答應他會完成攝影的。結果等時辰一到,放火燒屋時,卻發現杜可風半醒不醒的。等他醒過來時,墨鏡非常生氣的告訴他,因為少了這個鏡頭,所以我們電影算拍失敗了。杜發愣的看著他,過一會把衣服弄濕,衝到現場去拍畫面。
只要看過《東邪西毒》的人都知道,裡面的故事全部重改,改的讓金庸很不高興,並且再也不授權給王了(我在想,當金庸看完《東成西就》後,可能會覺得墨鏡沒這麼可惡)。問他為什麼這麼改?他的答案很簡單:“因為我想做點不同的。如果按照小說拍,那類似的作品多的去,哪需要我來拍呢?要我拍,就得拍點不同的。”於是一部魔改奇幻大作就此誕生,並讓當時的觀眾震驚的說不出話:而片商本來想趕新年檔期的計畫,也被兄弟作《東成西就》給完成了。於是乎,票房再次撲街,雖然在大陸的口碑不錯,而他自認為這是他最完善的作品。
據說王慶祥還被梁朝偉的氣場震攝到了十年過去了,又是跟功夫有關的片,不過這次不是“武俠”,而是“武術”。墨鏡對這兩者的定義,前者是帶有魔幻色彩的(怪不得改得這麼魔性)、後者是帶有現實主義的。他選了當時還不太被人所知的葉問,並把它定性為《一代宗師》。除了李小龍之外,葉問還有個事情深深感動著墨鏡:本來李小龍火候聯繫他師父,說他願意給師傅一間公寓,只要葉問錄下他打拳的視頻後發給他,但葉問拒絕了。他說:如果他要做,就不會做給一個人獨享,而是給他所有的學生看。後來看到葉問後人拍的影片,影片裡年事已高的葉問正在並痛苦的吃力的打木桩。顯然他放棄了交易後預期的舒適,一心只有為武術的傳承留下一點貢獻。這剛好符合墨鏡想表達的一種理念:一個人一輩子只做一件事,做精一件事,那他就是一代宗師。
大概二十多年前,當時最紅火的香港導演王晶,公開表示他對墨鏡王(王家衛)的藐視。王晶不僅在公開場合上擠兌人家,甚至還在自己的電影裡安排個角色,他戴著墨鏡,走路跌跌撞撞,引人發笑。那個時候的香港,王晶每拍一部賺一步,還與多名女演員傳出不少花邊新聞;反觀墨鏡王,除了處女作《旺角卡門》和《重慶森林》以外,其他電影在票房上都慘遭撲街。而且墨鏡王結婚的早,也相對保守一些(那為什麼墨鏡會拍這麼多癡男怨女的情節呢?他說都是靠自己腦補出來的),所以在春風得意的王晶看來,墨鏡除了拍些悶的無聊,騙些小文青的片子外,似乎沒什麼本事。
奈何想,二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回憶九零年代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時,王晶和他為數眾多,但大部分都因品質低劣的作品逐漸被人遺忘。而他當年鄙視的墨鏡王,卻被視為是與許鞍華、關錦鵬、徐克、劉鎮偉、吳宇森等一線大導齊名的大導演,甚至是香港片裡最為耀眼的奇葩。當2017年第9届里昂盧米埃爾电影節頒獎,並宣布“after all, dark glasses are undeniably classy。”(畢盡,墨镜不愧是墨鏡),甚至當觀眾逐漸拋棄王晶的新作,卻擁抱墨鏡的《一代宗師》時,我們知道,歷史將給予一個正直的、專注的、甚至是堅持的,一個公正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