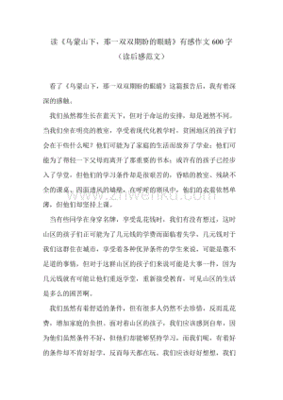
《乌蒙山记》是一本由雷平阳著作,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页数:2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乌蒙山记》精选点评:
●非常精彩的书
●诗人用写惯了诗句的笔和手写散文,流畅度自是不必说。看这本书,更是印证了小镇之于艺术的某种重要性,刘慈欣的阳泉,贾樟柯的汾阳,李娟的阿勒泰,雷平阳的昭通。滇东北的野性,空旷,原始,注入到写字人的血液里,他们的笔下就分裂出许多条龙,许多座山,许多条彩虹。这本书里的奇幻,间歇的愤懑,不经意的讽刺,绵延不绝的乡愁,给昭通,土城乡甚至整个乌蒙山都罩上了一个神秘癫狂的面纱。这种缥缈的感觉,只能来自于阅读。哪怕怀着朝圣的心去昭通,脚步也接触不到这种怪诞,同时又充满诗意的生活与人生。
●文章短而有力,想象似诗的想象一般,喷薄出一幅幅生活的画面,人的悲剧是注定的,荒诞浸入了时间、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们犹如作者开出的一个个玩笑,带着些许嘲弄和搞怪,在彼此间的回荡中,却具有了某种象征性。
●诗人是巫师,守灵人,佛爷,灵魂工程师,梦的解析者,播种希望的人,太阳之子,思想奠基者,先躯,转世灵童,鬼神的送信人,神一样的人物,降魔者,典范,圣贤,宗师,万世师表,标兵,拓边者,舵手,摆渡人,精神导师,灯塔,守护神,战神,黑熬神,色鬼,酒鬼,大仙,土地爷…突破想象的边界,潜入历史和往事中,与人性对话,与神性同行。小短篇既迷人,又让人痛苦
《乌蒙山记》读后感(一):《乌蒙山记》记录
雷平阳散文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像传统散文是对简单人事的描绘、记述,以及穿插于其中的作者的思考与抒情(这类散文多具写实性),在自序中,作者怀疑现实世界的真实。因此,即便《乌蒙山记》看上去记述的多是发生在作者家乡乌蒙山一些小人小事,但此处的“乌蒙山”更像是一个以现实地名命名的虚构世界,是由现实世界延伸出来的一个更高、更广阔的精神家园,是承载作者精神洪流的载体。在这一载体中,作者追求的是凌驾于现实之上的更高的真实。也正因如此,其散文不是基于现实层面上的叙事和说理,而是思考本身。在“乌蒙山”这一虚幻的世界中,他的叙事和说理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关系。
《乌蒙山记》将作者有关灵与肉、生与死、时代与人民、个人与集体、瞬间与永恒等问题的哲学思考蕴含于发生在这个虚幻世界的人和事中,这使其散文具有浓厚的荒诞性和象征色彩。因此他的散文是“活”的散文而不是“死”的散文。同时由于思想的流动性,他的许多散文文本呈现出一种片段式的“未完成”的状态,可被一再地补充和改写,也由此获得了更多的阐释空间和可能性。
《乌蒙山记》读后感(二):乌蒙山记
这是一部雷平阳的散文集,他本身已经形成了十分强烈很具有个人色彩的写作风格,因此他写散文或者小说也像在写诗歌。 首先他的诗歌或者说文字,就像是博尔赫斯的本土化成功范例,跟朱岳一样,把博尔赫斯的魔幻意象改造成中国文化习惯的本土意象,从而写出了一篇篇读起来异调新鲜但是内核很平实的优秀作品。有点像贾樟柯和博尔赫斯的结合体。 其次就是,很像高级版故事汇。除开最后一篇,其他每篇文章都是亦真亦假的故事,中间还穿插着很多云南本土诡谲幽冥的鬼神文化,(雷平阳好像很喜欢表现这点)但是不得不说,由于行文杂碎外加意象过多,而且估计作者本身意不在此,所以每篇文章都是思辨性大于故事性。很多篇章无头无尾,人物的行为更多是为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服务,为了这个思想,无论做多么奇怪的事情,都发自人物内心,而且基本不做过多阐述,故事之间很喜欢留白,因此不论是理解人物还是理解剧情,对于读者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前面也说了,意不在此,我个人是觉得可以接受。 在看这本之前,我看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那本书跟这本,都是一篇讲述一个小故事,相比之下,高下立见。雷平阳的文章彼此之前虽然没有连贯性,但是在行文写作上,自带一种美感,诗意,很有可读性,善于谋篇布局,每次的留白和浓墨重彩之间处理都不错,不会乏味,尤其善于虚实结合,把一些乍一听难以置信的故事,例如追求天葬的僧人,麻风病者,涉及云南鬼神文化的故事,都写得在真假之间摇摆起伏,克制又有冲击力。而另外一本,虽然文章之间是以死亡为唯一单线穿连起来的,但是作者比例不够,叙述起来像写直线日记,再来是文章中刻意添加的很多方言,添油加醋,反而削弱了可信性,要知道这本书最大的卖点可是“真实记录”。对比明显,我投雷一票。
《乌蒙山记》读后感(三):我看乌蒙山记180205
正如豆瓣有些书评所说:雷平阳的这本散文短小有力。我在新年伊始翻开这本装订精美的小书,第一次从书架上拿下这本书的时候,崭新的书页,干净的封皮,一看就是小众图书,但是我还是被它的封面吸引住了。一层耀眼银色的布面包裹着封面、封底和书脊,在银白色的布上斜着的印有平阳手写的几排字,写字的具体内容没有注意,我迫不及待的翻开扉页,便对亲笔手写的序吸引住了。作者写得七扭八歪的字并不好看,却给人真实的感觉。中学语文老师总是说:字如其人。我的字并不好看,却也是个爱写点东西的人,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写字七扭八歪的作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于是,把乌蒙山记带回了家。
从此之后的每个临睡前,我都会期待的翻开它,沉浸在精短的故事中,喜欢之至总要给老公读上几句。跟着书中的文字,我的思绪飞到遥远的昭通,在乌蒙山顶盘旋,在金沙江边休憩...每次不舍得合上书页坠入睡眠的我,总梦到迷失在故乡的胡同里,那时候每家每户的院墙都那么高,上小学的我总一个人超近道而钻进曲折的胡同里。恐惧总在拐弯处和你的背后,我背着书包一直跑,害怕从哪个地方窜出吓人的“大哑巴”。可超近道和冒险精神总促使我钻进这迷宫里,而这本书又再次拉我走进它。
我们对待故乡的感情总是矛盾又复杂,思念令我们渴望靠近,而它生硬的改变又让我们厌恶,就像“金沙江只停留在父亲的回忆里”那样,家门口那片树林我好久不去了。时代发展的卷轮把尴尬的故乡拉扯的面目全非,胡同里那些沟壑的脸庞和干瘦的拄着拐杖的手掌都一个个消失了,吓人的“大哑巴”连“啊啊”也叫不出声了。我越是迷失在梦中,就越是想念儿时的故乡。
书中大多故事都极其精彩,简短的文字,尤其在结尾处总留下意味深长的感觉。叙述有力,让每个故事都丰盈饱满,总有无限的畅想空间。而作为诗人的平阳,更是把诗的特色带入到散文中,读起来又是另一番感受。
在我心里,这是本称得上好书的书。
《乌蒙山记》读后感(四):乌蒙山祭
诗人是这样的,天才用感官和情绪献祭文字构造无限的空间,地才用真实的空间当作素材献祭给情绪和文字,雷老师明显不是前者。
我喜欢雷老师不是因为我喜欢诗歌,是因为我喜欢云南。群山是什么?群山是祖先的尸骨,死亡如乌云般笼罩在群山上空,永恒的棉被,温暖山谷里的子孙。群山用死亡亲吻雷老师赋予他无尽缠绵的感怀,但对于世代聚居于此者,惟究极残酷尔。
不信你随便找个带搜索的社交软件搜搜昭通,看出来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云南所有大搞旅游的地方我都去过,但我没去过昭通,传说昭通出土匪,出肉串,千禧年后,开始出写字的。雷老师的忧郁带着匪气,从死开始,可能也会用死结束。对于诗来说,沉郁有余但一点不灵动。散文就好很多,我觉得他的邻居都是亡灵,哭号反复回荡在山谷之中。他用自己的脆弱织就网子拦下,写成了这本书。嗨呀,哭哭惹惹,走过那样的路翻过那样的山才能捕捉囚居于此的哭号,真的。乌蒙是昭通的旧名,清朝的时候有个云南巡抚叫鄂尔泰,是雍正的心腹,他在废除西南地区土司制的时候上奏说乌蒙这个名字晦气得要死,不如直接改个反义词,就这样乌蒙变昭通。后来三百余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名字叫啥根本没有用,你问问山,问问水,问问巴蜀再问问黔贵,哦还要问问古滇。飘摇之地,要怎么办?问问唐继尧问问龙云,问问罂粟田再问问大矿坑。然后问问铁路,问问G85,which called银昆高速。问问5g,再问问传说中的云,坟山和污河能不能上传?
当然雷老师的忧郁不能代表西南的忧郁,甚至不能代表昭通,不过土匪、军阀、肉串和无尽的尴尬新闻也不能代表。按理说西南高原的太阳非常非常亮,我不知道昭通太阳如何,不过我知道光线强的地方影子也浓,对吧。我喝多了瞎逼呲哦,雷老师也许捕捉到了千百年来乌蒙积垢的一瞬,但你知道什么吗,等到他所书写亡灵全部离开的时候,他的乡愁将会不值一提。群山不管看起来多么坚不可摧,都会坍塌成为真正的平原,到那个时候,光和影子融在一起,没人分得清谁是谁。
《乌蒙山记》读后感(五):雷平阳的乌蒙乡
昭通作家雷平阳,久闻其名,未拜读其作,于昭通作家这个群体了解不足,只读过夏天敏的几篇中篇小说,王单单的一些诗,今算是完整读完雷平阳的该本散文。作为生于乌蒙大地的子民,对这里的山水风土人情几乎等于零,只觉得大山太高太多阻碍了交通,拦住了与世界的路,生活在这里的人,好政策被打折扣,人情大于一切,贫富差距过大,物价高,人力贱,物资贫乏,经济落后,人民被外面的人称为“刁民”,努力生活的人都想走出去…… 这些粗略的感受在雷平阳的文字中能找到,在《乌有乡》中他这样写到“类似的村庄,我在里面生活过,像一只生活在巨大宫殿或寺院里的鼹鼠。更多的时候,则是小白鼠,在实验室里,被培育,接受尚未确认功效的一剂剂疫苗,做杀死人类或医治人类的试验品。” 在《泥丸》中,关于他最切身的感受是“我读书,有了工作,后来的人以为读了书就会有工作,结果他们没有找到工作。我知道,村子里有很多人一直在骂我,说我带了坏头。让我内心压抑的是,很多家庭,为了供孩子上学,家徒四壁,负债累累。”
在《与小学女同学擦肩而过》中,多年后遇到曾经的小学女同学,“昭通是个没有生与死界线的地方,坟地和村庄总是混杂在一起。我听说过的死亡,先是祖辈,然后是父辈,接下来是同辈。最近几年,听说我的下辈中也有人跳河或喝农药自尽了。清明节的那天,我去给父亲扫墓,在通向坟地的小路上,我与一个小学时的女同学擦肩而过,不敢与她打招呼,因为我不知道她是活着还是死了。”
在《仓皇》中,“索伦·克尔凯郭尔问:“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做好基督徒?”金沙江河谷里的人紧闭着嘴巴,谁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从山洞里出来,浑身浸染了蝙蝠气味的巫师又问:“如果没有了庙宇和鬼神,没有了先贤祠,没有了祖先的坟墓和神龛上祖先的目光盯着你们,你们会干出些什么荒诞的事情来?”
在《蠢蠢欲动的生活》篇,雷平阳写到“在东莞打工的乡下男人,生活中只有三件事:在流水线上打捞血汗钱,在出租房的窗口看着小街上来来往往的妓女手淫,在邮局给家人寄钱。”
太多太多熟悉的昭通人的日常生活被他书写在纸上,发表,出书……但我知道虽然昭通有近五百五十万人口,读雷平阳的书的人大概连千分之一不到,书中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看起来荒诞不经,实则都是真实的事,所谓荒诞现实应该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