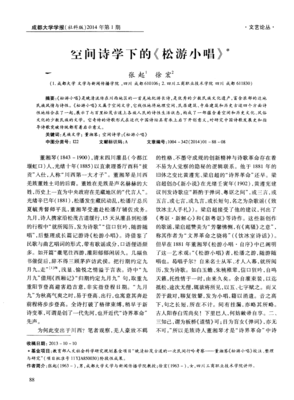
《空间诗学》是一本由[法]加斯东•巴什拉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空间诗学》读后感(一):时空居所里流淌的诗意之于寻找
我个人很喜欢法国作家。看到作者是法国人,特意百度了一下,信息很少。法国人就喜欢把玩语言这东西,他们将文字的诗性和哲学性结合得还特别“高大上”。本书所讲的空间也是哲学范畴的空间,几无建筑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借空间的壳讲哲学和诗学。可喜的是,书中拿来作例子的诸多诗句差不多都是没有读过的,而诗评又相当之精彩。甚至而,完全可以把这本书当做一本诗评集子来看。可以说这是一本读着会忘记吃饭的好书。稍稍可惜的是这翻译,也是减去一星的原因。准确不准确不敢说,只是通读下来,统一感略显不够。另外长句特别多,还多是虚词副词堆砌出来的长句。也许译者是为了表达得更完全些,冷不丁丧失了语言的美感,这样似乎就得不偿失了。而这种语言美感的丧失,是连后记提到的亡羊补牢的校对工作都难以修复的。
《空间诗学》读后感(二):生活在别处
提起我们居住的“家”这个建筑物,我们想到的名字一般是房子、屋子、公寓、《空间诗学》这本书提出一个名字“家屋”——也可能是译者的再创造了。在本书里,作者认为家屋不止是实际物理空间上的存在,更重要是我们精神深广意识的居所。 作者强调和赞美“白日梦”、“私密感”,以及家屋对这二者的意义。这里“白日梦”并不是我们传统观念里认为的那个关乎不劳而获不切实际等消极意义上的贬义词。在第一章里作者提到:“......如果我被要求明说家屋的主要好处,我会说:家屋庇护着白日梦,家屋保护着做梦者,家屋允许我们安详入梦。人类的价值,不仅只有思维和经验,白日梦的价值,标志了人性深层的价值。白日梦甚至拥有自我调整价值的殊荣,它从自身的存在获得乐趣。”“身在自己孤寂独处之空间时,白日梦比梦来得有用。”“基本上,阅读诗,就等于在做白日梦。” 作者对家屋最重要的“私密感”也是赞赏有加。实际上,第三章“箱子.抽屉与衣橱”就是在探索与抽屉、箱匣相关的私密意象,第四章“巢”和第五章“壳”也同样都是借鸟类和软体动物来隐喻私密空间的恬静感,仿佛“童年去而复回”。 全书确实存在大量篇幅的精神分析、隐喻研究。初看前面的序文和作者导论,容易被其玄奥晦涩的理论名词吓懵。但从正文第一章开始,作者还是注重由浅入深的讲述,其间引用了非常多的诗句(个人偏爱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诗)。文字清丽流畅,优美而颇具古风,像一条让人愉悦的小溪。另外,诗学、建筑学、心理学有很多和美学有共通点,阅读过程中曾不止一次联想起起李泽厚《美的历程》,以及台湾美学大师蒋勋的很多观点论述。尤其本书中对私密感和孤独的尊重,与蒋勋老师的《孤独六讲》提到的“孤独或许就是美学的本质”一说相映成趣。 作者对“巴黎没有家屋,大城市的居民活在一层一层叠床架屋的盒子里...”的批评,用在当代中国也毫无违和感,我们的大多数何尝不也生活在一个个复制黏贴般建立起来的毫无诗意的城市水泥盒子里呢。 还有,作为一本包含了哲学、美学、文学研究(诗学)的心理学著作,本书名为《空间诗学》,全书很少提到“建筑”二字,却被著名建筑现象学(还有这么一门学问)学者诺伯格.舒尔茨列为“建筑必读经典”,是不是很神奇。
《空间诗学》读后感(三):认识空间
一开始是被书的封面吸引,三个舞者在黄色的背景下跳着芭蕾舞,多么的富有诗意啊,其次是被书名《空间诗学》吸引,由于自己是数学专业的,一提到空间,我的反映就只有欧式空间,即普通的n维空间,所以非常好奇空间中蕴含了哪些诗学。 看着看着,我才顿悟,这居然是一本关于建筑学的书,特意去百度了下,《空间诗学》与海德格尔的《存有与时间》《建居思》以及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中有关空间的章节并列为建筑必读的经典。 在书中,作者认为空间并非填充物体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家屋,化抽象为具体,这也是数学里常常用到的。注意,作者说的是“家屋”,而不是单独的“家”和“屋”,我想在所有人心中,“家”是一个名词,一个温暖的地方,是受了委屈和挫折的避风港;而“屋”也就是通常说的房子,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杜甫说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尤其是对在外打拼的人来说,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哪怕空间不大,可以遮风挡雨,就是自己的家。故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作者想要传递给读者的,特别是建筑师要明白:设计房子时,它的外观是否好看,内部是否舒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给住的人一种家的感觉。 于我而言,家屋就是我最喜欢的空间。举个例子:常常与朋友约好出去玩,但到了玩的那一天,我会找各种理由拒绝。为此,爸妈总笑我是“宅女”,因为只要有足够的食物,我就可以一直不出门。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从读大学开始,我们在家的时间就越来越少,只有寒暑假能回去陪家人,倘若毕业留在外地工作,可能只有过年才会回家。租房子或是住公司宿舍,那都没有家的味道,因此我也只想把握当下的时间,尽可能多的留在自己的家屋,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作者说“被居住过的空间实已超越了几何学的空间”,对于这一点,我不太认同,毕竟几何空间覆盖了n维,n是趋近于无穷的,而目前居住的空间,我想再怎么大也还是在地球内,当然以后说不定可以到宇宙中去。或许每个人思维方式不同,对“空间”范围的理解也就不一样,像我学数学,理性上就会偏向于几何空间,而作者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就认为家屋所包含的空间更广,但不可否认,作者对于空间的认识真的很独特。 看完整本书,我终于可以回答我最开始的疑问了,何为空间诗学?答曰:“建筑学就是栖居的诗学。”倘若对空间现象感兴趣就看看这本书吧,绝对会让你大开眼界,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空间。
《空间诗学》读后感(四):可以说是梦的空间解析
书中人的心灵在现象学心理学范畴中被分为两种层级,一种是在精神上或说是在心智上的存有,通过的是依靠思维与逻辑,站在客观与理性之上提出概念,也有如诗中所隐喻,这些理论早在20世纪列斐伏尔的后现代空间研究中就有验证,他把复杂的空间性思考建立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把单纯以时间为量度的固有思维打破,让时空有了并置性,这也使得他所建立空间性与社会政治的媾合有了新的探索价值。
巴什拉的空间学说是第二种层级,是列斐伏尔所研究的初始形态而并未被他关注的,却可以说是更为诗意、人性化、存在想象中的空间形态。那是人灵魂中的意象,完全投射在个人主体层面之上,在发现与重复发现的过程中,人意象的产生是先与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判断的,所以在巴什拉的书中会认为这样的空间是关乎个人的一种回响,而并非需要他者的共鸣。共鸣是经验的吻合,而回响却是内心的涤荡。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云层深处的黑暗呐,淹没心底的景观。”万青的歌词一直回响在脑海,初听来这句歌词仅仅是震撼,而不知道震撼在哪里。现在用巴什拉的思想加以理解就有所领悟了。这短短几行字藏着一个人的时空崩塌,“三十年”与“大厦崩塌”’把它们所处的向度极近湮灭,内心的庇护所不复存在,空落的感觉如同被世界遗弃。其中的悲凉结合万青80年代的人文情结使得这首歌让人彻透般的动容,那是被国内年轻人誉为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天阶(《Stairway to Heaven》),是这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我们在营造自己的空间家屋的产生,是我们最初也是最私密的空间。当外界变化得复杂且危险,我们的空间就越发显得拥有足够的保护力与幸福感,在冬天严寒北风呼啸的清晨,你裹着大被在温暖的家屋里睡大觉,你绝对体会过这种内心的幸福感。这源自于人最初而来的对未知对黑暗的恐惧,而当我们的欲望足以让我们能站的更高、掘的更深,到未知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把空间资源整合,如同今天的互联网社会一样串起了我们全新的空间结构,慢慢体察我们不再发现那些诗意了,功能性与经济价值取代了原初的本能感动。外部世界的存在被削弱,内部的私密感在强化。
诗人的想象空间远比科学家所能用数字计算出来的空间更大。在21世纪,我们提出了大数据,所谓的大数据也是关乎人的经验,加以重叠再重叠,使得这个认知得以足够准确,看似能够代替人类了,快速有效的完成各种各样的技能,可到头来我们知道了,这些虚拟的数字没有想象的空间,没有创造,没有灵魂。更接近与自然万物的是我们自己本身啊,所以我们能认知这个世界的奇妙。我们每一天无非都是在给自己造一个梦,在真实的时空中造梦,那个梦的景象会越来越被自己所吸引,因为那就是我们内心想要的,我们都憧憬诗意的人生体检嘛。
《空间诗学》读后感(五):从精神根源朝向浩瀚的温暖与悲凉
思考了很久,不知如何为一本书定义,这绝对是《空间诗学》的作者加什东•巴仕拉在遥远的法国砸向我这个未知的读者的难题。然而,我却为这样的难题深深着迷,说着迷似乎程度仍嫌不够,换作迷恋应该更为妥当。原因在于,看书名以为是一本诗集,看简介却是建筑设计师必读书目,封面描述为空间心理学经典之作,但最终读完之后仍然无法将其在诗学、哲学、现象学等任何一个领域下归类,就是这样一本数不清道不明的书籍,带给我深深的感动。正如黑塞在《流浪者之歌》中所表达的,悉达多对一条河流的深爱——跟河学,倾听河的声音,然而仅仅瞥见河的一种奥秘,他的灵魂就已经被拴住了。
《空间诗学》就是这样,从“家屋”这一概念动身,一步步将我们带入了诗意空间和深广意识的河流。
作者笔下,家屋是现实空间,更是深邃梦境。“我的家屋是通透的,可以把它拉过来,紧紧地依靠着我,如同护卫的盾牌”,家屋是每个人的来处,是自身的栖息地,只有加上了非现实的情态氛围,人才能获得深刻。如同童年诞生的老房子是“地窖”,在幽深的黑暗的空间里,只有梦想令其起风飞扬。
从家屋开始的步步深入,我们打开“抽屉、箱子与衣橱”,走进“巢”,从“外壳”走向自然,在“角落”与“微型”的探秘中探索空间原型的想象,以及宇宙的宏大与浩瀚、内与外的辩证、圆的现象学。纵览全书,每一种意象的深刻与文字传递的优美和谐统一,相依相存,委实当得起“诗学”二字。
“谁会来敲家屋门?门扉开,吾人进。门扉掩,巢穴藏”,“家屋庇护者白日梦,家屋保护着做梦者,家屋允许我们安详入梦”,在作者庞大的知识架构之下,典雅的诗句,动人的描述随处皆是,令人感怀。众所周知,家是我们身体和灵魂的庇佑之所。作者此处的表达却是另一番景象——“家屋为人抵御天上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生命在美好中展开,它一开始就在家屋的温暖胸怀里被怀抱着、保护着。”极具风格的语句,顿时把家屋这样一种物体幻化成了活生生的存在。既然有如此温暖的表达,之后得出的家屋具有母性特质的结论,以及家屋“取得了一张人脸”的诗句就显得那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走下去和向上攀爬,以高度的明显不同描绘了我们的来处和梦想。用乔耶•布思凯的话来说,“如果只有一层楼的话,我们都无法再身为人了。只住在一层楼的人,他的阁楼变成了他的地窖。”因之,家屋在世间的现实的处境就显得更加难堪。诚如作者所言,“巴黎根本没有家屋”,城市的居民是活在一层层的盒子里的,没有地下根系,没有接近天空的感觉。没有私密,只剩机械。“我在巴黎的噪音下,沉沉睡去”。
一座宫殿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留给私密感的,而城市不正如同庞大的宫殿。返归到原始意象之中,小小的落脚处、小巢、小窝或是小角落。一间单纯的茅屋,这种人文建筑之中最简单的形式,可能恰恰是我们最深切的遥远的怀念。
家屋透过窗口的灯火张望着我们,而我们呢,在孤寂的无措的远方,是否也在张望着那个曾经的或者说永远的来处?
讨论了这么多,只是本书的第一章节。藉此,方才登上《空间诗学》的第一级台阶。
《空间诗学》读后感(六):沙漠是海水的回忆。而生命,一场旋转卡门。
今日读罢《空间诗学》。作者法国人加斯东·巴什拉。译者龚卓君、王静慧。三个红裙女人在凝固的金色火焰中舞蹈,是为封面。
巴什拉,鞋匠之子,一战士兵,物理学者。巴什拉拒绝过往自己的实证思维,开始诗意地研究哲学。
是书由导论及十个章节构成,谈及家屋、巢、外壳、角落、微型、私密的浩瀚感、内与外的辩证、圆的现象学,其中家屋从地窖、阁楼、茅屋、天地、抽屉、箱子、衣柜说起。
书前两篇序言: “在临终病床旁,我们也会听到即将去世的老妇轻呼亡夫之名,所有在世的亲昵倾巢而出,倏尔亡故。” 余序之情景浩瀚而感动。“家是人在世界的角落,庇护白日梦,也保护做梦者。”这是一种想象的分析,我们可以去想象杜甫草堂,去分析许多电影。
毕序叩问巴什拉家屋中的女性形象,“女性主义者认为他把家视为亲密、安全的避难所,而忽略了家庭暴力,以及妇女的家务劳动。我们凭什么理所当然认为家比街道安全?家这个让男人可以做白日梦的避难所,其实正是社会期待女人生产维持的场所。男人把家视为理所当然,甚至要求女人去经营这个空间。对于女人而言,家除了亲密、安全之外,也经常是劳动的场所,甚至是遭受家庭暴力的地方。”不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将女性诗歌中“家”的形象同男性诗歌作比较。
巴什拉如何诉说家屋中的性别?“家务劳动维持着家屋的存在安全感……把十分古老的过去和当下的时光整合在一起。家务活动唤醒了沉睡中的家具……在家具与墙壁的亲密和谐当中,我们可以说,我们终于意识到一栋家屋是由女性所建造的。男性只知道怎么样从外部去建造一栋家屋,他们很少了解怎么样为文明上光上蜡。”
这世间的美好命题,有时语法暗含陷阱,即使是很坚定的女性主义者也会上当。我们试着“学会思”,试着去“自觉”,在此基础上,试着去“反思”。
近日我的思维方法,第一次从自然科学走向精神科学,从理性走向非理性。我体验见精神科学的真理的独特性。此前我还是很理科思维地去看待这一切的。阿西莫夫《基地》里的心理历史学家们,则是对实证主义与数学思维如何决定精神科学的幻想的巅峰。
“在此,诗的读者被要求不要以对象的方式看待意象,更不应视之为对象的替代品,而应掌握它特定的真实。”诗的“真”,即荷尔德林“最生动的生”。不轻易下概念,不用范畴去定义谁,而是去言语它,形成唯美的回响。
“许多形而上学系统会需要绘图术。但就哲学而言,任何捷径都造成损失不赀,而哲学知识不可能从图式化的经验里得到进展。”如有人说:你的哲学没有集合论。可以这样回答他。
科学的诗歌分析,会怎样支离诗意?一个罗马人告诉一个把眼光抬得太高的鞋匠:“鞋匠不要评断鞋子以上的地方!”巴什拉戏谑道:“精神分析师不要评断子宫以外的地方!”哈哈!这人太坏了。
现象学态度下的阅读建议:“现象学的态度要求我们在我们自身当中,创建一种阅读的骄傲,这种骄傲会给我们一种幻象,让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参与到此书创作者的作品当中去了,在第一次阅读时,我们还处于过于被动的状态,还很难获得这样的态度,因为就此而言,第一次阅读的时候,读者仍然有一点儿孩童的意味,这个小孩还在阅读的怀抱当中享受。但是,每一本好书在被读完之后,都应尽快地再被重读。在第一次阅读所带来的的梗概轮廓之后,接下来才是阅读的工作。那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作者所面对的课题是什么。然后是第二次阅读,然后是第三次阅读……它们一点一滴带给我们这个课题的解答。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为自己给出了一个幻象,让我们以为,不论是这个课题,还是它的解答,我们都胸有成竹。心理上的微妙差异在此出现了,‘要我来写,我也会写成这样’。这让我们变成了阅读的现象学家。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没有认识到这种心理方面的微妙差异,我们就仍然只是心理学家或精神分析师。”
绘画之意义:“问题根本不在于精确复制一副已在过去出现的景象。而在于我必须完全让它以耳目一新的方式再生,而且这一次,要以绘画的样态让它重生。”“当代的画家不再将意象视为可感知现实的纯粹代替品。普鲁斯特说到艾尔斯帝画的玫瑰时,就已经指出,它们是‘这位画家培养出来的新品种,就像某些聪颖过人的园艺家一般,他为玫瑰家族增添了新秀。’”
“诗歌是一种自由之现象”,于是,“诗人和画家乃是天生的现象学家。”
巴什拉说:“累积知识必须伴随有相等的忘怀所知的工夫。非知并非无知……以诗歌来说,非知乃是一项基本条件,如果写诗有什么技巧存在的话,乃是用于联结意象这项次要任务。”诗在非知。如果我说:“诗在忘技”,又似乎自欺的成分多了些。
“于是,在所有的理性之外,展开了梦的场域。”
另一些笔批:
“对于那些已经找到庇护之所的存有者来说,只需用‘雪’这个字,就同时表达了天地,也解消了天地。”兰波《爱的荒漠》:“就像在冬夜,一场雪就窒息了明确不移的世界。”“在这整片遍布天地的雪白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宇宙的否定状态……因为外在世界的存有感被减弱了,反而让他们体验到,各种私密感质地的张力被强化了。”
“即便我们已不再拥有阁楼,阁楼上的小房间也一去不回,我们曾有过对阁楼的爱、曾经在阁楼小房间上住过的事实,却依然长存。”大一时写《阁楼》:“永不开花的阁楼无谓春天/一刹止步的阁阳无谓夏天/梦境已知的阁窗无谓秋天/未必可能的阁灰无谓冬天/有一座阁楼居住在背面之野/我会去,我们会去的”。巴什拉说阁楼是理性的方式来做梦,地窖是深渊里的非理性在做梦。《古董商》有超级地窖。
“梦屋”的存在:“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存在着一间梦屋,一间属于梦的记忆的家屋,它失落在遥远、真实过去的阴影当中。我把这个梦的家屋称为我们诞生的家屋的地窖。”
“我们彼此所交流的,只是一个充满秘密的方向。”夏宇有诗:“那个向前标示却不断后退的箭头/原是一大群逆向飞行的蜂//已经是上个世纪/我们存的一大罐蜂蜜//我们的窃窃私语/我们的窃窃私语”。方向与时间、甜蜜与静谧、我们与秘密。
巴什拉问:“如果字词是一户户的家屋,每户都有自己的地窖与阁楼,那么,哲学家难道被判定非得住在地面楼,用普通话对外交际吗?当建筑师、空间规划师、文化心理学家和诗人早已窝进语词家屋的各个角落,哲学家的确该脱离地面楼,往阁楼、地窖的角落里探索,蜷缩在‘文字家屋’中让梦想萌芽。”将言语结构比喻做建筑,两个圆精准的相切。
“然而与其和擅闯者抗衡,或以力量的符号吓唬他,还不如干脆误导他。盒子本来就是一个套一个,最不重要的秘密就放在第一个盒子里。”爱情乃至生活亦此理。
“我的朋友,你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它对你来说,大概不算什么,而即使你来过这个地方,你也没有办法感受我现在所感觉到的种种视觉印象和色彩,我已经就这些细节一一地加以描述了。对于此,我必须为自己辩护,你也不必试着用我所说出的结果来再现它。就让整个意象在你内心漂浮吧,就让它转瞬即逝吧。即使对它只有稍纵即逝的念头,对你来讲,已经足够。”何其恳切而清醒。
“在世间之饥馑”,多么真的命题。而现象学家的任务:“在某个时刻必须有一副饿狼的肚肠,以此面对一只躲进石头里的猎物。”
“跟空间不够比起来,太多空间更令我们窒息。”《三体》描述高维空间时很狭义。
“我们要重复逻辑家的说法,认定一扇门不是开着,就是关着的吗?”重新评估隐喻。“这扇门嗅出了我的味道,它迟疑着。”
梵高说:“或许生命是圆的。”拉封登说:“一颗胡桃会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圆。”还减什么肥,生命是圆的。
“或许所有的物质终将征服自己所处的空间,获致自己的扩张之力,漫过与超越一个几何学家总想借此界定它的表层界面。”是为空间诗学。
“哲学家、画家、诗人和语言作家,提供了我们纯粹现象学的文献。现在要运用它们来学习把存有汇聚起来,就得靠我们自己了。而我们的任务还包括,把这类文献的多样面貌给呈现出来,让它变得可亲可感。”这是现象学家的回荡与任务。不妨用现象学的视域,“去哲学化”,整理诗学文献,呈现我们的前见,并抛掷着飞。
另一些等待回荡的断章:
“如果只有一层楼的话,我们都无法再身为人了。只住在一层楼的人,他的阁楼变成了他的地窖。”
“我们灵魂的塔楼永远倾颓了吗?……我们注定要成为‘塔楼已被铲平’的一群吗?”
“我们如何日复一日,落脚于‘人世一隅’。”
“一个空抽屉是无可想象的,它只能被思考。”
“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研究某种东西,其实却只是开始做某种白日梦。”
“家屋庇护着白日梦,家屋保护着做梦者,家屋允许我们安详入梦。”
“软体动物们的座右铭也许该是:活着必须是为了构建自己的家屋,而不是造一间屋子住进去而已。”
“往昔无可抗拒地变成一只瓢虫。”
“的确,对于那些想要找到一种世界之哲学本质为何的人,可以给他们如下的忠告——寻找它的形容词吧。”
“孩子目光所及之处,率皆盛大庄严。”我不要我的小孩快快长大。
“微型世界是‘巨大感’的庇护所之一。”
“我有双手可以撷取你,我梦中纤细微小的百里香,我那极度失血苍白的迷迭香。”
“有一个在地窖里的死者,她不想死。”
“我听见自己闭上双眼,然后张开它们。”
“在想象的领土里,为何没有年轻的森林?对我来说,我只能冥思故乡的事物。”
“因为我们活在我们不在的地方。”
“主导我童年时期生活教育的格言之一:吃东西时嘴巴不要开着。”
“人的存有,是多么样的一条螺旋线啊!而这条螺旋线,又蕴含了多少峰回路转的动力!我们不能在当下明白,自己究竟是正在往轴心跑,还是正在逃离。”
“正因为太多的骑乘和太多的自由,正因为视野毫无改变,虽然我们极度渴望奔驰,但彭巴草原却变成了我的监狱,这个监狱要比其他的监狱来得大。”
“对波德莱尔而言,人类的诗意宿命就是作为浩瀚感的镜子。更正确地说,通过人,浩瀚感变得可以意识到自身。波德莱尔的眼中。人是一种辽阔的存有者。”
“因此一株树的命运就是长大。它传衍着这个命运。树木使每一件环绕在四周的事物长大。”
“它有极端的个体性,它的孤傲不群,它在社交上的脆弱。”
亚历山大·杜马在他的《回忆录》里说道,他小时候,极其无聊,无聊到要掉眼泪。他妈妈发现他怪怪的,他正在因为太无聊而啜泣着,妈妈就说:
“杜马究竟在哭个什么劲呢?”
“杜马在哭,因为杜马有了眼泪。”
克罗德尔《玛丽的告示》:
“维欧兰(盲人):我听见……
玛拉:你听见什么?
维欧兰:与我同在的事物。”
另一些旁思:
亨利·博斯科描述家屋如何与狂风战斗的文字,可以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对读。
“当我们住在一栋庄园领主的大宅第里面时,我们就梦想着一栋农舍;而当我们住在一栋农舍里的时候,我们又梦想着住在宫殿里。尽管如此,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农舍时光和宫殿时光。”杜甫的农舍时光与宫殿时光,这也是一个角度。
“就价值意涵的领域来说,一把钥匙在锁门的价值上要超过其用以开门。圆球形的门把通常被提到是用来开门的。”从私密感的价值角度来看,“推敲”可有新解。
读书亦是私密感的建筑,可以从中获取浩瀚感。考察中国文学的空间,可以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找家具。《太平广记》有七千则故事,可以当杂志。
巴什拉读诗,有三类人出现:文学批评家、精神分析师、现象学者(场所分析)。巴什拉不屑于前两者,他不要打碎来读这一切,不要用范畴去套这一切,不要见梦言性,不要不要,全都不要。他要一个浑圆的完整。他说:“一位文学评论者,必定是一位严苛的读者。经过了像手套外翻这样过度复杂的操作,作品反而被降格,成为政治家的部分措辞。”《孩子的政治》那篇对《天气之子》的电影评论,无疑是这类评论的佼佼者。他又说:“对精神分析师而言,诗意象永远有一个脉络。然而当他对它加以诠释,他便将之转译为一套跟诗意逻各斯大不相同的语言。事实上,没有什么比‘翻译者,背义者也’这句话更适用于此的了。” 在精神分析师眼中,“每一个圆整的东西当然都在要求爱抚。”
我的幻相的小书《梦的形式论》,与《梦的解析》本是形式与内容之殊途,但在“理解”与“回荡”这一对更高的对立中,却没有什么可以高尚的了。
巴什拉提到“梦想场所”,梦想是一个召唤所有事物的聚所。今年四月我也在赛博空间制作了属于我自己的“梦想所”。赛博空间亦有诗学,但不知谁来书写。
巢与壳。是扁圆与螺旋。是哺乳与软体。是分享与孤独。是开放与封闭。是安全与复活。是阁楼与地窖。是乡愁之旅行与在家之旅行。是搏击之小憩与恬静之疗愈。是家屋:天空向森林的投影。与我们:深海对沙滩的抛掷。
诗意化的哲学比诗更是诗。这是诗意的水库,收敛一切泛滥。是情感哲学。是读诗与被诗读的哲学。是形容词的幸福学。无数浩瀚的句子袭向我,裹挟以高维度的私密感。我只能回荡百分之一,并尽情站立在它们中央。沙漠是海水的回忆。而生命,一场旋转卡门。
另:巴什拉有书:《梦想的诗学》《火的精神分析》。巴什拉推荐马克思·皮卡德《寂静世界》。中国同方向书:王建元《现象诠释学与中西雄浑观》、刘若愚《现象学与文学批评》、余德慧《诠释现象心理学》《生死学十四讲》《生命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