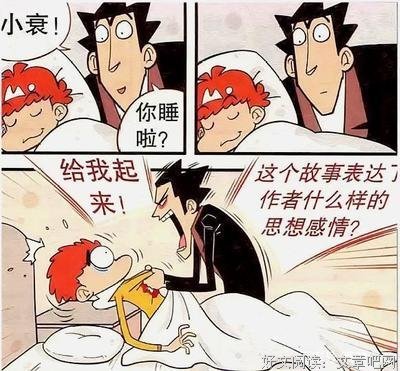
《金鸡》是一本由[墨西哥] 胡安·鲁尔福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2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金鸡》读后感(一):拉丁美洲的宿命与轮回
整篇小说里面没有太多的心理描写,起初试着通过人物的行为去理解他们,读到后半部分放弃了这种企图,仅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命运写下的种种奇异故事。
主人公迪奥尼西奥·宾松救下了比赛失败即将被杀死的金鸡,这只出现在题目里的动物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翅膀受伤的金鸡与手臂残疾的宾松命运相连,金鸡只在小说开头出现,却已经预示了宾松的一生,有沉寂,有辉煌,曾被命运眷顾最终又被抛弃。
他的一生中三个重要的女人:母亲,妻子,女儿。将生命力赋予金鸡的母亲,开启了他传奇的人生;带着他迈进命运布下的游戏的妻子——“阉鸡女郎” 贝纳尔达·古蒂尼奥,给他幸运却被怠慢;继承了父母命运的女儿,回到原点,开始新的故事。
似乎一切都是宿命与轮回,宾松在小说开始之时一无所有,连埋葬母亲的棺材也买不起,到人生结束之时又变回一无所有,最终躺在他为母亲准备的棺材里。追求自由的幸运女神贝纳尔达,她曾是生命的象征,精明强悍,却被禁锢和遗忘在大厅深处的阴影里直到生命逝去,那是因自己的幸运而赢得的庄园。女儿出生时拥有一切,却最终走回跟父母一样的道路。
贝纳尔达是一位性格坚韧的女性,而她同时也仿佛命运之神的化身。宾松依靠她带来的运气让罗伦索·贝纳维德斯输掉了庄园和其余财产。当贝纳尔达死去,一切开始失控,宾松输掉了多年积累下的全部财富。小说的结尾,他们仿佛早已失去了自我意志,变成了宿命控制着的提线木偶,无可抵挡的,被命运之手拖向那个注定的结局,最终黯然离场。
《金鸡》读后感(二):情歌
|所以拉美的斗鸡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娱乐活动啊……百年孤独的起源也是为了摆脱因斗鸡而被刺穿喉咙的那个灵魂的羁绊才踏上寻找马孔多的翻山越岭(莫非老马是在致敬么,以及无人给上校写信)|
—————————————————————-
他却看着对手,似乎在说:要捣鬼,你的手还笨了点。对方好像明白了,把牌递给迪奥尼西奥・宾松并说“您洗牌和发牌吧。”
他这样做了。
突然他感到要输了。他看到了自己如何一触即溃。
“我疏忽了。”他辩解说。
但是一小时之后,他输了个精光,全部赌注都跑到那位圣路易斯律师的手里去了。
就在那时候,他听见了一阵姑娘的笑声。这是响亮的笑声,欢乐的笑声,好像要把夜空划破似的。
他把脸转向妻子所在的地方;但是只见她很安详,睡得很熟,对那使他烦恼的笑声没有任何惊恐的反应。
“一定是我的女儿。她总是在这个时候回来。”他说,就像在回答什么人的问题一样。
然而在阿里亚卡兄弟中,似乎谁也没有问他什么。对方町了他一眼:“您说吧。堂迪奥尼西奥。”
他看了看自己的牌,把它们扔在绿色的绒布上。“我不赌了。”他回答道。
从家里的什么地方,响起了一首歌的开头,那是深沉而又遥远的声音:
请你去问夜晚的星星
是不是听到了我的哭声
请你去问它们,为了爱你
我是不是孤苦伶行。
请你去问温顺的小溪
是不是看到我的泪水流淌;
请你去问整个世界
我的心是不是无比惆怅···
如同回声一样,他听到了阉鸡女郎用热情的声音唱的同一首歌,那是她在斗鸡场的舞台上唱的,当时她正在看着地上那只色彩鲜艳的死了的金鸡。
他又听见了对手的声音:“您分牌吧,堂迪奥尼西奥。”
......
几天之后,那个曾经应有尽有的姑娘,就只有用嗓子来维持生活了。她在科科特兰的斗鸡场的木板台上唱歌,那是墨西哥最偏僻角落里的村镇。她也像母亲刚开始唱歌时那样,歌声中饱含着孤苦伶仃的感情:
孔雀啊,捎书的鸿雁,
你又要去“金钱”村;
人们要问我在做什么,
你就说我哭得伤心
我的血化作了泪水,
都只为我心上的女人···
“关门!”斗鸡开始了,吆喝的人叫道。
《金鸡》读后感(三):鲁尔福的遗珠之作
《金鸡》这本作品集里收录了鲁尔福最后创作的一个电影脚本《金鸡》以及他的另外几篇遗珠作品。鲁尔福三部曲里其他两部都是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但是之后鲁尔福宣布封笔。某些同行还揶揄他江郎才尽。但是鲁尔福并没有就此放弃对自己的家乡墨西哥农村的关注,他转而希望通过电影的方式将墨西哥呈现出来,于是在1960年鲁尔福创作出了这个电影脚本,1964年拍摄成了电影,1980年才作为文字发表出来。
《金鸡》的翻译者赵振江为本书作序,他现在是北京大学语言文学系主任。他与爱人段若川都是拉美文学专家,后者是另一位拉美魔幻主义代表作家邦巴尔作品集《最后的雾·穿裹尸布的女人》的翻译者。而鲁尔福也承认自己在创作《佩德罗·巴拉莫》时受到了邦巴尔这部作品的影响。
《金鸡》这个故事虽然体量很小,但是由于它承担着电影的使命,所以故事情节特别丰富生动。这个故事里集合了鲁尔福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各种符号,比如母亲、复仇、生命循环。这部作品中有两位母亲:主人公宾松的母亲以及后来成为宾松老婆又为他生下女儿的阉鸡女郎——贝纳尔达。贝纳尔达与其他作品中灰头土脸的女人还不太一样,她曾经有过辉煌灿烂且自由自在的人生。但是也许正因如此她承担了小说中魔幻的任务。她美丽又有幸运体质,就像沙漠里出现的绿洲、干枯的植物开出的花,绚烂但又虚幻。宾松一夜暴富然后又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的经历完成了一个循环,正如所有苦难的墨西哥农村人那样,永远翻不了身。
此外这部作品集中有一篇《死后》,是以死者的视角来叙述有关临死及死后的情景。这篇跟邦巴尔的《穿裹尸布的女人》有着相似的角度。鲁尔福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垂死时被活埋的人的感受。最后,鲁尔福说:“人活着的时候惩罚总有尽头,但是死人永远要受罚,因为死亡是永恒的。”没有出路,不管活着还是死了。
我有个感觉,鲁尔福的作品虽然主题永远是贫穷、死亡、痛苦,但是读完之后并不致郁。我认为是鲁尔福富有张力的文字解救了读者。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也好似在跟着农民们一同行走、奔跑、喊叫……
《金鸡》读后感(四):三本薄薄的“小书”,讲述拉美土地上最后的男人与女人
有一位作家,他一生只留下三部虚构作品,却成为《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导师;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也曾盛赞,说他的小说“世界文坛最佳”;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作品传入中国,启发了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在内,一代中国作家的创作。他,就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鼻祖,胡安·鲁尔福。
2021年1月正值作家逝世35周年。八十年代起,鲁尔福的作品被国内学者、研究者争相译介;进入版权时代后,译林出版社竞得独家版权,系统译介并常年耕耘。《佩德罗·巴拉莫》《燃烧的原野》稳居豆瓣高分,“想读”人数破万,绝版后一书难求。新版“鲁尔福三部曲”完整囊括了目前可授权的鲁尔福虚构作品:《燃烧的原野》是众多文学爱好者的心头挚爱,此前绝版多年;《佩德罗·巴拉莫》加西亚·马尔克斯倒背如流,各版本常年加印;《金鸡》是鲁尔福百年诞辰纪念版在中文世界的首度引进,收录十五篇鲁尔福文学国度的璀璨遗珠,这一版补充了鲁尔福撰写的“《金鸡》故事梗概”、“电影诗”《秘方》、一封给爱人克拉拉的信及鲁尔福于1945 年至1984 年间创作的十二个短篇小说,部分首次面世。三部读者期待多年的重磅力作,由知名译者赵振江、屠孟超、张伟劼、金灿从西班牙语直译,丛书封面独家采用鲁尔福私人摄影,展现作家眼中广袤而迷人的墨西哥大地,藏读两宜。
没有鲁尔福,或许就没有《百年孤独》
以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为代表的拉美“文学爆炸”繁荣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诞生了一批新意迭出、惊艳文坛的佳作。实际上,“文学爆炸”百花齐放的盛况,得益于四五十年代起“先锋派”作家们的锐意创新,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便是其中翘楚。鲁尔福虽然作品不多,但已足以成为二十世纪拉美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鲁尔福比《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大十岁。两位文豪间曾有一段趣闻: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作陷入瓶颈,一筹莫展的时候,有朋友扔给他一本书,让他好好学一学,这本书就是鲁尔福的名作《佩德罗·巴拉莫》。加西亚·马尔克斯读完后,整整一年无法再读其他作家的作品,因为觉得他们都不够分量。更关键的是,他直接在《百年孤独》开篇借鉴了《佩德罗·巴拉莫》的文字:
“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百年孤独》,1967)“雷德里亚神父很多年后将会回忆起那个夜晚的情景。在那天夜里,硬邦邦的床使他难以入睡,迫使他走出家门。米盖尔·巴拉莫就是在那晚死去的。”(《佩德罗·巴拉莫》,1955)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赞叹鲁尔福为“拉美文学王国最早的国王”,他深情回忆:“我能够背诵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全书,且能倒背,不出大错。”并坦言从鲁尔福的作品中“找到了继续写书而需寻找的道路”。
“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鼻祖,引领拉美“文学爆炸”的潮流
鲁尔福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流派的开山鼻祖、“拉美新小说的先驱”,是墨西哥国家文学奖、比利亚乌鲁蒂亚文学奖、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得主。
1917年,鲁尔福出生于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小镇。处女作刊发于自创杂志《美洲》,此后陆续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并于1953年以《燃烧的原野》为题结集出版。《燃烧的原野》以十七个故事讲述龟裂大地上的苦难与抗争、酷热与荒凉,成为墨西哥现代文学的开创性作品之一。
两年后,鲁尔福最为人熟知的代表作《佩德罗·巴拉莫》问世。通过一段寻找亡父的故事,鲁尔福徐徐展现了拉美这片人鬼莫辨的土地。小说不仅立意深刻,在艺术形式上也富有新意,迄今仍被认作“拉丁美洲文学的巅峰小说之一”。在《私人藏书:序言集》中,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丝毫不掩饰对鲁尔福的喜爱:“《佩德罗·巴拉莫》是西班牙语各国文学中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也是所有文学中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1956年,鲁尔福回到首都写作商业电影脚本,此后不久《金鸡》完成。《金鸡》于1964年拍成电影,由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联手改编,拉美文坛三巨头“梦幻联动”,文学创作与电影工业碰撞出耀眼的火花。两位文豪凭借《金鸡》捧得墨西哥电影大奖“银色女神”奖,《金鸡》更是荣膺“墨西哥百部最佳电影”。
1962年以后,鲁尔福几乎不再发表新作,他一直在墨西哥国立印第安研究所工作,直至1986年逝世,享年67岁。消息很快传遍世界,大师们纷纷哀悼。在西柏林,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称鲁尔福为“现代拉丁美洲文学之父”,并重申了他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一众拉美文豪的深远影响。在伦敦,古巴作家卡夫雷拉·因凡特称,“尽管距离《佩德罗·巴拉莫》问世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鲁尔福的作品却愈久弥新。无论美洲还是欧洲,鲜有作家在停笔多年后还能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在首都蒙得维的亚,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深切缅怀鲁尔福,称其为“拉美有史以来最伟大小说的作者”。
当苍茫大地时间停摆,鬼魂昼行
如果你看过皮克斯动画《寻梦环游记》,一定震撼于其中展现的墨西哥亡灵文化。“死亡不是分离,忘记一个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消逝。”电影中那种生死无界,庆祝亡灵节、欢迎亡者回家的观念,根植于墨西哥的传统文化与信仰。
阿兹特克人认为,人死后,若灵魂得不到宽恕,便难入天堂,只好在人世间游荡,成为冤魂。于是,《燃烧的原野》中,死人可以开口说话,向生者讲述不幸;《佩德罗·巴拉莫》里,苍茫大地鬼魂昼行,一座时钟停摆、生死模糊的村庄中,巨大的孤独成为一切的主宰。
作家不仅模糊了生死的界限,也打开了时间的入口。消解的时间里,回忆与叙述你一言我一语地散落在风中。在那里,时间仿佛停止了,人们谁也不关心一年又一年如何过去,“一个个日子,开始又结束。然后就是夜晚。只有白天和夜晚,直到死去的那一天。对于他们来说,死是一种希望。……坐在门槛上,看日出日落,头抬起来又低下去,直到最后一身的弹簧松弛了,然后一切归于平静。时间没有了,好像永远生活在永恒之中。”时间是比人能承受的最重的负担还要沉重的东西,当麻木和无望将人们包围,只剩下一种睁眼活着的孤独,而这孤独是永恒的,它盘旋在拉美广袤土地的上空,哀转无绝。
2017年,为纪念鲁尔福百年诞辰,墨西哥文化界筹办了一部纪录片,鲁尔福的儿子胡安·卡洛斯·鲁尔福循着父亲坐在托卢卡火山岩石上的照片,重游其生前之路。人们惊讶地发现,熔岩穹丘的形状棱角,历经大半个世纪,依然分毫不差。这片辽阔土地上空似乎漂浮着无数时间的入口,而逝者的低语也在耳边不停盘旋,重复讲述过去的故事。
“小人物”的悲哀与困境,每个人命运轨迹的写照
鲁尔福写普通人的命运。父母给女孩准备了一头母牛作嫁妆,以期其不致堕入红尘,可偏偏一场洪水把牛冲走了,一同消失的是女孩未来的希望;烈日暴晒,农民们分到一片寸草不生的大平原,而政府的人却说,“你们可不要高兴坏了”;为讨生计,青壮小伙不惜以身犯险跨越国境,挫败回乡却发现老婆和人跑了……在这片“让忧伤筑了巢的地方”,生活的重担压在人们肩头,让人窒息,“就像是在活蹦乱跳的心头敷上了一大块烂泥”。在这里,生是死的开始,死是生的希望。
也有“走运”的例子,一个一无所有的小伙,偶然间通过斗鸡发了财,却终因挥霍无度一贫如洗。半生辗转,一夕尘土。用鲁尔福的话说,“命运之神是不会骑着蠢驴走的。”在作家笔下,命运如同一个大转盘,或许每个人一生都会经历从贫穷,到出现转机,到达顶峰,又峰回路转,甚或反反复复几番起落,而这荒诞的轮回之路,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命运的写照。
鲁尔福善于以诗意而细腻的笔调展现残酷﹑绝望的美洲大地,谱就一曲拉美土地守望者的悲歌。对此,富恩特斯认为“胡安·鲁尔福反映的是拉美土地上最后的男人和女人。”鲁尔福展现的,不仅仅是墨西哥的乡土世界,更是对人类命运的反思,在满是尘土、热浪和孤绝的文字里,试图呈现从贫瘠土壤中盛放的原始、丰饶而顽强的生命力。
参悟生活真谛的“金句王”,令人过目难忘的“情话大师”
爱恨情仇,背井离乡,岁月流逝,人生轮回……鲁尔福的文字不仅精炼,且“金句”频出,涉面颇广。关于生死,他写道:“要绝对地确定哪里是生者与亡人之间的界限已属不可能。……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知道死亡的年岁有多长。”因此,要“想一些愉快的事情,因为我们将会被埋葬很长的时间。”关于工作怪相,他说:“在这里,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人变成了机器,而机器却被当成人来对待。”关于生活愿景,他说:“人必须生活在自己觉得最开心的地方。人生短暂,长眠无期。”
在鲁尔福的字里行间,还能品出某种刻骨铭心的爱情。《佩德罗·巴拉莫》中不可一世的独裁者,面对青梅竹马却有着无比柔情的一面:“那时世间有个硕大的月亮。我看着你,看坏了眼睛。”“我凝视着被雷电照亮了的雨丝,每次呼吸都是一次叹息。我一想就想起了你。”小说对情话的“信手拈来”,或许也源自现实生活中鲁尔福与克拉拉之间的爱情。在《金鸡》收录的一封写给爱人的信中,鲁尔福撒娇似的写道:“你知道我的这颗心属于你……这位小伙子心烦意乱,想比现在还要爱你。”收录有八十余封鲁尔福与克拉拉往来信件的“情书集”《致克拉拉的信》,也将于明年与读者见面。
我们常问,拉美文学,除了《百年孤独》我们还能读什么?或许,在“魔幻现实主义”鼻祖、墨西哥文学大师胡安·鲁尔福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打开拉美文学的另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