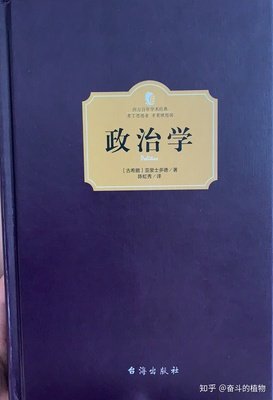
《精神政治学》是一本由[德] 韩炳哲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1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精神政治学》读后感(一):情绪资本主义
同时对于feeling/emotion/atmosphere三者的区分,对我来说是比较新的一点内容。
其实读的过程中隐隐约约让我联想起德波景观社会里描述的一些观点,跟情感资本主义一道,构成这个颠倒再颠倒,沉浸在消费主义狂欢的世界中。
the ego grapples itself as an emeny.
《精神政治学》读后感(二):无题
书中提到的精神控制,不免让我想到。三天可见的pyq现象,人们依赖着三天可见的pyq维系着一股神秘感,却不知早已被网络信息留痕所生成的大数据看的透透的,甚至可以预见你潜意识的想象,对你的思绪干扰及预判,人就好似一个傀儡。5G时代的来临 更让那没有思想的我 暴露无疑,在这个时代里好似无意识的裸奔。我则是那个散漫在各个媒介以汲取新思想赖以生存的吸血虫,又好似那个摇曳在各家论述的跟屁虫。
摘课本:
1.绝对的自由和交际现在变成了被控制和监视
3.数字化的精神政治权则能够有预见性的干扰心理变化的过程,它也许可以在速度上超越自由意志,赶在自由意志之前发挥作用,这可能就意味着自由的终结
4.大数据是纯粹的叠加产物,永远得不出结论,永远无法终结
《精神政治学》读后感(三):统治的新形式
《精神政治学》读后感(四):评《精神政治学》
《精神政治学》读后感(五):一点吐槽
批判理论爽文的套路:启蒙颠覆为神话、自由颠覆为强制、个性颠覆为从众,把对手刻画为资本的神学、消费的目的论。
爽文家的最高境界真的不是段子手吗?
反正看这种文的时候我的心理就是:“嗯,很有趣,说得很有道理……可是,知道了又能怎样呢?”
作者暗示的出路是“掏空主体”(sub-ject意味着屈从;pro-ject以自由之名走向强制;),在无目的的游戏中获得解放的潜能。典范是白痴(Idiot)和小孩子。不能用“有个性”来描述小孩子,自主选择的才能叫个性,小孩子的特征则是容易被周遭感染、甚至可以说没有独立自主的意志,作者则称此为“独特”、“空无”、“纯粹的内在性”、“无人格的Ereignis”。
(。。我觉得又是饶舌作家的闪烁其辞,而且略带神棍气。还有一股子我哲学家高高在上的味道,和土豆公社的影评风格如出一辙。如果这些哲学王们能从内部角度给出对具体事例的分析与批评(然而这似乎不是“哲学”的任务),或许会更深刻。好比一提到追星就说别人盲目幼稚而罔顾群体内部的差异,那用这种论调写出来的东西也只是供人娱乐而已,摸清套路以后基本上都能知道他下一句要讲什么,不同的只是修辞。
*
很快地翻完这本书(译笔顺畅)以后看了下译者好像没有专业背景。鸡蛋里挑骨头:
1、psycho译成“精神”好像不妥当(甚至有蹭黑格尔热度的刻奇之嫌),因为“精神”更接近于表达一种整全性的存在(holy spirit)与认知,还是“心理”好一点,因为作者用psycho更多是表达一种反应机制,指称在大数据透明社会中人被操控的现象。
2、project译成“客体”,虽然我也不知道译成什么好(想了一个好玩的译名“策体”)。
3、Transcendenz“超然”、“超越论”,Theologie und Teleologie“宗教性和目的性”……读着有点懵
《精神政治学》读后感(六):值得思考的『精神政治学』概念摘抄
【自我优化】=【自我剥削】?【个人自由】
【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 QS)
“数字不能叙述自我。算数不是讲述。我只为我,要感谢的是叙事。是叙事,而不是技术,引发了自我找寻,或说自我认知。”
【自我书写】——自我担忧的践行
“自我书写致力于追求真相。把自己记录下来,有助于形成个人伦理。数据主义则清除了伦理与真相的自我定位功能,并且让这种自我定位沦为自我控制的技术。”
【自我定位】=【自我监控】
“浪漫派的基调就是对平均和常规感的厌恶。他们用稀有性、不确定性以及突发性来反驳统计、计算出来的极大的概然性。浪漫派以其中意的奇特性、异常性和极端性来反对统计学的常规性。”
【痴言痴语】
德勒兹(Gilles Deleuze):“毫不夸张地,我认为,他们装傻。装傻,一直以来也是哲学的功能之一。”哲学扮演的是一个装疯卖傻的角色。哲学从出事就与痴傻紧密相连。
“鉴于交际强迫和从众强迫的存在,痴言痴语可以说是一种对自由的实践。”
《精神政治学》读后感(七):自由意志是否存在
《精神政治学》读后感(八):精神政治学
作者在这本书中对《爱欲之死》中的“我能”比“我应当”产生更多的强迫性,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我应当”可以归为本我,“我能”贴近于自我,即自由意味着摆脱强迫,“我能”便变成了自由强迫摆脱强迫,这句拗口的话表达了一种根源性的强迫,所谓物极必反而已。
作者探讨了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变种,将被他人剥削的工人阶级转化为自我剥削的企业主,即将阶级斗争转化为自我斗争。这种自我剥削并无阶级之分,也使得人们不能形成阶级同盟,“在新自由主义功绩社会中失败的人,要自己承担失败的责任,并以此为耻,而不是去质疑社会或者体制。
”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宗教,人们为了受到约束而创造了上帝,每个人都是背负罪债的罪人,而资本同样让人们背负债务 ,俨然是让人们成为负罪之人的新上帝。
在政治中,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让公民变成消费者,政客们就如同商家,消费者相对于商家是被动的,所以消极的对待政治活动,这也造成了政客们不是比谁更好,而是比谁更差。
在技术上,作者提出大数据可以量化并预测人们的行为,新自由主义政权正如对待消费者一样,是鼓励人们去消费的,包括人们的情绪。传统稳定社会的理性宣传手段,在生产水平处于一定程度会到达极限,会让人们认为是一种强迫和压制,显得呆板和不知变通。这样与自由相伴的感性便取代了理性,感性相对于理性更加易变,这样生产中便带来了更多变化,感性相较于理性更有效率,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作者认为当人被彻底量化,就会失去意义。作者的书名精神政治学,在美国利用社交媒体,掌握选民偏好的例子上得到了体现,利用微目标定位吸引选民兴趣,通过大数据预测使演讲更迎合选民喜好,国家越来越像市场,公民越来越像消费者。
作者认为精神是推论的集合体,而大数据将会产生绝对的认知,从而使精神回到绝对的无知。作者把大数据比作启蒙运动的统计学,而统计学中的概率只能给出当下的平均值,并无法准确预见未来。
私以为这本书的翻译同样有直译的偏向,虽然还不至于产生那种所有字都认得,一眼看过去就是读不懂一句话的感觉。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新自由主义在潜移默化的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作者在书的末尾的最后一段提了句如何摆脱“樊笼里”,想来人生在世,绝对的自由也很难吧。
《精神政治学》读后感(九):韩炳哲和他的《精神政治学》
韩炳哲在《精神政治学》中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观点,比如数字化社会是规训社会和控制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智能手机成为新的监控工具,自我优化实则是自我剥削,消费资本主义是对情绪的消费……
初看这些观点,切中当下社会发展的新样态。但我怀疑,这些观点可能不是韩炳哲个人的创见,如同《在群中》和《爱欲之死》,是博采众长的结果。
之所以提出这个论点,是因为在阅读吉尔·利波维茨基的《空虚时代:论当代个人主义》《超级现代时间》时,已经发现相似观点。《超级现代时间》出版于1983年,远在《精神政治学》之前。
《空虚时代:论当代个人主义》论述“后现代”,《超级现代时间》则更进一步,吉尔·利波维茨基认为西方社会在“后现代”之后进入的是“超现代”,一种现代性发展到极致的时期。
“超现代”特点是超级个人主义、超自恋主体和超级消费主义的盛行,人失去了“后现代”时期无忧无虑的状态,为不确定的未来感到忧心忡忡。
在《空虚时代:论当代个人主义》中,吉尔·利波维茨基认为人在后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是自恋,“在日常生活中将自主自我管理的自由理念加以具体化的革命,后现代社会基本的价值观,最重要的是自我,个人自我完善与个人自由。”
当人无止境地自我完善,自我实现,实际上正入社会管理的下怀,不再是福柯所说的生命治理,而是一种规训内化的自我管理,“社会矫正的顺利进行也不再取决于纪律的约束与高尚的情操,而是要依靠自我诱惑。”
“自恋作为一种弹性的、自治的控制新技艺,通过非社会化实现了社会化,实现了个体与支离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和谐,使得大行其道的纯自我的全面发展也变得光荣起来了。”
这与韩炳哲提出“自我优化被证明是毫无保留的自我剥削”的观点如出一辙,“新自由主义政权将他人剥削转变成波及所有阶级的自我剥削”,自由实际被精准控制。
这同样表现在消费上,人在进入“超现代”社会后,在“消费中所要寻找的,是一种感觉、一种情感享受。它更感兴趣的是感觉新事物的经验,而不是名誉地位。”韩炳哲提出相似的观点:“今天,我们最终消费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情绪。对商品的消费不无尽头,然而对情绪的消费则是无边无际的。”
在《超级现代时间》之中,吉尔·利波维茨基已经发现当下社会不再是福柯式的规训社会,甚至越过了奥威尔式的监控社会,发展为规训和监控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说,一种自我规训社会的诞生。
这就是超级消费主义的陷阱,人不断满足自身欲望追求的过程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加速发展一体两面,人看似实践自由意志,实际上是消费资本主义诱骗的谎言,结果是失去自身,也就是成为奴隶。
“功绩至上的主体(Leistungssubjekt)自认为是自由的,实际上却是一个奴仆,是没有主人强迫却自愿被剥削的绝对的奴仆。没有主人强迫他去劳动。活着这件事因为只剩下劳动而变得纯粹。”过劳死于是成为当今时代的典型。
不过,韩炳哲论述大数据和智能手机时提出的观点,是吉尔·利波维茨基的书中没有的,两者都是最新出现的事物。无论如何,韩炳哲提出的“精神政治学”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弊病,值得人深思。
《精神政治学》读后感(十):《精神政治学》摘抄三则
《自由的危机》
每一种机制、每一种统治技术,都会创造一些用来向自己表达虔诚信仰的圣物。这些圣物是让人就范、折服的工具。它们使统治物化,且变得稳定。虔诚就是一种屈赋。智能手机就是一种数字化的圣物,一种最能对数字化表达忠心的圣物。作为主体化的工具,它和玫瑰念珠发挥着同等的作用。在便携性方面。玫瑰念珠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智能手机。不论是玫瑰念珠还是智能手机,二者皆服务于自我检测和自我控制。通过将监视的任务委派给个人,统治提高了它的效率。“点赞”(Like)就是以数字化的方式说“阿门”(Amen)。我们“点赞”的同时,就已经屈从环境威力法则(Herrschaftszusammenhang)了。智能手机不仅是有效的监视工具,也是移动的告解室。脸书则是数字化人类的全球犹太会堂(Synagoga)。《痴言痴语》在1980年的斯宾诺莎讲座上,德勒兹发现:“毫不夸张地,我认为,他们装傻。装傻,一直以来也是哲学的功能之一。”……只有傻瓜才能理解“异于是”(das ganz Andere)。痴傻从各种事件和个别性中抽丝剥茧,为思想开辟出排空主体和心理作用的内在平面(Immanzfeld)。哲学史就是一部痴言痴语(Idiotismus)史。知道自己无知的苏格拉底是一个傻瓜,怀疑一切的笛卡尔同样是个傻瓜,“我思故我在”彻底是一句胡话。思考的内部缩减成全了另一种思考的发端,思考通过向自身的回归,重新抱朴含真。今天,社会上的异己、蠢材或者傻瓜好像几乎都消失了。数字化全面联网与交际,大大提高了从众强迫(Konformitätszwang)的效应。……鉴于交际强迫(Kommunikationszwang)和从众强迫的存在,痴言痴语可以说是一种对自由的实践。……傻瓜是现代的异教徒。 纯粹的内在性是既不能被心里化、也不能被主体化的空无(Leere)。内在性正是在这种“空无”的映衬下显得轻柔、丰满、自由。傻瓜的特征既不是个体性,也不是主体性,而是独特性。因此,傻瓜与还不能称其为独立个体的孩子在本质上相似。构成其此在(Dasein)的,不是个性上的特征,而是无人格的自在发生(Ereignis)。……傻瓜可以进入的内在性层面,是去主体化和去心理化的矩阵,是使主体摆脱自身,拯救其进入“虚空时代无限空间”的否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