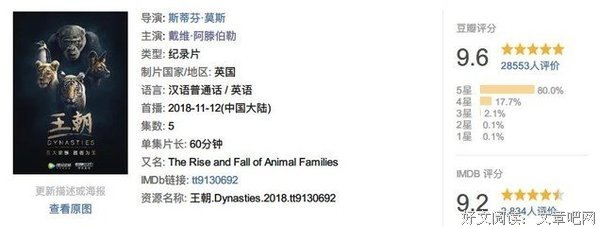
《草原王權的誕生》是一本由林俊雄著作,八旗文化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NT$550,页数:4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草原王權的誕生》精选点评:
●毕竟证据太少,想说明的东西又那么抽象。
●还是挺不错的一本书,我觉得最优秀的地方就是对于考古发现的介绍和整理,以及作者本身对于东西方文献内容的分析和解读。上面看有人觉得这本书定位有问题,我觉得倒不是,其实照顾可读性的时候作者也是向普通读者传递一些学术思想,我觉得这样的书要比那些讲故事精彩得书更有价值。当然本书的内容也不是十全十美,作者本身把游牧者起源与骑马做捆绑显得有些奇怪,而且对于部分考古和文献的解读我觉得还有待讨论。
●大三看的(上学期) 这段时间疯狂痴迷游牧民族文化
●其实挺一般的,没什么有趣的新观点,比起学界研究更像科普读物,林俊雄先生差不多是复读式的重述了一遍07年在讲谈社写作时的观点,以1970年南西伯利亚斯基泰古坟为论据的“东方起源论”和以斯基泰墓葬汉朝金制品为论据的“汉-匈奴-斯基泰”贸易路线,以及通过独特的二重棺椁在Tsaram首次出现对匈奴起源的推断。首次见到这些观点是蛮有意思的(虽然也是来自学界考古发现和学界发表文章的总结与统计),但是第二次再看特别是作为近年刚出版书看未免有拿07年的老调在19年重弹的意思
●主要描述斯基泰时期和匈奴时期,分别用历史记载和考古资料讲诉,斯基泰前简短讲诉马、骑马和游牧的起源,匈奴之后简述前突厥时期或匈人时期。斯基泰的鹿石传播,东西方文化影响;匈奴的青铜鍑形制从东方到西方等;骑马技术和硬式马鞍;匈奴的大型墓葬和定居点遗址;斯基泰的木乃伊制作文化等
●史书记载与考古发掘的结合,对于这段模糊的历史也许是最好的叙述方式了。
●長書評已發表於《晶報‧深港書評》,原題為「歐亞遊牧文明起源的新認識」。請參見https://mp.weixin.qq.com/s/DSTvEVlspsrgk3AjR137-w?fbclid=IwAR0fNGfhnKO0Y7lL3B81eLOxCCAsnUae68B6UPpfHbhlGeFRkwgAp_RZbSo
●从考古学、神话学等角度解读早期草原政权的历史。在考古资料的介绍和引申上做的很好,囊括了俄、蒙、日的大量成果,也带到了一些考古学界的八卦哈哈哈。但缺点在于历史叙述的节奏没有把握好,尤其是斯基泰人和匈奴人之间过渡地好生硬,以至于前脚还是神话、仪式、墓葬、美术交织而成的洪荒色彩的斯基泰历史,后脚就来到了明朗、亲切、几乎就是通俗版史记的司马迁笔下的匈奴历史,这还是有点违和啊,按说作者也多次强调中国北部草原与东欧、中亚草原的联系,却未能在此基础上深化对草原历史的整体表达,略遗憾。
●这套丛书给人最大的启发是作者擅长在全球史的视野中,发现东西方历史叙述的共通性,本书伊始,作者列表对比希罗多德《历史》中对斯基泰人生活习性的记述,对比《史记》中司马迁对匈奴人的记述,总结分析出上古时期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特性,继而积累了丰富的考古学术史材料,打通了日、美、中、俄、蒙各国公布的考古资料,尽可能地复盘了斯基泰人和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和历史源流。从另外一个层面思考了考古学之于重塑历史的意义,以及没有后代的民族历史始终存留偏见与缺憾。
●两大部分,一个分析对比考古发现,一个梳理检验文字资料。受钟老师书的影响,阅读过程中始终觉得作者在突出或者暗示某些地区的起源可能性。。早于丝路的交流,令人惊讶的东西传播,西欧人所谓地理大发现的中端是海洋,欧亚大陆的草原又何尝不是游牧民发现未知世界的海洋。
《草原王權的誕生》读后感(一):草原帝国前传
本书的副标题就直接说明了两个研究点,斯基泰和匈奴。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两个民族的历史多有模糊之处,幸好,早期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笔下分别描述了这两个民族。相比之下,司马迁对匈奴历史的描写更加清晰,也使得匈奴的史料较斯基泰人更多。当然,汉匈百年战争读者多已比较熟悉,作者深厚的考古学功底才是本书的特色。
草原气候的干燥带来了游牧生活,和一般认知不同,是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骑马证明更早,而草原骑马证据则要到公元前九到八世纪。作为欧亚大陆北方大草原东西早期的两个强大游牧民族,斯基泰和匈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其实也是对游牧民族的整体概括。斯基泰人是幼子继承制,而突厥和蒙古也是如此。
游牧民族早期多建立巨大的坟墓,用于宣传草原王权,这也是作者用于考证草原王权起源的直接证据。除了王坟,还有按照远近大小递减的陪葬坟。等到政权稳定了,为了防止盗墓,坟墓会越来越小和隐蔽。坟中像定居王国一样有着彰显权威和富贵的大量陪葬品。斯基泰的文物受到西亚和希腊文明影响,而匈奴的坟墓出土物也多见汉朝元素。在斯基泰坟墓中居然发现了战国镜子,证明早在丝绸之路之前就有以阿尔泰为中枢的欧亚大陆东西向商业交流。
匈奴有据可查的登场时间是在秦统一六国前后,利用秦末乱局顺利壮大,并在汉初持续压制汉朝。和中原不同,匈奴对于汉人的接纳包容度很高,不论是投降还是俘虏都很容易身居高位并得到信任,中原的叛乱分子多寻求北方支持。草原王朝不仅有游牧民,还有大量的农耕、商业人群。而且对宗教的包容度也很高,各种宗教人士都可以并存。在匈奴失势后,内附的匈奴仍保持较高独立性,直到王莽时代才强迫其正式纳入新朝政治体系。但是南北分裂后的匈奴再无力和中原开展全面战争,成为半依附中原的群体,一直要等到刘渊的崛起了。
《草原王權的誕生》读后感(二):读书笔记
一、 1.作者讲述了在蒙古发掘的情形与思绪过程,得出该地区的赫列克苏尔确为游牧民古墓,并且该墓表明了权力阶级的产生和社会分化。 2.本节作者阐述了证明游牧民群体中动物的家畜化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已有的研究确切表明家畜化是从人类定居方式时开始的。 3.游牧是何时产生?怎样产生?这是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更好的解答,不过在前八、九世纪时,草原突然出现大量的骑马活动,这就是斯基泰游牧民的开始。 二、 1.斯基泰人从何而来呢?希罗多德的《历史》揭示了三种情况。第一和第二都是说明斯基泰人起源于神话,是神与地上的女人的后裔。这两种说法都有相同之处,那就是都是由外来人与本地人结合而形成的游牧民集体。 2.第三种情况是怎么样呢?也许斯基泰人是外来入侵者,将在黑海北岸的辛梅里安人赶走,这就是外来说。值得一提的是,外来说也是后来史学界多数认同的学说,一开始是被本地说支配的。 3.现在的研究者几乎不相信希罗多德所说的斯基泰人驱赶辛梅里安人一说。关于斯基泰人起源问题,现在仍无定论,作者提出了可能的观点,那就是斯基泰人也许不是统一的集体,而且一群群独立的佣兵集团,“服务”于西亚地区的各个国家,同时也进行着劫掠的行动。 三、 1.斯基泰西部的文化艺术是独立发展的,但也受到波斯和希腊的深刻影响,这是一种交融的草原文化。 2.斯基泰东部的文化艺术是独立发展的,并不受外界太大的影响,年代较西部较早。东西部都是存在交流的,这一点可以在其相通的艺术特点反映。 3.斯基泰后期的文化艺术愈发深受波斯希腊的影响,而且此时也出现斯基泰东西方交流的现象,也出现了中国的影响。作者推论,此时也许出现了一条从希腊到中国的草原之路,而斯基泰是这一切的交汇中心。 四、作者通过大量考古事实作依据,提出了斯基泰是具有王权结构的游牧民集体,而且还通过斯基泰后期的东西部考古遗址所展示的遗迹,指出了从东到西的迁徙潮的可能性。 五、在东亚蒙古高原上存在着相当势力的游牧集体,从西周开始就不断侵袭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双方有来有往,但总体上是战国一方处于劣势。到了秦统一,蒙恬北伐,将游牧势力击退,但是到了汉初又被白登山之围,被迫和亲。中国北方、西域以及蒙古高原起初分别为月氏、匈奴和东胡三大游牧势力,但到了匈奴莫顿单于时期,就东灭东胡,西征大月氏,形成了一个统一草原的匈奴势力。 六、司马迁笔下的匈奴是具有王权阶层、军事组织、祭祀活动的一系列特征的游牧社会。匈奴虽说是游牧社会,但其内部也需要农耕作业的支撑,而这些农耕者多是汉人以及农耕化的匈奴人,其与汉的经济往来互为补充(马与丝绸等)。武帝时期一改和亲政策,发动对匈奴的一系列战争,最后取得上风,开辟了西域。 七、匈奴与汉帝国的交锋对峙,你来我往,总的趋势是匈奴的衰退(由于各种原因)以及汉的前进。匈奴衰退的原因有内斗、天灾、叛乱和饥荒等因素,到最后直接引发了匈奴的东西分裂局势。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其兄)的大规模内斗,最后呼韩邪败走降汉,在汉的支持下统领着东部匈奴,最后将穷征黩武的郅支单于统领的西部匈奴败退中亚,从此失踪。 八、本章主要从考古学的视角看待匈奴,说明了匈奴存在着农耕与游牧的经济形态,其社会方式也受汉与中亚的影响。也提到了现实政治对考古研究的影响。 九与十、匈人是匈奴人的后裔吗?作者初步的向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一论争的主要观点,说明这些仍待核实。作者还讲了以匈人为代表的游牧群体在东西方交往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不能用定居型社会的观点去评判游牧民有无文明的观点,主张应该根据游牧民的情况来判定游牧文明。
此篇鄙人读不通,一知半解不得要领,敬请谅解。
《草原王權的誕生》读后感(三):欧亚游牧文明起源的新认识
按:本文已发表于《晶报‧深港书评》,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DSTvEVlspsrgk3AjR137-w?fbclid=IwAR0fNGfhnKO0Y7lL3B81eLOxCCAsnUae68B6UPpfHbhlGeFRkwgAp_RZbSo
在欧亚世界的历史长河中,骑马游牧民常常扮演着传递东西文化的角色,而他们与定居民族之间的交往与冲突更是推动历史演进的主要动力之一。而分据欧亚东西两端的匈奴与斯基泰,则是开骑马游牧民国家先河的两个人群。他们在历史上建立了强大的游牧政体,并且对南方的定居文明造成威胁。但由于骑马游牧民很少留下本民族的历史记载,因此后世要了解他们的历史,常常得仰赖定居民族对他们的描述,而这些描述又不免带有偏见,并且视骑马游牧民为野蛮与残暴的人群。时至今日,透过考古发掘与科学分析,让我们在文献史料之外,有了更多的材料能够重建这些骑马游牧民的历史图像。而接下来要讨论的这本《草原王权的诞生:斯基泰与匈奴,早期游牧国家的文明》可以算是结合传世文献与新近考古成果,建构斯基泰与匈奴历史的尝试。
该书作者林俊雄(Toshio Hayashi)为日本古代中央欧亚史与中亚考古学家,研究主题包括游牧民国家的出现与扩张、欧亚大陆草原上的石像、丝路上狮鹫图案的传播,以及马具与打火石的起源等等。著有《欧亚大陆的石人像》(2005)、《狮鹫的飞翔——以圣兽观察文化交流》(2006)、《游牧国家的诞生》(2009);合著有《中央欧亚史》(2000)、《中央欧亚的考古学》(1999)。
作者说明了选择用骑马游牧民一词来称呼斯基泰与匈奴的缘由。他不赞同已故东京大学东洋史名誉教授江上波夫(1906-2002)所提倡的“骑马民族”概念。作者认为所谓 “民族” 概念作为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实体,恐怕并不适用于古代欧亚的游牧民,因此选择了比较中性的“骑马游牧民”一词。而斯基泰(Scythian)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骑马游牧民当中最古老的一支,他们于公元前八世纪起就活跃于今高加索与黑海北方的草原地带和西亚地区,成为波斯帝国与希腊的重要对手。匈奴则是稍晚于公元前三世纪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以今蒙古高原为根据地,和东亚的秦汉帝国相对峙。可以说他们塑造了后世游牧与定居社会互动的模式,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
首先骑马游牧民的诞生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配合。作者认为遍布蒙古高原的赫列克苏尔(俄文khereksur)石塚不仅是象征骑马游牧民兴起的遗迹,也是显示草原权力产生的指标。而骑马游牧民在欧亚草原上的登场也历经了一段漫长的过程。最早是公元前七千至前六千五百年间,羊逐渐成为主要的家畜。接着自公元前五千五百年开始,气候开始逐渐暖化,开始出现草原干燥化的情形。但是促进草原游牧化的因素,除了气候以外,还有技术层面的因素,即车与骑马技术的发展。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明了车。到了公元前两千年,在乌拉尔山东侧以南西伯利亚与中亚出现了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以及西侧的斯鲁布纳亚文化(Srubnaya culture),已知这两种文化开始制造青铜物品。到了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人类开始使用马衔(马嚼子)与马镳。而到了公元前九至前八世纪,草原上骑马的证据突然暴增,而这被视为是斯基泰系文化的起源。
作者梳理了文献与考古材料,试图说明斯基泰人的起源。他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例,讨论了希腊文献中对斯基泰人起源的三种说法,分别为宙斯后裔说、海克力士后裔说,以及外来说。作者认为只有第三种外来说缺乏神话色彩,才是最可信的说法。简言之,外来说主张斯基泰人原先为亚洲的游牧民,但因为不敌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入侵,因此西迁至高加索北方至黑海北岸的草原地带,驱逐了当地的原住民辛梅里安人(Cimmerian)。然而直到1980年代前,外来说在考古学界(特别在苏联)并不是主流看法。作者一方面归因为苏联考古学受到唯物史观的指导,重视社会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忽略外来影响,另一方面当时也确实尚未发现东方草原上存在更早的斯基泰人遗迹。这种情况要到1970年代前半,位于南西伯利亚的图瓦共和国境内发现了阿尔赞(Arzhan)古坟(一号坟)后,斯基泰人外来说才逐渐成为主流学说。
基泰文化的特征为其风格强烈的动物图案,特别是在马具与武器上的纹饰或装饰。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许多中后期的斯基泰古坟在北高加索与黑海北岸被发现,并且伴随着大量的精致金银制品出土,当中充满了希腊与西亚影响的痕迹,而又以西亚较早。因此过去认为斯基泰艺术起源于西亚,但随着欧亚东部草原考古的开展,东方起源论逐渐占据上风。可以说初期斯基泰艺术并未受到希腊与波斯等邻近文化的影响,充满了原创性。斯基泰艺术受西亚影响之处体现在对猛兽、鹿眼的表现方式与石榴图像的应用;而受希腊影响之处则彰显在希腊风格的狮鹫(英文Griffin或Gryphon,也译为格里芬)图像的应用上。然而1971至1974年在图瓦所发掘的阿尔赞二号坟,当中都未见西亚与希腊式的出土物。且该坟的时间约为公元前七世纪末,时间较西部遗址来得早,因此成为斯基泰艺术东方起源论的有力支持。另外作者还指出,从中国新疆伊犁河上游出土的塞迦文化物品中,发现了受到阿契美尼德王朝与古典希腊时期风格影响的格里芬图像,而且在今阿尔泰共和国境内所发掘之斯基泰后期文化之巴泽雷克(Pazyryk)遗址中,也发现了中国的丝织品与战国时代的镜子。可以说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两三百年的时间,阿尔泰地区的人就已经开始跟欧亚东西两端的文明进行交流了。张骞只是沿着原有的贸易路线旅行而已。作者以此强调了史前丝绸之路的存在及其重要性。
在欧亚大陆西部,也存在与斯基泰同期的其他文化。包括了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文化、巴尔干半岛上的色雷斯文化与安纳托利亚半岛上的吕底亚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在美术样式上类似,而且都以大型圆形坟墓为主。作者介绍了图瓦的阿尔赞古坟、哈萨克斯坦的齐列克塔古坟、别斯沙特尔古坟,与北高加索的克拉斯诺伊兹纳姆亚一号古坟。这些古坟的出现代表从青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生产力提高,掌权者所控制的财富也大幅增加。加上与地中海和西亚文明的交流,使得工艺技术也有所提升。这些巨大古坟的出现及豪华的陪葬金属工艺品,显示掌权者以此夸示权利,也象征着王权的出现。斯基泰时代可说是草原的古坟时代。
到了公元前三世纪,匈奴登上了欧亚大陆东部的历史舞台。作者主要以中文历史文献记载,搭配考古材料,以描绘其历史发展轨迹。文献部分大致以《史记》与《汉书》等正史的记载为主,叙述了冒顿与老单于的故事。较有可观之处的是他从考古证据来探讨匈奴先祖与月氏。作者指出公元前四至前三世纪,北亚草原地带的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地区,分别是1) 北京、河北省地区;2) 内蒙古中南部;3) 宁夏、甘肃省地区。它们彼此间虽然稍有差异,但大致与黑海沿岸的斯基泰文化和阿尔泰附近的巴泽雷克文化相近。而关于月氏,作者倾向将其领域扩大解释为蒙古高原西部至新疆。如此一来,巴泽雷克文化就可以被视为是月氏的遗留。这个说法最早由日本的榎一雄(Kazuo Enoki)与苏联的鲁坚科(Sergei Rudenko)等考古学家于1950年代末期所提出。
作者质疑了过去以文献建构的匈奴政治社会体系,而且试图用今日的蒙古文化与风俗来理解过去关于匈奴的记载。例如,《史记•匈奴列传》中对匈奴社会中存在四王二十四长与其兵力共四十万骑的记载,就被作者视为无法自圆其说。而为了解释匈奴的王与将领名称都带有左右方位,他以今日的蒙古人方位观坐北朝南来解释,左手边(蒙古语züün)就是东方,右手边(蒙古语baruun)就是西方。另外司马迁记录匈奴无封树堆土为坟之俗,从后来《汉书•匈奴传》记载乌桓发掘匈奴单于墓一事,可以说明外人其实知道单于墓的方位,而作者利用了蒙古国诺彦乌拉古坟,来重建匈奴贵族坟墓的可能样貌:即以方坟为主,并且出土汉朝的丝绢与漆器。作者据此解释所谓匈奴坟墓“无封”之俗,实际上是低坟丘之意,而且刻意不显眼。另外,从文献与考古证据(例如位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的伊沃尔加遗址)都说明,匈奴内部除了游牧民以外,也存在西域绿洲与汉朝逃人所经营的农业聚落。另外,随着欧亚东西两端的物质文化交流开展,各种概念与文化也同时在不同人群中流通。例如带有中国龙图像的铜镜与腰带在阿富汗与黑海北岸出土,说明龙的母题也传到了中亚与南俄。
匈奴与西元四世纪入侵欧洲的匈人是否为同源一事是过去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最早是由法国历史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所提出的匈奴与匈人同源论所引发。对此,作者认为虽然匈人的作战与生活方式与斯基泰、匈奴相同,很可能是亚洲系的骑马游牧民,但没有足够证据断言匈人就是匈奴。而在公元三至六世纪前半叶间的前突厥时代,在欧亚草原西部,主要的考古遗物包括贵金属工艺品、马鞍装饰与鍑(游牧民族在仪式中使用的釜)。而马鞍、马镫以及“匈型”鍑从欧亚草原东部传到西部的过程,也说明游牧民在欧亚大陆上不仅弘扬自身文化,并且也扮演促进东西文明交流的角色。作者在结语中也反思了斯基泰与匈奴这些由游牧民所建立的国家是否能符合以定居民族的标准来衡量其文明程度,并且坚信游牧民及其文化也会继续在中央欧亚的草原上延续下去。
作者林俊雄在写作该书时引用了许多蒙古国的新近考古成果,然而过去中文学界缺乏一本蒙古国考古学的综述书籍可供读者参照。如今有了新的译作引进入中文世界,实为学界福音。这就是2019年5月出版,由前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D. 策温道尔吉、前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主任D. 巴雅尔等人合著的《蒙古考古》。原书蒙古文版于2002年发行,2008年发行俄文增订版,由D. 莫洛尔俄译。简体中文版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潘玲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远东人民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所博士生何雨濛等人翻译。内容涵盖了石器时代至蒙古帝国时期的蒙古国考古成果。
以该书开头提及的赫列克苏尔为例,《蒙古考古》一书对这个称呼的来源做出了解释(178页)。该词源自当地蒙古人见到这类遗存,误以为是9世纪当地的黠戛斯人墓葬之故。但实际上赫列克苏尔的年代比黠戛斯人至少早了一千年。另外还可以补上根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特尔巴依尔对赫列克苏尔的讨论,他提到该词源于蒙古语的Киргис хүүр(Kirgis khüür),意为黠戛斯人(据信为今日吉尔吉斯人或柯尔克孜族的先祖)之墓,后来才音转为khirgisüür。参见特尔巴依尔,《赫列克苏尔遗存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北方民族考古》第2辑(2015年),57页。
该书作者林俊雄质疑了《史记•匈奴列传》中对匈奴社会中存在四王二十四长的说法,此处的匈奴四王即左右贤王与左右谷蠡王(235页)。但是在同系列丛书中所收录的京都大学东洋史名誉教授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国的漫长遗绪》中则有另外一番解释。杉山正明将匈奴的左右贤王视为最高的两王,其下各领十二长,故有二十四长。杉山正明并且认为这个二十四长的组织可以对应到后来北周始祖宇文泰所设立的“西魏二十四军”,还有十三世纪拉施特(Rashid al-Din)《史集》中记载的突厥源流神话《乌古斯可汗传说》中乌古斯可汗六子下属的二十四个军事集团。杉山正明认为这种左右两翼与二十四个集团编组,成为了后来成吉思汗二弟与四子下属的二十四个千户编制的原型(78-88页)。杉山正明这种结合传说的讨论,提供了读者另一种看待历史记载的方式。
另外,作者观察到早期苏联考古学强调斯基泰人原生论,是因为受到唯物史观的指导,重视社会内部力量演化,忽略外部影响的缘故。美国卫斯理学院考古学教授科尔(Philip L. Kohl)过去是考古学界中批判唯物论与民族主义的一名健将。无独有偶,他在《青铜时代欧亚大陆的形成》一书中,对中亚考古也有过类似的观察。他认为过往与现今的中亚考古研究存在一种现象:即便研究认可了中亚与其南方与西方邻接地区有人群移动以及密切的交流关系,但仍旧强调内部的演化发展。
《草原王权的诞生》附有详尽的时代年表,也提供了许多的考古遗物图片,让人赏心悦目。不过在编辑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手误,例如23页提到赫列克苏尔源自蒙古语khirigsuur,然而现代蒙古语写作Хиргисүүр,故拉丁转写应为khirgisüür。75页提及俄罗斯语言学家阿巴耶夫(Vaso I. Abayev),书中误植为V. Abaycv。这里也提醒读者注意。
综上所述,该书是日本学界从世界史与考古学的角度,探讨早期游牧文明在欧亚大陆上的发展。作者不仅回顾了学界在这个领域的经典研究成果,并且也对一些过去研究中在理论与具体观点上所存在的偏误进行了批评。他在高度评价游牧文明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不忘反思过去以定居农业文明的标准评价骑马游牧民历史时可能产生的扭曲。本书值得对游牧考古学与中央欧亚史前史有兴趣的读者细细品味。
《草原王權的誕生》读后感(四):絲路、紋飾與遊牧民:想像「野蠻」與裁決「文明」
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入侵羅馬的匈人,都作為定居文明「野蠻搶劫者」的形象而廣泛存在於不同時空中定居文明官方—民間史料文獻的「野蠻」敘事中。從古希臘的希羅多德到西漢的司馬遷、東漢的班超,再到古羅馬的阿米阿努斯[1],他們都是歷史的記錄者,他們將親眼所見或者間接傳聞記錄于史冊,成為後世讀者研究「野蠻」繞不開的文本材料。不同的是希羅多德與司馬遷較之班超、阿米阿努斯,更加客觀、細緻,他們雖然是定居文明塑造的知識菁英,但能夠細緻、理性地觀察與定居文明大相徑庭的另一種社會結構、風俗習慣、喪葬祭儀、軍事動員,並將他們視之為與定居文明可比較的敵對政權。司馬遷因此落下了「袒護蠻夷」的罵名。[2]區別於希羅多德與司馬遷,東漢的班固與古羅馬的阿米阿努斯對「野蠻人」的敘事中,充滿著定居文明對「未開化蠻族」的鄙夷與恐懼。(班固:)「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而獸心…蓋聖王制禦蠻族之常道也。」(阿米阿努斯:)「匈人比歐洲所有的蠻族還要野蠻許多。」[3]不同的視角衍生出了不同的敘事,不同的敘事又影響、塑造著後來人們對「非定居文明」歷史的認知。於是乎這種高高在上的「蠻族想像」與「文明裁決」不同程度地存在於不同時空的人群中,無論政治、知識菁英,亦或街頭巷尾的販夫走卒,他們的「想像」與「裁決」根深蒂固,即使通過「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等一整套特定的「框架、聲音與敘事結構」,將其本散落在官方史籍、民間筆記與神話傳說中毫無關聯的零星記敘重新編排出來,從而將鑄就而成的國族、族群認同完成「自然化」的過程[4]。但即便這樣,大多數人對歷史記敘中的「古代民族」還是沿襲著古人「華裔秩序」、「文明-野蠻」的思維習慣,這種富含價值判斷、先入為主的「中心視角」導出的歷史解釋也充滿著緊張的敘事張力。森安孝夫認為在中國,這種對遊牧民鄙夷、排斥的觀念「起於宋朝,尤其是明朝以後編纂的大型漢籍叢書裏面…遊牧民族或少數民族的相關資料,遭受到了蓄意排斥和忽視」[5]。但正如筆者上文所引在東漢時期,(班固)對非「定居文明」群體風俗習慣、文化行為的鄙夷心裏就很明顯,相關的敘述很多,篇幅所限茲不累述[6]。因為這涉及到一個更為深刻又老套的議題,如何定義「文明」(civilization)。在這個意義上,林俊雄教授的《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陳心惠譯,八旗文化,2019年。原作名為『スキタイと匈奴 遊牧の文明』)有了更為緊迫的「祛魅」使命,以及更為深遠的學術意義。如何還原一部草原遊牧民的獨立、延續的歷史敘事,並將其歷史意義置於同「定居文明」等同的高度上。正如林俊雄在文章中所指出的「文明原本是在城市型定居社會的基礎上所產生的用語」,文明(civilization)本身就帶著顯著「定居」、「城市」的一系列標識與符號。因此,「對於沒有城市的遊牧社會而言,原本就與文明無緣,反而是站在與文明相反對的位置,被認為是野蠻之地也無可奈何。」[7]如何破除「定居文明」的「中心化」視角,如何用不斷出土的考古實物匡正歷史記敘的偏頗之處,這種問題關懷讓學者對游牧民與世界史的反思有了更為寬廣的意義。
談起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大陸課本與相關紀錄片中首先呈現的是「張騫開通西域」、「浩浩蕩蕩的駱駝行商」等指向性很強的象徵符號與文化圖景。這些符號與圖景構成了觀念中「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的重要性不需要我過多敘述,國內外大量學者自會將張騫開通西域、中亞商隊、絲綢等一系列象徵符號串聯成完整的「絲路」圖景。在他們的論述中絲路的演變歷程,就是以西域綠洲絲路(或者天山南北兩條線路)逐漸轉向海洋絲路的歷史必然。即使國內偶有學者呼籲重視內亞草原的傳輸路線、尊重歐亞草原的考古成果,但阿爾泰路線始終從屬於天山南路的綠洲路線,學者對西域絲路的分析與論述更多地著墨於西域綠洲路線上的城市國家與中亞商業民族。榮新江在《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中,詳實地探討了西域諸國與李唐文化的交流與互動,在文章序言中提到絲綢之路「早就在漢代以前就存在於中西之間」,但仍然認為「在伊斯蘭化以前,通過古代新疆的東西方交涉史的開展,離不開所謂絲綢之路」[8],在對絲綢之路緣起的分析路徑上,榮新江也是延續著兩漢審視周邊的敘事風格。既然榮新江認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對「絲綢之路」的定義,以及他認識到近代以來「學術研究的深入、考古發掘的進步,絲綢之路的含義越來越廣,範圍越來越大」,那麼他又何必因循守舊,自困于「西域路線」的窠臼呢?作為榮新江老師得意門生的付馬博士[9],在其近作《絲綢之路上的西州回鶻》中,探討了回鶻對殘唐「二庭四鎮」接管的三個階段,並用語文學角度分析了東部天山地區城鎮地名及其社會經濟的繁華程度。作者認為回鶻利用唐朝治理西域的經驗,在唐對西域治理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唐朝遺留下的城鎮戍堡體系已經發展成為一片以城市為中心的聚落群體,天山北麓地區真正展現出相當體量的城市定居文明因素,這不正是絲綢之路天山北道沿線經濟發展的明證嗎?」[10]可以看出付馬博士優秀的語文學能力與對西域諸文明體的深刻洞察,但是筆者覺得遺憾的是,這種無意識的「路徑化」絲路研究,使得許多更為寬廣的視角與敘事都被遮罩、淡化。在這方面,日本學者更為「激進」些。
森安孝夫回溯「絲路」概念的學術史歷程,認為自李希霍芬男爵創造出die Seidenstrasse,一直到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活躍的二十世紀上半葉為止,由於對「古代絲織品的遺物或是發現有關絹布貿易文書的遺址,即使在中亞也幾乎僅限於綠洲地帶而已」,這種出土實物的貧瘠導致「綠洲絲路」儼然成了絲綢之路的代名詞[11]。森氏將「綠洲絲路」的擴展歸功於日本明治以來東洋史學認知進路的深化,尤其是內陸亞洲史學與東西交通史學的卓越貢獻,使得學術界逐漸接受「絲路」不只是「綠洲之路」,還包括貫穿中亞的歐亞的「草原之路」。顯然森氏的論述有著「自吹自擂」之感,他將二十世紀上半葉蘇聯的考古工作、歐洲學者的研究等一系列原創性成果選擇性屏蔽。但不可否認日本學者在歐亞草原文化研究的積累與努力,林俊雄在《草原王權的誕生》中所引述京都大學考古學家梅原末、提出「絹馬貿易」的松田壽男博士、聚焦於中央歐亞出土絹織物紋樣、織布技巧與文化交流史的阪本和子、研究亞洲史多年的宮崎市定等。他們為「新絲路」概念的擴展與深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本書(《草原王權的誕生》)作者林俊雄先生正是他們的繼承者。
林俊雄用大量考古出土資料,有力地反駁了「綠洲絲路」中心說,將「綠洲絲路」開拓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及其作為傳播者的「歐亞草原遊牧民」歸置到了更為廣闊的「中央歐亞」的歷史語境裏。林氏在『最早開啟的絲綢之路——草原路線』一節中,認為「格裏芬」的傳播路徑大致沿著「從希臘殖民城市所在的黑海北岸往東前往草原,最終抵達阿爾泰地區的路線。希羅多德也有記載這一條路線,考慮到斯基泰時代,草原地帶的東部和西部盛行同樣的文化,彼此之間有所交流,這一條路線的可能性很高。」林氏通過對巴澤雷克三號墳與五號墳出土中國絹織品、六號墳出土中國戰國時代(西元前四—前三世紀)鏡子的美術史比較,認為在「中國還不知道西亞與希臘、西方也不知道東亞存在的時候,阿爾泰地區的人已經開始和波斯、希臘,還有中國進行交流了。」阿爾泰線路的便捷之處,就在於空間距離比起綠洲路線更為近些,所耗費的時間也更為短些。「阿爾泰路線行程幾乎全部都是通過草原地帶,途中則以阿爾泰為中繼點,這當中沒有難以越過的大山脈或沙漠」。甚至也不存在被綠洲城市國家收取通行稅確保通行安全等現象[12],遊牧民高頻的移動性使得該線路既成本低廉又極其便捷。事實上,早在張騫開通綠洲絲路之前,以阿爾泰地區為中轉點,通往高加索、黑海地區的草原交流之道,早就已經運行了數百年(也有說上千年)。根據前蘇聯學者E.H.切爾內赫對古代歐亞大陸北部冶金技術、器物的分析,「卡拉蘇克的器物斷斷續續地向遙遠的東方延伸,橫跨近三千五百公里。它們廣泛發現於薩彥—阿爾泰地區、新疆、蒙古高原、華北、遼河流域,幾乎達渤海灣。草原器物的另一條傳播路線往南和東南方向。類似的器物達到陰山北麓的半沙漠和沙漠地帶和晉陜高原,接近黃河流域的商王的方國。」[13]可見歐亞草原內部聯繫的緊密。這些「歐亞草原的遊牧民」擔負著文化傳播者與技術交換紐帶的角色,他們將中國的奢侈品「絹織品」、「鏡」,實用工具「硬式馬鞍」、「馬鐙」傳播至西方,又根據自己的喜好改變東西方美術的樣式與圖案,再傳播到東西方。「他們居住的中央歐亞草原地帶也是鏈接歐亞大陸東西、所謂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他們不僅弘揚自己的文化,同時也擔任將東方文化帶往西方,西方文化帶往東方的角色。」[14]他們連接東西,吸收各個定居文明的藝術審美、製造工藝,並將其結合產生的多元成果帶往不同時空下的人群中。黑海北岸、高加索、烏拉爾、阿爾泰、天山、蒙古高原到處都有他們的身影。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自己的文字,也無法表述自己的歷史,對他們的認知依賴於定居知識菁英的記錄、新出土的考古實物。在這個基礎上,對「他們」的重新發現有了必要。
按照主流考古學與美術史學者對歐亞大陸草原地帶出土文物藝術風格的分期,西元前八/前七世紀至前四世紀構成「斯基泰時代」,前三至後三世紀構成「薩爾馬提亞時代」,六世紀後半以降構成「突厥時代」,而「薩爾馬提亞時代」與「突厥時代」的三百年空隙則被部分學者稱之為「匈人時代」、「民族大遷徙時代」、「前突厥時代」(《草原王權》作者林俊雄更認可該說法)[15]。這種分期劃分,基本以不同時空下的主流族群集團為標識。流轉於蒙古高原、阿爾泰、天山、烏拉爾、伏爾加河、北高加索、黑海北岸的歐亞草原遊牧民,天然具備「定居文明」所不可比擬的「自由移動性」。林俊雄通過對百年來歐亞大陸草原地帶考古學知識的積累與整理,一幅延續、流動的「遊牧民」世界史的畫面呈現在讀者眼前。他們具備文化自信,他們將東方的「鏡」傳播至西方,將西方的技術工藝傳播至東方,又將自我的藝術審美自信地保留在手工作坊的製成品之上,「他們根據自己的喜好改變東西方美術的樣式與圖案」[16]。如林俊雄所引述的「北阿富汗黃金遺寶」(即阿富汗北部蒂拉丘地(黃金之丘)遺跡,由前蘇聯考古學家薩瑞阿尼迪(Viktor Sarianidi)在一九八七年著手發掘)中的(西漢時代)「連弧紋銘帶鏡」(三面)、「印度風人物的象牙梳子」、「土著化中亞風格的希臘羅馬諸神圖案」、帶(中國風)龍的劍鞘[17],以及諾彥烏拉墓地六號墳中出土的毛氈「最外側邊線用的是中國製的絲織物,內側的圖案則繼承後期斯基泰動物圖案的傳統。」[18]不僅如此「歐亞草原遊牧民」的審美習慣具備穩定的延續性。比如「動物紋飾」。動物紋飾是「遊牧文化」最為顯著的特徵之一,無論黑海北岸、高加索地區的「斯基泰人」、蒙古高原、阿爾泰地區的「匈奴人」,亦或哈薩克的「薩爾馬提亞人」,甚至就連「綠洲城市」地區,都發現了高度具備共通性的動物紋飾。由於篇幅所限這裡著重探討下「鹿角」、「雙馬神」紋飾、「格裏芬」紋飾,它們經過「歐亞草原遊牧民」的傳播與改造,如何深遠影響了東亞、西亞地區的藝術審美,從而展示歐亞草原與東西方文明的緊密聯繫。
按照主流考古學與美術史學者對歐亞大陸草原地帶出土文物藝術風格的分期,西元前八/前七世紀至前四世紀構成「斯基泰時代」,前三至後三世紀構成「薩爾馬提亞時代」,六世紀後半以降構成「突厥時代」,而「薩爾馬提亞時代」與「突厥時代」的三百年空隙則被部分學者稱之為「匈人時代」、「民族大遷徙時代」、「前突厥時代」(《草原王權》作者林俊雄更認可該說法)[15]。這種分期劃分,基本以不同時空下的主流族群集團為標識。流轉於蒙古高原、阿爾泰、天山、烏拉爾、伏爾加河、北高加索、黑海北岸的歐亞草原遊牧民,天然具備「定居文明」所不可比擬的「自由移動性」。林俊雄通過對百年來歐亞大陸草原地帶考古學知識的積累與整理,一幅延續、流動的「遊牧民」世界史的畫面呈現在讀者眼前。他們具備文化自信,他們將東方的「鏡」傳播至西方,將西方的技術工藝傳播至東方,又將自我的藝術審美自信地保留在手工作坊的製成品之上,「他們根據自己的喜好改變東西方美術的樣式與圖案」[16]。如林俊雄所引述的「北阿富汗黃金遺寶」(即阿富汗北部蒂拉丘地(黃金之丘)遺跡,由前蘇聯考古學家薩瑞阿尼迪(Viktor Sarianidi)在一九八七年著手發掘)中的(西漢時代)「連弧紋銘帶鏡」(三面)、「印度風人物的象牙梳子」、「土著化中亞風格的希臘羅馬諸神圖案」、帶(中國風)龍的劍鞘[17],以及諾彥烏拉墓地六號墳中出土的毛氈「最外側邊線用的是中國製的絲織物,內側的圖案則繼承後期斯基泰動物圖案的傳統。」[18]不僅如此「歐亞草原遊牧民」的審美習慣具備穩定的延續性。比如「動物紋飾」。動物紋飾是「遊牧文化」最為顯著的特徵之一,無論黑海北岸、高加索地區的「斯基泰人」、蒙古高原、阿爾泰地區的「匈奴人」,亦或哈薩克的「薩爾馬提亞人」,甚至就連「綠洲城市」地區,都發現了高度具備共通性的動物紋飾。由於篇幅所限這裡著重探討下「鹿角」、「雙馬神」紋飾、「格裏芬」紋飾,它們經過「歐亞草原遊牧民」的傳播與改造,如何深遠影響了東亞、西亞地區的藝術審美,從而展示歐亞草原與東西方文明的緊密聯繫。
「雙馬神」紋飾。一九七八年河北易縣出土了12件帶有雙馬神紋飾的金銀牌飾、馬具。而且在三十號墓中出土的金柄鐵劍、飾品上包含大量鹿、熊、合成獸等,研究報告稱種種現象「顯示了燕文化與北方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23]。翌年,在內蒙古準格爾旗西溝畔戰國墓地中也發現了紋飾、製作工藝高度相似的雙馬神藝術品。一九八三年與一九八五年,在寧夏同心縣倒墩子西漢中晚期遊牧人墓中發現類似的多件雙馬神紋飾的藝術品。雙馬神的範圍在新疆地區也有廣泛的分佈,輪臺縣瓊巴克古墓、吐魯番艾丁湖畔漢墓中都發現了類似的雙馬神紋飾牌,並且在吐魯番艾丁湖畔漢墓中,「雙馬紋透雕牌飾和漢初銅鏡共存」。[24]關於「雙馬神」紋飾,林梅村推測其源於「吐火羅系統」的月氏人。林梅村進一步指出,「吐火羅藝術對燕文化的影響不僅表現在金銀裝飾藝術上,可能還滲透到燕文化建築藝術中。燕下都出土瓦當和闌幹磚上的雙龍文與南西伯利亞出土的古代遊牧人黃金牌飾上的雙龍紋如出一轍,藝術母體可能都淵源於吐火羅人雙馬神宗教藝術。」[25]雙馬神信仰廣泛存在於歐亞大陸,在西元前3200-前2200年裏海—黑海北岸地區的顏那亞文化中就發現了雙馬神信仰。[26]透過雙馬神紋飾,可見歐亞大陸空間聯繫的緊密型,而在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不是張騫開通西域後中亞商人集散—中轉的「綠洲絲路」,而是經由歐亞草原遊牧民主導的「草原路線」,通過便捷的歐亞草原,遊牧民將黑海北岸、烏拉爾、阿爾泰、蒙古高原、天山精密地聯繫在一起,甚至將他們的生產技術、藝術審美不斷滲入周邊定居文明中,為推進人類文明的演進提供了重要的作用。
「格裏芬」紋飾。格裏芬是西亞世界所幻想的獅子與老鷹的合成獸,在西元三千年前就廣為西亞人所知。之後在不同時空以不同形態出現在神話傳說、雕塑模型、器皿紋飾當中,並且隨著遊牧民的移動、傳播,後期具有明顯本土化傾向。首先來看「斯基泰時代」的黑海北岸、高加索地區,舒爾茨三號墓中出土了裝飾有格裏芬頭的金製王冠。王冠中的格裏芬周圍點綴著整齊的花朵與水滴形的垂珠裝飾,林俊雄推測「刻有花朵圖案的王冠常見於亞述美術當中」,而水滴形的垂珠裝飾則更多出現在「希臘的貴金屬工藝當中」。通過北高加索地區出土劍鞘、王冠的分析,可見歐亞草原遊牧民對東西各地工藝技術、紋飾美術的吸收與融合。[27]再來看後期斯基泰「格裏芬」紋飾的變化,由於長期混跡於西亞地區的各個文明體之間,(斯基泰)始終廣泛參與西亞世界的政治衝突與合作中,並且與希臘殖民城市「眉來眼去」,這就難免受到「希臘化」的影響,因此後期斯基泰美術最顯著的特質就是濃鬱的「希臘」色彩,因此考古學與美術史也將這一時期的「斯基泰美術」稱之為「希臘化斯基泰(Graeco-Scythian style)美術」[28]。這一階段「可以看見許多顯著的傾向:包括開始使用棕葉飾(棕葉開展的圖案)和唐草紋這類的植物圖案,動物的表現更加寫實」(上同)。在一九七一年於黑海北岸發掘的托羅斯塔(Tolstaya Mogila)古墳中,挖掘出土的項圈中,呈現了「鷹型格裏芬」[29]襲擊馬、花、蔓草等一系列濃鬱的希臘色彩。再將我們的視線轉向「不太遙遠」的東方。阿爾泰地區的「巴澤雷克」五號古墳出土的「覆蓋在馬鞍」的毛氈裝飾[30],為我們展示了混合西亞、中亞多種元素的格裏芬襲擊山羊的畫面。本土色彩為濃厚的當屬天山地區伊黎河上游出土的「鍑」,對望的兩隻「獅型格裏芬」耳朵、角、鬃毛、羽翼都有著非常顯著的本土化特徵。[31]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二七年,俄羅斯(前蘇聯)人科茲洛夫(Pyotr Kozlov)[32]領導下的團隊調查挖掘了諾彥烏拉古墳遺跡,其中五號與六號墳中出土了含有紀年標識的「漆耳杯」,底部標識「建平五年…」(西元前二年,西漢末年哀帝年號),在六號墳木棺下鋪的毛氈上,呈現了一幅「如狼的怪獸襲擊如氂牛的的動物」的畫面,而且「如狼的怪物長有枝角,角的尖端和尾部的尖端是格裏芬的頭部圖案」[33]。事實上,這種將格裏芬紋飾內化於其他動物身體的頭部、枝角、尾部的做法,在後斯基泰時代非常普遍。不論是巴澤雷克古墳中「格裏芬吞噬大角鹿」的帽飾[34]、薩爾馬提亞王墓中出土的「木芯貼金的鹿雕像」,還是中國陜西省北端神木縣納林高兔出土的「擁有鹿角的合成獸」、內蒙古自治區杭錦旗阿魯柴登出土「合成獸腰帶裝飾」,都有明顯的「內化」特質。宿白先生也在自己的《考古發現與中西文化交流》一書中,探討了歐亞草原對東西亞兩端溝通的重要意義,以及東西美術交流史的考古依據。在對西漢時期匈奴北部地區美術紋飾的遺跡、遺物的分析中,也引出諾彥山下墓群中出土帶有「翼獸」的毛氈,這裏的「翼獸」就是融合內化的「格裏芬合成獸」。並且宿老指出,「這裡匈奴墓中出了大批氈製品而且上面繡出的有翼獸、植物紋也都是在西方影響下匈奴地區生產的…禽獸爭鬥紋,是從西亞經中亞一直到河套地區遊牧民族流行的紋飾,可以推測這類東西起碼也是在西方工藝影響之下出現的。」
林俊雄在自己的《格裡芬的飛翔——聖獸所見之文化交流》[35]中,通過「格裡芬圖像的誕生——從美索不達米亞到西方」、「格裡芬圖像的展開——從美索不達米亞、伊朗到西方」、「新格裡芬圖像的展開——以希臘為中心」、「格裡芬,向東而翔」、「之後的格裡芬」五個部分,描述了「格裏芬」的誕生、傳播、融合的歷史過程,以及探討了一直到古羅馬、薩珊波斯、李唐王朝、拜佔庭與中世紀歐洲,「格裏芬」是如何作為一種藝術符號被消融、吸收於本土雕塑、壁畫當中的。由「鹿角」、「格裏芬」紋飾演變的時空歷程,可以窺見東西文化交流的緊密與頻繁達到何種程度,在這其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便是「歐亞草原遊牧民」。
純粹遊牧民的歷史登場很晚,他們的前身就是在降水、地形與資源過度地帶的兼漁獵、採集混合作業的「混合經濟人群」[36]。林俊雄在文章中也提到這一點「在德雷耶夫卡和波泰所屬的西元前四千年紀至三千年紀,人們以定居聚落為中心,從事農耕和畜牧的復合經濟」[37]。關於他們的起源,學者眾說紛壇,比較有影響力的是「氣候轉變說」,如俄國學者阿納托利·哈紮夫認為「乾旱的氣候使部分兼營牧業的農民放棄農業,專注於畜牧而變成遊牧人群」[38]。王明珂在其著《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分析青海河湟地區遊牧社會的形成,將河湟地區牧羊人能夠突破環境資源限制,利用河谷上方高地水草的原因歸之於:①西元前2000年-1000年全球氣候的乾冷化,使農業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在這一點上王明珂延續了「氣候轉變說」基本論調,只不過在具體細節上有所調整;②長期的定居農業生活,導致該地區出現人口擴張與資源分配不平均。為了逃離「統治者」的剝削,他們逃往高低,「依賴馬、牛、羊過活」[39],逐漸形成了河湟地區的遊牧社會。「氣候轉變說」與「環境壓力說」在學界呼聲很高,林俊雄雖然沒有正面回應「環境壓力說」,但對於「氣候轉變說」,他主張對「不能僅用氣候變動說明一切」[40]。
林俊雄將遊牧民的起源歷程歸置到三種敘事的演進中,首先是自然環境的變化,林氏對自然環境促進遊牧產生的基本思路延續了「氣候轉變說」。「西元前三千年紀中期,氣候逐漸乾燥化,黑海北岸的闊葉樹林消滅,取而代之的是向外擴展的草原,在哈薩克則形成了半沙漠和草原。結果,草原地帶成為比農耕更適合畜牧的風土。」氣候的變動,使得很多半沙漠的地方開始變成草原,這也為馴化家畜人群的遷徙提供了資源基礎。其次是人對家畜狩獵、圈養、馴化,以及對家畜皮、毛、乳、肉類加工的具體利用演變,塑造了遊牧民的衣食住行與生活習慣。從最開始直接狩獵,為了當日來回放牧而將「封閉型」圍欄變成「開放式」圍欄[41],以及對綿羊、山羊、牛、馬等家畜毛、皮、肉、乳、牽引(牛、馬)、騎乘(馬)的利用[42],遊牧先民從動物的身上獲得了日常的衣食住行,型塑了他們長期延續的生活習慣。這裡引申一下,遊牧先民或者說「混合經濟人群」在走向純粹遊牧的「生存抉擇」之前,首先經歷了一場「生產資料的抉擇」。根據王明珂對河湟地區農耕社會向遊牧社會的轉型研究,發現豬、狗的數量不斷減少,而像羊、牛、馬等移動性高的家畜數量迅速擴張。王明珂認為「一邊養羊一邊務農,在家庭人力運用上會有無法避免的矛盾…(養羊—務農)任何一方的擴張,無論是多養羊或是行較精緻化的農業,都必須放棄另一方。」為什麼呢?因為養魚農業有著無法化解的生產困境,為了避免羊群侵犯莊稼作物,「混合經濟人群」必須將羊移到更遠的地方去放牧。[43]最後,林俊雄著重探討了「技術」如何塑造了遊牧民。林氏認為車與騎馬的導入,是促進草原遊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早期的騎乘馬匹由於相關技術的發明與生產未曾展開,以及「由於馬背上有脊柱突起,如果直接跨坐在馬背上,胯下會很痛」,所以人類對騎乘的掌握出現的較晚。美索不達米亞出土的描繪「驢式騎乘」圖案的泥板並不普及[44]也證明了這一點。既然掌握騎乘如此困難,其感覺也談不上舒適,不成熟的騎乘被「兩輪車」的取締也就成為必然。比如安東尼認為「在烏拉爾至哈薩克間的草原上,於西元前二千年至一千七百年左右發明瞭帶有輻條的車輪,而印歐語族的軍團就是乘坐著兩輪戰車,威脅南方的安寧」。[45]當然林氏通過對該時期出土考古實物的分析,認為出土的材料還不足以支撐「戰車」已經廣泛用於軍事,而烏拉爾和哈薩克的墓中出土的兩輪車最多只能容納一人乘坐,將其「解釋為把死者送往來世的車子較合理」[46]。在對「戰車」廣泛應用的質疑基礎上,林氏對歐亞草原的「技術」生產開始聚焦於「馬銜」、「馬鑣」等控馬工具的生產。早在西元前十四世紀後半期埃及的浮鵰中,就開始出現騎乘者通過馬銜馬馭的畫面,而在前十世紀之後的西亞與地中海地區的土偶、浮鵰畫、繪畫圖案中,呈現騎馬形象的資料開始激增。而草原地區大量騎馬證據的增加,晚於西亞地區一兩百年。從中可以管窺歐亞大陸「技術」的傳播與交融如何型塑了草原遊牧民的技術史。歐亞草原遊牧民本身就是「混合經濟人群」走向移動放牧的結果,他們依賴於與周邊定居文明的物質交換,從而滿足自身單一生產之外的物質需求。歐亞草原上的遊牧民本身就是世界史發展的產物,是定居文明的生存抉擇的一次轉型。當他們掌握戰車與騎乘術,一艘搭載著地中海、北非、西亞、中亞、東亞各定居文明美術紋飾、製造工藝、生產技術的「超級文化航母」,就開始在歐亞大陸多節點的互動網絡中自由航行。
關於游牧民的技術,這裡做個補充。他們在西元前三千紀,就已經在歐亞大陸北部熟練地展開了復雜的冶金工業。E.H.切爾內赫長期致力於古代歐亞大陸北部冶金工業的研究,他通過自然科學方法實驗,分析了五萬件早期歐亞大陸的金屬器、礦石和礦渣樣品,為相關研究者描繪了一幅冶金技術的起源和傳播路線的畫卷。[47]在這裡需要注意一下早期歐亞草原對中國的物質—文化的影響。E.H.切爾內赫通過對學界爭論焦點的回顧,著重探討了殷商青銅冶金起源於何地的問題所引起的諸多分歧。比如M.羅越將殷商冶金技術的起源地視為西亞的「安德羅沃文化」。JI.C.瓦西裡耶夫也認為西方文化推動了殷商中國地域社會文化的發展變化,他進一步指出西方的快馬戰車、青銅套管、青銅軛、日常用品與武器,在中國沒有源頭(瓦裡西耶夫認為源頭為卡拉蘇克文化)。切爾內赫順著瓦裡西耶夫的思路,也對殷商文化的本土發展產生了質疑「中國古代的冶金出現的非常突然,並且一出現就是成熟的狀態」[48],對此切爾內赫感嘆道「它們(殷商時期的青銅器)的鑄造使用複雜的多塊範;範的內側覆蓋複雜而繁縟的刻文。這樣高超的金屬加工技術很難在黃河和長江流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中找到淵源。」[49]切爾內赫認為最早的源頭可以上溯到以阿爾泰地區為中心的「塞伊瑪—圖爾賓諾類型」,「它是冶金技術向東傳播的源頭。這個源頭給中亞帶去了金屬生產技術:在那裡出現了許多冶金中心,並形成了中亞冶金省。其中一個邊緣而且最靠東的冶金中心是殷商時期的中國,儘管古代中國生產的是另一套器物(造型複雜的容器等)。」[50]隨著相關考古研究工作的展開,西方、日本學者對「技術西來說」的呼聲越來越多,從冶金工業逐漸擴展至「戰車」、「馬車」,麥克奈爾在他的《世界史》中認為「西方戰車的到來,可能導致了商王朝的建立」[51]林巳奈夫在『中國先秦時代の馬車』中提到「中國殷代出現的單轅馬車與近東的馬車在構造、套馬方法、駕馭方法上是完全相同的…擁有馬車的極少數人費盡艱辛,駕駛著他們自己的馬車從遙遠的近東地區來到中國,以這種方式將馬車傳入中國,並在中國仿製出來。」[52]當然,這種「技術西來說」也受到國內學者的質疑與批判。林梅村通過對幾十年來華北、西北地區先秦考古研究報告對殷商的造車工藝、工具進行了梳理,認為「公元前2100年—前1800年左右中國的造車工具中最重要的工具空首銅斧已經在天山南北和河西走廊廣為流傳…先秦文獻所言造車工具的完整組合在公元前2000年-前1800年左右已經在中國北方草原初步形成,這套工具很快進入夏王朝統治的中心地區。」並且將先秦造車的青銅工具視為不同於巴比倫、印度、埃及、安納托里亞等地的獨立文化系統下的產物,「不同文化系統的青銅工具製造出的戰車是否同源,令人生疑。」[53]況且,E.H.切爾內赫自己也認為殷商復雜、高超的冶金加工技術,「類似的情形不見於西方同時期的使用金屬的文化」,而且不同於卡拉蘇克文化(作者認為其冶金技藝與殷商最像),商和西周絕大部分青銅器物的都是用於祭祀和儀式,而卡拉蘇克金屬器中的最重要,也是最常見的器物是武器。切爾內赫進一步指出,由於從西元前兩千紀開始,草原上的畜牧文化作為連接歐亞東西兩端的主要橋樑,使得復雜的技術、文化交流不斷反應在金屬器上[54]。換句話說,正是由於他們的橋樑作用,本土起源的中國冶金不斷借鑒草原器物的技藝、紋飾,產出了復雜、精良冶金工藝品,由此可見草原游牧民對歐亞文明發展的衝擊與互補。
二零一九年二月,葛兆光先生的《想像异域》韓文譯本在首爾面世,韓國西江大學史學科教授桂勝范寫了一篇名為《裁決文明》的書評,文章中提到「朝鮮人真的想像了清朝的情況嗎?朝鮮燕行使直接目睹的風景與其相關記錄真的是出自想像嗎?難道不是裁決的產物嗎?」,桂勝范進一步解釋到訪問清代北京的朝鮮使臣,在出發之前,就已經利用「華夷分辨」意識將自己徹底包裝起來。因此,當他們目睹「堂子祭天」、「季文蘭故事」、「胡漢衣冠」等事件后,用「華裔變態」的意識對「所見之事做出了正誤裁決。」[55]葛兆光也對桂勝范的批評做出了回應,他指出「燕行使們更多並不是像一個法官在冷靜和客觀地「裁決」,而像是帶有情感和溫度的「評價」」[56]。桂勝范與葛兆光的互動為我們理解游牧—定居文明的關係與定位提供了一種新思路。傳統中國天下、五服、華裔觀念薰陶下的中原士人對周邊族群的認知,是出於「他者」的想像,還是「華裔分辨」觀念下的「文明裁決」。是某一種敘事長期佔據主導,亦或兩者敘事交纏、消長。這些思考為我們重新審視歐亞草原游牧民的歷史定位提供了寬廣的視野。
林俊雄在書中花了大量篇幅探討了司馬遷所描述的匈奴形象、游牧國家中的定居聚落。由於游牧生產效率極低、易受天氣條件左右,無法自給自足,因此非常依賴對周邊定居文明的定期掠奪、互市貿易。林氏將松田壽男分析游牧民生產方式的模型,用來探討游牧國家中的定居聚落,認為大規模的農耕與遠距離中轉交易的經營,需要聚落與作為商品集散地的城市,而「司馬遷斷言這些都不存在於匈奴」。[57]林氏通過對文獻與上世紀蒙古高原考古研究報告的分析,認為匈奴游牧國家中非游牧因素的聚落主要來源匈奴對華北地區漢匈邊境郡縣人口的擄掠、自發的逃亡,以及如中行說、李陵、李廣利等精英的歸誠。[58]而前蘇聯考古學家達維多娃在一九六八年的報告中指出更為寬泛的範圍「定居化的匈奴人、被匈奴征服的原住民(丁零等)、(來自中國的)俘虜和逃亡而來的外來工匠階層」[59]。匈奴的單于任命部落首長,協同匈奴武士監視和護衛聚落民,防止他們中的漢人逃往南方。[60]林氏將這種游牧政權下的農耕聚落,以及管理方式對比漢軍在西域經營中的屯田制度,認為這與漢代的屯田制非常相似[61],并提出匈奴擄掠漢人,強制他們從事農耕的「徙民」行為,在後來的鮮卑、柔然、突厥等游牧國家和五胡十六國時代的北方胡族政權,以及北魏、遼等游牧民出身的王朝中,經常可以看到。「匈奴的例子可以說是這些王朝的先例」。[62]不僅於此,林氏梳理匈奴社會結構、對外關係與財政收入時,指出匈奴對漢文書的文字書寫、對草原游牧民、聚落農耕民、手工業工匠、西域諸定居政權的課稅,來源於類似中行說這樣懂得財政管理的中原官僚,他們將西漢的統治和管理的技術帶給了匈奴。[63]足以可見漢人想像的一個「純粹」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並不存在,雖然移動的游牧是他們最重要的生產方式,但他們能夠寬容地吸納各種生產,利用專業人群從事專業工作,「徙民」是最為直接的證據。
這裡需要注意中行說身份轉型后導致文化認同的轉變,中行說警示匈奴統治階層「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褲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64]中行說從中原文化宮廷宦官的身份轉變為匈奴權臣后,文化認同也相應發生徹底的變化。他建議匈奴統治者抑止漢衣食文化、審美習慣的滲透,提倡迴歸匈奴騎射、衣食傳統,甚至面臨漢使的責難,他嘲諷到「由於(匈奴)法制簡單、容易執行、且君臣之間隨意,因此國家的政治也有如活動肢體一般自在,沒必要像中國一樣,受到無意義的表面禮儀之束縛。反而是中國常見親族彼此殘殺,或是殺了主人取代主家的事。」[65]可以看出游牧民在尊重草原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孕育出了他們獨特的風俗習慣、社會結構。
定居文明對他們的「野蠻想像」顯然是「他者」中心視角下的「文明裁決」。中原對北方游牧民的鄙夷完完全全建立在自己的中心視角下,當中行說實現身份轉換,以匈奴為中心反觀中原文化,敘事的差異立馬顯現出來。無法書寫自身歷史的游牧民,面對具備歷史書寫話語權、中心視角極強的中原文化,難免遭受被「想像蠻夷」的待遇。但這種想像包含著太多文明裁決的意味。利用「夷夏」包裝自己的史學敘事與認知進路,本身就是視中原文化為正統,非正統即為異端的文明裁決。而且這種中心視角的「文明裁決」又是普世的,并不獨存於東亞一隅。遭受斯基泰入侵的西亞、匈人入侵的馬羅、蒙古入侵的東歐,這些對游牧民的恐慌與排斥的敘述不斷出現在歐亞大陸的官方史籍、私人著史、旅行家手記中。這些騎馬游牧民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軍事擴張常常瓦解了許多定居民的抵抗意志。這些定居民在學術著作和通俗小說中多為「文明民族」,但他們對遊牧民的恐慌不僅記錄在歷史文獻裡,而且反映在口頭傳說和民間神話中。「這些這些魔鬼是誰?這些禽獸從哪兒來?他們是哪個蠻夷?是野蠻的、被上帝詛咒的韃靼?人們說,死屍培育了這些邪惡的觀念,而且在任何語言中都不會消退。看,這是因為人類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所以主才給我們降如此殘酷的懲罰。正是這樣的神秘現象困惑了歐洲(包括英格蘭群島在內)基督教世界的統治者達十三個世紀」,類似的聲音在歐亞大陸的很多地方都可以聽到[66],無一例外,他們都是定居文明。
不同于E.H.切爾內赫提出游牧民的軍事入侵刺激了定居民對其展開「野蠻想像」的觀點,王明珂為我們審視文明與野蠻提供了另外一種思考。王明珂利用歷史人類學的(historical anthropology)研究方法,對先秦時期中國北方游牧民、以及「華夏」意識的起源進行了細緻的觀察。他指出氣候變遷(乾旱化),導致「混合經濟人群」不斷移動化、武裝化,南下入侵、爭奪宜農宜牧的土地。這種持續的入侵造成了華北長城地帶人群資源競爭的緊張關係,為了防止這種入侵,到了西周—春秋時期,「一個以「農耕」與「定居」為標記的華夏認同逐漸形成」,並且將居住在黃河中下游平原的人凝聚在一起。而北方那些以畜牧為主(兼農耕),時常遷徙的武裝人群,則被「華夏」視為野蠻的異族。等到生態過度地帶的資源衝突持續到春秋戰國,北方諸國紛紛修建以長城為標識的邊界。那些被迫北撤的混合經濟人群進入鄂爾多斯等地區,徹底走向移動化、游牧化,放棄了定居、農耕、養豬。[67]「華夏意識」通過仇視外者實現凝聚內部,通過對游牧民的「野蠻想像」完善華夏的內部認同。對「非我族類」的「文明裁決」是基於華夏認同本身的封閉與孤傲,但這絕不意味著「華夏意識」的「野蠻想像」與「文明裁決」是一成不變的。它不斷隨著現實境遇的變遷、衝突而被刪減、修正,甚至強化。五胡十六國時代的到來,為封閉的華夏帶來新生,使其能夠「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68]在這個背景下,鮮卑色彩濃厚的李唐皇帝才能夠說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這樣的豪言壯語。
筆者覺得《草原王權的誕生》一書中最大的遺憾,就在於林俊雄對游牧「文明」的不自信。林氏在本書中反思了「蠻族想像」背後的認同錯位與現實危機,「文明」一詞本身就是對城市型定居社會的概括,他包含了城市、權力、巨大建築物、審判制度、文字等一系列定居社會產生的象徵符號。而與定居社會生態環境、生產邏輯大相徑庭的游牧社會,他們生產出的風俗習慣、氈帳、遷徙、馬牛羊等象徵符號,原本就與「文明」無緣,甚至是站立在與文明完全相反的位置,被認為「野蠻」也是無可奈何。[69]並且林氏談到,突厥系可薩人建立的城市中,由於他們依賴商業交易稅的財政收入,為了吸引各地的商人,採取了類似近代「宗教寬容」的宗教政策,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在七位城市法官中各占兩額,而剩下的一名留給異教。「這個事實讓近代歐洲的歷史學家大感吃驚,一直處於對立的三宗教竟然平等的對待」,而同時期的歐洲,佔據主導地位的基督教以宗教迫害聞名於世。呵呵,誰是「野蠻」,誰是「文明」,讀者有目共睹。可惜的是,林氏為了給予游牧民應有的「文明」高度,不斷從游牧民歷史進程中尋覓定居文明的「文明標識」。他回顧本書討論的諸多議題,指出匈奴社會存在的從事手工業與農業的聚落、匈奴人將西域綠洲城市間接納入自身統治之下、斯基泰人與希臘人的殖民城市保持了良好的關係、回鶻人、可薩人、保加爾人在草原上建設城市,試圖證明游牧社會也符合「定居文明」的「文明標準」。他強調草原上也存在王權、巨大建築,以及引入的官僚制度、文字等[70]諸多「定居文明」的「文明標準」。這種附會定居「文明標準」,無意中貶低了游牧文化的獨創性與高度。筆者讀罷,大感可惜。
[1] 【古羅馬】歷史學家,Ammianus Marcellinus (約330~約395)。[2] 參見【日】林俊雄:《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陳心惠譯,八旗文化,2019年。《匈奴的衰退和分裂:內部鬥爭、投降、飢荒、叛亂:多災多難的使節團》。[3] Res Gestae,XXXI.,2,1-10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4] 參見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5] 【日】森安孝夫:《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騎馬遊牧民眼中的拓跋國家》,張雅婷譯,八旗文化,2018。《序章》。[6] 五胡十六國的北朝、鮮卑色彩濃郁的李唐是割裂「蠻夷」敘事的插曲。[7] 【日】林俊雄:《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陳心惠譯,八旗文化,2019年。《結語:遊牧國家有文明嗎?》。(後文對《草原王權的誕生》的引述以章節為主)[8] 榮新江:《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見《第一編 絲綢之路 :一、古代新疆是絲綢之路乾線的必經之地》[9] 現為現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研究員。[10] 付馬:《絲綢之路上的西州回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283頁。[11] 【日】森安孝夫:《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騎馬遊牧民眼中的拓跋國家》,張雅婷譯,八旗文化,2018。《絲路與世界史:何謂絲路》。[12] 《動物紋飾與黃金的美術:後期斯基泰的美術:最早開啟的絲綢之路¬——草原路線》[13] 【俄】E.H.切爾內赫、【俄】C.B.庫茲明:《歐亞大陸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王博、李明華譯,中華書局,第271頁。[14] 《草原王權的誕生:結語》[15] 《匈人是匈奴的後裔嗎?匈人的習俗與文化:「前突厥時代」的美術》。[16] 《匈人是匈奴的後裔嗎?匈人的習俗與文化:遊牧民對世界史的影響》。[17] 《從考古學看匈奴時代:中國文化與匈奴文化的廣佈:北阿富汗的黃金遺寶》。[18] 《從考古學看匈奴時代:匈奴的王墓:諾彥烏拉墓地的出圖品》。[19] 《動物紋飾與黃金的美術:初期斯基泰的美術—西部:劍和鞘的製作者是誰?》[20] 《動物紋飾與黃金的美術:初期斯基泰的美術—西部:阿爾贊二號古墳的衝擊》[21] 《動物紋飾與黃金的美術:後期斯基泰的美術:阿爾泰的奇跡》[22] 《蒙古高原的新勢力:匈奴的先驅者:匈奴興起前夕的草原文化》[2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前揭書,730-731頁。//轉引自林梅村:《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27頁。[24] 林梅村:《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28-31頁。[25] 林梅村:《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28頁。[26] 林梅村:《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32頁。[27] 《草原的古墳時代:初期斯基泰的美術—西部:受希臘的影響》[28] 《動物紋飾與黃金的美術:後期斯基泰的美術:希臘化斯基泰美術》[29] 格裏芬圖紋按照頭部的形狀可以分為「鷹型格裏芬」、「獅型格裏芬」,一般愛情海、希臘、西亞地區「鷹型格裏芬」佔據統治地位,而西伯利亞南部、中亞地區以「獅型格裏芬」見長。[30] 《動物紋飾與黃金的美術:後期斯基泰的美術:巴澤雷克文化的特徵》[31] 《動物紋飾與黃金的美術:後期斯基泰的美術:格裏芬的傳播》[32] 彼得·庫茲米奇·科茲洛夫(俄語: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1863年9月26日—1935年10月3日),俄國探險家、考古學家。出生於斯摩棱斯克,1884年隨普爾熱瓦爾斯基在新疆、西藏以及蒙古一帶探險。1893年獨立率隊。1907年,科茲洛夫在內蒙古阿拉善盟額濟納旗境內的額濟納河下游接近居延海發現了西夏古城黑水城遺址,發掘出文物三千餘件,其中包括僅存的西夏文、漢語雙語詞典番漢合時掌中珠。1924年,科茲洛夫在蒙古國的諾音烏拉山發現匈奴古墓群,獲得大量漢朝和匈奴文物。1926年後退出探險生涯,定居在諾夫哥羅德。人物簡介來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彼得·庫茲米奇·科茲洛夫/1850818?fromtitle=科茲洛夫&fromid=6149262&fr=aladdin[33] 《從考古學看匈奴時代:匈奴的王墓:諾彥烏拉墓地的出圖品》[34] 西岸:《格裏芬的飛翔》,連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7f097c0b0100s2ys.html[35] 【日】林俊雄:『グリフィンの飛翔——聖獣からみた文化交流』,雄山閣,2006年7月5日初版發行。[36] 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5頁。[37] 《騎馬遊牧民的誕生:遊牧的產生與發達:歐亞草原地帶的遊牧化緩慢》[38] A.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p.95.//轉引自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5頁。[39]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允晨文化,1997年,106-107頁。[40] 《騎馬遊牧民的誕生:遊牧的產生與發達:騎馬遊牧民的正式誕生》[41] 《騎馬遊牧民的誕生:遊牧的產生與發達:遊牧是在何時、什麼情況下產生的》[42] 《騎馬遊牧民的誕生:動物的家畜化:家畜的角色》[43]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允晨文化,1997年,第108頁。[44] 《騎馬遊牧民的誕生:遊牧的產生與發達:先有馬車還是先會騎馬?》[45] 轉引自《騎馬遊牧民的誕生:遊牧的產生與發達:先有馬車還是先會騎馬?》[46] 《騎馬遊牧民的誕生:遊牧的產生與發達:先有馬車還是先會騎馬?》[47] 【俄】E.H.切爾內赫、【俄】C.B.庫茲明:《歐亞大陸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王博、李明華譯,中華書局,第1頁。[48] 【俄】E.H.切爾內赫、【俄】C.B.庫茲明:《歐亞大陸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王博、李明華譯,中華書局,第191頁。[49] 【俄】E.H.切爾內赫、【俄】C.B.庫茲明:《歐亞大陸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王博、李明華譯,中華書局,第270頁。[50] 【俄】E.H.切爾內赫、【俄】C.B.庫茲明:《歐亞大陸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王博、李明華譯,中華書局,第191頁。[51] W. N. Mcneill,History of World,Oxford,1979,pp.49-50.//轉引自林梅村:《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35頁。[52] 林巳奈夫:《中國先秦時代の馬車》,《東方學報》29冊,280頁。//轉引自林梅村:《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35-36頁。[53] 轉引自林梅村:《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65-66頁。[54] 【俄】E.H.切爾內赫、【俄】C.B.庫茲明:《歐亞大陸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王博、李明華譯,中華書局,271-274頁。[55] 【韓】桂勝范:《桂勝范評<想像異域>丨裁決文明》,丁晨楠譯,《澎湃·上海書評》,2020-03-09。連接:https://mp.weixin.qq.com/s/sbAQ1jRRTSNz3j_t2RyBIw[56] 葛兆光:《傾聽來自韓國學界的聲音——回應桂勝范教授對<想像異域>的評論》,《明清史研究》,2020-03-16。連接:https://mp.weixin.qq.com/s/cKZrad7hwsrISsTriwfmcg[57] 《從考古學看匈奴時代:游牧國家中的定居聚落:匈奴有農耕和定居聚落嗎?》[58] 《從考古學看匈奴時代:游牧國家中的定居聚落》[59] 《從考古學看匈奴時代:游牧國家中的定居聚落:中蘇對立的陰影》[60] 《從考古學看匈奴時代:游牧國家中的定居聚落:伊沃爾加城塞聚落的機能》[61] 根據尾形勇對屯田制的分析,認為自西漢武帝、昭帝時期開始的中國屯田,有兩種擔任不同角色的兵卒,分別是「鎮守烽火臺的戍卒」、「進行屯田的田卒」,本書作者林俊雄也持此觀點。參見【日】尾形勇,<考察漢代屯田制>,《史學雜誌》,七二:四,一九六三。//轉引自【日】林俊雄:《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陳心惠譯,八旗文化,2019年。《從考古學看匈奴時代:游牧國家中的定居文明:伊沃爾加城塞聚落的機能》[62] 《從考古學看匈奴時代:游牧國家中的定居聚落:伊沃爾加城塞聚落的機能》[63] 《司馬遷所描繪的匈奴形象:游牧社會和農耕社會:從中行說的發言中所看到的事情》[64] 《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65] 《司馬遷所描繪的匈奴形象:游牧社會和農耕社會:叛變投靠匈奴的宦官中行說》,《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原文為:君臣簡易,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66] 【俄】E.H.切爾內赫、【俄】C.B.庫茲明:《歐亞大陸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王博、李明華譯,中華書局,251-252頁。[67]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允晨文化,1997年,144-145頁。[68]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03页。[69] 《草原王權的誕生:結語》[70] 《草原王權的誕生: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