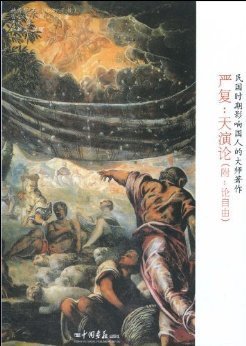
《活色严复》是一本由陈美者著作,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页数:1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活色严复》读后感(一):第一次读懂了遗老遗少
严复于我,向来只是历史书上的寥寥几句定论。我们看历史人物,信奉盖棺定论,又最痛恨晚节不保。而这本书让我第一次走近这些遗老遗少,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平视他们。严复或是郑孝胥都是有污点的历史人物,无论是位列复辟筹安会之列还是出任伪装满洲国总理大臣,如今看来都是为人所不齿的行为。林纾也好不到哪里去,每年远赴光绪帝墓前只为一次长哭,我们完全可以很有历史优越感的嘲笑他。然而,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遗老遗少们,也曾是热血少年、奋勇中年,他们只是被困在大清这个精神上的原生家庭里,终不得解脱。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有“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传统,他们只是作了当时当下自己认为的对国家最好的选择而已,谁又能保证自己始终看得清历史潮流始终能顺流而下呢?你可以嘲笑他们的行为,但不能嘲笑他们的初心。没有一次又一次的试错,何来今日?
《活色严复》读后感(二):“活”着的严复——读陈美者《活色严复》
看完一本书后,再回过头去一再品味书名,这多少算不上是典型的文学现象,毕竟如果对一个味同嚼蜡的书名进行回顾,则是一种机械的、自限的行为。但陈美者的《活色严复》却让我品咂,如是者再三,原因就在于它以简短的词汇蕴含了丰富的内涵。
我一直注意的是“活”字。它看似寻常,但欲深入了解陈美者笔下的严复,则需深察之。仔细揣摩它,便可从中见到本书在呈现严复这个人物的性格、形象等方面的精髓。
何谓“活”?文学史上几多经典作品,无不昭示着一个道理:文本所刻画的人物之所以“活”,乃在于他的动态变化。他生活在世界上,感受世界,奔波于世界,更深刻的是世界的芜杂与丰富让他的心灵不断变化,甚至走向矛盾的深处。他就以此成为一个“活”的人,此“活”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动作、行动,亦是他心灵的动态。当然,前者最可能的是他“狭小”的个人日常世界,而后者的伟力在于人在时代、思潮等面前的内心世界的波动。只有一再地行动,一再地波动,才能见出人物的“活”。陈美者的《活色严复》就在于揭示了严复的“活”。其主要因由在于“不如意”,即严复的“活”正隐含于此。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评论家曾念长专门为本书写的《写作与同情》这篇文章,他很到位地指出了这个基本问题,大胆地写道:“西学第一人还在,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还在,袁世凯的幕僚也还在,但美者将有着这些身份的严复来回到人间烟火中来,让他在柴米油盐中奔波着,在家国动荡中煎熬着。”正是在这些撕裂的日常生活、政治生活中,严复成了一个“活”的人,一个奔波、煎熬的人。
但一个人“活”着,并不仅在于他的身体劳累等,更在于他的心灵运动。心灵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面貌,而正是强烈的精神面貌反过来昭示着一个人确实“活”着。陈美者深刻地写出了严复的心灵运动。比如,严复对后世的重大影响便是他翻译的那些著作。然而,对这一成就,严复自己如何看待呢?陈美者就写出了他的复杂心理:“在外人看来,作为一代翻译家、思想家,严复的人生当然算是成功的,可严复对于自己毕生经营的翻译与学术,有着一种难以细说的复杂心情。他对儿子说:‘有志之士,须以济世立业为务,不宜溺于文字,玩物丧志。’又有诗句道:‘文章一小技,旧戒丧志玩。’”这明显是一种心理的错位。但在这一错位的巨大断裂中,我们才窥见了严复的心灵活动,才知道他的所思所想。我们感知到一个不依寻常规定的人,看到了严复心灵里“求而不达”的丰富的痛苦。也正因为此,严复“活”着的、深刻的矛盾才显露无疑。
其实,严复是一个言说不尽的对象,陈美者的这部书只是这个对象世界里漏出来的一道光。这光可能还会令人诧异、不习惯,但它终究实在,更展现了艺术的魅力。我们从中感受到一个“活”的严复,活生生、活灵活现。陈美者用文学的方法写出了不一样的严复。
《活色严复》读后感(三):在挫败感中燃烧 (by 万小英)
读《活色严复》,让我想起现在一个网络流行词:“丧燃”。意思是面对生活的沮丧,努力燃烧着。陈美者笔下的严复倒有些“燃丧”的意味,因为其“燃”的一面,几乎成为一种常识,但是你见过“丧”的严复吗?《活色严复》陡然让我们发现,为世人所崇拜的严复原来一生都在被挫败感折磨着。
对福州人来说,严复再熟悉不过了。他是福州的骄傲,是福州精神的一种代表,是福州文化的一种体现。他是近代启蒙思想家,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曾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监督、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纂;翻译有《天演论》等,系统地将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等介绍到中国,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郎官巷严复故居中的雕像这些都是严复生命中的“燃点”,是世人眼中荣耀的生命段落,但《活色严复》似乎有意跳过这些,笔墨重在严复的诸多不顺与“心结”:对科举的执着,对生计的经营,对为国所用的渴望,对老病的悲凉等等。
严复是矛盾的、深邃的,人生经历复杂、跌宕。他受过西式教育,也翻译引进西学,但骨子里还是传统的士大夫,对自己没能金榜题名一事无法释怀;他提倡西学,但晚年意兴阑珊手捧的依旧是《庄子》;他的翻译作品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经典,但他个人对君主制寄予厚望;他也排斥新式的自由婚姻制度,其女儿遗憾地孤独一生……
在清末新旧更替的时代,似乎总有选择题,往这边还是往那边。但其实,人往往只有一种机会,那就是被自身个性与认识牵着走,而严复走着走着,往往就会走过头。严复成于时代,也沮于时代;成于自身的追求,也沮于自身的局限。
在翻译《天演论》的时候,严复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归纳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开创性地将生物进化论拓展到社会进化论,对中国近代社会启蒙起到非同寻常的指导作用。对严复来讲,也存在着怎么“竞择”,怎样“适存”的问题。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有些颓丧,觉得自己对社会已是“无用之人”。他大概也被自己创造的“口号”打击了吧。
《天演论》陈美者敏锐地捕捉到严复的内心感受。颓丧与振奋,于人生不过是寻常。只不过对那些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常常将目光聚焦其闪亮之处。陈美者以一个年轻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将严复的“黯淡”之面照亮出来。这样的严复,反而让我们觉得亲近。
《活色严复》行文笔调理性,架构逻辑具匠心,以阳岐、马尾、郎官巷三个地理坐标作为观测点讲述严复丰富的生命世界。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仅是写了严复,而是通过严复,写出了人生的许多真相——思想与现实总是有着巨大的裂缝;心里捂着的一个个“结”堪不破,如何安身立命;自己感受的人生和他人感受你的人生何其不同——这些说的是严复,何尝不是说芸芸众生?可以说,只有六万字左右的《活色严复》是本小书,但不失厚重内涵。
我与美者有一面之缘。当时一起边走边聊,我们各撑伞走过一段小街。我的伞一直是张着的,但是美者每次走到树或屋的阴影处时,都会将伞收起,走两步有太阳,又张开,如此反复,几乎是无意识的动作。真是可爱的人!也终于有些理解,她能打磨出《活色严复》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是这般严谨耐心之人。
《活色严复》作者陈美者在郎官巷# 该文原载《福州日报》9月16日第6版。
《活色严复》读后感(四):“孰谓冥冥中无鬼神哉”:严复在郎官巷的最后一个十二月
《活色严复》一书,以福州阳歧、马尾和三坊七巷三个地理坐标为观测点,书写严复的不同侧面。位于“三坊七巷”中郎官巷的严复故居,是当时福建省督军兼省长李厚基为严复购置的。严复于1920年底回到福州,居住在这里,直至1921年病逝。严复于此居住的时间不长,但这里是他落叶归根的地方。本文选自《活色严复》,作者陈美者,曾刊发于“澎湃·翻书党" 。 严复自幼读私塾,深受传统文化浸润,虽精通西学,骨子里还是一位传统士大夫。当社会进程风云多变、国家前途不明朗时,他为家国命运担忧,自恨年老无用,只能求诸神灵。他对《周易》颇有造诣,精通卜卦之术。1911年2月到9月之间,正值动荡之时,严复频频占卜,占财、占婚、占升官、占外出贸易、占临产吉凶等。在极为脆弱无助之时,严复俨然以卜卦作为人生指导。随着际遇的改变,严复职场得意,受到袁世凯的重用,此后日记中就不再提及占卜。1918年后,严复年老衰病,身心疲敝,他又笃信起扶乩之事来。
郎官巷 严复故居1918年4月10日,《时报》刊登了上海灵学会出版的期刊《灵学丛志》的广告,其中竟有严复对上海灵学会的支持。上海灵学会的组织者俞复与严复相熟,《灵学丛志》的第一、二期都有寄给严复。严复很感谢,第二期十本收到后,除自留一册外,将其他九册分送身边朋友。严复的态度是认真的,不仅阅读这份杂志,还与至交谈论。1918年4月29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得严又陵书,极持灵魂不死之说,于余所谓‘无知之灵变而不灭,有知之灵逝而不留’者犹未了解也。”相对于郑孝胥不冷不热的口气,陈宝琛的反应热烈多了,还把自己1887年在福州鼓山的扶乩活动,详细告诉了严复:
当年陈宝琛赋闲在闽,为遣兴,在鼓山灵源洞下建听水斋,方便游山玩水后在山上留宿。在听水斋中,他曾连续两个深夜和同行的几位诗人一起扶乩,主要问“光绪十五年以后国事”。
深夜、山洞、玄诗……这些元素,让“丁亥六月山居之事”充满灵异气氛。严复听后大为惊服,觉得很是灵验,“孰谓冥冥中无鬼神哉”,连忙又把这件事告诉了俞复。
陈宝琛、严复的共同好友林纾也曾说到扶乩这件事。林纾是个浪漫文人,他在《畏庐琐记》中记下自己读到或听到的各种奇怪、有趣的事,其中不乏神怪之事,比如《为鬼梳头》《为鬼拍照》等。但他写下这些,主要还是出于一种小说家的猎奇心理,觉得好玩。对于扶乩,林纾的态度显然有别于陈、严二位。在《许由父》篇中,林纾写道:“有轻薄子,自言能调乩仙,下笔成诗,颇有佳者。有许姓少年,颇知其谬,往往举古事难之,乩不能答。”林纾还对乩仙所提之问,进行一番考证解答,颇有戏谑之味。
严复所在的时代,会笃信扶乩的读书人,一般还有以下共同行为特征:写古体诗、抽大烟、纳妾、采用干支纪年,并对帝制怀有眷恋,在转型时代,无所适从,焦虑惶恐,不知如何安放身心。
严复墓地1920年12月24日,严复派三子严琥到老家阳岐尚书庙请丹。第二天,严琥回到郎官巷,为父亲带回三道符。这是在尚书庙扶乩时,降仙罗真人所赐的。严复服下这三道符后,情绪略有些激动,一口气写了四首诗,其一为:
权利纷争事总非,乱来十见日周围。 天公应惜炎黄尽,何日人间有六飞。
六飞是古代皇帝的车驾。当晚,他睡眠很差,哮喘得厉害。
这是严复在郎官巷度过的最后一个十二月。
《活色严复》《活色严复》读后感(五):与挫败感同行的人
与挫败感同行的人
在读关于严复的这本薄薄的小书前,我对严复的了解正如这本书勒口的几句介绍那么粗浅:
“严复(1854-1921),初名传初,曾改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福州)人,曾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清朝学部名词馆总纂、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等职。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其八大译著,包括《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系统地将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等介绍到中国,对近代中国思想史和文明转型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他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上,成为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中国人所共享的知识体系的一个知识点,他是近代史上最早开眼看世界的那批人中的一个,而正如绝大部分人只知《天演论》之名而并未真正读过这本书,绝大多数人也只知严复之名,并不真正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在“名”与被简化了的观念之后,我们所认识到的,往往是书上一桢模糊小照。我们记住了他的“重要性”,然后通常失去了深究的热情。
因此,我不能妄测作者——生于1983年的陈美者,一个文学刊物编辑,写作这本书的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在朋友所写的书的长序里,可以看得出她写以写性灵派的散文见长。也许是因为身处福州,因为三坊七巷依旧,严复、林纾、林觉民们的余响依然在读书人的心头回荡,文字后辈们,依然想着追摹往日荣光。然而吸引我认真读起这本书的,是曾念长的序的第一句:“挫败感折磨了严复一生,也穿过百年时光,折磨着那个试图走进严复世界的人。”
那么,这个“严复的世界”,是个怎样的世界?严复的世界,有一个现实的世界,少年丧父,幸而入新成立的马尾船政学堂学习新学,又赴英留学,之后在北洋水师水堂供职多年,渐以译著名满天下,就任过多所学校校长,但时间都不长,在履历上读起来显赫,实则并未成其功尽其志。他亦有政治抱负,接触过的最高统治者,一为光绪,一为袁士凯,只在晚清政局中擦肩而过,从未进过权力的中心,理想初有即告破灭,时代前锋转眼老朽,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也只能“袖手躬居,坐观陆沉”。但严复的世界,还有一个著述的世界,他的译著建构起一个近现代世界的理念版图,“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他立功之业未成,而立言之业光耀千秋。
第一个世界关乎历史,第二个世界关乎学术,都兹事体大,并不是这本小书所能言尽言彻的,《活色严复》里也写严复的人生经历与译著事业,然而并没有进入到洞察历史与辨析学术的维度,她在祖厝与故居的行走,在史料与作品、信札的阅读中,走向的是严复的第三个世界,他的心灵世界。
“1918年的一个冬日,寒意袭人,阔别家乡二十五年的严复归来,回到福州阳岐。
不知当夜他是否成眠。或许是听着风摇木窗、雨落天井,时不时咳嗽,起身服用药膏一匙再去卧床,或抽一口水烟,就有一团雾气升腾,于这幽深光影中,看见少年往事历历。”
这样的文字,是对一个人的处境的想象。处境——不是历史,是历史给到每一个具体的人那一段具体的时空和物质,而建立在这样的时间与物质基础上,有了人的感受与人的情感,人的思想。心灵世界是物我合一的,面对一个历史人物,得从线性的历史中建构出一个有真实感的,立体的处境,在那个处境里体会到人物的所感所思,才贴近了他,他的居所,他的身体,他的内心。
在这个维度上,我读到《活色严复》这本书的好,与美。这种写法,既要有对材料的掌握,而又要有一种越过材料面对一个人物的“心心相映”——因为她的考证,不仅是资料的验证,当她写一种处境,一种心情时,要通过自己的“心证”。是不是曲解了,是不是滥情了,甚至是不是言过其实了,文过饰非了。这是一种文学能力,越过史料,见到人心。但这种能力,又往往是被忽视的——相比于历史与学术,去还原严复某个阶段的心灵感受,其意义何在呢?相比之“对近代中国思想史和文明转型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这样可以划重点的意义?
我想陈美者是自然而然地向严复的心灵世界靠近的,一个人的天赋与才能把自己引向某个世界又建构某个世界,她重新编织一种叙事方式,这种叙事用了一些小说的写法,但叙事的笔调更是散文的,容纳进她对史料的整理与取舍,对处境的想象,以及对这种想象的评议。她写得简洁而朴素,在想象与评议上都比较克制,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不同流俗的、相当古典的文字的品德。
明晰的结构、流畅的文字让读者进入了一个严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似乎是与严复有了一种单独相处的,较为亲密的关系。少年的不易,中年的烦忧,老年的病弱,他是不停挫败的,但又是不停在“行动”中的,无论是求学、工作、翻译、照顾家人族人,乃至最后的重修尚书庙,他是一个一边感叹“浮名满世、资力浅薄”,一边其实行动力极强地过完一生的人。他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把笔伸向了未来,但同时,生活的方式与观念,又带着往日的浓重遗痕。在读过这本书之后,我的脑子里有一个我能想象与理解的严复,反过来,那段历史也更有温度。
这本书前曾念长的序《写作与同情》极为可读,对历史对文学乃至对作者,都有很独到的见解。他写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内在真实的美者,或者竟如她笔下的严复,是一个被人生埋没了笑意的人。她大抵也是充满了挫败感的,却无宏大的人生叙事可做注脚。”——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宏大的人生叙事,而总都还品尝过挫败感,但“被人生埋没了笑意”吗?这我有点怀疑,不止因为书末勒口上作者的照片上有一个显然的笑容,而且因为她在后记里这么写:
“时日绵长,三年过去,我甚至怀疑自己写不完这本书了。最记得一个夏季午后,天黑,暴雨,雨打在青石板上,雨打在芭蕉叶上。我端坐书桌边,透过层层叠叠的书籍,透过木窗,冷冷地看着这场雨,看出雨珠一滴滴的狠劲。我舍不得动,继续伏案,只是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待完成书稿,我定要好好地淋一场雨。”
——一个能看出“雨珠一滴滴的狠劲”依然下定决心“好好淋一场雨”的人,是一个能与挫败感同行的人。对挫败感的观察与体味,是她连接历史、文学与自我的纽带,至于一个没有宏大人生叙事的人,能有勇气直面另一个相当重要与伟大的人的心灵世界,是文学,给她的力量。
《活色严复》读后感(六):在字里行间苏醒过来(by 张家鸿)
陈美者的《活色严复》是一册厚重的小书。小书之“小”指的是篇幅与体量,整本书不足七万字。厚重之“重”在于它是作者全情投入的心血之作,并非操刀于纸面上的雕虫小技。严复难写,因为他所处的是新旧交替的时代,也因为他自己是个贯通中西的人物。要把一个复杂的个体置放于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进行考量、省视、探究,进而品咂出其精气神,实非易事。基于此,《活色严复》对陈美者或是别的有野心的写作者来讲,都是一次极具难度的写作。传记写作的难度,不在于走传主走过的路、读传主写的译的著作,而在于如何走进传主的心里,触摸他的脉搏,聆听他的心跳,感受他交集百感与杂陈五味。
读过《活色严复》,我印象最深的是严复的科考经历。如果说严复的一生有缺憾的话,科举的屡战屡败当是其中之一。即便是在1880年被李鸿章调至天津水师学堂任职之后,他依然于1885年回闽参加科考,虽然结果还是名落孙山。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足可见其勇气与毅力。然而,其心中的痛楚与挣扎也是不难想见的。更有意思的是, 1910年严复受到朝廷恩赏被授予“文科进士”。次年,辛亥革命枪声响起,授予他进士的这个朝廷画上句号。对一生汲汲于功名的严复来讲,这样的履历与结果岂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道明?只见陈美者写道:“对严复来说,心中的某些东西也被击溃了。清廷授予他的这个名分,亦成了一个遥远而伤心的念想。”我也是从这句话起开始认定,陈美者笔下的严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否则“活色”二字从何而来?
阳岐河上的午桥他疼爱外甥女何纫兰,视如己出,一会儿担心她身体不好,一会儿又期望她有所进步。他对杨度的为人深恶痛绝,斥其首鼠两端,筹安会开会、请愿等事情他均未参加。他既看好袁世凯又反感袁世凯,因此常处于左右徘徊的境地之中。他晚年一直在为返回故乡还是定居北方而犹豫不决,左右摇摆。他年轻时用心于西学引荐,晚年才忽然意识到孔孟之道是最好的矿藏。他和郑孝胥的友情跨越几十年,有分有合,有喜有悲,有亲密有隔阂。这是我品读的第一本关于严复的传记,却觉得好像严复尚在人间。有一股温热的气息从字里行间传递出来。
放眼严复生平,最意味深长的莫过于他用力最深的执教鞭与走仕途令他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常心生无奈、沉痛、悲愤;反倒是主业之余的翻译成全了自己的青史留名。比如,翻译家严复之影响力岂是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可以相提并论的?因此,把主要笔墨置于何处,便成了摆在作者面前的问题。陈美者并没有对他“翻译家”的身份大写特写,而是把他的翻译及其作品视为必要且合理的人生要素,进行冷静平和的叙述,还原其具体的心境与处境。
更为难得的是,这册小书写的不止是一个严复,写出的还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法马尾海战中,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战斗中福建海军全军覆没,船政二十多年积攒起的家当毁于一旦。在铺垫过这样的背景之后,再请严复登场亮相,就让传主有了发声的可能。比如他反对求和,因为求和会让本就伤了国本的中国雪上加霜。比如他认为国家平时不留意真正有能力的人才,一旦发生战事,则必定无人可用。最有见地的莫过于他认为“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困耳。”以此为基础,作者进一步诠释道“如果人心涣散,大力练兵购船又有何用?”由此可见,严复对战争的失利的表层及深层原因的分析不可谓不独到深刻。李鸿章、袁世凯、吴汝纶、林纾、郑孝胥等诸多晚清重要人物,均在书中有多少不一、轻重不等的登场。即便是简单的几个镜头,也能起到有力支撑起传主的作用。
即便如此,我深知“活色”二字是陈美者的自我冀望。她心中所期盼的,笔下依然力有未逮。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掉进了时空隧道,固执,幼稚,野心勃勃,想要用细小的碎片描摹一段历史,还原出一个人物的活色。”正因为如此,她与严复的心灵对话并不因这本书写作的终止而画上句号。在现世的繁忙之中,能够走近一个历史人物,走进一颗特殊的心灵,无疑将是持续一生的重要命题。
严复晚年主持修建的尚书祖庙为历史人物撰写传记,最怕的是作者持有后来人的居高临下。居高临下者主要在于占据道德制高点之后的惯性批判。这样的批判难免让笔触拐弯、让传主变形,甚至让传主成为作者可以随意涂鸦、捏造、篡改的人物形象。当读者明显感到随意的臆想与虚构多过基于文献资料的探究与考证,传记已不是传记。此外,传记写作还忌讳隔靴搔痒,沦为由时间串连起的材料堆砌和累积。如此一来,则文字是疏离的、文本是拼凑的、传主是僵死的、灵魂是虚无的。很显然,《活色严复》没有居高临下也不是隔靴搔痒。一册传记倘能在读者心中树立起一个真实的传主,是足以令作者欣喜甚至自豪的。真实,既是传记写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最高要求。让传主在书里倾吐心声从而打动读者,让读者与传主之间如面谈,这便是“真实”。真实与否并无具体的衡量标准,如果有就看其是否能够真正打动读者。
迎风站在马头江岸走过细长曲折的郎官巷,读过严复翻译的西学著作,琢磨过严复人生的种种际遇,并把这些与传主有关的点点滴滴,存放于心中经过多年的发酵、提炼、结晶,陈美者才让沉寂于历史深处、安躺于故纸堆中的严复,在字里行间苏醒过来,进而传递出低沉的慨叹、肆意的笑声、隐约可感的哀伤、清晰可见的壮志。陈美者的文字自有一种引力,把读者拉扯住专心地听她讲故事。这种引力不是似有若无的,几可算是强烈的存在,让人有置身现场的灼热感,离开时产生明显的若有所失之感。正因为如此,我才把《活色严复》读得很慢很慢,一天读一节或两节,竟也把它读了许多个日子。如此,我才把一册小书读出很重很重的感觉,并因此而私心里想推荐给更多读者。
尚书祖庙楹联上的严复印章《活色严复》读后感(七):写作与同情
写作与同情
曾念长 (文学评论家、福建省文学院副院长)
挫败感折磨了严复一生,也穿过百年时光,折磨着那个试图走进严复世界的人。
我不曾想,在美者笔下,严复竟会活得这般不如意。几年前,我读了一篇文章,了解过严复的科举失败史。但那也只是在一个具体方面说说严复的不走运,在世人眼中,实在无损于他的得意人生。严复是挤进了历史圣殿的人,是有故居可以挂牌的人,是被成群结队的游客瞻仰着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想象,他这一生都被挫败感缠绕着呢?据我所知,美者写过一稿,不满意,又重写一稿。我未曾见过第一稿,但我想,那里面的严复或许是另外一种生命风景吧?就像我们在传记作品中读过的许多历史人物,几乎都活在同一种人生模式里——在风雨泥泞中砥砺奋进,最终开拓出一种昂扬励志的生命境界。
不去想美者最初是如何写严复的了。她最终呈现给我们的,确凿无疑是一个无法摆脱挫败感的严复。数次科考失利,暂且不说了,许多人都知道,那是严复早年的耻辱,和一生的心病。但是到了晚年,严复总该是有许多得意事可以显摆的。当他在1918年回故乡阳岐时,本该是一副达人荣归故里的气派,可是没有。回顾一生,家累和国忧齐涌心头,严复竟被淹没在一种遗世情绪中。第一章《行香尚书庙》,美者站在阳岐村这个地理坐标上写严复的家累、国忧和科举之殇,区区万字写尽了严复一生的不得意。但她没有就此打住,到了第二章《风起马头江》,以马尾船政为地理坐标写严复在海军、教育和翻译三个领域的经历,本可以让严复得意一些的,结果照样是沮丧,用美者的话说,就像是一手好牌被打烂了。这一番梳理下来,似乎再无伤心事可写了。但是到了第三章《夕照郎官巷》,美者站在一个名流云集的地理坐标上,却听出了严复内心忧伤的交响。郎官巷是福州三坊七巷之一巷,我时常遇见一队队游客站在严复故居的门前,听导游滔滔不绝讲述一个欣欣向荣的严复,丝毫没有美者笔下的失意和感伤。大概没有其他人会如美者这般,将严复的挫败感写到这份上了。我发现,美者笔下的严复,竟是一个没有笑容的人。我想严复一定是笑过的,在被船政学堂录取时,在抱得美人归时,在日进斗金时,在与友人畅叙时。然而,所有与辉煌相遇时发出的笑,都已烟消云散了,只剩一副凝重而忧伤的面孔。
1889年冬着丧服的严复似乎是存心的,美者不想让严复过上好日子。可仔细想想,又不是这样的。
我隐隐觉得,倘若不是隔着遥远时光,美者多半不会对严复产生兴趣。大体来说,严复理性有余,却少了点感性浪漫的生气。他热心于功名和时事,专注于实用之学,早期以进化论思想为时代演进推波助澜,后期则求诸中式传统,试图力挽时代狂澜。这样的人,不能不说伟大,却将现实世界拥抱得太紧,显得有些无趣,不大可能引起美者的精神共鸣。我读过美者的生活散文,大体印象如下:感觉至上,总能在日常生活的紧张间隙里发现诗性之光。这样的美者,自然与过于理性的严复不太相称。若在同一时空,两个人对话起来,估计是要冷场的。我只能这么想,美者走进严复的世界,是一种误会,也是一次例外。她只能以自己的眼光来打量严复,却意外卸下了附加在严复身上的各种概念标签,让他重现出一点常人的活色来。西学第一人还在,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还在,袁世凯的幕僚也还在,但美者将有着这些身份的严复拉回到人间烟火中来,让他在柴米油盐中奔波着,在家国动荡中煎熬着。第一章第一节写严复的家累,第三章第一节写严复居无定所,不能不说是美者的独特敏感。她从最日常的饮食起居中看到了严复人生虐心的真实。今天我们走进严复故居,多半只会遥想当年,严复是如何一等风流人物,又怎知他一生求个安稳居所而不得呢?杰出人物往往被各种概念打扮得光鲜亮丽,似乎真如中国人挂在口头上的那句好话——万事如意了。但是回到常人层面,总是十之八九不如意的。严复如此,美者或许也是这般。
当我读完这部书稿,我告诉美者,我想从同情的角度来谈谈她的这次写作。她似乎觉得不妥,问我,她有什么资格对一个历史大人物表示同情呢?我未做解释。我知道,今人理解的同情,是一种道德安抚,是优越者对弱势者的怜悯和关怀。而我说的同情,不过是一种朴素眼光。它回到了初始语义,用来表示一个写作者感知世界的基本态度和方法——人同此情。
读《活色严复》,我分明看到,一种同情心照见了严复,也照见了走进严复世界的那个人。生活中的美者也常有笑对人事的时候,但那也只是表面的真实。内在真实的美者,或许竟如她笔下的严复,是一个被人生埋没了笑意的人。她大抵也是充满了挫败感的,却无宏大的人生叙事可做注脚。唯有从她的生活散文里,我们可以隐约读到她对平庸现实的不满,和与世界无可和解的冲突。
从同情心出发看严复一生,其命运转折的关键节点发生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这是严复仕途的终结,也是他治世理想的破灭。美者多次写到了这个转折点,看似一种重复,在情感逻辑上却是一种无心的自觉。现在看来,严复晚年的悲情,早已是被这个转折点注定了的。今天我们把严复定位成一个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看到了他的不朽功业,然而回到当时,这些都只不过是严复无心插柳得来的,而他真正在意的,却是求而不得的现实治用和现世功名。杜甫曾经心疼李白不得志,在诗中说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话其实也适用在严复身上。严复之名,或许不负千秋万岁,但是朝他身后看去,却是寂寞的影子。这种寂寞跨越时空,百年之后凝成心事絮语,回响在一个同情者的内心里。在第二章,美者重点写严复在海军、教育和翻译三个领域的经历和成就。说起来,这部分内容是学术界研究得最透彻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美者再写这些,真有点拾人牙慧了。我通读书稿,就觉得这部分最为刻板和无趣,像讲解员历数一个名人的重大成就。但是写严复,这些生命历程又是无法越过的。美者其实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好在行文到第三节,写到严复的翻译事业时,一笔神来,陡然翻转了第二章的平庸局面。美者用了几千字篇幅描述严复从事翻译的始末,使我们顿然明白,严复实则是因治世心切,却又无从着手,才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的。而当政治理想最终破灭时,严复对自己的翻译事业也就颇为怀疑,竟然把它说成是东抹西涂、妄窃名誉之举了。简单点说,挫败感意外成就了严复的翻译,而翻译终究还是加深了严复的挫败感。这可真是与众不同的发现啊。倘若不是因为怀有一种同情心,美者写到严复的翻译,估计也只能人云亦云,重弹信、达、雅之类的老调了。
郎官巷,严复在这里去世然而这个带着一身晦气的严复,多少显得有些可疑。他被一种灰暗情绪笼罩着,成了一种主观的存在。真实的严复,总不至于是这样的吧?
可是真实的严复在哪里呢?
真实的严复只有一个,但他已消融在特定时空之中,不可重现。实证性写作试图通过见证和逻辑,无限接近这个唯一真实。但文学创作不应抱有这种野心。文学是承认昨日不可重现的,由此生成了看待过去的独特方法。崔护两次到访长安南郊一个村庄,见景生情,写了一首极有口碑的《题都城南庄》。当他写下第一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虽有些动人诗意,但终究还只是停留在故事层面。一俟写出下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故事转化成文学,诗性光芒就散发出来了。欧阳修有一首词,写元宵之夜,上阕流传极广——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倘若没有下文,这两句不过是文雅一点的俗段子罢了,算不得真正的文学。只有领会了下阕的妙处——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我们才算接受了文学的教育。我从中得到了教益,明白在现实世界无可挽回时,文学便诞生了。张岱写前朝梦忆,曹雪芹写大观园,白先勇写台北人,有着如此穿透人心的力量,或许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现实的世界,又以同情心创造了一个精神的世界。而那些能够将现实世界牢牢抱住的人,固然可以洋洋得意,可以舞文弄墨,可以附庸风雅,但他们终究腾不出一只手来,推开文学这扇窄门。
我读美者写老家往事的系列散文,总能看见那种在生命流沙中生成的诗性。但现在,美者需要面对的,是一个与其个人记忆没有直接关联的生命世界。当她带着同情心走进这个世界,那个唯一真实的严复已消失,无数个局部真实的严复却复活了。美者并没有效仿多数传记作品,以线性时间来安排写作,从而避免了走进唯一真实的死胡同。她以一个个地标为想象起点,将严复的个人史从线性时间中解放出来,重构一个具有立体时空感的生命世界。就如一幢层次繁复的建筑,外围有多个入口标识,每进一个入口,我们都能遇见一个严复,似曾相识,又不尽相同。有多少个地标被书写,就有多少个严复在复活。每写一个严复,都是一次同情的抵达。每一次抵达,都意味着踏进一个凝聚着历史魂魄的地标,与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相遇。
同情是一种诗性智慧,隐含着非凡的想象和洞见。我由此判断,美者是以真正的文学手法来写严复的,自然不同于一般的传记作品。严格说来,以文学的方法来重构严复的生命世界,是不太可能的。一则严复的时代离我们不远,尚未生成时空距离以供我们重新演绎历史。二来严复的生命世界填满了各种实证性史料,失去了传奇性。“活色严复”难写啊。倘若有人像罗贯中写曹操一样重构严复形象,恐怕是要被唾沫星子淹死的。我似乎看到了美者的压力。她努力搜集源头资料,将书籍高高叠起,埋下头去,一丝不苟做笔记,生怕哪里不实,被抓住了把柄。我倒不反对这个实证劲儿。然而面对史料和逻辑,美者多少显出几分拘束,甚至牺牲了诗性。她毕竟还是感觉至上的,面对失去了血肉和细节的史料,内心并不感到十分贴近。我说美者走进严复的世界是一种误会,也是一次例外,实则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大概她对“活色严复”之难写,事先不曾有过充分估计。
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写过一本有关李白的小书,用了一个有趣的书名——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世人印象中,李白不是浪漫洒脱的嘛,何以在李长之笔下变成了痛苦的形象?这般理解一个诗人,经得起考证吗?李长之在自序中说道,考证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或许也是更重要的,则是同情——深入诗人内心世界,去体悟,去吟味。李长之是真正的批评家啊!他用纯正的文学眼光,来看待文学中的关键问题,写出来的文章自然也是让人感到真切的。美者似无做个批评家的志向,走进严复的世界,或许真是个意外,但是通过这次写作,她恰好显示了天生拥有的,那种被李长之认为更重要的文学眼光——同情。
一个人通过一次写作,发现了一点自己,就是了不起的收获了。
《活色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