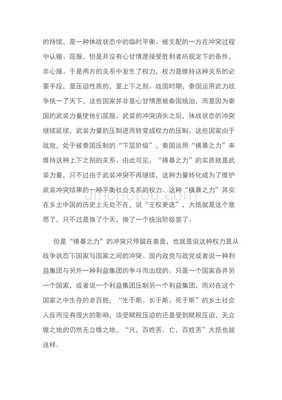
《自由与权力》是一本由[英] 阿克顿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42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由与权力》精选点评:
●可以读很久,很有思想的书
●演讲稿,所以找来英文版用来背背
●: D081-53
●柏克在1790年到1795年之间的言论,几乎成了法律和预言。为什么柏克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是的,他是多么地渴望彻底的自由——良知的自由、财产的自由、贸易的自由、奴隶的自由,等等。既然如此,柏克为什么还要站在反对彻底自由的立场上呢?是什么原因使他产生这样的认识的呢?这是缘于他对历史的理解,对过去的权利要求、对时间的权威、对已逝先辈们的意愿、对历史的连续性等因素的理解。在柏克以前也有人持有这方面的认识,但是,他们只把握了保守主义的其他部分内容。柏克则是一个十足的保守主义性质的人,这种十足性也把柏克信奉的其他所有原则都涵括起来,使得柏克第一个成为既是自由主义又是保守主义的人。这就是统一性和一致性的事物。其实柏克也不是一致的,但是,最后占优势的事物的存在又是源于统一性。
●有抱负的自由主义
●阿克顿勋爵是剑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大部头的《剑桥近代史》的编者。他的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长期成为全球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课题,他被称为自由主义的预言家和历史的裁判者。《自由与权力》是阿克顿关于政治自由主义哲学的论文集,也是阿克顿思想的精髓。
●自由与权力的平衡,需要制度界定,也需要道德界定
●无论何时,只要某个单一的明确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无论该目标是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国家的安全或权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对一个抽象观念的支持,此时国家走向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惟有自由要求实现对公共权威的限制,因为自由是惟一有利于所有人们的目标,惟一不会招致真心实意反抗的目标。
●公权力在ZG基本没有边界
●第一部分译的不错
《自由与权力》读后感(一):阿克顿:《剑桥近现代史》首任主编
阿克顿:《剑桥近现代史》首任主编
——认识每一个值得认识的人,读过一切值得一读的东西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伯/文
当阿克顿勋爵于1902年辞世时,他的名字并不为一般公众所熟知。也许有人知道,他是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士之一、剑桥大学史学教授、大部头《剑桥近现代史》的主编,还是1886年的《英国历史评论》的创建者之一。
如今,阿克顿已获得了一个预言家的地位,他最大程度地超越了19世纪中叶在英国根深蒂固的岛民心态乃至狭隘意识。
阿克顿,1834年生于那不勒斯,他有着复杂而高贵的家庭结构。阿克顿的世界主义情怀不只是个信条或修养的问题,而是他整个生命的本质。他早年是在那不勒斯、巴黎、伦敦等处的家族住宅中度过,他不久即可用几乎同样流利的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英语交谈和写作。后来,他在餐桌边使用几种语言,以方便和全家人交流。
阿克顿所受到的教育,突出反映着19世纪后半期天主教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学派。阿克顿于1850年到达慕尼黑,师从杜林格。正是杜林格用自己对学问的尊敬鼓舞了他,这种尊敬后来使师徒两人一起,陷人了同教会里一些势力的冲突。学术自治的原则,是阿克顿全部政治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
据说,阿克顿认识每一个值得认识的人,读过一切值得一读的东西,这两种优秀品质,即是从他到慕尼黑求学开始。他饱览史学、哲学、文学和神学方面的书籍,开始搜集藏书,后来数量变得极为可观。他周游各地,他同英国、欧洲大陆甚至美国的几乎每一位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和天主教信徒,以及很多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都建立了私交。他不仅生为贵族阶层的一员,而且很早就在知识、宗教和政治精英中间获得了类似的地位。
阿克顿晚年自称一生碌碌无为,他做过《剑桥近现代史》首任主编,为世人留下半部体例独特的史学著作,但除此之外未曾写下过什么黄钟大吕之作。我们今天看到他唯一的那本文集《自由与权力》,也不过是几篇演说、文稿和若干宗教文章杂凑而成的一册,然而这样的一本文集留给我们的智慧却超过了许多鸿篇巨制。
《自由与权力》读后感(二):书摘两篇:哪里有人民的良知,哪里就有自由+伟大人物几乎总是一些坏人
哪里有人民的良知,哪里就有自由
——弱势群体的安全状态是自由的试金石
阿克顿/文
诚实的民族才能得到自由
●自由属于那些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而不是那些尚未成熟或正在走向衰败的民族。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以什么标准来判定上述两种情形呢?以该民族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的内容作为依据。如果一个民族不尊重在陪审团面前所发的誓言,不受教育的培养,对不诚实的行为也不加以谴责,难道这样的心态还能与良知沾上边吗?哪里有启蒙人民的良知,哪里就有自由,反之,自由则不复存在。仅仅有物质上的快乐享受而缺乏精神思想的活动,只会使这个民族堕入麻木不仁的状态。
弱势群体的安全状态是自由的试金石
●自由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不依附于各种利益、各种狂热激情、各种偏见或各个阶级的一种状态。
●自由的试金石是身处弱势的少数人所享有的地位和安全状态。
●自由蕴含着这样一种理念价值:使老人安享天年,救治有疾患的孩子,拯救战争中失败的幸存者——因伤残废和绝望的士兵;自由也蕴含着这样一些努力:尽最大的努力和花最大的代价去改造罪犯,而不是把罪犯送上绞刑架时去祈求刽子手廉价的可怜。
●自由的本义:自我驾驭。自由的反面:驾驭他人。
自由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获得的
●自由根源于、存在于免遭国家权力任意干涉的私人内部领域之中。对良知的尊重与敬畏是所有公民自由的萌芽。
● 自由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它不是处于静止的僵化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努力和不断生长的状态。
只有当人们学会遵守和服从某些法则之后,自由才开始真正出现。在此之前,自由表现为无拘无束的放纵和无政府状态。所以,我们切不可把自由视为原始社会的表现形态。当然,原始社会也存在着某些自由的因素,例如他们不太看重权利,他们懂得某些少量的义务。
权力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腐败的力量
——伟大人物几乎总是一些坏人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
绝对权力会败坏社会道德。历史并不是由道德上无辜的一双双手所编织的一张网。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伴随着暴虐权力而来的往往是道德的堕落和败坏。
●不是为自由而存在的权威就不是权威,而是暴力。权威基于自由的原因而存在,就像手段基于目的而存在一样。但是,有些思想权威则只适合于它自己——它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作为一种实现更加高尚事物的工具。这是一种神圣的权利。
●只要条件允许,每个人都喜欢得到更多的权力,并且没有任何人愿意投票赞成通过一项旨在要求个人自我克制的条例。
古罗马人发现了这么一个道理并按这个原理建构了罗马共和国,那就是:权力,一旦它处于分立状态时,那么就没有必要取消它的存在。
对权威的限制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一个政府受到有效的限制时,它才是合法的。
●围绕着是集权还是限权和分权所展开的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现代历史的一种伟大的律动。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斗争,诸如宗教之间的斗争、种族之间的斗争、政治形式之间的斗争,实际上都是各种权力为增强和维护自己或弱者为捍卫自己而进行的永恒努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对暴力的坚持不懈的抵抗中,自由发挥了战斗的威力,自由获得了拯救并得到了发展。
●主张绝对权力的理由是:在某些地方你总得需要绝对权力来为自己增强信心、撑腰打气,因为你无法避免人性的软弱给你造成的困难。但是,我们的主张是:把绝对权力放到责任的集中营里吧!
《自由与权力》读后感(三):自由来自信仰
如诗歌一般的用词,如赞美神一般赞颂自由(权界),如警惕恶一般警惕专制,不论其来自自称上帝代言人的教会、自称君权神授的国王、主张绝对平等的革命党人、坚持统一论的民族主义者。
一、阿克顿生平
·显赫的贵族家庭背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勋爵
·太过博学以致不能写作,史学文学哲学神学。
·自由主义之目的,保守主义之手段。
·断言历史与政治密不可分。历史,政治,哲学,神学应四位一体。
·当时争夺世界的是代表开明代表开明学识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与自恃代表上帝的罗马专制教会之争。
·“我在自己的基本道德立场上是绝对孤立的,因此我无能为力。……用应者无几招人反感的文章去行善,让我的观点产生影响,其可能性是如此之小,因此我没有权利牺牲自己的安宁和教育孩子的责任。与其把时间用于一场无望的战争,还不如干点别的。我的生命过去被虚掷的越多,现在就越有必要转变,更好的利用余下的时光。”
—阿诺德汤因比:阿克顿是时代精神的一个奇特的牺牲品,工业主义不停的逼迫人们发掘新资料并相信劳动分工,他的窒息性影响使一个自由史的研究者手足无措,是近代历史学家中最伟大的头脑之一变成了才华虚掷的编年史编辑。
二、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是中世纪以后兴起的事,之前的中世纪神学并不认为历史有多重要
·文献与考据
·观念
三、古代自由史
·自由是古老的,而专制是新生的
·古老的自由,从部落到宗教信仰时代都保持着自由,哪怕是奴隶制时代,都坚信自然法高于成文法。
—犹太人之所以是上帝的选民也即他们坚信信仰上帝是为保障个人之自由而反对无限制度。
—古希腊到雅典时代才明了这一点从而留下不朽的文明成果,可惜文明太快地从新生到青年再到成年乃至衰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留下的著作是那个时代少数的文明之光,此外其他如柏拉图亚力士多德都无法在自由这理念下有所建树,尽管他们在政治学上奠定后世无法超越的基础。
·圣经新约中的思想,同样是经济学的前提。
—西罗马则被自由的蛮族人(条顿人)慢慢侵蚀,在那里文明停滞了500年,使得西方的学者得去东方的阿拉伯寻找古希腊文明。对此的对抗是领主与教会联盟形成军事权力的拜占庭帝国。但如果不是自由城市、工业、市民阶层的兴起(包括社会主义抬头),包括英国的大宪章和自由思想的确立,西欧将仍在俄罗斯式的帝国专制统治中。这个过程长达一千年之久。
—16世纪开始,马基雅维力的学说与专制君主制反扑的互构。是一种精致的邪恶哲学和自从斯多噶学派改造了异教的道德观以来从未有过的彻底的道德堕落。
—加尔文在布道,贝拉明在演说,只有马基雅维里在统治
—16世纪,欧洲各地国王倡导君权神授,而神权成为附庸,只有在极少数的学者思想家提出政治在于保护人类良知,提出君权民授。
—贵族政体的最佳保护是道德的败坏。—欧洲王权依靠联姻维系。
—那些曾长期尘封于孤独思想家的心灵和拉丁文卷册之中的朴素思想,即人类应当自理其事,国民为国家的行为向上帝负责的思想,是在美洲突然以一个用人权作为旗号的世界征服者的面貌,出现在他必定征服的世界面前。
—亚当・斯密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最终源泉的学说(来自圣经)同财富的生产者实际上由国民组成这一结论之间的关系。西哀士正是基于这一结论颠覆了古老的法国。
五、新教的惩罚理论
(重点在最后一段的总结)
—天主教一开始是宣扬自由的,只是在等他统一了精神世界之后才为了维护教会组织而变得不宽容,
六,美国革命的政治原因
—重点是开始的引言和最后一段总结,中间是论述过程。
—开始是说地方自治与联邦要求统一存在天然矛盾,美国自独立战争召开立宪会议起就一直作妥协而没有实质性制度安排,这为后来的南北分裂与战争埋下种子。(废奴运动只是一借口,本质是南北之间的根本差异)
—中间说明,民主制形成的多数人的统制仍然会形成专制暴政。而所谓的选举也会被操控而变成有限的权贵选举。此一问题在模仿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党上台后,远比保守的联邦党严重。
—最后说明,民主制需要历史条件,单一民族且平等化,否则就形成对其他种族和少数阶层的专制暴政和社会无序。而在多民族与多阶层社会中,君主制恰恰提供了一种较好的臣民统治关系和社会秩序反而使社会福利更高。所以,法国大革命在法国没有问题而放到其他国家反而造成灾难后果。美国也这样,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在美国制造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社会为个人利益提供保护,国家则是实现某种价值目标的工具,以国家之名实行统治只能是上述条件具备的民主制,否则专制暴政更甚于君主制,这点上共和之罗马与帝国之罗马便是例证。
七、法国大革命
—从费拉开始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也同时一场血与火的闹剧。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都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他们都不是自由。
八,与罗马的冲突
—罗马教廷在与科学与文学的冲突中证明了自己的腐朽与专制
—两次著名的冲突与挑战,一是??认为科学与信仰属于两极,二是??,代表德国神学与自由的学术界与罗马的冲突,而教廷显然以维护信仰之名行维护专制权威之实,用威逼和诈谋之术使德国学术界对罗马产生不屑。
—阿克顿自己解释了办的评论与罗马冲突的解决的理由,一是不愿在学术和真理上屈服于罗马的强权,二是不愿以坚持评论来挑战天主教信仰权威,所以选择了停办。并将希望留给了未来和后人。
九,梵蒂冈公会议
详尽地记录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事前的布局、各方立场,事中演绎、各方反映和搏弈,以及最后“教皇永无谬误说”出台的过程。这种资料的获得除了教廷秘书处外别无可能。
—各种搏弈:各种教会三百年来已到需要改革的地步;各方势力希望籍此申张自己的主张;地方教会希望更多自由而教廷希望更多独裁(宗教和世俗的权力)
—搏弈点集中在教皇的永无谬误说,一定程度上来自教皇身边的一个学派。
—公会议牵动各国皇室和宫廷,派员参加以防出现不利情势。
—会议中各种搏弈,主办方和与会方,攻防双方,通过议事程序,票选规则,时间安排(利用假期和公共事件),地点安排(使反对者人数缩减),人事安排,会前舆论,小道消息,利益交换。
—罗马要真正对付的只有两个,法国的现代自由主义和越山主义,德国的学术界。此后教廷的衰落也源于这两个。
十、阿克顿与克莱顿的通信
—治史者须有的对自由的认识和道德坚定得立场,否则研究历史无以为凭。
—克莱顿表达了典型的在遇到对专制权力人物作历史评价时,是否要做好人式中庸评价的困扰
十一,箴言,大美
《自由与权力》读后感(四):【转】冯克利:阿克顿—— 一个史家的信仰与智慧
在今日中国,拜官员腐败与政府反腐败之赐,没听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的人,也许已经不多;知道此言是出自阿克顿(1834—1902)之口的,大概也不乏其人。但是了解阿克顿其人其事的,却依然极不多见。1887年,他在给《英国历史评论》主编克莱顿的一封信中,写下这句令人过目不忘的至理名言,然而它仿佛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谚语,人们并不十分关心它的来源,这似乎是因为它的来源并不十分重要。
从某个角度看,确实如此。阿克顿晚年自称一生碌碌无为,他除了做过《剑桥近现代史》首任主编,为世人留下半部体例独特的史学著作外,本人未曾写下过什么黄钟大吕之作,因此我们今天看到他唯一的那本文集《自由与权力》(Lord Acton,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The World Publishing Co.,New York,1955),也不过是几篇演说、文稿和若干宗教文章杂凑而成的一册。
然而,如果一句话能像民间谚言那样世代流传,那也一定是因为它包含着某种智慧。阿克顿并非碰巧说出一句至理名言,他没有用系统的著述来陈述自己的思想,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系统的见解。汤因比曾言,阿克顿是时代精神的一个奇特牺牲品,工业社会不断逼使人们发掘史料,迷信劳动分工,使这位自由史的研究者手足无措,结果是“近代西方史学家中最伟大的头脑之一”,变成了一名才华虚掷的编辑。汤因比这些话自有他的道理,如果他拿自己的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与阿克顿相比,有如此惋惜之言当属难免。然而他称这个头脑全为劳动分工所害,却不太令人信服。阿克顿在史学上无所成就,以今天许多人的眼光看,其主因并非分工使他无所适从,而是他的“史以载道”,即西人所谓“read the faith into history(援经入史)”的倾向实在过于严重,这使他无法做到就史言史。
但是平心而论,阿克顿并非不知史实距道德说教相去甚远。他虽认为“满怀理想之士前仆后继,提醒人们小心僭主和暴君,不断宣扬神法高悬于邪恶的统治者之上”,多半会让我们想起儒家尤其是孟学;他虽称自由的启示包含在神的教诲之中,但是与科塞所说那些神游于形而上世界的“理念人”(the men of ideas)相反,他并不认为它的实现完全是来自先验的力量,而且取决于“进步文明的各种条件的汇合和共同作用”。他十分清楚,“金钱、土地或人数取得优势,从而破坏权力平衡的做法,充斥于全部历史之中。”他不时表现出对历史经验的明识,常使我们不能像有人所言,称他“在细节上全错了,其信仰却是正确的”。因此垢病其文为史以载道的做法,也多少失去了凭据。
阿克顿的史论中最可引起今人所注意之处,是他无论何时谈到的“权力”,并无特定的人称属性,而是泛指的。不管是信仰者的权力,王公贵族的权力,人民的权力,代表人民的、代表金钱的权力,或自称代表自然法、“进步力量”、正义与和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权力,总之不管什么权力,只要它以暴力为后盾(这是必然的),只要它失去制衡,成为“绝对的权力”,都会倾向于(“tend to”,译为“导致”,语势上未免太过强硬了一些)残暴、腐败和不义。
只有这样的权力观,才有可能为我们提供观察20世纪残暴政治的人都能从中汲取教益的识见。在他看来,政治生活中最可怕的局面,莫过于“道德与宗教不分,政治与道德不分;在宗教、道德、政治诸方面,只有一个立法者和一个权威”。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我们春秋笔法的本土史学中不得见的基本立场,即人间所能享有的无论宗教自由还是世俗自由,皆是权力平衡的产物。在论及古典时代的文明没落的原因时,他说:“个人、家庭、团体和属地(这些当然都是保持权力平衡所必需的社会要素)是如此卑俗,以至于统治权力可以把它们用于自己的目的。共同体支配着公民,一如主子支配着奴隶。由于忽视私人利益,忽视人民的道德生活及其进步,希腊和罗马都丧失了维系国家繁荣的关键因素。”他从这种现象中,读出了“侵害今日政治社会的种种谬误——共产主义,功利主义,对专制与权威、不法与自由的混淆”的源头。对于这些谬误的主义与混淆的观念,一百多年后的我们,肯定要比阿克顿有更切肤的感受。因此当我们看到阿克顿说,“只要某个单一的明确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无论该目标是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国家的安全或权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对一个抽象观念的支持,此时国家走向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不知是该佩服他的远见卓识,还是该为我们的愚妄而扼腕痛惜。
阿克顿对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多元化在制衡权力中的作用多有论述,他这方面的言论,当然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但往往被许多反自由主义者所忽视的另一面是,它也构成了现代知识传播或交往理论中的基本成份。今天人们谈论甚多的公共交往学说,许多论者不约而同地往批判理论或哈贝玛斯处追索,却没有看到自由主义有关共同体生活的大量言论,适足构成这种公共交往思想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个社会共同体形成的各项有利于个人自由的制度,既为我们提供了一道保护私人生活的屏障,更是一个有利于群聚与合作的架构,一个促进群体生活演变调适的对话环境,这是自由主义在。就此而言,阿克顿所秉持的自由主义传统,虽可名之为“个人主义的”,但它也是一种有关千千万的个人如何共处与合作的“群体之学”。像某些“批判理论”一样,自由主义把这种对话共同体的存在,视为一个让各种尚不知对错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在和平的环境下得以展开的过程,因为这是人们形成共同体的道德规范和公共目标所必需的社会学前提。在哲学认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大量有关“真理”如何产生(或无法产生)的言论,有心者不妨把它们与自由主义的共同体理论做一比较。譬如被国人忽视而近年来又因利奥塔等人宣扬而重新走红的美国哲学家皮尔士,他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便是他在“真理”问题上仍坚持客观主义立场,但也认为“真理”只能存在于一个在(科学)共同体的自由对话中逐渐形成或展开的无尽过程之中。再譬如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也把“正确”语用的形成,归因于一个语言群体习惯性交往的过程。其实,不惟真理和语言用法,尊约守信的习惯、权钱关系纳入法治、特权变为平权的过程,也莫不如此:没有参与的自由,没有对话,是不可能建立起取得共识的交往规则的(虽然它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理)。在政治哲学的领域,此类识见可以说随处可见。姑不论以鼓吹“开放社会”著称的卡尔·波普,不管是阿伦特的古典共和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者奥克肖特的“公民社团”理论,我们都可从中看到大量有关这种开放性共同体的思想。即或被许多人拿来与自由主义抗衡的哈贝马斯,不但明确认为市民阶层(“资产阶级”)是一个促发现代性的“对话伦理”的共同体,而且把它视为一支与专权和僵化体制相抗衡的最重要的力量——当然,没有哪个自由主义者会反对这样的思想。因此,就公共领域在对话中产生基于自由的共识的作用而言,西方自由主义和一些左翼思想流派的分歧,也许被人们做了过份的夸大。
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阿克顿有关教会和民族问题的文章,我们即可看到,他为解决教会和信众的分歧所提供的办法,其中即有坚定的保守主义信念,更包含着丰富的“对话交往理论”。对他而言,教会更像是一个对话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刻板严厉的“组织”,它对于信徒的价值,在于它为讨论和取得共识提供了一个场所。他说,“在教会中长期得到坚持和许可的神学观点及其他观点,是在时间的磨砺中获得真知灼见,并因教皇的默许而确立了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权威地位,因此如果不是出于轻率,便不能轻言放弃。”他在这里触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至关重要的政治学问题,即自由和权威的关系:教会虽是一个权威机构,但它真正的合法性并不来自它的制度化权力本身,而在于它和信徒的普遍信念相一致。只要它大体做到了这一点,激烈否定其权威不但不会带来变革,反而会引起分裂或反动,因为“硕果累累的胜利来自于天主教信众在知识、观念和信念上的逐渐演变”,它将迫使传统的代言人与新的环境相适应,最终克服抛弃成规的优柔寡断。因此最合理的改革方式应当是,在影响权威之前先影响它的信众,使其看法缓慢而平静地作用于教会,这样的改变“既不会产生任何破坏道德的冲突,也不会导致丧失体面的屈服”。但是这种体制中不言自明的另一面是,这一切都要以一个开放的“信仰共同体”为前提:教会不能禁止对“教令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审查,就让理智和良心上作出让步”;信众也不能“因为权威被滥用便抛弃权威”,因为“这两种做法同样都是罪过,一方是背叛了道德;另一方是背叛了信仰。将维护宗教真理的全部责任抛给教会戒律的执行者,并不能使良心得到解脱;干脆叛教也不能让良心释然。”
这种共同体哲学,也被阿克顿延伸到了他对当时正在崛出的民族主义的认识中。依他之见,他那个时代有三种最重要的“社会批判理论”,即“平等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所反对的,都是统治者因自私和滥用权力而造成的秩序。尤其是“得势前景最为看好的”民族主义,它“不仅是革命最强大的助手,而且是近三年来各种运动的真实本质”。虽然它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是“在它宣布已经进入的革命时代,它必定始终保持着力量。”伊赛亚·伯林曾在其名篇《民族主义》一文中断言没有哪个19世纪的思想家预见到民族主义在20世纪的重要影响。博学如伯林者竟未看到阿克顿的《论民族》一文,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但是不难想见,以一个天主教徒的普世情怀,阿克顿虽洞察到这股潮流的强大,却不可能对其表示完全认同。在他看来,民族主义故然有其提醒压迫的存在、提出改革方向的正面作用,却不能将它视为重建世俗社会的政治基础,因为单纯的民族主义“可以服务于截然对立的政治原则和各式各样的党派”。它把集体意志看得高于一切,把人们的各种利益全都纳入一个虚幻的统一体,要求其牺牲自己的习惯和义务。它也许会以民族自治、人民的自由和保护宗教为旗号,其实它却“只为自己说话”,“如果它无法和它们结合在一起,它为了获胜不惜让民族牺牲所有其他事业”。读到这里,我们也许更易于理解,为何在20世纪狭隘民族主义常常与好战黩武的军国主义形影不离。
不过这只是民族主义的一极。阿克顿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那种由启蒙运动培养出来的世界主义者,他不否定还存在着一种健康的民族感情。哈耶克在二战结束前夕一次题为《历史学家与欧洲未来》的演说中,曾特别建议把阿克顿的民族理论作为战后消除德国狭隘民族情绪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不但因为他要求史学家必须像阿克顿那样,不以价值中立为由回避道德判断,敢于说出“希特勒是坏人”,还因为在他看来,阿克顿持有一种十分开放的民族观。
他所肯定的另一种民族观,除了在反对专制宗主国或殖民政府这一点上与民族对抗的思想相同之外,其他没有任何共似之处。他认为民族利益虽然是决定国家形式的一种重要因素,但它并非至高无上。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天然地具有多彩多姿而非千人一面、和谐而非大一统的潜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多民族的共存还可构成对国家权力膨胀的最终限制,有可能被民族国家牺牲的私人权利,有机会因民族差异而受到保护。它以“分别存在的”乡土感情(我想这里有必要指出,这才是“patriotism——爱国主义”的本来含义),影响和牵制着统治者的行动。因此阿克顿也把一个主权国家内若干民族的共存比作教会的独立,认为它们可以发挥维护权力平衡的相同作用,“避免出现在单一权威的笼罩下四处蔓延的奴役状态”。他乐观地(也许是过于乐观了)认为,“同一国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对自由的验证。”由此他也否定了约翰·穆勒所宣扬过的一种近代自由主义的主流学说:“政府边界与民族边界相一致,一般而言是自由制度的必要条件”。
当然,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也可以印证现代知识理论中的一条重要原理,即差异是人类合作从而促进知识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正如他所说,“不同民族结合在一国之内,就像人们结合在一个社会中一样,是文明生活的必要条件。生活在政治联合体中较次的种族,可得到智力上更优秀的种族的提高。力竭而衰的种族通过和更年轻的生命交往而得以复兴。在一个更强大、更少腐败的民族的纪律之下,由于专制主义败坏道德的影响或民主制度破坏社会整合的作用而失去组织要素和统治能力的民族,能够得到恢复并重新受到教育。”这些言论中虽然些许透露出盛行于他那个时代的种族主义色彩,如果我们用今日的“民族平等”或“优势互补”之类说法加以纠正,我想阿克顿是不会反对的,因为在他的笔下,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国家,并不具有单一种族文化的神秘性,而是应当成为一个“促进融合的大熔炉”,它所逐渐形成的自由制度,可以使习俗、活力、创造性上各有所长的不同群体,相互传播他们的优点,扩大人们观察生活的视野。民族差别处理不当固然会导致严重冲突,但是只要待之恰当的自治,它也能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好处,可以使每个人都能“在邻居中找到自己的利益。……使文明和宗教的利益由此得到促进。”
虽有这些在当代公共哲学中仍充满活力的思想,但是在今人看来,阿克顿是不是个很老派的人物?其实不唯我们,即使在一百多年前他的同代人眼里,也难免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他的贵族身份,他坚持让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与自由主义并行不悖的努力,他的普世主义情怀和保守立场,在在与此后百多年来精神生活的大气候格格不入。当年哈耶克创立“朝圣山学会”之初,曾建议用阿克顿和托克维尔的名字来为学会命名,就几乎让到会的美国人拂袖而去。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不乐于把阿克顿引为同道,并非没有他们的道理。大概他们对阿克顿曾为美国宪政做过的出色辩护并不领情,倒是忘不了他不但有美国文化所讨厌的贵族身份,而且还给南方坚信联邦制的蓄奴分子说过好话——这也是一个从正确的理由推导出来的错误结论,因为他总是固执地认为,在维护自由宪政上,权力的平衡比权利的平等更重要。
其实,从阿克顿经常受人冷落的思想遭际中,我们看到的还是政治世界为价值排序这个几乎无终极解的难题。一时一地的问题,决定着一个社会在选择价值上的优先顺序。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民族独立,公共精神,私人空间等等,如果撇开时间因素不谈,无一不是极可取的价值,但它们又是只能在历史中,在具体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才能被人类选择,从而得到真实生命形态的价值。阿克顿所做出的选择,是自由和信仰无条件地高于其他价值,并且认为能够保证其安全的,只有建立在权力制衡原则上的宪政制度。我们可以把这看作只是他本人的信念,甚至是一个历史学家一厢情愿的反历史的偏见,不少人也会因此而批评他在平等、民主和人权方面的思想缺失。可是我们也没有理由忽视他教给我们的智慧:无论什么样的统治,只要存在不受限制的权力,都有走向腐败的倾向。他为此提供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绝对权力有可能“败坏良知,麻木心灵,使它失去对环境的理解力”。和阿克顿给人留下的史以载道的印象相反,他这些反复强调权力制衡的观点,说到底并非单纯来自他的信仰或理念,而是一种以信仰为根基的经验主义,或曰史家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