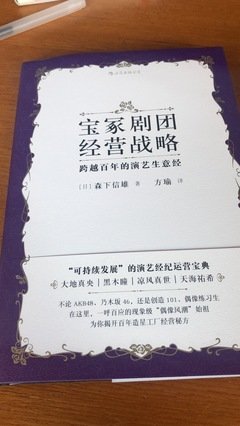
《钟形罩》是一本由(美国)西尔维娅・普拉斯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250图书,本书定价:14.8,页数:1900-01-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钟形罩》精选点评:
●我通过这里看你们 其实在罩中的不是我
●I am. I am. I am.
●小说结尾,主人公埃丝特即将离开病院走向未知生活,然而作者本人却在小说发表三周后选择自杀。 《钟形罩》的内容,以及小说本身的出版都有一种仪式感,普拉斯似乎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自我救赎或者自我证明——写出《钟形罩》,以完成她把自己从真正的钟形罩中逃离出来,告别过去然后面向未来(但结局却不如人意) “我怎么知道有一天——在学院,或者欧洲,某个地方,任何地方——那个钟形罩,还有它那种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扭曲视象,不会再度降临呢?”——普拉斯最终还是没能离开那令人窒息的透明钟形罩。
●The floor seemed wonderfully solid. It was comforting to know I had fallen and could fall no farther.
●曾一度很爱这本书
●真好,就像自己在说话。于我们而言,这个世界永远无法言归于好,永远是个噩梦。
●结构稍散,但如钟形罩压迫的气氛,可以确确实实感受到
●感觉后面她得精神病那段更给力一点哦,哦还有那个骗化学老师那段也好,好熟悉(那种装孙子的好学生。。。很多人都这么干过吧。。。)不过就在偶以为她会跟诺兰医生会有神马JQ的时候,戛然而止,好失落。。。(叫你带着一颗腐心去看。。。)总之,推荐!
●La Cloche de détresse
●普拉斯唯一小说。
《钟形罩》读后感(一):还活着
要记得小说字里行间的欢快和生动
就像她说话时把一股酒气喷在脸上
要记得崩溃前窒息时的煎熬和痛苦
就像我现在还用窗帘把你重重勒住
要记得对自己无所作为的深恶痛亟
就像这无力感将一辈子把我囚禁
要记得对死亡的向往和精打细算
就像它时刻在对你微笑跳一支诱人的舞蹈
要记得生活里的失意文字上的野心
不要在放纵里沉迷于时间的流去
要记得母亲的叹息阳光下的久坐
以免让平凡的时刻蒙蔽了你的眼睛
要记得黑暗里那个深深的坑洞
要记得游泳时突然不怀好意的停顿
要记得面对未来迷梦般绝望的时刻
因为此刻还活着
《钟形罩》读后感(二):心的躲避
说实话,刚开始看《钟形罩》的时候真的没懂。我之前听说过这本书,而且作者很吸引我的,她最后还是自杀的,我觉得这样能看透人生的作者写的东西肯定会有深度的。
埃斯特,即书的主人翁,从刚开始就显得有点不入流的。她对世界上所有事都感到不满,,这应该是她很多年在心里的积蓄吧。她的这种心理很值得细究,她或许在年轻的时候就收到过很多的伤害,所以厌世,就像人格分裂的病人大都是因为小时候受过伤害。
紧接着就说到了她的恋爱。她的朋友多琳,永远都是那么的吸引人,跟她在一起,埃斯特永远都不会被注意的,第一个莱尼,埃斯特其实第一眼就看中他了,可他眼中只有多琳。所以,“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关于多琳的决定。我下定决心,对多琳我只旁听,听她说话,但在内心深处我将不再跟她有任何瓜葛”,这是埃斯特在感情受挫后的决定。她的决定就是自己默默接受,从内心排斥别人,不会有别的方法。后来巴迪出现了,她符合了埃斯特所有的条件,他们在一起很好,但是很难迈出一步,不知道埃斯特为什么从心里不信任他,特别是后来她知道了巴迪跟她恋爱的时候还和一个妓女鬼混,这完全事埃斯特接受不了的,或许她期待的爱情即使“柏拉图式的恋爱”,所以知道最后她也没接受巴迪。书中有一句话“我是我自己的女人了”,是埃斯特在做完子宫帽检查后说的,这里好像也很明显的说出来了,她根本不期待有爱情,她后来把自己的贞操给了不怎么了解的欧文,她完全就像在完成一项任务。还有一个人,就是琼,她看其俩应该是对埃斯特有同性恋倾向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琼知道埃斯特和男人发生关系后选择了自杀。她不想她纯洁的恋爱有任何一丝的污点。
埃斯特的心理是模糊不清的,她看上去听清醒的,而且在精神病院也很配合医生的。
她是女性心里扭曲的代表,不能自我修复,只能借助整个社会的帮助。
《钟形罩》读后感(三):不谈生平,不谈自传
有很多书被赋予一种令人跳脚的评价,自传性质的,所以作者往往不认可,明明是化装舞会,你何必大声嚷嚷谁是谁呢,就当成海盗和女王舞会不行么?plath同学就更别提了,哪怕没看过她写的半个字,也耳熟能详她的桂冠诗人丈夫以及自杀时留下的两个孩子,前者太“痴情”后者太社会话题。大家伸长脖子看着才子佳人配对的成形,破裂,最后升华,早已经忘记故事里面是两个人类,而不是美人鱼和王子。前段时间看人评价纳兰词,写得最好就是悼妻的几首,可是即便他终身未能忘情也不影响莺莺燕燕的生活,本来么,文人的感情不也就是鳄鱼的眼泪,千方百计证明休斯背叛和矢志不渝都是可笑的事情。
单看书。plath说写钟型罩是想宣泄掉从前的种种,重新开始,我完全相信她。但是事情就是这样,有人死前去自己走过的地方收脚印,难道当真就了无牵挂了么,结果往往是越发有凭有据得舍不得了。埃斯特的女朋友矫揉造作,可是人人都喜欢她;她的男朋友乏味可笑低级庸俗,她却连分手也想用最温柔的方式;她的母亲爱她却不了解她,只会哭和按照别人的意见对待她;她是全优学生,没人知道其实她什么都不会;生活是道难题摆在面前,别人却质疑她怎么连跨过条小水沟的勇气都没有。她明明知道这些,却还是非不清楚对错,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世界都是错的只有自己是对的,除了疯子,所以她和屈原都成了疯子,一个被电击一个跳河。
最后诺兰大夫出现了。好吧好吧,此时此地出现一个女大夫实在让我怀疑些什么。尤其是某些句子。
大夫说,今天我有个好消息。埃斯特并不相信自己还会觉得什么好。大夫说,这个星期你都不会有访客了。大家一起看着埃斯特母亲送来的红玫瑰。(这个真是大哭大笑的情节)
大夫问,男人和女人最大区别是什么。温柔。
精神科的医生总是游离在情人边缘的。
不过我无意揣测作者本人,只说埃斯特,最后这样被拯救勉强说得通。问题在于,即使有爱情有知己有温柔,那个钟型罩还是存在着,还是必须吞下呼出的毒气生存,成为那个畸形的婴儿。plath没有写下去,怀疑她怎么写得下去,所有雄心勃勃的计划只要一根针就能戳破。所以这样的结局也算结局了,像好莱坞老电影里常有的,女人走到悬崖边上,下一个镜头是冷风呼呼吹着空无一人的悬崖。这样就可以了,我们需要的原本不是玉娇龙般优美的身段,我们要的只是这个结果,空无一人。
《钟形罩》读后感(四):想到你就要毁灭
“对于困在钟形罩里的人,那个大脑空白生长停止的人,这世界本身无疑是一场噩梦。“
普拉斯的处境似我。二十三岁,除了文学略通以外缺乏任何基本的生存能力,任何一次退稿都造成致命的打击,缺乏交流,诸事不顺,没有勇气一次性告别虚假的生活。爱情也渐渐熄灭,电疗除了带来噩梦般的经历之外与事无补,自己像个傻子然而还将继续傻下去。
埃斯特的经历并无喜感,与麦田捕手里的霍尔顿迥异,也并非所谓女权主义的呼喊,其实全书就一个主题,满纸满页地映入眼帘投射心中:过不下去了。所谓的前途完全唬不住人:嫁个教授,即便文学上琴瑟合鸣,仍要带着发卷为他准备一日三餐,哄睡哭闹的孩子,身心俱累之时还要担心明日家用入仍然不敷出。
何曾想到过写诗?电和暖气在伦敦旧居中经常未经通知就被停掉,鼻窦炎周期性发作,书评并不积极,母亲因小说暴露私事太多为由与之交恶,并一再阻挠美国版的发行,心理疗程卷土重来,丈夫休斯分居后音讯皆无,她一个人在厨房里颤抖着喝下冰凉的水,鼻塞,发抖,与世隔绝,如置一钟形罩内。
埃思特又高又瘦,对脂粉气倍感厌倦;身旁女友偏偏个个顾盼神飞,大放光彩。谁会因为会写诗吸引男性呢?在舞会上她总是最后被随便指派给一个丑陋而又怪异的男人。她遇人不淑,将钱花在去往奇怪的地点上,她爹的坟墓,一座海岛上的监狱。离开纽约前一天她把所有衣饰扔下楼去,看它们在夜空中飞散,让一切见鬼去,如果自己可以先见鬼的话。
回家以后埃斯特开始失眠烦躁,写作训练班拒绝了她,学校的课程已被他人先行选去,她想写小说,可是毫无猎奇经验,只有无穷的烦恼和21天的毫无睡眠。
“我看到日日年年如同一长串白色的箱子向前排列,在箱子与箱子之间横隔着睡眠,仿佛黑色的阴影一般。只是对我来说,那将箱子与箱子分割开来的长长的阴影突然啪地一声绷断了,一个又一个白天在我面前发出刺眼的白光,就像一条白色的,宽广的,无限荒凉的大道。”她不洗衣服和头发,今天洗了明天还得再洗,重复的生活愚蠢极了,为什么没人制止?
“我想什么事都只干一次,干完就拉倒。”
是什么挥之不去,始终要我们做个交待才肯罢休?琼自杀了,她的病情时好时坏,最终死在医院附近的一个湖边。医生完全不可信任,治疗方法全凭心情,病人是被摆布的玩偶,电疗椅在等待他们。
结局早就注定了。六月,纽约,下雪。
心不从所愿。
《钟形罩》读后感(五):从烂漫到疯癫:埃斯特的人间之旅
文/吴情
一九六三年一月,署名作者维多利亚·卢卡斯的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在美国出版,然而,这本书并没有给作者本人带来预想中的成功和经济上的帮助。之后经学者研究发现,这部作品实则属于美国当代著名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英国著名诗人特德·休斯的妻子。然而,一个月后,这位年仅三十一岁的才女,便在一个清晨抛下两个幼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普拉斯何以如此?这一问题只怕永远也无法找到答案。但时过境迁,再来看《钟形罩》这部带有自传性色彩的小说,或许多少能够窥作者心中一隅:安静中裹挟洪流,希望中满是绝望。
一九五三年,来自波士顿一所著名大学的大二女生埃斯特·格林伍德因为参加某次时装杂志征文比赛获奖,受邀前来纽约一家杂志社实习。学习之余,埃斯特见识了纽约的灯红酒绿和歌舞升平。纽约的一切对她而言,既魅力无限,又似乎饱含了拒绝。实习期结束后,埃斯特回到故乡小镇,可那里的忧郁沉闷使她难以忍受,精神逐渐趋于崩溃。在几次自杀未遂后,埃斯特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心理分析和电击治疗,在他人的所谓帮助下重建个人的生活信念。
生活在小镇的埃斯特为人独立敏感,对周遭的现实有着极强的感受力。纽约之行,在她原本近乎单调乏味的现实世界和人生方向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以及通向未来人生的多重可能性。在杂志社实习期间,埃斯特结识了能干的女性杰·西和多琳,前者年纪虽大,但充满自信,才能卓越,但在埃斯特眼里,她缺乏了女性作为女性的大半魅力,她不善装扮,衣着过时,是可怕的未来;后者聪明果敢,往往三言两语便能俘获异性,是难以学习和效仿的高调现时。埃斯特在多琳种种行为的撺掇下,竭力“送出”自己的“初夜”,但却阴错阳差地屡试屡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埃斯特的前男友巴迪·威拉德,时常(有意无意地)夸耀自己的性能力。
女性和男性,在性权利上已然是不平等。男性偏好保留贞洁的女性,自己却随意到处留情,毫无正当理由的双重标准之下,女性应当何为?埃斯特的行为看似荒唐,却是一种另类尝试,莫名的喜感背后是现实的无奈和辛酸。从性权利入手,埃斯特思考女性作为女性的独特属性,以及个体女性的的未来。大学时主修英语文学的她,热爱诗歌,喜欢《芬尼根的守灵夜》,重视精神远胜于物质享受。然而,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女性的生活几乎完全被家庭捆绑:数不清的家务劳动,服务讨好辛劳一天的丈夫,教育子女奋发上进。女性的主体性究竟何在?日趋保守的美国社会,重视工作的女性,尤其是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主要寄托在工作岗位上的新型女性,在舆论中逐渐被否定。相夫教子,似乎成了女性全部意义的实现途径。尴尬的是,男性话语本来无据,很多女性却对此趋之若鹜,奉为圭臬。
埃斯特与前男友巴迪热恋期间,两个人曾经一道参观实验室里的钟形罩,里面装着经过防腐处理的死婴尸体。此后,埃斯特眼前常常浮现出当时的场景,“钟形罩”因而也成为小说中的重要意象。没有空气进入的钟形罩瓶,无疑是一个独立于世的空间,它象征着窒息与死亡;另外,现实于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女性而言,何尝不是一个更大的、也更令人绝望的钟形罩瓶?
在对婚姻爱情的浪漫想象与残酷功利的现实的鸿沟中,埃斯特的精神世界走向瓦解和崩溃,直至被目为疯癫。此后,精神病院的精神分析和电击疗法,于她而言近乎熟稔。谎言与背叛,阴谋与爱情,在小小的四方空间内轮番上演。在埃斯特看来,人为设立精神疾病的标准很是荒谬,精神病院的存在基础是,只有你被诊断为疯癫,其他所谓正常人才能心安理得地继续自己的绝望生活而且拒绝醒来,继续自我欺骗、自我安慰。真实的情况呢,难道并非如此?
如要转载,【豆邮】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