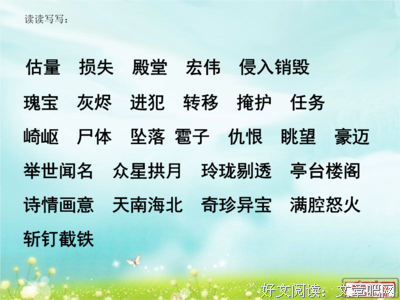
《校礼堂文集》是一本由(清)凌廷堪 / 王文锦点校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3.00元,页数:3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校礼堂文集》精选点评:
●腦子不是很夠用
●文辞华美
●越来越觉得这是个礼乐崩坏的时代了
●2007年脚伤了,躺在床上开始看的,现在5年过去了,我书架上的书还没有读完,郁闷。礼是一部分,其他的东西也好的很。裛露而婉转,向风而徘徊,就是他说的,感觉就是我一生的写照。记忆乱了,应该是2006年看的,还让谷老师把这写成了条幅,挂着呢。
●一个误幻化为骈文男的理工男,具有理工男的各种牯点。
●看了复礼
●被淩廷堪圈粉
●看不下去啊,到处都在硬骈,看的心累,没有那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啊……
《校礼堂文集》读后感(一):遥追凌廷堪,心折张寿安
我一向以为,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比较真切的理解,读民国前的书往往比读今人的书来得相宜。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正统、主流有着直接的体认,不需要像今人那样对其作现代化的阐释,也不需要使其屈就于西学分科的规范。
凌廷堪这个人,现在一般人知道的不会太多,但在乾嘉时期,却是声誉卓著的经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研究仪礼乐律方面尤有成就,对礼不仅下了很大的考据功夫,还有自己独特的阐发,其学术成就颇受时贤推重。所以,尽管现在的人已经很少提到他,我还是买了他的这本文集。
(本人于2001年6月间购得此书,未暇细读。不意同年11月间河北教育出版社就出版了台湾中研院学者张寿安的专著《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心折之余,亦兴井蛙之叹。)
《校礼堂文集》读后感(二):書校禮堂文集後
夜讀淩廷堪校禮堂文集,因念淩氏禮學,實多與荀子禮論相發明者。惟凌氏禮學大家,其大指蓋在抗衡宋人理學也。
淩氏文集之中,以復禮一篇,最明大指。而荀卿頌亦尊禮之言也。其好惡、慎獨格物、論語禮後諸說,處處尊漢抑宋,而特以禮學為武庫也。然其禮學特能尊古訓,而以荀卿禮論為主,若禮之起始,分等諸端,皆與荀卿相合,獨性善性惡一條不同,無乃不宋之能拒乎。
夫宋儒之抑荀,不過以性惡,乾嘉之間,漢學復興,宋儒性命之論,雖云正統,然好古之道日隆,疑宋之風日熾,荀學因之發揚,良有以也。觀此興衰之變,不亦宜乎。然則讀淩氏書者,當知淩氏之所攻訐,非濂洛關閩也,而濂洛關閩之末流也。
辨學一篇,洵足深味。至如復性三篇,意味迥深。上篇言性情為禮之原,而聖人作禮,以節人情。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禮猶規矩繩墨,所以復性之善者也。中篇言仁義禮道德之本義,道必緣禮以求之。下篇言聖人之道本平易,而宋儒援釋氏入儒學,究非本旨所關也。
《校礼堂文集》读后感(三):越读越惊喜
越读越惊喜。思想方面主张礼以节心,不违仁,复其性。继承戴震由情以达性、由学复其善的观点,然戴东原侧重于学以裁断,凌廷堪偏向于学以知礼。不过言「礼之外无所谓学也」就失之武断了。谈及学术风潮变迁,很有卓识,谓学术有盛衰废兴,「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之,千百庸众忿而争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众坐而废之,一二豪杰守而待之。故肆力于未盛之前,则为矫枉之术;攘臂于既兴之后,遂为末流之失。」
极有眼光,谓李斗《扬州画舫录》体例不高不卑,将为必传之作。又言钱大昕体大思精,识高学粹,集通儒之成,史学惟钱辛楣用功最深。
很讲情义,不忘业师知遇之恩,恒念良友相依之谊。章酌亭殁后,觅其遗稿不成而深悼,后校录酌亭手稿《浣香吟草》并为之作序,多年后,向阮元、王昶出示,欲使友人遗文得传。又,特为墓志铭,追忆二人穷愁互答、贫贱相依之时,深衷哀婉。「黄肠七寸,邈若山河;白首三生,惟通梦寐。」
《校礼堂文集》读后感(四):补篇
凌仲子生前所订文集《初稿》,乃抄本两大册及散叶。张其锦徒步宣歙淮海间编得《校礼堂文集》三十六卷,《诗集》十四卷《札记》六卷,又《晋泰始笛律匡谬》一卷。先是受阮元照顾,刻成《文集》先行。辗转十八年,始获金主合凌子生前所订刻成《校礼堂全集》。张其锦遂著《年谱》附于《全集》之末,以翼先师之文。今《札记》亡。据《年谱》略补《文集》于下。显之笔削。
辞鲁子山札 (《年谱》嘉庆十一年)
前此,教授知府接见之仪,有国家典例在,今则忝敬亭讲席,与阁下则宾主矣。在某卑贱,不能以礼自处,固无足惜。若乃仆仆于阁下之门,是并不能以礼处阁下矣。是以今日之招,虽郑堂、稚存旧雨咸集,竟不敢奉陪,非惟自爱其鼎,亦两全之道也。
与毕子廉书 (《年谱》嘉庆十二年)
淳安方君朴山,吾乡素奉为山斗者,其《文集》中,诋排宋儒不遗余力。盖朴山为西河弟子,故坚守师说如此,乃其主讲紫阳,从未一言道及,其卑视吾乡以为不足与语者何如?然则弟之厚待吾乡,反遭骇怪何也?朴山之薄言吾乡至此,而吾乡尚有依草附木,以借其渊源为荣者,一何可笑?又其所作《盍簪录序》等文,皆不入集,而吾乡凡自云其门下士者,《集》中亦未齿及姓名,其以吾乡人士为逆旅之藩溷可知,朴山《文集》具在,可覆按也。今之奉朴山为山斗者,其《文集》全未寓目,而徒诧吾言,是亦不可以已乎。然同志如足下,幸有数人,则吾道不孤矣。
此札,凡吾乡相好者,祈与之阅,天资高者,可以发其聪明,次者,亦可以破其沉滞,不足语者,不必也。语虽憨而心则诚,幸转致诸同学共谅之。
(今案,方氏编刻有《新安三子课艺》,并为之序,三子即:汪梧凤、戴震、郑牧。此《序》不入其子甲戌刻本《虚斋文集》。)
邗江三百吟序 (《年谱》无,据文,嘉庆十三年)
廷堪获交兰痴先生逾二十年矣,先生为阮伯元中丞舅氏又其少时受业师也。乾隆甲辰岁廷堪与中丞共学,即知有先生,其后入京师,识之于任幼植侍御所,先生不以为鄙,而下交焉。先生人品端谨学术醇粹,望而知为有道之士。中丞少时受业师,廷堪知者,一为李晴山进士,一为乔樗友茂才,其一则先生也。嘉庆十三年春三月,中丞再抚浙江招廷堪作西湖之游,冬初晤先生于节署,鬓发已苍然矣。语次,出所著《邗江三百吟》见示,其书以诗为经而纬之以山川人物,昔左太冲赋《三都》,考其耆旧,辨其物产,读者遂不敢以玉卮无当视之,先生之志亦犹是也。时将以此书授梓于是,僭识数语于简侧,非敢以为序也。 歙凌廷堪次仲拜书。
与阮抚军书(《年谱》嘉庆十四年,本年夏卒)
某向谓圣人所谓学,即指礼而言,若无显证,后读《论语》而得之,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四者度不云学而无礼之弊。又曰:“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 六者亦不云好礼不好学之弊。又“勇而无礼”与“好勇不好学”同谓之乱,“直而无礼”与“好直不好学”同谓之绞,其义甚明,何疑乎?此人所共见之书,惜予之而不能读也。由此观之,鄙说不戾于孔子可知矣。
严厚民上舍杰,赠宋张玉田《词源》二卷,取而读之,与愚昔所著《燕乐考原》,若符节之不爽。其书世无传本,心窃自喜,此皆独抒心得,非剿说雷同者可比。然则仆与阁下定交,尚非贸然互相标榜尊己卑人之恶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