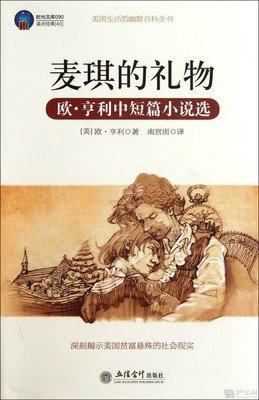
《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是一本由阿拉·古兹利米安著作,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元,页数:11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精选点评:
●有意思的小书。瓦格纳的部分跳过了,现在还没到时候,强啃没意思,听几年音乐,看几年理论回过头再看
●
●好高级啊。
●近期最佳
●对话,能给人以最迅速的启迪,尤其是本书这样艺术和社会的碰撞!
●很有启发性的书
●最初读这本书的时候,还不认识萨义德,只是觉得他在音乐上非常有见解,后来才知道这是位了不得的人物。两位大师对于音乐的探讨让人眼前一亮
●贝多芬先写“渐强”后写“立即弱”,这意味着“立即弱”之前最后的音符应该是“渐强”中最响的那个音符。而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这很难做到,很难控制声音,为了创造“立即弱”的效果,什么都是困难的。容易的做法是把“渐强”演奏到某一点上,然后就停止,你就能很舒服地进入到“立即弱”的部分。但是悬崖的整体效果就失去了。这就是我要说的:音乐演奏上的勇气,不在于你演奏什么,在哪里演奏。这种勇气,我觉得是解决所有人类问题都需要的一种勇气。只有那些很平庸的东西才能够得到一致的反馈。
●从两个角度共同解释一个流传最广、最感性的语言。你会发现你希望找到的一切道理,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
●读完对巴伦博伊姆的映像不是一般的好
《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读后感(一):灵魂最有力的表现手法之
♏: 罗曼·罗兰将音乐看作是“灵魂最有力的表现手法之一。”
未打开这本书之前,自己对于音乐乐评的印象只是简单地停留在感官状态的表述中,然而最后才了解到音乐的广泛纬度。其与社会性、政治性、宗教归属、哲学、教育等多方面地共通与相异。
此前的认知,仅仅是通过一首歌、一谱曲获得愉悦或悲伤情感的宣泄与赞同。然而,通过巴博伦伊姆与萨义德的对话,才体认到音乐艺术的深度表现力。
最好的音乐是打破寂静的艺术。贝多芬《英雄》的壮阔即是对岑寂的最有力对抗。但什么是真实,什么又是幻象。音乐不是停留在白纸上的黑色音符。只有在被演奏的那一刻才是全然的音乐。
还是有很多的与政治、哲学互相渲染的方面,仍不能完全读懂。注定是一本在今后吃掉更多的古典、交响、戏剧后重读的一本书。
2015.09.04
《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读后感(二):事物是用一定方式发声的
音乐不是与各种意图打交道,而是与音响打交道。 太多人关注对自己身份的肯定,关注自己的根,自己文化的价值,以及自己的归属感,很少有人把自我向外界括展,从而具有更宽阔的视野。 从无序到有序,从悲凄到喜悦。起无无声,止于无声。为了挑战自然规律,你必须懂得规律,懂得事物是用一定方式发声的,并且懂得为什么。 《奥德赛》——他是一个好奇的人,他的离家不是简单的离家,他离家是为了发现能够吸引他的东西。 长音符含有一种对永恒的渴求,对流动生活的反抗。 怎样让自己与第一个声音相结合,并期望自己一直伴随着它,直至结束。 不断学习和创造是相互矛盾的。 如果你想诉说一些很个人的东西,那一定是有人欣赏有人唾弃,争议是必定的。 一种很肤浅的对音乐的诠释:也就是没有任何冒险,不要陷入任何深渊,不用走任何极端的黄金之路。 这会影响到演奏的速度,因为如果内容贫乏,那么只能加强速度。 操纵与让步之间存在的必要关系,在我看来是所有做音乐的基础。其实也是人类存在的基础。 我们应该记得音乐的体验,做音乐的行为,就是要使声音进入一种连续、互相依存的状态。速度是与内容,音量相联系的。 音乐是一种社会哲学,它之所以变得如此难懂和难以接近,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社会的僵化。
真声与假声的转换,大调与小调的转换。还有属音和弦在主音上得到释放。 德彪西的很弱是无形的,而贝多芬的则是在表达和声音上有着外在的核心。他在寻找真正的贝多芬,而这个贝多芬是其他人无法了解的。
你能体会到很多关于人性的东西,你会理解到很多东西都不是你第一次见到的那个样子。
《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读后感(三):《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之读书札记
《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之读书札记
缘起
注定是顺利而愉快的春游。虽然景色凡善可陈,但还是一路欢笑。为了减轻背负了本子后书包的分量,出门前随手取了本Ghost力荐的《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巴伦博伊姆与萨义德谈话录》。
思考因为车上各类对话或其它屡屡被打断。于是使用Keyword办法。
Keyword I
巴伦博伊姆:我回家的感觉是一种动态的感受,一切都存在。音乐也是一种动态。当我拥有流动的感觉时,我最高兴。
II
巴伦博伊姆说:巴赫的音乐,在很多地方,都是为了赞颂上帝,因此,他使用了史诗般的形式。赋格曲已经成为音乐殿堂里的真正组成部分,是靠一块砖一块砖垒积起来,一层垒上一层,完全是为了赞颂上帝或者教会。
两天里,我把这张小提琴协奏曲听了无数遍,在颠簸的车上或者寂静无声的凌晨。巴伦博伊姆有些混淆了我关于音乐与音符的概念。但他同样承认“永恒”。(他说道:每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针对它创作的时代;一方面是向着永恒。……超越时间的意思就是,不仅不受那个时代的限制,而且永远具有现实性。)
演奏者在演奏作曲家作品的时候,究竟应该以哪个方面为重点呢?是创作的时代背景还是作品“永恒”的特质?“兼而有之”,更像一篇音乐评论里的常用词。
巴伦博伊姆对“古乐器运动”的评价似乎有欠偏颇--“向后看的做法”。而其所说的“永恒”是否也可以有两个部分组成,即历史性和现实性呢?这里的“历史性”并非纯粹指那个创作的时代,而是一种“历史语境”,目的是为了更加清晰、公正地表达“永恒”的精神。
任何介质、形式,都是在“现代人”这个载体上实现的。使用什么样的乐器,采用什么样的曲谱。羊皮纸,或者花体字,所有并排的音符,终究都要通过“现代人”的大脑反映出来,这个过滤的过程,对于一般交响乐团和“本真派”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听过电子版巴赫赋格的人都知道,无论曲调、速度如何变换,巴赫还是巴赫。它不是小溪,是永恒的大海。
附Q评论:
quot;每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针对它创作的时代;一方面是向着永恒。……超越时间的意思就是,不仅不受那个时代的限制,而且永远具有现实性。"这是非常对的。即便是本真派演奏也必然会体现这点,而且本真演奏不仅“重现”过去时代的精神,本身更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特征的体现。从某个角度说,本真演奏比个性演奏更富有我们时代的现实性。
无论本真演奏还是个性演奏,都是对音乐真谛的探索。而所谓探索艺术的真谛事实上是在创造艺术的真谛,艺术永恒不在于某些艺术品恒久不变的价值洞穿亘古,而在于它们的生命力一直被新的时代以各种方式重新唤起,古代的精神与当代的精神间形成对话,远古的声音在当代的心灵中撞出回声。
III
很意外地在田的房间里看到这本书。《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巴伦博伊姆与萨义德访谈录》的原版即《Parallels and Paradoxes -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Edward W. Said / Daniel Barenboim)这本刚读完的书,印象深刻非常。薄薄一本,读了近3周。每每在颠簸的汽车上玩味书中精彩的对话,都会突发傻笑。
对于田得意地给我看首页Barenboim的亲笔签名,报以淡淡一笑。此老头的钢琴演奏或者指挥,都不喜欢。用Mercurio的话来说,便是“虽然我很不喜欢巴伦波伊姆的指挥,但是这样行动着的人,感觉很服之.”。(见豆瓣上田对该书的评论:西东席明纳:萨义德与巴伦波伊姆)
田反复强调懂得7国语言的barenboim先生是位大学者。这点,在书里已一再领教。能对音乐进行如此深刻探讨、分析,Barenboim先生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人。(当然这和本人对音乐评论及音乐家关心太少有关)
先前一篇札记有说到,这本书引发我的思考更多的是在“社会”上,而非“音乐”。流动,作为音乐的一种特质,充满着“不确定性”、“偶发性”,挑战传统的“定义”。书里讨论的“音乐”不再是狭义的“音乐”,不是人们惯常聆听的“音乐”。作为特定“社会背景”下的“音乐”,它更像一种折射社会的现象,或者是被用来探讨社会的对象。
我害怕把音乐“玄虚化”,也敬畏把音乐“哲学化”。于是我说,我佩服巴先生的“你必须有勇气接受发展过程中各种元素的流动。每一次发展,每一次分离,都意味着把某些东西甩下。”同样也折服Said先生针锋相对的回应:“我认为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接受。……比如贝多芬,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他有一种反抗。我认为不是一切都可以化解的。”
quot;但你从一种生活进入另一种生活,这也是生活的这一部分。”(巴语)
现实的发生有其不可逆转性。我们化解的是否应该说,并不是现实,而是现实的意义。我们所摒弃的亦不是现实,而是现实的意义?
音乐会因其不可重复性,为人们所追崇。而真正不可重复的是“音乐”本身。唱片转了又转,谁能说前一刻和后一刻是完全相同的体验。作为载体的“人”本身是流动的,这便已决定了“音乐”的“多变”。
然而,思考和演奏,最终将被证明是两码事。思考的好处是否能在“音乐体验”中获得运用,或者帮助提高?我感性的以为,音乐在实践中,必定会偏离理性的轨道,有着自身超乎寻常的自我意志。
(to be continued)
《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读后感(四):音乐中的探索者
2002年3月6日,由于以色列军队拒绝担保其人身安全,钢琴家暨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依姆不得不宣布取消计划在巴勒斯坦的拉马拉举行的音乐会,举世为之震惊。但是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感到奇怪,因为以色列公民早已被禁止进入巴勒斯坦控制区,任何原因都不例外。同年,一本巴伦博依姆和萨义德的音乐对话录诞生,题为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相应与相抵: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时隔三年,2005年的8月21日,拉马拉终于迎来这次迟到的音乐会,这也是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第一次举行巴-以跨文化盛事。同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巴伦博依姆、萨义德谈话录》的中文译本。对于很多人来说,音乐是高雅生活的佐料,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音乐能够触动人类的灵魂,消除隔膜和罪恶。
一
巴伦博依姆和萨义德一样,都有着复杂的文化背景,这迫使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认同要比别人思考得更多、更深。巴伦博依姆的先辈是俄国犹太人,后移民至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巴伦博依姆出生后又随父母移居刚刚建国的以色列。而萨义德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家庭,却信仰基督教,他的父亲甚至为美国人打过仗;后来萨义德成了一名东方学专家,他的后殖民批评在西方思想界掀起了巨澜。
巴伦博依姆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对巴勒斯坦的同情,“通过掠夺另一个民族的基本权力来成就我们的独立,这样的逻辑讲得通吗?犹太人的历史上有这么多苦难,受过那么多迫害,怎么能对邻国的痛苦无动于衷?”他还主张犹太人打破二战以来的禁忌演奏瓦格纳的音乐(希特勒最喜爱的音乐),并身体力行,在特拉维夫音乐节上亲自指挥瓦格纳的歌剧,引得耶路撒冷市的市长痛骂他“厚颜无耻、傲慢自大”。本来巴伦博依姆还准备指挥瓦格纳的《女武神》第一幕,但是遭到大屠杀幸存者们的强烈抵制,以至于艺术节的官员不得不请求他更换演出曲目。最终巴伦博依姆用舒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换掉了瓦格纳,但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不过演出结束后的安可曲,他向观众表示仍旧要加演瓦格纳的作品,并请不想听的人提前离开。大部分观众对此举报以热烈的掌声,但少数人依然不能认同。巴伦博依姆用希伯莱文做了半个钟头的演讲,要求抗议者能够放下成见。“如果我们能用瓦格纳的音乐做手机铃声,为什么就不能在音乐厅演奏呢?”
他的行动引起了萨义德的注意,之后萨义德邀请巴伦博依姆去哥伦比亚大学的米勒剧院主持周末座谈会,讲解瓦格纳。两人一见如故。
二
1999年,巴伦博依姆与萨义德力排众议成立了一个管弦乐团,该团由数目相当的阿拉伯及以色列青年音乐家组成、并且是世界上唯一聚集了以色列人、叙利亚人、约旦人、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埃及人的团体——这就是“西东诗集管弦乐团”( 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西东诗集》为歌德生前的同名巨著)。他们希望向世人证明:通过音乐,在战火中的敌人也可以和平地共存。萨义德逝世前一个月时对记者说:“这是我一生所做过最重要的事之一。”
然而,许多人生活在战火中,却在音乐厅里看到自己的孩子和敌人的孩子一起演奏音乐,感情上难以接受。巴伦博依姆遇到过各式各样的父母,有些非常赞成,有些持怀疑态度,而有些根本就拒绝去听音乐会。“我尤其尊重那些阿拉伯国家来的孩子,他们背负了许多来自国家、社会的苛评,”巴伦博依姆说。
也有人激烈地认为这是一种哗众取宠的游戏。生于以色列、后来成为巴勒斯坦国立音乐学院阿拉伯音乐理论系系主任的Khaled Jubran对媒体说:“有些人说音乐无国界,简直一派胡言。音乐是我见过的最依赖于本土文化的艺术,贝多芬的音乐就是德国的,德彪西代表法国,威尔第代表意大利。音乐绝不会让不同的心灵更贴近,更不要说两派互相憎恨的心灵。”在他眼中,这样的乐团无非是利用异国情调来吸引观众,全无真正的价值。
对于此类指责,我们可以在《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中找到有力的回应。巴伦博依姆一直力图证明,你不一定非要变成一个德国人才能演奏德国音乐,以色列或者阿拉伯孩子也可以拉小提琴、中提琴。萨义德回忆在西东诗集乐团的排练中,一个阿拉伯孩子兴致勃勃地教马友友如何在大提琴上拉一段阿拉伯风格音阶,之前这孩子可一直认为阿拉伯音乐只有阿拉伯人才能演奏。
乐团成立之初,巴伦博依姆选择了两位首席小提琴,一个以色列人,一个黎巴嫩人。起先两人之间气氛非常紧张,可是经过柏林爱乐、芝加哥交响乐团成员的调解,加上马友友的大师班以及巴伦博依姆和萨义德的夜间文化对谈,年轻人慢慢开始了解自己的历史,以及“敌人”的历史。
巴伦博依姆曾经说过:“我的信仰,也是萨义德的信仰——只有当某一天人们可以无阻碍地在世界任何角落演奏音乐,这项事业才算完全实现。现在,我们不能去叙利亚,不能去以色列。当你看到这个乐团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在这些伟大的音乐作品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埃及人、以色列人、来自利物浦还是非洲的廷巴克图。”
2004年巴伦博依姆在拉马拉开设了为四到五岁的巴勒斯坦难民儿童准备的音乐幼儿园,费用由巴伦博依姆-萨义德慈善基金会支付。现在他希望能在加沙地区开另一个幼儿园。“在柏林,一个小时的小提琴课为的是让人们对音乐产生兴趣;在巴勒斯坦,一个小时的音乐课是让人们暂离暴力和斗争。音乐的意义在这里是那么的不同。”
《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读后感(五):将音乐带向文化阐释的乏力感
萨义德与巴伦博依姆(一个主要面对文字,一个主要面对声音),在他们的交谈中,常常会传递给我一种感受——当文字与声音相遇时,其表现力总是败下阵来。文字总是有太多的意图,与音乐相比,缺乏最直接的神秘感。这种落差感,甚至在同样地使用语言而以不同方式(文化/文学性的,与音乐结构性的)来诠释音乐时,都会有所体现。这种落差,不是谁更正确和谁的表达更有魅力的问题;而是两种方式的直接碰撞。
例如对于贝多芬,巴伦博依姆从纯粹的和声学角度来探讨他的第四交响曲。“引子是对主调音乐的探索。一开始是一个降B音,也可以是升A音,可能是任何一个音。然后弦乐加进来,因为是同音,让你对调性一片茫然。在引子的最后,你基本上有了乐曲开始时的降B调属和弦,唯独不知道是大调还是小调。主要速度是快板,整个显示部有两个主题,都证明确是降B调。这样的搭建有怎样的目的?换言之,降B成为这部作品的本调。然后通过一个非常精巧的等音变化,亦即当降B音和升A音成为同一个音时,在发展部的结尾,我们突然到了异乡。为什么说是异乡?因为本调已经被搭建起来了。这就是被我们称为主调音乐的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本调的概念,然后去一个未知的领域,然后再回来。这是一个需要勇气和无法逃避的过程。这是对主题的重申,你称之为对自我的确认,对已知领域的舒适感——为的是能够去往完全未知的地方,并具有迷失方向的勇气,然后又意想不到地再次发现这个熟悉的领域,让我们重返家园。这就是(贝多芬的)音乐。”显然,巴伦博伊姆将(音乐)结构看做一种情感的表达形式,而将情感看做一种结构。
同样是“第四”,萨义德无疑在听巴伦博依姆的演奏时看到各种情景。关于家、发现、回归的神话:“奥德赛”。“他离开家是为了发现能够吸引他的东西,当然也有威胁他的东西。这是关键。为了最终返家而经历冒险。一切回到起点的时候并不是稳定的回归。在这种回归中,你能感觉到一些新的东西将要产生。这是一种很有震撼力的经历。……而‘伊利亚特’里另外一种经历,就是漂泊和无家可归。换言之,希腊人远远地离开家,很多人都像阿喀琉斯一样,最后死去了:他们回不了家。这里没有回家,但却有一种深刻的无结果的结果。荷马着意描述一种纯粹的死亡力量。存在着一种无意义,最终只有战斗本身。音乐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在第二维也纳乐派的音乐中,调性的缺失正是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一种永远的放逐,因为你不会再回来。这种预示存在于人类的经验之中。一种流亡音乐,不只离开人类社会,而且也离开了调性世界。如果他们所承袭的调性世界意味着被广泛接受的世界,那个拥有着习俗、习惯,以及某种确定东西的世界的话。而在这个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中,能够看到一种力图恢复并且无法实现这种愿望的意识,比如普鲁斯特、乔伊斯、艾略特,还有其他人。”
巴伦博依姆的忠告又是怎样的?“运用这些联想、还有这些术语应该有个极限。这些词,比如救赎、光荣、革命,无论什么,如果想用音乐来描绘这些想法都会有一定危险。对于绝对音乐所要表达的真实意义需要在声音世界和声音的关系上寻找。而听者则需要将其与自己所处的情况相适应,无论他处于良好的状况中,还是无家可归的状态,或者是在斗争之中。”例如,对歌剧,瓦格纳的歌剧。巴伦博伊姆并不忽视文本,但更着意寻找音乐本身的真实,“尽管瓦格纳是先写歌词,然后才有音乐,但他是在寻找一种将两者结合的艺术形式。他使声音与语言完美且明显地结合在一起,而其中的表现力并不在于它表现了非常强烈的感情,比如爱情、死亡,或者其他什么,而是拟声法,语言音节的读音配合着音乐的声音已经是乐曲表现力的一部分了。如果先去研究文本,然后再看音乐是否与之相符,当然肯定是会相符的,因为必定是要相符的,但这样,就无法获得将两者分裂开来研究所能获得的那种音乐表现方面的深度。如果你把音乐融入你对文本的理解之中,你就降低了其表现力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运用意象,尽管有时运用意象是非常享受的。卡拉扬说:你需要告诉管弦乐团的只有六样东西:声音太大、太柔、太晚、太早、太快、太慢。当然,这要在将整个曲目完全消化之后才能做得到。”
文字符号的表意常常无意中带有较大的扩张性,而音符本身——对于声音——则是无声、沉默的表达,准确而恐怖。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文学性、意象性的阐释常常更令人享受,它玄妙而诗情画意(即便是讲述最为痛苦的事情);而音符及其构成的声音时空,却因其精准的存在方式而不那么容易亲近——然而,它的表现力也许更为深刻(而不是泛滥的),令人敬畏。同样作为文本形式,乐谱几乎不会像文字那样容易失控。
巴伦博依姆的阐释,仿佛能够在我眼前架构起一个音符的时间与空间,形成一种强烈的召唤,让我相信,人能够彻底地沉浸在声音的世界(黑洞)里,而无关其他,甚至文化意义上的思想、情感,等等。那是音乐真正的、纯粹的“自律性”。就像巴伦博伊姆对待当代作曲家(如第二维也纳乐派,卡特、布莱兹、伯特威斯尔——普遍被认为难以理解,不适合聆听)的方式是内在于音乐的,通过反复演奏而熟悉并充分理解,仿佛它们是一百年前的作品。而相反,对于贝多芬——他不是过去的音乐家,也不是当代的,而是现代的作曲家,则带着发现的眼光去演奏,仿佛那些乐曲是今天写的。
最终,萨义德与我的感受是相同的吧——“音乐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音乐在很深的层次上,也许是对文化移入和商品化的最后抵抗。”
当然,享受音乐与了解音乐,常常又是两回事。对照萨义德的《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来读,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这一问题。而且,首先要明确的是,萨义德深入讨论的是一种“风格”。
在敲出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脑子中一直响着各种旋律——当然,他们比我的表达远远美妙、纯净得多。
闺密要结婚了,帮她选了《费加罗的婚礼·苏珊娜的咏叹调》作为婚礼上的背景音乐。那明亮盈转的高音,此刻正在脑中回荡……
http://www.weamea.com/search/searchBySingleMusic.action?words=mozart%2C+wolfgang+amadeus+-+no.11+canzona_+voi+che+sapete+che+cosa+e+am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