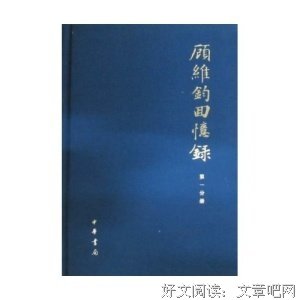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是一本由顾维钧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45元,页数:44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精选点评:
●研究民国时期的外交关系必备
●不是人造就时代,而是时代造就人。
●卓然于世
●读民国史真的又精彩又充满人生哲学。特别是外交史,真的不比战国诸子百家来的逊色呀。Ps:最后一任老婆好像活了115岁还是118岁………
●膜拜
●1/13。在哥大读到国际法博士,参加辩论社编辑部,暑假加强德语,然后六周学会美国学生四年的拉丁语……然后回国……巴黎和会……废除与比利时不平等条约案是唯一一个中国与常设国际法院发生接触的案子……嗯,当成中国国际法史来看也不错。
●昨天在图书馆学不进去,路过一排蓝色的书,孤零零地一排分外显眼,忍不住翻了几页,等手头的事情做完,想把全册都看完/才看完一册
●对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又有了一次洗刷般的认知。虽然是回忆录,还是能看出大的政治家必然有深不见底的腹黑……
●很多史料,只读了第一册,后面都是晦涩的史料,读着需要勇气和耐心。内容就是顾维钧的外交家生涯,顺带科普了三次感情,还特意去上海的顾维钧陈列室膜了。总之,可读,这样的人生挺好的,该遇到的都遇到了,没有遗憾的一生。
●让我对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有了一次洗刷般的认知。也让我对旧式官场的生活,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和政治态度终于有了一些理解。顾维钧与当时国内外政治舞台上的众多关键人物接触之多,私交之深,让我感到惊讶。若你想了解民国时期的政治历史外交以及一位民国精英、哥大学霸的成长史,相信这本书不会让你失望。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读后感(一):一人难扭转大环境
1888-1932,包括童年、留学、任职北洋政府、巴黎和会、退隐之后再次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这段经历。可能是口述的原因,可读性差了点,比较细碎。影响最深的不是巴黎和会部分,反正弱国无外交嘛,就是各种被强国耍着玩的节奏;而是北洋政府期间,虽然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总统、内阁、国会每天忙忙碌碌,貌似为国为民的殚精竭虑,却不知他们只不过是在军阀的铜雀台里面玩过家家的游戏而已,因为他们的行政命令其实大都出不了铜雀台,而且,总统内阁更换的速度也是大家轮流坐坐过过瘾的感觉。关于少帅张学良,在顾看来有点优柔寡断,且不谙世事之感,一个字概括“嫩”。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读后感(二):福寿双全 流芳百世
好几年了,懒症发作,读完书,脑子思绪万千,就是不肯落于笔下。但最近读了《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这是多年来读到的最好的回忆录,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
顾维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学生时代是哥伦比亚大学学霸,博士神速读完,就直入总统府、外交部为官,年纪轻轻就当上驻美公使、外交总长,乃至代总理、署理总理,并执掌摄政内阁摄行大总统职务。虽然被后起的两个新政权通缉,但后来又获两者的平反或肯定。顾氏政坛不倒、形象不坠,最大的光环就在于巴黎和会慷慨陈词,不卑不亢,有为有节,成为爱国外交家的典范,让不同阵营的政治人物在争夺爱国道德高地时必须推崇他、景仰他。20年代北洋各派内阁纷纷倚为外交总长、总理,到90年代电影《我的1919》,都能说明这一点。顾氏关注外交、不卷入国内政争;为人谦和,处理复杂关系游刃有余,凡此种种,顾氏不仅福寿双全,而且流芳百世,堪称完人。
北洋时期,顾维钧不仅做过政府首脑,还担任过摄政内阁总理,虽然还不算国家元首,但毕竟代行过国家元首职权,职位达到了顶峰。可惜的是与其13册回忆录篇幅比起来,第一分册含三卷442页篇幅过短。恐怕与其作回忆录时手头缺乏第一手资料、只能凭记忆、参考台面上的史料回忆有关(据第二分册记载,1936年顾开始记日记,其后史料更加详尽而准确)。即使这样,这段回忆录仍留下了对北洋要角的精彩回忆,一些文字反复被各种人物传记引用。如对曹锟的评价,虽然能力平庸,但知人善任,自知之明,是一位信任、尊重责任内阁、专业部长的称职元首。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读后感(三):李某人的一则故事
1923年-1924年中苏谈判,旨在恢复中苏间的外交关系。苏方代表为加拉罕,中方则为王正廷,该人是一个很有政治野心的政治家,外交经验丰富,曾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五代表之一,但其为人颇有问题,惯使手腕,做过些不光明的事情。其本身本来与南方政府有关联,但后来逐步靠拢北洋政府,并希图更高的政治权力,后来他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但也龃龉甚多。
谈判中,王正廷不按照一般程序,先向当时外交总长顾维钧汇报,以便其提交内阁审议,便在协议草案上签字,严重失职。顾维钧要求看协议草案内容,结果令其“大失所望,极不满意”,他把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归为三条:
“第一条是有关涉及外蒙的一些问题。协议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以及同其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但苏俄同所谓的“独立外蒙”签署的条约和协议却没有提到。既然特别指明是沙皇政府所签定的条约,这就是默认了苏俄与外蒙的条约。我认为,中国政府绝对不能轻易作出这一重要的让步。
“第二条是苏俄从外蒙撤军问题。苏俄正是依靠这些军队来维持他们所谓的外蒙“独立”的。虽然双方代表对撤军问题曾进行了讨论,但协议草案中的有关条款却规定,一旦中国同意撤军是有条件的,从而使自己处于完全听任苏俄摆布的境地,而苏俄则可以认为中国提出的条件根本无法接受而长期屯兵外蒙。此外,这一特殊条款的含意也今人十分不快,似乎苏俄在那里驻军是合法的,而且有权在撤军之前提出种种条件。
“第三条是关于在中国的俄国东正教会的房地产权问题。协议草案的第三条声称东正教会的所有地产都必须移交苏俄政府。但据我所知,以往的条约并未在法律上准许外国使团、宗教团体以及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占有土地。而且中国政府从无任何记载表明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拥有多少财产,它们的土地在哪里,有多少,因此中国履行这一义务是极为困难的,而且会遭到地方当局的强烈反对。”(P334-335)
当然,后来内阁否决了这一协议,并请苏方代表再次仔细看王正廷的全权证书,明确规定了他所达成的任何谈判结果,必须呈报政府,并应经政府批准。
顾维钧写到:
quot;虽然王博士签署的协议草案没有得到孙中山博士和南方政府的明确支持,但在各省的高级将领中的确得到了支持。除此之外,苏俄使团的宣传机构在王博士的政治盟友们的协作下,也开始产生一定的宣传影响。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是那个由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士与加拉罕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因此我便对他说,他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由于考虑到李大钊教授的意见与我的见解完全相反,我便告诉他,鉴于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没有必要就此问题与他讨论。于是我说了句“请原谅”,便起身告退了。这些所谓的大学和学生界的代表们有可能受了苏俄使团以及王博士手下人的劝说和鼓动。
……我曾收到一份由北京政府所管辖的各个省份的高级将领和督军们拍来的电报,其中包括吴佩孚将军。当时,人们认为他是北方的领袖,至少是军界的领袖。此外,他还是曹锟政权的主要支持者。这份通电是由齐燮元和长江下游、四川、河南以及山东等省的督军签署的。电报显然是在吴佩孚将军的怂恿下发来的,但其幕后操纵者却是王正廷博士本人。电报中所讲的与以李大钊为首的代表们所提出的非常类似,亦即认为协议草案是表明中国能使人承认它是与一个外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国家的第一个协议。电报还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即既然这是中国所签订的最好的协议,我有何把握能把它修改得更好?"(P339-341)
这后来,顾维钧还受到了炸弹威胁,所幸无恙,但警察最终没要找到幕后指使者,释放了寄来炸弹的两名学生。顾维钧写到,“我相信,正像那两名学生自己讲的那样,他们是受人之命订购炸弹的,而不是自己的意图。当然,当时确实有些GCD特工人员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活动。”(P345-346)
再后来,由于顾维钧的坚持,加拉罕不得不妥协,经再三谈判,最终修改了关键的三点,签订了协议,即《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并互换照会。这时,中苏之间的正常关系建立起来了。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读后感(四):顾维钧的1919
数年前的那部《我的1919》,无疑算是一部好电影。陈道明的演技尤其让人陶醉,可圈可点之处不少。但是当我翻过这本《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卷之后,我发现了一个事实——艺术是艺术,历史是历史,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
在看过影片之后,过顾维钧的这本回忆录就立刻引起我的注意。我想我完全有理由把影片剧本的取材乃至于创意和这本公布不久的文献联系起来。所以想当然在思维将顾氏的大名带入电影主题的那个代词主语的位置。以至于认为并没有面对史料本身的兴趣。数年之后,偶然翻开回忆录。发现实际上远非如此。看过第一卷中的相关内容,很快就会发现——《我的1919》并不等于“顾维钧”的那个1919。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无非是在告诉我们历史基于个体内在的事实。而不是历史虚无的一种托辞。太多的喑呜叱咤在1919这个大舞台展开。以至于一个真正的作家面对这个题材的时候一定会兴奋的欣喜若狂,继而充满迷茫和疑惑。太多的来龙去脉需要疏理展现。
回忆录文体的冗繁琐碎在所难免。何况《顾维钧回忆录》是其晚年口述而成。但“巴黎和会”这一部分的内容,浑然天成,毫无滞碍。几乎处处惊险,喜忧交替。要之,从使团内部人事斗争开始,到列国的倾轧,舆论的大哗,怎一个乱字了得。在一片乱象之中,实相庶及得之——
一个远离主战场的东方古国为什么卷入这场战争?为了向德国宣战,段祺瑞政府饱受四方攻击。通过参战收回山东利益是最大的目的。在胡里胡涂地“战胜”之后,似乎也没有谁想到赞扬一下段氏的“高瞻远嘱”。而如今的国人也很少会想起为了一战战胜国的荣誉,数万中国民工在欧洲战场上付出了全部的苦力和鲜血的代价。我们的电影也不例外。但这些代价在整个战局中的贡献却实在有限的很。论功行赏,自然难为上首。从这个角度说,巴黎和会的结果并不出意外。但是从政府、知识阶层到普通民众都抱着“一洗国耻”的幻想。难逃幼稚之讥。
当然,说时人“幼稚”无疑是把问题看的过份简单了。这显然不是单纯的智商问题,而是时势使然。一个群雄割据,势力纷杂的国土,民众、舆论也是各怀其心。到这里,方才明白近代日本之兴,华夏之衰。其实其中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大道理。一言以蔽之,“尊王攘夷”也。“王”不必是君王;“夷”未必为西人。用现代的话语道来,无非“内部整合,开拓竞争”而已。至于“民主”、“自由”、“宪政”等等大道理,的确也十分重要。但在中西大变的紧急形势下,如何谋图自存乃是第一要义。
1919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大时刻。对于这个时刻最激烈的时间点,中国在巴黎和会断然拒绝签字的图像。并不存在。《我的1919》影片的最后,由陈道明饰演的顾维钧站在签约会场上有这样一个场景——
和约正式签字开始。
轮到中国签字,各国代表的目光纷纷注视着顾维钧和王正廷。
顾维钧慢慢地拿起了和约文件,凝视着……
一些代表已经意识到将有事情要发生了……
顾维钧将文件倒扣在桌上。他环顾会场,肃穆庄严。
顾维钧(缓缓地):“(英语)尊敬的主席先生,副主席先生,秘书长以及所有的代表们,我很抱歉,中国不能在和约上签字。因为,这不是和平的条约!”
克列孟梭、劳合.乔治面面相觑。
威尔逊满脸羞愧。
牧野等日本代表张惶失措。
顾维钧:“(英语)它充满了欺诈、罪恶,它是强盗的条约。它出卖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出卖了一切公正与和平。中国人民对此深感失望和愤怒,我代表我的人民要对你们说,中国决不会签字!”
全场默然。
一些同情中国的人士朝中国代表团竖起大拇指,无声地表示支持和赞扬。
顾维钧和王正廷在与会代表们的目视下,昂然朝镜厅外走去……
(电影剧本全文 )
何等的慷慨激越,大义凛然。可惜这只是影片编剧的“神来之笔”——
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椅子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卷,209页)
http://blog.donews.com/klaas/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读后感(五):李某人的一则故事
1923年-1924年中苏谈判,旨在恢复中苏间的外交关系。苏方代表为加拉罕,中方则为王正廷,该人是一个很有政治野心的政治家,外交经验丰富,曾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五代表之一,但其为人颇有问题,惯使手腕,做过些不光明的事情。其本身本来与南方政府有关联,但后来逐步靠拢北洋政府,并希图更高的政治权力,后来他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但也龃龉甚多。
谈判中,王正廷不按照一般程序,先向当时外交总长顾维钧汇报,以便其提交内阁审议,便在协议草案上签字,严重失职。顾维钧要求看协议草案内容,结果令其“大失所望,极不满意”,他把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归为三条:
“第一条是有关涉及外蒙的一些问题。协议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以及同其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但苏俄同所谓的“独立外蒙”签署的条约和协议却没有提到。既然特别指明是沙皇政府所签定的条约,这就是默认了苏俄与外蒙的条约。我认为,中国政府绝对不能轻易作出这一重要的让步。
“第二条是苏俄从外蒙撤军问题。苏俄正是依靠这些军队来维持他们所谓的外蒙“独立”的。虽然双方代表对撤军问题曾进行了讨论,但协议草案中的有关条款却规定,一旦中国同意撤军是有条件的,从而使自己处于完全听任苏俄摆布的境地,而苏俄则可以认为中国提出的条件根本无法接受而长期屯兵外蒙。此外,这一特殊条款的含意也今人十分不快,似乎苏俄在那里驻军是合法的,而且有权在撤军之前提出种种条件。
“第三条是关于在中国的俄国东正教会的房地产权问题。协议草案的第三条声称东正教会的所有地产都必须移交苏俄政府。但据我所知,以往的条约并未在法律上准许外国使团、宗教团体以及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占有土地。而且中国政府从无任何记载表明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拥有多少财产,它们的土地在哪里,有多少,因此中国履行这一义务是极为困难的,而且会遭到地方当局的强烈反对。”(P334-335)
当然,后来内阁否决了这一协议,并请苏方代表再次仔细看王正廷的全权证书,明确规定了他所达成的任何谈判结果,必须呈报政府,并应经政府批准。
顾维钧写到:
quot;虽然王博士签署的协议草案没有得到孙中山博士和南方政府的明确支持,但在各省的高级将领中的确得到了支持。除此之外,苏俄使团的宣传机构在王博士的政治盟友们的协作下,也开始产生一定的宣传影响。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是那个由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士与加拉罕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因此我便对他说,他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由于考虑到李大钊教授的意见与我的见解完全相反,我便告诉他,鉴于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没有必要就此问题与他讨论。于是我说了句“请原谅”,便起身告退了。这些所谓的大学和学生界的代表们有可能受了苏俄使团以及王博士手下人的劝说和鼓动。
……我曾收到一份由北京政府所管辖的各个省份的高级将领和督军们拍来的电报,其中包括吴佩孚将军。当时,人们认为他是北方的领袖,至少是军界的领袖。此外,他还是曹锟政权的主要支持者。这份通电是由齐燮元和长江下游、四川、河南以及山东等省的督军签署的。电报显然是在吴佩孚将军的怂恿下发来的,但其幕后操纵者却是王正廷博士本人。电报中所讲的与以李大钊为首的代表们所提出的非常类似,亦即认为协议草案是表明中国能使人承认它是与一个外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国家的第一个协议。电报还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即既然这是中国所签订的最好的协议,我有何把握能把它修改得更好?"(P339-341)
这后来,顾维钧还受到了炸弹威胁,所幸无恙,但警察最终没要找到幕后指使者,释放了寄来炸弹的两名学生。顾维钧写到,“我相信,正像那两名学生自己讲的那样,他们是受人之命订购炸弹的,而不是自己的意图。当然,当时确实有些GCD特工人员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活动。”(P345-346)
再后来,由于顾维钧的坚持,加拉罕不得不妥协,经再三谈判,最终修改了关键的三点,签订了协议,即《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并互换照会。这时,中苏之间的正常关系建立起来了。